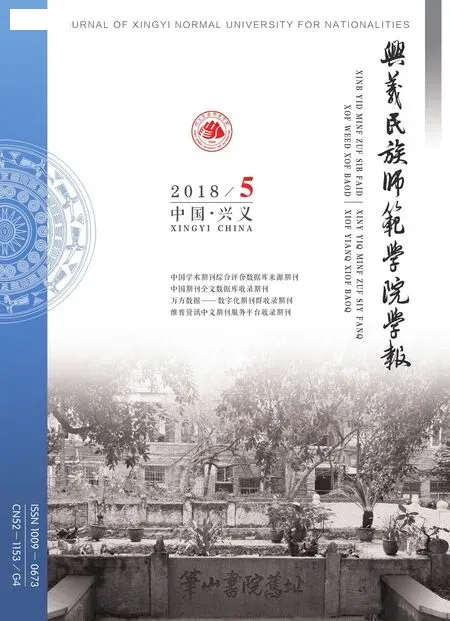从叙事学视角解读自传体小说《抵达之谜》
2018-02-26王诗颖
王诗颖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贵州 兴义 562400)
一、引言
《抵达之谜》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维·苏·奈保尔所创作的一部全面反映其人生的自传体小说。与拉什迪、石黑一雄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的印度裔作家奈保尔有着极其复杂的文化背景,长期的旅行经历使其作品风格独树一帜。因此,其身份其作品在文学界备受关注。奈保尔的小说不仅主题思想深刻,而且叙事形式多样,笔下的文字令人着迷。《抵达之谜》一书详尽地记载了他在“古老的英格兰心脏”十年旅居生活的感知,同时也传递了作者对文化自觉的认识。本论文剖析了小说中独特的创作技巧,以叙事学的视角阐释作品中身份、情感抵达从困惑到顿悟的内涵。
二、叙事学理论下的文本解读
米歇尔·布托曾经指出:“小说是绝妙的现象学的领地,是研究显示以什么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或者可能以什么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绝妙场所,所以小说是叙述的试验室。”[1]叙事视角、叙事方式及叙述人的选择决定着小说整体结构的变化。叙述人、小说中人物和读者之间保持着一种道德的、情感上的审美距离,小说尽力使话语对象自身的内在张力得到充分展现。
所有的叙事作品都有一个叙述者,他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这个行为通过对一定叙述话语的操作与铺展最终创造了一个叙事文本。读者便是依赖于这位叙述者的叙述而了解一个故事,感受到一些世态炎凉。我们接收一个故事是从他的兴致勃勃的回忆开始,以他的缄默告终。故叙述者乃是读者在同叙事作品的文本相照面时最先接触到的。而叙述者的叙述视角在文本解读中显得尤为重要。叙述视角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自西方现代小说理论诞生以来,叙述研究界对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颇感兴趣。学者们发现,视角是传递主题意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无论是在文字叙事还是在电影叙事或其他媒介的叙事中,同一个故事,若叙述时观察角度不同,会产生大相径庭的效果。[2]《抵达之谜》总共包含五个部分,分别以“杰克的花园”、“旅程”、“长春藤”、“乌鸦”和“告别仪式”为题,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回忆记录了“我”于1950年从加勒比岛到英国后努力学习成为著名作家的个人历史。这种叙述视角模式为“外视角”,即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外。如在“旅程”里,我们读到这么一段话:
And indeed there had been a journey long before,the journey that had seeded all the others,and had indirectly fed that fantasy of the classical world.There had been a journey;and a ship.The journey began some days before my eighteenth birthday.It was the journey which——for a year—I feared I would never be allowed to make.It was the journey that took me from my island, Trinidad, off the northern coast of Venezuela,to England.[3]113
在这段叙述中,读者可以清楚地感知到作为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从自己目前的角度来观察往事,也称之为回顾性视角。由于现在的“我”处于往事之外,因此这也是一种外视角。年老的“我”作为叙述者在话语层运作,年轻的“我”则作为人物在故事层运作。第一部分“杰克的花园”的背景是70年代,主人公此时已经离开伦敦住在威尔特郡山谷的农舍里。关于为何从特立尼达来到伦敦和离开伦敦的叙述,被延后至第二部分“旅程”。《抵达之谜》中叙述者“我”讲述了其生长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特立尼达岛,十八岁时荣获英国留学奖学金后便离开了特立尼达岛,先乘飞机从西班牙港到波多黎各,再乘船从纽约到南安普顿,抵达梦寐以求的英国。毋庸置疑,这段历程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此时的“我”是年约半百的作家,寄居在威特郡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乡村花园的小木屋里,思考着过往人生以及走向死亡的生命无常。奈保尔以及他的叙述者的身份几乎是完全吻合,即我与叙述者的功能重合,他就是我的眼。文本的时间不断地穿梭在现在与过去中。这一切并没有依照事件先后顺序呈现,而是根据主人公的思绪与回忆重现,整个叙事呈现出明显的“错时叙事”(anachrony)。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叙述者为了追忆往昔刻意打乱了叙事时间。此外,使作品在形式方面独具特色的是庞杂且富有想象力的空间描述:从特立尼达到伦敦,从伦敦到威尔特郡,关于地理空间和人物视觉体验的描述话语一直伴随着人物搬家和旅行。[4]
德国文艺学家G.E.莱辛曾经提出:文学作品因其语言属性决定了它存在于时间中。[5]在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小说中,时序的颠倒错乱是惯有现象,也是独特叙述艺术的体现形式。小说的第一章“杰克的花园”所发生的时间是叙述者已经在英国定居生活了大约二十年,为了更好地创作环境和调养身体而搬到索尔兹伯里的乡间峡谷,也是在此遇见了杰克;而后第二章“旅程”的时间倒叙至叙述者离开加勒比海区的特立尼达,初来英国乍到时旅途中所见所闻所感;后面三章节所发生故事的时间再次拉回到现在。从宏观上看,小说整个叙事结构呈现为非线型。换言之,叙事作品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时间开端,小说总是从故事的中间开始叙述,小说中的五章内容中的时序安排正阐释了这点。
三、抵达的困惑及顿悟
《抵达之谜》的叙述者“我”的家乡特立尼达在1498年被欧洲人哥伦比亚发现,之后便一度沦为了西班牙、法国的殖民地。在1595年,英国占领了特立尼达。由此可见,长达四百多年的侵占史导致特立尼达的文化充斥着殖民文化。而在这种被殖民的文化背景下,“我”接受了英国教育和英国社会文化,甚至向往移居英国都市。毋庸置疑,英国宗主国文化已然在年轻的“我”心目中确立了优越的地位,叙述者也在不断认同英国文化。与此同时,“我”对本国文化却极度排斥。在《抵达之谜》中,“这个地方的美,使我内心中产生了对它强烈的爱,强烈得超过我熟悉的任何其他地方”。[6]不难理解,“我”对风景怡人的山川峡谷之热爱溢于言表。然而,定居英国长达二十年,“我”无法忘记特立尼达的衰败,发誓要离开那里:
To see the possibility,the certainty,of ruin,even at the moment of creation:it was my temperament.Those nerves had been given me as a child in Trinidad partly by our family circumstances:the half-ruined or broken-down house we lived in,our many moves,our general uncertainty.Possibly too,this mode of feeling went deeper,and was an ancestral inheritance,something that came with the history that had made me:not only India,with its ideas of a world outside men’s control,but also the colonial plantations or estates of Trinidad,to which my impoverished Indian ancestors had been transported in the last century---estates of which this Wiltshire estate,where I now lived,had been the apotheosis.[3]55
通过描述故乡特立尼达以及印度的历史衰败,叙述者的这种不确定性和文化不自信反映了其是否要认可过去身份的迷茫和困惑。
叙述者一直渴望获得英国文化身份认同,满心渴望成为作家。然而,尽管“我”接受英式教育,“我”的身份却与黑人没有区别。在英国伦敦,“我”陷入困境,在这里有一种作为陌生人的紧张感,无法融入,找不到归属感和认同感。叙述者初来英国对其文化身份是从属又背离的状态。在小说的整个叙述过程中,提及了由于叙述者想出版一本关于故乡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的书,然而他未能找到写作素材,因此不得不前往他所最为熟知而不愿承认的出生地寻找素材。在宗主国之于文明和殖民地之于落后的二元对立当中,“我”在反省和审视被自己遗忘的特立尼达和印度身份。通过文中的作家与人,我们知道叙述者最终趋于认同他的殖民身份,而作为一个旅居英国多年的移民作家,他又兼具英国身份,由此得出奈保尔具有杂糅的身份。奈保尔的身份认同是极其复杂的比较模式,属于一种混合身份又是异体的合成身份认同。
《抵达之谜》这一书名源于叙述者在庄园发现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基利珂(Giorgio de Chirico)的作品。凝视这幅名为《抵达之谜》的超现实的画作后,叙述者发挥其想象力,给读者讲诉了一个历史故事:
My story was to be set in classical times,in the Mediterranean.My narrator would write plainly...He would move from that silence and desolation,that blankness,to a gateway or door.He would enter there and be swallowed by the life and noise of a crowded city.Gradually there would come to him a feeling that he was getting nowhere;he would lose his sense of mission;he would begin to know only that he was lost.His feelings of adventure would give way to panic.He would want to escape,to get back to the quayside and his ship...Only one thing is missing now.Above the cut-out walls and buildings there is no mast,no sail.The antique ship has gone.The traveller has lived out his life.[3](106-107)
可以看出,这一情境与作者奈保尔的经历极其相似,抵达了繁华的城市,而后在这座城市中深感迷茫、漂泊无根和难言困惑。最初的新奇之感变为内心对异乡背叛的恐惧,蓦然回首,生命旅程已走向尽头。进一步的阅读会发现《抵达之谜》综合了虚构和非虚构因素,也模糊了传记文学、小说与散文的界限。研究奈保尔的专家提摩西·威尔斯把《抵达之谜》称为“传记式小说或小说式传记”。[7]奈保尔以自己的方式解释《抵达之谜》中事实与创造的融合。他的感觉就是我的感觉,我不想去杜撰一个人物,让他在这乡村有一个假的冒险。从自传体小说的角度来看,我没有杜撰一个人物去乡村体验生活,也印证了小说叙述者寻求身份认同实际上是奈保尔自身在寻求身份认同。从广义上说,身份认同主要指一个文化主体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做出选择,主体需要将其中一种文化视为文化自我,而将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身份认同的嬗变,文化主体不再拥有恒定不变的身份认同感,身份认同总是处于一个变动的过程中。通过不间断地探寻自我身份,奈保尔发现,对于英国社会文化身份,从始至终有一种既从属又陌生的感觉;而对印度和特立尼达的殖民文化,经历了茫然、反感到顿悟、认同的过程。
四、结语
综上所述,“抵达之谜”犹如其名,作者的身份和内心情感的抵达对于读者来说一直扑朔迷离。此外,小说结构分为五大部分(Part)的编排也可谓独出心裁,突出作者内心情感的支离破碎。小说中叙事的视角也传递了作者是否抵达的主题。奈保尔将绘画艺术转化为以作者自身经历为基础的文学想象使小说具有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作品的叙事结构及人物、事件的互见也使得小说传递艺术之美。首先,《抵达之谜》打破了传记、随笔与小说的界限,呈现出后现代派小说杂糅的特点。传记因素能真实传达离散者的生活体验,而虚构的特征使得人物和背景的象征意义得以展现。其次,对同一话题的不断探索修正从形式上体现了来自殖民地的作家不断地认识、不断地改变认识的过程。再次,通过历时追忆、回到母国种种体验,奈保尔深刻审视了特立尼达人们真实生活的各种现状以及对自身身份的界定。通过解读小说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和叙述方式,作者对其身份问题进行了彻底地回忆叙述,我们可以发现奈保尔以一种内省的方式坦诚记录了主人公从故乡到他乡过程中始终存在的漂泊感。对于移民流散裔作家而言,这种漂泊感既是历史视角下对个人命运与民族历史关系的历史追忆,也代表了奈保尔从个人叙述视角回忆往昔。在叙事学视角的解读下,小说无疑向读者揭示了奈保尔身在此地追忆故乡之情以及对文化自觉的认识从边缘走向中心,继而探讨小说的“抵达”主题。《抵达之谜》也因此“抵达”了英国经典文学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