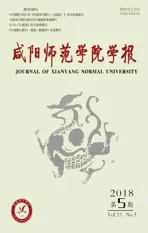评臧知非《秦汉土地赋役制度研究》
2018-02-24王文涛
王文涛
秦汉土地、田税、徭役制度影响深远,是以后历代赋役制度的历史基础,是把握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变动、社会矛盾发生与变化以及王朝兴衰的核心问题。
臧知非先生的近著《秦汉土地赋役制度研究》,重新梳理和解读了土地、税赋、户籍等方面存在较多争议的问题,为秦汉土地赋役制度提供了新的认识。大作得到评审专家的认可,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实乃学界幸事。该书虽为新著,立意却是在三十多年以前。1983年,知非先生攻读史学硕士,即对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土地制度、阶级关系与社会变迁等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奠定了扎实的研究基础。读博期间,又从土地关系入手,系统探讨了春秋战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此后,作者对战国秦汉土地赋役问题的思考从未间断,并时有佳作发表。所以,该书实为作者数十年学术研究的重要结晶,思虑精深,厚积而发。
全书近48万字,分为八章。所论主要问题有:战国授田制的形成基础与历史内涵,秦授田制的历史特点,汉代授田及其私有化的历史过程,秦汉田税征收方式与农民田税负担,算赋制度,更役和更赋,户籍制度中的疑难论见,傅籍制度中的“算民”与“立户”的关系,“自占田”的制度意义及其程序与功能,傅籍与户等变动,以及战国秦汉时代农民身份特点及其变迁的必然性。
该书的总体特点,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云:“以总体把握为前提,问题意识为先导,得出新见为标准,把握规律性为目的。”作者在广泛吸收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囿成说,勇于探索,在诸多方面提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新见。例如,关于井田与授田的关系,作者认为,井田制不是传统理解的土地分配方式,而是土地、军赋、户籍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是战国授田制的历史基础。战国授田,是在“方里而井”的基础上采用“提封田”法计算土地面积,然后授给农民,此时的农民是国家课役农,不是后世理解的小自耕农。国家授田的目的是通过控制土地资源来控制人口,满足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需要。
作者系统考察了授田制度的历史基础和实施演变过程,明确提出和论证了不能用“名田”代指授田。商鞅在秦国推行授田制,确定社会等级、爵秩、身份,授予不同数量的土地住宅以及其他权利,司马迁将其概括为“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1]2230关于秦代“名田”,自古至今论者颇多,学界既有观点可归纳为三种不同解读:军功爵者增加的占田;自我申报所占土地后的合法土地;不是独立的土地制度。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全面系统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人所未思,另辟新说:“名田”是在授田制条件下,国家按照名籍授予编户民土地,“名田宅”是“以名籍授田宅”,“占”是验证、核实。“名田宅”是指名籍在授田制中的功能而言,不宜理解为以名籍占有田宅。“名田宅”的“名”,是“名籍”之省,不能得出“名田”是自我申报田宅的结论。授田以土地国有制为前提,体现的是土地国有制的经济属性,而“以名籍占田”不能体现土地国有制性质。秦朝统一授田制度,在制度层面按照秦国社会等级重新分配土地,是对六国经济结构的大调整。秦朝授田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因为领土的改变、自然条件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多样性和政策的调整,农民实际授田数量、土地空间分布、田亩形制因地而异,呈现出多样性,不能按照每夫百亩的制度设计来理解秦朝授田制度和田亩形制,体现了秦朝统一之后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汉代土地私有制大发展,《二年律令》中有授田制度的明确规定,该问题亦是秦汉史研究的焦点之一。见仁见智,认识不同。有学者认为,秦亡汉兴,刘邦称帝伊始,颁布的“复故爵田宅”诏,是重复以有功劳行田宅、满足高爵的原则,不是为了授田给普通农民。其时土地有限,无法实行普遍授田给农民。《二年律令》所述授田制并非现实实行的制度,而是旧制度的遗存,或是对旧制度的追述,是出于稳定社会秩序、宣传仁政而做出的姿态,其实是一纸具文。作者的研究认为,在汉初不存在人地关系紧张、授田制难以为继的问题,刘邦“复故爵田宅”诏本身包含授田给普通农民的制度内容,“以功劳行田宅”“满足高爵”正是以此为基础。《二年律令》是实际施行的制度,证明汉朝建立伊始继续实行授田制,按照每夫百亩授田;在田亩形制上也延续秦朝的二百四十步亩制,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秦朝授田制内容的认识。汉文帝没有废止授田制,授田制废止是个历史过程。文帝十三年(前167)“除民田之租税”是制度性变革而非临时优抚的举措,这一制度性变革的基础是“农商并重”,进一步深化了税收结构变动问题的研究。
土地和人口是农业社会的核心问题,户籍、田租、赋役制度都是配合土地制度设计和改变的,抓住土地分配这一核心问题才能科学地揭示全部赋税制度。作者清楚地认识到:“土地所有制性质及其分配形式,是社会集团、阶层、等级、阶级的构成基础”,“人身控制是实现赋役的保障,实现赋役是人身控制的目的”。[2]433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揭示秦汉社会矛盾变动的内在逻辑,才能准确把握土地与赋役的关系,同时也能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
梁启超先生说:“凡学问上一种研究对象,往往容得许多方面的观察。而且非从各方面观察,不能得其全相。”[3]2要想在前人反复耕耘的研究领域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作者不仅勇于也善于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创新,全书的文章结构几乎都是这种范式。
运用新材料,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手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了一系列战国、秦汉简牍,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秦汉历史的认知,关于土地、田税、徭役制度的研究成果尤其令人瞩目。但是,由于简牍资料缺乏系统性,对其含义的理解有相当难度,加之研究方法和学术视野的局限,得出的研究结论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作者凭借深厚的学术积累,在研究中充分运用并善于解读简帛和考古资料。例如,作者对算赋之“算”的考察,很有新意。“算”的词性和含义具有多样性:作为动词,指计算活动;作为名词,本指计算用具,后将计算的某一数量单位,或和计算有关的考核的奖惩单位称之为算,还引申为服徭役者的代称。其具体含义要根据语境分析,不能仅凭字面含义理解,更不能把文献和出土简牍中的“算”都解为算赋之省。作者引用居延汉简、张家山汉简、凤凰山汉简、云梦秦简、里耶秦简和西汉天长纪庄木牍中相关的大量资料,论证了“算”是核实之意的观点,因要先“算”而后“赋”,遂有“算赋”之称。作为单独的税种,算赋有一个生成和发展的过程,起源于“算民”而后“赋”之,其早期,“赋”的内容并非人口税,而是包含了所算之民应该承担的各项赋税徭役义务,而后逐步地收钱以代替服役,即徭役货币化,成为单独的人口税税种。再如,对于“市井”的解释。在分析了诸多考古发掘所见战国、秦汉水井群遗址之后,作者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井的作用日益凸显,市与井的关系日益密切,遂有‘市井’之称”。这种建立在考古资料与文献结合基础上的研究,结论新颖,令人信服。
从新的角度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得出新的结论,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例如,关于秦汉田征收方式,学界观点不一。作者从授田制度的以授促垦、以授保税的总原则出发,系统考察了“税田”制在两汉的存续情况,认为“以顷计征、按户征收”的看法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再如,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田家莂》中所记“熟田”“旱田”的性质,学界普遍认同“熟田”是种植水稻之田,“旱田”是种植旱作物之田。但作者并未轻易采信成说,而是通过全面考察东汉田租征收制度、汉末人口流动、《吏民田家莂》姓氏以及东汉宗族关系,做出新的推论:“吴国把出租的公田分为旱田和熟田两类,旱田免收租米,熟田则亩收一斛二斗”,旱田每亩缴纳六寸六分布和三十七文钱。虽然此说并非定论,但足可自圆其说,体现了勤思求新的研究理路。此外,作者对前人的注释并不盲目轻信,敢于大胆置疑,不惟古、只唯实的学风贯穿在全书之中。作者的新见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恕不一一。
我读研时虽然系统学习过秦汉土地赋役制度这门课程,却没有什么研究,本不敢妄议,权借以评论之名,行拜读之实吧。因此,评议虽不全面,亦不乏一得之见。《秦汉土地赋役制度研究》的确是一部创见颇多的佳作,作者的创新求实精神值得肯定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