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琦“重生”:当年惊了崔健的女孩,就没想过要被记住
2018-02-23张文政
张文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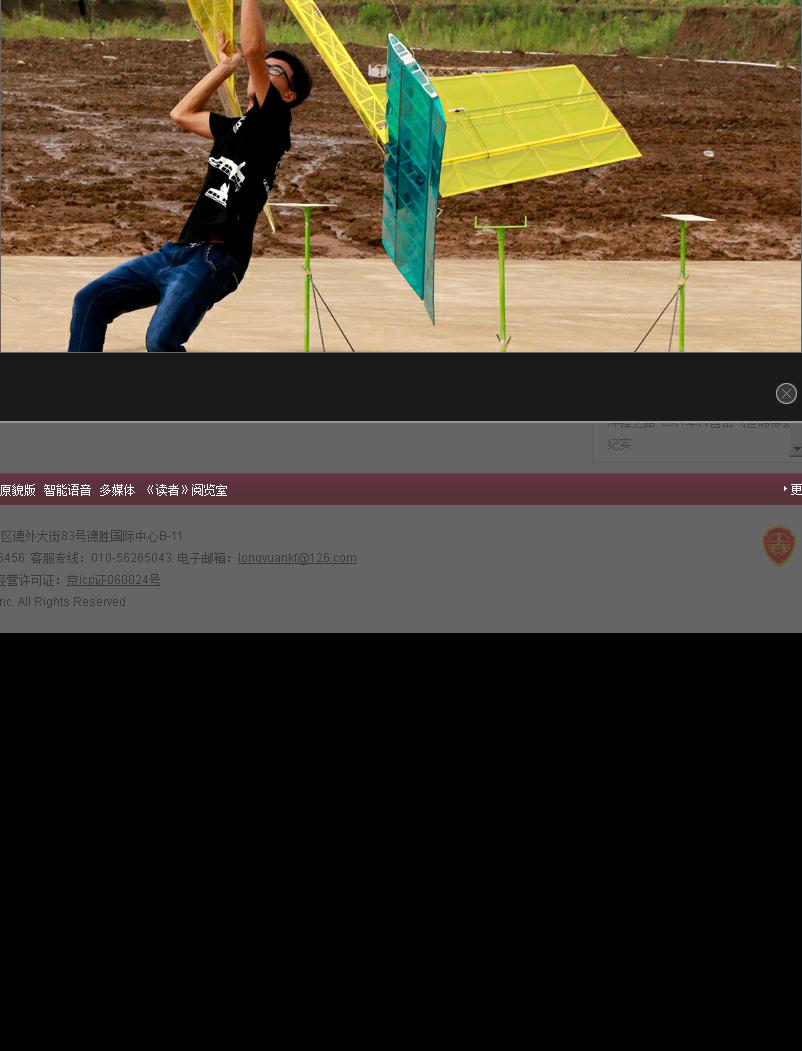
单亲家庭长大的罗琦,正在适应做一个合格的单亲妈妈。
不同质感的黑,在一袭黑色装扮的罗琦身上重叠。
她喜欢黑色。“好像按照专业的美学来说,黑色就是没有颜色,但同时所有的颜色又都在里面。”她曾如此解读这种颜色。
面对人群的大部分时间,她都躲在自己刻意营造的黑后面,躲在宽大的墨镜后面。
13岁跟着草根歌舞团出道,16岁成为指南针乐队主唱,18岁被半截啤酒瓶刺穿左眼,22岁在南京机场毒瘾发作被出租车司机拉到公安局……她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天才少女,同时也诠释了什么叫残酷青春。
北京东四环外一家咖啡馆内,采访前,摄影师和罗琦站在楼梯间互动。她话少,腼腆,多以自然且淡的笑回应。托着托盘的服务生上上下下,木板发出咚咚咚咚和吱呀吱呀的响声。没有人对她多看一眼。
20年前的北京,罗琦是地下摇滚圈尽人皆知的场面制造者。音乐人洛兵回忆:“唱那个‘小小鸟的时候,底下什么老崔(崔健)、臧天朔一听全惊了”。
20年后,流行音乐界的面孔刷新了幾番,她站在两段台阶的相接处,没人知道她是谁。
1
2014年因产子临时退出《我是歌手》舞台后,罗琦除在次年完成了入行20年来的第一次个唱,再度陷入沉寂。
最近几年,她独自一人在德国带孩子,鲜少回国。儿子出生不久,她成了单亲妈妈。
她为儿子取名“早早”,意为来得有些早,自己尚未做好准备。
不过新生命诞下,她坦然接受。“虽然很累,虽然要为他做出很多很多的改变,但是我觉得快乐永远多于那些辛苦。”罗琦对火星试验室说。
2017年10月底,她接到签约公司—音乐人谢天笑创建的XTX工作室—通知,从柏林回到国内,献声11月初的赤水河谷音乐季。之后,她开始为自己的全国巡演与来自意大利的合作伙伴大章鱼乐队进行紧密的排练。
巡演的名字叫“重生”,意味明显,11月24日在长沙启动,之后一路辗转武汉、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计划于12月16日在成都谢幕。
《重生》是罗琦的一首新歌,由台湾作词人娃娃为她量身定制。“为我而写,为我自己的生活、心理状态而写。”罗琦说,新生命的到来,带给了她不少感悟。
摇滚歌手谢天笑从美国回来正碰上罗琦进棚录唱。那首歌本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但还是一下子被触动。
“她唱得那么感人。”谢天笑回忆,“她音色有点哑,也有质感,再加上她独特的经历,能赋予音乐不一样的感觉。”
在谢天笑眼里,同样的歌,只要罗琦一开口,绝对和别人不一样,“她唱的每一首歌都是自己的故事,都是她心里的声音”。
他明显感受到了罗琦当上妈妈后的改变。两人上世纪90年代就认识,常聚在一块喝酒,喝多了就给崔健等一堆朋友打电话,想起谁就给谁打,也不管几点,然后第二天再跟对方道歉,“打扰到朋友了”。
罗琦这次回国,谢天笑发现她很少喝酒。“她懂得了更爱护自己。那天我们聚会她说不喝酒,就一滴都没有喝。”他觉得罗琦身上多了份责任感。
以前,罗琦很少正经做饭,“就喜欢吃着方便面,看着copy show(模仿秀),觉得特别香”。儿子出生后,她学会了用蔬菜和鸡蛋做宝宝餐,口味也变得清淡,“就我们俩,我也懒嘛,不愿意做两份,就做一份,跟他一块吃”。
从叛逆的摇滚歌手到生活被柴米油盐填满的单亲母亲,这种转变于她而言并不容易。一年前,她曾炖了一碗鸡蛋羹,得意地把照片发到微博,感叹“给儿子的鸡蛋羹终于成功”。
在德国的生活,罗琦几乎一切都围绕着儿子转。没有帮手,她也不觉得需要托付给保姆或其他什么人。
回国这段时间,儿子被接到爸爸那儿照顾,她很安心。“孩子呢,是每时每刻都会想念他,他永远都在这里。”她用手指指向自己心脏的位置,“偶尔有时间会看一看他的照片,但是我知道他很好,他现在是在幼儿园,(或者)他现在应该回家了。”
有了孩子,她心里变得踏实。“就不像以前会突然一下—惊慌失措的那种,现在就会定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臭脾气被孩子磨没了,以前是‘哇,现在是‘呼—深呼吸一下,好,这样跟你讲(话)。”罗琦做出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罗琦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11岁那年,父母离异,她被判给了母亲。家庭的破碎给她的童年带来了至深的影响。
小时候的罗琦有极强的占有欲,或跟她很少真正、深刻地被爱有关,她缺乏如何去爱别人的经验和社会训练。
“她的表情不管多么热烈,神情却一如既往地冷漠着,任何事物,哪怕在她怀里,也离她很远。”知名音乐人、曾担任指南针乐队词作者的洛兵在《我的音乐江山》一书里回忆罗琦给她的印象。他写罗琦的那篇文章名叫《天才及疯狂的冷漠》。
罗琦在后来的成长过程里或多或少有在赎还上一代的情感债务。“她有点敏感,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别人也许听到就算了,她会往心里去。”谢天笑说,“音乐、朋友,她一直都很在意。有了孩子以后,孩子也理所当然在她在意的范围里。她焦虑也源自敏感。焦虑这种太细致的东西我能感觉出来,但没办法详细描述。”
儿子出生后,成了罗琦的生活重心,她把尽可能多的爱都给予了他。“现在问我的话,我也是说我肯定不要孩子,但是既然上天给了我,那,我觉得就是恩赐吧。”
爱是罗琦频繁谈论的一个字眼,她说这是自己唯一的信仰。“爱在你的心里,其实你自己就是一座教堂或者就是一间佛庙。”她再次用手指指心。
2
这次回国,罗琦借住在东四环附近朋友的家。1998年罗琦离开北京去德国时,四环路还没有连成一体,如今北京的变化过于巨大,以至于她常常迷路。
采访前20分钟,她找不着咖啡馆的位置,不得不向助理周静求助。“我罗琦姐可能找不到这里了。”周静说。她从咖啡店二楼的落地窗眼巴巴朝外望了一会儿,旋即下楼,向东走去,然后又返回来一直向西。endprint
此前一天,罗琦想去新源街,查到675路公交车,等她跳上去,车驶到通州才反应过来,坐反了。
罗琦很宅,她用了两个“特别”来修饰这种状态。出门对于她很难。
这跟她早年的状态恰好相反。那时候,她最想做的一件事,是走出去。
1975年,罗琦出生于江西南昌,父母离异后她和外婆一块儿住。家庭的破碎让她变得叛逆而独立。那个年代流行霹雳舞,她常把用来学习的时间拿来练习跳霹雳舞,迟到、早退、逃课是家常便饭。
13岁时学校劝她退学,她没和母亲商量,就擅自在退学通知书上签了字。之后,她一度被母亲安排到自己所在的服装厂上班。但没几天,她就厌倦,偷偷跑出去,跟几个小伙伴成立乐队,后加入邻县一个草台班子做伴舞、唱歌。
16岁那年,她偶然听到邦·乔维(Bon Jovi)的歌,迷上摇滚,只身一人闯荡北京,后被知名音乐经纪人王晓京发掘,成为指南针乐队主唱。
因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很快罗琦就在北京摇滚圈闯出名声,被誉为“中国摇滚第一女声”。小小年纪就收获无尽荣耀。
那些年,羅琦常唱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嘶吼“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这首歌一定程度上是她的心声写照。
她个人的第一首歌《不想是小孩》是洛兵根据她的思路作的词,写的是“不想再年少/不想再弱小/不想是小孩/去找我的梦/去找我的爱/去找我的未来”。
那时的罗琦急迫成长,希望融合到新的圈子和秩序。她喜欢跟比她年长的朋友共事、做音乐。“那个时候的心理状态是希望自己能够成熟一点,能够跟他们平起平坐。”
洛兵在书中回忆过那段时光。1990年代初,罗琦和指南针乐队的吉他手周笛、键盘手郭亮、鼓手郑朝晖、萨克斯手苑丁、贝司胡小海(后来是岳浩昆)挤在三元桥附近几间面积狭小的平房里,“小碗喝酒,小块吃肉,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花。当然最重要的是,有唱片一定要大家听……活活听坏了王晓京好几台音响,他却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几支蜡烛,几瓶啤酒,一把箱琴,几个又狂妄又热情的小孩谈天说地,指手画脚……”
罗琦是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不过十几岁,比其他人平均要小五六岁,但彼此相处融洽,并无年龄上的隔阂。
然而,就像烟花一样,属于她的辉煌时刻很短暂。1993年,罗琦在酒吧给女伴过生日时,喝高了,与人发生冲突,对方从桌子上抓起一个啤酒瓶,用力磕碎,握着剩下的半截捅进了她的左眼。此后很多年间,她都用一块纱布蒙着眼睛。
她喷薄的音乐之路也由此出现拐点。1997年毒品事件爆发后,她远赴德国治疗,并长期留在那里生活,从此淡出公众视野。直到2014年参加《我是歌手》,她才又一次站在聚光灯下。
罗琦说她前半生没有意识到割裂和区隔,总能很快融入一个新的状态,那些过去的事情,仅意味着“发生过”、“经历了”,“最期待的是自己现在这一刻是什么样的状态”。
“没有被大家所关注或被媒体所报道,并不等于我的生活就停止了,我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不过是你不知道而已,你完全没有必要为我而尴尬,我反而会觉得你太操心了,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生活轨道、自己的生活。”罗琦说,“世界这么大,怎么可能仅仅用一个标签代表。”
2012年,在一场电子乐派对上罗琦与树音乐创始人、CEO姜树相识,达成最初的合作意愿。第二天,罗琦又打电话过去,直直地问:“老妖(姜树的绰号),我可以相信你吗?我可以相信你吗?”
姜树回复:“是的琦姐,你可以相信。”
第三天、第四天,这样的通话重复了十几次。在那之前罗琦并没有稳定的经纪签约,一年下来,演出机会寥寥。她有她的顾虑和不安。
2013年下半年罗琦应许参加《我是歌手》,有来自姜树的鼓励。
2017年6月,罗琦签约谢天笑的XTX工作室。罗琦不喜欢媒体来采访、拍照,关于她抗拒媒体的描述,出现在数篇公开报道中。名声最盛时,罗琦开门看到是记者会直接关上门;面对过于细致的提问,她会转向助理:“需要这样像查户口一样地问吗?我感觉这样问像进了派出所一样”;采访中途若崩溃失控,她会起身就走。
人们关于罗琦的记忆钟摆停在一袭黑衣、冷漠且酷的女孩儿的样子。她喜欢黑色,认为它有包容一切的内涵,暗示黑色背后站着一个内心更丰富的自己,却对阐释更加完整的自己显得有些无能为力。
3
谢天笑说,以前罗琦喝了酒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特别外向,可以开玩笑,天南海北地谈各种音乐”,而现在大多数时候,她“特别内向,甚至有时会害羞”。他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罗琦尝试保持清醒,也把周遭事“看得更真实、更自然了”。
在德国,罗琦偶尔周末和朋友到Club跳舞。她觉得好听的歌,常常记不住名字,只记得旋律。每天在读的书她也记不全作者名,“那个作家叫什么Patrick,就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法国的作家,他最擅长就是写短篇”。她说的是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人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她把能买到的莫迪亚诺的书,都买来收藏。
她习惯了独来独往。一个人去看电影,一个人去买东西,一个人去吃饭,社交圈仅有几个人,简单私密。一天忙完,儿子睡着,有时候她会“找一部片子看,然后再休息”。她喜欢美国的剧情片,没有粗糙设计的宏大冲突、陷入俗套的剧情线,或是单薄的英雄式主角,看起来稀松平常,没有惊涛骇浪,就像她现在的状态。
希区柯克说,电影是减去琐碎片段的人生;戈达尔说,电影就是琐碎的片段。罗琦当下的生活更接近后者。
“我觉得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改变了吧。”说这句话时,她已经42岁,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棱角分明。
“您希望怎样被记住?”
“我就没想过要被外界记住,为什么要记住啊?最好别谈我。”她说。
坐在咖啡店窗边,罗琦的注意力会被窗外的什么吸引,可目光却没有落在景物上,视线好像被内心的某种东西牵住,停在了半空中。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