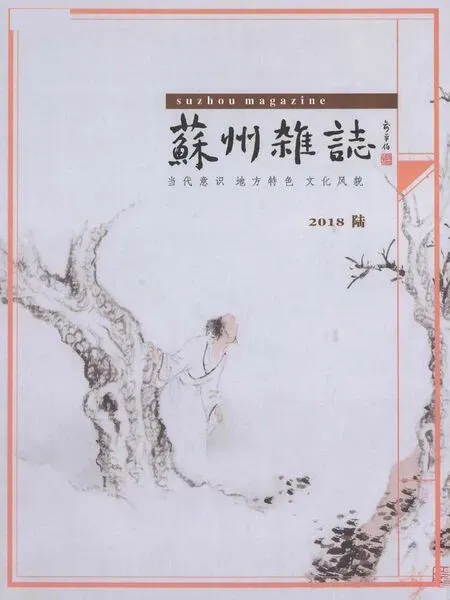杨明
——流淌、悖论与变奏
2018-02-23夏天眉
夏天眉

我闭上眼,杨明的雕塑在我脑海里盘旋,像鹰要寻找食物——艺术在捕捉观众。我第一次见到杨明的作品,是画廊里的一件陶瓷马。一匹瘦小的马儿,站立在湖泊的中央,身边是蓝绿色的湖水,湖水漫过它的腿。你的脸照映在湖面上,湖底的白砂静谧无言,没有鱼儿的搅动、没有石子的涟漪。这匹马静止在此,时间和声音也都一同静止了。我和杨明提起这件作品,他却说,这类作品我是警惕的。我想他是在警惕漂亮、优美和抒情,那他更想展现什么,优美的反面吗?
杨明告诉我一个故事。早年在杭州的一次展览上,来自同学的一件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件雕塑的表达手法如此陈旧,简直就是一个中年人的作品,而不是出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之手。当时的那种震惊,导致杨明头也不回地逃离陈旧的写实传统,决心要做出不一样的作品。
背离写实的结果是《黄昏1(1992)》,这件作品一出现就夺人眼球:一条皮囊一般的人体垂挂在椅凳上,就像达利画笔下的时钟,在时间的热浪中融化了,有历经沧桑的疲惫,也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幽默。这条皮囊瘫软在那里,看着忙碌的人们和车辆煞有介事川流不息,上帝似乎喜欢在此刻开玩笑——嘲笑人类的自信。“我在不自信的时候表现更好”。抛弃写实,而没有走向抽象,杨明是在抽象与具象之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不是写实,也许是写意。
《蚀(1993)》是杨明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作品是一条被侵蚀的石凳,被侵蚀的部分软软地垂挂下来,隐约是一个人形。虽然这条石凳仍然是一个完整坚硬的整体,但杨明却营造出了柔软的感觉,用硬塑造软,用流淌打破僵硬。流淌、柔软,与坚硬本来是相悖的,却出现在同一件作品上。或者,其实柔软是一种欺骗,其实雕塑一直是坚硬的,但它伪装成柔软的样子,并唤起你对柔软的回忆。这种悖论的两极,还出现在杨明其他作品上,是一种连续性的实验。
呼吸可能是最单纯的事情。呼吸系列的作品也是如此,简洁明了,舒展与收缩相连接,将看不见的呼吸物化为实体。在荒地里站立着的呼吸系列异常肃穆,呼吸之间是否千年。为雕塑取名呼吸,以强有力的雕塑作品表达轻微的“呼吸”——沉重的雕塑,与不能承受之轻,以悖论的形式被联系在一起,千斤拨四两,这是杨明的智慧。
面孔系列是流淌这一元素发挥到极致的作品,而美到极致就会带来恐怖。曾有艺术家策划过一个讲解雕塑作品的行为艺术。面对各种各样的雕塑作品,讲解者被要求展开想象,为雕塑作品作出自己的解读。当看到杨明的面孔系列作品时,我想象它是沼泽地遇难者的头部,这确实有恐怖的成分。这次讲解雕塑的行为艺术作品似乎在向艺术史抛出疑问:艺术作品必须有自己的故事吗?历史是否在故事之内,艺术是否在故事之外?
那件名为《我的面孔(2008)》的不锈钢作品,一个看不清五官的头像,银色的粘稠液体流淌下来,覆盖了所有皮肤。液体是滚烫的,更是冰冷的。毛细血管窃窃私语,你是谁我是谁,你在想什么我在唱什么歌,我在遗忘你你在吃掉我。只有头像在尖叫。仿佛从过去到未来,只有头像在无声地尖叫。
《湃-per系列(2016)》是流淌的变奏。极致之后,变化是结果。外在的变化是材料——在十五年前就有人向杨明推荐过聚氨酯这一材料,由于材料的不可控性杨明没有采纳,但是现在杨明主动选择聚氨酯却恰恰是因为材料的不可控性。这种难以控制使得雕塑的过程转变为材料的“自我创造”,材料在空气中发生反应不断生成自我,没有意识、只有本能的自我,这一不断生成的特性就是雕塑的力量,雕琢与塑造的力量,而聚酯氨却在塑造它自己。对于聚氨酯的作品,杨明还赋予了强烈的色彩。常常是明黄色和黑色、亮粉色和黑色之类强烈对比的色彩组合,左边是星汉灿烂,右边却是黑洞,一边是辉煌,一边是陨落,左手打开,花瓣随风摇曳,右手握紧,光从指缝间溢出。湃-per系列还包含误入地球的陨石、学习站立睡觉的石头、揉成团后被抛弃的铁皮,顶光打下来,他们漂浮在尘埃之中。
在古代中国,雕塑是工匠的工作,只在近现代开始才有了雕塑家这样一种身份,而这种身份在杨明这里一直是强有力的主宰者形象,直到使用聚酯氨,杨明才开始“放手”。杨明的作品中,流淌的感觉是一以贯之的。杨明说,也许这种流淌的感觉对于他来说就是最有力量的。我想,流淌的力量是不同速率的,可能是滴水穿石般延绵,也可能是暴雨冲刷般强烈,从石凳上缓慢的侵蚀,到抽象形体的色彩爆发,都是流淌的变奏曲。而我再回想那匹站在湖心的小马,它确实不在这个序列中,优美的反面是什么,是瘫软的人体,是悖论式的实验,是极致带来的恐怖,是塑造自己的特殊材料。优美的反面是追求本质的探索力量。
在当代雕塑界,能被人们提起的雕塑家并不多。有人转向公共艺术,有人转向新媒体,杨明却不受外界的影响,只被“流淌的感觉”紧紧抓住,纯粹地、无声地接住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