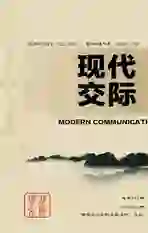“劳动者”与“性别”之名的相遇及其新的可能性
2018-02-20赵欣悦
赵欣悦
摘要:通过一部编年体例女工个人故事的口述史,试图去思考曾处于城乡之间尴尬状态的“新工人”群体的另一种新的可能性,在与“老工人”“农民工”“新中产”“新穷人”等这些概念命名的比较中,在女工们对于文化、情感与爱的诉求中,试图去探求时代变迁历史中的“劳动者”与个人生命历程的“性别”之名相遇的可能性,并且在对生命的书写与创造中,去寻找历史主体之名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新工人 女工 劳动者 性别
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21-0247-02
《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是吕途老师“中国新工人”三部曲的第三部,正如吕途老师自己在前言中所阐述的:“《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是对生命本身的体会,是对生命力的歌颂。”[1]就像这本书的封面,让人久久不能忘懷的是凋敝的枝丫和视线所及的农田,还有那用粉色字体镌刻的书的题目。由此当我们阅读34位中国女工所思所想的生命故事时,会去思考时代变迁下的“劳动者”与个人生命历程的“女性”身份之名的双重叠加与相遇的背后,是否具有“寻找历史主体之名”新的可能性。
一、与时代变迁下的“劳动者”之名相遇
戴锦华老师在为《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所做的序言中曾说:“女工们的,也是今日世界劳动者、生产者、供养者与服务者的故事。”[2]而透过34位女工的故事,可以看到从1950年到1990年,这四十年间时代变迁的历史,并且看到作为“劳动者”的她们是怎么与“新工人”之名相遇。
(1)“新工人”与“老工人”。回顾近现代中国时代变迁的历史,与“劳动者”之名的第一次相遇,应追溯至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而“新工人”与“老工人”在城乡的身份上也存在一定差异,无论是70年代的第一代打工者,还是没有依靠务农为生的第二代打工者,抑或从小在城市长大的第三代打工者,“新工人”面对“回不去的乡村、待不下的城市”的尴尬状况,而这种尴尬是曾经的“老工人”不曾拥有的心灵感受。
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中的第一个女工的故事,就是折射这种“劳动者”之名变化的现象,而这个“曾经的主人翁”就是1951年出生的三婶。这个故事的讲述按照编年的叙述方式,从三婶的上学经历开始讲起,笔墨较多放在了三婶不同时期的工作经历上,三婶的命运与时代变迁的历史紧密相连,面对慢慢被私人承包的工厂,三婶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这或许也是透过三婶的命运,在与时代大潮下的“劳动者”之名相遇,寻求主体之名的一种可能性的尝试。
(2)“新工人”与“新中产”。之所以在“工人”和“中产”之名前加了限制性定语“新”,则说明这是伴随时代变迁的历史出现的一种对于生产和消费方式主体的全新理解。
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中1976年出生的老赵,面对在广州S厂打工二十年的时光,老赵很难说清楚对于自己打工的这座城市的感情,可以看到广州作为中国“世界工厂”的重镇,产业工人在流水线上的工作塑造了那些消费景观和消费商品,而这个过程使得作为生产者的“新工人”们成为被隐藏的“他者”,而与“新工人”共处于相同消费社会的结构中,“新中产”也处于尴尬之地。因此,“新工人”“新中产”与“劳动者”之名相遇,则为未来寻求自身身份诉求提供一种可能性。
二、与个人生命历程的“性别”之名相遇
(1)对于“文化”的诉求: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新工人”群体中的女工们,在寻找集体归属感的同时,也在竭力表达自己对于个人生命历程的感悟,用诗歌、音乐的形式彰显着自身对于文化的诉求。作为曾是被社会“边缘化”的女工们,可以看到文化已成为她们个人生命历程的一部分,在她们行为中有一份对生命的笃定与从容。法国思想家阿尔都塞就曾明确阐述过艺术是以“看到”“觉察到”和“感觉到”的形式,而不是以“认识”的形式。所以女工们对于文化的诉求,也是她们对于自己流水线上生活的一种“觉察”“感觉”,而不是一种“认识”,甚至可以说女工们在寻求的一种文化,仿若文学的“陌生化”效果使其恢复到对于生活的体验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
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中1985年出生的段玉从小在爷爷、奶奶的陪伴中成长,之后在卖汽车配件的过程中,感到北京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于是自己买了一把吉他,而这也是段玉第一次在吉他的旋律中体会到一种消除寂寞和忧愁的方式。所以对于文化的诉求,让段玉和孩子共同成长,在与个人生命历程的“性别”之名相遇的过程中,发出了超越作为女工,更多是作为“新工人”这个群体的声音。
(2)对于“情感”与“爱”的诉求:对生命力的歌颂。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中“选择一个人生活的可爱姑娘”1987年出生的小贝,像范雨素一样,她把对于“情感”与“爱”的诉求指涉为自己的母亲,可以说小贝的人生选择,是一种直面人生,直面自己对于“情感”和“爱”的诉求作出的主体选择的结果。在小贝的个人生命历程中,与“性别”之名的相遇,带给她的不是困惑和焦虑,而是一种对生命的笃定与从容,当她选择在苏州工友家园工作时,她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并且那种身份认同感,让她知道过一种主动不被控制的人生是可能的。
三、“寻找历史主体之名”的可能性
戴锦华老师在为《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所作的序言中提出了“21世界最急迫的问题之一,即我们是否仍可能或应该在阶级之名下集结?”[3]。可以说,这些因素为“劳动者”与“性别”之名的相遇,“寻找历史主体之名”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中我们看到的是访谈者与言说者之间的生命对话,我们看到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吕途老师不仅仅是“女工”们遭遇的记录者,“新工人”们生存状况的思考者,更是践行“由生存而尊严,而不是以尊严为代价去换取生存”[4]观念的行动者。因此,正是这部编年体例的女工个人故事的口述史,让知识分子对于底层问题的参与,不再只是处于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也不再是简单的“看”与“被看”的关系,使得这一集体、社群的名字不再只是停留在知识分子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的书写上。因此,通过《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阅读,我们每个人在字里行间中与时代变迁下的“劳动者”之名相遇,与个人生命历程的“性别”之名相遇。或许,这就是文字所能传达的不仅是身体的跨越,更是内心的迁徙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吕途.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2]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J].开放时代,2014(6).
[3]理查德·J.莱恩.导读鲍德里亚[M].柏愔,董晓蕾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4]张慧瑜.新中产与新工人的浮现及未来[J].中国图书评论,2013(4).
责任编辑:张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