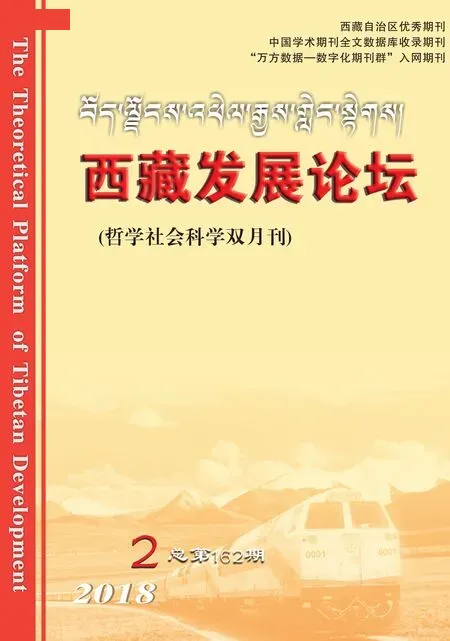试述藏源文化与山南的关系
2018-02-20左俊玲
罗 勇 左俊玲
源,本意指水流的起始处,引申为来历、根由。我们经常说,山南是“藏民族之宗 藏文化之源”,细细思“源”,还真是源源不断,渊源深厚,名副其实。下面,本文将从史学的角度,对山南之“源”,进行梳理,讲清“源”来如此。
一、藏民族之“源”
无论哪个民族?对于自我的起源,皆为首要之关注。藏民族概莫能外,“猴子变人”的传说,遍及整个藏族地区,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已成整个民族的共识。
神话是传说的故事原型,传说是神话的社会历史。这个比达尔文进化论早1000多年的认识,绝不是胡编乱造,而似有确凿的证据,其发生地就在山南,贡布日山腰的“猴子洞”见证了这一切。
传说:“洪荒时代的西藏,在山南泽当贡布日山的洞里,住着一只母猕猴,她饱尝着大自然的景色,吃着洞外菩堤树上的果子,过得很快乐,只是感到缺少伴侣的寂寞。天神‘帕巴见日色’知道了母猕猴的心意,便化人身来与她成亲,生下的子女就是西藏最早的人类……”
《贤者喜宴》记载:最初有一只猴雏。《总遗教》则载述:初有六猴雏。继之蕃衍众多,分为四部,并彼此发生争执,此即为所谓西藏之四人种……,据传,菩萨(指父猴)携其子孙,并向他们示以不种自然之谷物,说:“吃吧!”众猴因食谷物而变成人,他们食自然之谷物,穿树叶之衣,在森林中如同野兽一样生活……,而遍及于西藏。
位于贡布日山的猴子洞,海拔4060米,距山顶70米,是自然形成的岩洞。传说中的猕猴与罗刹女就是在这个洞里结合、繁衍后代的。岩洞附近的岩壁上,有一个猴子头形,据说为传说中的父猴的自然显影。岩洞东南石壁上,有一幅彩绘壁画,一只手捧曼扎的猕猴坦然安坐在牡丹花上。洞内外还有线刻的佛像石板和五彩经幡。最神奇的是洞外那棵野生葡葡树,据说是当年猴子们曾摘食过。
藏族史学家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考证,猕猴在藏语中含有小猿猴的意思,而罗刹则是栖身于岩洞吞食其他动物血肉的一种猿类。这就意味着生活在雅鲁藏布江沿岸森林里吃野果的一种小猿类(森林部族)与居住在岩洞里吃动物血肉的大猿类(山地部族)结合,实行族外婚,繁衍子女,逐渐在高原上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形成早期人类。
猴子变人的传说,在西藏广为流传,后来又记录进各种藏文典籍,如成书于公元11世纪的《国王遗教》、16世纪的《贤者喜宴》等,并被画在藏传佛教寺院的壁画或唐卡里,如布达拉宫主体建筑红宫的走廊上,有两处就描绘了这个藏族人起源的故事;罗布林卡内达赖喇嘛住的新宫二楼经堂里,也有这个故事的壁画。
这些记载与传说,虽然带有一些宗教色彩,但是,它仍然反映了古藏族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经历了由猿到人的历史时期。与山南泽当“猴子洞”邻近的贡嘎县昌果乡及琼结县下水乡,均发现了人类活动的“昌果沟遗址”和“邦嘎新石器时代遗址”。同样,在离“猴子洞”不远的雅鲁藏布江沿岸的桑日县达沽至今仍生息着数量庞大的猕猴群体。传说与历史,历史与现实,就这样紧密地交织着。
二、高地农业之“源”
猕猴与罗刹女结合,产生了藏族最早的祖先,他们从猴子洞出发,把活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来到雅砻河与雅鲁藏布江交汇之处,在这片河谷地带尽情地嬉戏与觅食,进而形成了“泽当”一词。“泽当”藏语意为“猴子玩耍的坝子”或“猴子游戏场”,也就是今天山南市首府所在地。无独有偶,在泽当镇,有一条通往“猴子洞”的街道,当时百姓称之为“百日街”,藏语的意思是“猴子刨土”。
吐蕃人的先祖是一只猕猴与一位岩罗刹女,这对夫妻的后裔为半猴半人者。他们虽然已经能直立走路了,但浑身却长满了毛,面部呈赭色和扁平状,某些说法中还认为他们拖着一条尾巴(也有一些人认为他们的尾巴已经脱落)。猴祖为他们指定的居住地区为南部的林地,他们在那里又同母猴巧配姻缘,所以其数目越来越多。
《西藏的文明》记载:“仲夏,他们备受雨淋日晒之苦厄;隆冬,又为大雪和寒风所折磨;他们一无食物,二无服装”。他们的祖先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此佛出于一片大慈悲之心,为他们带来了“七种粮食”(荞麦、粗青稞、芥菜等),也有说是五种:青稞、小麦、大米、芝麻、豌豆。这样一来,他们才在雅砻地区的索当一带开垦了第一批农田,那些猴人,才逐渐获得了人形。
索当位于雅砻河谷。雅砻河发源于雅拉香波雪山,呈南北流向,流域面积920万平方米,形成雪山冰川、田园牧场、河滩谷地、高山植被等地貌,在泽当镇注入雅鲁藏布江。河谷内气候温润,地势开阔,水源充足,具有发展农业的天然优势。
可以推断,藏民族的先民们,经泽当镇,溯雅砻河而上,在河谷索当开荒种地,由游牧采摘过上了相对固定的生活。因而,索当被称之为“西藏第一块农田”,也称之为西藏土地之母。至今仍保持有每逢播种的季节,藏族人都要到这里抓一把神土,祈求祖先的保佑。伴着农业的发展,相应的村落随之产生,即诞生了雅砻索卡也就西藏的第一个村庄。
“1994年,西南农业大学农学系的学者在昌果沟遗址的大型灰坑内发现了一批古青稞化石粒,这是当时在全区范围内首次发现的史前大麦考古遗存。之后,1995年,在同一灰坑内发掘出一批与古青稞化粒伴生的类似于去壳的‘粟’的小型碳化粒种子,学者推测,青稞可能是昌果沟先民们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且同时又栽培相当数量的粟。”在邦嘎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以磨盘、磨石为主,其它的还有敲砸器、砍砸器、砍斫器等,这说明当时的农业已具有了相当大的规模”。[4]至今,在雅砻河边仍然有许多水磨坊,当地百姓利用天然水力磨制糌粑。
农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起源于雅砻的吐蕃部落,先后出现了七良臣(也称七贤臣),其中好几位都对农业发展有过杰出的贡献。第一位贤臣如来杰,“……将草滩开垦为农田……开始有了牲畜和农事。”第二位贤臣则“丈量土地,蓄水为湖,引水灌田。”第三位贤臣则“在木头上钻孔做成犁耙和轭具,使用犏牛、黄牛实行耦耕,使平地得到开垦。”第五位贤臣“以秤、斗计量收支,调剂农牧业区的食物,倡行双方满意的买卖和换工合作。”第六位贤臣“将山上的居民全部迁到河谷平地,使农民在田地边盖房定居,开垦平地为农田并引水浇灌。”
三、藏文明之“源”
如果说“猴子变人”只是蛮荒记忆,那么吐蕃(或称悉补野)部落则是文明之始。在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吐蕃”、“雅鲁”等字眼出现频率较高,有必要对其进行探“源”。
传说,很久以前,在雅砻河谷过着游牧生活的人们,某天在赞塘阔西(今乃东县卡多乡)发现了一个英姿勃发的小伙子。他的言语举止与本地土著完全不同,无法沟通和交流,牧人们没了主意,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这个年轻人,便派人回聚居点报告。氏族长者派出12个颇为聪明的苯教巫师上山,盘问小伙子从哪里来。小伙子以手指天,巫师们以为他是从天上来的,是“天神之子”,格外高兴,便伸长脖子,给这位“天神之子”当轿骑,前呼后拥地把他抬下山来,公推他为部落首领。人们尊称他为“聂赤赞普”,也就是“用脖子当宝座的英杰”。藏语里,“聂”是“脖子”的意思,“赤”是宝座,“赞普”是“英武之主”。自此,历史上把藏王称为“赞普”。这个聂赤赞普,就是后来叫作“悉补野王统世系”的第一位王,也是出现在藏文史籍中的吐蕃部落的第一个首领。苯教典籍还把聂赤赞普说成是色界天第十三代光明天子下凡。
聂赤赞普到底来自何处?藏文古碑刻中记载:“初,恰亚布拉达楚之子聂赤赞普为人世主,莅强妥神山以来……”“赞布天神之子鹘提悉补野,仍天神来主人世也……”“神圣赞普鹘提悉补野化身下界,来至人间……于雪山高耸之中央,大河奔流之源头……自天神而为人主,德泽流衍,建万世不拔之基业焉”。《雍布拉康目录(中等本)》载:“昔,波沃地方有名为姆姆尊之妇女,生有九子,最幼者取名‘乌比热,眉目俊秀,指间有蹼,具大法力,乡人不容,逐之出。’前往蕃地方时,适逢蕃人寻王者,于强朗雅列空相遇,众人问:‘汝为谁,自何来?’答曰:‘吾自波沃地方来,欲往蕃地去。’又问:‘汝可否做蕃地之王?’答曰:‘尔等以颈载吾,吾自有法力与神变也。’众人便遵其命,以肩舆载之,尊其为王,并上尊号为聂赤赞普。”
敦煌出土的吐蕃历史卷中载有:“开疆辟土,修筑城堡,自吐蕃四部悉补野氏有……”据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考证,“悉补野”为“波杰”之古译。“波”即波沃(今林芝市波密)地区之意,杰即首领之意,“波杰”即来自波沃地区的首领。从此,天神出任人主,雪域得安宁,把人们从饥饿和战争的痛苦当中解救出来,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在雅砻地方修建了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
据考证,“雅鲁”源于“雅砻”,是两个可以相互转换的词。根敦群培的《“吐蕃”一词来源考》有载:“聂赤赞普等一般被称作蕃王或悉补野,看起来很像是地名转变为王名。事实上,王名转变成地名也是有可能的。”
吐蕃从此起步,雅江而此得名。起初,雅砻赞普的领地只是从雅拉香波山脚至雅鲁藏布江边,范围极小。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吐蕃本身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吐蕃的疆域曾一度发展成上至雅鲁藏布江源头的象雄,下至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工布地方,而原来“雅隆”一词的涵义也不断扩大,包含了南至门域地区,北至羌塘无人区的广大区域。因雅砻赞普的统治区域与雅鲁藏布江的长度相当,所以从这时起这条江就叫做雅鲁藏布江。
四、藏传佛教之“源”
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在向青藏高原传播过程中,大量吸收苯教的仪轨而形成。纵观整个藏传佛教史,其融合发展的过程是在山南地区完成的,因而山南也可称之为藏传佛教之源。
据史料记载,托托日年赞六十岁时,天降“玄秘神物”于雍布拉康,包括《诸菩萨名称经》、《宝箧经》、两部如意经卷、金塔、牟陀罗印等。故此,有西藏最早的佛经为《宝箧经》,最早的咒语为“赞檀玛尼”(意为极为珍贵之物)的说法。但当时语言不通,佛教在吐蕃未能得到传播。
松赞干布(617-650年)时期,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地方政权,东西联姻,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大唐文成公主,引进佛教,翻译佛经,是为佛教在青藏高原传播之始。“为镇压魔女之左肩,松赞干布前往雅砻”建昌珠寺。“昌珠”意为“鹰叫如龙吼”,取意大鹏鸟与龙相斗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传说,这是西藏建立最早的佛堂。据说,文成公主进藏后,一段时间里,她夏天住雍布拉康,冬天迁居昌珠寺。
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藏,带来了大规模的汉文化输入,兴起了超荐亡灵的“七日祭”,是为超荐佛事习规之始。但佛教在吐蕃真正得以发展是赤松德赞(742-798年)时期,他采取了一系列兴佛强政的措施,包括剪除崇苯大臣,迎请寂护和莲花生大师入藏,修建桑耶寺,剃度七觉士等,但所有这些举措基本上都是在山南地区完成。
公元762年,根据寂护的设计,莲花生大师主持,赤松德赞亲自奠基的桑耶寺动工兴建,779年建成。桑耶寺规模宏大,布局奇特,据说是以古印度婆罗王朝在摩羯陀所建的欧丹达菩黎寺为蓝本而建,全寺的建筑完全按照佛经中的大千世界布局:中央为世界中心须弥山,由一座藏、汉、天竺三种风格的三层“乌孜大殿”代表;大殿南北建太阳、月亮两殿,像征宇宙的日、月双轮;乌孜大殿四个角上分别建有红、白、绿、黑四座佛塔,代表四大天王;大殿四周还均匀分布着四大殿八小殿,代表四方咸海中的四大部洲;寺庙建筑群的外围是一道圆形的围墙,象征世界外围的铁围山。整个寺庙建筑布局与密宗的曼荼罗(坛城)有几分相似。
经过考察,在法王赤松德赞的主持下,莲花生大师任大轨范师,由寂护大师担任大亲教师首先剃度了拔·塞囊、拔·赤协、巴阁·白若杂纳、杰瓦却央、昆·鲁益旺布、马·仁钦乔和藏·列珠等7人出家。西藏历史上把这首次剃度出家的7人称为“七觉士”(亦称“七试人”)。而法王赤松德赞、大亲教师寂护、大轨范师莲花生,也因为度化西藏历史上的首批僧人而被后世称为“师君三尊”。桑耶寺也就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座有出家僧人住持修行的寺院。
结语:山南人自己说,有西藏“十个第一”:西藏第一位国王——聂赤赞普、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第一座佛堂—昌珠寺、第一座寺院—桑耶寺、第一部藏戏—巴嘎布、第一块农田—索当、第一个村庄—雅砻索卡、第一部经书—邦贡恰加、第一个村党支部—克松村党支部……路漫漫其修远兮,溯“源”山南,“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2]恰白学术思想研究课题组(编)·恰白·次旦平措学术论文汉译集[M].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3]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4]西藏社科院《西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贡献》课题组·西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贡献[M].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5.
[5]次旦扎西·阴海燕·吐蕃十赞普[M].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
[6]夏玉·平措次仁(著)·羊本加(译)·藏史明镜[M].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