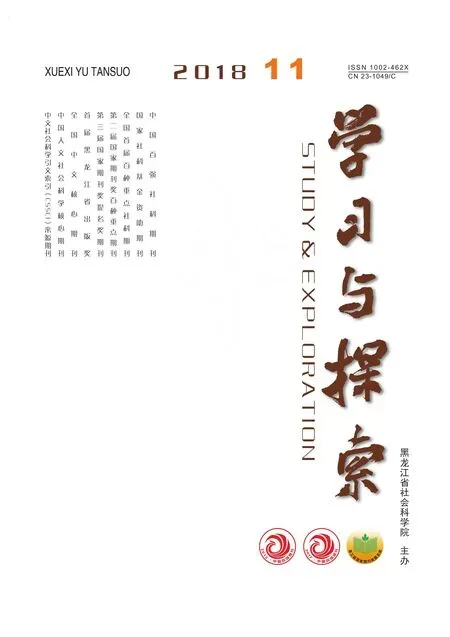张謇和涩泽荣一的儒商思想比较
——基于中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观的视角
2018-02-20向婉莹
曾 丹,向婉莹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武汉430072)
一、引 言
张謇(1853—1926)和涩泽荣一(1840—1931)是中日两国近代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两人大致处于同一时代,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经历,饱受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熏陶。两人所处的时代都是本国由封建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转型、西方列强入侵、各类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特殊历史时期。面对当时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外来压力,两人均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在实业救国的过程中始终坚守着儒家的价值理念与道德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实业经营活动的准则,提出了一系列有别于欧美经济伦理的儒商思想。他们的儒商思想都强调商人从商应秉持儒商人格、义利两全、竞争意识等观点和主张,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正因为如此,多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在分别对两人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两人儒商思想的共性特征及其对当时各自国家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然而,无论是从推动东方儒家经济伦理的发展,还是从促进本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工业化发展来看,涩泽荣一的儒商思想所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其影响也更加广泛和深远。这表明,两人的儒商思想尽管相似,但实质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于两者儒商思想存在差异及其对社会影响不同的成因,周见(2007)认为,两国在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及国家意识形成条件、官僚制度、企业体制、企业家队伍结构及社会文化普及水平等方面的不同是造成两者儒商思想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而马敏(1996)则认为,张謇和涩泽荣一儒商思想的不同结局与个人理念之外的“经济因素”,即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条件之总和的不同有关。诚然,作为实业家的张謇和涩泽荣一个人儒商思想的形成肯定与各自所处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文化传承和企业制度有关,但是,19世纪中后期,同受儒家文化影响、同处社会转型的中日两国之所以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上存在越来越大的差异,无不与当时两国提出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观有关。当时,面对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和外敌入侵下西方文明的冲击,两国的思想家先后提出了“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观。这两种发展观既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但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两国选择了不同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从而也决定了张謇和涩泽荣一儒商思想结局的不同。从这一角度来讲,两国不同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观才是两者儒商思想存在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在比较分析两人儒商核心思想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同时,只有基于当时中日两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观的视角,对比分析两者儒商思想之间差异性的成因,才能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而这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二、张謇与涩泽荣一在近代中日企业史上的贡献及地位
张謇被誉为中国“现代化推进者”“现代化的开拓者”,是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张謇出身于内忧外患之下大厦将倾的清朝末年,从幼年开始接受私塾教育,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像所有求取功名的读书人一样走上科举之路。虽荣登状元,但历经26年奋斗之久的张謇对科举登仕已渐生厌倦之心。在甲午战争的影响下,张謇开始怀疑仕宦之路,并最终在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号召下弃官从商,投身商海以期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张謇主张按照儒家伦理道德观来规范企业家的行为。在他看来,从商道德极其重要,是衡量企业经营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弃官从商之后,张謇于1895年在南通筹办了大生纱厂。“大生”一词来源于“天地之大德曰生”。在纱厂创办之初张謇就认识到,让民众能够饱腹暖体、脱离困苦是儒者应尽的职责,所以将纱厂取名为“大生”。大生纱厂正式运营之后,获利颇丰,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因此,张謇又于1904年、1915年相继开设了大生分厂。创办纱厂的成功给予张謇极大的鼓舞,之后张謇又陆续在轮船、水利、钢铁、造纸、机电等领域开办了数十家企业(王敦琴,2005)。同时,为解决农民生计问题,张謇开办了一系列农垦公司,在通州境内开垦百万亩新田,并分配给每户农民一定的田地,使数十万民众有了生活保障(王敦琴,2013)[1]。虽然在动荡的社会条件下,张謇的实业救国之路最终没能实现,但他作为企业家却不以积累个人财富为唯一目标,始终担负起社会责任的儒商思想和行为,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和尊敬。
涩泽荣一在日本被冠以“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等数个桂冠。他出生于时局动荡的江户末年,经历过江户、明治、大正、昭和四个时代,参与了日本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历程,在经济领域为日本的近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1873年,时任大藏少辅一职的涩泽荣一因是否增加军费和财政预算的问题,与当时的大藏卿大久保利通政见相左而弃官从商,投身实业界,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公司银行——第一国立银行,①第一国立银行最初由涩泽荣一筹划立案,以兑换商三井组和小野组双方为核心设立。由于第一国立银行的创办资金完全依靠三井组和小野组双方的投资及部分社会募集资金,所以虽名为国立银行,但在性质上属于拥有货币发行权的私营股份制银行。由此踏出了发展工商业、实业救国的第一步。在辞官从商之际,涩泽荣一清楚地知道,商界亦如同政界一般,需要为了各自利益进行无休止的争斗,投身其中如若想坚守自己从商的初衷,不为利益所迷失心智,沦为金钱的囚奴,是极其困难的。经过艰苦的思索,涩泽荣一认定只有将《论语》中儒家的道德理想与谋利的经营活动相结合,才能实现自己富国富民的理想。自创办第一国立银行,开创日本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性质的株式会社之后,涩泽荣一先后在金融、钢铁、机电、矿山、纺织、铁道等众多行业建立了500多家企业。此外,涩泽荣一还积极推进儒家伦理道德在民众中的普及,苦心于培养新一代实业家,设立女子教育奖励会以支持女性教育。其创办和支持的学校、教育团体近200个,其中最早、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积极筹集资金在1875年与他人共同创办的“商业讲习所”。该讲习所是当时日本的第一所商业学校(鹿岛茂,2014)[2]。涩泽荣一在其丰富多彩的企业家生涯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儒商思想和儒商人格风范。
共处于儒家文化圈,张謇与涩泽荣一的儒商思想皆植根于儒家伦理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共通性,但由于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经历等方面的不同,两者的儒商思想必然存在不同之处。
三、张謇与涩泽荣一儒商思想的核心观点
(一)儒商人格观:“言商仍向儒”与“士魂商才”
张謇与涩泽荣一都强调工商兴国,主张通过发展工商业来实现国富民强。由于自幼饱受儒家道德思想的熏陶,相似的文化背景使两人在商人人格的塑造上,有着极其相似的主张,分别提出了“言商仍在儒”与“士魂商才”的理念。
张謇主张商业和实业救国,并认为应按照儒家道德思想来规范商人的经营活动,反对为了私利而背弃仁义道德。面对风雨飘摇、苦于内忧外患的中国,张謇认为,“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中国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张謇,1994)。在张謇看来,自己从事商业并非为了一己私利也不是迫于生计,而是在国家备受外辱、国力衰微的现状之下,唯有兴办实业才能实现救亡图存的抱负,“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王敦琴,2013)。同时,张謇坚信若要拥有高尚人格,绝不能缺失仁、义、礼、智、忠、孝、信、悌等儒家道德伦理。因此,应将追求资本主义之利的实业活动同崇尚儒家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对此,张謇主张“言商仍向儒”。他指出:“吾国人重利轻义,每多不法行为。不知苟得之财,纵能逃脱法律上之惩罚,断不能免道德上之制裁”(张謇,1994)。在张謇看来,创造财富、求取利润应符合经商之道和做人的道义,从商道德是保证企业经营活动最终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涩泽荣一对日本工商业者理想的道德人格提出了自己的标准,这就是“士魂商才”。涩泽荣一认为,“士魂商才的真正意义,就是要具有卓立人世间所必备的武士精神,但仅有武士精神而无商才的话,在经济上又会招来灭亡之运,故有士魂尚须有商才”(涩泽荣一,1994)[3]。在此,所谓士魂是指受到《论语》所滋养,集正义、廉直、侠义、勇为、礼让等美德为一体的武士精神。而真正的商才“原应以道德为本,舍道德之无德、欺瞒、诈骗、浮华、轻佻之商才,实为卖弄小聪明、小把戏者,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商才”(涩泽荣一,1994)。虽然一些工商业者觉得经商之道与武士精神并无关系,但在涩泽荣一看来,士魂和商才两者并不矛盾甚至缺一不可。而且无论是滋养士魂还是培养商才,归根到底都需要从《论语》中得到教诲和启发。“士魂商才”的核心是道德的完善,一个商人要想成功,首先要有高尚的品格,有了高尚的品格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涩泽荣一将“士魂商才”确定为日本商人的理想人格,为日本商人的经济活动设定了一个高尚的动机:经商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一己的私欲,而是为了实现理想人格;商业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为了日本国家和民族的兴盛;经商不但同塑造理想人格没有矛盾,而且还是实现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径。通过这种论证和阐释,涩泽荣一确立了经济发展在价值观上的合理性。
(二)义利观:义利两全
义利之辩,即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关系的问题,是从古至今各个国家的企业家和经济思想伦理学家在工商业发展过程中一直关注的现实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辩历经千年,积累了丰厚的遗产。张謇与涩泽荣一的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形成了相似的义利观。
在义利之辩的问题上,张謇提出了“非私而私也,非利而利也”(张謇,1994)的看法。他认为,企业家创办实业的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富国致强的大义,而不是为了追求私利,虽然非出于主观意志,但是从结果上看又能给自己带来经济方面的利益。张謇强调了义的重要性。他认为,“然以不信不义之国人,而冀商业前途之发达,是则大车无輗,小车无軏之行矣”(张謇,1994)。对他来说,信义是商业前途发达的保证,缺之则不能前行。同时张謇也认为,“据正义言之,其可以惶惶然谋财利者,唯有实业而已,此又鄙人兴办实业之念所由起也”(张謇,1994)。显然,张謇虽然忠实于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却并非排斥利益,而是提倡以义取利。
在主张工商立国的思想指引下,涩泽荣一又提出了“利与义合一”的观点。涩泽荣一用《论语·里仁》中“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得之,不处也”(程昌明,2000)所表达的思想来支撑其利义合一的主张。涩泽荣一认为,不应当反对人们的求富欲望,而应当提倡人们去学习和掌握用道德的方法去追求利益的本领。他指出,“我对物的追求,如果没有极大的欲望和相当可观的利益——我是绝不会着手进行的……只求在实业界获得发展,这才是增产逐利的本分。若全然不顾及此道,则国富难成。因此,若问致富之根本何在?则当以仁义道德、公正之理为本,舍之,所求之富则不可能持久”(涩泽荣一,1994)。因此,在涩泽荣一看来,离开义的利必不长久,离开利的义流于空谈。传统儒家思想中虽然承认义利统一,却并不从正面来论证求利的正当性,而是认为对求利必须加以限制。如果过分强调义而造成了贬低功利的结果,以至于形成义利截然对立的观念和耻言功利的社会心理,就会对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对于以往人们对于儒家思想中“仁则不富、富则不仁”的误解,他认为,“孟子也主张谋利与仁义道德相结合,只是后来的学者将两者越拉越远,反说有仁义而远富贵,有富贵则远仁义”(涩泽荣一,1994)。“所谓实业,无疑以谋求利殖为本旨。若商工业无增殖之效,商工业即无存在的意义……但所谓图利,如果全为一己之利,根本不顾他人,那又不然了……真正的利益,若不基于仁义道德,则决不可永续”(涩泽荣一,1938)。涩泽荣一指出,“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于道德有亏”。在涩泽荣一看来,所谓仁义,除忠君爱国、国益为先之外,还包括博爱、诚实、信义、节俭、勤劳等品德。
涩泽荣一引用了大量《论语》中具有古典性的“仁、义、利”等概念进行论说,从而将传统的“义利之辨”提升到了“公私关系论”。他认为,应将从事商业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分为公益和私利两种不同的利。公益就是“超越私利私欲观念,出于为国家社会尽力之诚意而得之利”(周见,2004),“推动真商业的不是私利私欲,而是公益公利”(周见,2004)。因此,在涩泽荣一看来,商业经营表面上是“私益私利”,实则是“公益公利”,资本主义的本质不是“私”而是“公”,所有的利益都应该是“公益”。公益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以公益为利就是以国家社会的利益为目的从事工商业活动。他指出“所谓公益与私利本为一物。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若非可为公益之私利,即不能称之为真正之私利。商业的真正意义也就在于此。是故我主张,从事商业的人都不应误解其意义,应专营可致公益之私利,因这不仅可带来一身一家之繁荣,且同时可致国家之富裕,社会之和平”(涩泽荣一,1977)。显然,涩泽荣一的公益与私利合一的理论不仅调和了传统观念中私利与公益相冲突的矛盾,而且强调了“专营可致公益之私利”是实现个人和国家富裕与和平的动力。
(三)竞争观:“不争·让利”与“其争也君子”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受中国儒家文化的深厚影响,早期的张謇赞同和为贵的思想,有时甚至倾向于以“不争”和“让利”去实现“仁”的道义。张謇曾多次对世人阐释过“大同”的概念,他坚信世界最终将走向大同。只是张謇所提倡的世界经济大同不是通过激烈的竞争来实现,而是以和平共处、国际合作的方式来达到的。张謇指出:“欧战告终,华府会议之后,世界未来大势,骎骎趋于大同。而就实业论,亦有不得不趋向大同之势,此察究世变者类能道之。”由此可见,张謇更为强调的是实业的大同之势,而忽略了实业竞争的重要性(张謇,1994)。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后,因年年盈利,吸引了许多其他商人准备到南通开设新厂。张謇得知后,连连上书上海商务总会,请求总会劝止其他商人增设新厂。张謇认为:“窃维工商实业,无不以统系而成,以倾挤而败”(张謇,1994)。由此足见张謇反对工商业之间的无序竞争。民国成立后,因为接触到日本、西欧一些比较先进的理念,张謇开始吸收西方的进化论思想,重新赋予儒家思想一些现代意义,如竞争意识和竞争精神。他指出,“国与家相消息而维系者也,国积民,家积族。民不竞不智,不智故日安于惰而流于弱,弱故外侮得而乘之;族不竞不才,无才故日离于独而澌于微,微故强宗得而藐之。是故善谋国者,必智其民;善谋宗者,必才其族。智之才之道,必使不惰而奋于勤,不独而萃于群。群生竞力,勤生竞心,而国乃存,而家乃兴。必常有新家,而后能常有旧国”;“士竞学,农工商竞业,而天下乃无不大之族,无不昌之国”(虞和平,2004)。不过,比起农工商企业间的竞争,张謇认为竞争观的重心在于教育与学问方面,他认为:“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之竞争也,农工商之竞争,学问之竞争。”(虞和平,2004)张謇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和提升人们的竞争意识和竞争力,只有培养出大批科技与实业人才,在“学问”上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追上世界进步的潮流。他办实业与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具有高文化素质与技能的人才,并源源不断地输入企业中去,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服务,更多更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
早在日本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涩泽荣一就认识到了竞争的重要性。他指出,“国家要取得健全地发展,无论在工商业,还是在学术技艺,抑或是在外交方面,都要经常保持与外国竞争必胜的信念,这不仅适用于国家,个人也应如此,若经常有劲敌树之左右,却没有与该敌竞争且必须胜出的气概,就绝对不会取得发展进步”(坂本慎一,2002)。另外,在强调竞争的重要性的同时,涩泽荣一指出,竞争具有善意和恶意之分。他认为,“对所有的行业来说,竞争都是必要的,有了竞争,才能激发勤奋的动力。所谓‘竞争乃努力与进步之母’固然是实情,但竞争还是有善意和恶意两种类别的……如果竞争的性质不善的话,虽然有时会使自己得到许多好处,但多半是既妨害他人,也会最终让自己蒙受损失。而且,此弊病不只限于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而已,有时也将祸延整个国家”(涩泽荣一,1994)。虽同为竞争,但善恶相异必然会给企业乃至社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涩泽荣一竭力劝解商人尊重彼此间的商业道德,努力从事善意的竞争,尽量避免恶性竞争。他的这种竞争观念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建构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也提升了企业的内在凝聚力,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奠定了文化基石。
(四)社会责任观:谋利与反哺的平衡
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在利用其享有的权利与社会资源来牟取利益的同时,理应承担相应的慈善责任,做到牟利与反哺的平衡。张謇与涩泽荣一在从事商业活动时都怀着儒家传统道德的仁爱之心,并积极从事各种慈善公益活动。
张謇怀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从事实业经营的同时,兴办了大量的慈善事业及社会公益事业。张謇的人道主义思想,首先来自儒家传统仁爱思想的影响;其次,他自幼生长在穷苦农家,深知民间疾苦与生活的艰辛,由此产生的对弱者的同情心、悲悯心又成为其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基础;再次,张謇通过访日,以及同英国传教士的接触,受到了近代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慈善事业与近代西方慈善事业在观念、做法上的差异,了解到西方近代慈善事业更为注重的是“教”而不是“养”,即所谓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只有教会受助者足以独立生活的技能,才能使他们真正脱离贫困,从而发挥慈善事业最大的作用。在其开办的大生纱厂取得较高收益之后,张謇开始积极兴办各类慈善公益事业。从1903年到其逝世的二十年间,共办有育婴堂、养老院、医院、贫民工场、残废院、盲哑学校等16所(王敦琴,2013)。其中尤以盲哑学校的设立最能体现张謇主张“教”与“养”的慈善观点。张謇在清末创办各类学校的时候,认识到了盲哑人教育的重要性,在领头创办盲哑学校的同时,也呼吁社会发展盲哑人教育事业(虞和平,2004)。
涩泽荣一认为,工商企业者在坚持诚信、善意竞争的同时,还应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他指出,“如果富豪之士妄想漠视社会,以为他离开社会,亦能维持其财富,对公共事业、社会公益弃之不顾,则富豪与社会大众必然发生冲突。不久,对富豪的怨嗟之声就会转化成社会的集体罢工罢市,其结果将给富豪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一个人在谋取财富的同时,也要常常想到社会对他的恩义,勿忘对社会尽到道德上的义务”(涩泽荣一,2007)。这里,涩泽荣一所指的义务,主要是实业家在获得利润后回馈社会和国家,促进社会进步的义务。
涩泽荣一在成功创办众多企业的同时,不忘为日本社会福利事业做出贡献。涩泽荣一在弃官从商的第二年(1874年),开始任职东京会议所会长,并由此参与到东京福利院的发展建设当中,之后在1876年担任东京养育院的事务局长,并于1885年开始担任院长。此外,涩泽荣一还清醒地认识到,要搞好社会福利事业,首先需要的是资金,若想成就义举、把开展慈善活动长久地办下去,高超的经营手腕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涩泽荣一为了维持福利院的正常运作,巧妙地利用鹿鸣馆时代上流社会女性们的虚荣心,在鹿鸣馆、华族会馆以及歌舞伎座等场所举行慈善义卖,并将义卖的收入全部捐献给了福利院。
四、张謇与涩泽荣一儒商思想的差异性
(一)对儒商人格塑造的出发点不同
虽然涩泽荣一与张謇的商人人格观都强调了商人从商必须按照儒家的道德思想来规范自身的经营活动,而且都为其理想中的商人人格提供了相似的画像,但两者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张謇的“言商仍向儒”是基于商人人格的完善和道德自省的基础而提出的,其目的是要求商人在从商的同时保持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思想;与张謇不同,涩泽荣一的“士魂商才”论是为日本商人提供一个理想人格的参照系,为日本商人的经济活动提供一个高尚的动机,其目的是纠正当时日本盛行的轻商、贱商观念,为商业活动的正当性正名,并以此确立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价值观上的合理性。因此,从出发点来看,张謇的商人人格观是维护儒家道德的人格观,而涩泽荣一的商人人格观则是借用了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来说明日本国民从商正当性的人格观。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角度来看,张謇的商人人格观在论证其主张的工商实业救国方面是不彻底的,并未摆脱其根深蒂固的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思想桎梏;相反,涩泽荣一的“士魂商才”则要彻底得多,不仅有利于为其“商工立国论”提供思想基础,而且也为日本国民从事工商业活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道德规范。当然,也应该看到,涩泽荣一的“士魂商才”也继承了日本宗教神道文化体系中以“大和魂”为根基的武士道义。武士道强调以“死身”来义勇奉公,从这种盲目效忠的封建思想中衍生出的极端民族主义又成为日本财阀与军国主义相互勾结的思想基础。因此“士魂”虽在商业上起到了规范商人经营活动的道德指导作用,其也存在一些不可辩驳的负面意义。故作为实业界领袖的涩泽荣一不仅致力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也极力鼓动日本的对外经济扩张。在鼓动日本对外经济扩张的过程中,涩泽荣一提出了“日中经济同盟论”。涩泽荣一指出:“就我帝国政治经济的将来而言,现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中国提供原料,日本进行原料加工,并用以满足中国的需要,这完全符合互通有无的经济原理。”另外他还指出:“从地理上和历史关系上说,我国都必须成为东洋之盟主,以开拓清、韩之文明……战后欧洲列强皆更着眼于东洋,拼命扩张其商权,而我国有鉴于此,当更明确意识,我国不但须在利权竞争上不弱于彼等,还需更进而超出一头。”显然这一主张类似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其真实目的在于推动日本对华的经济扩张,确保日本的原料来源及海外市场,确保日本在亚洲地区的霸主地位,成为能够抗衡西方列强的强国(周见,2015)。在1876年日朝修好条约签订前后,涩泽荣一积极推动第一国立银行面向朝鲜进行经济扩张,并于1878年开设了釜山支行,后又陆续在元山、仁川设立了办事点,负责征购沙金、缔结关税条约及银行券的发行。第一国立银行的一系列活动都成为日本政府推动对朝经济侵略的支点,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朝鲜的殖民地化(岛田昌和,2011)。由此可见,涩泽荣一的经济扩张主张已经与其儒商思想背道而驰。
(二)义与利的侧重点相异
虽然张謇与涩泽荣一都主张“义利两全”,但两人对义与利的侧重却是存在差异的。张謇利义两全观的侧重点是义,而且,这里的义是救亡图存的大义,求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义。因此,他的利义两全可以理解为重义而求利。而涩泽荣一的义利两全观是以利为重心的,但他同时强调,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追求私利必须建立在博爱、诚实、信义、节俭、勤劳等品德的基础上。只有坚守儒家道德的义,才能在工商业活动中持续获利。因此,他的利义两全可理解为求利而重义。
张謇和涩泽荣一的义利观都是建立在其对宋代程朱理学的批判和全面恢复孔孟之学的主张基础之上的。但张謇的“尊孔”是为了还原孔子儒家思想的本来面目,纠正宋儒曲解孔孟思想的不切实际之词,而并非对当时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轻商思想进行批判。作为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张謇内心对商人从事商业活动是轻视的。在创业活动遇到困难时,仍将与商人为伍称作“伍平生不伍之人,道平生不道之事”(张謇,1994),并始终“耻言货殖之利”。而涩泽荣一批宋儒、尊孔儒的目的是借助对孔子义利之辩的分析来说明利用正常手段获取利益是不违背仁义的,并以此说明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正当性和重要性,呼吁全社会重视工商业的发展。
(三)竞争意识维度上的不同
从张謇的竞争观的演变过程来看,早期的张謇并未摆脱中国儒家思想中和谐文化的影响,主张以“和为贵”为理念来发展工商业和振兴实业。后来虽然受西方进化论的影响,张謇强调竞争意识和竞争精神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兴办教育来培养和提升人们的竞争意识和竞争力,进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但是,其对竞争的认识仍停留在个人、企业、民族、国家应具有竞争意识和竞争精神这一意识层面,并未上升到该如何构建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通过有序竞争来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进而增强国家实力的这一高度。
与张謇不同的是,涩泽荣一再强调竞争意识对国家发展和个人进步的重要性的同时,强调了尊崇商业道德,从事善意竞争、避免恶意竞争的重要性。涩泽荣一认为,“竞争也有善与恶,这里我把它分为善意竞争与恶意竞争两大类别。比如,每天早上比别人起得早,发奋学习,在智力和上进心方面超过其他人,这就是善的竞争。但是,如果以仿冒、掠夺的方式,将别人努力所得来的劳动成果拿来当作自己的,或以旁门左道的方式来侵害他人,这就是恶的竞争……我建议,努力从事善意的竞争,尽量避免恶意的竞争。所谓避免恶意的竞争,也就是尊重彼此的商业道德”(涩泽荣一,2007)。因此,从维度上讲,涩泽荣一的竞争观不仅强调了竞争意识,更指出了商人和企业如何实现有序竞争的途径。
(四)谋利与反哺的轻重差异
在张謇看来,企业是他实现自己社会理想的手段,是谋利的工具。为了筹集大量资金实现自己救民、富民、育民、护民的社会理想,只有选择创办可以名正言顺谋利的实业。正如他所言,“据正义言之,其可以惶惶然谋财利者,唯有实业而已。此又鄙人兴办实业之念所由起也”(张謇,1994)。所以对于张謇而言,反哺社会才是企业谋利的意义所在。正因为如此,虽然张謇一生中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成绩斐然,功不可没,但其慈善公益事业均以自费的方式支撑。由于资金投入巨大,经常造成经费短缺的问题,从而给他的实业经营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可从1925年张謇在对自己和家族的地方自治业绩及其投入情况的总结中窥见一斑:“今结至本月计二十余年,除謇自用于地方,及他处教育、慈善、公益可记者,一百五十余万外,合叔兄所用已二百余万;謇单负债,又八九十万。”(张謇,1994)
涩泽荣一则将企业自身发展看作是实现自己社会理想的目标,成为一名能够成功经营企业的商人就是其最高理想。他认为企业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企业应该先将重心放在自身发展之上,利用企业利润扩大再生产,等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拥有余力时再反哺社会,也更有能力将其持续下去。涩泽荣一在担任东京养育院院长后,养育院多次因资金短缺导致运营困难,几度面临停办。但涩泽荣一利用第一国立银行的资金购买国债和公司债券所获利息来维持养育院运营的方法,使其经营状况得以好转(周见,2015)。
五、儒商思想的差异性与中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观
前述表明,张謇和涩泽荣一的儒商思想在商人人格、义利观、竞争意识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类似性,但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虽然反映的是张謇和涩泽荣一两人主观上对从事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认识的不同,但客观上也反映出当时两国对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和路径选择的不同,从而也导致了两者儒商思想对后世影响和结局的不同。
张謇和涩泽荣一所处的时代都是中日两国由封建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转型,同时面临西方列强入侵的特殊时期。面对经济社会转型和西方发达国家入侵的压力,当时,在两国都出现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工业化来实现富国强兵、抵御外来侵略等思潮,并提出了相应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观,如中国洋务运动思潮的代表者提出的“中体西用”观和日本提出的“和魂洋才”观。两种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观在倡导学习近代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文明和经济制度、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但在如何学习、学习的侧重点及目的方面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也是导致张謇和涩泽荣一儒商思想形似而神不似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洋务运动思潮的代表者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虽然强调了中西二学相需并举,不可或缺,但在处理两者的关系上,则认为应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心身,西学应世事”。因此,在洋务运动的代表者看来,尽管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非常必要,但应坚持以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文化意识形态作为根本。尽管西学包括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但西学只能置于“辅”的地位。学习西学的目的是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教制度来完善和巩固中学体现的封建统治制度,或者是利用西学来培养个人适应世事、善于变通的能力。
由日本幕府晚期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提出的“和魂洋才”在强调学习和了解西方先进技术的必要性的同时,更明确指出,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物态文化,也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法律和教育制度等意识形态文化,而且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即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文明制度时,应坚持东方的道德观念。佐久间象山认为,东洋文化道德与西洋文化两者之间是调和共存的,不存在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问题,而应该是经纬交织、相互钩贯的。这里的“东洋道德”是包含了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在内的、适应当时经世致用思想的日本民族精神,即日本人所拥有的伦理观、道德观、审美观和价值观,如强调对领主忠诚的日本佛教理念、“利义两全”的日本价值观等。
从上述中日两国“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两种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观来看,主张“中体西用”的中国思想家对于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认识是保守和不彻底的,其出发点是维护既有的封建制度或完善个人的能力和修养;而倡导“和魂洋才”的日本思想家对于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工商业制度采取的是兼收并蓄的态度,其出发点是在坚持东方道德观念的基础上,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也正因为如此,基于“中体西用”观的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而日本基于“和魂洋才”观的明治维新则取得了成功,并最终促使日本在19世纪末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大国。
身处那个时代的张謇和涩泽荣一,其儒商思想显然受到了当时各自国家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观的影响,两者儒商思想在外在内容上的相似性和实质内涵上的差异性,导致了两者在社会影响和结局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