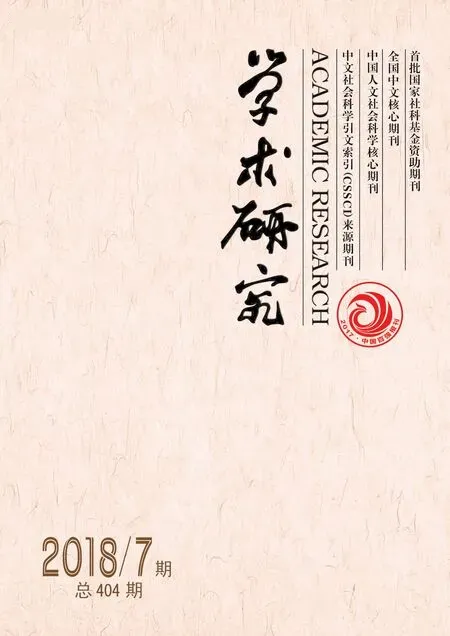一种文体生成论
——“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的再思考*
2018-02-20陈民镇
陈民镇
刘师培曾于《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一文中提出“文学出于巫祝之官”的著名论断,全文如下:
《说文》“祠”字下云:“多文词也。”盖“祠”从司声,兼从“文词”之“词”得义。古代祠祀之官,惟祝及巫。《说文》“祝”字下云:“祭主赞词者。(《辅行记》第七之四引作:“祭主申赞辞者也。”)从示,从几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巫”字下云:“巫,祝也。又曰,古文巫如此。”案古文“巫”字,盖从两口,即《周易》“兑为口为巫”之义。虞翻注《周易·大有》云:“《大有》上卦为兑,兑为口,口助称祐。”口助者,神之职也。与《说文》“祠,多文词”之谊,互相诠明。盖古代文词,恒施于祈祀,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今即《周礼》祝官执掌考之,若六祝六祠之属,文章各体,多出于斯。又颂以成功告神明,铭以功烈扬先祖,亦与祠祀相联。是则韵语之文,虽匪一体,综其大要,恒由祭祀而生。欲考文章流别者,曷溯源于清庙之守乎?①刘师培:《左盦集》卷8《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83页。原载《左盦集》,1910年直隶木刻本。
“文学出于巫祝之官”既是在讲文学的发生,也是在讨论文体的发生,可视作一种文体生成论。该文论述简略,且不无可商之处;其结论富于启发意义,但有待进一步的补苴与论证;其结论又多遭后人误读,有待厘清。出土文献所提供的新材料与新认识,为我们重新考察“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这一命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以下试作考论。
一、“祠”“祝”“巫”训释之失
刘氏是从“祠”“祝”“巫”诸字的字源切入讨论的。仅从个别字的字源入手,很难说具备充分的论证力度,这自然与该文作为学术札记的性质有关。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刘氏对相关字的解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有必要加以辨析。
首先看“祠”字。刘氏据《说文》“多文词”的说法,认为“祠”从“词”得义。“祠”为祭名,尤指春祭。祭祀确实需要文词相伴随,但说“祠”从“词”得义并无确据。甲骨文中已见及“司”,有的辞例可读作“祠”或“祀”。目前所见明确的“祠”字可追溯到春秋晚期。至于“词”字,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目前的材料只能追溯至战国。①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96页。尽管“祠”“词”存在同源的关系,但“祠”从“词”得义的说法并不能得到古文字材料的支撑。相反,“司”“祠”在前,而“词”系后起。如此一来,刘氏对“祠”的字源解释,难以作为“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的论据。刘氏之所以强调“词”,这是因为他将“词”与“文”等同,视作韵文之类的纯文学,而与“笔”相对。②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9页。《中国中古文学史》1920年初刊于北京大学。刘氏所谓“文学出于巫祝之官”,实际上是“韵文(词/文)出于巫祝之官”。
刘氏指出职掌祠祀的王官主要是祝和巫,故继而讨论“祝”与“巫”的字源。刘氏引述《说文》之说,但《说文》中无论是“从人口”的解释还是“从兑省”的提法,都不正确。甲骨文中“祝”作(《合集》27082)或(《合集》32671)、(《合集》15280),象人跪于地上或跪于神主之前祝祷之形。到了西周,“祝”字所从逐渐由跪坐人形变为站立人形,与“兄”混同,如清华简《程寤》简2的“祝”便写作。许慎由于没有掌握较早的文字材料,因而他对“祝”的解释并不准确,将其与“兑”相混,乃至拆解为“人”“口”两部分。《说文》所引《周易·说卦》“兑为口”“兑……为巫”,讲的是易卦的搭配与演绎,也与“祝”“兑”“巫”的字源无关。刘氏在此基础上的发挥,自然也便难以达到论证的效果。
刘氏据《说文》,认为古文“巫”字从两口,即《周易》“兑为口为巫”之义。所谓“兑为口为巫”,与“巫”的字源解释无关。而所谓的从两口之形,仅见于《说文》《汗简》以及《古文四声韵》中的“传抄古文”,尚未在出土材料中发现。甲骨文的“巫”字作(《合集》36511),象某种法器,西周金文延续这一字形。到了战国,“巫”字中间长横以及两个短竖发生变化,如侯马盟书写作,此后的字形基本延续这一线索。晋系的侯马盟书已经出现的字形,而楚系竹简中,也出现了天星观1号墓卜筮简所见、清华简《程寤》简2所见以及望山1号墓简119所见等字形,三体石经《君奭》所见亦可参看。可见,战国时期的“巫”字出现增益“口”形的现象(不见两“口”的字形),但增益“口”是战国文字的一种常见现象,通常没有特殊涵义。有的“巫”字还在上方添加横线,这也是战国文字的常见饰笔,并无特别的意义。除了增益“口”形,楚文字的“巫”还增益“日”形。无论如何,增益“口”形的现象无关“巫”的本义,而是后起的构形,并不能据此说明巫官与文词的关系。
尽管刘氏的字源分析并不准确,但他所提出的“古代文词,恒施于祈祀,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的论断颇值得我们重视。如果一定要从字形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祝”字象祝祷人物之形,而祝祷这一行为自然需要文词参与。至于强行拆解出“口”之类的构件,则很难说合乎古文字本身的发展规律。
二、从官守论到泛巫论
刘师培持“古学出于官守”的官守论,并以此解释中国文学的发生。这一论调虽然未必全面,但不无合理之处。与此相关的泛巫论,既曲解了刘氏的官守论,也歪曲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形。
刘氏所说的“巫”“祝”,指的是巫祝之官,属于王官,而非广义的巫觋。“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需要与其“古学出于官守”论结合起来考察。“古学出于官守”是刘氏的一个重要观点,具体而言,他认为古代学术出自官守(尤其是史官),六艺、九流、术数、方技均出于史,③参见刘氏《古学起原论》《古学出于史官论》《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古学出于官守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说》诸文,见氏著《左盦外集》卷8、卷9,《刘申叔遗书》。远祖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而近承章太炎“诸子出于王官说”。①朱维铮:《导言》,刘师培:《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8页。刘氏重申《汉书·艺文志》及章学诚、章太炎诸氏的论点,强调学术出自王官,文学也出自王官。在《周末学术史序·文章学史序》中,他认为后世“文章”多源自墨家与纵横家,而墨家出自清庙之守,工于祷祈,其文尚质,以理为主;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工于辞令,其文尚华,以词为主。②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文章学史序》,《刘申叔遗书》,第526-528页。原载《国粹学报》第1-5期,1905年2月23日至6月23日。除了同样将文学追溯到“清庙之守”,还强调行人之官对于文学的影响。
《文章学史序》中的文学观与刘氏其他文章中的文学观看似有所矛盾,实则有内在的理路。这便涉及刘氏对“文学”的界定。在刘氏眼中,“文”与“文章”是不能等同的:“盖‘文’训为‘饰’,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故道之发现于外者为文,而言词之有缘饰者,亦莫不称之为‘文’。古人言文合一,故借为‘文章’之‘文’。后世以‘文章’之‘文’,遂足该‘文’字之界说,失之甚矣。”③刘师培:《论文杂记》,《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第118页。原载《国粹学报》第1-10期,1905年2月23日至11月16日。刘氏主张只有“韵语俪词之作”才合乎“文”的本义,④刘师培:《论文杂记》,《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第119页。“‘文’也者,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由古迄今,文不一体。然循名责实,则经史诸子体与文殊,惟偶语韵语体与文合”。⑤刘师培:《文说·耀采篇第四》,《刘申叔遗书》,第707页。他认为狭义的“文”主要是韵文,来自于古代的“文言”,是注重声韵、对偶和藻饰的文字,这与《文心雕龙·总术》“有韵者文也”⑥[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55页。的观念是相符的。刘氏的文学观受其乡贤阮元影响颇深,每言“阮氏《文言说》所言,诚不诬也”。⑦刘师培:《论文杂记》,《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第112页。而“文章”的概念,则包括韵文和散文,《文章学史序》所讨论的是“文章”。在《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一文中,所谓“文学”,指的主要是韵文。有学者认为刘氏树立起了广义的文学观,⑧黄春黎:《刘师培文学起源观考论》,《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实际上,刘氏恰恰过于强调狭义的文学,甚至将文学局限于韵文,认为有韵之文“别于六艺九流之外”,⑨刘师培:《论文杂记》,《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第114页。这种以后律前的做法很难说合乎先秦杂文学的实际情形。究其因由,在于他从中古时期文笔之分的观念入手,进而将文笔之分的认识贯彻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他虽然注意到先秦“文”的多义性,但仍认为韵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
刘氏基于官守论的文学发展观并非没有可商之处。他认为“墨家之学,远宗史佚,复私淑史角所传。史为宗伯之属官,与巫卜祝宗并列”,⑩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文章学史序》,《刘申叔遗书》,第527页。又认为墨家出自巫官,⑪总之即《汉书·艺文志》所称的“清庙之守”。⑫刘氏极为强调史官在古代思想史中的地位,然而,在处理史官与巫祝之官的关系时,往往纠缠不清,对墨家来源的认识即是如此。而且,刘氏既然认为韵文出自清庙之守、巫祝之官,墨家由其派生,而墨家之文却偏偏质木无文,这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刘氏还强调诗赋之学出自行人之官以及由行人之官派生的纵横家,⑬这是从诗的外交作用以及赋的铺排特征出发的。但诗赋本身可以归入韵文,而刘氏又强调韵文出自巫祝之官,这显然是前后龃龉的。
刘氏“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影响颇广,但后人对刘氏的观点多有误解,如其所谓“文学”,指的是韵文,而非一切文学;其所谓“巫祝”,指的是巫祝之官,而非一般所说的巫觋。不少人误读了刘氏的观点,而由此衍生出的泛巫论,倾向于将中国上古文化的种种现象归为巫觋的创造,将人文理性已甚发达的三代文明视作巫风缭绕的社会,甚至将禹、汤、周公、孔子、屈原等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一概视作大巫。譬如在清华简《耆夜》刊布之后,有学者据此指出周公系巫祝。①付林鹏:《由清华简〈耆夜·乐诗〉看周公的巫祝身份》,《中国文物报》2010年8月20日,第6版。然而《耆夜》全篇围绕饮至礼展开,其核心为“礼”,周公作为饮至礼的“主”,其后又摄周政,绝非“巫祝”的身份所能涵盖。仅仅据周公赋诗、劝侑等行为便判断周公为巫祝,不免有过度推论之虞。此类看法由来已久,与泛巫论的倾向密切相关。
弗雷泽(J. G. Frazer)在其名著《金枝》中曾提出“巫术时代”先于“宗教时代”的论断,②J. G.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25, pp.56-60.这一具有浓郁单线进化论色彩的观点虽很早便遭致马林诺夫斯基(B. K. Malinowski)等更注重实证的人类学家的批评,却在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譬如有学者将夏商周三代归纳为“巫觋时代”“祭祀时代”“礼乐时代”三个阶段,③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1页。有学者分为“神”职历史时期、“巫”职历史时期以及“史”的历史时期三阶段,④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45页。或作“巫术时代”和“数术时代”的二分,⑤陶磊:《从巫术到数术——上古信仰的历史嬗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再如不少论者将晚起神话视作“巫术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活化石”,⑥晁天义:《“巫术时代论”影响下的中国古史研究》,《求是学刊》2005年第1期。均存在将复杂现象简单化乃至混淆讨论对象时代性的情况。而另外一种倾向是,将“巫术时代”的时代范围无限扩大,乃至于将商王视作大巫、将占卜视作商王朝的头等大事乃至于全部政治内容。⑦陈梦家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商王系“群巫之长”,参见氏著《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李宗侗认为上古时期“君及官吏皆出于巫”,参见氏著《中国古代社会史》,台北:华冈出版社,1954年,第118页。张光直指出商王即是巫师,参见Shang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192-194; Art, Myth,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44-45。如若寻绎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历程,这些看法很难说合乎实际。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贫富的分化乃至阶层的分化,公共权力以及国家机构也便应运而生。在此过程中,弗雷泽在《金枝》中所强调的“公众巫术”发挥了关键作用。有论者认为《国语·楚语下》所载观射父的著名论述中“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⑧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14-515页。指的是“个体巫术”的时代,而颛顼“绝地天通”则标志着“公众巫术”的出现。⑨江林昌:《诗的源起及其早期发展变化——兼论中国古代巫术与宗教有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但细味文本,在“少皞之衰”之前便已是一个“民神不杂”的时代,彼时不但有巫、觋之职,还有祝、宗等王官,即所谓“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总体而言,观射父的这段话可分为五个层次:先是追溯“古者民神不杂”的时代,巫、觋、祝、宗等各司其职;第二阶段是少皞氏衰落的时期,九黎之乱导致“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前一个阶段所建立的秩序遭到扰乱;第三阶段是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使复旧常”,重新恢复到第一阶段的状态;第四阶段是尧舜至夏、商的漫长历史时期,大致维持颛顼“绝地天通”后的状态;第五阶段是西周末年、宣王之世,重、黎之后“失其官守”。这段话固然是中国早期宗教观念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王官地位变迁的缩影。《楚语下》中提到的“巫”“觋”已经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巫”,而是属于王官,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宗教祭祀的权力实际上被中央王权所垄断,具体的操作者为王官阶层。不少学者将中国商代之前甚至殷商一概描述为巫风缭绕的社会,这种泛巫论或者“萨满主义”由于脱离中国古史的语境而遭致饶宗颐、李零等的批评。⑩饶宗颐:《历史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作反思与检讨——“巫”的新认识》,中华书局编:《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华书局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96-412页;李零:《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页。饶先生在反思“萨满主义”的同时,强调以“礼”来代替“巫”。“礼”的起源虽与巫术或原始宗教有密切的关系,但成熟后的“礼”与“巫”已经不能同日而语。自中国文明产生以来,“礼”已经成为中国文明的主线,祝、宗、卜、史、巫等王官的司职,也需要纳入到“礼”的视野中考察。
泛巫论所称的“巫”,也未必等同于中国古代的“巫”。①张光直意识到wizard、witch、sorcerer、soceress、magician等西方词汇与“巫”的区别名,因而使用了源自通古斯语的saman/shaman一词。陈来也指出:“我们并不预设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巫’即完全等同于人类学家所说的巫术的施行者(Magician),也不预设‘卜筮’就是巫术。”参见氏著《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20页。美国学者梅维恒(V. H. Mair)也反对将“巫”等同于“萨满”,他在饶宗颐的启发之下对“巫”的语源展开研究,认为汉语“巫”来自原始印欧语,参见氏著 “Old Sinitic *Myag, Old Persian Maguš, and English ‘Magician’”,Early China, vol. 15 (1990),pp. 27-47.中国文明不像有的古代文明一样长期政教不分,甚至教权凌驾于政权,而是世俗王权很早便统摄专职化的巫觋阶层。李泽厚认为巫的特质在中国“大传统”中以理性化的形式坚固保存、延续下来,②李泽厚:《己卯五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第40-43页。不过李氏将中国古代文明的理性化估计得过迟,而且过于强调所谓的“巫史传统”(Shamanism rationalized)。除了一部分巫觋继续在“小传统”中存在,还有的巫觋进入了“大传统”,成为王官。《尚书·君奭》云:“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③[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3页。“巫咸”“巫贤”的构名与前文的“保衡”等一样,当是“职官+私名”的格式,巫咸、巫贤俱是担任“巫”一职的官员。巫咸也见诸清华简《楚居》。清华简《程寤》简2记载文王受命时使“灵名总祓,④整理者读作“俾灵名凶,祓”,此从孟蓬生说。参见孟氏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清华简〈尹至〉、〈尹诰〉研读札记》(2011年1月5日)一文下评论。祝忻祓王,巫率祓太姒,宗丁祓太子发”,⑤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36页。这里“巫”与“灵”“祝”“宗”一样,均为职官。《楚辞·九歌·东皇太一》王逸注:“灵,谓巫也。”⑥[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6页。“灵名”指名叫“名”的“灵”,以下“祝忻”“巫率”“宗丁”等均为“职官+私名”的形式。从《程寤》看,巫、灵与祝、宗一道负责“祓”。祝、宗、卜、史当具有同源关系,在分化并司职王官之后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东周以降,王官下移,“巫”的地位下降,有向“小传统”转移的趋势。
《楚语下》并没有涉及“前王官时代”(王官出现之前的时代),在出现国家、进入文明社会之前,自然不会存在王官。尽管我们难以用“巫术时代”这样的术语来指称“前王官时代”,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在王官出现之前,巫术与原始宗教应已存在。刘师培并没有考虑到“前王官时代”,而是直接将文学追溯到巫祝之官。在我们重新审视其“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时,不妨将视野放宽至“前王官时代”,也将考察对象扩展至巫祝之官以外。
三、巫祝之官与“六祝六祠”
《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一文认为,韵文总体来说都源自祭祀行为,无论是《周礼》“六祝六祠”还是颂、铭等文体,皆是如此。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将文学的起源追溯到巫祝之官,那么“前王官时代”是否已经有文学或者韵文的萌芽?巫祝之官之外其他王官所创造的文本,是否便不算文学?王官以外的人物,是否与文学无涉?韵文以外的文字,是否便不算文学?
刘师培所提及的《周礼》“六祝六祠”,见于《春官·大祝》,太祝之官掌“六祝之辞”,所谓“六祝”,指“顺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筴祝”。⑦[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08-809页。凡祝皆有辞,而其辞又多韵语。今本《尚书》有《金縢》一篇,它在清华简中有相应的文本:“周公乃为三坛同墠,为一坛于南方,周公立焉,秉璧戴珪。史乃册,祝告先王曰:‘尔元孙发(月部)也,遘害虐疾(质部),尔毋乃有服子之责在上(阳部)。惟尔元孙发(月部)也,不若旦(元部)也,是佞若巧能(之部),多才(之部),多艺(月部),能事鬼神(真部)。命于帝庭(耕部),溥有四方(阳部),以定尔子孙于下地(歌部)。尔之许我(歌部),我则厌璧与珪(支部);尔不我许(鱼部),我乃以璧与珪归(微部)。’周公乃纳其所为攻,自以代王之说,于金縢之匮,乃命执事人曰:‘勿敢言。’”①参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58页;陈民镇、胡凯《清华简〈金縢〉集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9月20日。周公为祝祷仪式的主角,但书写简册并代为祝告的是史官。古书多“祝史”并称,《大祝》所见的一些文体也为史官所职掌,如“六辞”之一的“命”,无论是青铜铭文还是传世文献均明言由史官参与。史官的职能相对更广,大卜、大祝、大史等王官共同构成大史寮,广义的“史”可包括“祝”在内。“祝告先王”之语虽非严谨的韵语,但也可以看出有意识地押韵,大致存在“质月合韵—月元通韵—之部韵—真耕合韵—耕阳合韵—歌部韵—鱼歌合韵—支微合韵”的线索。上述祝辞四言与杂言相混,不但韵律和谐,句式也相对整饬,如“尔之许我,我则厌璧与珪;尔不我许,我乃以璧与珪归”,已是较工整的对仗。在祝祷结束之后,“周公乃纳其所为攻,自以代王之说”,其中“攻”写作“”,②今本《尚书·金縢》作“功”,《史记·鲁周公世家》作“质”,过去歧说迭出,莫衷一是。“说”写作“敚”,实际上均属于《大祝》所谓“六祈”。楚简多见“攻解”之语,即解除,周公自以为“攻”,殆以祝辞解除武王之祟。“功”“说”均为祭祷环节,“说”之后每伴随“攻”,具有主动采取攘除措施的性质。③臧克和:《祝由与攻敚——释“以其古敚之”兼及战国楚简祷祠的结构意义》,《简帛与学术》,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161页。可见,“六祝”“六祈”在《金縢》中得到一定反映。祝祷仪式伴随着相应的祝辞,祝辞用于沟通人神,往往注意措辞,多用韵语。
最值得注意的是“六辞”。据《大祝》,“祠”“命”“诰”“会”“祷”“诔”诸体均与祝官有关,刘师培指出“文章各体,多出于斯”。饶宗颐亦指出:“六辞者:祠、命、诰、会、祷、诔。后世文体可追溯焉。……卜掌卜事,而祝以文辞事神。今殷墟甲骨出土数万片,皆卜者贞问之语,其祝者之辞则罔见,殷人之文学,宜存于祝辞;而祝辞书于典册,卒归澌灭。”④饶宗颐:《选堂赋话》,《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11《文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第445页。原载何沛雄编:《赋话六种》,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75年。饶氏亦强调“六辞”对于文体起源的意义,并且指出卜、祝需要区分,卜辞与祝辞不同,祝辞因书于竹帛已不可获见。在刘、饶二氏的基础上,邓国光对“六辞”作了进一步考论,⑤邓国光:《〈周礼〉六辞初探》,《中华文史论丛》第5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周礼〉六辞初探——中国古代文体原始的探讨》,《汉学研究》1993年第1期。修订稿收入氏著《文章体统:中国文体学的正变与流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邓氏强调刘氏巫、祝不分,应予以订正。从《周礼》看,巫官似乎没有参与与言辞相关的工作,主要通过乐舞动作沟通人神。祝官同样扮演沟通人神的角色,但侧重于文辞。“六辞”中的“命”“诰”属于官文书,应为史官所掌。“祠”“祷”“诔”等文体则主要用于沟通人神。值得注意的是诔,它与行状之祖“诔”不同。《论语·述而》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⑥[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84页。这里的“诔”当作“讄”,指祝祷之辞,刘师培则误认为是诔文之诔。⑦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文章学史序》,《刘申叔遗书》,第526页。再看“祷”。《左传》襄公十八年载献子的祷辞:“齐环怙恃其险(谈部),负其众庶(鱼部),弃好背盟(阳部),陵虐神主(侯部)。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幽部)焉,其官臣偃实先后(侯部)之。苟捷有功(东部),无作神羞(幽部),官臣偃无敢复济(脂部)。唯尔有神裁之(之部)!”⑧[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65页。上述祷辞或鱼阳通韵,或鱼侯合韵,或幽部韵,总体而言是押韵的。“祷”与“祝”在通常情况下可以通用,浑言之则同。从目前的材料看,“六辞”的文体均极重文采。但这些文辞总体而言篇幅简短,功利性较强,虽然注意文句的对称、音节的工整、音韵的和谐,但往往语气生硬、表现手法单调,与诗歌一类的文体存在明显的不同。
清华简《金縢》的祝辞较为原始,甚或可以追溯到周初的文本,该篇的叙事性内容则相对晚出。⑨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双剑誃群经新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55页;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53页;程浩:《“书”类文献先秦流传考——以清华藏战国竹简为中心》,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39页。值得注意的是,祝辞一概用时代性较早的介词“于”,与叙事性内容用“於”形成反差,亦可说明其时代性。作为宗周礼乐文明的产物,这一祝辞具有重要价值,因为类似的早期祝辞几乎都没有保存至今。随着王纲解纽,本来由王官垄断的知识与思想资源开始向其他阶层扩散。针对“诸子出于王官”说,李零认为,“学”与王官无法对号入座,“术”和王官有一定对应性。①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21页。这突出表现在,战国时代开始,巫术空前兴盛,数术方技之书不断涌现,其“术”又显然承自王官。表现在祝辞中,便是有一部分仍保留在“大传统”中,而有的则滑向“小传统”,并与巫术相结合。
四、简帛文献所见祝辞的文体特征
除了与“六祝六祠”相关的材料,简帛文献还出现一些祝辞,虽然未必与巫祝之官有直接联系,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祝辞的文体特征。清华简第3辑中有一组“祝辞”,原无篇题,因篇中屡见“祝曰”之辞,整理者拟题作《祝辞》,其文曰:
恐溺,乃执币以祝曰:“有上皇皇(阳部),有下堂堂(阳部),司湍彭彭(阳部),苟兹某也发扬(阳部)。”乃予币。
“踵弓将射翰音,扬武即求当(阳部)。”引且言之,童以骮,抚咢,射音也。②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64页。部分释文据其他学者的意见订正。整理者认为“祝”读作“呪”或“咒”,引《礼记·郊特牲》疏云:“祝,呪也。”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63页。江林昌师也认为这些所谓“祝辞”实际上都是巫咒之辞,希望直接指令自然神,以达到自己的愿望。④江林昌:《清华简〈祝辞〉与先秦巫术咒语诗》,《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一般认为,宗教的重要特点是神控制人,而巫术的重要特点是人控制神。《尚书·无逸》孔颖达疏:“以言告神谓之祝。”⑤[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2页。真正意义上的祝辞,是属于宗教而非巫术的。而这些祝辞显然难以单纯用巫术或宗教来界定,它们可以说是战国以降“大传统”与“小传统”交融的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们向神祈求免于溺水之祸、止息火灾以及射猎成功,并且配以“予币”“乃投以土”等仪式。“有上”(天神)、“有下”(地祇)、“司湍”(水神)以及武夷,都是祈祷的对象,神的地位是相当崇高的。“苟兹某也发扬”、“兹我逞”、“扬武求当”等措辞的语气,则有一定的巫术意味。这些祝辞的语言特色颇值得注意:“有上皇皇,有下堂堂,司湍彭彭,苟兹某也发扬”⑥“有上皇皇,有下堂堂”,整理者读作“有上茫茫,有下汤汤”,此从王宁说,参见氏著《清华简三〈祝辞〉“巟巟”“堂堂”补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5年9月6日。一句中,“皇”“堂”“彭”“扬”均为阳部字,句句押韵,文多四言;“救火”一则中的“冥”和“逞”均为耕部字,亦为韵语;“皇皇”“堂堂”“彭彭”“冥冥”作为叠词,修辞考究;“射戎”“射禽”“射音”诸则,句式相近,颇有重章叠唱的意味。刘师培说“巫祝之职,文词特工”,所言不虚。
上述祝辞是作为典籍类文献保存在清华简中的,文本形态已然凝固。而在包山楚简、望山楚简、葛陵楚简、秦家嘴楚简中,则发现有属于私文书的祝祷之辞。这些祝祷文主要用于祷病,由于它们多残断简略,多不见完整的祝辞文本。它们直接向神祇祝祷,更近于“大传统”。可以想象,祝辞一开始都是实用性的文本,像清华简《金縢》《祝辞》这样固化为经典文本的,显然极为罕见。
战国秦汉简帛所见巫祝之辞一概为韵文,且偏爱某些韵部,如押阳部韵以及与阳部相关的韵部。所祝祷的对象,其称名也往往奠定全篇祝辞的押韵基调。有时“皋”之类的拟声词,也能引领全篇押韵。“苟”之类表述祈使的副词,“令”之类表示命令的动词,出现频率较高,可反映其语体色彩。这些祝辞往往配合行为,为巫术或祭祷仪式服务。属于祭祷的祝辞,往往伴随祭品的陈设和投掷,用语相对典雅;而属于巫术的祝辞,则涉及顺势、触染、厌胜等巫术方法,①吕亚虎:《战国秦汉简帛文献所见巫术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82-308页。用语相对鄙俚。它们大多已经属于巫术,或者可以归入广义的“数术”。但它们仍有着沿承自王官的烙印,如除了以“号”“呼”引入,还常用“祝曰”“祷之曰”,可见其“祝”“祷”性质,有的仍然是对某神祇的祝告祈祷,当是对“大传统”的沿袭。再如此类祝辞常用拟声词“皋”,它也见诸《仪礼·士丧礼》《礼记·礼运》“皋!某复”,郑玄注云:“皋,长声也。”《说文》释“皋”云:“礼,祝曰皋。”这是巫术仪式中经常呼叫的一种声音,②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289页。刘信芳曾认为“皋”指西皇少昊,参见氏著《秦简〈日书〉与〈楚辞〉类征》,《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但其源头应是“王官时代”的礼典。战国秦汉简帛的材料虽然不足以说明早期巫祝之辞的情况,但鉴于形式与内容的继承性,仍是不可多得的辅助性材料。它们与《金縢》等文献所见祝辞一道,勾勒出此类文本的概貌。巫祝之辞对文辞的追求,确乎启导了后世的诸多文体。
五、结语
从太祝“六辞”以及相关的巫咒文本看,巫祝之官的确注重文辞修饰,当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就这一层面而言,刘师培的“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可谓卓识。但巫、祝需要区分,祝官的地位显然更为重要。而且,若追溯文学的萌芽,还要进一步追溯到“前王官时代”。早期的咒语或巫诗或许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但应非唯一的源头。据《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有人作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③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2页。看起来是极古朴原始的诗歌,应为较早的韵语和偶语。据《吴越春秋》,所谓“古者”,甚至在神农、黄帝之前。由于材料晚出,未可尽信,但它至少提示我们:中国文学的源起,巫术或原始宗教应非唯一的路径;过去所强调的“劳动说”等说法,仍有参考价值;诗歌的起源,与音乐有密切的关联。刘氏曾指出“上古之文,其用有二:一曰抒己意以示人;一曰宣己意以达神”,④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文章学史序》,《刘申叔遗书》,第526页。亦强调“达神”之外,尚有另一途径。
刘氏认为狭义的“文”出自巫祝之官,引“六辞”及颂、铭为证。但“六辞”中并非完全是韵文,譬如命、诰。刘氏还撰有《文章学史序》,较《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早五年发表,但所论更为全面。《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为札记性质,故论述简略,且侧重于韵文与巫祝之官,不及散文与史官等王官。在《论文杂记》中,刘氏对箴、铭、碑、颂等“文章之有韵者”的源流加以搜讨,认为“上古之世,崇尚文言,故韵语之文,莫不起源于古昔”。《文章学史序》则全面阐论巫、史、祝、卜与文体流别的关系,强调了韵文之外如传志、叙记等文体,并涉及史官的撰述。因《文章学史序》所论为“文章”,较之“文”更为宽泛。该文论“巫祝之官,亦大抵工于词令”,“虞翻注《周易·大有》卦曰:‘口助者,祝之职也。’此祝必工文之证也”,“盖周代司祭之官,多娴文学”,⑤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文章学史序》,《刘申叔遗书》,第527页。皆可与《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一文相参看。此外,《文章学史序》还论述了行人之官对于“文告之辞”“威让之令”“羽书军檄”诸文体的影响,该文可谓王官与文体流变关系的专论。追溯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及观念的源起,尤其是诗歌,当追溯到“前王官时代”,但不少与政教有关的实用性文体,确实只能溯源至“王官时代”。⑥陈民镇:《王官与文体的初肇——以〈诗〉〈书〉为考察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年第3期。因此,刘氏基于官守论的文体生成论,自有其合理性在。欲理解刘氏的“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需要对刘氏的文学观、官守论有明确的认识,还要结合其文体流变的总体认识予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