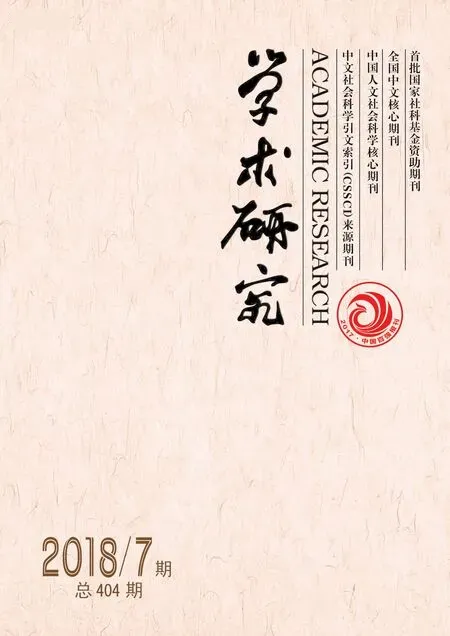论正史“怪异”书写与小说“志怪”之关系*
2018-02-20王庆华
王庆华
在史部类目中,“正史”①“正史”作为史部文类概念,确立于《隋书·经籍志》,本文之“正史”主要指称古代目录学中的“正史”概念。处于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②[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97页。作为“史之流别”,“小说”③本文之“小说”主要指古代目录学中“小说”概念,以文言“笔记体小说”为主体。虽位于“史之末”,但也具有一定“补史之阙”之价值,可成为“正史”取材对象,“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并小说亦不遗之”。④[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397页。对于“正史”与“小说”关系,虽然前人已多有论述,但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梳理。正史具有“怪异”书写之传统,历代正史中,灾异、祥瑞、神怪、方术之事或多或少均有所书写,并在入史标准、书写功用、题旨趣味、故事类型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叙事规范。志怪小说载录大量鬼魅、精怪、神仙、异物、妖变、物化等人物故事,有部分内容可为正史编撰提供素材或参考。正史“怪异”书写与小说“志怪”比较接近,两者存在诸多相通之处。本文以系统梳理古代史学和小说理论批评的相关论述为基础,力求还原古人对正史“怪异”书写及其与小说“志怪”关系的理解认知和评价。
一、古人对正史“怪异”书写之基本评价取向
探讨正史“怪异”书写,需要首先了解古人对其认识评价。《左传》《史记》作为正史之先导,不仅奠定了正史诸多叙事传统,而且也借助相关评论建构起古人对叙事传统的基本评价取向。因此,本文以古人评价《左传》《史记》“怪异”书写为例,阐明古人对正史“怪异”书写之基本评价取向。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①[汉]郑玄注, [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4-1485页。受到夏、商、周鬼神观念支配和影响,《春秋》及《左传》《国语》等先秦史籍,对鬼神怪异之事亦多载录,如《左传》“昭公八年”之“石言于晋魏榆”、“庄公八年”之“豕人立而泣”、“宣公十五年”之“魏武子有嬖妾”等等。这实际上确立了一种书写传统,可看作正史书写怪异之滥觞。对此,后世史家、文人的认识评价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从“自然而然”、“疑信具传”、“妖由人兴”等角度予以认同肯定,如章炳文《搜神秘览序》:“及乎神降于莘,石言于晋,耳目之间,莫不有变怪,有不可以智知明察,出入乎机微,不神而神,自然而然。或书之竹帛,传之丹青,非虚诞也。”②转引自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86-87页。王祖嫡《师竹堂集》卷九《刻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而范武子谓其失诬,不知左主记事,疑信具传,史之体也。”③[明]王祖嫡:《师竹堂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2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09页。周召《双桥随笔》卷四:“《左传》虽好语怪,然其云妖由人兴也。”④[清]周召:《双桥随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子部儒家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423页。他们认为,《左传》记载的怪异之事可能确实存在,而且即使令人将信将疑,将其载入史册,也符合史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书写原则,同时,这些怪异之事大都与“人事”相关,也自有其重要价值。另一种则从“不语怪力”角度予以质疑批判,如王充《论衡·案书篇》:“左氏得实,明矣,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⑤[汉]王充《论衡》,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365页。皮日休《皮日休文集》卷九《书》之《鹿门隐书六十篇并序》:“仲尼修《春秋》,纪灾异,近乎怪。”⑥[唐]皮日休:《皮子文薮》,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8页。张商英《护法论》:“子不语怪力乱神。而《春秋》石言于晋、神降于莘,《易》曰:见豕负涂、载鬼一车。此非神怪而何?”⑦[宋]张商英:《护法论》,《诸子集成续编》第19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07页。显然,这应源于儒家的理性批评精神。相比较而言,对《左传》书写怪异持认同肯定之态度更占主导地位。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⑧[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页。《史记》不仅创设了纪传体正史体例,而且奠定了正史诸多书写传统、叙事规范。然而,对于正史“怪异”书写,《史记》实际上确立了两种看似矛盾的叙事传统。一方面,文中明确表示排斥“怪力乱神”,如《五帝本纪》:“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⑨[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页。《大宛列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⑩[汉]司马迁:《史记》,第720-721页。《封禅书》:“其语不经见,荐绅者不道。”⑪另一方面,文中载录史事,对于“怪力乱神”未能芟除净尽,不可避免地载录了一些鬼神怪异之事,如洪迈《夷坚丁志序》云:“若太史公之说,吾请即子之言而印焉。彼记秦穆公、赵简子,不神奇乎?长陵神君、圯下黄石,不荒怪乎?”⑫李樗《毛诗集解》卷三十一云:“受命之符,言文王受命,曰得赤雀丹书。言武王受命,必曰白鱼入舟。而司马子长犹且著于《史记》,其言殊怪诞不经。”⑬这实际上以自身的书写实践对载录鬼神怪异之事表示了肯定认可。与《左传》相似,对于《史记》书写“怪力乱神”,历代史家及文人实际上也存在着几种不同态度。或从征实传信、不语怪力乱神出发,以谨严“实录”的态度表示反对,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之《资治通鉴》提要:“见其大抵不采俊伟卓异之事,如屈原怀沙自沉,四皓羽翼储君,严光足加帝腹,姚崇十事开说之类,削去不录,然后知公忠信有馀,盖陋子长之爱奇也。”⑭或从“六合之内,何所不有”为其辩护,如王祖嫡《师竹堂集》卷九《刻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无论子长《史记》张本丘明,多神怪诡异,即《春秋》亦有然者。六合之内,何所不有?奈何以耳目不及为诬耶!”①[明]王祖嫡:《师竹堂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23册,第109页。或认为其书写怪异,都是经过精心选择而恰当的,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十五《经籍考》四十二“燕丹子三卷”:“周氏涉笔曰:‘燕丹荆轲事,既卓佹。传记所载,亦甚崛奇。今观燕丹子三篇,与《史记》所载皆相合,似是《史记》事本也。然乌头白、马生角、机桥不发,《史记》则以怪诞削之,进金掷鼃、脍千里马肝、截美人手,《史记》则以过当削之,听琴姬得隐语,《史记》则以征所闻削之。……其书芟削百家诬谬,亦岂可胜计哉。今世祇谓太史公好奇,亦未然也。’”②[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55页。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一“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附案:索隐曰:《国策》:‘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③[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13页。总体而言,古人对《史记》书写怪异亦基本持认可态度。
二、正史“怪异”书写的基本原则
《左传》《史记》确立起正史书写怪异之叙事传统,之后,历代正史“怪异”书写亦形成了自身独具一格的存在形态,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历代正史中的《五行志》《灵征志》《祥瑞志》《符瑞志》。此类记载在正史“怪异”书写中最为突出,以阴阳五行观念、天人感应思想为基础,重在载录各类灾异之“咎征”、祥瑞之“休征”及其推占、应验。作为吉凶征兆的反常现象,既有地震、水灾、旱灾、蝗灾、雷电等自然灾害,也有大量神鬼、怪变、复生等怪异之事,如牛运震《读史纠谬》卷六《宋书》“符瑞志”云:“《符瑞志》,皆记帝王图谶之事,类砌奇怪以为征应,殊非史体。”④[清]牛运震:《读史纠谬》,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272页。“五行志”云:“《五行志》,依《汉书》条列叙次,颇有章程,但其中亦有琐怪不经之事。猥用编次,徒烦笔墨,此史家好奇贪多之病也。”⑤[清]牛运震:《读史纠谬》,第273页。二、历代正史中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东夷列传》《四夷列传》《夷蛮列传》《诸夷列传》《异域列传》《夷貊列传》《南蛮列传》《北狄列传》《西戎列传》《外国列传》。其中,对蛮夷历史传说、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的记载,包含不少远国异民的怪异、荒诞之事,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八《四夷考五》“盘瓠种”云:“杜氏通典曰:按范晔《后汉史》蛮夷传,皆怪诞不经,大抵诸家所序四夷,亦多此类。”⑥[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下册,第2573页。三、历代正史中的《方术列传》《艺术列传》《方伎列传》。此类记载中描述方伎之士的占卜、作法等,多非常奇异之言行,如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二《问答》九“诸史”云:“《方术》一篇,如徐登、刘根、费长房以下,皆诞妄难信,不特王乔、左慈已也。”⑦[清]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86页。四、历代正史中《方术列传》等之外的“本纪”“世家”“列传”亦或多或少包含一些人物神异出生、遭遇神怪、奇特梦境等零散的怪异之事,如唐锦《龙江梦馀录》卷四云:“史传于圣贤之生,必述神怪之事,以见其异于寻常者如此。”⑧[明]唐锦:《龙江梦馀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122册子部杂家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53页。对于正史为什么书写怪异之事、以何原则载入怪异之事,历代史家及文人还是有着相对比较一致的看法,实际上形成了一系列共识性的基本书写原则。
在古代传统史学看来,正史书写怪异之事,须“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明人事之得失”,与朝廷大政、家国兴衰等紧密相关。如刘知几《史通·书事》云:“若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江使返璧于秦皇,圯桥授书于汉相,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⑨[唐]刘知几著, [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30页。彭希涑《二十二史感应录》“绪论”云:“史书体例不志怪神,然有可以明人事之得失者,虽涉灵异不以为病。”①[清]彭希涑辑:《二十二史感应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绪论”第1页。同时,正史书写怪异之事,须“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可劝诫警示,与历史人物或朝政之评价密切相关。如刘知几《史通》云:“三曰旌怪异……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②[唐]刘知几著, [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册,第229页。“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且周王决疑,龟焦蓍折,宋皇誓众,竿坏幡亡,枭止凉师之营,鵩集贾生之舍。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禄来钟,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测也。然而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③[唐]刘知几著, [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册,第63页。司马光《资治通鉴释例》“温公与范内翰论修书帖”云:“妖异有所儆戒,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及妖异止于怪诞,谈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④[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释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1册史部编年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319页。其中,为了更好地发挥怪异之事的劝诫作用,不少史家甚至主张应更多书写灾异而非祥瑞,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春秋左氏传”:“《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所以训寅畏、防怠忽也。”⑤[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20页。依上述两则基本原则,那些“无关劝诫、徒资谈说”、“靡劝靡戒”者,自然不具备载入正史之资格。如焦袁熹《此木轩杂著》卷一“神怪”云:“孔子不语怪神,所以立教且不语,非谓天壤间无有此物。后世史家记事,凡迹涉灵怪及仙佛变现冤雠报复之状,昔之所无,今之所有,虽欲削之,安得而削之。必谓史体不当,类稗官家言,欲一切刊去,以附于孔子不语之旨者,通人所不予也。唯其无关劝诫、徒资谈说者,斯则必在翦弃之条耳。”⑥[清]焦袁熹:《此木轩杂著》,《续修四库全书》第1136册子部杂家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71页。浦起龙《史通通释》外篇卷十七云:“按:志怪奚必去谐,撰史自宜识大。语有轩轾,意有堤防,非灾非祥,靡劝靡戒,必严诸此。”⑦[唐]刘知几撰, [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80页。其中,《五行志》《灵征志》《祥瑞志》《符瑞志》载录怪异之事,特别强调借助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理论将其与朝政得失、人事善恶联系起来,“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⑧[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页。注重发挥其劝诫作用,如《隋书》之《五行志》“叙”云:“《春秋》以灾祥验行事,则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示废兴,则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讹之占所以征验。夫神则阴阳不测,天则欲人迁善。”⑨[唐]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17页。《方术列传》《艺术列传》《方伎列传》记载方伎之士的占卜、作法等怪异之事,也是以劝诫为宗旨的,如《隋书》之《艺术列传》“叙”:“历观经史百家之言,无不存夫艺术,或叙其玄妙,或记其迂诞,非徒用广异闻,将以明乎劝戒。”⑩[唐]魏征等:《隋书》,第1764页。
虽然正史“怪异”书写作为一种叙事传统自有其合理性、正当性,但从“传信”“征实”之古代史学传统来看,此类内容写入正史,理应依据上述基本原则精心甄别选择,因此,不少史家、文人对于部分正史载录怪异之事过多过滥,多持反对批评态度,这一点在《晋书》《南史》《北史》等评价中,尤为突出。例如,刘知几《史通·书事》:“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按历代之史,惟《晋》丛冗最甚,可以无讥。至于取沈约诞诬之说,采《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诡异谬妄之言,亦不可不辨。”⑫牛运震《读史纠谬》卷十《南史》“宋本纪”条称:“昔人谓《南史》所载谣谶妖祥,颇涉猥杂,即此足以见一端矣。”⑬甚至对于史注过多载录怪异内容,亦表反对,如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二“谶纬害经”条:“今《三国志注》多引神怪小说,无补正史处,亦可删。”①[宋]陈善:《扪虱新话》,《续修四库全书》第1122册子部杂家类,第136页。《四库全书总目》之“《三国志》提要”:“(《三国志注》)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②[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403页。另外,虽然正史载录怪异之事作为耳目之外的反常异事或超自然现象,本身属于“若存若亡”者,但是其中也存在着虚实之辨、信疑之分。对于正史载录怪异之事流于荒诞不经、虚妄难信而有失史体,不少史家、文人更是予以严厉批评,如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上:“《晋史》多幽冥鬼怪谬妄之言,取诸《幽冥录》、《搜神记》等书,不知诚有其事否乎?”③[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页。彭孙贻《茗香堂史论》卷二:“南史。……梁郄后酷妬,及终化为龙,入后宫通梦武帝。…… 粟山按:此等不经之言,笔之于史,为失体。”④[清]彭孙贻:《茗香堂史论》,《续修四库全书》第450册史部史评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47页。牛运震《读史纠谬》指摘正史中此类怪诞之处,林林总总,有着集中表述,例如《晋书》“王恭传”:“徐伯玄事,亦近怪诞小说。”⑤[清]牛运震:《读史纠谬》,第247页。《南史》“王镇恶等列传”:“‘玄谟从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发东海王家女子棺,得玉钏、金蚕,女子尚生,能言。此可入怪异小说,不足混正史。”⑥[清]牛运震:《读史纠谬》,第373页。然而,正史“怪异”书写之基本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叙事理想,在历代正史书写实践过程中,具体到某一件或某一类怪异之事是否可以写入正史,因何写入正史,不同史家及文人见仁见智。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晋书所记怪异”:“采异闻入史传,惟《晋书》及南、北《史》最多,而《晋书》中僭伪诸国为尤甚。刘聪时有星忽陨于平阳,视之则肉也,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臭闻数里,肉旁有哭声。……此数事犹可骇异,而皆出于刘、石之乱,其实事耶?抑传闻耶?刘、石之凶暴本非常,故有非常之变异以应之,理或然也。”⑦[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161-162页。甚至对于一些荒诞虚妄之事,也有史家及文人认为“纪载不诬”或“恐不尽诬”,如毛晋《搜神记跋》:“顾宇宙之大,何所不有,令升感圹婢一事,信纪载不诬,采录宜矣。”⑧[晋]干宝:《搜神记》(古小说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54页。
三、正史“怪异”书写与小说“志怪”之主要联系
作为价值定位相距甚远的文类,“正史”与“小说”整体界限泾谓分明。其中,正史“怪异”书写与小说“志怪”之相通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志怪”小说起源与官方史籍书写怪异密切相关。“小说”源于史部之分流,唐前最早一批“志怪”小说的部分作品就是专门辑录官方史书中的“怪诞不经之说”而成。例如,“古今纪异之祖”《汲冢琐语》(约成书于战国),绝大部分是关于卜、占梦、神怪一类的“卜梦妖怪”之作,此书应是从前代官方史籍中专门辑录“卜梦妖怪”题材故事而成。另外,还有一些志怪小说作品专门载录重要历史人物依托附会之怪异传闻、诞妄传说而成,也与正史密切相关。例如,《穆天子传》,《四库全书总目》之《穆天子传》提要称:“旧皆入‘起居注’类,徒以编年纪月,叙述西游之事,体近乎起居注耳,实则恍惚无征,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古书而存之可也,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⑨[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205页。《汉武故事》,记武帝传说,主要为求仙和死后故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所言亦多与《史记》《汉书》相出入,而杂以妖妄之语。”⑩[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206页。
第二,正史“怪异”书写与小说“志怪”相互取材,存在混杂现象。正史编撰取材颇为广泛,既有官方的国史实录,也有“杂史”“杂传”“小说”等野史。其中,正史取材小说,属编撰之常态,如《史通·杂说上》:“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⑪朱弁《曲洧旧闻》卷第九:“《新唐书》事倍于旧,皆取小说。”①[宋]朱弁:《曲洧旧闻》(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7页。何焯《义门读书记》二十九卷“五代史”:“欧公作《五代史》,亦多取小说。”②[清]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89页。一般来说,正史书写怪异采录 “志怪”小说,主要集中于《五行志》《灵征志》《祥瑞志》《符瑞志》,“本纪”“世家”“列传”等传记类采录志怪“小说”,只有《方术列传》《艺术列传》《方伎列传》较多,其他相对很少(部分正史如《晋书》《南史》《北史》等书写怪异较多)。例如,《晋书》《宋书》之《五行志》的不少内容采自《搜神记》《列异传》《博物志》等魏晋志怪小说。《旧唐书》之《五行志》许多内容采自《朝野佥载》等唐代笔记小说。《新唐书》之《方伎列传》描写方伎之士的占卜、作法等奇异言行,有一些增文采自《酉阳杂俎》等。
不少“志怪”小说成书“考先志于载籍”,往往从旧书取材,其中不乏取材正史者,例如,干宝《搜神记》部分内容选自《汉书》《后汉书》之《五行志》。颜之推《还冤记》取材史事,所述皆报应之说,“大抵记中事实,多见正史”。③[清]王谟:《还冤记序》,转引自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上册,第63页。闵文振《异物汇苑》“引用书目”列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陈书》《南史》等;李石《续博物志》、徐寿基《续广博物志》曾取材于《汉书》《后汉书》《晋书》等;甚至有个别“志怪”小说大部分或全部取材正史,例如,窦维鋈《广古今五行记》,《宋史·艺文志》曾归入“小说家”,《玉海》卷五引《中兴书目》称其:“集历代五行咎变,叙其征应,类例详备。”④[宋]王应麟辑:《玉海》,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110页。许多内容采自《晋书》《宋书》《隋书》的《五行志》以及《史记》《汉书》《三国志》《南史》等。方凤《物异考》,《八千卷楼书目》“小说家”著录,书中分为“水异”“火异”“木异”等七门,摘录正史《五行志》而成。傅燮调《史异纂》,《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小说家”,“是书杂纂灾祥、怪异之事,自上古至元,悉据正史采入,凡外传杂记,皆不录。分天异、地异、祥异、人异、事异、术异、译异、鬼异、物异、杂异十门”⑤[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232页。,徐轨《史异纂序》称:“于是取二十一史及有明一代之书,凡事物之迥异于寻常者,为之州次部居,名曰《史异纂》《有明异丛》。”⑥[清]傅燮詷辑:《史异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9册小说家类,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619页。此外,部分“史钞”类著作,汇集历代正史载录的怪异之事,虽然未被归入小说家,但颇具志怪“小说”意味,如《四库全书总目》“史钞类”著录之《史异编》:“其书以诸史所载灾祥神怪汇为一编。”⑦[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582页。彭希涑《二十二史感应录》取材二十二史中的善恶报应之事,“绪论”称:“兄子希涑阅二十二史,取其事应之显著者,汇而录之。”⑧[清]彭希涑辑:《二十二史感应录》,“原序”第1页。正史“怪异”书写取材小说和小说“志怪”取材正史,特别是《史异纂》等全部取材正史怪异之事者,也被看作“小说”,实际上反映了正史“怪异”书写和小说“志怪”存在着一定程度混杂的交集。
第三,正史“怪异”书写与小说“志怪”的书写类型、叙事旨趣存在相通之处。整体而言,“志怪”作为小说主要类型之一,具有鲜明的相对独立性,如“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⑨[唐]刘知几著, [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册,第274页。“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⑩[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82页。“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⑪刘知几之“杂记”、胡应麟之“志怪”、《四库全书总目》之“异闻”一脉相传,皆指“小说”中载录鬼神怪异之事为主者,主要包括两种书写类型。一是以“异物”为主要表现对象,包括山川地理、远国异民、动植物产、精怪异象等,以体物描绘为主要表现手法,重在说明异物之形状、性质、特征、成因、功用等,大多为残丛小语。该类型源于战国后期成书的《山海经》,汉末在《山海经》影响下,出现了《神异经》《括地图》《十洲记》等一批仿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张华《博物志》、郭璞《玄中记》、佚名《外国图》等一批典范之作,逐步发展成熟。隋以降,此类专书创作不绝如缕,如唐代沈如筠《异物志》,宋代佚名《广物志》、李石《续博物志》,明代游潜《博物志补》、董斯张《广博物志》,清代徐寿基《续广博物志》等。同时,或为专卷,或为散篇,羼杂于笔记体小说中,如《酉阳杂俎》“境异”“物异”“广动植”等。二是以神仙、鬼魅、精怪、妖物、梦异、异人等相关人物故事为主要取材范围,具有一定情节性。自魏晋南北朝之曹丕《列异传》、干宝《搜神记》、陶渊明《搜神后记》、刘义庆《幽明录》、东阳无疑《齐谐记》、吴均《续齐谐记》等,到唐代之唐临《冥报记》、孔言《神怪志》、皮光业《妖怪录》、杜光庭《录异记》等,宋代之徐铉《稽神录》、张师正《括异志》、郭彖《睽车志》、洪迈《夷坚志》、王质《夷坚别志》等,明代之祝允明《志怪录》、杨仪《高坡异纂》、钱希言《狯园》等,清代之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袁枚《子不语》等,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当然,这两种书写类型在不少志怪小说中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羼杂情况,而且,也存在志怪与轶事相互羼杂情况。部分志怪“小说”与正史“怪异”书写在书写类型和叙事旨趣上高度相似。其中,书写“异物”的“志怪”小说与正史《五行志》在部分题材类型的叙事旨趣上颇俱共性,例如,张华《博物志》卷三“异兽”“异鸟”“异虫”“异鱼”“异草木”,与《五行志》之“羽虫孽”“龙蛇孽”“鱼孽”“草妖”“马祸”“羊祸”很相近。任昉《述异记》、刘敬叔《异苑》、沈如筠《异物志》、郑遂《洽闻记》等部分内容为灾异祥瑞、非常变怪之事。书写神仙、异人、梦异等人物故事的“志怪”小说与正史列传中的怪异之事在个别方面也颇为相似,例如,赵自勤《定命录》、吴淑《江淮异人录》、张君房《乘异记》等部分内容为相术知命、道流作法,颇类似《方伎列传》描述的推占、法术。
当然,小说“志怪”亦有其独特的价值功能定位,与正史“怪异”书写存在着显著区隔。虽然小说“志怪”与正史“怪异”书写存在一定相通之处,小说“志怪”因此而具有一定“寓劝诫”“补史之阙”之功用,但是整体看来,小说“志怪”最为主导的价值应为“游心寓目”“广见闻”“助谈柄”等,其所载奇奇怪怪之事,大多数还是无关史家旨趣和儒家教化,主要满足文人的娱乐消遣需要,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夷坚志》:“稗官小说,昔人固有为之者矣。游戏笔端,资助谈柄,犹贤乎已可也。”①[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6页。袁枚《新齐谐序》:“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②[清]袁枚:《子不语》,《笔记小说大观》第20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1页。小说“志怪”以娱乐消遣为主导价值的功用定位,使其在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一个低下的位置,面临着被多重挤压的不利发展空间,然而,正史书写“怪异”的种种原则及其独特的存在形态正为小说“志怪”的兴盛提供了空间和奠定了基础。儒家对待鬼神、怪异之事的态度,介于信仰其真实存在和理性否定其存在之间。“正史体尊,义与经配”,正史书写怪异,无疑为古人维护怪异之事存在的可能性和志怪“小说”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有力支撑,许多文人为志怪“小说”辩护,都是以正史书写怪异为依据的,例如,谢肇淛《五杂俎》卷五:“人死而复生者,多有物凭焉。……此事晋、唐时最多,《太平广记》所载,或涉怪诞,至史书《五行志》所言,恐不尽诬也。”③[明]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94页。何琪《夷坚志序》:“夫以神奇荒怪之事,委巷丛谈之语,盖儒者所不道。然观古经传之所称,后世史书之所录,并莫得而废焉。”④转引自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上册,第110-111页。正史书写“怪异”的原则,也大都成为了小说“志怪”标榜或攀附的目标,这也为小说“志怪”发展提供了文化空间。正史书写“怪异”独特而广泛的存在形态,不仅有力支撑了小说“志怪”的存在价值,更是从不同方面滋养了小说“志怪”,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