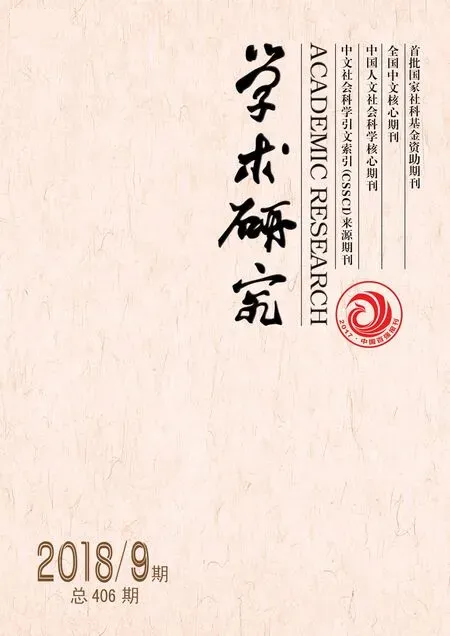卡鲁斯与创伤批评*
2018-02-19陆扬张祯
陆 扬 张 祯
一、克罗琳达的哭声
“创伤”(traSigmund Freu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under the general editorship of James Strachey in collaboration with Anna Freud,24 vols. London: Hogarth, 1953–74, vol. 18, ch.3. See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uma)不是痛苦。痛苦作为伟大文学的不竭源泉,两千余年前司马迁早有恣肆铺陈,一如《报任安书》中的悲愤之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比较来看,创伤作为当代西方前沿文学理论的一个因由,它更多被界定为某种不见天日的被压抑经验。美国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凯茜•卡鲁斯1996年出版的当代西方创伤文学理论的发轫之作,书名就是《不被承认的经验:创伤、叙事与历史》。
卡鲁斯开篇就将创伤与文学的关系,追溯到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第三章。她说,弗洛伊德发现一些人生活中有种莫名痛苦的格局,有些人九死一生之后,噩梦般的恐怖场面总会不断重复袭来,他完全不能自制,像是被命运捏在手心里面玩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著名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以下片段,她引了弗洛伊德的这一段话:“史诗的主人公唐克雷蒂在一次决斗时,无意中杀死了他心爱的克罗琳达,彼时她伪装披挂着敌方骑士的盔甲。把她埋葬后,他一路走进一片陌生的树林,那是让十字军军团闻风丧胆的魔法树林。他一剑砍向一颗大树,可是树干伤口里流出血来,还有克罗琳达的声音,她的灵魂给囚禁在树里,他听到她在泣诉,他又把他心上人砍了一刀。”aSigmund Freu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under the general editorship of James Strachey in collaboration with Anna Freud,24 vols. London: Hogarth, 1953–74, vol. 18, ch.3. See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在我们心理生活中确实存在一种时时无端来袭的强迫性重复行动,它超越了快乐原则。而在卡鲁斯看来,弗洛伊德引述的这个十字军骑士唐克雷蒂先是在战场上刀砍他心爱的穆斯林姑娘,然后又无意之中再度伤害她的栩栩如生情节,正是丝毫不爽地表出了创伤经验重复自身的方式,显示它如何锲而不舍,通过幸存者的无意中的行为,违背他自己的意愿,时不时卷土重来。这也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创伤神经机能症”。
卡鲁斯认为,弗洛伊德举的这个例子,在文学方面的意味其实要深长得多,而远不止步于弗洛伊德所说的重复强制。她说,让她刻骨铭心的不光有唐克雷蒂无意识的伤害动作,以及这动作在不经意间卷土重来,更有树木的哭声。那哭声悲哀而凄婉,而且偏偏是从伤口发出来的!唐克雷蒂不光重复先时所为,而且在重复之中,他第一次听到有哭声传出,让他明白自己做了什么。所以唐克雷蒂心上人的哭声,是见证了他无意中重复的过去。这个故事因此表明,创伤经验不仅是某人无意之间重复行为的一个哑谜,同样神秘莫测地释放了伤口中某种完全不同的人类声音,这个声音是自我的他者,那是唐克雷蒂本人无法充分理解的。卡鲁斯强调说,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无意间的重复伤害行为与见证哭声并行不悖,这最好不过地表明了他对于创伤经验的直觉和迷恋。
那么,这一切对于文学批评又意味着什么?卡鲁斯指出,弗洛伊德求诸文学来描述创伤经验,是因为文学就像精神分析,特别关心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在这个已知和未知的特定交叉点上,文学语言与创伤经验的精神分析理论交汇于此了。塔索长诗提供的这个例子,按照我的阐释,就不止是文学给更为宽阔的精神分析或经验真相提供了实例,我要说,它是一个更大的寓言,同时喻指着弗洛伊德文本中创伤理论的未尽之言,以及它们的言外之意:文学与理论之不可或缺的联系。”a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p.3.唐克雷蒂不知不觉之间,拔剑两次砍向他心爱的克罗琳达,这一后来方才意识到的莫名可怕事件,在卡鲁斯看来,也涉及到“创伤”(trauma)一词的原初语义问题。她指出,在希腊语中trauma是指身体上的伤口,但是这个词的用法到了现代,特别是在医学和精神病题材的文学中,最典型不过地如弗洛伊德的作品,创伤一语就不光用于身体,而且用于心灵。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就暗示心灵上的创伤尤甚于身体上的创伤,后者或可疗愈,前者则时时卷土重来。那么,什么是创伤?它的方位是在哪里?卡鲁斯的回答是,一如克罗琳达的哭声,初始不可闻,第二次伤害始得可闻,创伤也是这样,它不在某人以往的暴力事件里,而是在之后的日子里,死灰复燃、阴魂不散,缠绕在当事人心间。所以创伤不仅仅是一种病理,一种受伤害心灵的病症,它是伤口泣诉的故事,泣诉我们舍此无从得知的真相。而在这姗姗来迟的泣诉之中,真相不光勾连我们所知的事实,而且勾连着我们的行为和语言一无所知的东西。
卡鲁斯坦言她写作该书的宗旨是,在精神分析、文学与文学理论文本中,来言说并探究创伤经验的深刻故事。至于如何言说,卡鲁斯的方法不是直接提供创伤幸存者的具体案例研究,或者直接阐明创伤的精神学原理,而是探究已知和未知事件如何在创伤的语言以及相关故事里迂回曲折交缠一体。这是说,创伤理论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不可能是直截了当的,而必然是迂回曲折地层层推进。故弗洛伊德以降,创伤就并不仅仅是一种病理,而是深深涉及心灵与现实的神秘关系。卡鲁斯对创伤作如下说明:“就总体定义来看,创伤被描述为对某个或某一系列始料不及或巨大暴力事件的反应,这些事件发生之时未有充分理解,但是过后在闪回、梦魇和其他重复性现象中不断余烬复起。创伤经验因此超越了相关受难主体的心理维度,它意味着一个悖论:暴力事件当时所见却一无所知,而矛盾的是,它马上就变身为了迟到的形式。”b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pp.91-92.这个定义是相对的。卡鲁斯自己也承认创伤的理解可以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很难确定一个众望所归的定义。但是大体来看,创伤指的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事件,它是如此猝不及防,以至于当时都感觉不到它的伤害,惟事后在幻觉和其他外来契机中,时时袭上心来,一如克罗琳达的哭声。
二、读《摩西与一神教》
《不被承认的经验》第一章以“创伤与历史的可能”为副标题,专门就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展开了创伤分析。作者开门见山点明题意,指出近年文学批评日益关注后结构主义激发的形形色色认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几无例外让政治和伦理束手无策。文字被认为游戏有余,却不足与表情达意,是以永远无法接近他人的,甚至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一切给予政治和伦理评价的努力,也都化为泡影。对于这一趋势,卡鲁斯表明她有意来对照一种现象,它见于文学和哲学文本,也见于更为广阔的历史和政治领域,那就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独树一帜的创伤经验。惟其如此,被种种后现代话语消抹的历史,可望露出真相。本着这一视野来读弗洛伊德不辞非议、锲而不舍写完的《摩西与一神教》,在卡鲁斯看来,无疑便是叙述了犹太民族判然不同的另一种历史。
《摩西与一神教》是弗洛伊德晚年的收笔之作,阐述的是一个叫人瞠目结舌的思路: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弗洛伊德认为,摩西是将埃及本土宗教的一脉,即太阳神崇拜一神教,传给移民群体以色列人,带领他们逃离埃及,辗转迦南40年,直到被谋杀在荒野里。然而他的一神教义最终取得胜利,自己也变身为犹太民族的英雄先祖。弗洛伊德晚年这部匪夷所思的惊世之作,在卡鲁斯看来,是20世纪开拓性的创伤作品之一,它一方面通过犹太历史的虚构描写,就其历史和政治地位提出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就创伤阅读的角度来看,它又深切联系着我们自己的历史现实。是以弗洛伊德这部异想天开重写《出埃及记》的大作,有助于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灾难时代,明白在这时代之中来书写历史是多么困难。要言之,弗洛伊德在这里不仅提出了历史的观念,而且他的书写方法本身,也是直面历史事件,引导我们重新思考历史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应的伦理和政治关系。
关于弗洛伊德写作《摩西与一神教》的时代背景,卡鲁斯引了弗洛伊德1934年写给德国作家阿诺德•茨威格信中的一段话:“面临新的迫害接踵而来,我们再次反躬自问:犹太人如何走到如今这步田地,为何他们遭致这等潜在的仇恨?我很快发现了答案:摩西创造了犹太人。”aFreud to Zweig, 30 May 1934, in Th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and Arnold Zweig, ed. Ernst L. Freud,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p.12.卡鲁斯认为这段话足以表明,弗洛伊德写作此书是要探究纳粹迫害犹太人,何以变本加厉,一至于此。探究只能借古鉴今,所以弗洛伊德的历史叙述直追摩西,这位将希伯来人从埃及奴役中解放出来,让他们重获自由,回归迦南本土的大救星。犹太人的历史因此就是一部回归的历史,卡鲁斯指出,这对于精神分析本不以为奇,因为精神分析的著述就是在不断探讨各式各样的回归,诸如童年记忆的回归、被压抑记忆的回归等等。但是诚如弗洛伊德致阿诺德•茨威格信中的那句名言,“摩西创造了犹太人”,弗洛伊德叙写的回归委实与众不同,因为它超越了单纯的回归概念。假若摩西果真是通过解救希伯来人出埃及“创造”了犹太人,假若出埃及记将先时居住在迦南的“希伯来人”的历史,转变成了摆脱了奴役的独立民族“犹太人”的历史,那么出埃及记就不仅仅是一个回归(return)行为,更确切地说,它是出发(departure)的起点。弗洛伊德作为一个犹太作家,当他身处这个传统之内来书写自己民族的历史,面临的问题便是,一种文化的历史,以及它与某种政治的关系,如何难分难解地维系着“出发”这个概念呢?
卡鲁斯认为弗洛伊德兵荒马乱之间还有心思来写这部古代犹太史,是意在重新阐释《出埃及记》的性质和意义。按照圣经中的叙述,摩西是在埃及为奴的希伯来人一分子,最终成为他们的领袖,带领他们出埃及回到了故土迦南。而在弗洛伊德,一开始就宣布摩西本人其实不是希伯来人,而是埃及人,是法老的亲信及其太阳神一神教的狂热信众。法老给谋杀之后,摩西变身为希伯来人首领,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以便将前任法老危在旦夕的一神教香火保存下来。故此,弗洛伊德开宗明义改写了回归主题的性质:它主要不复是维护希伯来人的自由,而是维护埃及的一神教;不复是回归以往的自由生活,而是出发走向一神教的新的未来。这个未来不是过去的延续,而是与过去的决裂。如此来读《出埃及记》所叙述的犹太民族历史,它就是同时决裂又创立了一段历史。
按照弗洛伊德的叙述,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后,在一次叛乱中被杀身死;希伯来人掩盖了这个血腥行为,在之后流浪迦南的40年即两代人光景里,将摩西的太阳神同化进了当地一位叫做耶和华的喜怒无常火山神,与此同时,将摩西解救他们的经过,同化进了偏偏也名叫摩西的一位耶和华祭师名下。这一段叙述在卡鲁斯看来,足以说明犹太人历史中最重要的时刻,不是回归自由,而是压抑谋杀以及它的后果。这个后果如弗洛伊德所言,便是:“耶和华得到名不副实的至高荣耀……摩西的功绩给记在了他的帐上。不过这个篡位的上帝必须付出代价。他取而代之的那个神变得比他本人更为强大;历史一路发展下来,异军突起的神为他始料不及,那是被遗忘的摩西的神。毋庸置疑,唯有凭借这另一位神的观念,才使得以色列人克服千难万险,生存到了今天。”aSigmund Freud, Moses and Monotheism, English trans. Katherine Jon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39, p.62. See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p.14.弗洛伊德的观点归纳起来,是带领希伯来人回归迦南的埃及人摩西,和米甸祭师叶忒罗的女婿摩西,不是同一个人。摩西五经是张冠李戴,把两个摩西的不同事迹,合并到一个人身上了。同理埃及人摩西通力复兴的太阳神阿顿(Aton)一神教,也给似是而非地移植到了接替岳父成为耶和华祭师的米甸摩西的多神教上面,是以耶和华的名字开始大音希声,变成了“我主”(Adonai)。当以色列人在西奈荒野里立稳脚跟,得以重整旗鼓的时候,他们才回过神来,能够来忏悔当初谋杀摩西的血腥行径,并纪念摩西的事迹和牺牲,在摩西的影响之下来重建他们的新宗教。用弗洛伊德的话说,这就是幸存者的创伤经验。对此卡鲁斯的阐释是:“这一能力和回归,以及犹太人历史的开始,完全是通过一种创伤经验方才成为可能。正是这一创伤,即摩西事迹的忘却和回归,连接起了旧神和新神、出埃及的部族和最终成为犹太民族的部族。弗洛伊德的故事聚焦在创伤构成的出走和回归的性质,将历史的可能性重新定位在某种创伤性出发的性质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最终用来探究历史及其政治结果的中心问题便是:就历史成为创伤的历史而言,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b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p.15.
卡鲁斯认为,弗洛伊德这里并不是故作高深,用耸人听闻的创伤策略来抹杀和歪曲希伯来历史。特别是弗洛伊德书中把希伯来人的创伤历史比作俄狄浦斯情结,认为希伯来人压抑谋杀记忆,就像俄狄浦斯惧怕父亲阉割自己,而不得不压抑指向母亲的性欲,这导致很多读者认定这本书纯属信口开河,而毋宁说它就是弗洛伊德本人无意识生活的写照,是始终在纠缠着他的父亲情结作祟,是以回归也好,离别也好,说到底是意在辞别他的父亲,辞别他的犹太教信仰。但是,假如细读下去,事情远不似那么简单。卡鲁斯比较了《摩西与一神教》第三章第一节中作者提供的一个火车事故比喻:假定火车出事故了,有人惊吓不小,却没有受伤,然后他离开了现场。可是之后的几个星期里,他精神和运动上出现严重症状,这当然是因为事故当中受了刺激。所以这人患了“创伤性神经症”,在事故发生和病症第一次出现之间的那段时期,是为“潜伏期”。虽然火车事故的创伤性神经症和犹太人杀了摩西,然后压抑忘却血腥暴行,记忆又苏醒过来,开始忏悔文饰这段历史,这两者性质完全不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潜伏”。对此卡鲁斯表示这里“潜伏期”的概念是最值得重视的。她指出:“火车事故受害人经验中至关重要的,亦即事实上构成弗洛伊德这个例子里核心隐秘的东西,与其说是事故发生之后的忘却时期,不如说在于这一事实,那就是车祸受害人在事故发生过程中,从未真正体验到它的惨烈:如弗洛伊德所言,他‘显然没有受伤’,离开了。因此,创伤的历史力量,不光是它被遗忘以后卷土重来,而更在于唯有在势所必然的遗忘过程之中,以及通过遗忘,才第一次体验到它。”c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p.17.这是说,创伤自我意识的生成,比较伤害事件本身,潜伏期的因素更为重要,这是一段原始事件被忘却、同时回忆受外力激发,终而被孕育出来的时期。在卡鲁斯看来,弗洛伊德对于犹太文化的创伤性理解,正是生成在它一次又一次与世界范围反犹主义的不断对抗之中。是以弗洛伊德会不遗余力,来论证摩西的谋杀不是孤例,而是人类远古历史上儿子反叛弑父的无意识再现。甚至嗣后基督教与犹太教分庭抗礼,耶稣被杀死后取代上帝成为信仰核心,也显而易见是沾染上了这个血淋淋的俄狄浦斯创伤情结。
三、《弗兰肯斯坦》的创伤分析
本着以上认知,我们来看英国文学批评家,朴茨茅斯大学朱利安•沃尔夫雷斯教授对19世纪著名哥特小说《弗兰肯斯坦》的创伤分析。沃尔夫雷在其《创伤、目击、批评:意愿、记忆与责任》一文中,分别引了卡鲁斯与齐泽克的两句话作为题记。卡鲁斯的话是:“历史成为一种创伤的历史,意味着它指的恰恰是当其时没有被充分意识到的东西,或者换一种说法,历史唯有在无从琢磨其发生之时,方能得以把握。”齐泽克的语录是:“为对付创伤,我们求诸符号。”aJulian Wolfreys,“Trauma, Testimony, Criticism: Witnessing, Memory and Responsibility”,in Julian Wolfreys ed.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26.进而视之,沃尔夫雷斯发现,创伤批评见当时之未见,言当时之未能言的主题,还与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有密切联系。如德里达《另一个航向:反思今日之欧洲》中所说的伦理、政治和责任除非源起“谜点”(aporia)经验,别无其他可能,所以他们都是不可能的可能性。他并引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珊娜•费尔曼《证词:文学、精神分析与历史中的见证危机》(1992)一书的说法,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证词的时代”,换言之,即纳粹大屠杀、广岛和越南的时代。自然,还应该加上911事件。而牵掣其中的创伤经验,绝非仅凭理性能够陈述清楚。
沃尔夫雷斯肯定了卡鲁斯对弗洛伊德创伤经验强制重复特征的拓展分析。他指出,塔索史诗中上述唐克雷蒂场景深深打动批评家的地方,不光是唐克雷蒂的绝望觉悟,还有树干伤口里传出的克罗琳达的哭声。所以卡鲁斯没有说错,唐克雷蒂心上人的哭声,是见证了他无意中重复的过去。这个故事因此是表征了双重的创伤经验:一方面,诚如弗洛伊德已经认可的,创伤是某人无意之间重复行为的一个哑谜;另一方面,卡鲁斯则从中发现了另一种人类声音,它见证了当事人懵懂无知的真相。故而深入理解创伤阅读和创伤写作,我们必须牢记卡鲁斯的建议,那就是去聆听、求知和再现。这是说,涉及到创伤主题的批评阅读,以及相关的文学和电影写作,就势必要在挖掘和分析见证的同时,来挑战和质询我们的见证。沃尔夫雷斯认为,这和齐泽克的看法也是殊途同归。他引了齐泽克《论信仰》中的一段话:“创伤概念和重复概念之间,有一条天生的纽带,它见于弗洛伊德的名言,人若记事不清,便注定重复以清:创伤从定义上说,是人记忆不清的东西,即是说,通过使它成为我们符号叙述中的一个部分,来回忆它。如是,它朦朦胧胧地重复自身,卷土重来,梦寐萦怀纠缠住当事人——更确切地说,不断在重复自身的,恰恰就是这一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来准确地重复/回忆创伤。”bSlavoj Žižek,On Belief,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36-37.创伤的原始事件难以确切还愿,而这也恰恰致使噩梦莫名,频频重复袭来,在沃尔夫雷斯看来,齐泽克上面这段话,正是言中了我们思维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剧烈断层结构。创伤是一段尘封的记忆,它就尘封在我们的无意识里。
由此我们可以来看沃尔夫雷斯对玛丽•雪莱1818年出版的著名妖怪兼先驱科幻小说《弗兰克斯坦》的阅读。小说的情节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天才姑娘玛丽•雪莱知名度仅次于《呼啸山庄》的哥特式小说,倘若《呼啸山庄》也可以被归入这一文类的话。小说是书信体裁,但是叙述人始终如一,他不是别人,就是怪人的创造者,青年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虽然这个名字,后来甚至阴差阳错,被指代到了怪物自身上面。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出身在那不勒斯的一个日内瓦富贵人家,求学在德国南部多瑙河畔的英戈尔施塔特大学,小说写他化学出众,迷醉生命起源,相信凭借知识积累,通过尸体最健全部分的嫁接拼合,注入科学能量,可以起死回生,创造生命。年轻的科学家日以继夜,锲而不舍,终于大功告成,一个高达2.4米的科学怪人,活生生矗立在他面前。怪人面目狰狞,心底里却在企盼着爱。不料想竟被大惊失色的造物主维克多心生厌恶,喝令怪人。半年后,家乡传来消息,兄弟威廉死于非命,仆人又给机巧嫁祸,上了绞架。须臾怪人现身,倾诉孤独,命弗兰肯斯坦复造一异性与其相伴,不然杀死他所有好友亲朋。弗兰肯斯坦无奈从命,却终究寻思这怪人如此邪恶,再造一个配偶,代代繁衍下来,岂不给人类带来无穷祸害。乃在成功之际,又肢解了作品。一路跟踪到英国的怪物目击之余,赌咒发誓“婚礼上见”。好友克勒瓦尔再度死于非命后,婚礼上弗兰肯斯坦全副武装,搜寻怪物,却被怪物寻隙掐死了新娘。可怜的科学家天涯海角追踪怪物复仇,直抵北极,终因精疲力竭、不抵严寒,奄奄一息之余,被于此探险的沃尔顿船长搭救,遂讲完怪物故事,与世长辞。
沃尔夫雷斯指出,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殚精竭虑造出来的是人又不是人,实际上是一个人形怪物,它是在不断警醒我们自我观念内部的一种他异性。是以玛丽•雪莱处心积虑暗示,她的这个故事并非一派胡言,在科学上也并非全无可能,因为它至少揭示了我们的想象可以达到怎样一种地步。换言之,这个故事在心理和想象层面上的理解,要比它所提供的科学和现实知识珍贵得多。对此沃尔夫雷斯的评价是,我们在这里一方面是见证了物理与精神世界之间转移过程的独特写照,另一方面,也见证了这写照其实无能为力表出认识论的危机。这是说,《弗兰肯斯坦》面对当时风起云涌“新”科学带来的认识论危机,打通外部物理空间和内部心理空间,表征出一种创伤的文化经验。创伤发生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两者的肉身分别是青年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和他痴迷科学、走火入魔之余创造出来的怪物。这个他者原是自我一手炮制出来,然而一旦出笼,便不复为自我能够制约,反而上天入地噩梦般追踪起了自我,一如怪物形影不离地跟踪着他的造物主。不为别的,只为创伤复仇。反过来亦然。这一作为重复强制的创伤情结,在小说的结构上表现也为明显。这是一部以见证人视角且由见证人本人开讲故事的作品。不但以第一人称叙述,而且重复叙述。如怪物不平自己诞生后遭遇的孤独和歧视,小说就安排了重复叙述的场景,一次是在日内瓦,怪物杀死威廉后向弗兰肯斯坦交心;另一次是在北极,小说结尾怪物在弗兰肯斯坦死后,对沃尔顿船长作身世交代。你来我往,跟踪追击,不为别的,只为创伤复仇。无怪乎沃尔夫雷斯说:“维克多•弗兰克斯坦可能拥有科学知识,但是他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他对自己行为的意义一无所知,所以他给自己制造的怪物幽灵穷追不舍。同样,小说叙事只有通过形形色色的复制和重复,方能传情达意。其素材上内部和外部无以弥合的裂缝,其持续不断在提醒主体的分裂,都在以一个特殊的声音,宣告着现代性的创伤。”aJulian Wolfreys,“Trauma, Testimony, Criticism: Witnessing, Memory and Responsibility”,in Julian Wolfreys ed.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p.142.
这还是凯茜•卡鲁斯建构的批评模态:创伤作为无人认领的、不被承认的被压抑事件,它永远是我们无意识之中一个无以解开的心结,自此以往,我们的一切日常语言和日常经验,将莫不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而上述现代性的创伤,是叙事人的创伤也是读者的创伤。作为造物主的叙事人凭借科学造出他者,一个伤痕累累给弃之如敝履的怪物,却无法对他负起责认。读者也同步为之心悸。这个怪物太不像人类,又太像人类,这都是我们如饥似渴科学梦种下的创伤吗?小说的叙事人当时浑然不知,过后频频惨食恶果,却依然未解创伤的根本因由。现代人的这一创伤困境,沃尔夫雷斯发现甚至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已经有迹可循。《资本论》的第一句话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b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页。这个“庞大的商品堆积”,岂不同样是个一旦被人类创造出来便不复为其主人控制的怪物?要之,创伤之无所不至,如影随形地追随着我们,究竟可以如何书写出一个更为清晰的物理和心理谱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