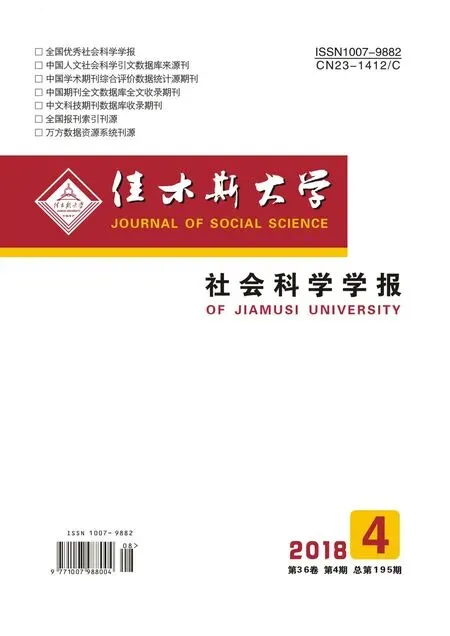叩问真实:论张抗抗《隐形伴侣》中的童话变奏*
2018-02-12李琴
李 琴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张抗抗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讲述的是一对知青恋人肖潇与陈旭在北大荒相爱却因相守艰难,最后只能分开的故事。小说以女主人公肖潇的视角,巧妙设计一系列的童话故事穿插于文本之中,人物心理与童话变奏相融,游离于社会现实与童话故事两者之间,给予现实生存处境与内在精神追求以双重思考,一再地叩问着生命的真实。所谓“变奏”,原本属于音乐领域的专业术语,变奏手法是指“一种将原型曲调加以变形之后,进行再重复的旋律发展手法”[1]80,而文学中的变奏也就是指在原作品的基础上添加一些修饰或者作一些变形,使得文本具有更丰富的表现形式。《隐形伴侣》中的童话书写,正是在已有的童话原型基础之上,对原故事作了一些修饰与变形,使之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更好的表现了主人公的感情与思绪,同时也传达出作者对于“真实”更深层次的思考,文本具有了更丰富的文化意蕴。
一、 梦幻般的童话书写:变奏曲的多面展示
《隐形伴侣》以女知青肖潇的视角,穿插讲述了一系列的童话故事,使小说洋溢着梦幻般的奇妙色彩。其中包括雪白的天鹅蛋、丑小鸭、农夫与金鱼、海的女儿、青蛙公主、小蝌蚪找妈妈、七色花、快乐王子、海的女儿等,都是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张抗抗小说中的童话书写,是在童话原型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将人物的心理发展过程与童话故事相融合,尤其是在童话中加入大量主观的幻想与情绪,呈现出多样化的童话变奏。
作者将童话书写融入对女主人公肖潇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写到肖潇对于童话的执着,还写到肖潇在童话基础之上添加了自己的个人幻想,常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童话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试图在现实世界里追求童话世界里的自由,她这种自由不羁的幻想与童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特有的童话幻想来抒发心中所感所想。所谓“童话幻想”,是人物在一定情况下对童话的幻想,这种幻想有着多方面的展现,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积极的正面幻想,指幻想力向提纯、美化的方向驱使,另一类是消极的负面幻想,指幻想力向扭曲、丑化的方向推动,这两类幻想在《隐形伴侣》中都有具体的呈现。当肖潇心情愉悦、情绪高涨时,更多倾向的是正面幻想,正如当她和陈旭在湖边浅滩上惊喜的发现一只仙鹤时,她想到“如果能捡到一只天鹅蛋就好了”[2]33;当肖潇生产后没有奶,牤子送来半麻袋鱼时,在她眼前出现了一只雪白的天鹅,天鹅本身即是高贵与美好的象征,而这只天鹅“停在她脚下,怀里滚出一只洁白的天鹅蛋。”[2]195这便是对美好事物的进一步幻想,并与个人的主观期待完美相融。正如高尔基所说,“童话幻想能够打开通向另一种生活的窗子,幻想更美好的生活,有一种自由的无畏的力量存在着和行动着”[3]149,童话的确具有如此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而当肖潇情绪低落或者遇到难题时,负面幻想则会一涌而出。小说写到陈旭、泡泡儿等人在男宿舍打群架时,肖潇想到的是“那只天鹅蛋呢?一定是碎了,中午在低头就碎了”[2]10之后与陈旭分手,也一再想到破碎的天鹅蛋。然而,肖潇在产生负面幻想之后,又多次借童话来倾诉对于自由的渴求。正如在经历了生活的艰难和陈旭的欺骗,肖潇受到身心双重折磨之时,多次喊出这一祈求:“老爹爹,放了我吧,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2]32这正是借《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童话,表达着肖潇内心对自由、安稳的极端渴望,童话中的金鱼是遇见了一个好心的渔夫,从而化险为夷,肖潇也幻想能像金鱼一样转危为安,回到平稳的生活中去,真正获得自由,这是对安稳的渴求、对美好的向往和对自由的真切呼唤从而获得继续坚持、努力奋斗的勇气。因此小说整体上还是以积极向上的童话幻想为主,呈现出梦幻般的童话世界,这些幻想在某种程度上都能十分吻合地反映主人公的真实情绪。
童话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并非全是虚构,实际上也来源于生活。正如著名世界童话家安徒生也曾有过相关论述,认为最奇异的童话也是从现实生活里产生出来的。张抗抗正是基于对北大荒生活的熟悉,从而将北大荒特有的元素与童话故事相结合,在表现肖潇与童话的关系时,非常真切自然地呈现出与生活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下,肖潇对于童话的幻想也随之变化。当小说开头写到陈旭和肖潇准备逃离北大荒时,小说出现了《渔夫与金鱼的故事》的场景,金鱼“苦苦哀求:老爹爹,放了我吧,你要什么我都给你”;而在经历了一路颠簸,终于逃离北大荒时,原本以为新的生活即将开始,但回到杭州的她,同样面临着无家可归的窘境,即使跟随陈旭回了家,仍没有安身之地,只能躲在一间小黑屋子里,此时肖萧再次体会到了人情的冷漠与生存的绝境,她深刻认识到自己此时就是一只丑小鸭,只能选择再次逃离,“这是因为我非常丑陋的缘故!小鸭想。于是它闭起眼睛,仍然继续逃跑”。这个即将要逃离的家乡是原本自己所期望的美好归处,而能去往的地方却是原本逃离的北大荒,这种多重纠结下的折磨,给肖潇带来了更深层的心理创伤。回到北大荒,结婚的两人慢慢融入当地的生活,感受到小日子的满足,此时肖潇重拾了对生活的幻想,幻想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然而,随着孩子的不期而至,为人父母的肖潇与陈旭矛盾越来越多,肖潇无法真正直面陈旭的欺骗与丑恶本性,在迷惘和挣扎中的美好幻想也随着破灭,她感到了丑小鸭原有的弱小、丑陋和无助,因此在写到奇丑无比的小鸭子脚下有一中洁白的天鹅蛋时,“忽而那只蛋裂成了两半,从中飞出一片白云,悠悠地升上天空去……”倘若说肖潇还坚持相信丑小鸭一定会蜕变为美丽的白天鹅,但却又因生活的打击而表现出“丑小鸭何时才能变白天鹅”的无力感,美丽的天鹅蛋终将破碎。直到小说末尾,“金鱼”的童话原型还在文本中穿梭,“金鱼们朝一条大网中游去,又从网眼中穿出,摇摇尾巴不见了”,若有若无的童话幻想穿插于人物描写之中,到底什么才是真实,哪部分是真正的美好,却又无从知晓,这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与虚幻相交融的浪漫世界。作者虽然不直接去描绘北大荒的真实生活,但是借助幻想去塑造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却又具有现实意义的形象,通过对于美好童话故事的展现,间接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与残忍,借童话幻想来让女主人公肖潇内心的情感得以自然的宣泄,一再地叩问着生命的真实,以追寻超我的自由。
二、 多因素的童话生成:女作家的深刻体察
《隐形伴侣》中有如此梦幻般的童话书写,与作者自身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少年时期对于童话故事的喜爱与女性作家和童话之间的亲密联系,成为张抗抗善于在小说中进行童话描写的重要原因。正如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所说,“人的这类精神活动始初的痕迹应当到儿童那里去探寻。无论是诗人,还是儿童,都能够创造自己的幻想世界。”[4]59可以说作家的童年生活对其创作有着重大的影响,张抗抗小时候大量接受了“渔夫与金鱼”“丑小鸭”“灰姑娘”等童话原型故事,这得益于母亲的启蒙教育。张抗抗的母亲自己就写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1948年印成了《幼小的灵魂》一书,抗抗在三十年之后还是非常爱读这些作品,正如张抗抗回忆母亲时说道:“她教会我背诵普希金的长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会在她学校举办的文娱晚会上,用童稚的声音清晰地朗诵起来:在蔚蓝色的大海边,住着一个老头儿和他的老太婆……”[5]4,这些都成为作者童年挥之不去的记忆。
除此之外,张抗抗从小就很喜欢童话并且看过很多童话故事,“妈妈经常从学校借回来那么多的童话和儿童文学,《灰姑娘》《丘克和盖克》《鲁滨孙漂流记》,都是我从小熟读的书。妈妈有时开玩笑就叫我‘丑小鸭’,我非常喜欢安徒生的童话。”[5]6这些童话故事深深地影响了张抗抗的小说创作,因此《隐形伴侣》中反复出现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与《丑小鸭》,尤其是丑小鸭的故事让张抗抗更有感触,正如作者所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也像一只可怜的‘丑小鸭’,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飞到天上去。”[5]6可见丑小鸭的形象已成为张抗抗心灵镜像的反映。可以说,这些童话被定格为一个个电影镜头,存储在作者的头脑中,几乎可以伴随一生。
童话,是天真纯洁、浪漫梦幻的代名词,“童话书写本身就实现了从创作到出售的全程连贯的烂漫,成为一种浪漫的表达方式与言说可能。”[6]253因此,童话不仅仅局限于天真的儿童群体,女性实际上也拥有天真烂漫、纯真可爱的气质,成为童话的忠实追随者,张抗抗即是如此。实际上,女性与儿童向来都被认为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而被关注。“女性和儿童在相当漫长的时期内处于从属地位,都曾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讨论‘第二性’时,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就看到无论是男权社会还是女性自己,都把女人看成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孩。”[7]19女性与儿童一样实际上都具有天真浪漫的气质,对童话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之感。尤其是女性成为母亲需要养育孩子时,会给孩子讲述大量的童话故事,这又拉近了女性与童话之间的亲密关系。两者的这种亲近关系使得女性创作更易于受童话的影响,张抗抗也正是更倾向于以纯真的童话来表现女主人公的复杂心理。在主人公肖潇回忆自己母亲时,直接以自己儿时对于童话的回忆为素材:“她讲了一个《快乐王子》,又讲了一个《海的女儿》。是妈妈讲给她听的,她再讲给妹妹听。”[2]87这就是使得童话故事代替现实生活成为了肖潇对于童年的回忆,此时的童话故事已经具有了更深层的内涵,成为联系着母亲、肖潇、妹妹三个女性之间的精神纽带,也成为他们共同的集体记忆。
三、 悲剧性的童话破灭:善与恶的真实表露
在肖潇经历了精神的磨难之后,并不曾找寻到自己坚持的那份真实,她一直坚信着丑小鸭一定会变成白天鹅的愿望,终究还是破碎,不仅没有蜕变成白天鹅,还陷入了更深的困惑与迷失之中。这种童话的悲剧性破灭,既是社会使然,也是时代的必然。然而,不得不指出,借用虚幻的童话世界,来追问真实,事实上就已经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主人公所一直追求的善的真实。满嘴谎言的陈旭所代表的人性恶的真实,是为肖潇所不能接受的,她甚至不承认这也是人真实的一面。她一直所追求的隐性伴侣,实际上也是在真假、善恶之中,肖潇自始至终得不到自己追求的真实。小说最后以极具悲剧性的童话破灭作为结局,也真实的揭露了善与恶存在的必然,无论是肖潇追求的善的真实,还是陈旭人性的恶的真实,都是不可比回避的必然存在。
张抗抗作为一名北大荒知青作家,始终关注着知青,但向来主张反映知青人性之恶,展现知青历史中的阴暗面。在她看来,“知青的历史,实际上是时代的悲哀。知青不仅只有值得炫耀的经历,更多的是恶,是黑暗。”[8]295因此她在《残忍》写下了牛锛、马嶸的恶,《白罂粟》中写到狮子头的恶,到《隐形伴侣》写下了肖潇、陈旭的恶。知青的这种恶是在文革开始时在城市里就已埋下的恶果,紧接着又把恶带到了诸如半截场的北大荒。正是这样的社会,处于一个法律没有法庭的时代,真的真实与假的真实相互交织,向来憎恶撒谎与欺骗的肖潇,也无奈成为虚伪的代言人,昔日美好的童话理想难以生存,成为泡沫。而正是她所痛恨的丑恶的世界使她自己也成为一个虚假、不道德的伪君子。事实上,作者将肖潇与童话相融合,一再地对真实发出强烈的叩问,正是在指出我们不能只看到善与美的真实,而恶的真实、丑的真实也是不可回避的必然存在,正如作者所说:“我的知青作品不是时代的一个简单诠释,不是简单述说知青的苦难,也无意探讨知青运动的得失,而只是籍此揭示更深的人性”[8],在真与假中揭示人性的真实,这也是作者对于知青历史给予的深层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