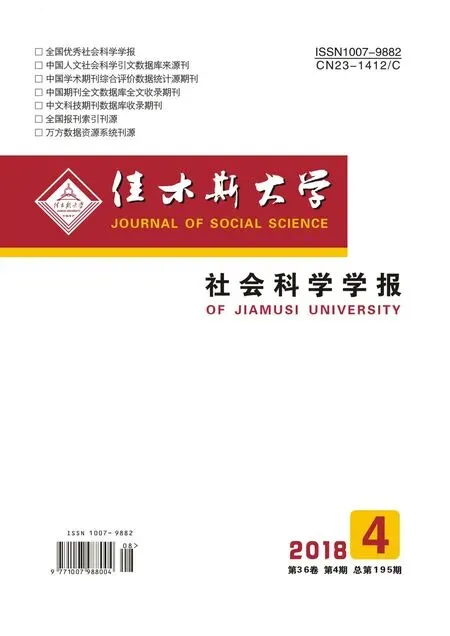罗烽文学创作中的民族主体意识*
2018-02-12王璐
王 璐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罗烽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重视对民族感情的表达,民族主体意识突出。在创作过程中罗烽不回避惨烈的现实,将当时社会的黑暗、生活的悲惨,真实、全面地展现出来,透过生活的苦难体现出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普通大众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罗烽的文学创作融入了更多的政治思考,从多元的视角,对战争背景下的中国社会有更敏锐的感知,而这也是罗烽文学作品打动人心,引人深思的主要原因。
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视角下的民族主体意识
罗烽在文学创作中具有鲜明的责任感,文学与革命是他人生中的两大主题。五四新文学运动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起到了引导与推动的作用,现实主义创作思想也对罗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
(一)反抗性
对罗烽文学作品中的地理分布进行分析,可见他放眼中华,叙事场景多样,不拘泥于东北。在关注东北沦陷的同时,也描写抗战背景下全中国乃至世界,并且这些描述并不是平铺直叙,简单的还原和再现。罗烽绝大多数小说都与抗战相关,其中较为典型的包括《特别勋章》、《万大华》、《空军陆战队》、《一条军裤》等。这些小说所展现的都是真实生活中曾经发生的,被罗烽收集提炼,成为时代的定格。在罗烽的写实创作中有种典型的表达:对底层广大群众进行描写,呈现人性的真实,显示战争中生活百态,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操。
《第七个坑》从名称到内容叙述都展示了罗烽独特的创作视角,写实的创作风格。小说以东北沦陷为背景,战争之前的沈阳城社会大众的生活相对平静,而战争成为撕破安逸假象的利刃。鞋匠耿大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最初日本人攻占沈阳,耿大内心深处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家国意识,他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生存问题,想要尽快脱离战争的窘地,为了生存决定寻求舅舅的帮助。然而他被日本人抓了壮丁,被强迫去挖葬坑,用于填埋日本侵略者屠杀的中国民众。小说前半部分耿大身上有着典型的小人物特质:懦弱、胆小、屈从强权,一直按照日本人的安排行事。随着故事的推进,耿大被自己眼前的一切所震惊:他看到一个个与自己相同的中国人被埋葬在自己亲手挖的坑里,甚至这其中还有自己舅舅的身影。他的内心开始出现害怕、惊恐、愤恨、仇视等情绪,这种情绪的转变是层层递进的,是随着压迫的增加、现实残酷的加重,不断累积的,使得第七个坑成为爆发的界点。第七个坑在小说中具有多重意义:第七个坑是日本人将要埋葬耿大的坑,突出了日本人的残暴冷血;第七个坑彻底激发了耿大内心的仇恨和反抗的勇气,成为抗争精神爆发、民族意识觉醒的关键;第七个坑埋葬了耿大作为小人物的懦弱、胆怯,埋葬了他对战争、对列强不切实际的幻想,让耿大获得了重生。耿大的反抗让人血脉贲张,让读者看到一味忍让、怯懦无法获得真正的安逸,只有勇于反抗、直面鲜血才能改变现状,打击侵略,获得真正的平静。
(二)批判性
罗烽小说的批判性主要针对两个方向,一方面要对日本侵略者的恶行进行控诉,同时也将目光投注在了统治阶级身上,看到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爱国热情并没有让他失去冷静的思考,相反在对社会现实进行认识的过程中,罗烽有着更加克制的一面,他在创作过程中对中华民族自身存在的劣根性给予了揭露,痛批了当时民族精神层面的畸形。小说《特别勋章》中罗烽将人性的拷问对准亲情,故事以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成立为背景,伪满洲国警备司令的儿子作为新青年充满爱国热情,不与父亲为伍,积极投身起义。父亲为了利益、仕途,牺牲父子亲情,演出了一场“大义灭亲”的闹剧。这种描述看似艺术的夸张,实际上却正是对伪满统治下真实的描述。在作品《左医生之死》中罗烽也运用了相同的叙述手法,该作品成功塑造了一个虚荣、自私、懦弱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战争来临后,左医生安心做顺民,在战乱中不断钻营想要获得更多的好处,但事与愿违,不仅没能保持安逸的生活,还被自己的亲人陷害,为别人替罪。左医生对虚荣的追求最终成为致命的枷锁。左医生之死打破了现实生活中顺民们自我构建的假象,让他们看清对侵略者一味的顺从,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1]。
二、双重身份视角下的民族主体意识
罗烽的作品对历史的真实性给予尊重,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由于其革命者的政治身份,使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罗烽本人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生积极投身于革命工作之中,曾经是文艺运动的灵魂性人物。他也曾表示,自己一生之中共产党员这一身份高于一切。我们不仅对作品进行文学层面的分析,还要考虑作者身份上的多重性,基于罗烽的多重身份,对罗烽创作中的民族主义意识进行深层分解。
首先,罗烽在对社会现实的揭露上更加的彻底,能够站在革命者的视角,对社会现实进行鞭挞,对普罗大众的抗争精神进行传递,其作品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呼兰河边》。萧红在同时期也曾创作小说《呼兰河传》,对二者进行横向对比,能够更清晰的感受到罗烽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政治倾向。萧红的作品中体现了浓重的个人情感,整个作品无处不融入她的个人回忆,其中既有对战争的关注,也有个人对往昔岁月的倾吐。而罗烽则给予战争更加直观的描述,在讲述放牛娃被杀时,将日军的残酷、凶狠、冷漠表现到了极致。让我们看到,战争对人类的伤害没有性别、年龄上的分别,即使是一个孩子在战争中也随时有被屠杀的可能。小说《荒村》中罗烽延续了这种批判的写作形式,通过批判揭露的方式,进一步唤起国人的民族主体意识。荒村中最令人震惊的描述在于村庄中已经几乎不见女性的身影,侵略者对村庄的女性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迫害,小说虽然以文字的形式呈现,但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却仿佛看到了夜色中的恐怖,听到了少女绝望的呼喊。而深井中传来的歌声,更是加深了读者对荒村中女性的同情,看到了女性在战争中的悲惨处境。而罗烽之所以对这些惨烈的场面进行描述,正是基于一个革命者的视角,抱着揭露罪恶、鞭挞现实的决心,传达抗日的精神,唤起大众的民族血性[2]。其次,罗烽文学底蕴深厚,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在人物塑造上趋于多样化,其小说中既有普通的底层群众,也有先进的知识分子,还有不屈的抗日英雄。在其作品《五分钟》中罗烽就塑造了一个让读者印象深刻的英雄形象——贺铮。“铮”有刚正不阿之意,而小说中的贺铮人如其名,从始至终无论是面对敌人的诱惑还是严酷的刑法,仍然坚持真理,不作奸佞小人。敌人给了贺铮五分钟决定生死的机会,贺铮却并未动摇,用纵身一跳诠释了自己的铮铮铁骨,而这也是小说取名五分钟的缘由。这种艺术上的创作,具有深意的写作手法,增加了罗烽作品中的耐人寻味,让读者能够切实体会到小说中所传递的民族精神。[3]。
三、 理性思辨视角下的民族主体意识
罗烽在进行文学创作过程中,坚持了理性思考的原则,能够从理性思辨的角度进行文学的创作,因此其笔下表现出的民族主体意识更加的冷静克制,有着更高层次的全局观念和审美判断。谈及理性涉及的关联词汇就是严肃、深沉,而这也是罗烽文学创作的主要特点。在小说《一条军裤》中,以物为线索,传达了军民感情,对军民关系给予了客观的思考。小说中主人公马彦德是典型的军人形象,有着革命军人不怕牺牲、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感。与其它文学作品中突出表现军人英勇形象不同,罗烽在该部作品中描绘了普通大众对军人的维护,对革命部队的情感。军裤在小说中是身份的象征,因为军裤的暴露,致使日军展开了搜捕,为了保护马彦德,一直被认为是弱者的普通村民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谎称军裤是自己的,最终被侵略者所杀害。罗烽在该部小说中传递出了军民团结,共同抗战的思想,这是罗烽对战争理性思考的结果,他意识到单纯依靠人民军队,单纯将普通民众定义为被保护的一方是错误的。广大人民群众有着惊人的战斗力,在抗战过程中只有军民一心,充分发挥多方面的力量,才能更好的与侵略者进行抗争。这样理性的思考,明确的政治视角,在同时期抗战小说中极为少见,可以说是抗日文学中的高峰之一。
除了军民关系,罗烽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也涉及到了战俘处理问题。该类问题很少得到文学创作者的关注,但罗烽却意识到这是抗战中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在小说《空军陆战队》中,罗烽转变了写作视角,透过被俘日本军官栗原的内心活动,展现出了我军的国际主义精神。栗原被抓后一直处于恐慌之中,他惧怕遭到中国军人的报复,在被救治的过程中一直怀疑医生会要了他的命,怕中国军人对战俘采取日军一样的处理方式。但是随着被俘时间的推移,栗原意识到中国军队是真正的仁义之师,不仅为其提供了医疗救治,同时给予了亲切的慰问。罗烽用大篇幅的陈述了空军高级军官对战俘的讲话,在讲话中军官并没有对战俘进行严厉地谴责,相反他认为日军战俘也是这场非正义战争中的受害者,日本的侵略不仅伤害了中国民众,也打破了日本军民平静的生活,同样将日本民众拖入苦难。在当时社会中,大众对日本军人充满憎恶,这样的文学作品无异于是抗战作品中的一股清流。罗烽清醒的看到了战争的本质,对战争进行了深度剖析,小说中呈现出的人道主义光辉,高格局的政治视角,使得读者对战争产生了更全面的认识[4]。
四、国际主义视角下的民族主体意识
罗烽在流亡过程中接触到了左翼文学,这一经历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增加了对白俄侨民的关注。罗烽的视角更加具有国际主义观念,他结合自身经验,看到了白俄侨民在中国的真实遭遇,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逐步扭转了社会大众对白俄群体的社会认知,让大众意识到白俄侨民与中国民众一样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是抗战过程中携手并肩的兄弟,是抗战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品《考索夫的发》是罗烽白俄文学创作的代表,在该部作品中罗烽通过对白俄侨民考索夫悲惨经历的描述,从国际主义视角对民族主体意识进行展示。主人公考索夫与真正的白俄侨民有所不同,是一个中俄混血儿。对于混血儿而言,最大的矛盾点就在于自身民族属性的选择。处于特殊时期,考索夫的混血身份使其陷入了万分尴尬的境地,关于国籍的问题经常让他感到羞愧和苦恼。罗烽在进行人物塑造的过程中,将现实里中俄混血儿的普遍遭遇都汇聚到了考索夫身上:他没有优越的家境,没有强势的父母,在生活中混血儿的身份让他备受嘲笑,最让他感到愤懑、导致他备受嘲笑的直接原因就是他一头黑色的头发。罗烽将作品定名为《考索夫的发》具有多层含义,其中最主要的含义之一就是引发故事开始,推动情节进行,同时考索夫黑色的头发也是他最终树立民族主体意识,找到民族归属感的关键所在。罗烽以头发为线索,通过“剃发”和“留发”,体现了少年民族主体意识的萌发和蜕变。[5]
幼稚阶段:剃发的考索夫认定自己为俄罗斯人,受到白俄反革命分子的影响,对革命怀有仇视心理,想要实现俄国沙皇的复辟,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幻灭阶段:考索夫将头发作为融入日本侨民的途径,将剃掉的黑发留长。头发并没有帮助考索夫成为日本人的一员,相反他极力想要逢迎并融入的日本群体,对他实施了惨无人道的轮奸。经历兽行的考索夫扯掉自己的头发,暗示考索夫对日本侵略者的否定,内心反抗意识的觉醒。清醒阶段:考索夫的父亲在为儿子复仇的过程中被害,考索夫也被逮捕入狱。入狱后他的头发开始新生,这次他坚持不接受剃发。考索夫已经在心中对自己的民族属性进行了选择,并将头发等同于自己的民族精神,通过留发的形式,坚持自己的民族信仰。最后,考索夫临死前留给母亲一缕黑发,是他民族主体意识的成型,是对自己中国人身份的肯定。
罗烽在民族主体意识表达上另辟蹊径,多处使用象征性的叙述方法,带有多重寓意。考索夫所经历的正是中华大地正在经历的,考索夫所作出的选择,也正是中华民族最终需要作出的选择。罗烽的国际主义观念对白俄题材文学作品进行了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增加了客观性和现实意义,并且通过创伤的描述,勾画出了清晰的民族主体意识,让悲剧折射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唤起读者的爱国热情,强化普通大众投入抗日战争的勇气和信念。
综上所述,罗烽在众多抗日文学创作者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思维更加的理性,视角更加的全面。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传递出罗烽鲜明的政治观点和民族意识。对罗烽作品再次研读,将罗烽一生的经历以及罗烽的政治信仰与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文学创作者,感受到了一个作家在抗战时期高尚的民族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