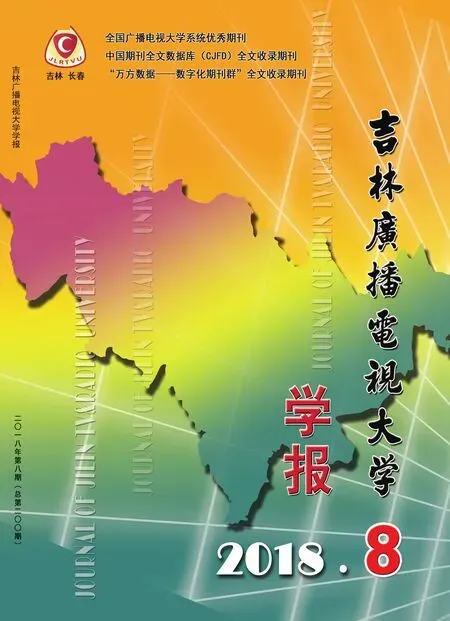电影《飞越老人院》和《百岁老人跷家去》的跨文化解读
2018-02-11王丽皓
王丽皓
(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一、电影简介和问题的提出
中国电影《飞越老人院》讲述的是老人院里一群各怀心事的老人,偷跑出老人院,去走自己从未走过的路,去看自己从未看过的风景,以实现自己最后的梦想,获取属于自己的快乐的故事。瑞典电影《百岁老人跷家去》讲述的是阿朗·卡尔松经历了自由、传奇和冒险的一生,在自己100岁生日庆典前的一刻逃离养老院,希望摆脱养老院里单调的生活,继续精彩的旅程。
虽然两部电影都被归类于喜剧,但是,《飞越老人院》里的中国老年人给人的感觉是压抑和悲情的,豆瓣影评里很多人都说自己看这部电影从头哭到尾,即使是笑,也是含泪的笑。反观《百岁老人跷家去》里的主角阿朗,则是活得随心所欲和无忧无虑,观影体验是开心地从头笑到尾。为什么两部影片都叙述了一个老年人从养老院出走,追寻自己梦想,追寻顺遂自己心意生活的故事,然而,中瑞两国老年人自始至终的心境却截然不同呢?以下拟从中瑞文化对比的视角对这种不同的心境产生的根源进行剖析。
二、跨文化分析
1、相互依赖与相互独立
Hofstede把各国文化用五个文化维度来区分,其中一个文化维度是“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根据他的理论,具有集体主义文化维度的人相互依赖,而具有个体主义文化维度的人习惯于相互独立。
Samovar在探讨文化的基本功能及其深层次根源时指出,文化服务于人类的基本需要,向每一种文化中的人展现出置身这种文化里的可以预知的世界,同一种文化里的人享有相同的世界观,从而带给人们安全感。
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父母对子女有养育的责任,有为孩子的婚嫁做物质准备的责任,甚至有照看孙辈的责任。反过来,子女对父母有尽孝道的责任,这个孝道,不仅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理想状态下,父母和子女都尽到了对对方的责任,双方是互相依赖的,这种依赖,让所有人都感觉到安全和幸福。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养儿防老”、“百善孝为先”等正是带给结婚生子的人以这种安全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子女的依赖会越来越强。
然而,现实生活不可能都是理想状态,当父母和子女对对方的期望落空时,失望和怨恨等情绪会随之产生,尤其是老年人那种老无所依的感觉更让人感到凄凉。在《飞越老人院》里,老葛和儿子的关系就是这样。老葛的妻子早年去世后,老葛很想和意中人重新组建家庭,然而,他的儿子却为了得到家里唯一的房子结婚而对老葛的婚事百般阻挠,最后,老葛被逼出家门,和一个自己并不爱但有房子的女人结了婚。老葛儿子的想法是:你是我父亲,你有责任给我婚房,即使你把房子给了我,你给我的还不够多,因为这房子太小太破,而且你也没能力给我找个好工作。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始终对老葛心怀怨恨,常年不来往。这种想法超出了传统文化里子女对父母的依赖范围,而且,孝顺的子女是不会为了自己结婚而把父母赶出家门的。
老葛在续弦老伴去世后,又被毫无血缘关系的续弦老伴子女“请”出家门,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只好到养老院投奔自己多年好友老周。为了宽慰想自杀的老葛,老周邀请他参加排练娱乐节目。然而,即使大家一起欢笑,老葛的内心一直是落寞的,究其原因,就是老葛的幸福是寄托在儿孙身上的,在他大半辈子里,从未享受到来自儿孙的孝顺和尊重,以及天伦之乐,他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反观《百岁老人跷家去》里的阿朗,活到了100岁,仍然风趣幽默,随心所欲,笑口常开,这和他所处的瑞典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和中国文化相比,瑞典文化是个体主义文化,人们从小就学到的处世之道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必须照顾好自己,不能依赖他人,包括家人。瑞典孩子自己挣零花钱,甚至自己挣钱周游世界是很普遍平常的事,父母甚至不用为孩子上大学、结婚、生子负责。当人们老了,伴侣之间会互相照顾,或者会自己照顾自己。不能动了,就去养老院。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幸福和子女没有任何关系。
在此文化背景下,阿朗的人物设定和瑞典科学家诺贝尔一样——一生未婚,一生充满奇遇并与炸药结缘。他的幸福只与他随时出现的疯狂想法有关,只取决于他自己,而与儿女无关。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后,阿朗住进了养老院,但是,那颗不安分的心却在养老院为他举办的百岁生日庆典之前蠢蠢欲动,他终于厌倦了在养老院里受到的看护和里面的规矩,逃出了养老院。逃出后仍然像他年轻时一样,把世界搅得一团糟,而他却乐不可支。无忧无虑的阿朗一定无法理解憋屈的老葛,因为他从未期待过被人照顾,甚至讨厌被人照顾,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
2、群体和谐与个体幸福
Scollon指出,在集体主义文化里,当集体内部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出现分歧时,集体的和谐总是被看作最重要的。③换句话说,人们宁愿牺牲个体幸福,也要维持集体的和谐。但是,在个体主义文化里,个体幸福高于一切。
在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里,家庭是十分重要的集体,人们为了赢得家庭的和睦而牺牲个体的幸福往往会被视作高尚的表率。所有人都有自己梦想,但是,有多少人从年轻时开始,为了孩子而放弃了五彩斑斓的梦,并逐渐满足于平淡的生活。电影中,老葛为了儿子放弃了自己的真爱,放弃了身心的自由寄人篱下。养老院里其他的老年人也都有没有实现的梦想,然而这些梦想止步于儿女们的制止,儿女们对养老院院长的解释表面上是为了老人的安全,实际上还是怕给自己惹麻烦。老人们为了与儿女和睦相处,只好叹口气作罢。中国自古有“人老雄心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等名句,然而,这些普通老年人,只好把梦想的实现寄托于几个胆大的同伴,借他们的眼睛看世界。
阿朗就不同了,在瑞典的个体主义文化里,他的所有行为从年轻时开始,就完全受他自己意志的支配。阿朗的人生旅途处处有精彩,他周游了整个世界,结识了无数名人,到了100岁还有勇气尝试新的生活并乐在其中。虽然故事是夸张的,但是,实际生活中的瑞典人确实父母和子女各有各的幸福生活,互不干涉。笔者在瑞典访学期间看到,有很多父母和子女之间和睦相处,但这种和睦是建立在父母和子女相互独立的和各自幸福的生活上,而不是建立在互相为对方做出的牺牲上。比如,瑞典老年人想出门旅游就旅游,不会看儿女脸色,他们也绝对不会给儿女当照顾孩子的免费保姆。
3、间接表达与直接表达
Hall把各国文化维度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④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的交际比较隐晦和间接,只有极少的信息通过语言编码的方式传递;在低语境文化中,人们的交际比较坦率和直接,大多数的信息通过语言编码的方式传递。
中国文化是高语境文化,受到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儒家思想强调“礼”,提倡用含蓄的语言表达,而不是有话直说,这样不仅可以顾全交际对方的面子,也会顾全自己的面子。但是,有话不直说有时会造成长期的误会。老葛就是一例,他受到儿子的粗暴对待后,委屈地和养老院里的老伙伴们诉说自己的苦恼,说怕孙子也记恨自己,总想找个机会跟儿孙解释解释,可老也张不开嘴。最后,当他有机会和孙子解释的时候,他还是张不开嘴,还是没有把当年的事说清楚,而是讲了个故事:一个儿子嫌弃年老的父亲总是指着麻雀问他“那是什么”,父亲告诉儿子,儿子小时候就总是连续这样问父亲,而父亲却始终不厌其烦地告诉儿子“那是麻雀”。老葛通过这个故事,委婉地表达了父子亲情。幸而孙子原本没有多少对爷爷的偏见,所以立即明白了爷爷的良苦用心,如果换做是老葛的儿子听这个故事,老葛恐怕就要白费劲了。
相比之下,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瑞典人的交际方式就是有事情就说清楚,而且越明白越好。阿朗就是这样,自己不能做的事绝不勉强答应。在车站,一个蛮不讲理的年轻人让他帮着照看行李箱,阿朗因为要赶长途汽车,坚决地说“不行”,而不是为了面子,宁愿误了车也要等那个年轻人。阿朗教导陷入爱情的年轻人要自己去争取,要现在就勇敢地走过去,直接告诉对方自己的想法。因为阿朗一生中都是这样有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他从未受过老葛那样的委屈。
三、结语
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和高语境文化,传统思想深厚的中国老年人往往为了家庭和睦而委曲求全,孩子是否孝顺对中国老年人的幸福感影响巨大。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瑞典文化是个体主义和低语境文化,其文化里没有“孝”这个概念,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孩子没有任何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使得中国人接触到很多外国文化,我们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应该做到“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即,我们虽然可以批判地借鉴外国文化,但是,绝对不能盲目地接受外国文化。在对待外国文化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各美其美”,即首先要认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一“孝道”坚决不能丢掉。在全国上下都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年轻人和中年人要以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尽其所能尊敬老人、爱护老人,尽量不要让《飞越老人院》里表现的对老年人的漠视等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