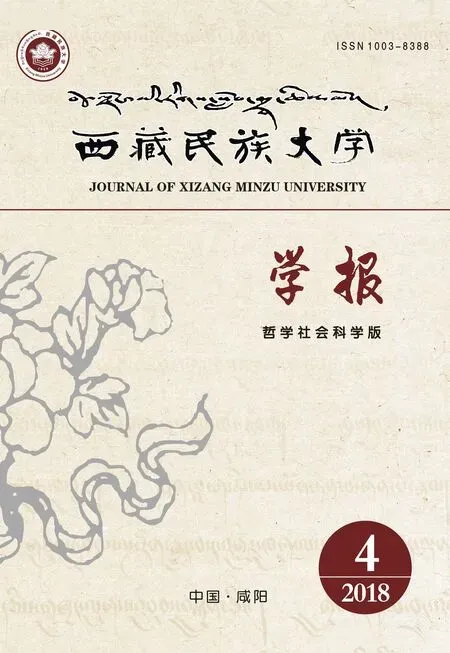探析戏师在藏戏中的核心地位
2018-02-10李宜
李宜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藏戏是藏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它主要流行于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及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国藏民族聚居区域。藏戏在长期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广场戏、面具戏和仪式戏等独特的演出形态,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藏戏作为传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被列入国务院、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又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戏艺术的传承和保护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笔者在多次调研中发现戏师是藏戏艺术传承和发展的灵魂人物,但是目前尚未发现有专家和学者撰文对戏师在藏戏中的核心地位进行系统研究。本文拟从戏师传授技艺、掌控演出节奏和调控演出气氛等方面来探讨戏师在藏戏中的重要地位。
一、戏师场下传授演员技艺并培养自己的衣钵传人
戏师在藏语中被称为“劳本”,常被尊称为“根拉”,主要负责传授藏戏艺术并掌管戏班的日常排练、演出等事务。戏师一般由戏班中的第一温巴(“温巴”,意为“猎人、渔夫”)或者第一甲鲁(“甲鲁”,意为“王子、太子”)这些品质优良、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担任戏师的演员必须熟悉全剧、声音洪亮、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随机应变能力强。
1951年前,寺院教育几乎垄断了藏区的整个教育,普通民众要识字,只能进寺院学习。而民间藏戏班的戏师从小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大多是不会读写的文盲,从而形成了藏戏沿袭至今的言传身教、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藏戏的口耳相传形式决定了戏师是藏戏艺术传承的主体。首先,他熟悉并掌握每出剧目中全部的唱腔、念诵、道白、舞蹈和技艺。其次,根据戏班中每位演员的自身条件分配不同的角色。最后,亲自传授该角色的唱腔、韵白、舞蹈等内容,直到演员可以登台演出。可见,戏师是藏戏艺术的传承者,其表演水平直接决定戏班的整体演出水平。由于藏戏演员大多为业余性的,平时是农牧民或者僧人,演出前临时组织起来进行排练,演出结束后,戏班解散,演员回去从事原来的工作。因此,戏师是藏戏艺术传承的灵魂人物,是戏班中所有演员学习藏戏表演艺术的老师,受到戏班成员的尊重,往往也成为管理戏班排练、演出等事务的班主。
除此之外,戏师还担负着培养接班人的重任。当戏师年龄较大不能登台演出时,他在戏班中挑选一个记忆超群、嗓音洪亮、随机应变能力强的演员做为自己的衣钵传承人,并口传身授自己所会的所有藏戏艺术,使其尽快熟悉剧情并掌握技艺,以便他早日替代自己。目前,随着藏戏老戏师的相继离世,一些表演难度较大,短时间内不易掌握的传统技艺已经失传。迥巴戏班在开场戏中穿插演出的“波多夏”情节是其流派艺术特色之一,类似于今天的杂技表演,演出时,一个身上压着石条的温巴躺在地上,其他两个温巴用铁锤砸石条,石条被砸碎,人却安然无恙。可惜这种迥巴派的传统表演艺术已经失传。昂仁县的旦巴部长告诉笔者:“掌握‘波多夏’的戏师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此种技艺当时没有传给后人,现在已经失传。”如果现在不注重保护戏师,其说雄、唱腔等诸多传统技艺无人继承,就会像迥巴派中的“波多夏”杂技表演一样,出现“人走艺亡”现象。
目前,藏戏共有十一位戏师入选文化部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是藏戏不同剧种、流派的传承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以超人的才智、灵性,贮存着、掌握着、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类别的文化传统和精湛技艺,他们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接力赛’中处在当代起跑点上的‘执棒者’和代表者。”[1](P24)因此,只有保护好藏戏传承人——戏师,才能确保藏戏艺术世代传承。
二、戏师进行二度创作并掌控场上演出节奏
戏剧是一门综合的舞台表演艺术。戏师为增强藏戏的演出效果,不但在场下对剧目内容进行二度创作,而且在场上表演时还根据实际情况对藏戏演出节奏及演出时间进行二度创作。这些都体现出戏师在藏戏中的重要地位。
剧作家写作剧本的艺术活动被称为“一度创作”。而演员根据剧本在舞台上或银幕上运用各种手段塑造艺术形象的活动叫做“二度创作”。二度创作的基本原则是依靠剧本。藏戏独特的文学剧本形态是戏师必须对剧本进行二度创作后才能传授演员技艺的原因。
藏戏剧本严格来说并不是现代完全代言体形式的戏剧文学剧本。它主要采用藏族民间说唱艺术“喇嘛嘛呢”艺人说唱时用的底本,称其为藏戏故事本更为合适。该故事本没有显示藏戏剧目演出时必有的净场驱秽、奉神祭祀的开场戏“温巴顿”(“顿”是“开场”之意)及最后祝福迎祥的“扎西”(“扎西”汉语意为“吉祥”)结尾这些仪式性表演内容。其主要表现剧目的核心内容“说雄”(“雄”汉语意为“正文”、“中心”,“说雄”即为“全剧之中心”)部分。说雄部分由散文和韵文两部分构成。散文部分主要交代时间、地点、环境、动作和情节发展等内容,语言精炼、生动形象。诗歌韵文部分表现角色之间的对话和唱白,“诗歌部分可以根据不同的人物,配以不同的唱腔,演出时由演员演唱”[2](P629)。唱词多用藏族民歌的比喻、排比形式,有时又吸收民间俗语、谚语,既富有文采又通俗易懂。藏戏这种韵散相间的剧本结构模式是戏师进行二度创作的基础。
藏戏故事本情节很长。戏班演出时,如果完全照本宣科难度很大。为了方便表演,戏师常根据剧目内容、情节结构和观众需求以及自己多年的演出经验对文学故事本进行二度创作。戏师改编演出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第一,戏师在观众喜欢的剧目内容中根据生活实际添加戏剧情节;第二,戏师通过唱腔、韵白等艺术手段重点加工某些剧情使演员能够细致而详尽地在场上表演;第三,与主题有一定关系的内容放到戏师的剧情解说中一带而过;第四,与主题无关的情节,演出时全部删掉。戏师对剧本进行“二度创作”后,再分配角色,传授技艺、指导演员排练。由于戏师的个人喜好及对相同剧情所采用的明场、暗场处理方法不一样,不同戏班在表演同一种剧目的相同剧情时则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演出形态。在传统剧目《卓娃桑姆》中,王后哈姜逼迫卓娃桑姆飞回天界,用鸠酒毒疯国王并将其关进黑牢。随后,哈姜连续三次派遣屠夫兄弟、渔夫兄弟及贱民兄弟去杀害卓娃桑姆的两个孩子。身处仙境的卓娃桑姆为保护自己年幼的儿女,多次化身为不同的动物出手相救。笔者在拉萨调研时发现不同戏班在场上演绎这部分剧情时呈现出不同的表演内容。有的戏班借助各种动物面具在场上生动形象地演绎出这段剧情:卓娃桑姆首先变成白药蛇为中毒蛇而亡的儿子吸毒疗伤;然后,她化身猴子给在密林深处忍饥挨饿的儿女采摘野果充饥;接着,又化身大鹰、大鱼救护被扔下悬崖的儿子;最后变身鹦鹉帮助儿子成为白玛坚的国王。而有的戏班则对卓娃桑姆化身各种动物救助自己儿女的情节做暗场处理,在戏师的剧情解说中用三言两语、蜻蜓点水般一带而过。可见,不同戏师在二度创作中对剧本内容取舍点不同,在观众面前的表演内容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使观众“虽观旧剧,如阅新篇”,每次都有新的审美体验。这也许是藏戏出现“每年重复来回演同样的戏剧,藏人也不讨厌”[3](P213)的观赏场面的一个原因。
藏戏韵散结合、海纳百川式的开放性剧本结构为戏师在剧目内容方面的二度创作提供了较大的创作空间。戏师在排练前经过整体艺术构思把剧本中毫无生命的文字符号变成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角色后口传身授给戏班中每个演员。
现场演出时,戏师作为剧情讲解人通过说雄形式随时根据演出时间进行艺术创作,使藏戏剧目的演出时间呈现出长短伸缩自如的特征。说雄是藏戏的正戏部分,表现一定的戏剧情节和冲突。演出时,戏师从围成半圆或圆圈的队列中走到表演区中间,用连珠韵白的念诵形式介绍一段戏剧情节,引导角色上场。演员依照剧情讲解人所讲述内容到表演区扮演剧中不同角色,通过唱腔、对白、动作、舞蹈等方式演绎完上述剧情后回归原位。随后,场上演员则一起帮腔或舞蹈。戏师再出列接着介绍下一部分剧情,演员再入场地中心表演,然后所有人一起伴唱或伴舞。如此演出程式循环往复,一直到完成整个说雄部分的演出。剧本内容全部搬到场上表演,可以连续演唱四五天,也可以通过戏师大段的说雄压缩到一天演完。而演出时间长短的变化则主要通过戏师的说“雄”来完成。当演出时间较为宽裕时,戏师按照原先排练的内容按部就班地解说演出;当所剩时间不多时,戏师则根据实际演出情况进行多度创作,把原计划在场上演出的一些剧情内容简单处理,“以说代演”压缩到自己说雄中,加快演出节奏,节约演出时间,以便进入下一段更精彩的剧情当中。英国外交家查理·贝尔在《西藏志》中也提到藏戏剧目演出时间可以调控变化:“剧本殊长,每出约自上午十时开始,于九小时后演毕,其时天犹未晚。此尚系缩短者,如全演之,每出须时数日。”[4](P207)汉族戏剧表演中较难处理的时间和空间转换问题也能通过藏戏中戏师的叙述来完成时空变化。戏师“有时几句‘雄’词就算过了较长的时间单位,或几天,几个月乃至若干年。地点变化随内容而发生,说到那里,就算抵达了那里。演出的整个过程,是场景变化的整个流程,是时间延续的一定限度的浓缩后的再现。”[5](P117)
藏戏传统剧目可以连续演出四五天,也可以通过戏师的说雄压缩到一天甚至两三个小时演完。戏师的说雄充分展示出叙述体说唱文学时空转换纵横捭阖、挥洒自如的优势,体现出藏族说唱文学对藏戏艺术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为研究汉族戏曲从说唱体向代言体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活化石般的学术研究价值。汉族戏曲剧本完成后,其中的故事情节、角色的台词和动作已经设计好,演员在场上一般不能随意增加或删减表演内容,剧目演出时间也基本固定。与汉族戏曲比较而言,藏戏则给演员的场上表演提供了较大的二度创作或多次创作的空间。
戏师通过对剧本的二度创作使文字符号变为活生生的角色并通过说雄引导角色上场,并根据演出时间长短的要求随时调整演出内容及戏剧情节的详略。不同戏班在演出相同的剧目时,观众经常会有意外的惊喜。戏师对剧本的二度创作和掌控场上的演出节奏,体现出戏师在藏戏艺术中的核心地位。
三、戏师插入即兴表演并调控场上演出气氛
藏戏在台上演出过程中,戏师通过说雄来调整剧情的详略、繁简来掌控剧目的演出节奏,同时还可以根据演出剧情随时针砭时弊,或者插入民间歌舞、喜剧演员的滑稽表演来吸引观众,活跃现场的演出气氛,促进了藏戏艺术的传播和发展。
藏戏传统剧目不多,平时主要演出《诺桑王子》《文成公主》《卓娃桑姆》《朗萨雯蚌》《白玛文巴》《顿月顿珠》《智美更登》和《苏吉尼玛》这八大传统藏戏。这些剧目可以连续演出好几天,也可以一天连演八、九个小时。观众比较熟悉剧情且观看演出时间较长,容易产生疲倦心理。如何改变这种沉闷的演出气氛是对戏师场上掌控能力的考验。“藏剧多为历史故事,主其事者须极俳优之能事,专心以赴之”[6](P29)随机应变能力强的戏师常根据观众的情绪和现场情况来随时调节演出气氛。他往往通过说雄临时打断剧情,穿插进与剧情毫无关联、能迅速吸引观众的民间歌舞、滑稽表演或藏族杂技等内容来吸引观众注意力。当所有演员共同舞蹈或载歌载舞时,演出场地鼓钹齐鸣,观众精神为之一振,沉闷的现场气氛立刻活跃起来。藏戏传统剧目《卓娃桑姆》中所穿插地舞到观众群中做各种动作并和周围群众积极互动的牦牛舞表演,经常使演出气氛达到高潮。
演出时,戏师常把最近发生的随意杀生、虐待老人等时事加入到自己说雄中,针砭时弊,教育观众,引起共鸣,增加戏剧的教化作用。他有时还通过说雄临时穿插进喜剧演员的滑稽表演,来调动观众情绪。藏戏中的喜剧演员则常利用广场演出“演员与观众同处在一个平面空间,而且相距很近,便于形成双向交流的格局和戏剧时空的自由转换”[7](P31)的优势,在表演中增加与观众的互动环节,激发观众的兴致。2013年,笔者在罗布林卡观看《白玛文巴》中国王命令神行大臣去找白玛文巴来觐见的情节时,扮演神行大臣的演员在去白玛文巴家的途中突然说:“唉,走了这么长时间的路,有些口渴。”说罢,便走到一位观众面前向他讨要了一碗酥油茶来喝,引起其他观众哈哈大笑。神行大臣的这段小插曲既和剧情有一些联系,又增加了场上和场下的互动,为观众所喜欢。藏戏的广场演出“属于一种通过最大限度的开放空间来实现演员与观众直接交流的表现形式。”[5](P115)演员与观众的这种双向交流,调节了演出气氛,加强了演出效果。
有时,戏师在藏戏中穿插的喜剧演员插科打诨的即兴表演甚至与剧情没有直接关系,却受到观众的欢迎。法国著名藏学女专家亚历山大·达维·耐尔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写道:“在演出单调的宗教剧时,常常穿插一些小丑们的打诨,他们的对语和正戏的内容无关,丝毫也无感人之处,完全是一些放荡的甚至是猥亵的动作和言词。神秘的戏剧也好,简短的打诨也罢,同样都会受到观众的欢迎,幕间,演员们还出来跳跳舞。”[8](P96)作者提到的“小丑们的打诨”便是藏戏中喜剧演员的滑稽演出。这些喜剧演员游离于剧情之外的即兴表演有吸引观众,调剂演出气氛,增强喜剧效果的作用。
演出时,戏师根据观众的情绪和现场情况,临时打断剧情,通过插入民间歌舞、杂技和喜剧演员的滑稽表演等手段来吸引观众、调控演出场面,显示出其在藏戏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结语
六百多年来,在藏戏沿袭至今的言传身授、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中,戏师是传授藏戏技艺的主体。演出前,他对韵散相间的藏戏文学剧本进行二度创作,再根据演员本身条件分配角色并传授技艺。由于戏师的个人喜好和演出经验不同,对同一出剧目内容的取舍点不同,在观众面前呈现出多样化的表演内容。演出时,戏师常因时制宜调整演出内容及剧情的详略,使剧目演出时间长短伸缩自如;同时他在演出过程中还穿插进歌舞、杂技以及喜剧演员插科打诨的滑稽表演来调剂现场的演出气氛。总之,戏师在戏班中既要负责传授藏戏艺术、培养自己衣钵传人,又要做为剧情讲解人通过说雄来掌控藏戏的演出节奏和调节演出气氛,以加强演出效果。戏师表演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该戏班的整体演出水平。戏师依靠自己在场下、场上的巨大作用推动了藏戏艺术的发展,显示其在藏戏中的重要地位。戏师在藏戏中的重要作用揭示出藏戏独特的演出形态,反映出藏民族特有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再现了说唱艺术输入戏曲的初始形态,并为研究汉族戏曲从说唱体向代言体的演变轨迹提供了活态的研究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