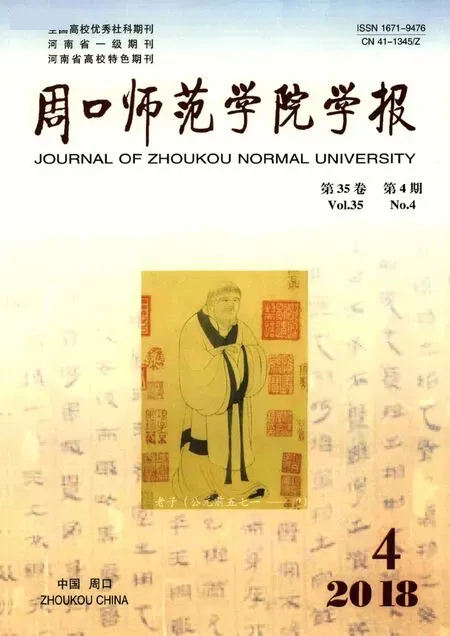关于中国古代天下思想的讨论
——基于日本学者的考查
2018-02-09常笑
常 笑
(1.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上海团校,上海 200083; 2.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083)
天下思想是中国古代政府稳固其统治的重要依据,历史的变迁不断对其理念进行着更新,成为中国外交思想的特色内容。我国有关天下思想的研究早在19世纪末便有所体现,到20世纪80年代的近百年时间是天下思想研究的深刻探索时期。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从思想史和传统文化等角度出发,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中国学界对于天下思想最早的阐述是康有为成书于1902年的《大同书》,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郭沫若《青铜时代》(194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钱穆《晚学盲言》(1987)等做了进一步阐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天下”一词在中国学界再度引发关注。
在一海之隔的日本,同样有一批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对天下思想进行着激烈的讨论。关于“天下”一词的内涵,日本学界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天下”就是中国,将其理解为国家;另一种认为,“天下”是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尽可能多地向外围扩展的世界。本文列举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的观点,通过比较、考查,分析日本学者的中国天下观,并提出一己拙见。
一、“天下=中国”说
以安部健夫、山田统等为代表的学者持“天下型国家”观,即“天下”就是中国。
安部健夫的《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是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天下思想的代表性论文,先后收录在1956年出版的《哈佛·燕京·同志社东方文化讲座》和1972年出版的《元代史的研究》中。他批判了“中国人没有国家”“中国从未以国家或民族形式存在”的既有主张,认为“天下”一词正是为了重建战国纷乱的政治秩序而生,因此,在实际应用上并非“天之下”,而是有其特定的范围,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指“中国”的统治疆域,相当于中国的“国家”这一概念。同时,提出了五点看法:第一,“天下”概念的出现源于战国而非西周;第二,创造天下观念的是墨家而非儒家;第三,“天下”所指的范围是中国而非世界;第四,战国时期提出的“天下=世界”的观念,直至汉武帝时代才具有影响力;第五,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优势的是墨家和儒家的“天下=中国”的观念[1]。
将“天下”理解为“中国”的日本学者还有山田统,他的《天下观念与国家的形成》论文收录于1981年出版的《山田统著作集(第一卷)》。他认为:“‘天子自身之王国乃是京师,即所谓中国’,‘其他则由诸夏之国’所构成。后来原本仅仅意指天子之王国的‘中国’,在交通圈与政治交涉圈的扩大中随之扩张,不久诸夏、中国与天子就成了同义词,意指包括了诸夏、九州在内的闭锁空间整体,而与四海之外的四夷形成了直接对峙。”[2]10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尾形勇对于“家”“国家”和“天下”的论述,即天下秩序是家族秩序、国家秩序的放大,并将“家族国家观”的概念引入天下观。天下秩序中的君臣之礼,源于家族秩序中的家人之礼。天下秩序同时包含国家秩序的“公”和家族秩序的“私”,家族秩序发挥了基础作用,国家秩序制约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家族秩序。正如江户中期儒者浅见纲斋所言:“其人所为,先为家,次为国,其十分之一杯,为天下。虽立家、国、天下,然其实则为家。国、天下乃家之大也。其家则为人。云人者,人伦也。故以家始而为国。天下之本,而相属于超己。图己之道外,无家之道。家之道外,无国、天下之道。”[3]
在考查天下思想的过程中,一些与“家”有关的词频频出现,“天家”“国家”“公家”“皇家”“官家”“大家”等,另有一词“天下一家”更是常见。尾形勇将“天下一家”的理解分为三点:第一,天子“以四海为家”“以天下为家”,范围虽广,君义和王法皆通达无阻;第二,天下合并、统一为“一家”,是一个整体;第三,四海之内,没有界限,都是天子的领土,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无外”。同时,“天下一家”表现出国家秩序和家族秩序之间的紧密联系,正如日本近代东洋史学家桑原隲藏所说:“根据中国人所信奉的,天下是个大家族,家族是个小天下。所以,国被称为国家,天下被称为天家,又称为天下一家。在国家和天家的词语中,体现着把家作为国和天下的原型的思想。天下和家族只是范围广狭的差别,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4]
古代中国虽不同于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而是王朝国家,但具有“制度典章的政治连续性”,更具备“宗教语言礼乐风俗的文明一惯性”[5],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向周边扩散,王朝所管辖的地理范围之内即为国家。
二、“天下=世界”说
部分日本学者持天下等同于世界的看法,代表人物有田崎仁义、平冈武夫、村井章介、西嶋定生、石上英一、堀敏一等。
田崎仁义是最早对天下概念进行系统探讨之人,他通过对中国古典经书的分析,认为天下是普天之下,是无限的世界;领土无限的思想,就是大一统思想;服从于君权的人民没有范围限制,全体人类都可以受王权统治。
通过研读中国古典经书、论述天下思想的日本学者还有平冈武夫,他以《尚书》为考察文献,认为天下是共同有着“天”的理念的人们的所居之处,它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界限,是一个世界。并提出,天下型世界观是以“天”“天子”“民”“德”四个词为基础而形成的。
村井章介、西嶋定生、石上英一都在地理区域方面,阐释了天下即是全世界的观点。村井章介指出:“(天下)并非指特定国家的支配领域等,表示的是无限延展的空间”,“是应该超越中国的国家领域并覆盖包括夷狄在内的全世界的”[2]14。
同时,西嶋定生表示:“天下,顾名思义,就是为天所覆盖的整个下界=地上,即世界本身;而所谓‘王天下’,就是君临全世界的意思。”[2]12在论及东亚世界的形成时,也提及“华夷思想是区别夷狄与中华(中夏)的思想,由此又产生将中国置于天下中央,而称周围居住者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四夷思想”。而夷狄区别于中华的依据并非种族或地域,而是“对周室之‘礼’的体会如何”,“是如何编入以周天子为中心的秩序体制”[6]95。由此可见,包括中华与夷狄在内的天下之范围,不是根据地理和家族的因素划定的,故而夷狄同时存在于中国的内外部,而天下也不仅仅只限于中国国家的所在区域。
石上英一同样将天下理解为世界,并从地理范畴论证了天下是由中国和夷狄所构成的帝国。他指出:“(秦汉王朝)创造了皇帝与帝国;前者是以支配世界=天下为目的的君主权力,后者则是为了实现地域性世界编程体系机能扩张的国家机构。中国所构想的世界,是由华夏=中国与周边的外夷所构成的。”并将古代东亚世界的国家类型分为帝国型和藩国型两种。“在藩国型国家的内部构造之中也阶层性地将诸民族、诸部族集团、诸地域包摄在内,并依靠皇帝权力的确立与小世界(或拟似世界)的编成而得以向帝国型国家发展。”[2]14中国天下格局的发展模式正属于此。
在论及天下观的形成方面,堀敏一将天下观念通过中华思想做以表述,引用了《春秋公羊传》中的文字:“《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根据《春秋》所载,在各国看来诸夏为外,在诸夏看来夷狄为外。堀敏一表示:春秋时期四分五裂,各国、诸夏、夷狄之间存在内外观念、远近关系并不稀奇,“国与国之间、诸夏和夷狄之间存在歧视是时代特征”。但在《公羊传》立书的“战国末期到秦汉时期,正值天下趋于统一的时代。其中自当包括夷狄,所以区分内外的差别意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而春秋时期存在的华夷之别的观念,随着中国的统一而弱化,中华思想逐步发展完成。中华思想确立的标志是“把夷狄也纳入文明内部的中华帝国成立”[7]。在中华思想中,皇帝是包括中国内外各民族在内的中华世界的君主,而非仅是中国小范围内的统治者。笔者认为,从其内涵、发展历程来看,这里的中华思想等同于天下观念,堀敏一的天下观是一种中华帝国世界观。
三、不同时期的“天下”
如上所述,天下范围等同于中国还是世界,在日本学界分为国民国家论和帝国国家论两大派系,多年来始终是日本学界争论的焦点。前者倾向于将天下政体理解为民族国家,后者则侧重天下政体控制四夷的帝国性质。
笔者认为,从特定的角度来说,天下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世界。但无论是国家还是世界,其状态和范围都不是永恒的,具有时代性、可变性。先秦时期持“天下=世界”之说,“天下=中国”之说体现于秦汉大一统后至元朝的帝制时期,而明清以后多数人持“天下=世界”之说。
(一)先秦时期将天下等同世界
先秦时期,诸侯割据,中央通过分封管理地方,各地具有独立的统治权;加之戎、狄、蛮、夷分布四周,战乱时有发生,政局不稳,国家尚未统一。何况“天圆地方”“天似穹庐”的天下观念深入人心,这是中国古人对天最初的认识和想象:天像一个巨大的圆顶,倒扣在人们进行生产生活的世界上方,将所有人、事、物囊括其中。从高度来看,一切都处于天的下方;从广度上看,一切都被天所笼罩。这种直观的认识,使天具有权威性,使天下的世界具有唯一性,也使人们产生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基于这种认识,天下格局基本形成,天下秩序得以维持:从地理空间来看,华夏处于天下的中心,夷狄处于天下的四周,形成众星拱月的态势;从管理方式来看,华夏奉天之命,其王权具有合理性,夷狄处于华夏的统治之下;从文明角度来看,华夏重礼重德,对夷狄恩威并施,通过宗藩关系、朝贡往来等获得夷狄的敬仰。
因此,正是受地缘限制,古人认为视野可见的天之下的地区即是全部世界,不知在未知的地域还有其他人类和文明的存在,因此彼时的天下观,即已成为一种在认知方面存在不足的世界观*当然,先秦时期即使中国尚未统一,从空间范围来看,其所在大部分区域在地图上处于后世的中国之中。故而“天下=中国”之说也不无道理。。
(二)秦汉至元注重统一的帝国
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由于各部族的往来增多、人类活动的空间变广,天下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秦灭六国,结束了诸侯争霸的战乱局面;西汉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治一统,进而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中国的帝制特征逐渐鲜明。
西嶋定生在论述秦汉帝国的形成时指出:这个过程“克服氏族制而出现专制君主制与个别人身支配,再以这两者作为基本的结构而形成了统一帝国”[6]36。秦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统一帝国,全国人民由皇帝“直接统治”,即皇帝是国家权力的唯一“母体”,只有皇帝才能统治人民,官僚只不过是“皇帝权力的代行者”;统治的方式是实行“个别人身的支配”,即被统治者并非像先秦那样作为氏族集团被支配,而是以个体的形式、一个人一个人地被管理。也就是说,“始皇帝建立统一帝国,是建立了由唯一最高的君主对全国人民进行个别人身支配的体系”[6]50。这种统治方式透出帝国的性质。
渡边信一郎总结日本众学者的思想,就“天下”的概念得出结论:天下以禹迹=九州=中国这样的传统观念划定的范围,以户籍、地图为基础,对编户百姓进行统治、管理和支配领域。同时,通过朝贡关系,将周边的夷狄囊括在其自身范围之中,呈现出帝国的面貌[2]44。“天下型国家”的特征因此突显出来。
(三)明清以后认为天下无限大
对于前文所提及的堀、石上、村井等学者将天下视为世界帝国的观点,笔者尚存一定质疑。渡边信一郎虽然认可了将古代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作为帝国来把握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同样提出“将帝国概念直接与天下概念等置这一点尚有疑问,遑论无限世界”[2]15。
随着不同文明的发展进步,各地分别以国家的形式呈现在世界舞台之上,并进行联系、往来。尤其在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以球形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它不属于某个帝国,但各个国家、地区都被涵盖于整个世界当中。从其地理空间来看,“天下”的内涵因此有了新的内容。根据我们现有科学得出的结论,宇宙即是天,是无边无际的,世人无从知晓其范围和边界,因此,天(宇宙)是无限的,天下可以是无限世界,而帝国不是。
再者,古代天下思想的性质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是一元而非多元的,如“天下一家”“王者无外”等思想;第二,它是权威而非制衡的,如等级制度、尊卑秩序的体现;第三,它是向心而非外扩的,如同心圆的统治模式;第四,它是道义而非自利的,如强调德治、非战思想。可见,古代天下思想所建构的世界秩序,是一种具有等级但并没有征服与被征服、殖民与被殖民关系的国际秩序。
姑且不论世界各国应平等相处这样的国际秩序理念,仅从范围和性质来看,若将帝国直接与天下对等,也未免有失偏颇。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文明相互融合和碰撞,天下理论包含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成为宏大又复杂的理论体系。对其的理解,学界多有讨论,众说纷纭。今后有关天下的争论仍会继续,实时的国际往来还将为各方观点增添新的论据,需要我们更加思辨地去学习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