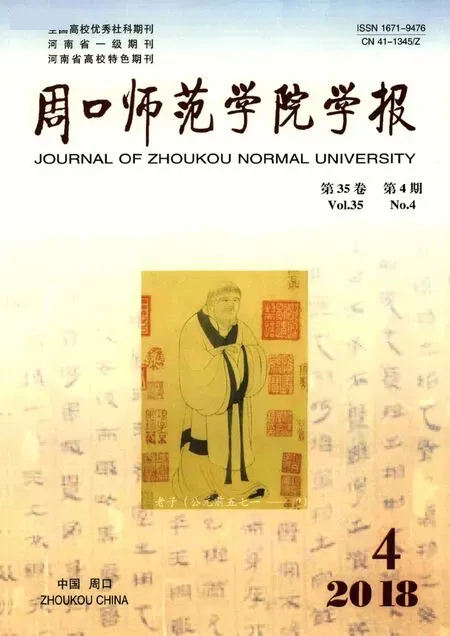飞向不同方向的三只鸟
——“周口作家三俊鸟”小说合论
2018-02-09冯庆华
冯庆华
(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近年来,“周口作家群”中的几位年轻作家开始崭露头角,引人关注。为了推广和关注周口文坛新生力量,周口文联、周口作协与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在2016年专门召开一次关于三位年轻作家的研讨会。三位作家的名字分别是红鸟、飞鸟和孙全鹏,考虑到三位作家名字都与“鸟”相关,便取了“三俊鸟”这么个名字。该命名一取吉庆祥瑞之意,二是套用在过去一年刚刚举行过的一个性质类似、规模更大点的“河南作家八金刚”学术研讨会的名字。笔者系统性地阅读三位青年才俊的作品也是肇始于此。
在阅读的过程中,能感受到三位周口作家创作过程中因为年龄、时代、地域文化影响下展现出来的一些同质性因素。比如他们的写作题材大多都与豫东农村相关,如孙全鹏的《幸福的日子》中爸爸部队复员后回到村里养鸡,《西瓜熟了》围绕着偷西瓜展示了乡村民风的朴素善良,《风波》《秋奶奶与阿婆》也都是围绕农村的日常生活来表达一种善良的人性。飞鸟的作品如《老孬》《一个小时多少钱》《海的替身》也多是写到农村发生的事情,只是在飞鸟的作品中,较多写到农村人在当下社会转型期的新经历,以及这些经验带来的身体和思想的诸多变化。另外相对于红鸟和孙全鹏,飞鸟的叙事比较讲究技巧,也常用象征和隐喻传达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红鸟的小说如《娘的小羊》《到冰雪美人》《到北京去看北大》等也多是写到发生在豫东南农村的一幕幕场景。当然这里主要想谈一下三位青年作家的不同之处。由于不同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成长经验等,这些不同以及各自的局限应该是更值得关注的地方。
一、红鸟:一切景语皆情语
红鸟的作品有一个自己常用的叙事空间——颍河镇,他的小说题材基本上都取材于这个空间。在主题方面,红鸟的小说可以概括为一个关键词:情感。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从情感出发。当然导入这个方向之前,红鸟似乎有过其他方面的探索。如《冰雪美人》写自己青春欲望萌动时期的尴尬,也写到了薄荷姑娘的人性美;《那年夏天的知了》则写到自己因为一只知了所激发的成长成熟。这些小说可以说属于成长励志类小说,这是一个作家最初走上创作道路从自身经验开始写作的表现,也是作家写作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在同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在《去北京看北大》中则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此时的红鸟已经很注重文笔的简洁,很少拖泥带水。
儿子转眼就高三了,说高考就高考了。
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再次像蝴蝶一样翩翩而来。
儿子高兴地跑到李金榜的病榻前,双手把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捧到父亲的眼前。
儿子说,爹,快看,北大!
除了简洁,他本时段的小说常常试图在篇末营造余韵和回响。
儿子想不通,身患重病的爹,什么时候去的北京看的北大呢?
这篇小说中传达出红鸟对于人生意义的思索。所谓考上北大,就是一种心愿,心愿完成了,真正的北大上不上也就无关紧要了。这里北大也类似于人的一种欲望,就像一种意志的完成。按照叔本华的观点,意志使人痛苦,克服这种痛苦就是理智的生活。“摆脱无穷欲望纠缠的途径就是理智地思考人生,了解从古至今的各国伟人的丰功伟绩,伟人们仅仅为这种敬慕的心灵而存在。”“无私的理性就像一缕芳香,升腾在意志世界的缺陷和蠢行之上。”[1]李金榜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中的天才,他考上了北大,但因为学费和突如其来的横祸让他失去了上北大的机会。他又在编织艺人的职业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并在儿子考上北大后获得了精神上更进一步的满足。
《我被谋杀》又在进行一种叙事试验,用一个死去的“我”的视角进行叙事。生活在贫困潦倒中的一家人,把小儿子送给别人,大儿子把家里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小儿子得了胃癌被别人送回,他认为是母亲选择男人时的不负责任造成自己的悲剧,所以一心要报复母亲。他把父亲威胁母亲的枪里装的假子弹换成真的,最后这颗真子弹却阴差阳错地打中了自己。这篇作品似乎有意模仿先锋叙事,如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方方的《风景》等,整个作品弥漫着一片阴沉、黑暗的情绪。
这种情绪和叙事的试验终结于《陈城啊,陈城》,这篇小说算是友情、同学情感的书写,作品一洗之前严肃、沉重或阴暗,以非常轻松、阳光、调侃的笔调叙事。
前一段时间大家都感冒了,大有非典的趋势,寝室的几个不是发烧就是感冒,大家陷入白色恐慌中,有一次物理课那个老师大惊:班上人这么少?班长呢?然后群哗:生病去医院了!老师又问:副班长呢?群哗:发烧打吊针呢!老师大惊,接着问:团支书呢?那个团支书战战兢兢地站起来,说:老师,我还活着……
这篇作品之后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围绕情感,尤其是亲情展开。《十八件毛衣》叙述了一个微不足道甚至连平凡都称不上的女性惊天动地的母爱。“我”妈妈王美丽生下儿子后得了月子病,在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时:
就整天待在床上织毛衣,织了一件又一件。父亲说,歇歇吧。她说,不歇。还是一件一件地织毛衣,她的手被毛线勒了好几道血印子。到了夜里她也不睡,点着煤油灯织毛衣。一件毛衣她都要织很久很久,可是她仍然织得很认真,不敢有丝毫马虎。
在去世前,“妈妈”一共织了18件毛衣,她用尽自己生命残存的一点力量,让自己的孩子从1岁到18岁每年都有新毛衣穿。《娘的小羊》通过娘与小羊成长过程的描写,表达一种围绕母爱升腾的温馨的家庭氛围。《平安树》从“我”5岁写起,深情讲述了伴随自己成长的伟大母爱。《十八岁的电影》《思念一只乌鸦》则表达了厚重的父爱,当然后者描写父爱来自“继父”,更让读者感受到爱之博大。
梳理红鸟的小说,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为期不算太长的写作生涯的发展脉络。红鸟从《去北京看北大》《那年夏天的知了》开始从书写自身经验进入写作,并在这个过程中开始了自己的一些人生领悟。在差不多同一阶段的《我被谋杀》开始在叙事技巧方面进行有意识的训练。在他认为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写作技巧都稍有积淀后,才选择了“亲情”这样一个方向进行写作。所以,读者看到的《十八件毛衣》《娘和小羊》《思念一只乌鸦》《平安树》等便是他较为晚近的作品,这些作品试图表达作者本人对于人与人之间情感尤其是父母之情的感动,这种描写当然有现实的基础和真实的成分在里面,但同时也与某种理念包括伦理教化有关。这种选择情感厚重,但对人性的发现却比较单薄。此类叙事作为人生某一个阶段的写作方向无可厚非,甚至是必由之路。因为个体必须感动过、期待过,同时也忧伤过甚至绝望过,才能真正进入人生和写作的更高境界。就像曹雪芹没有少年时期锦衣玉食、纨绔风流和后半生举家食粥、门可罗雀那种对比,就写不出《红楼梦》这样厚重的传世名著;鲁迅如果没有过少年时期“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经历也不可能有以后鲁迅那些说理、写人高屋建瓴、入木三分的白话文经典了。一个作家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感动“亲情”“友情”,或歌颂“爱情”的层面,也是这个作家需要突破格局的时候了。
二、飞鸟:矛盾与冲突
飞鸟的作品常常表达一种冲突,尤其凸显人性中善与恶的博弈。如《海的选择》,海因为拿不起8万块钱,没能娶上那个女人。但他的老板黄泥鳅花钱娶回了那个女人,或许是因为用钱买回的女人,或许黄泥鳅本人就是那种对女性缺少尊重的人,黄泥鳅经常虐待这个女人。他对于这个女人的虐待激起了海的义愤,海用椅子砸了黄泥鳅。之所以说出于义愤,因为海并非因为真的喜欢那个女人,而是那种对于弱者的同情。后来这个女人多次欲接近海都被海回避就彰显了海的人性善。海身上的人性善相对于黄泥鳅身上的人性恶,形成了对比与冲突。同一篇小说中还涉及本真人性与被异化后人性的对照。黄泥鳅似乎就是一面镜子,这个女人对于钱财的欲望让她陷于冤冤相报的仇恨怪圈,黄泥鳅对这个女人和海的迥然不同的态度似乎给出了一种启示。对比黄泥鳅对那个女人的虐待,尽管海打了黄泥鳅,黄泥鳅并没有因此记恨海。因为海已经跟了他七八年,他了解海的为人。作者似乎想告诉读者,被物质异化的人性即便收获了金钱,等待他的仍然是痛苦。只有精神层面的善的付出才能得到善的回报。
还有转型期社会激发起个体的新与旧的习惯性思维之间的冲突,这类冲突涉及的主题与孙全鹏的小说有相似之处,只是孙全鹏的小说中只呈现出两种倾向,没有展示冲突。如飞鸟小说《一小时多少钱》中的方六,在村里开小卖部补贴家用,因为村里壮年男人大多外出务工,经常有老人和妇女找方六帮忙。受到新闻里有人陪人聊天每小时20块钱的启发,方六贴出了帮忙每小时15元的广告。结果无论是村里人还是自家人看方六的眼光都变了,他们甚至宁愿在外面找价格更高的人也不来找方六。包括方六的妻子也在电话里埋怨方六,方六的行为让她觉得很没脸面。这就是典型的新旧两种思维的冲突,但这种冲突比较复杂,不好简单地判断是非对错。但无论是作品中的人物还是现实中的个体,由于因袭了传统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对于新的价值标准势必产生难以接受的尴尬,有时甚至会产生敌对情绪。只是冲突双方,或说新旧之间,孰优孰劣作者似乎也不易分清。
飞鸟小说中还写到传统伦理与人性的冲突这一从“五四”以来就备受关注的主题。如《安妮》中安妮的后娘不让安妮上学,但安妮后来仍然依靠努力创立了自己的事业,让后娘和爹的晚年过得安静祥和。安妮是美丽而善良的,但安妮对于后娘刻薄寡恩的善良回应也让人反思这到底是一种人性的善良还是一种奴性,值得置辩。这里牵涉关于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精神的思辨问题。孔子说的“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便昌明了这种精神的可贵性,只靠屈服与忍耐是无法让恶者为善的。
此外,笔者认为飞鸟的小说是3个作者里面最具有明确叙事追求的,读者可以在阅读中随处读到这种叙事探索和追求。读飞鸟的小说,可以随处看到作者有意尝试象征性叙事,小说中的很多细节都带有象征意味。如《海的选择》中这样描写海用椅子砸了黄泥鳅之后的行为:
回到家,海把早上托人买回来的皮鞋脱掉,扔进垃圾堆,十根红肿的脚趾头一起欢呼。海换上布鞋,用条被子裹几件衣裳,走了。
这里十根红肿的脚趾头因为摆脱了不合脚的鞋的欢呼,似乎是海与那个美丽女人不合适关系的象征;“皮鞋”也似乎是现代文明与物质环境的象征,海把“皮鞋”扔进垃圾堆似乎象征着海对物质诱惑的拒绝;女人的美丽像把黑暗的屋子里所有的光都吸到她身上了,与那个皮鞋擦洗过后光亮得像刚洗完澡的小猪崽,散发出鲜活的光芒,这一切又可以看作欲望对象的象征。其他如《一只怪异的猫》《一条饥饿的狗》简直就是一片意向与象征的丛林。文本中人物几乎都是一种能指符号,有时作者甚至都不愿给笔下的人物命名,直接用数字进行编码。《一只怪异的猫》中3和5两个人都是符号。3要寻找那个锤子,砸那个猫,到底是猫还是兔子叙述者一直也没说清,似乎也是一个精神出问题的人。《遇见另一个自己》更像一个叙事迷宫,让读者在其中难辨东西。这里我们同样可以把叙述者当作一个疯子。就像论者评价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视角一样,唯其精神不正常让我们看到人性中被掩盖的贪婪与恶是如何展示自己的。如赵毅衡所言:“小说用智力上有问题的人做叙述者,往往就预先埋伏了这样一个判断:被‘文明社会’玷污了的智力与道德败坏共存,现代社会文明过热,文化不够者反而道德可靠。”[2]《一条饥饿的狗》中的狗被少年玩弄的过程,就是个体因为贪欲被诱惑走上犯罪道路最终锒铛入狱的过程,这又是一次寓言性叙事的探索;小说《站笼》里,飞鸟也是有意演绎一个官员如何从最初的关注内容到后来关注形式以至于坠入形式主义的过程;《老歪》《海的选择》《一小时多少钱》这些小说中,飞鸟都在尽力揣摩个体心理,这种心理与时代无关,更多与个体的个性本质有关。其中有人性的阴暗面,也有人性中温馨的内容。因为对于人个性心理的揣测,飞鸟似乎更靠近哲学层面的思考。
三、孙全鹏:异化与坚守
孙全鹏笔下经常写到一个地名,叫将军寺。在这个小镇里,生活着这样一群人物。他们像豫东每一个村镇的大众一样,日复一日生活,在看似平静的生活表面,因为人与人的交往产生一些或小或大的涟漪甚至波澜。通过这些涟漪和波澜,读者可以读到作者对于时代变化的观察,对于时代变化在一个普通村镇或一个普通人身上投射影像的描摹。可以说,这些变化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客观分析是有好有坏,但不可否认,时代变化给人性带来的异化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异化让个体抛弃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把个体带入物质和欲望的陷阱。
《幸福的日子》设定了一个叫“将军寺”的小镇。故事情节围绕“爸爸”、老锅、桃红等几个人物展开。“爸爸”曾经在越战中为了掩护师长身受重伤,伤好后又谢绝师长的挽留回到家乡,在老家养鸡和开小卖部谋生。“爸爸”很快成为村里的富人,引起周围人艳羡。老锅和桃红是夫妻俩,曾经淳朴厚道。在新的时代里,老锅所擅长的补锅补盆技术已经没有用武之地,看到“爸爸”靠养鸡赚了钱,便想向“爸爸”讨教养鸡的技术。“爸爸”当然不会拒绝,但提出了条件,就是让老锅在养鸡场无偿帮忙一年。这似乎是个苛刻的条件,因此也引起村里人对“爸爸”的偏见。其实“爸爸”这样做的初衷是想让老锅在帮忙的过程中认真学习养鸡的整个流程,这可以从老锅学习结束“爸爸”对老锅的送别看出来。老锅、桃红学会养鸡后开了自己的养鸡场,却不再和“爸爸”来往,为了多赚钱他背弃自己最初学养鸡时不和“爸爸”争生意的承诺,用低价销售的方式招揽生意。但即便这样,每次当老锅需要帮忙时,“爸爸”仍然不计前嫌地伸出援手。直到桃红为了多卖钱,腊月二十九赶集卖鸡蛋,结果回来的路上遭遇车祸死亡。在村里人冷眼旁观中,“爸爸”帮老锅埋葬了桃红。后来老锅又被利益诱惑,被收鸡的贩子骗走了鸡,在绝望中自杀。此时“爸爸”又收养了老锅的儿子福子。
很明显,在村里的各种人物中,大部分人作为冷漠的旁观者,表现出“恨人有,笑人无”的国民劣根性。这是一个传统的话题,“五四”以后,各种反思、批判已经很充分,不多做讨论。这里试图从转型时代人性出现的新问题在小说中的表现做一下梳理品评。《幸福的日子》中除了“旁观者”,读者还能看到传统文化背景下得到道德肯定的群体在这个转型时代浪潮冲击下开始溃散。有人仍在新的环境中顽强坚守着传统道德规范,如“爸爸”,他虽然通过养鸡、开小卖部赚了不少钱,成为村里的富裕户,但仍不忘初心,坚守着传统的伦理道德,比如仁义。小说中反复提到父亲是“性情中人”“爸爸性格豪爽,热心助人”,当别人取笑老锅的罗锅时,“爸爸”总是伸出援手等,甚至在老锅背弃前言和“爸爸”争生意时,“爸爸”仍然以德报怨,帮老锅埋葬桃红,老锅自杀后又抚养老锅的孩子。可以说,“爸爸”自始至终都是仁义的化身。但最初同样表现得老实厚道的老锅却在市场经济时代,被物欲冲昏头脑,不知不觉间变成“非我”,异化后的老锅在追逐金钱时最终从精神到身体失去自我,演出一场家破人亡的悲剧。小说的叙事过程彰显了作者的价值观念。
这个评价体系便根源于传统的道德观,参照的仍然是“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准则。这说明这种道德准则已经深入每个人的内心,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道德观能如此长期存在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除了历朝历代的重视推广,也说明它们迎合了社会中个体现实生存的需求,算是中国古代的“普世价值观”。尽管大众普遍信奉这些信条,在当下社会却又被一种新的观念诱惑着,那就是金钱。对于金钱的追求在世俗社会中是由来已久的,但在传统社会中有礼教的规约,比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及其他做人行事的道德准则等。传统社会当然也不乏见利忘义之人,但这些个体往往成为社会谴责的对象,“市农工商”的等级划分就说明了社会整体上对于“重利轻别离”的商人的歧视。现代社会这种规约已经近乎完全被破坏,似乎有钱就有了一切,或许也有些许的谴责,但这种谴责声在整个市场经济大潮中显得如此微不足道,甚至那种坚守精神园地和道德底线的人被称为傻子和精神病。
孙全鹏另一篇小说《祖传的军功章》表达的也是相似主题。只是这个作品中,对于个体面对金钱时的撕裂和疯狂比《幸福的日子》更加不加掩饰。当然这个作品中还涉及其他元素,如情节开始时,“爹”住在城里儿子家里,农村的老家失盗,“爹”非常痛心:
他对小杰说:“就不该来城里住这么长时间,本来在老家住得好好的,你看看,你看看,东西都丢了吧。”爹开始埋怨起小杰。可是,他不明白老家有什么好,说句实在话,在他的印象里说不出来老家具体是什么,有时候很清晰,有时候变得很模糊,只是在节日时有一种奇妙的情绪在内心涌动——他在城市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开始想家,想老家。
这里叙述的农村人在外务工,老家无人看守以至于经常失盗,确实是当下农村社会的真实现状。但这个细节只是为下文将要关注的真正主题做铺垫,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此,而是关注人性在这个时代的变化。
老家往往意味着与传统相关的内容。“小杰”提到老家那种说不清的感觉,便是传统在年青一代人内心被新时代的元素稀释、模糊却未能形成新的精神寄托的表现。这些所谓的新元素多与物质和金钱相关。这种异化与《幸福的日子》中老锅的异化类似。他们向往着某种物质或者身份,殊不知这种追求本身便意味着人的异化。对于传统的失落,老年人因为成长于斯而倍感痛心,年轻人则因为接受了更多时代浪潮的淘洗,本就不甚牢固的传统伦理体系和道德观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爹很生气,哆嗦地说:“东西丢了就丢了?你说的倒好听,那可是我一辈子挣的啊,你睡过的被子,你娘缝过很多次的……”
有了这种区别,对于军功章,两代人便有了不同的态度,父亲的眼里那是感情的寄托,一种纪念,儿子、女儿、女婿们只关心它能换多少钱。
从这些作品中作者反映出的价值倾向还是很明显的,作者留恋传统生存状态,认为被“金钱”异化是不好的,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捕鱼》中将军寺的人再不能到将军寺河里去捕鱼了,因为这里将被开发成旅游区,政府禁止村民下河捕鱼,但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在河里捕鱼的。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民被剥夺了长期以来赖以为生的各种资源,也被剥夺了那种天人合一、怡然自乐的生存状态。
老瓦喜欢钓鱼和捕鱼,可他从来不用毒药下毒捕鱼,虽然那样方法快,可他从来不这样。
毕竟要生活,这成为老瓦家的主要问题,可他一点也不急。他经常对爸爸说:“你开饭店,又卖东西,还当老师,天天忙得要死,不也是挣不了几个钱吗?一点也不开心。你看我,一天天不也过来了?多快活。”
老瓦是“天人合一”的实践者,这与当下城市化及各种旅游区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目的,不顾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显得非常不协调。这种情形下,老瓦这种真正乐天知命、亲近自然的自然经济下的小民生活状态再也难以维持。因为他自己可以不顾官方权力的打压,却不得不顾及女儿、儿子的生活和生命。那群“蓝制服”敲诈他1万元,不交钱就不放人,小仙为了救父亲东挪西借还出去打工,后来钱实在凑不出来,救父心切的小仙便从老板娘那里偷拿了2000元,在被公安找上门时不堪其辱,服毒自杀。这里我们看到权力是如何以各种手段来规训一个不屈服的个体的。
作者对这种被金钱异化扭曲的亲情和人性的理解很准确,不过这种叙事仍然存在一种缺陷,显得为了服务于某个主题无意中把人物形象简单化了,因而对于这种场景和人性的展示不够真实。比如小杰把军功章交给妹夫的细节,在明明已经知道军功章值钱的情况下还会交给妹夫,显得这人是不是脑子有点太简单了;妹夫之前对小杰说过军功章大概值五六万,既然他想占便宜,何必后来再给他挑明值九万块钱,而给他分四万五呢?特别是已经因为军功章值钱的事和妹妹妹夫闹过,已经后悔了,后来再告诉他三叔,更显得这个哥哥既贪婪又愚蠢,不够真实。作者可以有自己的主题导向,但必须塑造真实的人性才让人可信。这些显然是为了凑情节勉强拉到一块,当然有“无巧不成书”的说法,只是衔接方面还需要打磨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