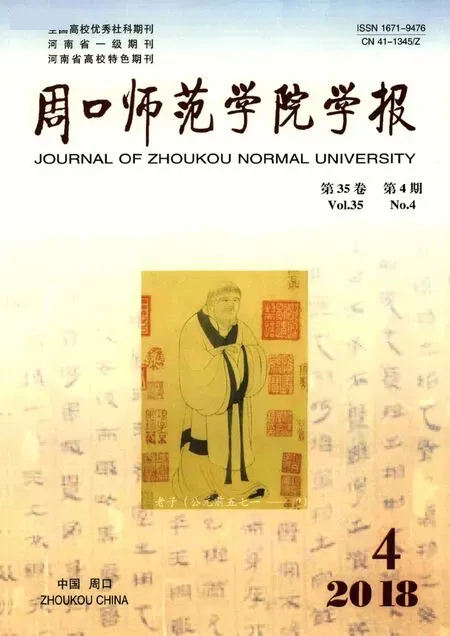历史、革命与人性
——柳岸长篇小说《浮生》的主题元素
2018-02-09刘成勇
刘成勇
(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柳岸的长篇小说《浮生》,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柳三跌宕起伏的一生,映射出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在社会、历史方面的发展轨迹。小说故事性强,人物性格鲜明。历史、革命与人性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三个主题元素,三者纠葛在一起,并有着独特的呈现方式,构成了较为复杂的文本意蕴。
一
读《浮生》的第一感觉,就是那种强烈的历史感。小说的上部“漂”从“194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写起,描写了解放战争、反右、“文化大革命”、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等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前后逾70年的历史随着社会变迁一路蜿蜒展开。
作者在处理这些历史事件时似乎并不仅仅满足于将其作为背景,而是写出了历史主体性,也即历史意志的呈现。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历史一旦形成,却又迫使创造历史的人沿着历史的轨道滑行而少有逸出的可能。尽管活跃在前台的是柳三以及像柳三这样的芸芸众生,但对这些芸芸众生命运起操控作用的还是历史。柳三一生风起云涌、大开大阖,看似是个人的自由行为,实质上处处受到历史的牵制。柳三在上半部的“漂”和下半部的“泊”,让人看到了历史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
柳三的父亲柳老万临死时希望14岁的柳三能守住祖上留下的家产,但柳三却志不在此,而是想走出柳家湾,出去闯一闯。他第一次走出柳家湾是因卖地参加革命而成为镇上分管生产的文书。尽管这个地方距离柳家湾不远,但毕竟从空间上和柳家湾拉开了距离。柳三也就越发自命不凡,越发看不起柳家湾的人,“觉得他们都是‘低等动物’”[1]14。为了撇清他和柳家湾的任何关联,他甚至拒绝了亲侄子柳立业请他在划成分时帮帮忙的请求,放出了“我跟你们不姓一个‘柳’”[1]15的狠话。但对于柳三来说,要想挣脱柳家湾是何等的艰难。在“干部—教师—校工—革委会特派员—特务/反革命/汉奸”的身份转换中,他又被遣回柳家湾。从离开的那一刻起就没想到回来的柳三对于这一切变故如坠云雾:“从大英雄成了反革命;从天堂掉进了地狱;从高高在上到低三下四;从呼风唤雨到叫天地不应;从众星捧月到被鄙夷蔑视。”[1]60在历史的轮回中,柳三又回到了他的起点。
柳三第二次离开柳家湾是因为同族晚辈柳小毛的陷害,只不过这次离开是以被动“出逃”的方式进行的。这一次他距离柳家湾更远,以至于逃到外省。“文革”结束后,他再次回到柳家湾。但他立足未稳,头上反革命的帽子还未摘下,就又有了离开柳家湾的打算——柳立业好不容易给他争取来的地又给退回去了。柳三是这样想的:
这地一分,他不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柳家湾人了?不就是一个农民?他不在乎地,新中国成立前他家那么多的地他都不要。他要是在乎地,就不革命了。……只要不离开柳家湾,他就没有福可言!他一定要找回丢失的东西,他不属于柳家湾,他终归还是要离开的[1]138。
经过一番折腾,柳三在平反之后分到公社教育办公室。但柳三果真就能摆脱“再回柳家湾”的宿命吗?退休之后,他还是回到柳家湾,并且死在这里。从年轻时就想走出柳家湾,为此而不惜割舍血缘和地缘的精神纽带;为了实现“游龙池穴”的梦想,试图挣脱历史的约规。但他最终回归柳家湾并且埋葬于此,不能不看作是历史和他开的一个玩笑。是历史将柳三牢牢钉在“柳家湾”,在主体性历史面前,人的所有努力和愿望不过是一个空洞回音。
当然,作者没有像经典现实主义那样在小说中建构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历史体系。当古典理性精心建构的整体性哲学在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下溃不成军的时候,个体生命脱颖而出。这是新历史主义诗学产生的哲学背景。在新历史主义这里,历史将自我分解为一个个富有戏剧性的现实事件,弥漫寄生于个体生命空间。换句话说,新历史主义的个人生命史消化含纳了庄严神圣的宏大历史,无数单个的个人史挤挨在一起,共同奏响了大历史的喧嚣,情欲、权力、人性、忠贞、背叛、堕落、金钱、名誉、地位等则成为历史乐章中最闪亮的音符。这些个体生命体征的局部放大就对历史意志有了侵蚀作用。
小说中,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分解为柳三以及柳小毛、齐四、尉迟清等的生命史、情欲史、权力史和人性挣扎史,他们在自我生命演绎的路途上,共同诠释着历史进程的内涵。为了能有效地抵抗历史意志的收编,文本以对日常生活中无聊甚至是琐碎物象的描摹消解着历史的庄严和神圣。在上部的“上访”“面见地委书记”以及下部的“老搭档”“外遇”“看病”“省城奇遇”等章节中,作者放大了日常生活的局部,以细节的重复和累积遮蔽了时间的存在。历史在这里几乎处于一种裹足不前的状态,显示出其强悍意志背后软弱的一面。历史与个体就这样构成了一种互为指涉又互为否定的关系。
小说的历史感不仅仅体现在1947年之后,它还有一个神话的源头,“游龙池穴”的传说为历史涂抹上灿烂斑驳的色彩。所谓的“游龙池穴”,据传是明朝万历年间一条小黑鱼在沙颍河第18个弯的一个大漩涡修炼所在,后成为人们妄想借此升官发财的风水宝地。传说本为无稽之谈,但柳三母亲开怀时柳老万所做的奇怪的梦以及10个月后柳三出生时的异象似乎又坐实了黑鱼的存在,小说由此生发出亦真亦幻的美学效果。
“游龙池穴”的传说时时出现在柳三生命的节点处,即如小说开篇所说:“我爷爷传奇的一生,和一个传说连在一起。”[1]1“游龙池穴”的在场性使得历史和个人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事实上,黑鱼的传说本身就是一种隐喻,作法淹没了方圆几百里土地的黑鱼在受到天神多年的拘禁和训诫后得一旨意:“你给人间制造了苦难,就去人间饱受磨难吧!”[1]2小说中的柳三一生又何尝不是命途多舛、饱受磨难。在柳三和黑鱼之间存在一种潜在的、神秘的对应关系。或者说,黑鱼传说以神话原型的方式成为柳三故事的副文本。就好像《红楼梦》开篇的女娲补天、木石前盟、太虚幻境以及《白鹿原》中的白鹿传说一样,《浮生》“楔子”中精心营构的这个神话背景为小说史诗性品格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
二
柳三的一生,最大的幸运是他卖掉家产和土地参加了革命,成为风云一时的“传奇英雄”;而他人生最大的不幸,也是因为参加革命而不断地在权力的巅峰和社会的底层上下沉浮。
柳三特别热衷于各种各样的革命。他的第一次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投奔了解放军,因为一颗子弹受了伤,再加上能说会道,在部队做了连参谋长,转业后做了分管生产的文书,“进进出出很是威风”。“文革”爆发给了他第二次革命的机会,贴出了沙洋镇第一张大字报,带领一班小学生成立了造反司令部,被公社革委会委以革委会特派员的头衔负责中心小学的全面工作。此时的柳三再次体味到革命给他带来的人生快意:“这何止是衣锦还乡啊,他就是这里的主宰。”[1]42“他不断为全公社革委会提供‘文化大革命’的‘先进’经验,他成了这里的红色政治领袖。”[1]43
与许多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写法一样,神圣崇高的“革命”行为在柳三这里还原为一种世俗冲动:革命就是夺权。在柳三看来,“解放革命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应该是这样。他是革命的受益者,他喜欢革命,他就是为革命而生的。革命就是他的亲爹亲娘,给了他想要的一切。柳三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中,每个细胞里都是革命”[1]43。有了这种对革命最务实的理解,他将革命内涵落实为人生不同阶段的“算计”,革命由此降格为生存的手段而不是人性解放的终极目的。
柳三对革命的算计开始于14岁时他对时局的判断:
他想,人的一生,该是你的,不争也是你的,不是你的,攥在手里也没用。他知道,这家产、土地早晚都不是他的。他不是个守财的命,他们老柳家没有一个是守财的命。虽然他心里不舍,可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况且这孩子不是他的。他要用这即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买下他后半生的通途,这笔账柳三算得很仔细。他觉得这才叫真算计[1]12。
他从乡文书转行当教师,因为他认识到教师“管得人多,威风”[1]18,就是区长见了他也得叫声“柳老师”。“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柳三就预感到这是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真是太好了,只有校长倒了霉,他才有希望。他该倒的霉已经倒过了,为什么这些人就不能倒霉呢?”[1]42当批斗教师再想不出花样时,他想到了妻子刘静雅是地主出身,和这样的老婆离婚才能在革命中“出奇制胜”。“文革”结束后,在平反的过程中,他以哄骗的方式见到地委书记。为了能晚退休几年,他故意将档案上的年龄改小以便多享受享受“台上的风光”。
但事物总是相反相成,历史辩证法从来不是空洞的律令。算计“革命”的柳三未能人生如愿,反而屡遭革命的“算计”。他卖地参加革命,革命却使他的一生在颠沛流离、惶恐不安中度过。从转行当教师开始,他的命运一落千丈、一贬再贬:观摩课上,他因所讲授内容离题太远而从中学调到小学;在小学课堂上,他将《小猫钓鱼》念为《小猫钩鱼》再被降为校工。“文革”批斗会上,本想狠批朱主任以报“遭贬”之仇,却因不认识“朱喾黉”三字出尽洋相。尽管他将名字改为“柳三红”以示对“文化大革命”的衷心,却因为随口说的一句“领子大”而被揭挖出18条罪状,成为现行反革命。他自作聪明改了年龄,却将“离休”改为“退休”,以至于退休之后福利大减。陈湖县实行殡葬改革,柳三提前三天坐化,他满以为“把握不了自己的生,却把握住了自己的死”[1]328;没想到因为省长调研使得火葬日期提前三天,“柳三,成了陈湖县殡葬改革开炉的第一任,在副省长的注目下,进了焚尸炉”[1]328。
柳三与革命之间的相互“算计”有着相互解构的意味。他与革命构成了一种共生关系:“革命”是由这样算计的人构成,革命空间也就充满了琐屑和卑微。换句话说,正因为革命本身的暧昧不明,才使得柳三这样的人能够一次次瞅准机会,在革命投机中游刃有余。
新历史主义小说往往在解构革命史的同时复活了民间历史,再现了平民百姓悲欢离合的日常生活世界。换句话说,革命的解构释放了民间空间,边缘人物站在革命的对面成为观照历史的主体,视点下移使革命的世俗性暴露无遗。但与其他新历史主义小说中人物多为山野村夫等边缘人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柳三是一个体制内的人,他的身份始终是国家的一名干部。这样一种身在其中的位置使得柳三不仅看清了革命的内部结构,而且熟络革命的游戏规则。在他看来,革命就是大胆与冒险。就像他自己这样,“原本该成为地主的人,不但没有成为地主,还成了国家的人,吃上了皇粮,当上了干部,这靠的不是命运,而是胆识、智慧、气魄”[1]18。他抓住每一次革命的机会以达到自我的人生目的。比如他与刘静雅的假离婚。他是在开批斗会实在想不出花样之后,想到了与地主出身的刘静雅离婚以划清界限。他自认为“这是一个高招,‘出奇’才能‘致胜’”[1]43。他精心地计算该如何顺利实施这一离婚策略:对刘静雅,先以物质麻痹,继以“大人物”的气势征服,再以一次次的做爱示爱,最后以严肃的谈话攻心。这一番过程下来,柳三几乎毫无周折地成功离婚,“再次成了‘革命典型’,声名大振”[1]48。当柳三做着这一切时,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会给刘静雅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和感受。他只是觉得为了自己的革命事业,刘静雅必须而且应该做出“牺牲”。在这样一种心理驱使下,柳三对刘静雅所说的话不仅气势十足、不容反驳,而且时时有一种理想主义、激情主义的壮怀闪现:“我现在是‘革委会’的人,干一番大事业是必然的。……”[1]47“生活多美好啊,你还想怎样?我马上就要发达了。你怎么就不懂夫贵妻荣呢?”[1]48“革命就得做出牺牲……人啊,要往长远看,要顾全大局……静雅,你得支持我,理解我,我也是出于爱护你才这样做的。你应该明白我的苦心。”[1]48可惜的是,柳三冠冕堂皇的话遭遇的却是刘静雅的冷漠与绝望,“革命”话语就此显出它苍白、空洞的一面。在柳三的革命无意识行为中,解构的利刃深入革命的肌理深处,形象地演绎了“革命就是夺权”的本质内涵。革命的神圣面纱就此揭去,宏大革命的自我叙事抵不过柳三自认“游龙”的心理动因,在革命祭坛上供奉的不过是人的“欲望”本能。
三
作者在后记中提出,有编辑认为柳三这个人写得太坏、“太灰暗”[1]332。确乎如此,在柳三身上,人性的卑劣暴露无遗。小说中的柳三,从他参加革命一直到死,很难说做过几件对于他人或是社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柳三人性的卑劣应从娶刘静雅开始。他在陈湖第二中学当语文教师时,倾慕于女教师刘静雅。刘静雅从开封女师毕业,漂亮、冷艳、高雅、贵气,最主要的是有气质。柳三费尽心机试图取得刘静雅的芳心,但皆以失败告终。于是在一个冬天的夜里,他强暴了刘静雅,又以英雄救美的方式赢得她的信任,最终使刘静雅心甘情愿与自己结婚。喜欢上一个人本没有错,但以这种方式达到目的,柳三的人品由此可见。他在教学方面被一贬再贬,从来没想到是自己知识不足所导致,而将之归为朱主任嫉妒他的出身和名声而对他加以陷害。“文革”期间恶毒批斗朱主任,并且在朱主任外甥柳小毛求情后对其动了酷刑、折磨至死。柳三人性之阴暗由此可见。逃难途中饿昏在地,被一老中医所救。老中医不仅收留了他,还传其医术、教其医德。柳三先是隐瞒身世、哄骗老中医的信任;在误诊致人堕胎后离开此地,他不仅拿了老中医为他准备的盘缠,而且取走了老中医视为传家宝的秘方。再逃难至一砖窑厂,他以“顿顿吃肉”的承诺笼络民工挤走管伙人而谋得管伙的差事。三天之后,带着民工一个月的伙食费不辞而别。继续逃难的过程中,他忽悠一个卤肉店老板说自己会烧窑来到梦楼大队,受到顶级待遇。第一窑砖烧毁,他连唬带骗,稳住了村里人。第二窑砖还在烧,他觉得没有把握,又骗取村支书结了工钱方离开此地。上部的“漂”看似展示的是柳三的苦难史,实质上暴露的是柳三人性的缺漏。
在下部,柳三做过的最坏、最“灰暗”的一件事就是出歪招致使齐窝头媳妇自杀。齐窝头是柳三的同事齐四的邻居。媳妇是个恶妇,气死婆婆,虐待公爹,并且在公爹面前自称老娘。齐四找到柳三,看他能出个什么主意治治齐窝头媳妇。柳三给出的主意是“就叫她娘,专门在人多的地方叫”[1]259。齐窝头果真就在饭场上如此照做,“齐窝头的儿媳妇虽然恶道,也经受不了这样的唾骂,喝药寻了短见”[1]265。齐窝头媳妇虐待公公固然不应该,但也罪不至死。柳三出的主意不仅致齐窝头媳妇于死地,而且趁势羞辱了其娘家。柳三出主意时已经预料到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因此他给齐四的“锦囊”里面还有如何解脱困局的方法:“如果她寻了短见,就让老人披麻戴孝去她娘家送信,其他人不要去,见了她爹娘就说,姥爷姥娘,俺娘死了,我来送信的。她父母见亲家如此称呼,必问其故,便以实情告之,他们断然不会找事。”[1]266无论是羞辱齐窝头媳妇使其丧命,还是阻止娘家来闹事的锦囊妙计的精确算计,都是对生命和道德的双重冒犯。柳三人性之卑劣由此可见一斑。
但作者并不将柳三归为“坏人”的行列,而认为柳三所表现出的这种“投机”特质为中国人身上所共有:“我悟出了这个人身上的特质,他骨子里的东西——投机。这种东西绝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中国人身上所共有的。因为文化,因为历史,因为现实,他身上便有了这些特质。这些特质是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熔化在血液里。你很难说,它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1]332当然,作者也认为,柳三的身上同时也表现了人性的弱点:“我从来没有觉得他坏,他身上的东西,我们很多人都有,不过在他身上更典型罢了。也许他真的很坏,可他生下来并不坏,虽然人性有人性的弱点,但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1]332
从这番辩解可以见出作者对柳三的“偏爱”。这种偏爱首先体现在叙述策略方面。书名《浮生》包含一种沧桑感,而上半部“漂”和下半部“泊”的小标题更寄寓着一种人生的辛酸与悲壮,讲述者“我——柳小果”的叙述身份设置则使整个故事笼罩上一层“追怀”的荣光:
关于我爷爷柳三的生平,柳家湾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版本,当然还有柳家湾以外的诸多盗版。我之所以想当作家,就是想为我爷爷写一本书。多少年过去了,我已经成了一名所谓的作家。可是关于我爷爷的书,却没有写出来。是我爷爷割断了我和他的气脉传承,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写不出我爷爷原本的样子。没办法,我只能把他写成小说里的人。我爷爷好像注定为小说而生,只是我笔力有限,不知能否写成一部好看的小说[1]1。
这是小说开篇的一段题词,限定了整个文本的叙述基调。除此之外,小说中还多次引用孟子的话,来为柳三做辩解或是作为柳三自我感觉的注解。他第一次想到孟子的话是连连遭贬之后,想到了《孟子·告子下》中的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觉得这段话就是针对他所写,于是“他不但不消沉,反而更加斗志昂扬。是的,如果没有这段话,柳三断然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他之所以觉得自己不平凡,就是能在这‘籍典经书’中找到同样的意境”[1]35。但就在这样一种自我安慰中,柳三失却了一份自我反思的机会。
其次,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当柳三表现出“国民劣根性”或“人性的弱点”之后,常常紧跟着就会有一种“道德豁免”,将柳三从道德法庭的受审中解脱出来。如他偷了药方、逃出大门之时老中医的反应:“老师傅站在窗前热泪双流,毕竟他们师徒一场,这个人的本质并不坏。”[1]88事隔多年之后,当柳三因为黄疸肝炎行将就死时,看到了这张药方,想起了老中医:“他真的很怀念他的师傅,老两口多好的人啊。”[1]260“柳三拿起那张处方,睹物思人,说了句:师傅,对不起。”[1]260在老中医的宽宥和柳三的忏悔中,人物的道德缺陷被缝合抹平。从梦楼大队逃跑之后,有了刘凤仙对他的挂念以及他对刘凤仙女儿的关切而赦免了他在梦楼大队骗吃骗钱骗色的罪过。而他治死齐窝头媳妇也是为了帮助朋友齐四,况且齐窝头的儿子也认为在这件事上没有错。原谅齐四也就是原谅了柳三,当事人的态度封挡住指向柳三的道德宣判。
也许,柳三的形象塑造透露出的就是人性的复杂之处,作者以其女性的宽容写出了一种未经过滤的、原生态的、超越道德评判的人性。但无论如何,如果考虑到文学作品的伦理性及其社会性,那么就不能不考虑“叙事底线的道德安全问题”[2]。这也是《浮生》值得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