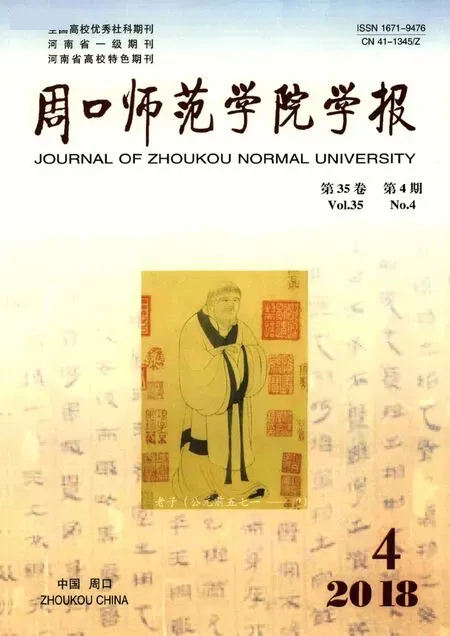从王尔德童话看其生命体验
2018-02-09李鹥
李 鹥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19世纪末期英国涌现了一批唯美主义作家和艺术家,奥斯卡·王尔德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从1887年到1895年这短短的几年,可以说是王尔德文学生涯的新时期,小说《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及其他故事》《道连·格雷的画像》、评论集《意图集》、戏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理想的丈夫》《认真的重要》等优秀作品相继问世。王尔德仅有的两部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他童话》和《石榴之家》也均诞生于这段时间。
童话作为离现实最远的一种文学体裁之一,以它离奇的想象以及单纯的情节将王尔德对“美”的深刻反思与对“爱”不懈的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9篇童话中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悟,使后来当王尔德为他的儿子读《自私的巨人》时总是噙满泪水,并说“真正美丽的故事总是让我哭泣”。
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主张“人生艺术化”,在《佩特先生最近的一卷书》中更是鼓励“以艺术精神来对待生活”。可以看到,唯美主义之于王尔德,不单单是作为艺术观,更是一种人生观,也只有了解到这一点,才有助于更好地解读王尔德的作品。
德国哲人狄尔泰认为,生命就是人类生活世界中具体化、客观化的精神生活;体验就是生活,世界由于体验而有其意义。狄尔泰尤其以诗人为例来说明生命体验。诗人的艺术创作,实际上就是从他自身的内在体验出发,去感受生活,透视生命的意义。本文拟从奥斯卡·王尔德的两部童话集中探讨他的生命体验。
一、唯美理想的描摹
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传统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信念已被动摇”,社会物质空前丰富,历史进入科学万能和实证时代,上帝不再是维系社会的核心,道德也失去了一切标准[1]204。正是在这样一个病态的时代,唯美主义悄然而至,如同蓄势的连翘花一般,开放在英国的土地上。
唯美主义理论来源于康德的美感经验的“无功利性”。在康德思想的影响下,唯美主义者愈加抵制现世的功利主义,一再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强调艺术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与道德无关。到了王尔德,他更是博取百家之长,形成了独特的唯美主义观。他似乎感受到这个时代的矛盾“‘彷徨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死,/另一个却没有力量诞生’”,“无畏甚至有那么点迫不及待地展露出先觉者的自觉——以艺术之‘美’来对抗现世的鄙俗”[2]6。王尔德认为艺术高于生活,在《谎言的衰朽》中说:“生活模仿艺术,生活事实上是镜子,而艺术却是现实”[3]343,“生活是艺术的最好的学生、艺术的唯一的学生”[3]344,“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之外,不表现任何东西。它和思想一样,有独立的生命,而且纯粹按自己的路线发展”[3]356。在一些学者看来,王尔德执着追求艺术不涉道德的理念和他的创作实践有所出入。这一点在他的童话创作里尤为人诟病。的确,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以超越道德的文学作品”,纯美的艺术与道德向来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尽管如此,这也不妨碍我们在解读王尔德童话的时候探讨他对唯美主义的渴望。
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什么才是王尔德所渴望的美呢?
张介明先生在《王尔德唯美叙事的理论和实践》中,参考王尔德《谎言的衰朽》《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等论著,概括出王尔德“以什么为美”的主要思想:以感性为美、以趣味为美、以想象为美及以形式创新为美。无疑,童话都可以将这几点囊括在内。
童话中,最富魅力的莫过于五光十色、自由自在的想象。除却童话中一贯的天马行空的想象,王尔德童话里更是多出一份诗人的感性,如《快乐王子》里因为爱上了河边的芦苇而耽误了行程的小燕子,又比如《打鱼人和他的灵魂》中因为爱上了人鱼,背着月光切下自己的灵魂的年轻打鱼人。王尔德的用语并不只是华美辞藻的堆砌,更具有一种韵律美、一种诗意,周作人认为王尔德童话“纯粹是诗人的诗”,“非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4]66。这些话语在作品中俯拾皆是:
那天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晴天。高高的有条纹的郁金香挺直地立在花茎上,像是长列的士兵,它们傲慢地望着草地那一头的蔷薇花,一面说:“我们现在完全跟你们一样漂亮了。”紫色蝴蝶带着两翅的金粉在各处翻飞,轮流拜访群花;小蜥蜴从墙壁缝隙中爬出来,晒太阳;石榴受了热裂开,露出它们带血的红心。连缕花的棚架上,沿着阴暗的拱廊,悬垂着的累累的淡黄色柠檬,也似乎从这特别好的日光里,得到一种更鲜明的颜色,玉兰树也打开了它们那些闭着的象牙的球形花苞,使得空气中充满了浓郁的甜香[5]401。
不单单是叙述性文体充满了绮丽的色彩,连平常的对话也极富诗意浪漫的情调。《快乐王子》中就有这样一段:
“朋友们在埃及等我,”燕子回答道。“明天他们便要飞往尼罗河上游到第二瀑布去,在那儿河马睡在纸草中间,门农神坐在花岗石宝座上面。他整夜守着星星,到晓星发光的时候,他发出一声欢乐的叫喊,然后便沉默了。正午时分,成群的黄狮走下河边来饮水。他们有和绿柱玉一样的眼睛,他们的吼叫比瀑布的吼声还要响亮。”[5]342
语言上的精美自然符合王尔德一贯的唯美主义主张,形式上华美的文风与超现实的童话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更让他可以恣意挥洒唯美主义的浪漫而凄美的艺术品质。
童话中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那些经久不衰的主人公形象。无一例外,童话里的主人公都是至美的形象,王尔德笔下的主人公也因为至爱而闪耀着至美的荣光。
《快乐王子》是一篇让人动容的童话:快乐王子原本是无愁宫里只知欢娱的王子,当他死后,人们就把他放在这儿,高高地耸立在上空。当看见城市的苦难时,快乐王子说,“我的心虽然是铅做的,我也忍不住哭了”。他一再请求小燕子将他身上的宝石以及金片给穷人送去,直到他自己变成了一无所有的难看的雕像。然而这份执着给王子带来的结果在现实中却是不幸的。陪他过冬的小燕子死去了,他的铅心也在那一刻裂成两瓣。快乐王子终于被送进了熔化炉。但故事的结尾,天使把这颗铅心和死去的小燕子送到了天堂的花园里,好让他们在那里欢唱。现实社会里无法容纳快乐王子,只有到天国里才能延续,好像纯净的爱只有在天堂里才会得到永恒,作家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否定和对唯美理想的追求。
《夜莺与蔷薇》是王尔德本人所喜爱的作品,他多次在寄友人的信中提到,称它“优雅别致”。故事十分凄美:夜莺听说她爱慕的大学生想要一枝红蔷薇,便四下寻找,但得到红蔷薇的代价是在月光下边唱着歌边用心血染红它。小夜莺唱了一夜关于爱情的歌,由一对小儿女之间的感情唱到在坟墓里永远不朽的爱,“这朵奇异的蔷薇变成了深红色,就像东方天空里的朝霞。花瓣的外圈是深红的,花心红得像一块红玉”。小夜莺死去了,心上还带着那根蔷薇刺。故事至此还没有结束,爱情的颂歌还没有奏起,情节便陡转之下。教授的女儿拒绝了这朵花,认为它没有首饰值钱。大学生带怒地把蔷薇花丢在了街上,花落进路沟,一个车轮在它身上碾了过去,大学生也再次回到了他的书阁。这个小小的故事可能会让儿童因为夜莺的死而失望不已,而对于成年人来说,这部作品显然有太多东西值得反思,除了惋惜夜莺为爱情的无谓牺牲,还可以感受到作家对残酷现实的控诉,那时的人似乎都少了一份情感。似乎美的东西都被这个世界无情地蹂躏摧毁了。读之越久,越能体会到凄婉,心里对这份至高无上的爱也愈加向往。
王尔德以艺术精神直面人生,体悟到生命中最动人的美,并赋之于童话,使得它们具有永久的生命力,这也是王尔德童话重要的美学价值。对于儿童来说,理解到这一层次着实有些困难,童话中主人公的死亡对于幼小的心灵绝不是一个小小的打击。然而,童话世界里展现出的至爱,无论是对成年人,还是对儿童,只要还存着单纯的心,这份爱产生的形式,无论是优美还是凄美,都能引起心灵的共鸣,都能唤起对唯美理想的渴望。
二、对现实生活的反思
“当习惯于在童话中寻找安慰,希望在童话中实现梦想的孩子们阅读王尔德童话时,通常会感受着某种程度的失望。”[4]15这并不奇怪,传统童话中一贯有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模式,或是说是故事在最后总是有慷慨许诺的幸福结局。为了达到这个结局,主人公可能要经过许多非人的磨炼、考验,然而作为儿童的读者处于弱势地位,“又不相信只凭自己的力量就能成功。童话故事告诉他会有魔力相助,这就点燃了儿童的希望之光。要是没有幻想,这种希望之光可能会被现实的困难扑灭。童话故事向他保证,理想王国终将获得”,这样它们很自然地“赢得了儿童的信赖”[6]。然而,王尔德童话里大部分主人公的结局都是以死亡告终,像前文提到的快乐王子与夜莺;《星孩》里星孩终于忏悔自己的过犯,戴上了王冠,“在他的国里充满着和平与繁荣的景象”,但王尔德好像铁了心一般要打破这祥和的画面,他接着又写道,“然而他治理的期间并不长久,他受的苦太大了,他受的磨炼也太苦了,所以他只活了三年。他死后继承他的却是一个很坏的国王”[9]。这么决绝,连一星点的希望都不留给孩子,仿佛告诉孩子这才是现实。让他们心生希望,后又亲手在结尾处摧毁这一点点希望。显然,这样一种陌生化的童话结局处理方式让孩子们始料未及,童话里引申出来的喻义他们还来不及理会,“死亡”这一冰冷的主题占去他们全部的关注力,好不容易筑成的美梦还没有体味多久,就一下子轰然崩塌。这种双重打击简直让幼小的心灵无法承受。那么,王尔德的童话又是写给谁看的呢?
王尔德在1888年写给《致G.H.克斯利》的信中提到,这几篇童话“既是写给孩子们,也是写给那些仍具孩子般好奇快乐天性的人们,以及那些能够在简单模式中体会出别样滋味来的人们”[7]371。随后在1889年1月,他在《致阿米莉·里夫斯·钱勒》中又改口道“并非为孩童所作的,乃是为18-80岁还童心未泯的人们创作的”[7]404。正因为如此,王尔德的童话包含了许多成人世界的东西,那些在童话中不常看到的死亡以及对真挚情感的否定,正是对现实世界的讽刺与鞭挞。那时的维多利亚处处充斥着腐坏与堕落,这份灰暗顺着作家的笔一路蔓延,整个童话蒙上一层荫翳。尽管描写的是美的画面、美的心灵,但似乎总有一种不可抗的外力让这些美的事物不得善终。超出儿童理解能力的悲剧结局以及作品中辛辣反讽的语言,对于成年人来说,反倒是一剂良药。
珍贵的友谊与纯洁的爱情向来是童话世界里加以渲染、加以歌颂的永恒主题。但在王尔德童话里,“爱情是多无聊的东西……它的用处比不上逻辑的一半。因为它什么都不能证明,它总是告诉人一些不会有的事,并且总是教人相信一些并不是实有的事”[5]353(《夜莺与蔷薇》)。友情是一再压榨朋友的绝妙理由,而灵魂对于商人来说更是毫无用处,“连半个破银圆也不值”[5]426(《打鱼人和他的灵魂》)。
《忠实的朋友》就是由一只梅华雀讲了一个关于友情的故事:小汉斯有一个极忠实的朋友磨面师大修。磨面师处处揩油,利用小汉斯的好心肠为他当牛做马,自己却口口声称“真朋友应当共享一切”[5]360。后来,在一个可怕的暴风雨夜,磨面师又差遣小汉斯去找医生为他的儿子治病。小汉斯找到医生之后,自己却迷了路,在风雨中淹死在沼地里。在这个故事里,小汉斯的牺牲并没有得到一点儿回报,他不像快乐王子和自私的巨人可以上天堂,至少给心灵带来些许慰藉。王尔德不愿意粉饰太平,似乎存心要打碎现实与童话之间的隔板,告诉人们好人时常没有好报。但童话总是要比生活多一些戏剧化滑稽化的处理,这篇故事叙述的是人的故事,但出现在叙述者口中的却是随处可见的小动物。这样比起人的转述,总叫人不至于太愤恨,倒是觉得故事里辛辣的讽刺背后多出了一些滑稽,可气之余多了许多无奈的笑。王尔德在故事开头,安排了母鸭教她的孩子们在水上倒立的一段:
“你们要是不会倒立,就永远不会有跟上等人来往的机会,”她不断地对他们说,并且她时常做给他们看,怎样才可以倒立起来。可是小鸭们并不注意她。他们太年轻了,完全不知道,跟上等人来往的好处[5]359。
又比如结尾处,母鸭评论河鼠的话:
他有很多的优点,不过拿我来说,我有一般的母亲的情感,看见决心不结婚的人,总要掉眼泪的[5]370。
本来因为小汉斯的去世,故事蒙上了一层阴郁的色彩,但随着河鼠、母鸭驴唇不对马嘴的对话的展开,似乎又将空气之中原本凝固的悲伤气氛一下子冲开了。这两种“看客”都代表小市民阶层,终日无所事事,拘泥在一片小池塘,思想沉闷几乎要发臭。母鸭虽没有河鼠这一自私的伪君子的形象那么可嫌,但她身上世俗迂腐的一套也着实可笑。《忠实的朋友》似乎有别于《夜莺与爱情》这一类童话,后者大多凄美而富有诗意,然而前者却是那么直白,颇类似于讽刺寓言。然而寓言里谈论的多是贪财与无知酿成不好的结果的浅显道理,还尚未涉及死亡。然而作家在其中糅合了更多当时的黑暗现实,虽然加了一个童话的框架,但无疑让作品的讽刺来得更为辛辣。王尔德用最简单的模式讲述了小汉斯的故事,在抨击他所处社会里纯洁的友情荡然无存的同时,也揭露了人心的冷漠,河鼠最后还在关心着磨面师的结果怎么样。这一点也常常表现在王尔德的其他童话中,比如《快乐王子》里市长看到一无所有的快乐王子时,称他“比一个讨饭的好不了多少”,接着就开始议论铸谁的象了;《西班牙公主的生日》里公主因为看到心碎的小矮人不再跳舞时,便大声宣布:“以后凡是来陪我玩的人都要没有心的才成”[5]420;《夜莺与蔷薇》里教授的女儿眼中只看得到金钱……上层社会说出来的蠢话恰恰是像不长心的人说出来的一样,他们身上只剩下自私自利,以及对生命的漠不关心与无情,这些都在这些童话中被作家毫不留情地一一揭露出来。丑陋的不仅仅是维多利亚社会,更是人心。
如果说,王尔德讲人的友情,把其中的诡诈渲染得极为丑陋,那么他谈爱情,则仍然带了几分柔情。比如《了不起的火箭》里“罗曼司是永不会死的。它就跟月亮一样,永远活着”,虽然言论一出,立遭其他炮筒的反对。
除了对友情与爱情的讽刺,王尔德还极力描写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快乐王子》中有许许多多挨饿受冻的小孩,《忠实的朋友》里是为了过冬不得不卖掉家当的小汉斯,以及《少年国王》里的三个梦境。第一个梦里少年国王遇见了衣食不足却仍被奴役做加冕礼服的织工,他说“早晨来唤醒我们的是惨苦,晚上跟我们待在一块儿的是耻辱”[5]392;第二个梦里他遇见了为寻找装饰在加冕节杖上的珍珠的奴隶,这个奴隶找到最美的一颗珍珠之后,就死了;第三个梦里他遇到了一群在河床上做工的人,那是一群为找寻嵌在王冠上红宝石的人。随后少年国王看到“死”为了得到“贪欲”手中的一粒谷子,不惜让疟疾、瘟疫蔓延在人群里,人全都死了。少年国王拒绝加冕的金袍、节杖和王冠,穿着自己的衣服走了出去,然而却有人告诉他:
皇上,您不知道穷人的生活是从富人的奢华中来的吗?我们就是靠您的阔绰来活命的,您的恶习给我们面包吃。给一个严厉的主子做工固然苦,可是找不到一个要我们做工的主子却更苦。您以为乌鸦会养活我们吗?您对这些事又有什么补救办法?您会对买东西的人说:‘你得出这么多钱买下’,又对卖的人说:‘你得照这样价钱卖出’吗?我不相信。所以您还是回到您的宫里去,穿上您的紫袍、细衣吧。您跟我们同我们的痛苦有什么关系呢?
“富人和穷人不是弟兄吗?”少年国王问道。
“是的,”那个人答道,“那个阔兄长的名字叫该隐。”[5]398
撇去其中的圣经意味不谈,穷人吃苦是苦,但不吃苦就根本没办法活下去,下层人民早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维多利亚时代带血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在作品中仅仅是冰山一角。
除了从人物的对话中加以披露,王尔德童话中对现实的反思还有很多是通过作品的反讽、对比的艺术手法来完成的。快乐王子在去世之前,他有一颗人心,不懂得悲哀是什么,只知道享乐,但当他成为雕像时,他的铅心反倒能体恤怜悯一切的穷苦了。小燕子没有力气再飞往埃及过冬,最终跌在王子的脚下,死了:
那个时候在这座像的内部忽然起了一个奇怪的爆裂声,好像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似的。事实是王子的那颗铅心已经裂成两半了。这的确是一个极可怕的严寒天气[5]346。
非人类之间的情感比人类之间的利益关系要清澈得多、高尚得多。没有一颗人心,反倒对世人的苦楚,对感情的珍贵,对周遭一切事物更为体恤怜悯。夜莺对爱情的理解以及献身远远高出了愚蠢而自私的大学生:
“拿死来换一朵红蔷薇,代价太大了,”夜莺大声说,“生命对每个人都是很宝贵的。坐在绿树上望着太阳驾着他的金马车,月亮驾着她的珍珠马车出来,是一件多快乐的事。山楂的气味是香的,躲藏在山谷里的桔梗同在山头开花的石南也是香的。可是爱情胜过生命,而且一只鸟的心怎么能跟一个人的心相比呢?”[5]349-350
夜莺是爱着生活里一切芬芳的,但是在她看来,爱情胜过生命,而自己作为一只鸟的献身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任何一颗有爱的心读了这一段都会觉得凄美异常。无怪乎《夜莺与蔷薇》是王尔德最喜欢的童话作品。我们会为夜莺的死感到惋惜和不值,而在唯美主义者王尔德看来,为爱献身无疑是最美最浪漫的了。而同时,夜莺的情感越崇高,人类的情感越显得猥琐、不值一提。
人们为什么不珍惜伟大的友谊?为什么不懂得同情?为什么打鱼人会受自己灵魂的诱惑而背叛对小人鱼的爱,只因为陆上的姑娘有两条腿?王尔德似乎存心要搅乱童话中所有的秩序,他的童话单纯脱俗的爱与美原本是存在的,但现实的力量太过强大,爱似乎永远不堪种种折磨,在作品中无力地死去。这无疑是对现实社会最强的控诉:还有什么比把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来得更教人伤心呢?
三、心灵深处的感伤和对灵魂得救的渴望
儿童文学是快乐的文学。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一种,通常应该有着轻松、明快的基调。童话似乎总应落座在奇境仙域之上,总是有奇妙的魔力保护善良的人们去战胜邪恶,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人们心中所想的童话。童话家们也都遵守着这一约定——有一些小苦难,但最后总是完满的。童话中常常出现的落难公主或是被兄长逐出家门的小王子,在一开始或是过着最苦的下层人民的日子,而他们凭借善良的本性总会赢得别人的尊重,自己也会在关键时刻得到报恩。那开头狠毒的后妈、狡诈的巫婆也越发衬出主人公品质的可爱,而来之不易的大团圆结局也越发可喜。与其说是作家这样安排的,倒不如说是童话作品需要这样一个结局,作家最需要做的是在“过上幸福的生活”这种模式之下创作出许多充满奇思妙想的有趣情节就可以了。但是王尔德童话打破了这一固有模式,带入很多成人世界的因素。童话是王尔德写作的绝佳载体,是其作为唯美主义者审视下的现实世界,一方面有着他理想的美善人物,一方面现实的种种不堪相继打压这份净土。他曾说约翰·马哈菲“有意识地从艺术的立场看待一切,而这也在成为我的立场”。正如王尔德自己所言,他的童话宛如“牧笛的低吟”,“真正美丽的故事总是让我哭泣”,所以他的作品欢乐少,眼泪多。
王尔德视艺术和美高于一切,在1886年《济慈情书被拍卖有感》一诗中,他就把济慈情书被拍卖与《圣经》四福音书中兵丁抓阄分耶稣的衣袍类比。这一幕被视为《圣经》中最黑暗的一节:
这是恩底弥翁怀着秘藏的情感
给他怀恋的人写的书信。
拍卖场里挤满吵吵嚷嚷的人,
正出价争购每一张可怜的信笺,
真的!对诗人激情的每一次搏动,
都开了价钱。不爱艺术的商人
弄碎了诗人水晶般的心,
以便他们的小眼睛能贪婪地紧盯。
岂未听说过?在古老的年代,
遥远的东方市镇黑夜笼罩,
一群兵丁高举着火炬跑来,
为一套简陋的衣衫争吵,
拈阄分一个不幸人的衣袍,
懵然不值上帝的惊讶和悲哀![8]212
面对现实的丑陋,作家可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不幸的是,生活中美和艺术时常被轻视,甚至被亵渎,这对于王尔德来说,是莫大的伤害,这份感伤的情绪自然而然被带进作品中:诉诸语言文字的,是诗性的语体;诉诸童话主人公形象的,是诗性的死亡。与现实世界一样,童话世界里也都是些庸人和无知的恶棍,艺术的美在他们手里遭到摧残,心里无望的王尔德只能通过基督来化解这场危机。
基督精神一直在影响着他的创作,包括他的诗歌、戏剧和小说。在现实丑与艺术美的碰撞下,艺术美只有通过死亡来净化自身,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而这里由基督角色来完成再恰当不过,因其本身就是受难者原型。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少年国王》《打鱼人和他的灵魂》《自私的巨人》《星孩》这5篇童话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宗教意味,有的出现了上帝的声音,如《快乐王子》中出现了耶稣受难的形象,《自私的巨人》里双手双脚有钉痕的小孩,这无疑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化身。《快乐王子》和《少年国王》带有明显的博爱精神,无私的快乐王子和少年国王是富有牺牲精神和博爱精神的典型,一般将其视为殉道者。《自私的巨人》和《星孩》则明显有一种“原罪”意识,通过自我救赎而达到灵魂的拯救,一般视其为自我救赎者。但无论是殉道者还是自我救赎者,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灵魂得救。至美形象的死亡背后是一个高贵灵魂的上升。王尔德似乎对“灵魂”格外着迷,他的童话中灵魂就经常以暗喻的方式出现,有时甚至出现了有形的形象。这种探索在其他体裁的作品中也有表现,比如他的《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灵魂更是可以出卖的。王尔德后来在《自深处》中明确指出:“基督一直在找寻的是人的灵魂。他把这称为‘上帝的国度’,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他把这比作小东西,一小粒种子,一小团酵母,一颗珍珠。这是因为,只有在摆脱了所有与之不合的情欲、所有习得的文化、不管好坏所有的身外之物,然后人才能领悟自己的灵魂。”[9]138王尔德所理解的《圣经》中的耶稣是富于爱的灵魂的象征,“他(耶稣)恳求那个他看了喜欢的年轻人,‘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时他心中想的并非穷人的处境,而是那年轻人的灵魂,那个正被财富所糟蹋的可爱的灵魂。他的人生观与艺术家无异;这样的艺术家明白遵循自我完善的必然法则,诗人非唱不可,雕塑家非用青铜思考不可,画家非以世界为他的心绪的镜子不可。这道理千真万确,就像春天里山楂树必得开花,秋天里苞谷必得金黄一样,就像月亮有条不紊地漫游天庭一样,何时如盘,何时如钩。”[9]139-140所以从表面看,童话里的生命在现实中死去,却又在灵魂中复活过来得到永生。现实的生命固然宝贵,而艺术的永生更加伟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自私的巨人里有许多说不出的感动,在少年国王加冕里更有一种自内心上升的敬畏力量:
百姓们敬畏地跪了下来,贵族们把宝剑插回剑鞘,向他行着敬礼,主教脸色发白,他的手颤抖着。“比我伟大的已经给你加冕了。”他大声说,跪倒在国王的面前[5]400。
《打鱼人和他的灵魂》是收录在《石榴之家》的童话。对于这一篇故事,研究者历来各执一词。有人对人鱼和打鱼人之间的爱情赞叹不已,有人说美人鱼的形象是肉体爱的代表,作品中表现的是灵与肉的分离与冲突,有人看到了“爱”胜过一切。这篇作品似乎更像作家本人的呓语,与王尔德同时代的叶芝是这样评价的,“《快乐王子及其他童话》是迷人而有趣的,因为他是在说故事……而《石榴之家》则充满了过多的装饰性,很少趣味性,因为他是在写故事;并且因为他在写作的时候……不再考虑某个特定的读者”[10]23。可见《打鱼人和他的灵魂》的创作出于自己的喜好,糅入了王尔德许多与其他作品不一样的思想。比起以往他的童话作品,这篇出现了特别多的童话形象,年轻的打鱼人,他的灵魂,小人鱼,女巫和神父,他们每个人的出现似乎都代表了一个声音。同一篇故事里,不再仅仅是正邪两种声音,而是各自有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形成了复调的格局。因此,也比别的童话难懂。
故事开场,打鱼人迷上了人鱼的歌声,然而人鱼族生来没有灵魂,要想在一起,打鱼人就要舍弃他的灵魂。随后打鱼人开始寻找舍弃灵魂的方法,他找到神父,神父严厉地呵斥了他,并称“世间再没有比人的灵魂更宝贵的东西……人鱼,他们是无可救药的”[5]425,与他们交往的人,“也会是无可救药的”[5]425。而在商人那里,灵魂一钱不值。后来,打鱼人找到了女巫,女巫先是惊恐,后来又以与她在月圆时跳舞做条件,答应了他的请求。打鱼人最终和灵魂分离了,和小人鱼到了海中。然而,灵魂每年都要求见一次打鱼人,第一年灵魂想以“智慧”打动它的主人,第二年又想以“财富”,然而都被打鱼人用“小人鱼爱我”否定了。直到第三年,灵魂告诉打鱼人,城市里有光着双脚跳舞的姑娘,这一下子就打动了年轻的打鱼人。然而,当打鱼人回到海边的时候,他怎么也唤不出他的小人鱼,便在海边住下。灵魂用许多恶去引诱他,又讲了许多善的事,可打鱼人心里的爱实在很强,没有任何作用。直到最后,灵魂乞求打鱼人让它回到他的心里去。打鱼人同意的那一刹那,小人鱼被海浪卷到沙滩上,死了,打鱼人心也碎了,灵魂趁机回去了,他们统统被海浪卷走。再后来,神父看到他们的尸体,大声地指责他们,把他们埋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几年后,坟上开出了很美的白花,人们把它放在祭坛上,闻到香味,神父的内心也在那天的布道上起了奇妙的变化。故事最终在神父对一切的祝福中回到原来的样子,像是什么也不曾发生。
故事的前半部分实际上是在阐释对“灵魂”的看法,世俗的商人只用金钱衡量一切,对此不屑一顾;另两类人态度十分激烈,一个是代表善的神父,他呵斥打鱼人着了魔,一个是明显属于对立面的邪灵——女巫。当她和打鱼人进行明显带有仪式意味的舞蹈时,魔怔的打鱼人忽然唤了圣名,在胸口划了十字,破了女巫妖计。至于这么做的原因,文本这样写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5]431,一如故事最后神父原本要讲上帝的愤怒,却讲了一个“爱”的上帝,“为什么这样说,他也不知道”[5]456。一切好像突如其来,王尔德也有意不点破。其实大可以这样说,第一次很明显是圣灵拯救了打鱼人的灵魂,让他免受“恶”的控制,这是关于善恶之争;而最后一次呢,则是爱柔化了属灵(善)的心,又借着属灵(善)的力量祝福这一方海域。王尔德理解的基督是一位爱的基督。
故事的后半部分开始描写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大框架下,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必导致爱的凋亡,但讽刺的是,象征爱情的人鱼在灵魂与肉体合为一体的一刻死去了,原因无他,被赶走的灵魂没有一颗心,就来到黑暗的世界上,它便受到世俗的玷污,变得诡谲多端,如同行尸走肉。看到这里,读者不禁会扪心自问,灵魂的真正气质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去守护它呢?但随着海浪的平静,人鱼的游走,王尔德在最后也没有给我们答复,似乎都朦朦胧胧。直到1897年在《自深处》中王尔德才写道:“艺术使得我们心有千千重。有艺术气质的和但丁一道流放去了,尝到了他人的艰辛,明白了他们的困苦:他们有一阵领略到了歌德的宁静与淡泊,然而心里对波德莱尔为什么会向上帝呼告又太清楚了:‘啊,主啊,给我力量和勇气吧/让我看看自己的身体和内心而不厌恶。’”[9]140这里有对现实的厌烦,更有对美与爱的呼求。
王尔德透过自己艺术的眼光,让许多富有爱的形象在童话里闪烁着奇妙的光,尽管他们在现实中死去了,却在天堂里得到永生。这是灵肉合一而不可分的存在方式,更是一切伟大艺术必经的,就像“别人看到的……不过是黎明越过了山头,而我看到的,是上帝的孩子在欢欣呐喊”。他用极美的叙事把个人的理想投影到童话世界的细节之中,人们通过那些支离破碎的影子,看到苦难,看到泪水,但渐渐地,也会看到世界的另一端。正如王尔德在雷丁监狱《致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剖析自己的心路历程:“我要尝遍世界这个院子里每棵树结的果……我犯的唯一错误,是把自己局限在那些以为是长在园子向阳一面的树当中,避开另一边的幽幽暗影。失败、羞辱、穷困、悲哀、绝望、艰难,甚至眼泪、从痛苦的嘴唇断断续续冒出来的话语、令人如坐针毡的悔恨、披麻布饮苦胆的悲情——这一切都是我所害怕的。正因为决心不过问这些,后来才被迫一样一样轮番将它们尝遍……我只有往前走,园子的另一半同样也有它的秘密留给我。”[9]122
这就是王尔德,一方面告诉你“难道制造不幸的神,不比你聪明吗?”,一方面又隐隐地告诉我们至爱至美永恒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