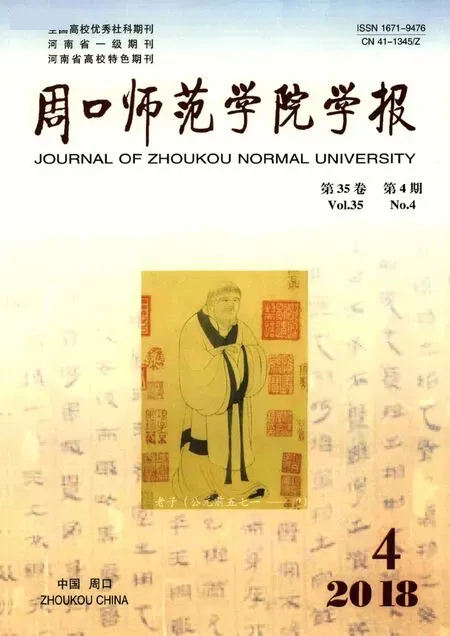从逆境中崛起的铿锵玫瑰
——解读《人树》第二代女性人物形象
2018-02-09吴艳红
吴艳红
(三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人树》(1955年)的出版开拓了帕特里克·怀特的世界文学之路,特别是197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从备受争议的澳大利亚本土作家华丽转身为世界文学大师。《人树》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虽然一面世就争议不断,但它的“史诗”气魄和“宏伟”构建让学者试图深挖其精髓所在。怀特在动笔之前曾说过,他构思的《人树》是为了“发现平凡背后的不平凡,发现神秘和诗意”[1]。小说主要是通过斯坦夫妇平凡的生活,表现人类生活的共同本质,即人由诞生到死亡的人生历程,是对生活的不断探索不断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随着人类的繁衍不息而代代延续,永无终结[1]。小说中涉及的民族历史和民族形象是令人难忘的,特别是69位女性的接连登场,笔者欲从烦琐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梳理出怀特创作这一宏伟场面的内涵和意义。
之前,笔者曾梳理过69位女性人物形象,并对第一代女性人物中的3位代表形象所承载的民族意义进行了解读。那么,对步入民族时代的第二代女性而言,她们身上又被寄托了怎样的意义?在此,笔者选取具有代表性意义的4位女性人物形象,阐释怀特是如何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来关注民族问题的。
一、历史背景
随着时间的推移,澳洲诞生了一批土生土长的新澳大利亚人,他们逐渐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人口组成部分。尽管他们被称为“喀伦西人”*“喀伦西”是英语单词currency(货币)的音译。那个时候,人们用“喀伦西”这个词来指澳大利亚当地使用的货币,所谓“喀伦西人”指的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与之相对的单词是“斯德林”,也就是英语sterling(英币),人们用这个词来指在英国出生的澳大利亚人。由于英币含金量较足,因此“斯德林”的褒义更多。参见曲卫国《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澳大利亚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124页。,但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为澳大利亚形成自己的民族特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喀伦西人”也是英国人的后代,因为他们的父母是英国人,但他们却和第一代移民完全不同。人们注意到这一代出生、成长于开创时代的喀伦西人,“健康、活泼、适应性强、积极向上,在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较英国人更能吃苦耐劳”[2]。喀伦西人与他们的父辈是不同的,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视这片热土为自己的家园。而父辈们对英国的眷恋和感情使得他们较年轻一代缺乏归属感。在年轻的澳大利亚人眼里,澳洲的历史于1788年英国第一舰队在悉尼抛锚时开始,他们对澳洲的历史充满了神秘的热情,认为那是浪漫的传奇和英雄的故事,正是这样的情感使得新一代澳大利亚人与生俱来更加乐观和自信。
在澳洲出生并成长的女性同样具有她们自己的特点。除了上面提到的对英国的态度和感情外,澳大利亚女性一直致力于自由和未来。虽然在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她们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却没有享受到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女性工作更努力,获得的报酬却更少。在自由和平等的道路上她们一直在奋斗。
怀特把女性这种复杂的情感注入《人树》中。小说中的第二代女性像现实中的女性一样经历了困难和奋斗的阶段。怀特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一般被认为是“现代人”的形象,她们崇尚自我,不相信上帝和传统的价值观念。本文探讨的4位女性虽然被置于同一社会环境中,却拥有完全不同的个性。她们都是从逆境中崛起的一代铿锵玫瑰。
二、艾米·帕克:幻想和失败的澳大利亚
有学者认为《人树》中的女主人公艾米·帕克的原型是怀特的母亲露丝。露丝是怀特大部分创作的女主人原型形象。小说中,艾米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婚前和婚后。可以说,结婚前的艾米过得并不快乐,她的生活充满了失败的痛苦。自幼双亲就离她而去,她只能和育有不少孩子的舅舅、舅妈一起生活。那时候的艾米可以说遭受着精神和肉体双重的压力。她不但要帮忙照看那些年幼的孩子,还要去其他家庭帮工来谋生;此外,由于缺乏父母的爱,以至于她也很难去爱其他的人,似乎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当她和斯坦成为一家人后,她才开始学着如何去爱,如何去尊重她的丈夫。
新婚宴尔,艾米是这个家庭的核心,而且,艾米“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建造之中。这使得她默不作声,一种举足轻重的感觉油然而生”[3]72。她的生活似乎开始了收获的旅程。根据艾米的故事和怀特的描述,笔者认为艾米象征着澳大利亚在走上独立的征程中幻想和失败的一面。怀特在小说的末尾称艾米是个“软弱的女人,她一辈子干什么都不成功”[3]673。
艾米·帕克是一个浪漫的女性。她爱幻想未来,爱憧憬美好的明天。结婚初期,她就梦想着和丈夫过浪漫的新生活。不仅如此,她还付诸行动。艾米在自己的屋外建了一个漂亮的小花园,花园里栽满了各式各样的玫瑰花。这些浪漫的幻想和举动都说明艾米期待着一种有诗意的生活方式。然而,随着新鲜感的逝去,艾米个性中那些负面的性格慢慢暴露出来,并影响了她的整个人生。她梦想的那些美好生活都在慢慢地失去,最后都只是“幻想”而已。
的确,小说中的艾米似乎一辈子都在“失去”。年幼时,她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婚后,她失去了第一个未出世的孩子。当艾米怀孕的时候年轻的帕克夫妇是多么的高兴。他们为孩子的到来绘制了一幅美丽的画面:可爱的小男孩降临在他们家。他们甚至想再建一个屋子,或者是一栋房子来迎接孩子的降生。然而,很快他们的梦想就成为泡影,艾米·帕克“撞在一堆黑魆魆的东西上面摔倒了”[3]85。就这样,她失去了自己第一个未出世的孩子。此后的几年,艾米怎么也怀不上孩子。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在乌龙雅洪灾中捡了一个孩子。艾米用遍所有的方法与孩子沟通,孩子都不搭理她。即使当他们把孩子带回家里,给孩子讲身边的环境和房子,大部分时间孩子还是保持沉默。第二天早晨,孩子就偷偷地离开了他们。至此,孩子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用皮尔斯的话说,孩子“重新回到人群中,只留下一片模糊的记忆”[4]。又过了几年,艾米终于生下雷·帕克。但这个孩子并没有给艾米的生活带来改变。虽然艾米非常爱这个孩子,怎么亲也亲不够。然而布利斯(Bliss)认为,“用爱或者对爱的需求是控制欲表现的一种方式”[5]。艾米与她的儿子渐行渐远:她不了解儿子的想法,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虽然偶尔会收到儿子寄给她的信件或者明信片,然而最终还是失去了他。有学者认为,艾米从特尔玛出生开始就已经失去儿子雷了。艾米那强烈的占有欲,使得她在想要紧紧抓住儿子的爱时,同时又把他从自己身边推开了。
艾米的占有欲还影响了她和斯坦的夫妻关系,使他们的婚姻走向尽头。斯坦·帕克从艾米的吃饭习惯中已经意识到艾米那种强烈的控制欲。有时候,艾米嘴里塞满了食物,却仍然滔滔不绝,她的声音里充斥着迷离和贪婪。不管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还是斯坦思想的起伏,艾米恨不得全部了如指掌。很多时候,艾米看起来对斯坦已经很了解了,然而事实上她从来没有走进斯坦的内心世界。最后,艾米自己都觉得她正失去对丈夫的控制。
正如艾米那一直失去的人生一样,被卷入二战的澳大利亚也经历了惨痛的“失去”的代价——在欧洲战场,阵亡将士人数为9572人;在亚洲战区,阵亡人数达17 501人;而在被俘的22 000名澳大利亚官兵中,7964人在战俘营中受折磨而死[6]。也许是因为怀特曾经在二战中服役过,他个人更注重战争的结果。澳大利亚“作为英国在太平洋的海外最大的前哨基地,在这次战役中遭受重创”[7]。怀特通过塑造这样一个拥有“失去”人生的女性形象,来揭示澳大利亚那幻想和失去的时代。
三、多尔:沉稳而内敛的澳大利亚
约翰·麦克拉伦(John McLaren)认为怀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经常是模糊的,这增加了读者对其小说和人物理解的难度。“每个人物都是小说的一部分”,他指出,“这种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被读者所了解。因此,读者必须掌握相关的背景才能确切地了解特定的人物的生活是可以忍受、理解和和谐的”[8]。这种认知,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多尔这个女性形象的生存困境。
多尔不像我们探讨的其他女性一样有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她一生孤独,生命中唯一的责任就是照顾她的兄弟。由于她“认为自己不能再照顾自己的兄弟而亲手结束了她兄弟的生命”[9]。她被当作小说中一个怪异的形象。的确,多尔在《人树》中的举止是怪异的,笔者认为,是多尔那沉稳而内敛的性格让她在不堪的人生中完成使命的。
出人意料,多尔这个所谓的怪异性角色年轻时被认为是一位高雅而沉稳的女士。她那高贵的气质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在奎克莱依家族,她是唯一能读能写的人,受到亲戚和其他人的尊敬。小说这样描述:
某种天生的端庄和她的棉布衣衫一起,紧紧地包裹着她。甚至还在光脚丫的时候,人们就管她叫奎克莱依小姐。她的侄男外女还没有出生,就要把她当作一个尊敬的对象,坐着大车或者轻便马车,后来甚至是坐着福特牌小汽车来看她[3]65。
然而,让人失望的是,优雅和高贵并没有给多尔的感情生活带来欢乐和爱情。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多尔就开始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她的父母已年迈,生活不能自理;两位兄长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弟弟是个弱智儿。所有的家庭重担全落在多尔一个人身上。也许正是生活的磨难锻造了多尔那坚韧不拔的性格。
多尔的性格可以说反映了当时喀伦西人鲜明的特点。在艰难的岁月中,人们与陌生的自然环境和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做斗争,这些造就了新一代澳大利亚人顽强、不畏艰辛的品质。不像英国人看重的是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他们性格中有着独特的方面,如追求平等、崇尚伙伴情谊、豪放豁达、乐观真诚等。他们也不像美国人那样自由,社会需要他们去追求成功和成就。这种竞争性诞生了很多工作狂和所谓的铁男子汉——指那些努力工作但从来不为艰苦的环境而哭泣的人。
多尔也是一位“铁”女子。她的生活看起来枯燥且一成不变,但她总是能够很平静地对待。她从来没有哭泣或抱怨自己的人生,而是默默地忍受生活现实带来的痛苦。多尔对生活的忍耐力源于她对大自然的热爱。她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让她的心境更加平和。她就像一件艺术品那样干净柔和。她也从来不会对人们生气。即使当她发现艾米对她和弟弟表现出不耐烦,她也总是默默地离开。而当人们有需要她的时候,她总能及时出现帮助大家。多尔很少跟别人沟通,或者去学一些新的知识,“多尔知道的都是与生俱来的”[5]。她用自己的方式生活在那个沉闷的世界里。
多尔的安静与平和表明她是一个内向的女士。她对母亲的爱是无声的,她的爱流淌在细微的生活中。她对弟弟的爱是无言的,她承担了所有的家庭劳作,让巴布生活在自己自由的世界中。而对斯坦的爱也是润物细无声的,她会为斯坦做一些小点心,虽然她的举动在背后经常被艾米嘲笑,然而,多尔还是多尔,她一直安安静静地在那里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多尔被一些学者看作是怪异的人物,但她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感与平和态度是非常可贵的。她是一位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家庭的积极的女性形象,是一朵从逆境中成长的铿锵玫瑰。
四、马徳琳:美丽而浪漫的澳大利亚
格里尔(Greer)(1999)宣称对女性而言最重要的是“美丽”,她认为“每个女人都知道,不管她其他的成就,如果她不够漂亮,那么她就是失败的”[10]。 这段描述直接指出女人的美丽对她们成功的重要性。翻开小说,显而易见,在怀特的笔下,马徳琳是一位美丽的女性。她的美丽不但吸引了男性的目光,同时也引起了女性的关注。在斯坦的眼里,马徳琳是“一件欲望品,然而她是冷漠的、遥不可及的,而且不可触摸的”[11]。对艾米而言,从她第一次见到马徳琳,她就深深地嫉妒了。在马徳琳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艾米在远处盯着她看了良久。小说中,马徳琳的美丽实在是太明显了。在阿姆斯特朗家里起火时,斯坦去救马徳琳,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马徳琳穿着一件肥大的长袍。那袍子在火光下闪出许多种光彩。她那满头秀发垂下来,披在肩头。因为下午天热,她把头发都解开了。因此,当她回转身面向他的时候——因为她不可能对他的到来充耳不闻——他觉得,他从来没有见过有谁能像这个穿着闪闪发光的长袍的女人这样光彩夺目,飘飘欲仙[3]252。
若干年后,当斯坦重新回到这座废弃的房子前,那一刻的美妙又重新回到他的脑海中。那么冷静的斯坦竟然对着鸭子大吼大叫,笔者认为,斯坦发泄的是心中的渴望和欲望。
兹维基(Zwicky)认为怀特笔下的女性角色都有她们自己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说家怀特并不描写男性和女性。他的想象力把男女人物都转换成高于生活的英雄主义,特别是女性,怀特为她们安上了天使或者鹰的翅膀来抗击澳大利亚社会现实的牢笼[12]。虽然小说中马徳琳是个“不够真实的人物形象”[13]35,但笔者认为正是因为马徳琳的美丽与浪漫情怀让她在小说中充当了一个美丽天使的角色。因为马徳琳的美丽,很容易就能引起小说中其他角色的注意,并做出一些举动,她成为试金石,从而帮助读者看到其他相关人物的多面性,能够综合地分析并理解那些角色特点。例如,马徳琳的美丽让读者看到了艾米的嫉妒、斯坦的渴望、小阿姆斯特朗的占有欲和阿姆斯特朗家庭的空虚,等等。人性弱点的暴露,让这些角色更加现实、更加丰满和更加人性化。
此外,马徳琳的美丽也给小说带来一些浪漫的元素,让小说读起来更加诗意。马徳琳和小阿姆斯特朗的交往在乡下人的眼里是爱情的魔力:年轻漂亮的女士为了爱从城里来到这个荒凉的郊区。这对年轻的读者来说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在那场大火中,斯坦和马徳琳之间的火花虽然让读者难以置信,却又那么真实。那么,马徳琳对小阿姆斯特朗是否有所谓的“爱情”就成了一个疑问。在小说的结尾,怀特没有忘记这位美丽的女士,塞尔玛把她带回这片曾经给她带来深刻记忆的土地。虽然怀特并未交代马徳琳回来的动机是什么,但是这种留下来的悬念和猜测让读者有了想象的空间。怀特通过对马徳琳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从侧面提升了女性的地位,揭示了女性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马徳琳最后离开了小阿姆斯特朗,这是她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女性走向新未来的重要决定。
五、欧达乌德太太:乐观、自信的澳大利亚
在所有的女性形象中,欧达乌德太太的性格是最有特点的,不过我们很难从她的人生中领略什么是辉煌,什么是幸福。在没有任何婚姻的承诺和婚礼仪式的情况下,她随欧达乌德先生来到这片刚开发的土地上谋生,成了“欧达乌德太太”。其实,她用欧达乌德太太这个名字不为别的,只是图个方便而已,而且虽然她与欧达乌德先生这样喝醉酒而置自己于危险境地的人生活在一起,但她并没有打算离开他。她就像那些新一代的澳大利亚人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性格。笔者认为,欧达乌德太太象征着乐观和自信的澳大利亚形象。
小说中,欧达乌德太太的出现让人印象深刻,怀特用“一种讽刺的、精确的并且滑稽却不带嘲讽的语言来描述两次非常喜剧性的场面但不喜剧的情节:与欧达乌德先生吵架以及她自己的弥留之际”[13]38。她除了是天生的乐观派,还是一个“不会回过头看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情”的人。她总能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起起伏伏。无论她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处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中,她总能勇敢地走下去。
首先,艰苦的现实生活没有打倒欧达乌德太太,而是试着去调整自己,学着珍惜目前拥有的。第一次和艾米见面,她就愉快地告诉艾米她所拥有的财产,其实,那只不过是“两口要下崽的母猪,一口小公猪。此外还有一群小母鸡”[3]55。欧达乌德太太和她的男人就带着这些家畜家禽开始生活。他们自己建了房子,虽然看起来奇怪,却也实用。当欧达乌德先生过度酗酒,家里无力负担时,欧达乌德太太就自己酿啤酒来满足她男人的酒瘾。
其次,欧达乌德太太总能看到生活中阳光灿烂的一面。她对周围的人都很大方。当艾米的母牛死掉,她就借一只母鹿给艾米去喂小牛。在她的世界里,朋友和邻居就应该在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忙。由于她丈夫是个酒鬼,欧达乌德太太经常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她的丈夫会拿着刀满屋子地追着她砍。但在丈夫酒醒之后,就会一切烟消云散,她从不指责自己的丈夫。在她眼里,欧达乌德先生是一个好人,只是偶尔会喝醉犯点小错误而已。她能够在被欧达乌德先生追砍后,立即就安静下来,自己一个人开始哼一支曲子。欧达乌德太太,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女人,她比小说中同时代的其他女性都要乐观。
再次,欧达乌德太太总是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当战争爆发时,几乎所有的男士都走进部队,扛起枪炮,只留下孤独的女人们在家里。这时候欧达乌德太太表现得相当独立:她说,是妇女们承担责任的时候了。她对邻居们充满了友善,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要收土豆的时候,她来帮忙;配种的时候,她为公牛抓着母牛[3]204。
此外,即使当她得了癌症,欧达乌德太太也从来没有表现出害怕或者绝望。她告诉艾米,她不会轻易倒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还与艾米分享那种超灵魂的体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欧达乌德太太早已融入新环境。在新的土地上,她的乐观、自信让她的生活更加灿烂。而这些优秀的品质在那个时代的澳大利亚女性身上都可以找到。
六、结语
上面提到的4位女性形象在小说中都属于第二代移民,她们各有特点。相似的地方是她们都爱澳大利亚这片土地,没有像第一代女性那样对英国有着感情寄托。而与第一代女性不同的是,这4位女性中至少有3位都有自己的名字。这显示她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身份,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她们是敢于追求自己梦想的女性。艾米种植玫瑰花,给自己的生活增添点诗意;暗恋斯坦的多尔,为自己的梦中情人做甜点;美丽的马徳琳离开小阿姆斯特朗,去追求自己的新生活;欧达乌德太太在没有任何形式或承诺下与欧达乌德先生相伴一生。就像怀特用“玫瑰花”来展示这一代女性的浪漫情怀一样:“玫瑰花可以是艾米园中种植的那些玫瑰花,也可以是她在通奸时地毯上的那些玫瑰花;是未生育的欧达乌德太太墙纸上的玫瑰花;还可以是马徳琳乳沟中的玫瑰花。”[14]然而,就像笔者前面提到的一样,她们又是不同的。由于控制欲而被戴上“失去”帽子的艾米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东西,特别是她的孩子们、她的家庭、她的爱情和她的梦想。被定义为怪异形象的多尔,她的人生遭受了孤独、苦闷和谋杀。而欧达乌德太太是小说中唯一面临死亡的角色。她的乐观帮她度过了生活中的许多难关,自信让她的人生更自立。也许读者会认为马徳琳是这4位女性形象当中最幸运、最快乐的人,美丽为她带来了财富、爱情、社会地位和生活的质量,然而她的生活中也有过困惑和痛苦。就像她置身于大火中却并不主动逃脱或者自救,这也许是她脆弱的原因。幸运的是,马徳琳还是活下来了并且开始了自己的新人生。
总之,文中的4位女性虽然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她们都能够勇敢地去面对。她们努力地生活,提高社会地位。她们是从逆境中崛起的铿锵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