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综合征”
2018-02-08晓晴
晓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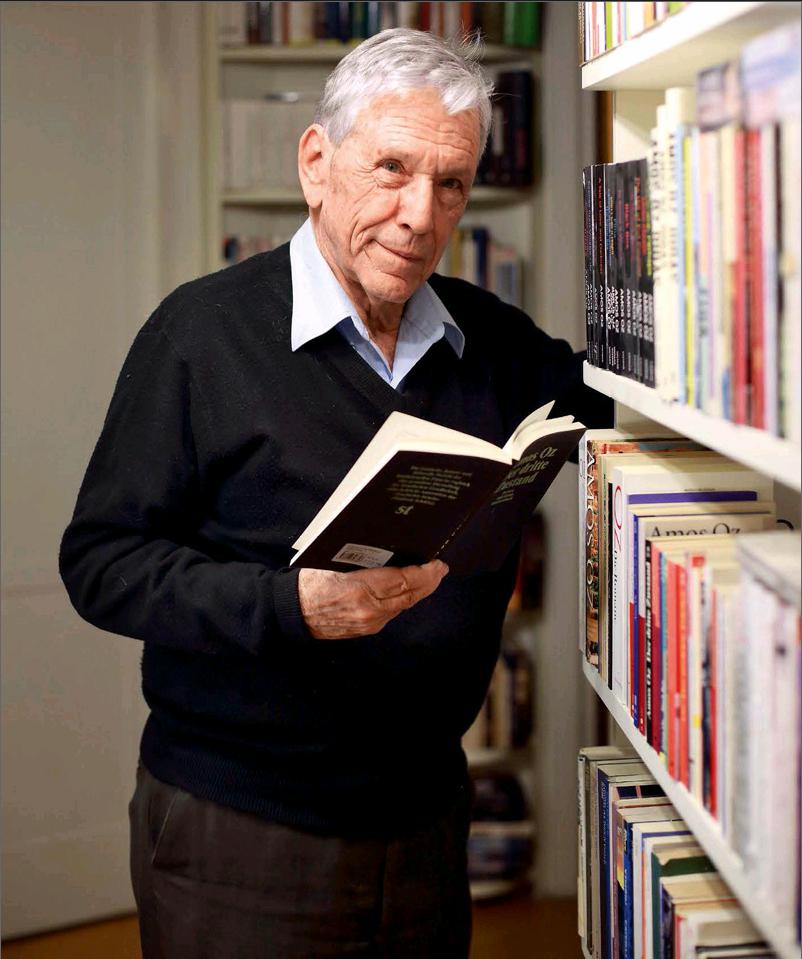
1834年的5月3日,17000名基督徒挤到圣墓教堂领取圣火时发生了意外,继而引发踩踏事故,造成约400多基督徒死亡,并由此引发暴乱。暴乱被镇压后,奥斯曼帝国大叙利亚总督易卜拉欣允许基督徒和犹太人重建他们在起义中被破坏的教堂和会堂。也是为了讨好欧洲人,奥斯曼苏丹颁布诏书,给予各少数民族平等的权利。易卜拉欣则邀请欧洲各国在耶路撒冷设立领事馆。1839年,第一任英国副领事到达耶路撒冷。这时,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势力开始进入巴勒斯坦地区。
作为基督教的圣城,耶路撒冷对欧洲的基督教君王有巨大的吸引力。1859年4月,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来到耶路撒冷,进入圣墓教堂时,“饱含眼泪和情感”,离开时,“禁不住哭泣”。为了方便大批的俄国朝圣者,俄国还成立了一个轮船公司,从敖德萨运送朝圣者往返耶路撒冷。他们还在耶路撒冷购买了地皮,建了莫斯科风格的小镇。
1862年4月,英国威尔士王子(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在100个土耳其骑兵的护卫下来到耶路撒冷。兴奋的王子甚至还想在胳膊上弄一个十字军刺青。1869年,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茜茜公主的丈夫,在参加完苏伊士运河通航仪式后,从埃及来到耶路撒冷。当时奥斯曼千人卫队护送,大卫塔鸣礼炮迎接,皇帝记道:“我跪在路边亲吻着土地。”他被“每件事物看起来都像从儿时故事和《圣经》中跑出来的那样”这种情感征服了。奥地利人也在耶路撒冷买地建设。其中一个就是苦路上的奥地利救济院。
随着欧洲人的不断到来,现有的遗址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热情和好奇心了,他们开始通过挖掘,以求找到更多与《圣经》有关的遗址和证据。所以从19世纪中开始,欧洲各国在耶路撒冷开始了一股考古热。其目的一是出于宗教的狂热,二是通过考古发现,更有利于控制耶路撒冷。除了俄国和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也加入了考古热,这股热就像20世纪的太空热,并被称作“和平的十字军东征”。
去耶路撒冷旅行似乎是一个时髦。从1800~1875年间,大约有5000多本与耶路撒冷有关的书籍出版。不过大都没什么新意。这股热潮里,当然少不了作家。当现实中的耶路撒冷变得衰败的时候,想象中的耶路撒冷开始激发西方人的梦想。
最早是法国“圣墓骑士”夏多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内(Francois-Ren)。尽管他承认,“耶路撒冷还是吓到我了”,但对他来说,也许耶路撒冷越悲惨,就越神圣,越充满诗意。夏多布里昂的《从巴黎到耶路撒冷》(Itinerary from Pairs to Jerusalem)奠定了欧洲人看待东方的态度。
1848年2月23日,俄国作家果戈理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为的是追寻精神上的慰藉和神灵的启示。作为一个俄国人,他认为只有一个地方能提供救赎,他写道:“在我去过耶路撒冷之前,我说不出任何话语去安慰任何人。”但果戈理的耶路撒冷之行是一场灾难,回俄国后拒绝谈论耶路撒冷。有趣的是,2000年,《英国精神病学期刊》将这种疯狂的绝望诊断为“耶路撒冷综合征亚型二:那些来到耶路撒冷并抱有耶路撒冷具有治疗能力的神秘观点的人——如作家果戈理”。
赫尔曼·梅尔维尔在37岁的时候已经因三部小说赢得了名望,不过1851年出版的《白鲸》一书却只卖出3000本。1856年,在忧郁与苦恼中,梅尔维尔抱着能够恢复健康的目的于1856年来到耶路撒冷,他同时还想来探求上帝的本质。“我的目标是——让我的脑海浸透耶路撒冷的大气,让我成为其神秘影像的被动主体。”他受到耶路撒冷“残破”的刺激,被其“未经激发的荒凉的裸露”而陶醉。返回美国后,他写下了一万八千行的长诗《克拉瑞尔》(Cleral)。
福楼拜也是这个人群中的一个,但他似乎对圣城的印象并不好,他形容耶路撒冷是一个“被围墙保卫的藏尸所,古老的宗教都在太阳底下慢慢腐朽”。
1866年,来自密苏里的新闻记者马克·吐温参加了一个号称“伟大的圣地欢乐游”的乘船朝圣游覽活动,但是他却将其改名为“伟大的圣地葬礼考察”。马克·吐温将朝圣视为一个闹剧,对那些美国朝圣者的虔诚进行了嘲讽。尽管如此,他还是悄悄地给母亲在耶路撒冷买了一本《圣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吐温当时住的穆斯林区的地中海酒店,在20世纪80年代被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首领沙龙买了下来,目的是将穆斯林区犹太化。现今这个建筑是一个犹太神学院。
到了19世纪后期,耶路撒冷到处都是追寻“天启”的美国人,以至于《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将这种症状与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相对比。林肯并非真正笃信宗教之人。1865年4月14日在与妻子去往福特剧院的路上,林肯还提议到耶路撒冷进行一次别样的朝圣,结果当晚在剧院里被杀,据说遇刺前不久,林肯还在小声嘀咕:“我是多么想参观耶路撒冷啊!”
1969年8月,一名澳大利亚游客大卫·罗翰(Michael Dennis Rohan)被强烈的神圣使命所压倒,前往阿克萨清真寺纵火。烧毁了阿克萨清真寺里的一座公元680年的原装木质布道台。后来大卫·罗翰被以色列有关部门在精神病医院里关了好几年送回了澳大利亚最后死在了澳洲的一个精神病院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