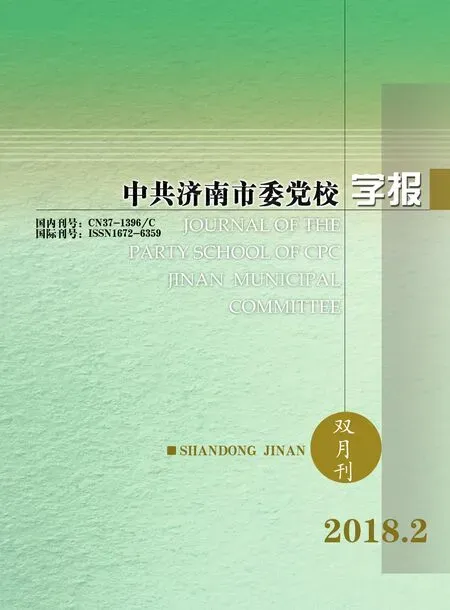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文化自信
——从传统政治文化维度的分析*
2018-02-07郭海龙
郭海龙
2017年,在十九大召开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前后,“文化自信”成为继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之后的第四个自信。文化自信离不开优秀的传统文化,而在各种政治思潮澎湃激荡的背景下,传统政治文化更是文化自信的根。文化,尤其是一个国家的传统政治文化是该国政治制度世代相传的“遗传密码”。
一、政治制度应当契合本国的传统政治文化
文化是政治制度的基因,政治制度需要与本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相契合,这包含两方面。
(一)政治制度源于文化
各国的政治制度演化的历史表明,“政治体制需要契合本国世代相传的独特政治文化基因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文化是政治的基因。”[1]只有改变政治文化,形成新的政治文化传统,才能从改变一国的政治机制(含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如果不顾自身政治文化和发展阶段而盲目机械照搬他国政治制度,就会产生各种社会冲突乃至政治乱局,即“水土不服”。目前,众多非西方国家实行宪政民主时就产生了政治乱局:“制度规范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制度规定形同虚设;缺乏‘fair play’的契约精神,导致政变、政治暗杀、政客恶性竞争的事件层出不穷,如尼日利亚的总统选举常常伴随着军阀混战”;[2]“一党主导型”政党制度和强人政治现象突出,[3]并有效促进了国家稳定,有的还促进了国家发展。这说明,“制度内容、法律规定容易照搬照抄,而宗教和政治文化以及政治传统则根深蒂固,难以从根本上改变”。[4]“盲目实行宪政民主导致国家失序,缺乏秩序最终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迟滞了社会进步,因此,这些本就落后的国家变得更加落后从而更加依附于强国”。[5]于是,这些国家“进入了 ‘强人政治-宪政民主-混乱-强人政治’的恶性循环之中,如埃及‘阿拉伯之春’以政治强人穆巴拉克下台为始,以政治强人塞西上台后穆巴拉克被释放为终”。[6]
西方宣扬的“宪政民主”实质上与西方的政治文化高度契合。宪政民主植根于基督教原罪说,“基督教的原罪说是整个基督教的理论与实践得以立足的基础”,“原罪的理论使得基督教对各种事情都在提防……随时准备发觉那无所不在的罪恶”。[7]弗里德里希在分析宪政论的起源时,认为“它根植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西方的宪政论是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8]这后来嬗变成为伦理学和政治学中人性自私论以及权力是“必要的恶”的认知,并进一步演化出防范和制衡权力的政治逻辑:对人性善良和权力正确行使的怀疑,使得西方的权力配置遵循着制衡原则。
此外,西方的宪政民主并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它是在中世纪中后期教权与世俗王权的斗争、专制王权与市民(即新生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权的冲突过程中才得以形成的,并“产生了政教分离的二元政治观念,由近代自由主义进行了传承”。[9]这种内在二元论一直存在,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宪政民主制本身就是民主与法治之间冲突原则的悖谬联结”。[10]这说明了西方国家法治的复杂性。当代英国法学家拉兹(Joseph Raz)也认为,“如果仅从原则上考虑,非民主国家实现法治可能比民主国家更容易”。[11]也有其他学者同样指出“民主和宪政关系紧张”。[12]
宪政民主渊源于欧洲独特的政治文化,“欧洲文明的主要标志或者欧洲文明的主要历史功绩必然是欧洲的宪政、法治、人权,因为,这种宪政、法治、人权是有别于其他文明的,它有其独特的法律文化秉性。”[13]欧洲法律史学派从欧洲宪政主义的历史根源认为:“两重因素构成了欧洲宪政主义的理论内涵,即一种精神——欧罗巴精神;一种理念——欧洲宪政法治理念”。[14]因此,“欧罗巴宪政主义传统是宪政民主需要具备的文化前提”。[15]
(二)政治制度应当契合本国的传统政治文化
这意味着政治文化传统发生变化时,政治制度也需要类似的调整,否则,同样会发生不匹配的现象。一般来说,一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是世代相传、经久不变的,但历史往往存在着例外,这正是历史让人着迷之处。而德国是在政治文化传统转变最彻底的国家,因而,其政治制度也相应地进行了改变,并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传统。“二战后德国在占领之下接受了政治文化彻底改造,从一个普鲁士军国主义乃至极权主义国家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比较彻底的国家,宪政民主得以巩固。但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而日本未进行彻底改造,国家主义残余至今仍然浓厚,右翼势力不时兴风作浪,右翼的自民党虽在野过几次,仍长期一党独大。”[16]德国、日本这种被打败导致传统政治文化中断的现象比较独特,更多国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发生的变化是一种微调之中的渐变。例如,以国家主义传统著称于世的法国,由于启蒙运动洗礼,使得“自身政治文化呈现出‘狮身人面像’般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兼容的神秘特征……法国半总统制和左、右两大政党也都兼容了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17]
对东方国家而言,传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相比,更是“体”与“用”或“皮”与“毛”的关系。例如,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认为,“万事难料,唯有一事我敢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终决定走向两党制,我们将注定平庸”。[18]对于华人社会的集权必要性,李光耀非常清楚。由于深谙此道,李光耀在新加坡开创的“威权主义”很契合其政治文化,为新加坡打造了平稳的社会氛围,推动了星岛崛起。这对中国塑造契合中华道统①的政治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中华传统文化氛围下,政治上十分有必要集权,不应贸然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
综上所述,德、日、法、新加坡等国政治体制契合了各自独特的政治文化。这一不约而同的现象再次雄辩地证实了一条关于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之间的道统铁律:要实现长治久安,政治体制的顶层设计要契合本国的传统政治文化。
二、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
“天下为公”家国情怀、和合共生文化特质、“大一统”整体思维,[19]外加上社会主义政治属性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内涵。
(一)“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出自《礼记》。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出于公心留下了许多光辉事迹,近代更有大量先驱为了振兴中华而终生为之奋斗。当代政治文化也传承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把自身定位为“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私利”的政党,各民主党派有着古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因而,各党派之间的共识远远大于分歧,精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政党制度既是历史形成的,又契合了“天下为公”的传统。
“天下为公”的另一表现是,中国人崇尚公权力对公共事务有用的一面,“公器”、“神器”即对公权力的敬称,“大公无私”、“公而忘我”是中国的政治伦理和道德情操。这与西方对权力“必要的恶”的强调和防范存在迥然差异。在中国,私人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公共利益,维护了中国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使得“中国崩溃论”不攻自破。相反,非洲、中东欧的一些国家却因实行“宪政民主”而出现了混乱乃至真正的崩溃。
(二)和合文化
“和”即《论语》所言“礼之用,和为贵”,强调和平共处;“合”即合作共赢。和合文化是一种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存在一些重大不同之处:
1.在政治上表现为大局意识、包容精神。如政协对人大等国家机关“监督不对立、协商不代替,为了发展生产力,同唱一台戏”。而西方存在党争无底限现象,导致政党政治呈现出“碎片化”状态,“缺乏整合使得西方国家屡屡遭遇民粹主义等的冲击,民粹主义甚至被认为是西方民主的伴生物”。[20]
2.在哲学上表现为重视调和与综合。中国党派合作是长期的主题,党派差别往往通过相互协商和让步而达成一致,形成政治共识,这使得中国凝聚力较强,为决策“一竿子插到底”创造了环境。而西方哲学重视对抗(斗争)和分析思维,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各党派互相拆台,合作共事是暂时的、不得已的举动。例如,2017年德国大选,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CDU)不得不在另择党(AfD)崛起为第三大党、理想的传统执政伙伴自民党(FDP)议席偏低的情况下,选择“曾发誓再也不与基民盟合作”②的社民党(SDP)组建德国历史上第四次大联合政府。
3.在社会生活上注重集体主义和亲友之间的相互依赖强。在中国,个人的事往往成为家庭和团体的事;中国各党派则以“公”为重,很少强调私利;中国社会的整合程度较强,西方各种思潮难以掀起波澜。而西方注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21]的个人主义且个人独立性比较强。“党派之间也比较独立、泾渭分明,以‘part(部分)’为词源的‘party’一词注重党派集团利益,更接近‘朋党’一词。”[22]
4.自古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中国社会崇尚秩序,整体意识比较强,政府自古以来就承担起教化百姓的责任,起到了政治学方面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政府的认同感、信任度较高。虽然这在某些方面被认为是愚民政策,但“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道德经》),教化使得人们规避了社会恶性竞争,降低了民众受极端思想蛊惑的可能性,不自觉地在思想领域筑起了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防火墙,保持着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西方崇尚个人自由,人们个性张扬、风格易变,在思想观念方面飘忽不定,公共理性精神难以持久,尤其是在危机发生时,“排外”、“贸易保护”、“逆全球化”等民粹主义思潮会泛滥成灾,令西方社会猝不及防,“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一些西方学者因此指出,“代议制民主必然与反精英主义的力量和民粹主义共存”。[23]
总之,和合文化重视调和与综合,使得中华文化不断汲取并统合各种文化资源,从而不断发展壮大。而西方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不断分裂所产生的文化隔阂,以及西方的条分缕析哲学思维,使得西方文明难以表现出整体感。鉴于此,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24]
(三)“大一统”观念
“大一统”整体思维也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
1.历代尊奉“大一统”思想。战国时,孟子在“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在“一天下”(《荀子·儒效》)主张中提出了大一统的主张。后者儒法结合实现大一统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其深刻,并得到了历代的贯彻执行。对此,清末谭嗣同曾以“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25]来进行评价。在“大一统”实施之初,短暂的秦朝和汉初60年只是军事、政治方面的统一,这种“大一统”缺乏精神方面的理论支撑、人心难服,是很脆弱的。比如秦朝时,人们长期在心理上抗拒秦朝的统治,农民起义也打着恢复六国的旗号。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根据董仲舒“大一统”学说(《春秋繁露》)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此后,“大一统”得以在思想文化方面确立,并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思维范式。西方则相反,例如查理大帝帝国曾昙花一现,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签署《凡尔登条约》瓜分帝国时,并无继续帝国统一的意识,而是相互确定了彼此的边界与平等的权利,使得统一的大帝国分崩离析。从那个时候起,除了拿破仑战争和二战这些非常时期外,西欧大陆就再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如今的欧洲一体化也难以实现实质的统一。
2.大一统催生了集权体制。大一统不仅是国家领土的统一,更是权力的集中统一。“历史上盛世一般都出现在大一统时期,如开元盛世、康乾盛世。而权力分散往往导致乾坤易数,危害社会。”[26]如东汉末年大权在外戚和宦官之间交替,导致纲纪松弛、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诱发了黄巾起义和军阀割据。总之,权力的集中统一是国家一统、政治变革成功、社会繁荣发展和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保障。
3.大一统也体现在中国的思想和宗教领域。秦汉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对思想领域进行规范和控制,宗教和思想流派也主动向国家政权靠拢,甚至以得到敕封的名号为最高礼遇。而诸如“竹林七贤”等不屑与世俗政权同流合污的文人,多数归隐山林,过着隐居生活,势单力孤,难以像西方那样形成诸如“雅各宾派”、“裴多菲俱乐部”之类与国家抗衡的团体或“罗马俱乐部”之类的独立人士集团。而欧洲在30年宗教战争(1618-1648年)之后才确立“教随国定”原则,之前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教会则动辄以革除教籍的名义对封建主进行制裁。
总之,政治权力的集中统一是中国千百年来独特的政治文化,这也是中华文明保持数千年不曾中断的主要原因。只要不是闭关锁国,“大一统”的中国会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汉、唐、明这三个朝代。这对于当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社会主义属性
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以来,社会主义属性已经在近代百年的曲折探索中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的政治传统。社会主义属性既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也是先进的中国人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主动学习的结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属性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这源于马克思和列宁的相关理论。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7]应当“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28]对于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而言,这是一种先见之明。二战后,欧洲的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或参政或执政,均未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未能 “埋葬资本主义”,反倒通过福利制度等措施完善了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弥补了资本主义原来的制度容易诱发革命和危机的种种不足,从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变成了资本主义病榻边的“医生”,乃至成为了资本主义遗嘱的“执行人”,已经被资本主义同化,难以改造资本主义。
之所以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民主精神并没有在宪政民主框架(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表现形式,即政体)中得到贯彻,民主被三权分立等立宪原则进行了限制,并被称作“共和主义”。美国多元主义大师罗伯特·达尔曾指出,民主是“经济自由的威胁,对那些作为财产权利的自由来说,尤其如此”。[29]二是资产阶级害怕占人口多数的无产阶级通过参加选举获得政权,从而不利于自身的统治。“19世纪的精英拒绝公民权的普及,拒斥那些热衷于‘议会道路’的社会主义者,并认为如果多数原则在严重不平等的现实当中得到贯彻,那么,绝大多数投票者会支持向富人征税而且将税收下移。”[30]这是美、欧国家当时政治方面“顶层设计”的真实情况。
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积极进行了设想,有两类。第一类以马克思、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为代表,他们主张民主就是大众参与。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在理论本质上比资本主义民主更真实、更具体。但是,由于超前于当时以及当前的政治经济条件而迄今尚未变成现实。第二类是列宁的设想,却在实践中独辟蹊径,取得了成功,并影响到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就是民主集中制(与“官僚主义集中制”是两码事[31])。这种民主集中制的主张,使得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也是中国革命成功和政治运行的现实逻辑。
上述经典作家的论述,既为当前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所实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未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文化自信
中国的传统、发展阶段和人口社会特征以及社会属性决定了民主集中制更适合中国,是中国应当长期实行的制度原则。
(一)长期的集权传统
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专制君主制传统的国家,“大一统”的思想在政治上、文化上都根深蒂固,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要办好中国的事情,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去谋划和实施,形成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而当代中国倡导包括“民主、平等、法治”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国家属性内在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则从理念层面给中国传统上习惯于集权和现实中需要集权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一条思路,这就是我国长期坚持的民主集中制。
需要澄清的是,民主集中制并不是民主和集中之间寻求平衡、求折中、取平均值,而是民主授权基础上的集中,即通过所有成员参与的权力授受机制把集中的权力授予中央机关去决策和执行,并通过各种途径对集权的机关进行监督,从而使得权力的运行高效且科学。现阶段,中国需要的是更加明确民主集中制内在要求的民主的权力授受环节。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十分契合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制度,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二)现实的发展要求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且内部发展不平衡的人口超级大国,要化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平衡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需要一个权威力量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中国是一个处于外部诱压型后发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正如亨廷顿等人认为的那样,外部诱压型后发现代化客观上需要通过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这需要集权的政治制度。[32]这方面,俄国-苏联、德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土耳其等一大批后发国家无一不是通过集权体制进行了外部诱压型后发现代化。
正是出于这种内在的文化自觉和真切的现实考虑,我们才能在深刻理解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树立起充分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才能在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一如既往、理直气壮地坚持十分契合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现阶段国情和政治传统的政治机制(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党体系。这正是文化自信的外在表现。
注释:
①中华道统是一个比较庞杂的体系,总体上代表了传统政治文化中关于政权合法性(“政道”)和治国理政之术(“治道”)两个层面的政治智慧,为避免歧义,本文多以“中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词汇表达类似的概念。
②社民党由于此前参加大联合政府而在议题上成为默克尔所在政党基民盟的跟班,在大选中,社民党处境尴尬:要是反对基民盟就是反对自己此前在大联合政府的政策,而若不反对基民盟则选民没法把社民党与基民盟区分开来。社民党的这种尴尬处境使得其党主席舒尔茨曾宣布“再也不与基民盟合作”。但是,为了抵御强势崛起的民粹主义政党另择党,社民党不得不与默克尔第三次组成“大联合政府”。
[1][2][4][5][6][15][16]郭海龙. 从政治与文化角度对西方宪政民主的剖析与反思[J]. 国外理论动态,2016(6).
[3]许苏江.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形势呈现的新特点[J]. 当代世界,2017(2) .
[7]Lord Acton.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M].Gibraltar: the Becon Press, 1948, pp.14-15.
[8]J.弗里德里希(周勇,王丽芝译). 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M].北京:三联书店,1997.1.2.
[9]W. Ullmann.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79, pp.7-8,229.
[10]Jürgen Habermas.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A Paradoxical Union of Contradictory Principles? [J].Political Theory. 2001, Vol.29, Issue 6, p.766.
[11]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p.211.
[12]Carlos Santiago Nino. The Constitu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M].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
[13]Uwe Wesel. Geschichte des Rechts in Europa[M].Muenchen: Verlag C. H. Beck, 2010, S.21.
[14]Hans Kloft. Die Wirtschaft der griechischroemischen Welt. Mue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2,S. 88.
[17]郭海龙. 略论国家主义对法国社会党政治观念的影响 [J]. 法国研究, 2014(2).
[18]【新加坡】李光耀. 李光耀观天下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176.
[19][21]季思.风云激荡方显中国民主的生命力[J]. 当代世界,2017(3).
[20]林德山.民粹主义是西方民主的伴生物[J].当代世界,2017(3).
[22][26]郭海龙. 《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构建纠错机制的良好开端 [J].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7(1).
[23]Benjamín Arditi. Populism as a Spectre of Democracy: A Response to Canovan [J]. Political Studies.2004, Vol. 52, 135 143.
[24]刘涛.汤因比的预言:中国文明将照亮21世纪[J].社会观察, 2013(3).
[25]谭嗣同全集·仁学[M].北京:中华书局,1998.337.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55.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06.
[29]Robert Dahl.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5, p.2.
[30]Ian Shapiro. Democracy and Distribution.Jedediah Purdy ed, Democratic Vitas: Reflections on American Democracy[C].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p.173.
[31]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60-361.
[32]【美】塞缪尔·亨廷顿(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