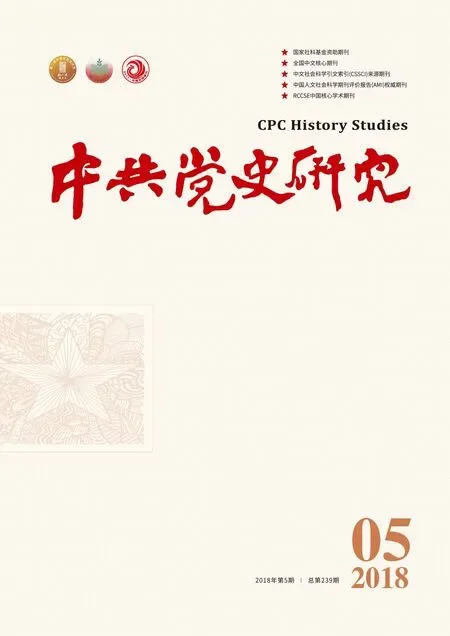上海“阿飞”:滚动的话语逻辑与基层实践走向(1949—1965)
2018-02-07刘亚娟
刘 亚 娟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国家权力开始向下延伸,揭开了城市基层社会清理与改造的序幕。通过划分“敌”“我”、“新”“旧”,中共将不符合新社会特征的文化形态具象化,进而自上而下、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城市旧疾,使基层社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净化。作为文化形态的载体,某些话语也伴随着这一进程逐步更新、嬗变甚至消失。如果将话语视为一种“活”的、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且或隐或现的权力关系的再现,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显然也是一部话语史,上海阿飞即是这部历史中最为典型的案例之一。“阿飞”这一称谓来自洋泾浜英语。在有限的学术成果中,阿飞均被纳入流氓的范畴,呈现刻板、片面和静止的形象。*关于“阿飞”的英文来源存在一定争议,概括起来有fit、fly、figure、fashion四种。以笔者目之所及,迄今未见有以阿飞为主题的学术成果,但相关通俗读物数量颇丰。参见程乃珊:《“阿飞”正传》(上、下),《上海文学》2001年第7、8期;程蔷、孙甘霖主编:《民俗上海·黄浦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30页;薛理勇:《上海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52、153页;叶世荪、叶佳宁:《上海话外来语二百例》,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1页。此外,关于游民改造的相关研究也多次提及阿飞,基本上属于“流氓”层面的解释。参见阮清华:《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34、179、209页。实际上,阿飞起初并非流氓,而阿飞与流氓的分合也折射出相当复杂的历史信息,天然可作为话语分析的素材。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尝试将话语分析的方法导入党史国史研究。在相关的研究中,话语的生成与演变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可循,不单话语的塑造与政治运动的走向相契合,地方实践也基本成为中央高层指示的直观反映*尽管以“话语”为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真正使用了话语分析方法的研究尚不多见,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参见陈灵强:“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生成与建构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刘怡:《从“麻雀”到“害人鸟”:五十年代中后期灭雀运动的话语逻辑》,《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不过,这种单调的线性逻辑并不足以解释阿飞形象与内涵的流变。阿飞释义不以历史前后相继的顺序排列并通往唯一终点,也不像编年体一般呈现所谓新旧交替的面貌。打不胜打的阿飞不仅再现了基层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其背后蕴藏的诸多信息更值得还原与深究。
一、小阿飞初现:时髦青年问题化
阿飞是近代上海的“特产”,其典型打扮是“三包一尖”(奶油包头、裤子紧包腿臀、裤脚紧包脚踝、尖头皮鞋)。他们既非上流青年的打扮,又多少有点摩登的意思,有几分“纨绔子弟”的味道,又夹杂些“轻浮举止”。*陈丹燕:《上海阅历三部曲·蝴蝶已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7页;周起凤:《石榴花开的时候》,《申报》1936年6月23日;频罗:《成衣匠的傀儡》,《申报》1936年11月3日;刘业雄:《阿拉上海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0页。旧时洋学生与上海滩的白领常称那些标新立异、打扮得引人注目的人为“这位阿figure朋友”,或是评论某些前卫的装扮时来一句“迭(上海话,意为‘这’)个人蛮‘飞’的”*程乃珊:《“阿飞”正传》(上),《上海文学》2001年第7期。。40年代从国外传来一种新式舞蹈,“两人对舞,摇头晃脑,抽肩膀,扭屁股”,上海人改曲谱名为“满场飞”,亦可以从中窥见“飞”字的独特内涵。在时人眼中,裤脚管细得像笔管、花得耀眼的衬衫、尖头皮鞋乃至于乘势凌空的“飞机头”,不过是爱漂亮的都市儿女的生活剪影*额前留部分头发,用吹风机压好再回旋,使头发向前高高翘起,形似飞机的头部,再涂上厚厚的凡士林,油光发亮,这即是“大包头”,或称“奶油包头”“飞机头”。参见李阿毛文,董天野图:《洋泾浜图说》,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7页;萧毓华:《风气》,《申报》1942年5月21日;云郎:《飞机头》,《时代周报》1946年第3期。。上海著名消闲小报《小日报》还有一撰稿者常以“阿飞”自称,阿飞在旧上海之流行可见一斑。
无论是“阿飞”这一称谓还是他们的典型装扮,均是美国文化与上海都市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对其影响最大的又是好莱坞电影。除了侠义爱情诙谐片、牛仔频繁出没的美国西部片外,在好莱坞明星中间风靡一时的“飞行热”,也直接推动了阿飞的产生。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大包头”“奶油包头”在当时被称为“飞机头”,阿飞也被戏称为“小飞机”。
新中国成立之初,阿飞多被冠以“小”,与沪上另一群体“老克拉”(洋泾浜英语,“克拉”即color)相对,展示了另一个年龄层次与时髦档次。阿飞之“小”首先体现在年龄上,他们以一二十岁的青少年为多;其次,他们徘徊街头,以奇特的衣着为炫耀,偶尔做一些起哄、欺骗、调戏之类的“小恶”,或者是跟着“大坏蛋”后面做点“小坏事”。
当时上海男青年中不乏以中山装配花呢法兰绒、镂花鞋者,而烫着波浪式的人造卷发、大穿标新立异人民装的也不在少数。“三包一尖”之所以迅速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它们堂而皇之地再现了所谓“美帝文化”,显示新中国的不少青年仍以模仿美国生活方式为荣*灵甫:《“阿飞”思想》,《文汇报》1950年11月10日;《抗美援朝代表会议,愤怒控诉美帝罪行》,《新民晚报》1950年12月6日。。从1950年6月开始,文艺界开展了一场清理好莱坞电影、肃清崇美思想的运动。刚刚创刊的《大众电影》随即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声讨好莱坞电影将好青年变成了小阿飞。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作家黄宗英将阿飞视为穿着红红绿绿的衬衫、小裤脚管,嚼着橡皮糖,整日在电影院门前徘徊,既没有家也没有国籍的海派青年们;而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于伶则直接将小阿飞视为青年人受美国影片“毒害”的明证*黄宗英:《两种文化》,《大众电影》1950年第1期;于伶:《期望》,《大众电影》1950年第1期。。从1950年9月开始,《文汇报》又以“你对美帝影片看法如何?”为主题在工、农、商、学中间展开了对“美帝”影片的讨论。不少青年现身说法,讲述自己受好莱坞电影“毒害”而变成阿飞的经历,从而将运动推向高潮。
不过,就在文教领域批判好莱坞电影的同时,一系列以阿飞为主题的滑稽戏却纷纷出炉抢占上海娱乐市场。多家滑稽戏剧场竞相以阿飞故事编成剧本进行演出,一时间阿飞戏满天飞。刚刚解放、生意不好的戏馆子,因上演阿飞戏而“出乎意料地生意好起来了”*歌今:《邻居伙伴成搭档,票友下海二笑匠》,《新民晚报》1950年6月23日。。各剧场上映的阿飞戏均十分卖座。上海的阿飞戏轰动一时,还吸引了香港片商来沪接洽,计划将其拍成电影。
阿飞戏上演之初是作为配合公安机关清理阿飞的教育活动之用,但在党报看来,这些戏把阿飞的“油腔滑调”写得很突出,或标榜阿飞智慧,或将之视为英雄,结果不是反阿飞,反而是“宣扬”阿飞了*《上海工人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人民日报》1952年6月23日。。滑稽戏多反映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主要受众是普通劳动者。文艺界对阿飞戏的批判愈燃愈烈,工厂对阿飞戏却兴趣不减。“新都”“新新”滑稽剧团应一些工友俱乐部之邀,专赴工厂表演*《阿飞总司令明日下工厂》,《新民晚报》1950年8月7日。。阿飞戏的问世与卖座,从侧面证实了阿飞文化在上海普通市民中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而在好莱坞电影遭到清理的同时,阿飞戏也呈现取而代之、再续阿飞形象的态势。
在随后展开的“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中,学校里的小阿飞作为落后分子的典型受到教育,一些工厂企业中的贪污分子也以阿飞型的青年出场。打扮时髦、“油头粉面”的小阿飞也成为运动对象,被要求开展自我批判*廉风:《三反运动挽救了黄泽民》,《文汇报》1952年3月14日;屠公望:《我是怎样腐化堕落的?》,《文汇报》1952年3月17日。。党报则将矛头从好莱坞电影转向阿飞戏,控诉舞台上的阿飞起着坏作用。阿飞戏此后也遭到有关部门的抵制,一度消沉。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界开展的运动中,阿飞的形象与内涵基本延续了近代上海的特征,即以“三包一尖”为典型装扮、做点儿“小恶”的时髦青年。脱胎于近代上海的阿飞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旧上海”“旧社会”的产物。也正是遵循着这一逻辑,阿飞作为新政权改造与整顿的目标之一,无形中为新政权施行一系列改造举措提供了契机。
二、“飞”进工厂:与流氓划清界限
1954年9月1日,团市委对解放后上海青年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上海仍然存在着不少流氓团伙,“诱使”青年逐渐走向“堕落”。团市委在报告中还专门提到工人阶级的不佳表现。*《关于青年中受资本主义腐化堕落思想影响的调查报告》(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489-51。另见《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关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毒害青年的调查报告》(1954年9月1日),转引自闵小益:《20世纪五十年代上海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述略》,《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根据上述情况,团市委向市委和团中央请示,提出在全体青年中开展一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的建议。
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呼吁各地坚决肃清流氓、盗匪,称有些流氓、盗匪“诱骗”青少年犯罪,少数“不法资本家”则用金钱、女人、淫乱书画和下流娱乐场所的吃喝玩乐生活来“勾引”意志薄弱的职工走上流氓、盗匪的道路。11月14日,《人民日报》再发表社论,认为一部分资本家正利用金钱、色情“引诱”青年工人,企图使他们“腐化堕落”,新中国第一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正式揭开帷幕。无论是《人民日报》的社论导向,还是上海方面的具体安排,都显示这场道德教育运动围绕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进行,在实际运动中又以青年工人为重点展开*《关于“积极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大体步骤》(1954年12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80-2-7-15。。
这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打击流氓盗匪的活动相辅相成、配合进行。从协作运动的角度上讲,二者恰好扮演了一松一紧的角色。上海市委将“流氓盗匪”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的帮凶”,认为其主要罪行在于“残害劳动人民”,“引诱青年”堕落。团市委进一步明确要求,不能把政府打击流氓盗匪的斗争和对青年进行正面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混为一谈,而要教育青年与流氓“划清界限”*《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开展贯彻反对流氓盗匪活动斗争和加强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的紧急通知》(1955年3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6-2-387-116。。
在宣传动员阶段,除了此前已经在全国进行推广的负面典型——中学生马小彦,上海方面还树立了两个工人典型——修布青工傅宝娣以及机械厂青工马承伦,但团市委对三人的宣传轨迹却并不相同。
首先,从负面典型的设计与舆论导向来看,两位青工的堕落均是掉进了“圈套”或受到“毒害”所致,所呈现出来的也均是“受害者”的姿态。不少工厂在发动青工讨论傅宝娣的案例时,均有意识地引导青工识别傅宝娣的工人出身,使之认识到傅宝娣的腐化堕落主要是受流氓勾引所致。*青年团上海市第二重工业委员会:《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情况反映》(1955年3月3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44-2-308-24。相形之下,马小彦的堕落则被视为剥削阶级出身使然,他也成为三人中唯一被公诉判刑的青年。这一结果引起了不少工人猜测,认为正是傅宝娣的工人出身使其免受惩罚,工人成分占点儿“便宜”。*《上海市长宁区委宣传部关于审判十三名流氓盗匪请示和教育情况的报告》(1955年3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1062;《青年团上海市委关于处理虞正钦、方振、王开生等十三名流氓盗窃分子后在群众中反映情况的通报》(1955年3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6-2-399-30。
其次,团市委在运动中反复强调注意区别流氓与阿飞、落后青年以及腐化堕落与生活作风上的一般问题的界限*《青年团上海市委关于在道德教育工作中发现的所谓“男女关系”等问题的通报》(1955年3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2-1049-3。。尽管承认工厂中存在一些落后青年,但在运动中并未将其与流氓相提并论。针对不少单位把婚姻恋爱不严肃列入“腐化堕落”或扣上“乱搞男女关系”帽子的情况,市委、团市委还不断发出通报,使基层组织认识到青年的男女恋爱、社会交际、衣着爱好等个人生活问题与“流氓行为”有着本质区别。运动对于青工中一些可能涉及“乱搞男女关系”的现象也作了回避和淡化处理。*《青年团上海市委办公室关于执行对广大群众进行反对流氓盗匪活动的宣传教育中注意几项问题的通知》(1955年3月1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2-2-54-6;《青年团上海市委关于处理虞正钦、方振、王开生等十三名流氓盗窃分子后在群众中反映情况的通报》(1955年3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6-2-399-30;《青年团上海市委关于在道德教育工作中发现的所谓“男女关系”等问题的通报》(1955年3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2-1049-3。
而从团市委扶植的典型上看,无论是马小彦还是傅宝娣、马承伦,实际上都呈现阿飞的形象特质。马小彦爱看好莱坞电影、穿小脚裤。傅宝娣、马承伦着“奇装异服”,与流氓为伍,流连于舞厅等娱乐场所。从运动的效果看,道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效果,对工厂学校的阿飞敲响了警钟。不少父母对阿飞本不在意,吸取了傅宝娣、马小彦的教训之后,也认为不能再麻痹了。很多男青工过去认为“搞女人”是自己的自由,现在也意识到须谨言慎行。*《青年团上海市委关于处理虞正钦、方振、王开生等十三名流氓盗窃分子后在群众中反映情况的通报》(1955年3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6-2-399-30。
由团市委主导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尽管呈现很强的温和性,但意义不容小觑。与此前主要将学校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战场有所不同,这场道德教育无论是主战场还是运动对象都发生了转移。教育的主要对象从学生转向青工,这一方面固然与知识青年进入工厂,为工厂的青年们送去了另一种文化形式有关;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即原本应该更为纯洁的工厂反而为亟待清理的基层文化提供了生存土壤。
在傅宝娣等人的故事中,“跳舞厅”均作为他们堕落的关键场所而存在。实质上,截至1954年9月底,旧上海所有的舞厅与音乐厅均已全部停业、转业,取而代之的是各单位举办的集体舞会。舞会起初作为健康的文娱活动而受到各方面的鼓励,但随着问题不断出现,各方批评也纷至沓来。不少读者向党报去信,称有单位以组织的名义开办个人舞会。由于舞会中女性通常比较稀缺,不少单位向社会上分发舞票邀请舞伴,参加的人成分复杂。出版社人员也反映,有工会组织到唱片商店里选买“充满了毒素”的爵士音乐唱片。上海市总工会宣传部的调查还显示,有的工厂舞会发展到放“黄色音乐”,把灯光弄得很神秘,丧失了警惕性。部分青年工人不能正确处理娱乐和工作的关系,因痴迷于跳舞而影响工作的情况比较普遍。*诸葛三:《文娱活动不能妨碍工作、学习和健康》,《文汇报》1953年10月30日;《本报二月份读者来信来稿处理情况》,《文汇报》1954年3月10日;《中小学生不宜参加交谊舞会》,《文汇报》1954年12月5日;蔡台:《上钢三厂开展了经常性的文娱活动》,《新民晚报》1954年1月23日;《交谊舞会中的唱片,应该慎重选择》,《新民晚报》1954年3月31日;马前:《严防“乘虚而入”!》,《新民晚报》1954年10月7日;《这样的“交谊舞会”》,《新民晚报》1955年4月27日;《上海市总工会宣传部关于目前基层举行交谊舞会中的一些情况和我们的意见》(1954年5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38-2-111-17。对此,《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上海某些工厂举行的跳舞晚会,已经成为“解放前放荡淫逸的旧式舞场的再版”,成为社会上流氓分子混进工厂、引诱工人堕落的一个媒介,这些不健康的因素已经严重地“侵蚀了”青年工人的思想意识*习平:《危险的“舞会”》,《人民日报》1956年12月3日。。
站在工厂的角度上看,工厂舞会之所以似禁未禁且风靡一时,除了工人业余生活的需要,青工的婚恋问题才是要因。“工资上百元,政治上党员,专业上技术员”以及“一粒星太小,三粒星太老,二粒星正好”等沪谚说明了当时青年女性的择偶意向。尽管工人在城市中逐渐树立起领导阶级的形象,但青工(尤其是年轻的产业工人)、学徒的级别低、工资少,在上海的婚恋市场上并不占优势。加上不少男青工又未形成正确的恋爱观,形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不少男青工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滋生了不正常的情绪。而鱼龙混杂的工厂舞会,给男青工与其他青年女性接触提供了一个空间。
除了“工钱要大”,青年女性对恋爱对象“不要土里土气”、面孔要漂亮的要求,也促使男青工向一种阿飞式的平民时髦靠拢。社会上的阿飞普遍会“玩”,出手大方,很多小姑娘很羡慕*《嵩山区关于团内部分团员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情况调查》(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489-51。。阿飞奇特的装扮,又很容易引起女人们的注意。不少男青工为找对象而结识阿飞并效仿。正因如此,男青工的“堕落”也往往与女人有关。
无论是工厂舞会的流行还是工厂青年向阿飞靠近,都从侧面证实了一种特殊的现象:一方面,阿飞在逐渐罪名化,其形象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另类时髦的层面;另一方面,接受、认可甚至服膺于阿飞文化的青年(特别是青年工人),其队伍仍在持续膨胀。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明确了“阿飞”不是“流氓”,青工被资本家“毒害”的话语逻辑则为青工中诞生阿飞这一事实提供了合理解释。不过,这一针对青工量身定做的阿飞释义并未被固定下来,而是很快伴随着形势发展而发生了变异。
三、政法进场:“流氓阿飞”的位移与扩散
实际上,早在团市委开展道德教育运动之前,民政与公安部门针对问题青年就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行动,但两部门所针对的对象并非学生与工人等有合理生活来源的小阿飞,而是社会上不务正业的闲散阿飞。公安部门“刮台风”般集中打击了品行恶劣、借势敲诈的阿飞,以及偷盗摸窃、危害治安的阿飞团伙。民政局也将阿飞列为应该被收容的“游民”之列。在实际处理中,两部门又习惯将阿飞归入“流氓”类,其中既包括依靠娼妓生活的小流氓,也有破坏秩序的犯罪分子,其表现与罪行可谓多种多样。*《上海市游民改造工作概况》(195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8-1-942-28;《上海市民政局关于游民的说明及处理办法(草案)》(1953年9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8-1-945-21;《游民残老儿童收容暂行办法(草案)》(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1-1357-1;《关于游民情况的初步报告》(1955年1月2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1-21-5;《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所编制情况调查资料之五》(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8-1-430-14;《调查汇报》(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8-1-954-65。也正因如此,直到1955年,双方对于社会阿飞应该法办还是收容仍然认识模糊,频频出现分歧*实际上,民政局从1953年开始连续三年颁布游民改造草案,对于“游民”的范围界定几经修改,争议不断。1954年民政局颁布《游民残老儿童收容暂行办法(草案)》,将阿飞再度列入游民。民政局领导提出质疑,认为阿飞是“法办对象”,不应该被收容。参见《游民残老儿童收容暂行办法(草案)》(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1-1357-1。。
进入1956年,阿飞问题变得更加棘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的到来,城市面貌和社会治安本该发生深刻变化,上海也理应呈现旧貌换新颜的图景。然而,公安部门却发现,尽管刑事犯罪在逐年下降,青少年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的比重却在明显递增。1953年青少年犯罪仅占全市刑事犯罪的8%,1955年下半年发展到19.6%,1956年上半年又增加到20.3%*上海市公安局治安办公室:《治安情况反映》1956年第5期,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1-31。。民政局也有类似观感,妇女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发现他们收容的娼妓呈现低龄化的趋势,其中不乏十三四岁的童娼*《1956年国庆节前收容工作》(1956年10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8-1-962。。
这种情况到了1957年后显得更加严峻。尽管公安部门对抢劫、杀人等刑事犯罪的打击卓有成效,民政局在妓女改造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的大背景下,社会上仍游荡着一大批问题青年这一事实始终无法得到合理解释*《上海将采取各种办法处理流氓行为》,《青年报》1957年5月24日;《上海市游民改造工作简况(1949年12月—1957年3月)》(1957年5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8-1-532。。更令工作人员感到不安的是,阿飞成分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多的青年工人和学生开始摆脱“小阿飞”的形象,他们在街头游荡、犯罪,“蜕化”为“流氓”*《上海市民政局关于游民收容标准范围问题座谈会记录摘要》(1956年9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8-1-964-28;《流氓阿飞活动日见猖獗》,《解放日报》1957年6月4日;《流氓阿飞害人匪浅,社会各界不能坐视》,《青年报》1957年5月10日;《有效地制止流氓阿飞活动》,《解放日报》1957年6月7日。。而相对于学校中的阿飞,问题青工虽不能称之为普遍存在,但其所作所为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学生更广。在“鸣放”运动中,远在厦门的旁观者即将矛头指向上海的青年工人队伍,称上海的流氓阿飞犯中“极大多数”属于这类人物。群众感叹很难相信是“一个工人”的所作所为之余,上海工人阶级的形象也大为受损*李罗芳:《“关于人民生活”的言论》,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宣传部编印:《右派反动言论集》,1957年9月20日;《怎样取缔阿飞分子?》,《文汇报》1957年6月12日。。
“流氓阿飞”作为存在于特定空间之内的小众表述,为民政局、公安局在小范围内使用。“工厂阿飞”“学校阿飞”——这些具有合法生活来源的“小阿飞”闯入两部门的管辖范围,使原本就内涵模糊、界限不明的阿飞复杂化。而相较于解放之初将阿飞都视为旧社会、十里洋场的残余“渣滓”,新上海层出不穷的阿飞由于解放时年龄尚小,已经不能算作是旧社会的产物,怎么界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仍层出不穷的阿飞也就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青少年犯罪日益严重的现实,使公安部门开始逐步取代青年团、工会以及学校,成为处理问题青年的主要部门。而原本只在机关公文中出现的“流氓阿飞”这一表述逐渐发生位移,频繁出现在党报党刊,替换了此前在党报中占主流的“小阿飞”*《本报读者来信揭发流氓阿飞害人事实》,《新民晚报》1957年6月7日;洛诚、吴兆祥:《“新都七兄弟”流氓集团为首分子诸学文被逮捕》,《新民晚报》1957年6月15日;《流氓阿飞邪气抬头》,《新民晚报》1957年5月11日;《许建国谈流氓阿飞问题》,《新民晚报》1957年6月5日。。《青年报》《解放日报》等报纸先后组织座谈,邀请妇女教养所、派出所、溜冰场、餐厅酒店、少年犯管教所以及部分工厂参加,专门探讨流氓阿飞问题。“流氓阿飞”也给各个单位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诉苦”工具。妇女教养所以“为流氓阿飞所侮辱”解释暗娼的出现。派出所将矛头指向法院,称自己是教育“无效”、扣留“无权”,指责工会“闹事来领”“领去不管”,一味依赖公安机关。溜冰场“惭愧”“苦闷”之余感叹“工作难做”。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则互相埋怨,认为对方只想推卸责任,让自己“包下来”。*《流氓阿飞害人匪浅,社会各界不能坐视》,《青年报》1957年5月10日;《配合公安部门取缔流氓阿飞,应该加强对青年的教育》,《解放日报》1957年6月5日;《上海市民政局关于游民收容标准范围问题座谈会记录摘要》(1956年9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8-1-964-28。
在一片抱怨声中,对政法系统办事不力的批评最为集中。《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发问:“每年夏秋,流氓阿飞活动就猖狂起来,几年来已成惯例。治安机关每年打击流氓阿飞有很大成绩,但是,为什么流氓阿飞的活动声势仍不减当年呢?”*《有效地制止流氓阿飞活动》,《解放日报》1957年6月7日。公安机关批评司法机关有过宽的偏向,从而助长了犯罪行为,要求司法部门严肃处理这类案件。各部门则一再强调应对那些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分子进行严厉打击。*《必须严惩流氓阿飞犯罪分子》,《解放日报》1957年6月6日;《流氓阿飞活动日见猖獗》,《解放日报》1957年6月4日。
与此同时,另一个空间发生的特殊事件也推动了“流氓阿飞”这一话语向工厂的扩散。原本忙于调查各厂贯彻《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情况的上海市总工会第二办公室(以下简称“二办”)并没有等来全国总工会的如期视察,而是迎来了“闹事”风潮*《兹接全总关于了解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的通知,转各产业生产部门的通知》(1957年1月2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2-2295;《全总和二办来往函书》(1957年4月1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2-2295。。1957年五六月份达到高潮的上海工潮,将作为“闹事”主力的青年工人推向舆论的中心。二办精心准备的以劳动纪律为主题的调查报告也随之进行了修改,青工劣迹成为报告的唯一主题。在这份报告中,二办断定阿飞不仅出现在新合营厂,即使在国营、老合营厂,其活动情况也是“极其严重的”*《上海市工会联合会第二办公室关于国营、老合营企业中流氓阿飞活动的资料》(1957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2-2295-28。。
根据二办所掌握的情况,这些阿飞的活动除了赌博、偷窃、斗殴之外,集中表现在“侮辱妇女”的流氓行为。从1957年1月至6月,上海锅炉厂工人中“侮辱妇女”的有17人,“强奸妇女”的有1人,流氓习气较重的有64人。大隆机器厂已发现“侮辱妇女”的有13人,上海自行车厂6个青年艺徒经常“胡搞”“调戏妇女”。上钢二厂初步发现,有严重流氓阿飞行为的就有七八个,已经逮捕的有2人。除了单独进行活动,工厂中还出现了不少开展厂际合作的阿飞集团。根据不完全统计,在5个机器厂和钢铁系统中,已发现6个阿飞集团。上海机床厂的两个流氓阿飞集团,平日出入溜冰场,争风吃醋,还组织斗殴,打伤工友。*《上海市工会联合会第二办公室关于国营、老合营企业中流氓阿飞活动的资料》(1957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2-2295-28。
在报告中,二办反复强调“这些人以青工和新进厂的工人为多”,并且相当一部分与领导为敌,带头“闹事”*《上海市工会联合会第二办公室关于国营、老合营企业中流氓阿飞活动的资料》(1957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2-2295-28。。相较于此前将青工的堕落视为“受毒害”“受引诱”“掉入圈套”,此时因参与闹事而形象受损的青工已经不再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不过,在这份调查报告中,问题青工虽然都被囊括在“流氓阿飞”的范畴之下,他们的具体表现却有很大不同。除了一起“强奸妇女”,更多人表现为“侮辱妇女”“诱奸”“威胁”等,其中还不乏“用香烟烧女生头发”“搂着女生听课”等行为。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犯有强奸妇女、奸淫幼女罪行者,一般均予以重判。而对于诸如“侮辱妇女”等行为却难以给出一个相对客观的定性与量刑,也因其最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材料中屡屡出现的“胡搞”,就与前文提到的“乱搞男女关系”有相似之处。早在新婚姻法推广前后,工厂中就发现青工中的重婚、遗弃、性关系混乱等情况比较普遍,其中重婚者又大多是男工,多数又有些恶势力或者比较“强横”的关系网络。*《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关于上海市青年工人、学生婚姻恋爱一些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展开婚姻法宣传的初步意见》(195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349-95。有研究者在讨论新婚姻法在北京工厂推广的过程时就揭示出这一问题,发现新婚姻法推广之后,青工的作风问题更加严重。参见庄秋菊:《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与北京工人婚姻观念的变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2期。在此前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中,团市委还专门批评了基层团组织过多地牵扯在生活琐事以及所谓男女关系问题上、给处理婚姻恋爱不严肃的青年扣上“乱搞男女关系”的帽子、把谈过几次恋爱的青工都看成是乱搞男女关系等行为。可以肯定的是,此前工厂中虽不乏举止更为恶劣的青工,但这些人也并未以“流氓”相论处。
不过,在从整风运动到反右派斗争的历史性转折中,“乱搞”与“闹事”的青工都面临着一个特殊时刻。上海工潮平息之后,作为“闹事”主力的青工队伍亟待整顿和惩处。上海各厂进而将取缔流氓阿飞和整顿劳动纪律一起进行,严肃处理了有严重流氓阿飞行为和违反劳动纪律的职工,强奸、诱奸妇女等性质恶劣的青工则被开除并交法办。
据资料记载,7月6日到10日,恰值全国反右派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毛泽东前往上海小住,其间视察了因“流氓阿飞集团”被二办点名的上海机床厂。此后不久,毛泽东在青岛主持召开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会后多次召集柯庆施等省市委书记谈话。*《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0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4—191页。不管是柯庆施的汇报可能透露了上海阿飞问题,还是上海地方党报对流氓阿飞铺天盖地的报道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原本只作为上海特产的“阿飞”在这一时期进入了中央高层的视野。
7月青岛会议后,毛泽东在与省市党委书记谈话要点的基础上形成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以下简称《形势》)。《形势》明确指出:“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毛泽东还特别提到:“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32页。《人民日报》随后以头版刊发文章,将阿飞与流氓、盗窃犯、凶杀犯、强奸犯等一同称为“罪犯”,而阿飞则与刑事犯罪分子一道,成为了“坏分子”。
毛泽东对于政法部门存在“重罪轻判”的判断,奠定了政法系统反右派斗争的基调。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均被认为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其主要错误在于把包括流氓、阿飞在内的刑事犯罪分子都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他们强调不要惩罚,而要注重进行教育改造。以往在实际处理中作为轻判条件的“劳动人民出身”“年纪较轻”等也受到广泛批判。*《打碎右派篡改法院性质的迷梦,高院反右派斗争取得大胜,彻底揭露刑事审判庭庭长、副庭长、研究室主任的反动言行》,《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2日;《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司法路线,上海司法界批判右倾思想》,《人民日报》1957年9月26日;集思:《切实批判在与坏分子作斗争中的右倾思想》,《法学研究》1957年第6期。
在全国范围内,作为政法系统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副产品,阿飞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但在工厂的环境下,对于阿飞的处理实际上执行的是另一套规则。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对工人中的极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流氓、阿飞以及严重违法乱纪的坏分子等要进行批判和斗争,对于情况特别严重或屡教不改的应该开除出厂,并作适当处理,但对一般思想落后、爱说怪话的人则要加以区别*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9日。。11月,上海市委工业部发布《关于在工人中划分坏分子的意见》,明确规定只有那些“有严重的流氓阿飞行为且屡教不改者”才被划为坏分子。而据当事人回忆,生产如何也是对阿飞进行定性的重要因素。*《上海市委工业部关于在工人中划分坏分子的意见》(1957年11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55-2-116;刘正新访谈(刘正新,1936年生,1949年进入中华玻璃厂担任工人,因着“三包一尖”多次受到批评),2018年1月15日;卫金南访谈(卫金南,1931年生,上海客车厂原厂长),2015年12月10日。
伴随着政法进场,阿飞坐实了“流氓”的身份。对于问题青年的态度从此前的“不管”走向“严惩”,加速了性质本较轻的“阿飞”与性质相对恶劣的“流氓”的合流。在“阿飞”被政治化与罪名化的形势下,不少阿飞改变了容貌和装束,把“飞机头”剪成“平顶头”,奇形怪状的衣服也暂时不穿*《在公安部门坚决取缔下,流氓阿飞纷纷坦白悔罪》,《青年报》1957年8月6日。。以“三包一尖”和“奇装异服”为典型特征的小阿飞内涵暂时隐退。党报对流氓阿飞的报道连篇累牍,法院审判与公安局逮捕流氓阿飞的新闻层出不穷。普通市民则对阿飞既恐惧又好奇,陆续有不少读者向《劳动报》投书请教什么是“阿飞”、“阿飞”从何而来?里弄中还出现了工人因随地小便就被当做“阿飞分子”,心理包袱重而服毒自杀的极端个案。*《新测字摊》,《劳动报》1957年6月7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编:《情况反映》1957年第24期,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54-1-2。“阿飞”借助领导人话语走出上海,成为全国范围内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但对于普通群众而言,弄不清楚报告中的字眼,对人民内部的犯法分子和流氓、阿飞、强奸犯、贪污犯等犯罪分子的区别认识模糊者不在少数*王影:《青岛市十六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在讨论邓小平同志报告中暴露出来的一些糊涂思想》(1957年10月26日),《内部参考》1957年10月28日。。
进入1958年,司法界陆续出现了劳动教养人员中并不都是敌我矛盾的呼声。还有人特别指出,对于劳动人民出身的无业人民,特别是受到勾引而堕落犯罪的青少年,应慎用“敌我矛盾”来分析或定性*黄汝坚、肖一华:《关于劳动教养人员的矛盾性质问题》,《法学》1958年第6期。。此后,政法的退场使得青年的教育问题重回团主导的历史情境中,而一度消失的阿飞内涵也随之呈现回归态势。
四、“阿飞”内涵的逐步泛化
从1959年开始,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此后又作出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决定。由于粮食供应紧张、物资紧缺,地下黑市和投机倒把活动开始增多。加之大量合同工、临时工、学徒工被精简出厂,不少工厂因原料短缺而停工,大量退职青年流向社会,成为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1961年10月,团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精神。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会议不失时机地将青少年中的道德风气问题提出来。根据各地团组织的调查,在1957年遭到沉重打击而一度消沉的青少年犯罪在1961年重新活跃起来。从1月到10月间,上海南市区青年犯罪案比1960年同期增加了93%。在黄浦、卢湾两个公安分局七八月份处理的65起相关案件中,参与者全部都是青年,其中大部分是刚刚开始活动的新手,青年工人、学徒占到23人。*《共青团上海市委关于在上海市青少年中集中地进行一次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请示报告》(1961年10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1-842-1;《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加强城市青少年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报告》(1962年5月3日)。根据这一调查结果,1961年底,团市委在全体青年中开展了新一轮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典型厂,彭浦机器厂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厂发现的问题青工主要活动包括深夜出去“盯梢”“吃豆腐”或以“偷窃”的方式获得资金,用请人溜冰、看戏、上馆子以及各种“下流手段”“勾引侮辱妇女”。团市委的干部在进行调查和分析时,又将这些人划分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流氓阿飞分子,即以吃喝玩乐为生活目的,经常成群结队出入公共场所,“勾引调戏妇女,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其中一些人进行投机贩卖、偷窃、扒窃、赌博活动以获取经费,有时因争风吃醋还聚众殴斗;第二类是有严重流氓阿飞习气的青工,表现为学流氓阿飞的样,盯女人的梢,跟着流氓阿飞分子搞投机贩卖、偷窃、赌博等;第三类是有流氓阿飞习气的青工,他们有一段时间跟阿飞出去,模仿阿飞的打扮,但自己单独活动少。*《抵制流氓阿飞行为对青年的腐蚀》,共青团上海市委:《团的工作》(1961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1672-84。
在对这些问题青工进行定性与处理的过程中,团干部沿用了反右派斗争后期使用的一套话语,即“流氓阿飞分子”,但这些流氓阿飞分子的“罪行”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困难时期伪造公章购买紧张商品、贩卖粮票、从事投机贩卖等活动的问题青年也被归为流氓阿飞分子,“流氓阿飞”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拓展。而与1957年一度将流氓阿飞定性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坏分子”有所不同,这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重返1954年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的轨迹,再次遵行“以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工厂通过邀请老工人做报告、推荐好书、举办讲座等方式,对这些流氓阿飞分子以及有流氓阿飞习气的青工进行思想教育。在运动推动的过程中,团市委反复强调基层团组织应执行耐心教育的方针,即使对那些情节严重必须法办或劳动教养的流氓阿飞也要作具体分析。*《共青团上海市委关于在上海市青少年中集中地进行一次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请示报告》(1961年10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1-842-1。
到了1962年,团市委主导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落下帷幕,但上海市公安局处理的流氓阿飞人数却仍然有增无减。伴随着问题青年活动形式的多样化,流氓阿飞的罪行也不断变化。根据黄浦公安分局治安科人员的反映,与1961年流氓阿飞的活动主要集中于“侮辱妇女方面”不同,新阿飞的活动范围进一步发展。除了贩卖、偷扒、暗娼外,有的还从事“从敌特电台中找关系”等反革命活动。黄浦公安分局从1月到7月共逮捕处理流氓阿飞147人,其中又以社会青年、青年工人为多。他们中有不少人已是“几出几进”,把进公安局视为“逛庙”。至于一般流氓阿飞习气,则更为普遍。*《共青团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流氓阿飞问题座谈会会议记录》(1962年10月1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1947-24。
这一时期的阿飞以溜冰场、文化馆、公园为主要空间活动。从1958年起,交谊舞活动被全面禁止,溜冰场开始受到青年的青睐。溜冰既被视为体育运动,实际上又有与舞会相似的性质。在快节奏的乐曲伴奏下,青年男女同样可以与异性肢体接触,“拉手揽腰”翩翩起舞。溜冰场也因之吸引了众多流氓阿飞流连其中,全市各大溜冰场也重新出现了“大包头”“小包头”“火箭鞋”“小裤脚管”等穿着“奇形怪状”的青年,这种情况在1962年春节前后达到高峰。据新成、新都、黄浦三个溜冰场统计,1961年全年在溜冰场发现的属于“勾搭妇女”“调戏”“乱搞男女关系”的事件有264起,而1962年一二月份就已经发现182起*上海市人委文教办公室卫生体育组:《新成等三所溜冰场制止流氓阿飞进行捣乱活动的情况和经验》(1963年4月3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3-2-221-12。。文化馆的情况也十分类似。黄浦文化馆因流氓阿飞聚集而被群众称为“皇宫”。公园则多作为阿飞活动的中间场所,天气热的时候集中“胡搞”。*《共青团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流氓阿飞问题座谈会会议记录》(1962年10月1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1947-24。
在1961年至1962年打击流氓阿飞的行动中,公安部门将其明显区别于“四类分子”,集中打击“少数阿飞骨干分子、盗窃分子”,而将“包头”“小裤脚管”视为“人民内部矛盾”,认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属于年幼无知、是非不分,只是追求“时髦”“漂亮”*上海市人委文教办公室卫生体育组:《新成等三所溜冰场制止流氓阿飞进行捣乱活动的情况和经验》(1963年4月3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3-2-221-12。。“三包一尖”的小阿飞内涵再次回归,并相对安全地生存了下来。与此前相比,作为各方打击对象的“流氓阿飞”的内涵实际上已经泛化。根据各个时期青年犯罪活动的特点,流氓阿飞呈现不同特征,也逐渐成为青年罪犯的代称。面对此时已“五毒俱全”的阿飞,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语境下,相关部门干部也开始用“阶级观点”来重新分析。正因如此,少数阿飞骨干分子、盗窃分子开始被贴上从事“反革命活动”的标签*《共青团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流氓阿飞问题座谈会会议记录》(1962年10月1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1947-24。。
1963年4月2日至4月15日,国家经济委员会召开工业交通企业开展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以下简称“五反”)运动座谈会。会议认为,各地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中均暴露出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工人阶级队伍的情况,有些职工“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好逸恶劳”,甚至进行流氓、阿飞等活动。会议认为,有的工厂已经形成了“新资本主义分子的集团”,还有的职工和反革命分子“勾结在一起”,或已“变为反革命分子”。4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该会议纪要,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五反”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2页。
在“五反”运动的推动下,上海出现了新一轮的意识形态整顿,但阿飞所呈现的内涵仍不完全严肃且一致。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要求各地应当依靠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对绝大多数四类分子要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4—37页。。在紧张的政治氛围下,公检法系统对阿飞的定性却鲜有介入。
1964年6月7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来信,披露了女顾客到上海高美服装店定制小裤脚管呢裤子遭到营业员拒绝,双方发生争执这一事件。“小裤脚管”再次被推向大众视野,其中不少人还目之为“新事物”,青年中又出现了追求时髦进而效仿的趋势。《解放日报》希望借此事引导读者开展广泛讨论,以引导广大读者认清“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危害性,在生活领域内进行一次“移风易俗”“兴无灭资”的自我教育。在讨论中,《解放日报》还专门安排读者讲述奇装异服的来历。上海耐火材料厂的一个职工称小裤脚管在旧上海早就出现过,“当时有些青年人受了美国黄色电影的腐蚀”,模仿电影中的流氓、阿飞,于是穿起了这种“怪式样”的服装。*《解放日报社关于奇装异服问题的讨论计划(草案)》(1964年6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73-1-543-39。新中国成立之初,曾以奇装异服为主要内涵的“小阿飞”又借助党报再度成为普通市民热议的焦点。与报纸所采取的“和风细雨”“具体分析”的立场相似,工厂团组织也同步对青工开展了温和的阶级教育。除了让喜欢梳大包头、穿花衬衫和小裤脚管的“落后青年”作为反面典型现身说法,老工人也再次发挥了样板作用。*《社会主义教育中怎么对新工人进行阶级教育的问题》(1964年1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2454-1。
1965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城乡社教运动由此发展为“四清”运动。7月,在团中央蹲点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上,上海方面反映了第一批单位“四清”运动的情况。报告指出,在青年工人中发现了不少“腐化堕落,严重败坏社会治安”的案例,流氓阿飞分子已经成为与团组织争夺青年的“主要对手”。据64个工厂的调查,共发现23件“流氓阿飞、腐化堕落”性质的案件,还有9件属于“现行反革命”性质。除以个人形式从事反革命活动的情况外,“四清”工作队还发现了以上海柴油机厂“KO集团”*所谓“KO集团”实际上是上海柴油机厂“四清”工作队和厂党委对该厂七名青工作出的政治定性。这七名青工平时一起吃喝玩乐,业余时间常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大谈“西方生活方式”“好莱坞电影”“女人”。他们并没有组建集团的意识,只是从动作片里知道了什么是“KO”(意为“打架斗殴”),觉得既洋气又好玩,于是就在各自的皮带上刻上英文字母“KO”作为共同的标记。他们在厕所张贴传单,上面写有“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我不能不为目前的半月工资只能买一双鞋子而感到羞耻”,还高呼“女人万岁”“美国生活方式万岁”,要求“立即开放舞会”。最终,该“集团”一名成员被作为“反革命分子”论处,另有三名成员被劳教。参见《从联司的产生发展和所作所为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二》,《东方红》1967年7月3日;《政治陷害者的卑劣伎俩》,《联司战报》1967年7月8日;陈先法:《民族泪》,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页。为代表的具有反革命性质的流氓阿飞集团。在分析上述情况后,团市委认为,青年工人中间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追求吃喝玩乐、穿着打扮的风气十分普遍,这些都为“反革命分子”在工厂活动并拉拢青工组成集团提供了条件。*《上海第一批单位“四清”运动中有关青年工作的几个问题——共青团上海市委在团中央蹲点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1965年7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1-1073-74。
在“四清”运动的形势下,工会、青年团、公检法、民政部门集体让位于政治运动,青工对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热衷和对于美国“洋”文化的追捧,受到严肃批判。阿飞在经历了“小阿飞”“流氓”“坏分子”等多重变异之后,又被打上了“反革命分子”的烙印。不过,政治高压之下,阿飞却并未就此消失。据团市委的观察,工作队一走,各厂流氓阿飞又卷土重来,侮辱妇女、猥亵幼女、偷看女工洗澡、乱搞男女关系的情况屡屡发生,还有些青年穿着尖头皮鞋、敞胸露臂的衣衫,以及“无法形容的三角裤”在厂里“蹿来蹿去”*《关于工业系统第一批“四清”运动已结束单位的当前情况和初步意见汇报(草稿)》(1965年8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1-1136-32。。阿飞以其顽强的生命力生存下来并延续至“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经过十七年层层累积的“阿飞”释义在浓缩的非常时期滚动重现。“三包一尖”在批判声中继续流行,“阿飞”与“流氓”一道重回坏分子的轨道,投机倒把成为阿飞的罪行之一,“流氓阿飞”随时有沦为“反革命分子”的可能。群众运动主导了阿飞的罪与罚,基层社会对“阿飞”的演绎也达到了顶峰。
五、结 语
本文以时间为线索再现了各个阶段的上海阿飞,目的并不在于呈现一副清晰的阿飞变化图,而是试图将那些妨碍叙述、常被剔除的“杂质”也展示出来。借用研究概念的历史变迁的相关学者的话,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不同释义产生后各方怎样理解它、怎样赋予它多重含混的意义,以及“在重重叠叠的言说实践中,又体现了怎样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和让人意想不到的历史内涵和政治后果”*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在整个十七年间,“阿飞”始终未见有明确的界定。相反,阿飞的罪与罚完全是依靠不同主体的多样描述与基层实践而实现的。谁来主导、谁来定性、谁来惩处、谁是罪犯等问题深刻地影响着阿飞在每一个阶段的走向。
在惩治阿飞的过程中,团市委的道德教育、民政部门的收容改造、公安部门的集中打击、法院的司法审判以及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等多股力量均介入其中。从1957年开始,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各界对阿飞的认知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日益猖獗的青少年犯罪使得政法系统频繁出现在党报党刊中,而原本仅为公安局等少数部门所使用的“流氓阿飞”这一表述也从机关文本中走出来,党报党刊反复使用却又不加以解释,使之成为固定搭配*正如Stubbs分析的那样,一旦媒体反复使用、传播某些词汇或固定搭配而又不予以说明,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渐渐习惯它们,尽管鲜有人能够清楚解释它们的内涵。参见Michael Stubbs. Text and Corpus Analysis: Computer-assisted Studie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p.194.。伴随着政法的退场与政治运动的暂熄,一度消失的“小阿飞”重回大众视野,阿飞的概念内涵逐渐走向泛化。各施力方或进场或退场,均以自己的立场对阿飞加以描述,而阿飞的多重内涵也被滚动地制造与呈现出来。
此外,“谁是罪犯”亦隐约影响着阿飞的界定与走向。相较于从一开始就被法办或被收容的社会阿飞,工厂阿飞处于相对隔绝与安全的“保险箱”中,普遍被视为“受害者”。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愈来愈多的问题青工对中共阶级路线的既有解释发起挑战,“如何解释这些劳动人民的堕落”成为新的问题。而伴随着“劳动人民”犯罪在两类矛盾之间的摇摆,工厂阿飞也在“受害者”与“害人者”的角色定位之间游走。
阿飞并不是任何一场政治运动的主要目标,却屡遭顺带解决。这使得无论是全国范围内还是上海地方,一旦面对青年问题,阿飞都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解释工具。阿飞的内涵由此得到层层累积,它既可以指代着“奇装异服”的青年以及有着流氓行径的问题青年,也可以指代工厂中的“闹事”青工和“五毒俱全”的青年犯。阿飞的内涵包罗万象,也因之总能成为运动目标。此外,阿飞的“罪行”总在变化,且能够和其他罪名任意组合。通过改变某个字眼或添加某个词语,它的罪与罚就可以随之改变。“小阿飞”“流氓阿飞”“阿飞分子”“流氓阿飞分子”等新称谓的出现实际上给了基层政权一个自主命名的权力空间,各方的博弈充斥其间,“阿飞”也因之成为一种伸缩性极强、适用性极广的污名。
中共中央高层、上海公安部门、团市委、普通市民、文艺界人士等均在不同时空中表达了自己对于阿飞的认知。在众声喧哗之下,各方对阿飞的解读客观上构成了复杂的“语料库”*有研究者曾提到20世纪50年代的灭雀运动实际上为政治高层提供了“话语库”(参见刘怡:《从“麻雀”到“害人鸟”:五十年代中后期灭雀运动的话语逻辑》,《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与麻雀不同的是,对于“阿飞”的定性和定罪始终是混沌与多歧的,而对“阿飞”话语的利用者也不仅仅限于高层。因此,笔者使用“语料库”以与之区别。。在这个语料库中,每一类关于阿飞的定性都在一个时期内真实存在并发挥效力,他们之间尽管存在一定分歧,却并没有消灭彼此的迹象。对于阿飞的批判和清理,一再将它拉回到普通市民的视野里,而阿飞文化也呈现越打击越流行的姿态。历史合力之下,“阿飞”不仅为党内高层提供了某些政治语料,更深入上海地方小情境,扎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极具象征意味的海派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