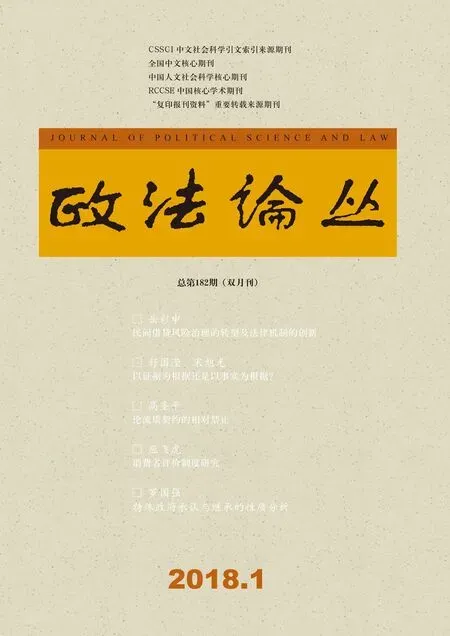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的性质分析*
2018-02-07罗国强
罗国强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产生的原因
通常情况下,以非宪法的方式进行政府更迭,不论是采取武装斗争(暴动、夺权、局部内战或全面内战等)还是其他斗争(罢工、游行、示威、集会等)的方式,都是在不长的一段时期内能够产生最终结果的。此时如果斗争失败,则不产生政府承认与继承的问题,业已做出的政府承认照旧;如果斗争成功,则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即给予新政府承认(通常是法律上的承认)、同时撤销对旧政府的承认,并使得新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全部继承旧政府所承受的权利和义务。
然而,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非宪法的方式所进行的政府更迭斗争都没有产生一个最终结果,甚至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此种斗争都无法尘埃落定;也就是说,此种斗争算不上是完全成功但也算不上是完全失败,可能基本成功但是留有尾巴,也可能基本失败但是留有余地,还可能在部分领土上取得了成功而在部分领土上没有成功,甚至可能与斗争对象势均力敌……那么,在上述情况下,政府承认与继承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了,而是具有特殊的属性,因为对同属一个国际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存在两个以上的争夺者,都主张自己应当享有同一国际法主体的主权及其代表权。
相比之下,国家承认与继承则并不存在特殊与否的问题,而仅存在承认与否的问题,因为不论是承认还是不承认,不论是法律上的承认还是事实上的承认,也不论是合并、分离、分立还是独立,权利义务不是由领土变更之后的一个国际法主体来整合,就是由数个国际法主体来分担,原则上并不存在两个以上政权争夺同一主权及其代表权的问题。①而出现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实现一般政府承认与继承所需要的有效统治,未能100%地得到实现。因为,只要以非宪法方式进行的政府更迭的斗争未能产生最终结果,不论是出现哪一种局面,也不论斗争各方的具体力量对比如何,但至少能够确定,没有任何一方对于本国领土实现了100%的有效统治。尽管我们说承认与否是一国政治决策,一国有权对处于政权更迭斗争中的各方选择承认或不承认,但其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法律原则和规则需要遵循。
交战团体或叛乱团体的存在是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产生的直接原因。实践中,存在长期开展以非宪法的方式推翻政府斗争可能的,一般是武力斗争的方式,而以武力的方式进行推翻政府斗争的组织形式,通常包括交战团体和叛乱团体两种。当然,这两种组织所寻求的目标,有的时候在于建立新国家而非新政府,此时就属于国家承认与继承问题,本文在此不加赘述。而当这两种组织所寻求的目标是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时,则属于本文所探讨的范畴。
(一)交战团体
交战团体是指属于国家内战斗争中的一方并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武装割据的政治军事团体。综合有关学者的论述,[1] P176笔者认为,构成交战团体的条件通常包括:(1)存在全国性的旨在颠覆现有国家或政府的武装冲突;(2)实际占领并有效管理国家领土实质上的一部分;(3)依据战争法通过有组织的武装采取行动;(4)他国有通过承认明确态度之必要。当然,其中最为本质与核心的要素,就是要确定内战的存在以及有关武装团体算得上是内战中的一方。比如,中国的解放战争就属于内战,国共两党各为内战之一方,而当时国内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武装,虽然实际上割据一方、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却无意颠覆国民政府,而只是在形式上统一的中央政府框架下分门别派争权夺利,故而不属于内战一方,不存在需要被承认为交战团体的问题。
由于国际法并不禁止叛乱与内战,故而原则上只要符合上述条件,旨在颠覆现有国家或政府的反叛者就可被视为内战中的交战方。对于条件不符合的反叛者给予承认是违反国际法的,而对于条件符合的反叛者拒绝给予承认,则由于国际法并不禁止国家这样做而不存在违反国际法的问题。在一国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其他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和尊重内战双方的合法权利,而承认内战中非政府一方为交战团体、保持中立的行为,不会影响发生内战的国家的国际法主体地位,而只影响该国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权的划分与归属。交战团体通过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在其所实际控制的区域内取得部分原属于本国中央政府的代表权并承担相应国际义务。②同时,交战团体作为战争法的主体,依据战争法行事的权利和义务也能够得到确认,这种战争法上的权利通常被称为“交战者权”。由于交战者权包含了超出一国政府在和平时期所行使职权的范畴(如实施国际封锁的权利),故而即便是原本就获得了法律上的承认的、作为合法政府一方,也可能在内战的情况下主张行使交战者权。
当然,在本质上,是内战的事实而非他国的承认导致了交战者权,因此承认与否对于此项权利本身是无损益的。有理由认为,交战者权是逐渐由叛乱者行使并获得外国承认而形成的,作为内战平等主体的叛乱者的权利源于法律运作而非他国的创造或认可,对交战团体的承认是对战争存在事实的确认,并不创造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权利或义务。[2]P333-350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尚不存在正式的对于交战团体的承认。到了182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裁决中指出,西班牙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内战赋予双方针对对方的所有战争权利。[3]而在美国内战(1861-1865年)中,围绕对英国承认南方“美利坚联盟国”及其政府的交战团体地位是否违背了其对“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政府的国际法律义务问题展开的讨论,关于交战团体的法律逐渐发展成熟,[4] P184对于交战团体的承认就作为一项正式的国际法内容被提出了。③
有学者指出,在某些例外的情况下,交战团体将不被承认,这些情况包括:(1)交战团体的构成要件未能完全实现;④(2)武装冲突未达到需要他国承认的程度;⑤(3)冲突具有国际性。⑥不难发现,这里的关键之处,还是在于考察是否构成内战以及是否属于内战中一方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对交战团体的承认属于事实上的承认,但是在交战团体转化为对全国实施有效统治的中央政权、他国撤销对此前政府法律上的承认而给予交战团体法律上的承认等特殊情况下(此种情况存在较大的干涉可能性),或者原中央政权因内战失利而降格为交战团体但是他国不愿意撤销对其法律上的承认的情况下,也可能给予交战团体法律上的承认。
(二)叛乱团体
叛乱团体是指从事了颠覆国家或者政府的武装斗争,但斗争规模尚未达到内战割据程度的政治军事团体。笔者认为,构成叛乱团体的条件通常包括:(1)存在旨在颠覆现有国家或政府的武装冲突;(2)实际占领国家领土实质上的一部分;(3)通过有组织的武装采取行动;(4)他国有通过承认以保护本国商务或侨民利益之必要。不难发现,上述构成条件是比照交战团体的构成条件来说的,基本上就是减损了交战团体构成条件的某些内容,尽管某些具体的叛乱团体实际上可能符合了交战团体构成条件的一项或者数项,但只要有一项条件没有符合,就不能够升格为交战团体。⑦而上述条件的关键,就是有武装斗争但是没有达到内战的程度。正是由于叛乱团体与现有国家或政府的武装斗争尚未达到内战的程度,对于叛乱团体的承认,在法律效果上远低于交战团体。承认本身并不使叛乱团体享有交战团体的任何权利,仅表示承认国对叛乱团体的武装斗争保持中立的立场,以达到保护承认国商务或侨民利益的目的。[5]P207-277一国拒绝承认叛乱者为交战团体,一般都是基于其不符合交战团体构成条件之一项或多项。比如,由于英国等诸多国家认为西班牙内战具有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内战的复杂性(即冲突具有国际性),故而佛朗哥叛军未被上述国家承认为交战团体,而仅被承认为叛乱团体。
交战团体的承认将产生特定的权利义务,而叛乱团体的承认则不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叛乱团体的承认,并不赋予其正式法律地位,而只能算作一种“事实上”的、出于有限目的的、不完全的对交战团体的承认;而且,他国通过承认赋予叛乱团体的法律权利义务本质上都是可撤销的,因为提出充分的理由去拒绝承认其为交战团体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他国有足够的依据去保持一种行动自由。加之前已述及,对交战团体的承认通常都是事实上的承认,那么这样一来,对叛乱团体的承认,就可谓“事实上的”事实上的承认,其法律效果相对弱了很多。也正是由于连作为通常情况下的事实上承认对象的交战团体的构成条件都达不到,故而他国对叛乱团体的承认,原则上不可能属于法律上的承认,即便他国对其抱着支持的态度,也应当至少在其达到构成交战团体的条件之后再来给予法律上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叛乱团体给予法律上的承认,是一种“轻率承认”,属于带有明显政治目的的干涉内政的行为。⑧
由于交战团体和叛乱团体的构成条件具有实质上的相通性,而仅在程度上不同,故而两者之间能够相互转化。在符合交战团体构成条件的情况下,叛乱团体可以转化为交战团体;而在交战团体不再符合交战团体的构成条件但尚能符合叛乱团体的构成条件的情况下,交战团体将转化为叛乱团体。但是,这种转化的依据必须是客观的,尤其是必须根据客观事实来判断是否已经构成内战,而不能由他国主观地予以裁量,否则就构成了“轻率承认”。
二、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的共性
作为政府承认与继承的类型之一,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具有跟一般政府承认与继承相同的共性。而这些共性,往往又是作为整个的政府承认与继承范畴,与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范畴相区别的特点所在。
(一)都属于政府承认与继承的范畴
较之一般的政府承认与继承,特殊政府的承认与继承总是容易与国家承认与继承相混淆。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予以明确,无论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政府承认与继承,都与国家承认与继承有所区别;尤其是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不应与国家承认与继承相混淆。
的确,长期的内战、割据或者分治状态,以及斗争各方有时可能还存在的既相互对立又在一定程度上合作的关系,容易给民众、尤其是受到蒙蔽的本国民众和不明真相的外国民众造成长期分治的各方早已各行其是、互不隶属,不再同属一国的错觉,由此似乎新旧政权之间的关系也就属于国家的承认与继承,而非政府的承认与继承问题。然而事实上,这只是基于政府承认与继承中的某种特殊性,才容易引起非法律专业人士的混淆。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仍然属于政府承认与继承,而与国家承认与继承无涉。无论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政府承认与继承,都是以颠覆原有政权为目标,而非以分裂国家、变更领土为目标,这种斗争即便时间较长、悬而未决,也不会自动改变其性质。长期割据或分治的状态,从法律性质上仍然属于内战的范畴,差别只是在于各方之间是否存在得到有效执行的停战协定,⑨如果有的话则内战属于法律上暂停或中止的范畴,如果没有的话则内战属于法律上未被中止、理论上随时能够继续开启的状态——只不过具体是否付诸实施取决于当事各方的意愿和态度。只有当斗争开始之前分裂已经形成(即便斗争各方均表明寻求或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图)、⑩斗争长期僵持且斗争双方均改变策略,决定各自建立国家的情况下,才能使得问题的本质发生变化,由政府承认与继承的问题变为国家承认与继承的问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与继承问题上,由于两岸长期分治、既对立又合作,容易给不明真相的台湾和国外民众造成两岸已经分裂的错觉,加上台独势力的歪曲和鼓吹,就越发呈现出将原本明确属于政府承认与继承范畴的台湾问题误导为国家承认与继承范畴的倾向,然而这是不符合基本事实和法律逻辑的。长期分治不过是内战未完结的产物,尽管新旧中国政府之间不存在任何停战协定,但出于顺应和平与发展潮流、团结中华民族并维护整个民族利益的需要,双方达成了不继续开启战端的某种起码程度的默契,并在明确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并未分裂、承认两岸政权性质对立的前提下,在政治经济等广泛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但容忍分治不等于容忍分裂,交流合作不等于确认内战的完结和分离的形成,无论如何,台湾问题本质上仍然属于政府承认与继承的范畴,导致台湾问题的中国内战则属于中国内政的范畴。
(二)都源于非宪法方式的夺取政权斗争
通过非宪法的方式颠覆现有政权,即革命或者叛乱,乃是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产生的源头。不论这种斗争最终是否完全取得胜利,其所导致的问题均属于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只不过视斗争胜利的程度而有一般与特殊的区别。因此,涉及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的新政府,都属于不符合旧有法律、尤其是宪法程序而上台的。这就使得政府承认与继承有别于政府沿袭和国家承认与继承。就政府沿袭来讲,不论新旧政府之间的政治对立多么明显、分歧多么巨大,但并不存在违宪的问题,新政府仍然是通过宪法所规定的方式夺取政权并上台的,这就不存在新政府的承认与继承问题,而只能被视为政权的合法沿袭与交接。
就国家承认与继承而言,虽然确实有部分情况属于违反既有宪法的产物,但也有很多情况不存在违反既有宪法的问题,尤其是在以和平的方式变更国家领土的情况下,往往反倒是在既有宪法的框架之下实现的;这是因为以和平的、协议的方式变更国家领土就意味着母国不反对,以宪法为代表的国家意志不仅未被违反,而且能够被母国做相应的修改以适应新的状况,而以单方面的、强迫的、武力的方式变更国家领土当然是受到母国反对,也是违反其以宪法为所代表的国家意志的。相比之下,只有政府承认与继承,无论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都必定涉及违反既有宪法的问题。
(三)都实现了起码程度的对国家领土的实际有效控制
一般的政府承认与继承以有效统治为条件,这就意味着对于国家领土100%的实际有效控制。但确实,在给定的时间范畴内,并不能保证新政府都能够实现这种100%的实际有效控制。在此,应当给定多长的时间没有确定的标准,也就是说要等待多久才能去对于实际有效控制的情况作出评估和判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上讲,这取决于国内夺权斗争或内战的进程,既有像苏俄政府这样2-3年间实现对俄国全境有效统治的情况,也有像新中国政府这样1949年至今尚未实现对中国全境有效统治的情况。但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只要作出某些情势属于政府承认与继承范畴的判断,就意味着有关主体至少实现了起码程度的对国家领土的实际有效控制。
一般意义上的新政府自不必说,实现了100%有效控制,即有效统治;交战团体也实际占领并有效管理国家领土实质上的一部分,而且由于构成交战团体要求其所涉斗争达到全国性内战的程度,故而其所实际有效控制的国家领土应当接近于全国范围的一半(内战在两方之间展开)或者大致不低于其他内战方(内战在多方之间展开),也就是说,其所实际有效控制的国家领土是具有相当范围的;叛乱团体的构成虽然不要求达到内战的程度,但该团体也实际占领国家领土实质上的一部分,其所实际有效控制的国家领土应当至少足以令其构成一种地方割据性的武装势力,否则其他国家也没有必要为了保护侨民和商务而与之建立某种联系,故而这种实际控制是一种起码的、足以撼动国内法律秩序、引发国际权利义务变更的,而不是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是微不足道的。
可见,不论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政府,还是作为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对象的交战团体和叛乱团体,都实现了起码程度的对于国家领土的实际有效控制,这种控制也是承认与继承问题得以产生的事实基础。
(四)承认对象都将享有或多或少的国际法律人格
所谓国际法律人格,是指某一实体在国际法上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资格。国际法律人格源于主权,其所包含的两大要素(独立而完整地参加国际关系的能力、直接享有国际权利并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是构成国际法主体资格的关键所在,[6]P86-87因此也是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所当然具有的。在政府承认与继承的语境下,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国家的国际法律人格理论上仍然是独立的、完整的和直接的,国家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的法律人格并不存在问题,国家本身的法律人格在国际层面上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但实际上这种资格行使权将可能在不同的国内政权之间转手,或者在内部斗争中被有关主体所瓜分,具体结果需视实际控制的程度而定,这就使得国家的法律人格虽然在国际层面上仍是完整的,但在国内的实际行使过程中却不得不被数个政权或主体所瓜分。
在新政府实现100%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国家所享有的国际法律人格将随着其对全国全部领土的实际控制,完全转移到新政府手中。而在新政府未能建立起100%有效控制或者国内政权斗争长期僵持的情况下,国家所享有的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际法律人格就必然面临在国内层面被割裂、被瓜分的命运;尽管他国或者国际组织可以选择仅承认其中一方为合法政权,然而在与他国或者国际组织的关系之外,其他的国际权利和义务仍然主要是依据对于国家领土的实际控制来判断和行使,而不可能仅仅依据他国和国际组织的态度就使得其他斗争各方所能够享有的国际权利和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归于消亡;由此可见,国内斗争各方均可在其控制领土的范围内行使一定的国际权利并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只不过程度因有关主体的情况而异。
一般意义上的新政府将完全继受国家的国际法律人格,全面行使有关国际权利并承担有关国际义务;交战团体将部分继受国家的国际法律人格,在其控制领土范围内一般性地行使相关国际权利并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叛乱团体将只能在得到国际认可的前提下、在其实际有效控制的领土范围内、事实上地行使某些特定的国际权利并承担相应国际义务,故而有学者指出,对叛乱团体的承认在国际法上并不是一项将具备坚实法律基础的国际权利赋予叛乱团体的行为,其不能产生更多或者更深度的一般性的法律权利。[7]P270-271
但在此,无论属于一般的还是特殊的政府承认与继承,有关主体都或多或少地享有一定程度的国际法律人格,能够行使一定的国际权利并承担相应国际义务,这一点是至少可以肯定的。
三、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的特性
作为政府承认与继承的一种特殊类型,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具有不同于一般政府承认与继承的特性。
(一)未能实现百分之百的有效控制
一般意义上的有效统治,通常都是100%的有效控制,尽管其实现需要一个过程,但基本上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从而造就了一般政府承认与继承的完全性。但在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上,有效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得到100%的实现,从而造就了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事实上的不完全性。不难发现,在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的语境下,有效统治所涵盖的因素(实际控制、稳定性和独立性)多数都存在程度减损的情况。
其一,在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中,未能形成100%的有效控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实际有效控制没有完全实现,从而形成了斗争各方对国家领土的不同组成部分享有实际控制,国家领土在法律上保持完整但在事实上被不同主体控制的局面。
其二,在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中,对于稳定性的要求是动态的和灵活的,但同时有一个最低值。尽管如前所述,对于稳定性的要求没有确定的国际标准,但显而易见,一个获得事实上承认的交战团体所需要满足的稳定性,低于一个获得法律上承认的新政府所需要满足的稳定性;而叛乱团体的稳定性则较之交战团体更差。尽管叛乱团体的稳定性存疑,但至少能够维系一定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对国家特定领土的实际有效控制,对于不能具备起码稳定性的、转瞬即逝的叛乱,国际社会并无给予事实上承认的必要。当然,如果叛乱团体的实际有效控制变得更加稳定,则能够发展成为交战团体。
其三,与前两项因素不同的是,在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中,对于独立性的要求不应减损。这是因为,独立与否本身是一个涉及质变的问题,只存在独立政权和傀儡政权,而不存在“半独立半傀儡”政权或者“部分独立”的政权。尽管一个政权可能会受到他国政府的资助、压力和影响,尤其是处于内战中的交战团体或者叛乱团体更是经常寻求境外势力的帮助和支持,也经常与境外势力进行各方面的合作,但关键问题的考量应当集中于一个方面,即对于大政方针的决策是独立自主还是受制于人、是自愿授权还是被迫让权、是仅仅借助外力还是纯粹就是境外势力的代理人。不论是新政府、交战团体还是叛乱团体,都应当具有独立性,否则就不符合有效统治原则的基本要求,不应被认为构成一个真正的政府或者政权,不存在给予任何程度的国际承认的问题。
而在符合独立性的前提下,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中的交战团体和叛乱团体在有效控制和稳定性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减损,从而导致有效控制未能百分之百的实现,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有效统治。
(二)不仅仅存在单一的法律上的承认
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之所以特殊,就是因为其不仅仅存在单一的法律上的承认,往往还既涉及法律上的承认又涉及事实上的承认,所以,并不能像一般政府承认与继承那样,给予新政府以法律上的承认同时撤销对旧政府的承认那么简单。
产生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最常见的情况,是一国及其政府业已获得国际社会上各国法律上的承认,而爆发了内战,此时他国可以选择继续维持对既有政府法律上的承认,同时给予内战中的另一方或数方(交战团体或者叛乱团体)事实上的承认;也可以选择撤销对旧政府法律上的承认而在法律上承认内战中的某一方为新政府,同时对于仍然实际控制领土一部分的旧政府给予事实上的承认(交战团体)。但不论作何选择,都将出现法律上的承认与事实上的承认并存的情况。
当然,如果他国就是坚持仅选择支持内战中的一方(不管是既有政府还是新兴政权)并给予其法律上的承认,同时甘愿不与内战中的其他各方有任何国际交往与瓜葛并拒绝给予其任何形式的承认,那么对该特定国家来说,则仍然仅存在单一的法律上的承认而并不存在多项承认并存的问题。但从宏观的角度上讲,对于涉及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的国家自身而言,则总是存在多种类型的承认并存的问题。因为上述主观倾向非常明显的特定国家通常仅占少数,多数国家都会根据事实情况和实际需要,而对内战采取更为客观的态度和立场,而同时给予内战各方某种程度的承认。
而在此,我们的研究主题是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故而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于涉及这一问题的国家自身,而不可能以特定他国的立场为主要视角,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上不仅仅存在单一的法律上的承认,通常还呈现出法律上的承认和事实上的承认并存的状态。只有当国家刚刚建立就陷入内战、他国尚未对其政府作出法律上的承认且对于内战各方没有政治倾向的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不存在法律上的承认的状态,但此时将存在数个事实上的承认,这也是其与一般政府承认与继承中仅存在单一的法律上的承认所不同之处。
(三)不承认原则专门针对法律上的承认适用
如前所述,不承认原则是国家依据国际条约对于新主权者承担了不予承认的国际义务。通常情况下,不承认原则既能够针对法律上的承认适用,也能够针对事实上的承认适用,甚至能够针对一切类型的承认适用。究竟针对何种适用,取决于国际条约的具体规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并不专门针对某一类型的承认适用。
如果国际条约没有特别指明的话,不承认原则通常仅适用于正式承认,即法律上的承认。也就是说,承担条约义务的国家,对于新主权者(新国家或者新政府),只需确保不给予法律上的正式承认,就算是履行了条约义务;在此基础上,如果基于事实上的便利和需要,而给予新主权者一定程度的事实上的承认,并不存在违反不承认原则的问题。但若国际条约予以明确的表示,那么不承认原则的适用范围既可以涵盖法律上的承认,又可以涵盖事实上的承认,还可以涵盖一切类型的承认。当然,不承认原则涵盖一切类型的承认的情况,通常是基于被承认的新主权者存在违反合法性原则的问题,否则,多边性国际条约以及国际组织并不会去干涉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给予新主权者以国际承认的问题,而是留待各国自由裁量和协商决定。因此,在一般政府承认与继承以及国家承认与继承问题上,不承认原则尽管多数适用于法律上的承认,但其并非专门针对这一种承认类型适用。
相比之下,在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中,不承认原则的适用是专门针对法律上的承认的,而其对于事实上承认的适用则通常被忽略。这首先是因为,在一般的政府承认与继承中,被承认的主体最终只有一个,不存在在数个主体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而仅仅存在决定是否承认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承认的问题,这些都是可以由他国自由裁量的范畴;如果要订立双边或者多边条约来规范不承认问题的话,那么凡属这个自由裁量范围内的因素(是否承认、是给予法律上的承认还是事实上的承认)都能够经由国家合意作出规范;更为关键的是,对于被承认主体来讲,是直接获得法律上的承认还是暂时先获得事实上的承认,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因为在此不存在与之相竞争的主张代表本国的其他政权主体。
而在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中,被承认的主体有数个(两个或以上),法律上的承认只能有一个,而各主体之间争夺的焦点也恰恰集中在法律上的承认之上,因此,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在数个主体之间做出选择,决定给予何方主体法律上的承认。当然,这本质上仍然属于他国自由裁量的范畴,但在此,因为这种选择的存在,故而如果要订立双边或者多边国际条约来规范不承认问题的话,那么不论是国内斗争各方还是国际缔约各国,其所关心的都必然是法律上的承认给予何者的问题;各国内斗争主体最需要的也都是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并令他国对自己承担不给予其他国内斗争各方法律上承认的义务,因此不论他国如何自由裁量,都必须在不同主体之间做出法律上的承认给谁不给谁的选择。基于此,不论是双边还是多边国际条约,如果要在这种情况下规范不承认问题的话,那么其只会关注法律上的承认的问题。因为对于法律上承认的争夺,才是对国内斗争各方至关重要的,才是他国政府需要做出明确选择的,才是订立有关国际条约、明确不承认原则的主要目的所在。可见,基于数个国内斗争主体的竞争状态,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中的不承认原则必然要专门针对法律上的承认问题来适用。
在新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缔结的关于正式建交的双边条约中,不给予旧中国政府(台湾当局)法律上的承认乃是其核心内容所在。1972年《中国和英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规定,联合王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规定,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在此,“唯一合法政府”的说法,恰恰是与法律上的承认性质相吻合的。这说明,通过此类具有双边条约性质的建交公报或联合公报,有关国家之间建立的是一种正式外交关系,他国给予新中国政府的是法律上的承认,而对新政府作出承认就意味着对旧政府承认的撤销,且他国依据有关双边条约,承担了不给予旧政府法律上承认的国际义务,这就是上述双边条约得以订立的主旨之一。但上述双边条约在明确关注和规范法律上的不承认问题的同时,或者没有提及、或者明确允许事实上的承认存在,这就意味着条约中规定的不承认原则并不适用于此,建交条约的订立并不妨碍他国基于种种现实需要,给予旧中国政府(台湾当局)事实上的承认。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提出要保持“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意即在法律上承认所涵盖的正式关系之外,会维持事实上承认所涵盖的非正式关系;中英联合公报仅仅说要“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而对是否维持非官方关系语焉不详,但这也意味着,其在撤销与法律上承认相对应的官方代表机构之后,若再行派驻与事实上承认相对应的非官方代表机构,并不存在违反双边条约的问题。可见不论这些双边条约采用何种说法,都将是否给予事实上承认的问题留给了当事国自己来裁量,其做与不做均可。这也充分说明,这些国家对新中国政府所承担的不承认义务是专门针对法律上的承认来适用的。
(四)全面继承原则出现例外
前已述及,全面继承原则是政府继承的一般原则。一般情况下,新政府的建立意味着旧政府的不存在或失去原有地位,故而政府继承属于全面继承,国家的所有权利义务均转属新政府。当然,在此前提下,新政府还可以适用自由裁量原则,选择不予继承或者部分继承,从而导致非全面继承的结果,但这只是基于新政府的主观意志及其选择,不存在全面继承原则受到损益的问题。
但在新政府未实现100%的有效统治的特殊情况下,是否全面继承则不再是新政府主观意志能够决定的,而是在客观层面上无法完全实现的。尽管国内斗争各方在各自的主观立场之上,都可以主张全面继承旧政府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上的权利义务,但在客观事实之上,在做出判断的时间节点,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实现100%的有效统治,各方均实际控制了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并实施了稳定程度不同的管理;随附于特定国家领土的相关权利义务,也只有由实际控制该领土主体来行使,从而形成了多个主体实际上分别行使随附于一国领土的权利义务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并不会基于某一斗争方的全面继承声明或者他国政府基于自由裁量权而给予某一方法律上承认,就会自动发生改变。能够改变这种局面的只有客观的继续斗争进程以及斗争的最终结果,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上述改变局面的因素都可以被预见不会出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全面继承原则就出现了例外。
很多学者认为,只有国家继承存在完全继承与不完全继承之区分,而政府继承则没有完全继承与不完全继承之区分。但笔者认为,这种主张只是针对一般情况或者新政府的主观立场而言的,其没有考虑到政府承认与继承中的某些客观现实与特殊情况。
王铁崖在《光华寮案的国际法分析》中指出,国家继承有完全继承和不完全继承,即全部继承和部分继承之分;政府继承则截然不同,政府变动不影响国家的同一性,一个国家始终只有一个政府,因此,政府继承只有完全或全部继承,而没有不完全或部分继承;在政府继承的场合提出“不完全继承”的概念是错误的,这个概念抹煞了国家继承和政府继承之间的区别,把它们混为一谈,它意味着政府变动后可以有两个代表国家的政府,从而产生不完全继承的结果。[8]P403但正如王铁崖本人在其文章开头就明确表示的,光华寮案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意味着上述主张的价值主要在于支持新中国政府的政治立场并为其服务,而并不在于法理上的逻辑思辨;如果对该案采取更为中立的立场和更为纯粹的法律逻辑,那么即便案件最终结果是一样的,其中的分析和思辨都会复杂得多,而不会对政府继承的类型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9]P1
《奥本海国际法》论述道,政府继承尽管严格上讲不是国家继承问题,但只要发生政府更迭,不论是按正常的宪法方式还是一次政变或革命成功的结果,那么一般公认,在所有影响国家的国际权利和义务的事务方面,新政权都将取代旧政权。这段论述通常被认为主张政府继承仅存在全面继承的理由之一。笔者认为,对于该书的论述,值得注意的细节还有:第一,该书仅在论及国家继承问题的时候表示,有时区分全面继承与部分继承是有益的,而并未提及政府继承与这种分类有何关联;第二,该书并未设置专门的小节来讨论政府继承问题,其中第八版几乎完全没有讨论政府继承问题(仅仅提及叛变被镇压后的继承),[10]P128其纳入国家继承一节中作为一目来简要讨论;第三,该书在论述新政权全面取代旧政权的前提之时,仅仅提及政权实现了完全更迭的情况,即宪法性的更迭、政变或革命的成功。[11]P235由此可见,《奥本海国际法》作为国际法教科书而非国际法上承认与继承问题的专著,并不打算专门探讨政府继承问题,也不关注政府继承是否存在特殊情况,而只是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待这一问题,并出于讨论的便利,将其作为国家继承问题中的关于全面继承的那部分原理足以覆盖的、无须赘述的一个简略问题,从而一笔带过。因此,不能由于《奥本海国际法》无意于讨论政府继承中的特殊情况,就得出不存在这种特殊情况的结论;也不能因为该书仅提及政权实现了完全更迭的三种情况,就认为政府继承仅涉及这三种政权更迭情况;更不能基于该书未在专门论及政府继承之时提及全面继承与部分继承的分类,就断定作者意欲否认在政府继承中存在这种分类。
不难发现,国家继承之所以分为全面继承与部分继承,乃是因为其是由于领土变更的事实而引起。在领土变更的类型中,除了合并之外,无论是分离、分立还是独立,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法主体,原有国家的权利义务都需要被分割为数个部分,并由相应的新国家继承。因而可以说,在国家继承中,部分继承是对应于分离、分立和独立的结果,全面继承则是对应于合并的结果,国家继承中既存在完全继承又存在不完全继承,是一种常态。相比之下,政府继承则是由于革命或政变而导致政权更迭而引起的,其参加者是同一个国际法主体继续存在情况下的新政权和旧政权,国家的权利义务不会因内部斗争而发生实质改变,且在一般情况下将全部转归新政府,因而可以说,在政府继承中仅仅存在全面继承,也是一种常态。因此笔者认为,上述论断如果仅从常态上来看,并不存在问题;但问题在于,政府承认与继承是存在特殊情况的,此时若还一昧认为政府继承只存在全面继承,则就不符合基本的客观事实,也将导致法律逻辑出现某种漏洞;只有承认政府继承存在特殊情况、全面继承原则存在例外,才能真正符合客观现实,填补可能的法律漏洞。
此外,尽管“全面继承”与“部分继承”在英文表述基本上是一致的——Universal succession & Partial succession,但是在中文表述上,不同的学者也是各持己见。对于前者,有的主张使用“完全继承”、“全部继承”的说法;对于后者,有的主张使用“不完全继承”[12]P1-2、“未完成继承”[13]P144等说法。笔者认为,原则上这些表述都是可行的,但也存在一些细节上的差异。“完全继承”更加倾向于表示新政府的继承囊括所有的权利义务内容,但实际上新政府可能会主动放弃继承某些权利义务内容,从而导致政府继承在事实上并不是完全的;而如果“完全继承”的说法存在某些漏洞的话,那么作为其对立面的“不完全继承”也就难以成为最佳选择,更何况有学者指出“不完全继承”有混淆“国家继承”与“政府继承”概念之嫌——因为“完全继承”与“不完全继承”原本属于国家继承中的类型,[8] P403尽管这样论证的出发点可能是基于主张政府继承中不存在“不完全继承”,但确实,国家继承和政府继承中的“完全”或“不完全”并不是一个意思,有加以区分的必要。“未完成继承”更加倾向于以一种“进行时”的视角来考察政府继承的状态,是对“不完全继承”说法的一种改进;但以“完成”与否的状态作为界定的标杆,难免容易造成某种印象,即真正意义上的政府继承就只有“完成的继承”,而这种“未完成的继承”算不上真正的政府继承,不是一种单独的政府继承类型,而只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继承的过渡状态;同时,尽管此种说法也承认有关的继承有可能完成,也有可能不能完成,但其对于“完成”的关注,至少从字面意义上讲,具有某种此项继承目前虽未完成、但是其最终目标和走向应当是完成继承的主观倾向。而众所周知,实际上此项继承的最终走势取决于国内政权斗争和国际政治博弈的最终结果,具有不可预测性。相比之下,“全面继承”与“部分继承”的表述更为客观和中性,前者主要表示政府继承所能够涵盖的范围是全部的国家权利义务,但是政府是否真的继承所有的权利义务内容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必一概而论;后者主要表示,在作出判断的特定时间段,存在权利义务的部分继承,而对于之后继承是否应该走向完成、是否有可能完成,则没有任何主观倾向的表露。因此,笔者认为采用“全面继承”的说法作为政府继承的一般原则,采用“部分继承”的说法作为该原则的例外情况,是比较合理的。
注释:
① 比如,2008年科索沃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迄今为止获得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08个国家的承认,但中国、俄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拒绝承认。对于承认的国家而言,就存在两个国际法主体(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来分担原有权利义务;对于不承认的国家而言,则仍旧是一个国际法主体(塞尔维亚)在承担原有权利义务。两种情况下都不会产生两个以上政权均主张代表同一个国家并承担同属一国的权利义务的问题。
② 承认国将承认交战团体在其控制领土上的权力,不将其行为视为个人行为并与其保持一定关系;交战团体将适用战争法,并对其所控制区域内发生的国际不法行为负责。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③ 与之相吻合的,就是有学者指出,在1865年之前,并不存在“对交战团体的承认”这一术语。See W. L. Walker, Recognition of Belligerency and Grant of Belligerent Rights, Transactions of the Grotius Society, 1937, pp.178-179.
④ 比如,叛乱者虽然强大、武装斗争虽然持久,但未能建立具有某种稳定性的政府机构。
⑤ 例如1831年的波兰暴动和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
⑥ 比如有学者认为,西班牙内战虽然主要呈现出内战的特征,但却具有国际斗争的特点和表现,故而不应承认叛军的交战团体地位。See Hersch Lauterpacht,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7, p.184.
⑦ 比如叛乱团体所涉武装冲突已经达到全国范围,其不仅实施了实际占领还实施了有效管理,他国不仅也有通过承认保护本国商务或侨民利益的需要还有明确态度之必要,但若叛乱团体不遵守战争法,则不符合被承认为交战团体的条件。
⑧ 比如,在2011年利比亚反卡扎菲政府示威中,各反对派于2月27日在班加西成立的“全国过渡委员会”。而在十天之后的3月10日,法国就匆匆承认该政权为“代表利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机构”并与之互换大使(法律上的承认)。到了3月19日,法国战机就开始对卡扎菲的利比亚政府军实施空袭。尽管安理会于3月17日通过了1973号决议,授权会员国在利比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强制执行禁飞”,也就意味着授权使用武力;但法国的空袭一开始就超出“执行禁飞”的范畴,实际上就是在对卡扎菲武装实施空中打击以帮助全国过渡委员会夺取利比亚政权,属于滥用安理会决议的、违反国际法的干涉行为。当然,由于此项干涉获得了成功,故而在其帮助下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利比亚新政府“全国过渡委员会”不会对此表示异议,也不会主张追究此项干涉的法律责任。
⑨ 很多停战协定都难以得到有效执行。比如,2014年2月以来,乌克兰东部民众组建民间武装,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寻求脱离乌克兰;2014年9月,各方在明斯克达成停火协议,但协议并未被真正执行;2015年2月,法德俄乌四国领导人达成新的明斯克协议,要求冲突双方全面停火,但到了6月,激烈冲突再度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爆发。又如,2016年12月29日,经由俄罗斯和土耳其斡旋,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达成停战协定,俄土两国作为停火担保方,但该停战协定在达成2个小时后就被打破;而此前无论是由联合国、美国还是俄罗斯调停的叙利亚武装冲突各方停战协定,都很快破裂。
⑩ 例如,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苏美两国军队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进驻朝鲜北半部和南半部,从此朝鲜半岛就处于分裂状态。1948年8月15日,朝鲜半岛南半部宣布成立大韩民国(南朝鲜);1948年9月9日,朝鲜半岛北半部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尽管两个政权均宣称致力于朝鲜半岛的统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其建立之前,分裂局面已经造成。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一场为了实现统一而使用武力的国际斗争,而非为了推翻既存政府从而使得本方政权上台执政的内战。由此,不论对哪一方而言,其所面临的承认与继承问题,都属于国家承认与继承的问题。
[1] Hersch Lauterpacht,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7.
[2] Ti-Chiang Che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Recognition, London: Stevens & Sons, Ltd., 1951.
[3] The Santissima Trinidad, 20 U.S. 283 (1822).
[4] Hersch Lauterpacht,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7.
[5] Hersch Lauterpacht,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7.
[6] 王虎华.国际公法[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7] Hersch Lauterpacht,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7.
[8] 王铁崖.王铁崖文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9] 罗国强.特殊政府继承中的时际法律冲突及其处理原则——以新视角重读“光华寮案”和联大2758号决议[J].太平洋学报,2017,3.
[10] [英]劳特派特.奥本海国际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1]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9th edition, Vol. I, p.209.
[12] 王晓波.中国的和平统一一定要实现——有关“一个中国”和“一国两制”的若干问题[J].海峡评论.1999,2.
[13] 郑海麟.海峡两岸关系的深层透视[M].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