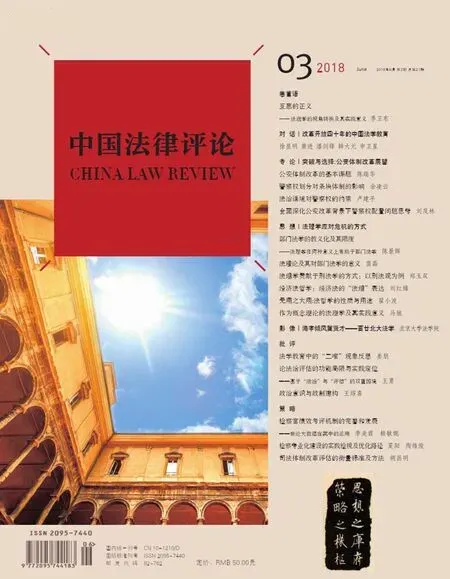法学教育中的“二唯”现象反思
2018-02-06姜朋
姜 朋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国的法学教育需要警惕“唯洋”与“唯书”(即“二唯”)思维的影响。
一、唯洋
曾有我国台湾地区来的法学家建议:“如果比较德国和美国类似的案子,把他们的判决搜集过来,整理出来,翻译成中文,[大陆]法院遇到同类案例的时候,马上就会改变判决的内容和判决的方法。”1《专家就东亚私法统一达成共识,中国法难独善其身》,载《法制日报》2009年10月20日。这段话提供了一个极致的法制“唯洋”论的样本。为讨论方便,上述高论可简化为:“将德国和美国的类似判决译成中文,中国大陆的法院就会据以裁断同类的案件。”
(一)逻辑解析
对照图尔明模型,2图尔明模型是英国哲学家图尔明(Stephen Toulmin)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其认为一个好论证包括数据(Data)或根据(Ground),即论证的事实证据、理由,亦即三段论中的小前提;断言(Claim),即结论;保证(Warrant),即三段论中的大前提或隐含假设;支撑(Backing),即用以支持保证的陈述、理由;辩驳(Rebuttal),系对反例或反驳的说明;限定(Qualifier),系对保证、结论的范围和前提的限定性修饰词。相关内容参见[加]董毓:《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走向新的认知和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121页。可知此高论的“保证”(大前提)、“根据”(小前提)、“支撑”、“限定”和“断言”分别如下:
(暗含的)保证:(1)不同国家都会出现类似的案例,(2)类似的案例(无论发生在哪)都应当受到类似或相同的处理。
根据:中国存在近似案例。
支撑:德国或美国法院的判决具有普遍适用性;可以作为他国的判决标准或依据。
限定:因该言论系在私法研讨会上进行的,仅针对私法而言,故其所说成案应仅指民事案件。
断言:中国大陆的法院应当在同类案件上以德国或美国法院的类似判决作为判断依据。
此间的第二项保证(大前提)显然与法律的国别属性和司法的主权特征有违,从而不真实。外国判例何以在中国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国法院的判决何以一定要改?其存在的“错误”或问题在哪?照搬异域成案的做法是否就一定能够克服之?况且,中国内地的法院素来缺乏单纯依靠先例(无需成文立法)而遽行断案的传统,中国的立法也已自成体系,远非白纸一张。故面对现实的纠纷时,法院何以能够且应当抛开既有立法及自己积累的司法经验,而攀附异域先例?对于这几点,高论者实在需要再做补充论证才行。
若另用三段论推理来分析之,可以看出该高论中其实嵌套着两个三段论推理,其判断逻辑如下:
推理Ⅰ:
大前提:(按其法律)德国/美国的有A行为的人应受到B类的对待
小前提:德国/美国的甲有A行为
推论:德国/美国的甲应受到B类的对待
推理Ⅱ:
大前提:德国/美国有A行为的人应受到B类对待
小前提:中国的乙有A行为
推论:中国的乙应受到B类对待
显然,如果不添加其他条件(如中国与美国或德国有相同的法律),第二个推理是无法推出相关结论来的。除了逻辑问题外,现实也为上述高论提供了绝好的反驳。
2010年1月29日,丰田汽车公司宣布,由于踏板问题在中国召回一汽丰田2009年3月19日至2010年1月25日生产的75552辆多功能越野车RAV4。此前,丰田公司已在美国对相关型号汽车提供“上门召回”服务,并对驾车返厂召回的消费者补贴交通费用,汽车修理期间提供同型号车辆供其使用。而在中国,车主只能自驾至4S店完成维修,还可能因零件缺货而多次往返。至于赔偿相关费用,更是无从谈起。3谢鹏、金笛:《浙江工商局为何单挑丰田》,载《南方周末》2010年3月25日。类似地,还有2000年的东芝笔记本事件,参见黄晓艳、王健椿:《交锋:东芝索赔案始末》,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此案的症结并不在于中国法院不知美国同行的相关判决,而在于立法层面的缺陷。2004年国家质检总局、发改委、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并未提及因召回导致的赔偿问题,这实质阻碍了中国的消费者对丰田公司提起诉讼。
由此反观前述高论,可以看出言者对美、德两国法律制度的高度推崇,也可以窥测出其认知上的偏狭与方法上的谬误,更有与中国内地司法实践的隔膜。
(二)细节追问
退一步讲,假设两国成案揭示的问题及提供的处理方法确实具有普适意义,值得国内审判机关学习,也不能推出后者可以径直拿来就用的结论。国际公约、双边条约尚且需要经由国内立法程序加以转化,更何况外国法院判例!除此而外,还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讨论,比如:
1. 如何选择(由谁、按什么标准)两国案例?何美欢教授曾提及到英国学习、引进美国证券法的一些细节,值得玩味:
如果某人希望很快地找到一套好的内幕交易法规,他可以从加拿大安大略省、英国、欧洲找到。乍一看,这些法规的合理性、协调性及全面性会让他相信这些法规比美国一团糟的判例更好。但是,如果他对这些法规的阐释有疑问,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他很快就会发现这些法规的背后是真空。在英国,内幕交易法规在几乎没有公众或专业讨论下就通过了,法规好像是从石头里爆出来的一样。如此复杂的法规可以这样产生,完全是因为英国和欧洲法域只是将美国的一堆判例法编辑起来,他们的产品好像第三世界的来料加工产品……英国等国家捕捉了在某一发展阶段的美国判例法,将它编织起来成为一幅漂亮的制定法。在那一刻,英国的产品可能比美国的好。但是,英国的产品好像是被割下来的花;在它最漂亮的一刻它已经死去。美国产品却是那棵树,花被割后,树还可以继续生长。4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153页。
虽然这里何教授强调的是直接阅读美国证券法判例的重要性,但也含蓄地批评了那种将别国判例径直成文化的做法。前述直接引入他国判例参照判决的高论与之并不相同,但除却移植后采取的具体形式上的差异外,法律移植所表现出的如同采割树上花朵般地“捕捉”他国某一发展阶段的法律,以及因而形成的法制的真空状态,却都是相通的。为了能够全面遴选他国判例,避免“真空化”,势必最好能全盘拿来。但英美语言相通,其奉行拿来主义自然少了一层阻隔,而要大举英译汉、德译中,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
此外,德、美两国都是联邦制国家,有联邦与州的区分。以美国为例,其有联邦和州两套司法系统,各司其职。比如在允许同性婚姻问题上,各州的立法不尽相同,各州法院的裁决也就不一而足。5又如,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美国亚利桑那州与联邦政府就出现分歧。2010年7月,美国司法部向位于亚利桑那州首府菲斯尼克的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州通过的严厉的新移民法违反了美国宪法。亚利桑那州州长于2011年2月提起反诉,指责联邦政府没能保证本州安全,却阻碍移民法的实施。张旸:《就非法移民问题——亚利桑那州与美联邦政府继续过招》,载《人民日报》2011年2月16日。选译成案时,是仅盯住联邦法院系统的判决,还是也兼及州法院系统的成案,抑或将联邦与州法院的成案“一网打尽”?很明显,后者的工作量势必惊人。
2. 更何况,判例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译介完成之后,若该判例又有变易,如被新的判例推翻,又该如何?这实际是所有选择继受别国法律的国家都需要直面的问题。是选择“盯(叮)住”立场,亦步亦趋,还是适时另起炉灶,着实是一种考验。更要紧的是,一国的立法如何让自己成为一棵充满活力的参天大树,而不是一朵枯萎凋零的落花(甚或只是一片虚妄的花影),恰是前述高论者未曾赐教的。
3. 言者力推德、美两国。然而,以世界之大,何以只遴选这两个国家的判例?鲁迅先生固然赞成“拿来主义”的态度,但也清醒地指出:“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6鲁迅:《给颜黎民的信》,载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一室编:《六年制小学课本(试用本)·语文》(第11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因此即使要“拿来”也并非必须“咬定青山不放松”,只取一家。读书如此,立法亦然。
况且,若仅将目标锁定为这两国,而两国判例却不一致时,又该如何取舍?一个例子是,阿司匹林在美国已然是药品乙酰水杨酸的通用名称,而在德国(乃至欧盟)则仍是拜耳公司的一款注册商标。郑成思教授更提到,各国在认定驰名商标时多会偏重本国利益。例如:法国法院从1974年至1991年通过判决认定了11个驰名商标,其中多数是法国商标;德国法院(及其行政主管机关)也曾将日本“三菱”商标判为与德国“奔驰”图形近似,将日本“田边制药”判为与德国“拜尔制药”文字排列近似。7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显然,在前述高论中,原本复杂的问题被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了。
(三)法学教育的疑惑
方流芳教授指出:
法律“倾销”是一种危害极大的法律殖民主义,它在当地摧毁了法律知识生产所必须的法律语言系统,虚构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法律同源性(homology)——法系,植入一种霸权主义的法律审美观——“接轨”。8方流芳教授的微博,2015年1月10日8时19分发布。
从法学教育的角度看,实行前述高论,除了要译介德美法院成案(不光是判决主文,还包括案件的事实细节、各方观点等),还需要法官具备识别异域判例与本国类似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上的)共通性的能力。然而,如何美欢教授所说,“凭借读一本关于自行车的书,听关于自行车的讲课,都不能学会骑自行车,骑自行车的技能不能通过传递口头或书面文字学习”。9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中国的法官自然不能当然地通过阅读外国判例就自动学会并运用于中国的司法实际。这就会倒逼中国内地的法学院提供相关的教育服务,使学生能够深入领会彼国的各种成案与判例,并能娴熟地提炼其中的法律精义,继而有意识地将其贯彻于、并彻底改造本国的法律实践。问题是,一味讲求异域先例的法学院,其培养的学生能否在就业市场上竞争过来自德、美法学院的同侪?若否,则在本国读法律势必不如留德、留美。如此一来,本国法学院存在的合理性安在?何美欢教授曾提到,“法国律师业已被‘掏空了’,这是由美国法律人攻破了法国的教育体系造成的”。10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显然,上述高论足以同时消解中国的既有立法、司法及法学教育存在的合理性,而将立法权、司法权和教育权统统拱手让人,其法律“殖民地化”的立意深远而昭彰,不可不察。
二、唯书
除了“唯洋”,还有“唯书”。试举一例。有经济学家跨界讨论法律问题,提到了“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
该理论的直接结论是,一个好的司法体系只要有法庭执法就足够了,寻找其他执法方式没有意义。前提是法律要把什么是犯法定义清楚,把对犯法者的惩罚设计为最优。在这种最优的法律下,假定所有人都是理性的,都懂得最优法律的惩罚,都会推理,所有的人在可能犯法前要计算,比较犯法所得的预期的好处和可能的坏处。最优法律制定得有最优的阻吓力,使犯法对所有人都是坏处大于好处,结果这个社会中人们就不犯法。只要制定的法律是最优的,法律是由独立的法庭执行的,就不存在其他更好的方式。也就是说,执法体制同执法的效率不相关。但是在现实中在最有法制传统的国家也存在着与法院并行的其他执法形式,如政府监管。为了认识它们,我们要寻找那些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的基本条件在现实中被违反了,这就是基准的力量。11许成钢:《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1期),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这是过度迷信“理论(假说)”的例子。其中,除了“所有人都是理性的”预设,认知误区还有一些。
误区之一,“制定的法律是最优的”。事实上,完备(最优)法律的存在,只能是一种理想。无论古今中外,都不存在绝对完备的法律。任何立法者都无法充分认知未来,其制定的法律注定只能因应有限的条件。一旦外部的环境发生变化,法律的改变也就成为必需。更何况,一个社会的法律渊源不只立法一端。如何美欢教授曾指出的,“我们生活中受制的大部分法律(广义),不是由国会、法院、行政机构等官方组织制造的,而是由‘坐在他们办公室的律师们,在尽力执行其客户意见时制造出来的’”。12David F. Cavers,"Legal Education and Lawyer-made Law", W. VA.L REV. ,Vol.54(1952),pp.177,179.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5页。在私人可以充任“立法者”的情况下,指望凭借充分“理性”,制定完备法律更是痴人说梦。因此,基于“存在完备(最优)的法律”这种迷信观点进行推理,论者如若自信,实乃自欺;若其不信却以之授人,则是欺人。至于听者误信,必在现实中处处碰壁。
误区之二,“一个好的司法体系只要有法庭执法就足够了”。法律体系不只有司法一个环节。司法体系也不可能只包括法院,执法自然也不只是法院的事。其他执法方式与机构也有其存在的意义。比如,为了惩处闯红灯、超速、乱停车等违反交通法规的人,就得依靠警察,法官是无法冲在第一线的。13假使立法已很清晰并合理,但仍有人违反之,而法院则基于“民不举官不究”的原则无法主动介入。比如,我国法律对最低婚龄已有明确规定,但仍有视而不见者。2016年2月,广西南宁市马山县一对16岁新郎新娘的婚礼成为网络焦点。罗婷、张帆、王昱倩:《大山里的早婚少年》,载《新京报》2016年3月1日。而立法机关的注意力却集中在是否降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起点。王姝:《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民法总则草案:委员关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下限10周岁改为6周岁,以及农村经济组织的法人类型》,载《新京报》2016年6月29日。又如,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特色是在司法救济之外,另由行政执法部门提供相关的救济。14陈郁:《行政执法“给力”知识产权保护》,载《经济日报》2014年4月14日。就效果而言,其实挺好。15参见《狠抓落实,严厉打击侵权假冒——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工作汇报会发言摘编》,载《人民日报》2011年5月6日。
误区之三,上述论者强调,当现实与理论模型不一致时,要去找寻现实的毛病(违反了哪些该模型的基本条件),而不去反思该理论模型是否存在问题。这是“唯书”立场的一种典型样态。古代笑话里讲过一个抄错祭文却说东家死错了人的酸秀才,16[清]游戏主人、[清]程世爵编撰:《笑林广记》,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就是秉持此类思维定式的绝好代表。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伽利略曾用尖刻的笔触描述了一位威尼斯哲学家观摩公开解剖课的情形:
解剖学家证明,粗大的神经干从大脑出发,经过颈部,延伸至脊柱,然后分支到全身,其中只有如线一般纤细的一支到达了心脏。为了(说服)哲学家,解剖学家极为细致地进行展示和论证。解剖学家转向(哲学家),问解剖结果是否令他满意,他是否相信神经是源于大脑的……哲学家考虑了一会儿,回答道:“你把结果如此清楚地摆在我眼前,如果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观点与你的结果相抵触,如果不是因为他曾明确表示神经是源于心脏的,我一定会承认你的实验结果是正确的。”17[美]苏珊·怀斯·鲍尔:《极简科学史》,徐彬、王小琛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87页。
以上种种认知误区与迷信,不只存在于跨界的经济学家脑中,类似的观点和认知模式在法学界也不乏其例。夏衍在《〈包身工〉余话》中提到了一位书呆子气十足的郑律师。当听说“包身工”的种种情形时,“他词色间觉得有点惊奇”,进而感叹说,“假使她们的工作情形和生活状况和你所说的一样,那明白地是构成犯罪的!”18夏衍:《包身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于是,郑律师
从桌上取过一本袖珍的六法全书,指着其中的一条说:
“除出包身制度根本不合法之外,这样的待遇工人,就构成‘妨害自由罪’的。瞧,刑法第二十六章第二百九十六条:
使人为奴隶或使人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19夏衍:《包身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当被问及带工头到乡下去和包身工父母乃至家长们订立的包身契约是否可以“自由废弃”时,郑律师表示:
“当然,这是无效的契约,民法总则第四章对于‘法律行为’的规定,明白地说:法律行为有背于善良风俗者无效;这儿所说的善良风俗,包括的范围很广,凡是人对人的凌虐酷使,都可以解释做‘有背于善良风俗’,所以这种契约本身就没有法律根据,加上,带工头到乡下去,用欺诈性质的方法缔结契约,这一点也可以构成刑事上的犯罪,刑法第三十二章诈欺背信及重利罪项下第三百四十四条:
乘人急迫轻率或无经验,贷以金钱或其他物品,而取得与原本显不相当之重利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
第三百四十四条,以犯前条之罪为常业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三千元以下罚金。”
带工老板的重利,不能不说是“与原本显不相当”,加以他们以这种犯罪为常业,简直以两罪三罪并发[罚]的犯罪。20夏衍:《包身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
“不,那要当事人自己主张,民法总则第四章第七十四条规定了对于这种‘依当时情形显失公平’的契约,‘法院得因利害关系人之声请,撤销其法律行为,或减轻其给付。’这就是说:利害关系人不声请,法院是不管的。”21夏衍:《包身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记者继续发问:
“既然这是一种‘有背于善良风俗’的社会现象,一种‘乘人危急轻率或者无经验’而用欺诈手段订结的契约,是一种‘使人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的’犯罪,那么有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护人民之责的‘当局’和‘司法检事’,不是应该很快地检举这种不正和犯罪吗?——要那些在恶势力支配下的无知识无经验的可怜虫自己起来‘声请’,那不是实质上纵容犯罪吗?”22夏衍:《包身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5页。
郑律师沉吟良久才说:
“照理是这样的事,社会局应该出来讲话的。”
……“对于这种‘包身制度’还是要用普通刑法来处理的,不过,假使男女工人年纪在十四岁到十六岁之间,那么照工厂法童工这项目之下,对于纱厂这种工作似乎是禁止的。”……“‘童工只准从事轻便工作’,‘有尘埃粉末或有毒气体散布场所之工作’是列入禁例的。”23夏衍:《包身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此番对话,直接导致了记者“对于法律的天真的想法”的幻灭。因为他已看到,
在中国人经营的纱厂,包身工制度已经渐渐的不“时行”了,可是,以吃人肉为常业的带工老板还集中在法律以外的东洋纱厂。在那“法律之外”的日商招牌之下,别说慢性的剥削,就是用凶器杀伤几个中国“奴隶”,有治安之责的人照例是不敢闻问的!24夏衍:《包身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6页。
英商纱厂里有六岁以下的童工,才出世的婴儿像物件一样地丢放在“有尘埃粉末和有毒气体散布”的机器身边,有人意识到这是犯罪的事吗?这是光天化日之下,警探保护着的工厂里俨存着的事实!——我知道,这一定是适合现社会善良风俗的事了。25夏衍:《包身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而当记者将这事实告诉郑律师,“他也只能报我以苦笑”。26夏衍:《包身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原来这纸上的、貌似完备的法律,在现实中对洋人却是不作数的。
“在所谓‘友邦’的掩护之下,问题自然又作别论了,工厂检查制度,不是就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吗?问题,还是在紧紧地束缚着我们的整个的不平等条约!”27夏衍:《包身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所有的现象,都可以在法律文本中找到对应的规范。若按本节开头提到的模型预设,法律该算是“最优”的(立法完备)。而现实中的种种现象皆与法律规定相违背,亦即“模型的基本条件在现实中被违反”,因而是现实出现了问题。然而,不能解决或回应现实问题的法律何以还能称为“完备”?在夏公的叙事中,除却司法机关(法院)外,未见其他执法机构,故按照前述有关模型的释义,“法律是由独立的法庭执行的,就不存在其他更好的方式”,然而,若当事人因故无从提起诉讼,整个司法程序便无从启动。无视人民的苦难、拒绝施以救济的法律及其运作还能算是“不能再好”?
归纳起来,这些谬误都反映了部分人群认知上的某种偏好,即希望能够从一种静态的、权威的文本(模型、假说)出发,去考察、衡量变易不居的现实,同时也往往不恰当地把法律文本当成了正确无误的参照系,而在遇到文本与现实冲突时,每以现实为非。殊不知,法律的精义与活力,原不在于让现实“合乎”于己(以及其所呈现的文本或承载的学说及模型),而在于法律本身就应该是“出于”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经验。因而,有效且负责任的法学教育便不能仅仅局限于理论的介绍和说明,而应同时也关注法律的实践,“睁开眼睛看世界”。否则,难免不会陷入郑人买履、邯郸学步的境地:明明有脚,却迷信外在的尺子;明明有自己的步态,却自动放弃,转去仿效别人,而又难得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