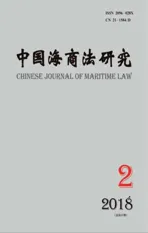执行国际海运管辖权条款之对比与策略分析研究
2018-02-06丁莲芝
丁莲芝
近年来,中国上海、厦门等港口城市陆续提出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这对于推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自贸区建设有以点带面的辐射作用,健全而强有力的海事司法权则无疑可以为其保驾护航。在国际海运实践中,彰显一国司法主权的最好切入点不外乎管辖权冲突时的博弈问题。笔者主要对中国当前海运司法实践中涉外管辖权条款的执行情况进行实证评估,并与中国管辖权立法进行对比,从而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
一、什么是国际海运诉讼管辖权?
国际海运诉讼视野中的管辖权是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一种,而对于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概念,中国学者认为,是指一国法院或具有审判权的其他司法机关受理、审判具有国际因素或涉外因素的民商事案件的权限,旨在解决某一特定的国际民商事案件究竟应由哪一个国家的法院管辖的问题。[1]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管辖权(jurisdiction)是国家对人和物进行控制、支配或管理的权力,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则是以国家权力为基础在国际社会范畴内对司法管辖权的分配。[2]68
因此,可以认为,国际海运诉讼管辖权是指某国或某地区法院具有司法权力的机构受理、审判具有涉外因素的海商海事案件的权限,用以解决该领域具体案件应由何国法院管辖的问题。从其权力来源看,有的来自于合同主体的约定,有的来自于国家主权力。管辖权条款作为意思自治下的合同约定,是国际层面司法机构审理案件权力的重要来源,而具有排他性的管辖权条款具有双重属性(dual nature),既赋予了指定法院拥有案件审判处理的管辖权限,同时意味着排除否定其他国家法院受理该争议的权力①管辖权条款根据其效力一般可分为排他性和非排他性,参见HARTLEY T C,Choice-of-Court agreements under the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the Revised Brussels I Regulation,the Lugano Convention and the Hague Conven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 4;当然现在也出现了第三种非对称性管辖权条款(Asymmetric Jurisdiction Agreement),参见MERRETT L,The Future Enforcement of Asymmetric Jurisdiction Agreements,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2018)67 ICLQ 37。。
由于各国对管辖权条款的姓公姓私的态度并不一致,出于主权等因素或者各国法律制度文化上的差异,管辖权条款并不经常被法院地法认定为有效,在国际海运业中不被认定为有效很有可能慑于其可能被用来规避法院地法的强制性规则而无法得到有效执行。[3]而从权力行使的时间来看,既包括(第一阶段)受理案件时海事法院查明自身是否有权管辖的问题,也涉及(第二阶段)在涉外海商事案件判决/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时,审查外国法院或其他机构是否有权审理案件的问题。而笔者主要就海运管辖权条款在第一阶段时是否实际得到有效执行进行对比分析论证。
二、中国司法实践管辖权条款执行情况实证分析
中国海事司法实践中执行管辖权条款时,主要问题是对该条款有效性和可执行性的认定。只有法院认可了当事人约定的管辖权条款,才可能决定其是否行使管辖权,从而是否受理该案件。下文主要从实际联系、诉因和格式条款这三面,分析中国法院在此问题上的态度。
(一)是否与争议有实际联系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简称《民事诉讼法》)②《民事诉讼法》虽然在2017年有微改,但因与笔者探讨主题无关,因此如无特别指出,笔者所称的《民事诉讼法》皆指2012年版。将协议管辖进行了较大修改,一是涉外和国内案件协议管辖统一化,二是将协议管辖的“实际联系”条件明确化,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第242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而2012年《民事诉讼法》在总编第二章“管辖”中的第34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可见2012年《民事诉讼法》除了在国内诉讼中增加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当事人也可约定管辖、将国内诉讼与涉外诉讼并轨之外,还扩大了协议管辖的范围,由原来的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的五个可选法院,扩大到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另一方面,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242条下何谓“实际联系”的争议,以列举的方式将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和标的物所在地作为有实际联系地点纳入可选择法院范畴。事实上,“实际联系”标准一直在海运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否定管辖权条款的作用。
在跨洋航运有限公司和海湾船用石油有限公司滑油供应合同管辖权纠纷一案③参见宁波海事法院(2013)甬海法商初字第313号,(2013)浙辖终字第96号。中,一审宁波海事法院裁定,争议润滑油供应合同当中约定的英国法院排他性管辖权条款无效。[4]上诉审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宁波海事法院的裁定,但裁决理由是,虽然滑油供应合同的管辖条款选择英国伦敦各级法院专属管辖并适用英国法,但该协议指向的伦敦,既非当事人住所地,又非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及标的物所在地,上诉人也未能举证证明伦敦与本案争议有其他实际联系。[5]可见,2013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判断管辖权条款效力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与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标准趋同了,不过到底怎样才具有“实际联系”,似乎只有符合“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五个地点的法院才具有实际联系,但既然都是这五者之一,那为什么2012年《民事诉讼法》又要再次提到“实际联系”呢?这似乎仍然有待明确。
类似的,宁波海事法院在智利南美轮船有限公司与轩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④参见宁波海事法院(2013)甬海法商初字第513号,(2013)浙辖终字第133号。中,认为协议管辖条款所约定的管辖法院所在地与该案争议并没有实际联系,应确认管辖权条款无效①本案涉案货物起运港在宁波,货物的卸货港在委内瑞拉贝略港,被告的住所地为智利共和国。涉案提单及担保函载明“纠纷应提交英国伦敦高等法院管辖”。。[6]上诉审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虽然维持了原裁定,但理由有所不同。其认为,虽然涉案提单背面条款及担保函约定“适用英国法”“英国高等法院管辖”,但均未排除其他国家有管辖权法院的管辖权,宁波海事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7]换言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张管辖权的依据不是所选择的伦敦高等法院是否与争议有实际联系,而是该管辖权条款并非排他性管辖权条款。可见对同一案件,是否采用实际联系标准,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看法,但都是主张本国法院具有案件管辖权。
不过经过改判的香港巨盛纺织原料有限公司租船合同无单放货管辖权异议案中,一审上海海事法院认为所约定的香港与案件争议没有实质性联系,二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却支持了香港法院的管辖权②该案争议发生于1997年,牵涉大陆货物进口方针对香港卖方和承运人的无单放货纠纷,争议提单背面条款约定“由本提单证明或包含的合同受香港法律约束,任何由本提单产生或与本提单相关的索赔或纠纷由香港法院解决”。。[2]97此案是为数不多的体现中国法院支持涉外管辖权条款的,但遗憾的是没能找到相应的判决书,因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上海海事法院裁决的理由不得而知。
(二)诉因是侵权还是违约
除了“实践联系”标准外,诉由也能作为中国法院审查管辖权条款有效与否的一个安全阀,且以侵权之诉否定管辖权协议中约定的外国法院作为管辖法院是中国法院不执行管辖权条款的常见理由之一。
在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与菲达电器厂、菲利公司、长城公司无单放货纠纷案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1998)交提字第3号。该案为无单放货案,牵涉提单背面订立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解决争议的仲裁条款,货方原告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主张不受双方所订立的仲裁条款的约束。同时提单法律适用条款是提单首要条款——明确约定适用《1936年美国海上货物运输法》或《海牙规则》。中,[2]97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广州海事法院的判决,认为:“被上诉人菲达厂以美轮公司无单放货,侵害其所有权为由提起侵权之诉,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受侵权法律规范的调整,而不受双方原有的运输合同约束……本案的货物交付地在新加坡,侵权行为实施地即为新加坡;现菲达厂持有正本提单,无单放货行为侵害了其对货物的所有权,故侵权结果发生地为中国。由于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不一致,人民法院可以选择适用的法律。由于本案侵权结果发生地是中国,原告的住所地、提单的签发地等也均在中国境内,本案与中国的法律有更密切的联系。况且菲达厂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后,上诉人美轮公司没有提出管辖异议并已应诉④不过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时撤销了一审和二审的判决,认为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侵权纠纷,并以侵权结果发生地在中国为由,对本案适用中国法律,不符合本案事实,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最后适用的是美国法。。”
在另一宗含有法国法院管辖条款的无单放货纠纷案⑤参见灌云县国际经济贸易公司诉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和邦辉船务代理(香港)有限公司无单放货纠纷案(1999)广海法事字第41号。中,广州海事法院支持外国管辖权条款有效,[8]但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推翻了这一裁定,认为该案是一宗无正本提单放货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因侵权结果发生地,即无正本提单放货损害结果发生在中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6条第1款的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广州海事法院应当受理该案。
鉴于这几起以诉因标准判断管辖权归属的案件发生时间较早(都在20世纪末),且都与无单放货纠纷有关,有理由认为,诉因在中国某一阶段也可以作为海事侵权案件管辖权判断的标尺,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专业性特征。
特别是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无单放货之诉设定为既可以作为合同之诉也可以作为侵权之诉,为合理利用此理由主张本国管辖权铺平了道路。但是无论学界还是理论界对此做法的批评都不绝于耳,厦门海事法院某法官曾直言,侵权纠纷一般不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的观点过于片面,其对于普通的民事侵权行为而言应该是适用的,但对于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则未必恰当。[9]118
(三)是否违反格式条款规定
第三种常见的判断外国管辖权条款的标尺是该条款有无违反中国的格式条款有效性要求。在温州惠利进出口有限公司诉智利南美轮船公司一案⑥参见(2012)甬海法温商初字第248号民事裁定书,(2013)浙辖终字第11号。该案争议点之一为管辖权条款的准据法是英国法还是中国法。涉案提单背面条款第23条记载了管辖权条款:“本提单及因本提单引起的任何索赔或争议应适用英国法,由伦敦的英国高等法院管辖。”(This Bill of Lading and claim or dispute arising hereunder shall be subject to English law and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English High Court of Justice in London.)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受理案件的法院地法即中国法处理管辖权争议①上诉人智利南美轮船称,依照涉案提单上明确约定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条款,本案的审理以及对管辖权条款效力的审查均应适用英国法,而非中国法,一审法律适用错误。,在管辖权条款效力问题上,认为涉案提单管辖权条款无效。理由是,提单上的管辖权条款系承运人事先在提单上印制,为承运人单方意思表示,并非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的共同意思表示,属于格式条款性质,排除了托运人在发生纠纷时选择法院解决争议的权利,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承运人自身的责任,加重了托运人参加诉讼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 40 条的规定,应为无效。[10]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上诉人拓××货运(××)有限公司因与慈溪××电器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无单放货纠纷案②参见(2011)甬海法商初字第348号,(2012)浙辖终字第00041号。中,也以类似的理由,根据《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支持了宁波海事法院的管辖权。[11]不仅如此,其他法院,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以“提单管辖条款的约定系事先以较小的字体印制在背面,且未尽到足够的提醒义务……成为承运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否定过涉外管辖权条款的效力③参见厦门中海联合贸易有限公司与鹏达船务有限公司管辖权异议案,(2010)闽民终字第450号。。[12]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总体上,中国法院对涉外海事海商领域的管辖权条款的执行率不高,能够找到中国法院放弃管辖权的涉外案件少之又少,亦即尽可能不执行外国法院管辖权条款为趋势。具体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看所选法院地与案件是否有实际联系;二是将管辖权协议禁锢在合同之诉中,并以侵权之诉为由不予执行,这里面主要以无单放货案件为多;三是将管辖权协议归为格式合同条款,并课以《合同法》相关规定,要么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合意,要么损害某一方利益,从而否定(承运人)拟定的管辖权条款。而其他不执行管辖权条款的原因,或者因为是当事人放弃协议管辖,或者并入主合同不成功,亦或者认为所约定的管辖权条款并非具有排他性质,等等。
三、海运管辖权条款在英国法院的命运
中国司法对待国际海运管辖权条款的考量因素是多重的,且不同的法院都有不同的标尺来判断外国法院管辖权条款的效力。国外法院对待管辖权条款的又是如何?是支持为主还是否定为主?理由又分别是什么?鉴于英美国际海运业为主导的现状,下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以英国为代表的判例法国家法院如何处理海运中的管辖权条款效力问题。
(一)意思自治优先于方便与否
Vitol SA v.Arcturus Merchant Trust Ltd④参见[2009]EWHC 800(Comm)。案的焦点之一是,英国法院对本案有无管辖权。原被告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了英国法院作为排他性管辖法院,后英国法院的被告在国外同时起诉英国诉讼的原告,发生典型的平行诉讼情形。最终英国法院判决支持原告Vitol SA公司的反诉禁令申请诉求,驳回被告Arcturus公司的反申请诉求,执行了合同当中约定的管辖权条款。
该案中当被告认为英国不是方便法院(England is not the forum conveniens)时,Blair法官称,合同双方约定排他性管辖权时,法院的选择优先于方便与否的考量(choice of forum overrides considerations of convenience),只要在缔约之时方不方便是可预见的。可见英国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理念的重视。
(二)是否有强有力的理由:方便、效率及成本等因素
M.C Pearl⑤参见[1997]1 Lloyd’s Rep 566(QB Adm)。案中,原告违反救助服务合同下韩国首尔排他性管辖权条款向英国起诉,英国没有执行管辖权条款,而是受理了案件,认为合同管辖权条款在有更强有力的理由(a strong cause)时可以不被执行。原告救助方提供了所有诉讼都应该在一个法域提起的事实证据,索赔规模较小应当在最方便和最高效(most conveniently and cost effectively)的管辖地诉讼,考虑成本英国是最好的法院管辖地。
但是,如果货方放弃了在更有利于自身的排他性管辖法院地起诉,选择在英国起诉,英国法院也可以不执行排他性管辖权条款而继续审理。如Baghlaf Al Zafer Factory co.BR for Industry v.Pakistan National Shipping Co.(No.1)⑥参见[1998]2 Lloyd’s Rep 229(CA)。案中,管辖权条款为承运人营业地巴基斯坦(适用《海牙规则》)法院管辖,货载起运地是西班牙Bilbao港,原告过了诉讼时效(1年),向英国法院起诉。对于英国是否该中止诉讼问题,Philip法官认为,提单持有人放弃了特定管辖权下更有利于自己的责任限制(《海牙规则》的责任限制规定更有利于货方),英国法院正常情况下应视为提单持有人有权忽略该条款,除非船舶所有人承诺不会利用更低的责任限制。
(三)看是否违反实体法强制性规定
海上货物运输诉讼中,有关管辖权的争议,特别是外国法院管辖权条款的执行与否,英国法院往往会依据《海牙—维斯比规则》第3.8条①《海牙—维斯比规则》第3.8条规定:“运输合同的任何条款、约定或协议,凡是解除承运人或船舶对由于疏忽、过失或未履行本条规定的责任与义务而引起货物的与货物有关的灭失或损害的责任,或以本公约规定以外的方式减轻这种责任的,都应作废并无效。有利于承运人保险利益的条款或类似条款,应视为免除承运人责任的条款。”作为判断。如果不触犯该条款,可能承认该管辖权条款,中止英国诉讼,否则会继续审理,乃至颁发禁诉令。
The Benarty(No.2)②参见[1985]QB 325(CA)。案中,英国法院在被告承诺不会减损责任的情况下执行了外国法院管辖权条款。一审法官拒绝中止诉讼。上诉法院推翻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并提出认定排他性管辖权条款是否违反《海牙—维斯比规则》第3.8条的时间是在合同方援引该条款定义争议的性质时。上诉法院在租家让步的情况下,认为这种情况下并不会免除或减轻被告在该规则下的责任,应该视为与其一致而被尊重。
相反,Citi-March Ltd.v.Neptune Orient Lines Ltd③参见[1996]l WLR 1367(QB Comm)。案中,如果货方执行外国管辖权条款会减损自己利益,则不予执行。争议提单中含有新加坡管辖权条款,货方未在1年时效内在新加坡起诉,但却又在英国起诉,四分之三被告在英国已应诉,卸货地及货损发现地、证人都在英国。英国法院为了防止判决不一致,及要求货方就同一损失在两国起诉有不公正之嫌,认为货方错过新加坡的时效并不是不合理的,据此认定英国有权管辖。该案中英国法院并没有执行提单管辖权条款,就是基于如果执行了新加坡管辖权条款,会损害货方的利益,减轻《海牙—维斯比规则》第3.8条赋予承运人的责任和义务。
这两起典型的案例都是根据《海牙—维斯比规则》第3.8条承运人不得减损责任和义务条款而判断外国管辖权条款是否可能会有损原告货方利益从而减轻承运人负担的情形,可见以实体法规定作为是否执行外国管辖权条款是英国法院在海上货物运输法领域常见的做法。
四、对比分析及策略建议
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简称《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条④《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条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中国海事法院对非内国人提起的诉讼,只要有相应的书面管辖协议,选择了中国的海事法院,那么其是否与案件有实际联系在所不问。但是从前部分不难看出,中国法院不执行涉外管辖权条款的最大理由是所选外国法院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而这个实际联系的判断标尺又是模糊的,即使《民事诉讼法》再次重申了五个备选地点,但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仍然是有疑问的。换言之,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管辖权存在内外不对等的情况,一方面对选择中国法院的管辖权条款协议不要求有实际联系,也不要求是否具有排他性等因素,另一方面对选择他国法院管辖的条款则课以苛刻的实际联系要求,除了在诉因和格式条款上做文章外,又审查是否有效并入、是否具有排他性等细节。实际上,彰显国家主权无可厚非,但这种保守的做法无疑有损于中国法院在全球的公信力,特别是在建设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大背景之下。因此,建议分别以宏观和微观视角,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维护国家主权,兼顾国际礼让
霍姆斯说:“司法权也属于主权……如果没有对争议的裁决就不能保护臣民遭受相互之间的伤害,那么有关私有财产权的法律就会形同虚设。每个人就会根据自然和必要的自我保存的欲望来运用自己的力量保留和行使自我保护的权利,这就会导致战争状态,与每一个国家通过契约建立的目的相违背。”[13]可见,司法权是主权的一部分,主权者有责任和义务积极行使司法主权,同时管辖权问题又直接影响送达、取证和判决及其承认和执行,只有先认定对某一具体案件是否有管辖权,才可能进一步确定案件其他问题。中国学界主流观点无一例外地在国际管辖权争议问题上支持尊重一国主权的做法。[14]284-285
但是尊重一国主权,是不是仅仅在本国的立法中体现无限宽泛的长臂管辖呢?实施司法主权并不是仅仅狭隘地无限地向其他国家抢夺管辖权。正如自由有边界,管辖权的行使在国际社会也有边界。胡伯所提倡的国际礼让说在此问题上仍有具有现实合理性。中国学者也意识到,既要维护本国的司法管辖权,又需要考虑国际礼让原则在解决管辖权冲突中的重要作用。[15]11-15
实际上如果各国都提倡国际礼让(comity),不会减损本国管辖权,反而是主权自抑的体现,而被礼让,则直接增加了某些具体案件的管辖权,有利于本国乃至世界各国司法管辖权的通畅运行。
当然,国家主权原则除了秉持礼让之说,也要增强国际合作,即以国际公约、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的形式制定国际海事诉讼程序规范,来防止和减少管辖权冲突。[16]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以国际立法的方式来协调各国管辖权是应然也是必然选择。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①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Convention on Choiceof Court Agreements,2005),又称《海牙公约》,是由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于2005年在海牙缔结的关于排他性管辖权协议相关问题的公约,其前身是1999年《民商事管辖权及外国判决公约》。公约第2条除外适用范围含有海商海事领域内容,包括:1)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2)海洋污染、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共同海损以及紧急拖航和救助事项;3)不适用于仲裁和仲裁相关程序。虽然不适用该公约,但作为先决问题而非诉讼之目的,作为答辩理由则不排除。因此,虽然中国2017年9月加入了该公约,但是即使将来该公约对中国生效,对中国海事领域相关问题的解决也影响有限。参见HARTLEY T C,Civil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s in Europe:the Brussels I Regulation,the Lugano Convention,and the Hague Choice of Court Conven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的生效虽然并不能解决海运诉讼中的管辖权冲突问题,但从欧盟布鲁塞尔—卢加诺体系②布鲁塞尔—卢加诺体系是调整欧洲市场内各国法院判决流通的规则体系的总称,包括《布鲁塞尔公约》《卢加诺公约》以及欧盟《布鲁塞尔规则》等,这些规则之间基本规定类似,适用范围及性质有所区别,统称为布鲁塞尔—卢加诺体系。该规则体系涉及案件在成员国的管辖权分配、判决在欧洲的承认和执行的协调。参见HARTLEY T C,Civil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s in Europe:the Brussels I Regulation,the Lugano Convention,and the Hague Choice of Court Conven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的运行可以预见,以国际协作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管辖权问题存在现实的可能性。
(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理念最初根植于合同法领域的“契约目由”原则,普遍认为由16世纪法国法则区别说的代表人物杜摩林(Dumoulin)创立,并被欧洲大陆、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所广泛采纳。[17]该理论在国际法领域主要是就国际合同的合同方有权选择所适用的法律来解决彼此间产生的争议,[18]可见传统上或主流的意思自治理论是就法律适用亦即准据法的选择层面而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4条也体现了这一原则。
既然意思自治是私法的灵魂,坚持传统公私法划分的观点会不自觉地将意思自治原则投射到诉讼法这一公法领域。如有观点认为,诉讼法上的选择主义和处分权主义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公法领域的直接延伸,如果将意思自治原则纳入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领域,意味着是将当事人的合意管辖上升到一定高度,有利于管辖权冲突的解决。[19]155这种观点将当事人约定的管辖权条款纠纷全盘公法化,或者将意思自治和“程序主体原则”联系起来,[20]合意管辖制度表明了国家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展示了程序法对作为程序主体的人的自由、尊严和独立地位的尊重和终极关怀,是宪法精神在程序法中的具体体现。[21]此观点对于肯定意思自治对解决管辖权冲突问题的态度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仅仅将管辖权问题归于公法领域,则不利于提倡运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来减少管辖权争议。
首先,从管辖权的协议性质来看,不仅仅囿于公法或者说程序法领域,同时具有强烈的私法性质。对于该协议的性质各国一般有三种观点:程序性质论、合同性质论以及折衷的诉讼契约性质论。[22]164-167诉讼契约性质论是在尊重当事人合意的同时寻求对此合意进行限制的正当化方法,因此既要进行合同法上的考察,也要进行诉讼法上的考察。[22]167
回到海事诉讼管辖权协议,诉讼契约性质论的观点比较符合实践中管辖权协议所呈现的特征。管辖权协议所关乎的管辖权的处理虽然是诉讼的一个环节,但是实际上当事人达成管辖权协议的时候仍然是秉持契约自由之精神,仍是意思自治原则之体现,同时也关涉一国法院的管辖权力,甚至会限制一国司法主权。此处更加强调的是管辖权协议所具有的当事人合意处分管辖权。
其次,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有助于提高商事活动的预见性,进一步实现海运主体的效率价值。美国学者认为,有效的外国法院管辖条款经常使得当事人既能够有效地规划他们的经济活动,也能够准确地估计产生于这些活动的诉讼风险。效率和商业上的主张才最强烈支持管辖权条款有效。[23]航运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效率和风险可控原则始终贯穿所有业务营运过程。司法公权力随意否定当事人合意管辖,不利于市场行为主体发展壮大。更何况,中国法院以格式合同条款的理由否定管辖权也有悖航运实际③传统航运业中,货方以中小货主为主,立法上偏向货方,但当前不少货主并非是所谓的弱势群体,如美国的批量合同下货方和承运人之间就不是不对等关系,又如某些大型货方如沃尔玛超市或必和必拓集团等,都不宜归为格式条款下的弱势群体。。
再次,从结果上,管辖权条款对司法主权的影响是可控的。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承认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效力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中国海事法院行使管辖权。通过财产保全(如扣押船舶)或者申请证据保全①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41条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19条。,海事法院仍然可以突破约定管辖,实施有效管辖。事实上,当代的意思自治原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随心所欲不受任何约束行事,就准据法的选择而言,其同时受到法律规避制度、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及强制性规则等的限制。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意味着海事法院不得随意否定外国法院管辖权条款。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四民事庭曾明确指出解决管辖权冲突要遵守协议管辖原则,协议管辖不应限制当事人选择与争议无关地方的法院,以保证当事人选择法院的公正性及独立性。[14]285
最后,从实践上看,国外司法实践也倾向于支持管辖权条款有效。正如英国大法官Longmore在OT Africa Line Ltd v.Magic Sportswear Corpn②参见[2005]2 Lloyd’s Rep 170,proceedings had been begun in the Toronto courts,Section 46 of the Canadian Maritime Liability Act 2001 provided for proceedings in Canada。案中认为,“国际礼让的真正作用就是确保合同方的约定被尊重……这是在维护意思自治原则,而不是在维护任何国家的法院”,彰显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优先于国际礼让的心声。
反观中国司法实践,各级各地法院不认可外国管辖权条款的理由不难让外界联想到中国对国际民商事交易主体意思自治的不友好。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有公权力参与的诉讼程序中,意思自治原则除了可以作为公法赋予当事人的权利的理论基础,还可以从诉讼管辖权条款本身的性质理解,他们自愿在合意的基础上把自己将来可能发生的相关争议提交给某个法院来管辖,而这背后的对价可能是商业上的某种利益让渡。例如,某跨国国际海运承运人可能面临来自散落在各个国家港口的货方索赔带来的诉讼成本压力,如果将排他性法院地选在主营业地或者某一有良好信誉的国际海事司法中心所在地,则无疑有助于降低运营成本,而这实际上可能相应地以对价的方式表现为海运费的降低或者服务质量的提升。
中国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经济活动中,希望本国商事主体在国外交易也能得到尊重。如果说一带一路倡议集中体现了中国更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渴望,那么建设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则是为了保障和巩固融入国际社会的成果,提高本国在国际司法协作方面的话语权。
(三)控制司法权力行使边界,提升当代司法理念
提高本国在国际司法协作方面的话语权,本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除了吸收借鉴某些做法外③如不方便法院原则,早在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第七问已经涉及该问题,而2015年2月4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一次在司法解释层面明确了不方便法院原则,参见该解释第532条规定。,宏观上看,司法权的恰当行使仍然需要考虑以下原则。
一是适度采纳承认预期原则。承认预期理论,也被称为“承认预测说”,是指如果中国法院预期外国法院的判决能够得到中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则可以不行使管辖权。[15]14-15采纳承认预期说有利于避免一事二讼,减少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也有助于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二是有效原则。有效原则又被称为有利于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原则,是指各国在确定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时,应确保其法院判决能够被执行和被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其强调的是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有效性。[19]145-147这决定了如果海事法院否定管辖权条款效力,主张自身有权管辖,或者上级法院二审时将管辖权裁给海事法院,必须使中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能够被执行。如Starlight Shipping Co&Anor v.Tai Ping Insurance Co Ltd,Hubei Branch & Anor④参见[2007]EWHC 1893(Comm);[2007]2 C.L.C.440。案,武汉海事法院径自审判的同时,英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也在根据仲裁条款仲裁,后英国法院还对中国原告颁发反诉禁令,中国法院作出的判决不大可能得到外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如果正确采用了有效原则,那么最后当事人获得充分司法救济的可能性更大。
三是法治原则。这里是指法院对管辖权条款是否执行的理由必须在法律上找到充分的依据。
中国法官不具有造法功能,但是由于具体实践的复杂性、立法的滞后性等多重因素,法院必须实际上兼顾“创立规则”的角色。[24]虽然法院司法权的扩张有助于采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最先受诉法院原则或者中止诉讼。但是,中国随意不执行管辖权条款的情况普遍,即使法官自己也提出,法院应不允许原告随意选择诉因就能十分容易地规避提单管辖权条款的适用,这种做法严重违背法理,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也是相当地不公平。[9]119-120
法院在应对海运领域的管辖权冲突问题上,理念的提升也很重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量。
一是从观念上看,树立服务型争议解决机构的理念,尽量减少海运当事人在管辖权意思自治问题上的司法干预,比如,当存在效力待定的管辖权协议仍然向法院起诉时,可以考虑“与其无效,不如使其有效”的合同法原则。
二是从工作作风上看,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提升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国际公信力。在处理涉外海事诉讼管辖权冲突时,为船货方市场主体提供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比如,当当事人违反管辖权协议,有滥用诉讼管辖权之嫌时,可以鼓励当事人提起违约损害之诉的私法救济。
三是充分运用“互联网+”对当代航运中心建设的影响,体现在海事诉讼管辖权协调上就是要有步骤推进外国法查明、境外当事人身份查明、境外证据审查和境外证人作证等制度与互联网的结合,最大限度方便中外当事人诉讼,提高海事法院的国际影响力。
当然时代在发展,国际航运市场瞬息万变,中国司法理念也在与时俱进,而各国之间司法管辖权的争夺仍是未来国际社会争议解决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如何变化,我们维护本国利益、使本国国民利益最大化的理念不能变,成为航运强国、海洋大国的目标不能变。
(四)借鉴他山之石,完善规则设计
打铁还须自身硬,除了把握上述宏观原则之外,要提高本国在国际司法协作方面的话语权,需要在自身制度建设上有所作为。回顾第三部分内容,英国在处理海事案件管辖权问题上务实灵活的做法是值得中国借鉴的。虽然由于国情不同,中国不可能也无法照搬判例法国家的做法,但是从全球海运行业中诸多当事人都约定英国法院管辖、伦敦仲裁以及适用英国法可以看出,商事主体对其司法的极其信任,折射出英国司法软实力依然主导着全球海运业。虽然这种软实力无法复制,但却可以提醒我们不断完善自身制度。
首先,借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修改《民事诉讼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在判断海运诉讼管辖权条款效力时,中国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事诉讼法》第34条,以此决定管辖权归属未尝不可,毕竟海商法一直以来作为商法属性而存续至今。但《民事诉讼法》的问题在于第34条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周延性。反观《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仅第3条就规定了排他性管辖权条款的定义、何谓“排他性”、其形式效力以及其独立性原则,在第5条明确指出判定管辖权条款有效性的适用法为约定法院地法,这就避免了受理案件的法院判断管辖权效力认定标准的不一致性,减少了国际间民商事判决的冲突机会。[25]这值得中国借鉴,并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有所体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借中国签署了该公约,正在审议加入之机,倒逼国内立法,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来完善中国海事领域制度的缺失并非没有现实可能性。[26-27]
另一方面,《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在此问题上则是完全空白,其适用范围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的海事诉讼”①参见《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2条。,只有确定某一国法院有管辖权的前提下,才能继续适用之,而现在的问题则是哪一国拥有管辖权。换言之,中国海事领域的特别程序法调整的是国内管辖权之间的分配,并非笔者探讨的国家之间管辖权的分配协调问题。[28]尽管如此,国内管辖权的完善仍然有助于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因此笔者建议吸收英国中止诉讼和禁诉令(anti-suit injunction亦称反诉禁令,或禁令)的做法②参见杨良宜,杨大明:《禁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切实在平行诉讼中维护本国司法主权。[29-30]如果将此比作“矛”,要比当前只是任意不执行外国管辖权这种“盾”的做法要高明的多,也能给他国的航运业利益方留下口实。虽然中国司法实践中也能通过实施强制措施达到类似的效果,但制度化的安排无疑更加有助于提高中国司法的透明度、可靠性和稳定性。应此,建议可以在时机成熟时优化明确相应规则。
其次,参考以英国为代表的务实做法,建立健全中国的案例公报制度。[31]中国近些年不时推出一批指导案例,一些海事法院会发布审判白皮书,海事海商审判的部分可谓做得可圈可点③比如,上海海事法院、广州海事法院推出的年度双语审判白皮书;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16年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和第二批涉“一带一路”十大典型案例;继英国出版社推出英文版的《中国海事商事法律报告》后,2017年度美国上线了英文版中国海事案例数据库,等等。。[32]但笔者分析这些(海商海事)案例后发现,鲜有涉及国际管辖权协调的,作为决定案件审理前提的管辖权问题似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值得肯定的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某些海事法院会出台中英文版的司法报告,涵盖了一些重要诉讼判决,多少增加了外界对中国司法的信心,但是,这些报告的涵盖面仍然有待拓展。
不过当前能够更好提升航运中心司法服务质量的方式是继续推进判决电子化、公开化。现在有的法院已经有选择地直播庭审(上海海事法院),有的已经开始短信通知立案(宁波海事法院),有的已经用微信等手段进行域外取证(广州海事法院),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互联网+”给司法权带来的挑战。司法权(海事法院)如何在被扩大管辖案件范围的同时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诉讼管辖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号)增加了海事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还有不少法院系统的声音认为海事刑事案件也应当归海事法院管辖。,[33-34]利用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机遇解决管辖权冲突问题是个新课题。笔者在互联网数个数据库中查找中国法院管辖权条款执行情况的案例后发现,有些一二十年前的案例始终找不到原始判决或裁决,特别是有些关系重大、时间又比较久远的旧案要案,这就需要进一步创造条件,使自海事法院成立以来的所有判决都得以对外公开,而且都以中英文双语的形式对外公开,这就对司法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再次,推进国家间的民商事管辖权合作的制度化。截至2018年2月,中国已与39个国家签署了国际民商事方面的司法合作协议,[35]虽然这些协议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如果将其实施形成固定长期的司法合作机制,并有相应配套的修改、解释和适用机制,那么可望在中国在与这些国家合作时减少冲突。时值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之际,统筹这些周边沿线国家达成长效司法合作机制应当是可行且实际的,这也为中国进一步以此为跳板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提供了机会。
五、结语
只有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之下,鼓励当事人意思自治下的合意管辖,约束海事法院管辖权扩张,同时又充分借鉴他山之石,才能够提高裁决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服务大局,实现最大程度上的分配正义。纵观英国法院在此问题上采用的务实、灵活的做法,我们需要绕开无法复制的方面,优化可能优化的制度安排,并且以点带面,先从某些沿线国家入手,达到以线带面的效果,并且,从海事领域这一特殊领域扩展到一般国际民商事领域,提升国际民商事活动的司法话语权,保障本国国民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司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