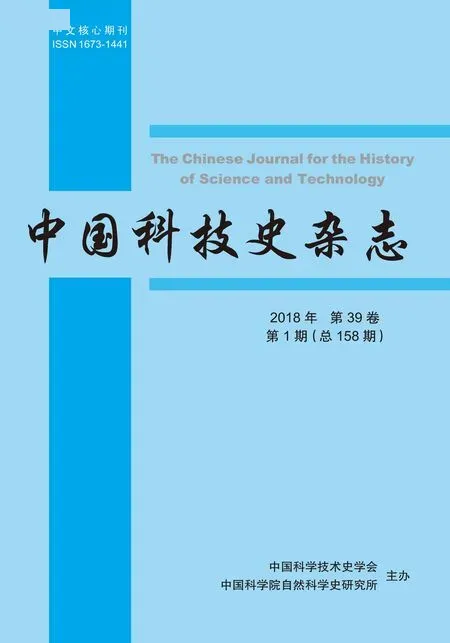新生代研究室的中外合作及其影响
——以德日进和杨钟健的两次合作考察为例
2018-02-06韩琦丁宏
韩 琦 丁 宏
(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2.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太原 030006;3.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太原030024)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西方近代地质学开始传入,外国学者也开始了对中国地质资源的调查。为加强本土的地质研究力量,1913年,经丁文江等人的努力,地质研究所得以创立,开始本土地质学专业人才的培养;1916年,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草创之初,在北洋政府矿务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等人的帮助下,调查所重点围绕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煤、铁等矿产资源的勘探展开工作。随后,在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的筹划下,中国地质学家开始涉足古生物学等领域。受经济发展和人才条件的限制,早期古生物学研究集中在无脊椎动物化石方面,主要由北京大学与地质调查所合聘的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教授及其学生承担。1928年,随着地质调查所机构调整和人才的充实,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发掘,并展开相应的地质、地层研究。本文依据已出版的德日进书信、《杨钟健回忆录》、相关地质学论著,以及新发现的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致翁文灏、杨钟健的书信,在国际合作的视角下审视德日进和杨钟健1929、1932年在山西的两次合作考察,还原考察路线,分析考察原因,并结合考察成果探讨其学术影响。
1 地质调查所的建立与中外合作
19世纪中叶,随着地质学科自身的发展和中国的门户开放,为了验证和解决具有特色的区域性地质学问题,外国地质学家纷纷踏足中国寻求解答,并调查中国地质和矿产资源,代表人物有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von Richthofen,1833—1905)、美国学者庞佩利(Raphael Pumpelly,1837—1923)、维理士(Bailey Willis,1857—1949)等,章鸿钊曾感叹道:“予尔时第知外人之调查中国地质者大有人在,顾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1],页21)
民国创立伊始,南京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政司下成立地质科,此后使用过“地质调查所”、“地质调查局”等名称,先后隶属于工商、农商、实业、经济等部门*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政司下设地质科,章鸿钊任科长,5月,实业部迁至北京,分为工商部和农林部,地质科隶属工商部,次年2月,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的丁文江应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的邀请来到北京,见到地质科只有一名科员,两名佥事,于是同张轶欧商量将行政为主的地质科变更为技术为主的地质调查所,丁文江任所长。1914年1月,工商部、农林部合并为农商部,地质科隶属农商部。参见地质调查所. 地质调查所沿革事略[M]. 北京:地质调查所, 1922. 1—2。1916年1月,改地质调查所为地质调查局。1916年2月2日,地质调查所由农商部矿政司管辖升格为由农商部直辖,设置了地质股、矿产股、地形股、编译股和地质矿产博物馆四股一馆,名称变更为地质调查局,但此局成立历史非常短。参见李学通. 地质调查所沿革诸问题考[J]. 中国科技史料, 2003, 24(4): 351—358。10月,地质调查局更名为地质调查所,自此地质调查所的名称才最终确定。参见地质调查所. 地质调查所沿革事略[M]. 北京:地质调查所, 1922. 1。此后隶属关系还有变动,1928年夏,隶属农矿部,1930年底,隶属于实业部,1937—1949年,隶属经济部。参见王仰之. 中国地质调查所史[M].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6.20。,主要承担地质填图、矿产调查等基础性工作。地质调查所成立之初,获得实业部次长马君武、矿务司司长何燏时的支持。时任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任期为1914年7月20日—1917年9月)对其寄予厚望:“民国凡百设施,求一当时可与世界学子较长短,千百载后,可垂名于学术史者,为此所(按:即地质调查所)而已。”[2]
在中国地质学科基础薄弱、研究人员匮乏的情况下,丁文江等认为早期地质研究应采取中外学者合作调查的方式。他指出“科学是西欧的产物,欧美人研究科学,至少已经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我们才不过二十年。人家当然比我们高明,我们当然要与外国人合作,受外国人指导,方始有能赶上人家的希望。”([3],页9)翁文灏也指出“我国地大物博,而生息修养于斯土者,不自研求之,自考察之,而坐待他国学者之来游,迨既知考察研求之不可已矣。而必要之知识,相当之经验,又不可不求学于他国之校与他国之师”[4]。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地质调查所开始聘用外国专家,以合作的方式研究中国地质。
开始阶段,合作考察并不顺利,存在外国专家的特长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现象。丁文江认为政府机关、科研人员、中外沟通等都有责任,他指出“许多研究科学的青年,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不愿意同外国人合作,也不愿意接受外国人指导。……外国人虽然比我们高明,但是他们不会说中国话,不知道中国需要什么,没有相当的中国人作领袖来指挥他,不但他不能尽其所长,而且还要误事。……一般的外国专家虽然比我们高明,但能够指导我们又能到中国来的人,却是少数”[3]。
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首批62名会员中,外籍会员多达22名[5]。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地质学短期内取得巨大进步,赢得极高的学术声誉。美国科学史家彼克(C. H. Peake)曾说:“地质调查所在国际学术界有其应有的地位。它的学者是知名的,它的杂志被人们广泛阅读,它的研究对发展地球的博物史知识做出了真正的贡献。西方学者把地质调查所称为民国时期最出色的科学研究机构。”[6]
2 新生代研究室的成立与中外合作考察
2.1 新生代研究室的成立与杨钟健的加盟
1899年,德国博物学家哈伯尔(K. A. Haberer)在中国药店收购了大量龙骨,并运送到德国[7]。1903年,经慕尼黑大学施洛塞(Max Schlosser)鉴定,发现类人猿牙齿化石一颗*施洛塞发现中国古人类牙齿,虽然化石标本的地点、层位等并不清楚,但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参见王仰之. 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简史[J]. 地质学史论丛, 1995, (3): 84—91;甄朔南. 新生代研究室在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地位[J]. 中国科技史料, 1984, 5(4): 87—89.,引起国际学界对中国古人类研究的兴趣。
1914年5月16日,受北洋政府邀请,安特生抵达北京出任农商部矿务顾问;1916年,他在山西考察期间,对当地丰富的古生物化石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后通过询问药店、咨询传教士、调查发掘等途径,收集化石出土的地点信息;1918年2月初,由燕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翟博(John McGregor Gibb, Jr., 1882—1939)处得知,周口店鸡骨山曾出土古脊椎动物化石;随即于2月22至23日前往周口店实地考察,并于3月迅速撰写了相关文章[8]。在安特生的努力下,次年9月15日,瑞典皇储古斯塔夫六世(Oskar Fredrik Wilhelm Olaf Gustav Adolf, 1882—1973)即委派拉格雷利乌斯(Axel Lagrelius,1863—1944)主持成立“中国委员会”,重点资助安特生在周口店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随后,在古生物学家维曼(Carl Wiman, 1867—1944)的推荐下,师丹斯基(Otto Zdansky, 1894—1988)和布林(Birger Bohlin, 1898—1990)先后来到中国协助安特生*师丹斯基在中国工作了3年(1921—1923),布林在中国工作了7年(1927—1933)。。
在安特生寻求国际帮助的同时,丁文江等非常关心我国本土地质学人才的培养,尤其是研究力量较为薄弱的古生物学领域。1918年,丁文江派遣周赞衡赴瑞典自然史博物馆师从古植物学家赫勒(Thore Gustaf Halle, 1884—1964)学习古植物学,并筹划派遣学者赴国外学习古脊椎动物学。
1923年7月,杨钟健自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经葛利普推荐,在李四光的安排下,10月26日,由上海乘法国轮船“阿吉”号,赴慕尼黑大学地质系随施洛塞和布罗里(Ferdinand Brolli)学习,专攻古脊椎动物学。1927年,在翁文灏、丁文江的建议下,经安特生、维曼、布罗里等讨论,杨钟健开始研究安特生和师丹斯基采自中国北方,收藏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啮齿类化石;次年,完成了题为《中国北部之啮齿类化石》的博士论文*我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第一部著作。参见陈星灿, 马思中. 新发现的杨钟健和安特生交往的一点史料[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5, 26(2): 135—141.。
1926年10月22日,在地质调查所、北京博物学会以及北京协和医学院联合为瑞典皇储举办的欢迎会上,安特生宣布了周口店遗址发现人类牙齿化石。以此为契机,步达生(Davidson Black, 1884—1934)申请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并于1927年4月16日正式启动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开始阶段,布林受邀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并负责古生物方面的工作,李捷负责地质方面的工作。为进一步推动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和第四纪地层研究,新生代研究室的成立也被提上日程。
1928年,杨钟健取道西伯利亚回国,经翁文灏举荐,被聘为地质调查所的技师,代替李捷主持周口店工作([9],页61)。1929年2月8日*1927年开始周口店的很多文件中就提到“新生代研究室”,但1929年4月19日,该机构才由农矿部批准正式成立。成立之初,翁文灏与步达生分别代表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签订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组织章程》和《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和步达生博士的详细协定》。《章程》和《协定》分别对新生代研究室的人事、标本保管、论文发表等进行了规定。人事方面:《章程》规定丁文江担任指导,翁文灏任所长,步达生任名誉主任,杨钟健为副主任,德日进为名誉顾问;标本保管:一切采集的材料包括人类学标本在内,全部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为了研究方便,人类学标本暂时委托北京协和医学院保管;所有标本不得运出国外;论文发表:《协定》规定,所有专业性的地质学及古生物学文章应优先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或地质学会的刊物上发表,只有经地质调查所所长同意后,步达生才可以在其他刊物上发表他的人类学文章。,地质调查所成立新生代研究室,丁文江、步达生任名誉主任,杨钟健任副主任,德日进任名誉顾问。此后,杨钟健、裴文中等逐步主持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
2.2 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顾问德日进
杨钟健赴德国求学期间,法国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德日进应桑志华(Emile Licent, 1876—1952)的邀请来中国开展古生物研究。1912年10月,德日进在法国自然史博物馆古生物实验室步勒(Marcellin Boule, 1861—1942)教授的指导下,开始接受系统的古生物学训练;1919年,服完兵役返回实验室撰写博士论文;1920年,被巴黎天主教大学聘为地质学讲席副教授;1922年3月22日,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古生物学博士学位。来华之前,他已出版法国古哺乳动物学和地层学的专著3部,在欧洲古生物学界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1923年担任法国地质学会副主席。
是年5月23日,德日进抵达天津*德日进自1923年5月来中国,到1946年3月离开,在中国前后工作了23年,期间虽多次短暂离开,但大多数时间都在中国度过。,与桑志华组成“法国古生物学考察团”,一起对宁夏水洞沟和内蒙古萨拉乌苏等地进行了发掘和研究。次年10月,德日进返回法国。1925年,法国耶稣会上级得到一份德日进有关原罪与进化论讨论稿的手抄本,认为其思想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禁止他在天主教学院授课,并决定让其离开法国到中国继续从事科学考察。德日进接受了该决定,随后向步勒申请经费,以考察团名义返回中国([10], p.31)。1926年,桑志华返回法国,以耶稣会中国北方教区(献县教区)的名义,恳请教廷同意德日进赴中国工作[11]。在此情形下,是年4月23日,德日进与桑志华共同乘坐Angkor号邮轮返回中国,5月29日抵达上海,6月5日到达天津([12],页299—300),6月28日至8月24日在河南、山西考察,9月21日至10月11日在泥河湾考察([12],页299—300)。10月22日,德日进应邀在古斯塔夫六世的欢迎会上做题为“How to Search the Oldest Man in China”的报告*此报告在《中国地质学会志》发表,见Teilhard de Chardin P. How and Where to Search the Oldest Man in China [J].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26, 5(3-4): 201—206.,分别以1925年美国中亚考察团在戈壁发现的旧石器以及巴尔博(George B. Barbour, 1890—1977)、桑志华发现的桑干河盆地化石群为例,说明了自1923年发现萨拉乌苏、水洞沟之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研究在地理空间和时间尺度两方面的最新进展。
随着周口店发掘工作的进行,翁文灏和丁文江深切认识到德日进的重要,经意大利耶稣会士龙相齐(E. Gherzi)推荐,翁文灏聘请德日进为顾问,参与地质调查所的地质考察。1927年4月26日,德日进与丁文江、翁文灏、步达生共同前往周口店现场考察,以顾问身份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工作[13]。1929年4月27日,德日进在写给朋友Max Bégou⊇n的信中,表现出了受此重托的喜悦心情:“我将越来越密切地与中国地质调查所一起工作,现在我已经以‘名誉顾问’的名义正式加入该机构。”([14],页44)
3 新生代研究室的中外合作考察
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之后,德日进、杨钟健一致认为要拓展新生代地质的研究范围,应对全国各地新生代地质状况进行调查和研究。1929年6月,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的支持下,德日进和杨钟健赴山西进行为期3个月的地质考察。
山西的黄土地层中埋藏着丰富的旧石器和古植物、古脊椎动物化石,是研究新生代地质的重要材料,杨钟健博士论文的化石标本主要来自山西。这里的地质条件,同正在发掘的周口店地点相似,与已发掘的萨拉乌苏地点相关,三者可互为补充和比较,是研究新生代地质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此后德日进和翁文灏的信中可以看出,德日进对山西“Reddish Clays”中丰富的化石和石器非常满意。。
1926年,德日进即到过山西*1926年,德日进和桑志华在山西和河南做了两个月的考察,发现了山西中部上新统湖相沉积地层,将汾河盆地的第三纪末到第四纪的沉积分为中心带、边缘带、主要带。参见Teilhard de Chardin P, E Licent. Observations sur les Formations Quaternaires et Tertiaires Superieures du Honan Septentrional et du Chansi Meridional[J].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27, (2): 129—148.,对该区域的地质状况较为熟悉。1929年4月至6月,在写给亲友的信中,他多次提及要与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赴山西进行一次为期3个月的地质考察。5月6日,他在致表姐玛格丽特(Marguerite Teilhard-Chambon)的信中写道:“这次尝试给了我去山西的勇气,对我以及我的同伴来说,山西之行很可能比我们刚刚完成的徒劳工作有趣得多。”([15],页122)德日进希望能在山西发现一些支持其研究的地层资料。6月17日,在致Max Bégou⊇n的信中他表示:“我希望在山西的考察能够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获得补充性的新发现,我去那里的劲头还是挺足的。”([14],页48)
当时,国内地质学界对山西的地质环境已有一定了解。庞佩利、李希霍芬、维理士、新常富(Erik Nyström, 1879—1963)、安特生、师丹斯基、那琳(Erik Norin, 1895—1982)等地质学家,分别从黄土成因、地层、地文等方面对其进行过研究。在黄土成因方面,根据黄土分布特征提出的水成说*1864年,美国学者庞佩利在观察黄土高原边缘的黄土后,提出“湖成说”。见Pumpelly R. Geological Researches in China, Mongolia and Japan during the Years 1862 to 1865[M].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866.119—123.、风成说*1868年到1872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考察了黄土高原腹地的黄土,提出“风成说”,他认为中国黄土主要是风搬运而来,同时水也参与沉积作用。见Richthofen F.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Vol. 1)[M]. Berlin: Verlag von Dietrich Reimer, 1877。1892年到1911年,俄国学者奥勃鲁契夫(B. A. Obruchev, 1863—1956)来中国研究黄土,进一步论证了李希霍芬的“风成说”,他认为中国黄土的物质主要源自亚洲中部的沙漠,是典型的风力搬运的结果,参见奥勃鲁契夫 B A.黄土的成因问题[M]. 乐铸等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8. 101—144.、“风成—冲积—洪积说”*1903年到1904年,维理士在汾河流域作地质调查,选用不同于传统“loess”的“Huang Tu”一词来描述黄色土壤的沉积,提出“风成—冲积—洪积说”,见Willis B, Blackwelder E, Sargent R H. Research in China: Description Topography and Geology[M].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07.等学说论辩激烈。在黄土地层方面,发现了“始新世”*1916年,中国政府矿务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对山西垣曲等地进行深入考察,并首次发现了始新世化石。化石、“三门系”*1918年,丁文江发现了“三门系”地层。1923年,安特生提出垣曲县河堤村有“三门系”地层,丁文江的“三门系”地层被学界了解。参见Anderson J G, Essays on the 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J].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1923, A(3):1—152.地层、“保德红土”*1919年,瑞典地质学家那琳到山西研究火山岩、成煤地层和植物化石等。1921年夏,师丹斯基在保德一带考察后,命名了“三趾马红土”等,此后又演化为“保德红土”等。、太原系*1922年,那琳结合在山西的考察成果,根据赫勒、葛利普对植物和动物化石的鉴定,建立了包括太原系、山西系、石盒子系在内的上古生界剖面。参见那琳. 山西太原地层详考[J]. 地质汇报, 1922.7—9.等。在黄土地文方面,在最初“四分期”*1907年,维理士在对山西和邻省调查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华北地区的北台期、唐县期、忻州期、汾河期四个地文期划分。参见Willis B, Blackwelder E, Sargent R H. Research in China: Description Topography and Geology[M]. Washington, 1907.的基础上提出“五分期”*1922年,李四光对河北省沙河县、山西省大同市西南口泉附近做了研究,认为这里有冰川地形和冰川条的痕迹。1923年,安特生在维理士的基础上,将华北地文期细分为唐县、忻州、汾河、板桥和马兰五个分期。1925年,王竹泉在维理士的基础上,将汾河流域地文期重新划分为吕梁、唐县、隰州、汾河、黄河等五个分期。参见王竹泉. 山陕地文发育史略[J]. 科学, 1925, 10(8): 929—938。王竹泉在《华北地文沿革之重检讨》中指出,他是在《中国地质图(太原—榆林幅)说明书》(1926)中将维理士的汾河流域的四期划分为五期的,但在《山陕地文发育史略》(1925)中已经有过论述。参见王竹泉. 华北地文沿革之重检讨[J]. 地质论评, 1937, 2(1- 6): 357—360.等。矿产资源方面,新常富出版了《晋矿》*1902年,应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之邀,瑞典学者新常富来到山西大学担任西斋教习,任教期间(1902—1913年)对山西矿产作了深入考察,并出版了《晋矿》(1913)(The Coal and Mineral Resources of Shansi Province, China. Stockholm, 1912)。等著作。
3.1 第一次合作考察(1929年夏)
1929年6月18日*关于这次考察的出发时间,《杨钟健文集》《西北的剖面》等游记没有准确的记载,《杨钟健文集》在“杨钟健年谱”中写道“1929年春季出差山西、陕西等地”,参见《杨钟健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杨钟健文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2.6。《西北的剖面》在“黄土沟中——山陕旅话”一文记述此次旅行是1929年夏天,参见杨钟健. 西北的剖面[M]. 北京:三联出版社, 2014.11。笔者参考1929年6月16日德日进致Christophe Gaudefroy信中记述“我后天出发去山西西部,以地质调查所名誉顾问的名义与一位中国地质学家同行。”参见Teilhard de Chardin P. Lettres l’abbé Gaudefroy et l’abbé Breuil, notes de Gérard-Henry Baudry[M]. Monaco: Editions du Rocher, 1988. 76—77。据此推测,德日进和杨钟健到山西的准确时间可能为6月18日。,德日进和杨钟健合作,到山西进行第一次地质考察。
这次考察由地质调查所组织,考察队在大同雇佣了骡子6匹*除经费原因之外,主要还是因为铁路和汽车路多在平原上,不宜于地质观察。。条件虽然艰苦,杨钟健却颇有“做主”的自豪,他曾写道:“我们骡队,虽不能和安德思(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 1884—1960)的汽车队比,也不能和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的骆驼队比,然而在实际上和性质上却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并且我们的骡队,虽然有一外国人,而我可胆大地说,我们的确是国货骡队。因为德君已受地质调查所聘任,而为我国服务了。”([16],页12)
此次考察自出发到9月18日返京,共历时三个月,途经28个县(市、旗)。考察起点是大同市东门,出发后向南到浑源,由此地经小石口到繁峙。由繁峙过代县到宁武,南行至静乐。由静乐向西北过岢岚到保德。再由保德北沿黄河经河曲,过黄河后抵达准噶尔旗,再向南折返,经哈拉塞*这里的“哈拉塞”是“西北的剖面”之中的原词,笔者结合“羊家湾到府谷”一段中提到的哈拉寨,以及内蒙古哈镇地理位置和介绍,认为这里“哈拉塞”应该是哈拉寨,现为“哈镇”。(应为哈拉寨,现为哈镇)到府谷。过黄河,西行过神木,经河套边境到榆林。自榆林东南,经米脂、绥德到吴堡,由此再过黄河向南,经石楼、隰县、大宁、吉县到乡宁填平(店儿坪*据书中记述,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和走访当地居民,认为这里应该为“店儿坪”,理由如下:第一,当地无“填平”这个地名;第二,当地方言中“填平”和“店儿坪”发音比较接近;第三,据当地老人讲,旧时店儿坪位于交通要道,并且有供骡马休息的旅店;第四,从步行和骑骡子的行程时间看,同游记中作者提到的从“吉县三候镇(吉县中垛乡三候村)到店儿坪再到圪丁石(应为丁石村)”的行程时间比较吻合;第五,从地理方位看,店儿坪位于乡宁县城的南边,丁石村和稷山县又位于店儿坪的南边,位置上同游记中的记述也对应。)。又由乡宁南行到稷山,最后由稷山沿汾河,经临汾、洪洞、灵石、介休、榆次等地回到太原,在太原遣散骡队,乘火车回北京。
此行考察重点是黄土地层、生物化石和史前石器,主要考察地点有山西大同市和保德县、陕西榆林市、内蒙古的准噶尔旗以及黄河峡谷等。特别考察了黄土地层,关注沿途的地质状况,尤其是地质条件较好的露头。杨钟健在游记中曾记述“山陕间的黄河,流于峡谷中,两岸高出约五十至一百多公尺以上,都是古生代或中生代岩石造成。”([16],页23)重要的地质发现包括:大同东约七十里第四纪初期的火山遗迹;内蒙古的哈镇、山西保德、陕西榆林和绥德以及黄河峡谷之间的红色土和黄色土等。
化石采集地点主要在保德、府谷、神木等地。在抱有殷切希望的保德冀家沟,他们遇上阴雨连绵的农忙季节,收获并不大。在神木有较大发现,德日进根据比利时等地的经验,在神木县东山一座寺庙的门口“立刻”判定一块长、宽均为“一尺多的足印”为禽龙足印*发现古禽龙足印化石的岩层为神木砂岩,其下为下侏罗纪绿岩系。“一尺多的足印”说明“古禽龙”很大,化石很珍贵,“立刻”一词,反映了德日进出色的专业素质。参见杨钟健. 西北的剖面[M]. 北京:三联出版社, 2014.37.。杨钟健也在“古禽龙足印”化石附近发现完整田穴鼠下颚化石*发现“古禽龙足印”化石当天发掘到一只田穴鼠化石下颚的前部,第二天又发掘到同一化石的后面部分。游记中举维曼教授用七八年时间才采集到一个完整鱼龙脊骨化石的例子,不仅说明这副田穴鼠下颚化石虽然前、后两部分颜色不同,还说明该下颚化石的珍贵,更表明当地黄土地层条件好。参见杨钟健. 西北的剖面[M]. 北京:三联出版社, 2014.37.。此外,在榆林、黄河渡口宋家川、乡宁圪丁石(丁石村)进行了重点考察,分别采集了啮齿类、三门系介壳等化石。
石器遗迹的考察是本次考察的第三个目的。相关考察主要集中在陕西榆林市的鱼河堡、米脂等地,并在米脂找到一块大型的新石器时代石器。
3.2 第二次合作考察(1932年夏)
1931年夏,地质调查所的化石采集员刘希古在太谷南边发现化石群。同年冬,巴尔博在太谷县发现三门系化石[17],引起了德日进和杨钟健对该地区的兴趣。1932年夏*德日进1931年2月经夏威夷来华,到1932年9月返回法国,共一年零七个月,是他第四次来到中国。,两人对山西东南部进行地质考察。
本次考察共计20余日,交通工具仍为骡子,考察起点为寿阳县,途经17个县(市)。考察队先对寿阳周边进行地质考察,然后由寿阳出发经羊头崖、道坪、东坪、长凝镇等地至太谷。在太谷经阳邑、回马,沿五马河(应为乌马河)过候目(更修*“五马河”应该为“乌马河”,另外,“候目”发现了许多化石,因此它在游记中较为重要,笔者通过采访当地百姓,得知“候目”为原名,现更名为“更修”,属于榆社县西马乡。)至榆社。此后经榆社县城到潭村,随后过武乡,再向西至沁县,经襄垣,过韩家岭、余吾镇、张店镇等地至浮山,再由南坡南行翼城,过中条山至绛县。再由绛县北行经曲沃至侯马,在侯马解散骡队,结束了此次考察。最后经洪洞、介休、平遥、太谷、榆次、太原,然后返京。
此次考察重点除山西省东南部新生代地层外,还包括榆次化石群。考察活动包括地质调查、化石采集等。考察地点主要有太谷县和榆社县更修村、潭村,屯留县余吾镇等地。
此时两人已经拥有丰富的野外地质调查经验,不仅能够通过化石确定地层年代,还能够根据地层寻找化石。本次考察虽然时间短暂但收获颇丰。沿乌马河行走时,他们观察到“两边已渐有土状如古代堆积”([18],页9),两人依据地层状况在榆社县更修村、潭村等地采集到大量化石。
地质方面他们主要对太谷、寿阳等地的土状堆积进行了考察。重点对寿阳的羊头崖、榆次长凝镇、屯留韩家岭、余吾镇以及临汾翼城附近新生代后期的红色堆积进行考察。考察认为,太谷堆积在地层的层位、性质以及化石的特征上都同泥河湾堆积相似。
化石采集主要集中在太谷、榆社、沁县等地。在榆社更修村,发现可以确定该堆积年代的三趾马牙齿以及很好的猪下颌骨和保存完好的象牙等化石。在榆社潭村发现了鹿角、完整的马趾骨、犀牛牙齿以及较为完整的象牙、剑齿虎头、猪下牙床、山羊头等化石([18],页23)。
4 考察成果和学术影响
两次地质考察在德日进和杨钟健一生众多的野外考察中占比有限。但是,以这两次考察资料为基础,结合周口店等地的化石资料,产出了大量成果*两人合作发表的主要论文和著作有:On Some Traces of Vertebrate Life in the Jurassic and Triassic Beds of Shansi and Shensi[J].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29, 8(2): 131—133;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Chou Kou Tien fossiliferous Deposit[J].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29, 8(3): 173—202; Som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Geology of China Proper and the Geology of Mongolia[J].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30, 9(2): 119—125;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Pre-Loessic and Post-Pontian Formations in Western Shansi and Northern Shensi[J].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Series A, 1930, 8: 1—37; Fossil Mammals from the Late 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J]. Palaeontologia Sinica,Series C, 1931, 9, Fascicle 1: 1—66; The Late Cenozoic Formations of S.E. Shanxi[J].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33, 7: 207—248; Fossil Man in China, the Choukoutien Cave Deposits with a Synopsis of Our Present Knowledge of the Late Cenozoic in China[J].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Series A, 1933, 11: 1—166等文章。杨钟健单独署名的论文和著作主要有On the Mammalian Remains from Chi Ku Shan near Chou Kou Tien[J].Palaeontologia Sinica,Series C, 1930, 7(Fascicle 1): 1—99; On the New Finds of Fossil Eggs of Struthio Anderssoni Lowe in North China with Remarks on the Egg Remains Found in Shansi, Shensi, and in Choukoutien[J].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33, 12: 145—152等。,“前后不到两年半,仅两人考察了3个月,即发表了两本专著论文,其效率之高,后人鲜有出其右者。”[19]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成功的中外合作考察,培养了本土古生物地质学人才,促进了古脊椎动物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进程。
这两次考察合作双方均为受益者,既验证、完善了德日进的生物地层学理论,又丰富了杨钟健古脊椎动物学野外考察的实践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学术成就和影响主要集中在黄土研究、化石群的发现、石器发掘、地质学理论和古脊椎动物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等方面。
4.1 开启山西旧石器考古与“榆社”化石群发掘
地质剖面中的旧石器和脊椎动物化石群的发现都与第四纪地层有关。根据地层中的旧石器和古脊椎动物化石可以验证周口店、萨拉乌苏、泥河湾的地层关系。德日进和杨钟健在地质考察中对旧石器颇为关注。1929年发现的中阳许家窑、大宁下坡地等旧石器地点是山西旧石器考古的开端,也是我国继北京周口店、宁夏水洞沟等地之后早期人类活动的又一批重要遗址[20]。
两人的共同考察还发现了许多古脊椎动物化石的新属、新种*仅在“中国北部新生代后期之哺乳动物化石”一文中就记述了4种新属,11个新种。,1931年之前,山西著名的“龙骨”出产地是保德县冀家沟,榆社系化石群还不为学界所知。结合1931年刘希古的发现,1932年德日进和杨钟健,依据地层走向和露头位置,发现了榆社县更修村、潭村等有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产地,开启了榆社化石群的发掘。当时,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周口店,未对榆社化石群进行发掘。但相关学术成果已经引起桑志华的关注,1934年,桑志华和汤道平(M. Trassaert)开始在榆社县进行大规模发掘。此后,榆社系化石群发掘出由第三纪上新世到第四纪更新世,非常完整的系列化石标本,成为研究亚洲大陆新生代第三纪晚期以来哺乳动物演化的重要化石材料[21]。
4.2 提出黄土研究的地质剖面法
中国黄土真正意义上的地层学研究始于德日进和杨钟健*安特生虽没有专门做黄土地层研究,但在《黄土地的儿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1934)一书中三趾马等发现都与黄土地层相关,这一方法被德日进借鉴。参见刘东生等. 黄土与环境[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65.44.。1926年,德日进借鉴安特生的研究方法,提出地质剖面的重要性,开创了中国古哺乳动物化石与地层研究并重的先河[19]。
德日进认为,相关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改变了我们关于黄河的侵蚀及其年代的观点。”*德日进致翁文灏信,美国乔治顿大学图书馆藏,原文记道“This modifies somewhat seriously our ideas on the erosion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its antiquity”。1929年,地质考察最重要的发现——“红色土(Reddish clays)”*考察结束,德日进给翁文灏地质成果简要报告的第一条就提到“红色土”,参见1929年9月30日德日进致翁文灏信,美国乔治顿大学图书馆藏,据“Young-Teilhard geological journey in W. Shansi and N. Shensi (June-September 1929) Short final report”翻译。即为该方法的直接应用。两人将山西、陕西一带广泛分布的黄土分为“黄土”和“红色土”,根据相关地文和化石的性质,将“红色土”自下而上又分为A、B、C三层*中国的黄土主要分为马兰黄土、离石黄土、午城黄土,其中马兰黄土为新黄土,离石黄土和午城黄土都为老黄土。德日进和杨钟健发现的“红色土”属于老黄土,其中,A层又称“静乐红土”,为上新世晚期沉积;B层属于更新世早期,相当于“泥河湾层”;C层属于更新世中期,与“周口店层”相当。。在此基础上,两人提出的中国北方新生代沉积相,生物地层划分、对比的方案,对我国第四纪地层的研究至关重要,为“黄土风成说”奠定了基础,推进了我国黄土沉积的研究[22]。
“红色土”的发现是黄土研究的基础,正如刘东生所说,“在黄土地层及古生物学方面,以杨钟健的工作较详,他对黄土中古脊椎动物化石做了详细地研究,为黄土地层的划分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对鼢鼠化石的研究为鉴定黄土地层提供了很好的线索。”([23],页11)后来德日进在进行地层研究时,进一步发展了该思想,不仅考虑动物群与地层的划分,还综合考虑动物与大陆、环境、岩石圈演化等的关系,这成为他“地学—生物学”研究的核心[19]。
4.3 将地文回旋发展到华北地文回旋
“地文回旋”是我国地文期研究的独特用词*即“一侵蚀一堆积为一周期”。参见邱维理. 中国地文期研究史[J]. 中国科技史料, 1999, 20(2): 95—106.,是维理士在山西考察时提出的*维理士以威廉·戴维斯(William Morris Davis,1850—1934年)的侵蚀轮回说为基础,将华北(河北、山西一带)地形演化分为北台期、唐县期、忻州期、汾河期四个阶段,将秦岭南坡及长江三峡地区划分为秦岭期、扬子期两个阶段。参见Willis B, Blackwelder E, Sargent R H. Research in China: Description Topography and Geology[M]. Washington, 1907. 75—83, 203—261, 319—339.,巴尔博等沿用了这一术语,德日进和杨钟健对它进行完善,建立了我国新生代研究的重要遗产——“华北地文回旋”[24]。
华北地文回旋分地文和循环两方面:地文方面,维理士等进行的地文期研究以文字叙述为主,照片和素描为辅。巴尔博强调区域间地文事件与地文期序列的平行关系[25],德日进、杨钟健认为不能只关注地面上山岭高低等地貌变化,还应该以地层研究为基础进行地文期的划分和断代。循环方面,巴尔博提出华北地文回旋的雏型,即两个侵蚀期之间有一个堆积分割[26]。德日进、杨钟健在巴尔博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地文回旋的“循环原则”*与前人相比,在地文期划分方法上以巴尔博、德日进和杨钟健的划分方法最合理,其一,对地文期有明确观察,每一期代表侵蚀面或堆积面,每一循环期由两期构成;其二,自红土分出红色土以来,各地文期明确了许多。Teilhard de Chardin P, Young C C.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Pre-Loessic and Post-Pontian Formations in Western Shansi and Northern Shensi[J].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Series A, 1930, 8: 1—37.,认为地文研究应在堆积期中寻找堆积[27]。卞美年认为划分地文期有周期划分和堆积断代两个主要原则:一侵蚀一堆积为地文演化的一个基本周期;必须有化石依据来确定堆积的时期[28]。实践中,该方法在其他区域的地层研究中得以广泛应用。
实际上,华北地文回旋的机制在于内营力(构造过程)和外营力(气候过程)相结合[29]。近年来“地文回旋”主要应用在三个方面*第一,借助新手段、新资料对已有的地文期进行深入研究;第二,对地文期的划分或地文循环模式进行新探讨;第三,将地文期的研究与环境演变相结合。参见邱维理. 中国地文期研究史[J]. 中国科技史料, 1999, 20(2): 95—106.,最主要的应用是古土壤*古土壤(或称化石土壤)是地质时期或历史时期自然景观的产物,记录了当时的母质、气候、生物群落、地形和时间等因素,它是古气候、古环境的一种良好的记录。参见刘东生等. 黄土与环境[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65.278.的古气候研究。刘东生等认为德日进和杨钟健命名红色土中所夹的“红色条带”*黄土和古土壤的关系比较复杂,当粉尘堆积速度大于成壤速度时形成黄土,当粉尘堆积速度小于成壤速度时发育成古土壤。一般发育较好且保存完整的古土壤剖面,可划分出腐殖质层、粘化层、淀积层和母质层。参见刘东生等. 黄土与环境[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65. 300.是埋藏的古土壤层,而对黄土与古土壤层多层叠覆的现象所表达的古气候意义成为现在研究第四纪黄土的关注点([30],页235)。
以上的研究成果和影响,归功于德日进和杨钟健亲密无间的合作考察,这不仅是感情的交流,还是学术的交流,既体现在生活小事中,也体现在学术成果上。更为重要的是为刚步入古生物研究的杨钟健提供了国际视野。
通过《剖面的剖面》等游记对考察过程的回顾,杨钟健在生活等方面给予德日进照顾,在化石采集、科研方法等方面经验丰富的德日进则给杨钟健较大帮助。杨钟健认为同德日进合作考察“实在是一种愉快,令人可忘征尘之苦。”([18],序8—9)德日进经常将欧洲最新的成果应用到中国的研究中,并将中国的研究成果及时地介绍出去,为杨钟健提供了国际化的研究视野。1930年11月3日,德日进致杨钟健信写道:
我希望你不久就会收到米尔恩·爱德华(Milne Edward*不能确定是亨利·米尔恩·爱德华(Henri Milne-Edward, 1800—1885)还是阿尔·米尔恩·爱德华(Alphonse Milne Edward, 1835—1900)的著作。后者专长于鸟类化石;前者是后者的父亲,专长于甲壳类、软体动物和珊瑚,1823年获得医学博士,后师从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 1769—1832)学习动物学,1832年任中央艺术学院卫生与自然史专业的教授,1841年任自然历史博物馆教授,1842年,他被选为皇家学会的外籍成员,1843年任索邦大学教授,1856年皇家学会授予他“科普利奖章”,1864年成为自然历史博物馆负责人。所著《英国珊瑚化石专论》(A Monograph of the British Fossil Corals)一书是古生物化石领域的经典之作。结合另一本书给翟秉志先生,这里提到的书可能为《英国珊瑚化石专论》。)的书(一本给地质调查所,另一本给秉[志]博士)*原名翟秉志(1886—1965),1902年7月,考入河南大学堂(参见樊洪业. 秉志先生早期学历考实[J].中国科技史料, 1989, 10(2): 43—45.),1909年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同年10月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主要跟随昆虫学家倪达姆(James G. Needham)求学,1913年获理学学士学位,1914年与留美同学任鸿隽、赵元任等共同发起“中国科学社”,1918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继续在美国费城韦斯特解剖学与生物学研究所跟随神经学家唐纳森(Donaldson)研究神经细胞生长。1920年冬,回到中国。1921年,在南京高师创建我国大学的第一个生物学系,任系主任。1922年8月18日,创立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任所长。1928年10月1日,北平静生研究所成立,任研究所动物部主任。1934年8月23日,在庐山莲花谷成立中国动物学会,任会长。主要研究领域是脊椎动物形态学、脊椎动物神经生理学、动物区系调查、分类学、古动物学等,专长于第三纪的昆虫、软体动物、龟类、鱼类等化石研究。参见翟启慧. 秉志传略[J]. 动物学报, 2006, 961—970.。如果你恰好还有关于中国啮齿动物研究报告的抽印本,你或许可寄一份给里昂大学理学院地质学实验室的维雷先生(Mr. Viret)。这个年轻人一年前出版了一本非常有趣的关于圣热朗勒皮伊(St Gérand le Puy)中新世阿启塔阶哺乳动物的书[31](许多啮齿类动物Rodents,甚至一些跳鼠科动物Dipodidae)。我将会请他分别寄一本给我们。我也已经请我的书商(书店名字为“骑士”Le Chevalier)寄给你,也是给地质调查所,一本施雷伯(A. Schreuber,荷兰古生物学家,该书用德文写成)有关大河狸属(Trogontherium)的有趣的研究报告[32]*此信藏于美国乔治顿大学图书馆。。
5 结论
正如丁文江等指出的,对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的中国地质学,尤其是人才匮乏的古脊椎动物学来说,合作考察对中外学者都是最佳选择。1929年,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之后,在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的组织和规划下,德日进和杨钟健在山西进行了两次中国学者主导、国外学者参与的合作考察。
1929年,48岁的德日进已是国际著名的古生物学家,熟悉中国的新生代地层,有丰富的中国北方地质考察实践经验。32岁的杨钟健刚从德国回来不久,野外地质考察经验亟待补充。在学术起步阶段,这种长时间的合作考察,使杨钟健受益匪浅,他不仅获得了有关哺乳动物演化的理论知识,还增加了化石发掘和鉴定的实践经验。杨钟健曾回忆“谈到我们在野外有关学术上的探讨,可以说,我之获益,比在学校时多得多。他(德日进)学识渊博,除古生物及地层外,于考古、人类、地文、岩石等方面均较我为优。所以我随时随地可以得到他的指教。”([9],页61)德日进也乐于为杨钟健提供指导,在1929年4月13日致表姐玛格丽特的信中写道:“我会接受在6月或7月和一位年轻的中国古生物学家一起到山西、陕西之间黄河沿岸的一些地点进行考察,为他提供科学上的指导。”([15],页120)
这种实地合作考察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了地层学、古脊椎动物学的本土化进程,是近代地质学国际化和本土化过程的积极探索和尝试。杨钟健曾指出“德氏历年在中国工作,凡与之共同工作及接近之青年,如裴文中、卞美年、贾兰坡等,对于近代地层及脊椎动物化石,起初时,无充分研究,经德日进之熏陶,成为国内有数专家。”[33]事实证明,这种合作考察的方式是成功的,合作双方都取得了大量的科学成果。更重要的是,这种合作考察提供了一种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为裴文中、贾兰坡等学者的培养提供了宝贵经验。
致谢承蒙美国乔治顿大学图书馆提供查阅德日进、杨钟健往来书信的便利,陈蜜博士提供了德日进的相关信息,谨致谢忱。
1 章鸿钊. 六六自述[M]. 武汉:武汉地质学院出版社, 1987.
2 张轶欧.《地质汇报》序[J]. 地质汇报, 1919,(1): 1—3.
3 丁文江. 丁文江自述[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
4 章鸿钊, 翁文灏.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M]. 北京:京华印书局, 1916.
5 Membership list for the year 1922[J]. 中国地质学会志, 1922,1: 97—99.
6 C. H. Peake. Aspect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science into China[J].ISIS, 1934.22: 173—219.
7 韩琦. 从矿务顾问、化石采集者到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科学活动[C]. 法国汉学(18辑). 北京:中华书局, 2018.
8 J. G. Andersson. Preliminary Description of a Bone-Deposit at Chow-Kou-Tien in Fang-Shan-Hsien, Chili Province[J].GeografiskaAnnaler, 1919,(1): 265—268.
9 杨钟健. 杨钟健回忆录[M]. 北京:地质出版社, 1983.
10 Teilhard de Chardin P.Accomplirl’Homme,lettresinédites(1926—1952)[M]. Paris: Grasset, 1968.
11 陆惠元, 侯云凤. 德日进和北疆博物院[J]. 中国博物馆, 2000,(4): 89—93.
12 Licent E.Comptes-Rendusdeonzeannées(1923—1933)deséjouretd’explorationdanslebassinduFleuveJaune,duPaihoetdesautrestributariesduGolfeduPeiTcheuly[M]. Tome II (1925—1930).
13 同号文. 德日进对中国地质古生物学的贡献——纪念德日进逝世60周年[J]. 化石, 2015,(2): 15—18.
14 Teilhard de Chardin P.Lerayonnementd’uneamitié.CorrespondanceaveclafamilleBégou⊇n(1922—1955)[M]. Bruxelles: Éditions Lessius, 2011.
15 Teilhard de Chardin P.Lettresdevoyage(1923—1955),recueilliesetprésentéesparClaudeAragonnès[M].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56.
16 杨钟健. 西北的剖面[M]. 北京:三联出版社, 2014.
17 Teilhard de Chardin P, Young C C. The Late Cenozoic Formations of S.E. Shanxi[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 1933,7: 207—247.
18 杨钟健. 剖面的剖面[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19 李传夔. 德日进与中国古哺乳动物学[J]. 第四纪研究, 2003,(7): 372—378.
20 陈哲英. 杨老是山西旧石器考古与古脊椎动物化石研究的奠基者[C]. 秦怀钟主编. 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 西安:西安出版社, 2008. 284—286.
21 陆惠元, 侯云凤. 德日进和北疆博物院[J]. 中国博物馆, 2000,(4): 89—93.
22 刘东生. 新黄土和老黄土[J]. 中国地质, 1959,(5): 22—25.
23 刘东生等. 黄河中游黄土[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64.
24 李吉均, 朱俊杰. 庐山的地文研究[J]. 地理科学, 1987,7(4): 306—315.
25 Barbour G B. Note on Correlation of Physiographic Stages[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 1927,5(3- 4): 279—280.
26 Barbour G B. The Geology of the Kalgan Area[J].MemoirsoftheGeologicalSurveyofChina, 1929,(6): 88—148.
27 德日进, 杨钟健. 中国人类化石及新生代地质概论[C]. 《杨钟健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杨钟健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2. 62—78.
28 卞美年. 评“远东地形与考古之研究”[J]. 地质论评, 1940,5(1-2): 119—125.
29 刘东生, 卢演俦. 德日进对中西科学交流的贡献[J]. 大自然探索, 1991,(3): 106—112.
30 刘东生等. 黄土与环境[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65.
31 Viret J. Nouvelles observations relativesla faune de rongeurs de Saint-Gérand-le-Puy[J].ComptesRendusdel’AcadémiedesSciences, 1926,183: 71—72.
32 Schreuder A.Conodontes(Trogontherium)andCastorfromtheTeglianClaycomparedwiththeCastoridaefromotherlocalities[M]. Archives du Musée Teyler, 1929.
33 杨钟健. 怀地质学家德日进先生[J]. 真理, 1944,1(4): 463—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