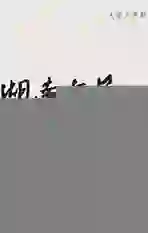从娃娃塘到娃娃塘
2018-02-01冯六一
冯六一
娃娃塘满满一池塘清水,究竟是什么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东井岭上谁也说不清楚。水是世上最寻常的,也是最珍贵的,我们对待水,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有时无比亲切,有时又熟视无睹。
水精怪着呢!洞庭湖里驾过船的米爹说,你亲近它,它处处行你方便;你要是得罪了它,不仅水路难行,说不定旋出几个水窝子,还会丢了性命。水是个妖姑娘,它说圆就圆,想方就方;激怒了它,天皇老子都拦不住,它平静下来,脔心你都看得到。米爹将水拟人化了,而且是个女人。他说的是俗世的水。而另一个叫加斯东·巴什拉的法国人说,水存在着一种眩晕,秉具物质想象的梦幻精神,并且契合了人的命运。巴什拉说的是精神的水,哲学的水。其实米爹和巴什拉,说的都是水,说的都是人,说的都是人和水牵扯不断的那些事情。
站在水边,面对那种布满玄机跳跃的银光,根本無法捉摸,就像我们无法捉摸自己。水可以升腾为云霭,在天上留下无数来去自如的痕迹,幻化出一片更加辽远而轻盈的世界。水也可以融入土地深处,潜藏于无形,滋养卑微而坚韧的生命。东井岭边娃娃塘的水,是升腾成了天空几丝云霭,没有根须般到处飘游,还是已经渗入了黑暗之中,融进了泥土的血脉?或者……总之,娃娃塘的水应该有个去处,在看得见的地方,抑或看不见的地方。
南方丘陵地带,池塘众多,它们总是隐匿在低处,鬼鬼祟祟的样子,好像永远不会干涸。那些来历不明的水,裹挟水汽到处游荡,它们与自己所处的大地和天空达成一种默契,上升或者下潜,氤氲出湿润的立体边缘,我们恍惚可以看到透出的斑驳光影。围绕东井岭,有大小不等的四口清澈池塘。岭子上的女人们,蹲在青石板上浣洗衣物,或者路过池塘,都会有意无意顾影自怜一番。女人除了对孩子,对水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好感。
那些钟摆一样兀自起落的日月星辰,也把这些池塘当了居所,每天归家似的,第二天时辰一到,又蹦跳出来了,简直是一个虚拟而又真实的神话世界。人身体里有一个主宰的魂灵,那些池塘的水里呢,应该也有一个。我有时怀疑,那是谁放置窥视我们的器物,感觉清幽幽的水里,深藏着眼睛,白天黑夜眨都不眨一下。看不厌吗,就那么些呆滞的房屋,菜地,树木,那么些熟悉不过的面孔,那么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还看得那么痴迷。也许它们根本就不是我们凡胎的俗眼,是另一种灵性的慧眼,具有更多的维度空间,注重的是时间长度,它们把我们放置在循环往复、荣枯兴衰里。所以,它们看出的是一种内在的大场景,需要广阔的视野和足够的耐心。
娃娃塘在东井岭的东边,约有五亩多水面,因其形状圆圆的如胖乎乎的娃娃脸而得名。那里常年氤氲着一团水汽和光色,幽暗的灯火一样上蹿,即使是有月光或者没有月光的夜晚,都会让岭子上的孩子萌生莫名向往。这也许是一种迷惑,一种使人无法预知而又急于抵达的迷惑。我想,娃娃塘名字起初的来源,应该是出自清朝末年或者民国初年东井岭上一个淳朴的原住民。那时东井岭还是古城的郊野,散落着一些孤坟荒塚,沉默寂然,只零星住着些种田种蔬菜的农民。他把娃娃塘当成了自己家的孩子,喊它时的满心欢喜,我们能够在时下不多见的花花绿绿的年画中感受得到。而这名字喜气盈盈的意蕴,似乎预示了娃娃塘是孩子们的乐园。也可以换个说法,娃娃塘是东井岭上孩子们的一件玩具,一件神秘莫测的玩具。
娃娃塘南面是轻纺公司仓库,北边隔一道土坝,下面一片洼地,一条小沟渠潺潺而过,不远处是官府修筑的老石井。堤坝有两米多宽,是东井岭通往东茅岭的一条便道。右岸是得胜大队的菜地,依岭子边,有几棵繁茂的樟树,几丛青翠的楠竹,遮掩着几间青砖瓦屋。左岸墈上是现在的云梦路,坐落着公交公司停车的院子,他们洗车冲出来的水,横过柏油马路,都流入了大塘里。再往前不远处,是古城经常集会的东风广场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古城第一台橘红色公共汽车从娃娃塘边的院子里披红挂彩地驶出来。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条线路就号称四路公交车了,只有两台公交车相向行驶,从先锋路老火车站,经竹荫街、京广铁路道口、东茅岭、五里牌,到花板桥的四化建,贯穿了古城有些人气的街道。四化建是刚搬迁来的大型化工建设企业,响当当地直属化工部。那时花板桥还是荒野之地,四化建像只大鸟,翅膀扇动一下,羽翼下就是它的地盘了。眨眼之间,现在花板桥成了市区中心,楼盘呼啦啦耸立起来,他们的土地都变成了真金白银。这单位有很多广东人,他们的到来似乎改变了古城的饮食习惯。见什么吃什么,他们的味觉是全能的,胃囊是全能的,蛇,黄鳝,乌龟,王八,猫,狗,老鼠,白鳗,河豚,蜂巢,蚕蛹,蚂蚱,对他们来说,仿佛世上不能吃的还没有生出来。原来本乡本土的人不爱吃,甚至感到忌讳的东西,都成了他们的上等佳肴。
开四路公交车的,都是经过挑选的女司机,身材高挑,模样俊俏。她们穿着合体的蓝工作服,戴着白手套,洒脱地握着方向盘,特别是转弯时,手臂画出女性特有的弧度,十分迷人,成了古城一道靓丽风景。但是开公交车握大方向盘,既是技术活又是体力活,这些漂亮的女司机,后来大多跳槽到各个单位开小车去了,公交车上才出现男司机。
塘边马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一到万物复苏的春天,枝干上伸展出无数嫩手掌般的叶片。夏日,树上那些淡黄球体裂开,蒲公英的绒丝一样到处飘飞,散布在空气里,弄得人喉咙痒兮兮的,浑身不舒服。进入秋天,凉风习习,阴雨绵绵,飘落的枯败叶片层层叠叠,覆盖着马路,被来往的脚步践踏,成了褐色泥浆。而在冬天,有人把碍事的枝干锯掉,光秃秃的树干举起拳头,恍若身体里爆发出了激昂呐喊,在无声震荡。很多年里,古城容貌几乎固化了,娃娃塘则像一台复印机,一年又一年,不断复制着这些老旧画面,即使局部有细微改变,也像人浓密头发里生出的一根白发,躲着掖着似的,不易被人觉察出来。
娃娃塘的水主要是德胜大队用于浇灌菜地,边上有闸门,还有一座小机埠。娃娃塘像一口扁平的铁锅,缓慢往中间深下去。东井岭上很多孩子学游泳,先从娃娃塘开始,手臂腿脚鱼鳍一样灵活后,再敢去洞庭大湖。清清池塘,泛着微微波浪,是一匹荡开的青色丝绸,被风鼓起道道光滑的皱纹。水是奇妙的物质,隐藏着无数乐趣和秘密。而夏天的酷热,成了一个充分的理由,岭上的孩子趁着到东井挑水,经常成群结队偷偷溜到娃娃塘游泳。而挑水的木桶,正好拿来当救生圈用。小不点的孩子,脱掉裤衩,露着小鸡鸡,直接跳下去了。稍大点的孩子害羞,穿着短裤游,上岸后躲在树丛或者菜园搭起的架棚里,把短裤使劲拧尽水,再穿在身上慢慢扯干。
水里隐藏乐趣,也潜伏着危机。父母们严厉的目光到处梭来梭去,在东井岭上织出了一张网,但孩子们细泥鳅一样,总是滑溜地从网兜里钻进钻出。父母恐吓我们,水里有落水鬼,会拖细伢子的脚,看你们怕不怕。岭子上经常传来父母骂孩子的声音,或者寻到娃娃塘来,揪着孩子耳朵或者大腿拖回家。但神秘兮兮的水,孩子们对它的诱惑无法抗拒。我刚开始学游泳,试探着下到水里,生怕水里蹦出什么怪异的东西来,只敢在洗衣的青石板边上,抓住一只漆着暗黄桐油的木水桶,沉沉浮浮,像摁住一个鼓胀的皮球。过了几天,胆子慢慢大些了,害怕的怪物也不见了踪影,便推着木桶往稍远的地方游。水线在木桶的半截处不时起伏变化,波浪碰撞,发出轻轻的“哗哗”声响,像谁半夜发出的呓语,听着有些含混不清。木桶半圆提手由于水的浮力和重心不確定,在水面左右摇晃,我的身子在水中随着手臂伸缩,双腿不断展开收拢,青蛙一样蹬水前行,嘴唇吐出银亮的水珠泡泡,伴着细微喘息。
爬上岸之后,怕家里发现,孩子们不会马上挑水回家,要在外面逗逗打打一阵子,等头发干透了才走。回到家里,水往陶缸里倒,眼睛露出了胆怯,还强作镇定。孩子们的遮掩是小儿科,经验老到的父母有的是办法,看孩子身上干干净净,他们脸上露出的神情似乎有些幸灾乐祸的意味。在手臂或者大腿上用指甲轻轻一划,如果现出一道泛白的痕迹,他们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证据。而面对确凿证据,孩子心已经发虚,晓得免不了要挨几竹枝皮肉之苦。可少年好玩的天性,使孩子们记不住这些皮肉之痛,第二天又到各家门前,使个眼色,悄悄相邀,趁着挑水去游泳。
起始我们扑腾得像一只只寻找食物的狗,用腿使劲刨动,弄得水花四溅。这种游泳的姿势,孩子们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叫“狗刨食”。当我推开木桶,自己慢慢扑腾一段距离,才发现,会游泳是一件多么神奇美妙的事情。随着夏天过去,又有一些孩子在水里慢慢变得自如了。如果站在某个高度看,娃娃塘会变得陌生,那些游泳的孩子像一群墨黑的小蝌蚪,漂浮在清亮的水上。夏天,孩子们身心无拘无束,仅一个娃娃塘,我们就拥有了整个水的世界。
孩子们脱离陆地,向水里鱼儿学习游水,恍若两栖动物,进入一种自由之境。孩子们是鱼儿,却没有轻巧的背鳍,也没有灵动的尾鳍,是一些显得有些笨拙的鱼儿。偶尔潜入娃娃塘的暗处,头颅像一柄旋转的小钻头,猛力掘进。水在黑暗中往两边纷纷躲闪,身体还没有完全穿行,水就在瞬间弥合了。在流动过程里,水滑过身体每一寸肌肤,孩子们得到了一种新奇的感受。帆船社的家长们从心底来说,还是愿意孩子们学会游泳。因为他们知道,孩子长大了,也许会顶班上船做水手,到江湖里去闯荡。而水火无情,看似柔软的水其实像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孩子们具有了鱼儿的基本技能,恢复或重新赋予了生命一种异样的行走方式,以前逢山过山,以后也可以遇水过水了。
孩提时的娃娃塘,让东井岭的孩子们有机会向宁静而神秘,自由而快乐的鱼儿学习,接近水的习性,感受着水的自然,神秘,明净,灵敏,柔软,坚硬,还有包容。
三十多年之后的一个夏夜,东井岭几个发小一起去相思湖游玩。
夜晚,相思湖的月,在幽兰而空阔的夜空毫无顾忌地一轮悬挂。在铁青而深邃的湖中沐浴一个,万古之月仿佛生出了野性。这样纯净的月光里,这样纯净的湖水里,这样纯净的风里,不跟着月光野一回,不把衣褪去,几乎就白活了一生。
几条汉子,在相思湖的夜色里,毫不迟疑,褪去最后一块用线缝织的布,把一切抛在脑后身后,赤条条,白晃晃,一个一个扑入湖中。那个爽,只有身体被湖水抚摩,被月光抚摩,被山风抚摩,你才能感觉得到,真的不可言说。人把身上最后一块形而美的布,自觉自愿地摘去,就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自己。山里的湖水,一点也不阴冷,还有些微温。水中的月儿,你静,她就直直地看着你,一点也不色情;你动,她就躲进浪里,仿佛怕弄皱她好看的衣裙。平常里身体难见天日的那些地方,外面的世界看不到它们,它们也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这时在灵水的触动下,开始了一次奇妙的漫游。回溯到赤裸裸跳入娃娃塘的感觉,除了剥去衣物裸露身体,其实我们还要剥去更多的累赘——裸露的也不仅仅是身体,还有心底不可名状的隐秘。
我没有在高过东井岭的地方看过娃娃塘,塘面的视野抑制在一定的夹角,我感觉它的水域非常阔大深远。很多池塘都曾以一口柔弱而强劲的水,呛灭过孩子生命的光焰,孩子清洁的魂魄融入了水中,和水中的鱼儿一起藏匿起来了。东井岭北边有一口池塘,塘磡陡峭,像一个盛汤的大花碗。铁路西边观音阁几个孩子过来玩时,不知深浅,衣服一甩,跳了下去,其中一个孩子显摆自己,往塘中间游,等到游累了想爬上岸时,滑溜溜怎么也够不着底了。当大人们赶来从水里将孩子捞起时,他脸色苍白,身子软塌塌的。大人赶紧将他翻过身来,肚子横在硬物上,放肆在背上揉压,但终无回天之力。孩子瘦小的躯体慢慢僵硬了。
也许东井岭上大多是船工的孩子,也许娃娃塘是一个平底锅,塘里从来没有淹死过孩子。娃娃塘成了东井岭上孩子们的一个伙伴,一个偌大的玩具,你随时可以扑通一声跳下去,扑入它的怀抱亲近它,和它融为一体。你也可以随时爬上岸来,湿淋淋地离开,它明亮的目光就那么轻柔柔望着,直到你的背影在岭坡上消失。娃娃塘对东井岭上的孩子们来说,是神祇的一种恩赐。与娃娃塘的名字有关吗?琢磨不透的世事,使我们感觉暗地里有一种神秘力量,编排着我们的游戏,也编排着我们的命运。虽然谁也不知道神祇是什么样子,但岭子上的老船工米爹说,好多冇看到过的东西不见得没有呢。
和我们如此亲密的娃娃塘的水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脑海里已经没有任何印象。我甚至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它干涸的模样,它就在一夜之间消失了。这种迅疾的消失有逃避的意味。几十年光景一晃而过,现在东井岭上又出现了一个娃娃塘,小时候的娃娃塘在丧失依存的形式后,空余出来的名字获得了一次再生。我们在记忆和情感上,要行走很远的距离,才能从此娃娃塘到达彼娃娃塘。
娃娃塘被渣土车从别处拉来的泥土填充覆盖后,建起了几栋五层楼房,只留下一条狭窄的巷子,沿着轻纺公司老仓库拐上东井岭。巷子两旁,排列着杂乱的小酒店、米店、美容店、麻将馆、早点摊、肉铺、修鞋店。还有近郊的人,盛夏时节,摆放一些清香四溢的栀子花,或者初秋一到,河西柔嫩的莲蓬又上来了。巷子里往来的人,港汊里的水一样荡来荡去,弥散出混杂的气味。池塘已经干涸消失,就像丢失了镜子,东井岭看不到自己的容颜,慵懒倦怠的妇人一样,不整衣衫,不理鬓发了。
地理的变迁,无端生出了许多凌乱不堪的岔路和巷子,它们连随意叫的名字都没有。那些日渐的改变,无声无息,我们猛然一觉,过去的真的过去了,眼前的景物已经面目全非。
东井岭西边,挨近京广铁路有一家制线厂,专门制作缝缝补补用的细棉线,地坪里经常晾晒染成各种颜色的棉线。那是一家只有三十来人的小集体企业,早已经倒闭,现在建成了一个很大的农贸市场,河西的、东乡的、外省的蔬菜,源源不断汇集于此。这里蔬菜品种比别的市场多,价格便宜,城市里很远地方的人都拖着小车子到这里来买菜,特别是退休老人,家庭妇女,或者下岗失业者,一月下来,还真省出不少银子。每日里人脚跟踢着脚跟,市声鼎沸。如若你问其中一个人——不管是买者,还是卖者,甚或路过者——这是哪里啊?必答曰:娃娃塘。
娃娃塘何时翻越东井岭,从东边跑到了西边?是不是那一池塘的好水,从地底的暗处潜流过来了?水是龙脉,有水就活,哪怕是徒有虚名。是岭子上的人不愿意失去娃娃塘这份旧情,重新赋予它這个名字,还是外来的人不熟悉东井岭地理,只晓得原来有个娃娃塘,误会所致?它遗失了清朝末年那个同样的证据,成为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疑案。但是眼下的娃娃塘,已经没有往日娃娃塘水的清凉与光泽,没有了向鱼儿学习的孩子,只有市场一浪高过一浪的喧嚣与张狂。
有一天,我从东井巷经过,忽然发现红砖墙上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标牌,隶书印刷体,赫然写着:桥东巷。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京广铁路上修建巴陵大桥后,东井岭改为了桥东新村。这显然是有关部门取的地名,展露着簇新与某些术语的气息。东井岭,东井巷,这样包含水系,余韵绵长的名字,具有治疗心灵荒芜的微妙力量,却只能生活在民间,成了别名,或者昵称,而且注定了它存世不会太久的命运。
五亩大小的娃娃塘,微缩地诠释了沧海桑田。很多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都可以不再存在,也可以改变原来依存的形式和方向。娃娃塘,一个不起眼的地名,在几十年的变迁中,就这样轻易失去了本真,而再生的变得越来越强盛,用日常的滋养形成了自己的生命体系。由此可以想见,那些载入史册的事件和文字,在一种庞杂的浩大之中,轻微的细节,还有多少是本真的留存呢?所谓的历史,其实更多的是选择,更多的是再生。
有一天,我不知怎么梦到背上长出了鱼鳍,但却在黑暗的旱地上奔跑,口干舌燥的我,到处寻找水,寻找光。醒来之后,我忽然感到一种孤独,一种无所适从的孤独。我知道这一辈子,已经无法逃脱,不知以后的日子,是我在等娃娃塘的水,还是娃娃塘的水在等我。
责任编辑: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