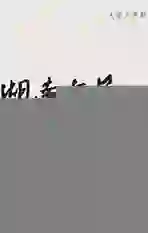放 生
2018-02-01苏大平
苏大平
李明玉起了个大早。今天,是她的生日,她要和几个“姊妹”一起去兰江边放生。这是一个久已许下的心愿,现在终于要兑现了。为了这次放生的事情,她们几个人还仔细地商量了一回。
李明玉以前也曾经放过一次生,不过那次不是选的水族,而是几只菜市场待杀的鸡。这是怎么一回事,说起来还有一个小故事。原来那是因为李明玉睡觉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引起的。她梦见了一群鸡关在一口开水不断在滚沸的大锅边的小铁笼子里,紧紧地挤作一堆。那时李明玉正好从那铁笼子旁边经过,忽然其中一只红冠紫毛大公鸡扯起喉咙竟然对她开口说起了话:“李明玉救我喔!李明玉救我喔!”那声音听起来真好像是打鸣一样,但非常哀伤。来来往往的过路人听了都无动于衷,唯独李明玉听出了这只公鸡是在向她呼救。她不禁大吃一惊,就不由自主地停在了铁笼子旁边。她看见那只公鸡把头伸了出来,一双圆溜溜的小眼睛紧紧地盯着她,露出恐惧和求救的神情。李明玉一下子就惊醒了过来。她虽然醒了,但是头脑还很昏沉,那只鸡,那么真切的一只红冠紫毛大公鸡,好像还在眼前盯着她看。还有,她耳朵边也好像仍然在缭绕着那求救的声音!李明玉躺不住了,她觉得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奇怪的梦,这应该是某种不可言说的神秘的心灵感应。她迅速打了一个电话给菜市场卖水产的表兄周老倌,叫他帮忙去看看是不是有一笼鸡,正放在活鸡出售店的一口汤锅边。周老倌那个时候一直对他这个“神经兮兮”的表妹不大怎么热情,两人虽然几乎天天见面,但却很少往来——主要是李明玉一直对他都很“冷淡”。至于“不照顾”他“哪怕是一点点生意”而“吃长斋”,倒还在其次。但是周老倌接到李明玉这一通莫名其妙的电话,虽说语气不怎么热乎,他还是答应替她到活鸡店去“瞄瞄”。果然,还真有一笼鸡,还真是放在一口汤锅边。最神奇的是,那笼鸡里面,也真有一只红冠紫毛的大公鸡。后来李明玉风风火火赶到菜市场,硬是要求周老倌和她一起去讨价还价,花了好几百块钱,才把那一笼鸡都买了下来。周老倌对她买这一笼鸡有何用处,一头雾水,但是他也不去过问。李明玉就是这种性格,她一直不大喜欢人家对她的事情问这问那的。好,托梦的鸡是已经救下来了,这事情其实还远远没有完。
李明玉把这一笼鸡买回了家,却不料大大地伤了脑筋。她的房子狭窄,只有五六十平方,已经相当破旧,是以前丈夫所在的单位分配的。自从她离婚以后,二十几年来一直独自居住在这里。除了时不时感到寂寞和空虚外,倒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其他不习惯的。多少年来,她经历了儿子的意外死亡和女儿的“反目成仇不相往来”——女儿总认为她太过于偏心,她认为李明玉只喜欢哥哥,什么都护着哥哥,什么都给了哥哥。这个白眼狼甚至在哥哥死后都没有跟她和解。随着时间的流逝,李明玉心中的创痛似乎已经渐渐归于平静或者麻木了。现在忽然在家里养上了一笼鸡,一下子就给她本来平静的生活添了很多不必要的煩恼。且不说没有地方把鸡放出来养着,只能还是让它们挤在那铁笼子里,单是每天它们臭烘烘的一堆排泄物,就叫爱好干净的李明玉没法忍受。这倒还是勉强可以克服的问题,只要委屈一下自己。但是就在买了鸡回来第一天的夜晚,那只大公鸡从夜半开始,就按时发出高亢的“李明玉救我喔!李明玉救我喔”的鸣声。这可一下子就引起了众怒。隔壁两家的人都来敲过门,语气很不好听。不过从那两家老头老太浮肿的眼泡也可以看得出,那从夜半冷不丁就开始的恶声,先不说使他们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惊吓,倒确实也是造成了对老年人宝贵睡眠的损害。李明玉往常大伤脑筋的隔壁老头的可怕鼾声,也实在是不再那么香甜了。在连续三天“遭受折磨”抱怨无效后,他们怒气冲冲地选择了报警。
片区派出所派了一个民警来敲门,李明玉起先还以为是一个“姊妹”来串门来了,不料一开门却是一个胖乎乎的青年警察。看得出来这个青年警察还是一个新手,甚至有点腼腆。他站在门口,不自然地抬起右手捏了捏鼻子,一股子热烘烘的鸡屎臭直冲人鼻孔。他张大眼睛,竭力压抑住好奇,探头探脑地越过眼前这个干瘪瘦小的老太婆的肩头往昏暗的房间里面窥视。李明玉虽然打开了门,但是她显然很不高兴,也丝毫没有让来人进到屋里去的打算。她一只手握住门边,好像随时都在准备把门给关上。她只是仰面盯着这个一脸疑惑的青年警察,脸色阴沉着一言不发。
“有人举报说您在家里养鸡扰民……”
“我养几只鸡扰谁了?我关在自己家里,又没有放出去!”李明玉不等青年警察把话说完,就气呼呼地嚷开了。
青年警察一脸尴尬,他窘迫地盯着这个倔强而有点神经质的老人,只好咧开嘴笑了笑,想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他伸手扶了扶帽子,看见李明玉的嘴角抽搐不停,她似乎一下子激动起来,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着,还回头向那逼仄的小客厅一角瞄了瞄。
“我扰民?我扰了谁了?是谁报的警?我要他跟我说个明白!说我扰民!鸡打鸣是天性,是天经地义的!我养鸡是我的自由,也是天经地义的!”
青年警察还是在笑着,他好像对眼前这个老人有点拿不准,该如何去劝说她,让她好生处理这件麻烦事。他语气柔和地说:“老人家,如今人家养一条狗,都要领养狗证。这是为了大家的生活干净整洁嘛!您家里养这么一群鸡,自己也……”
“这是我自己的事!跟别人有什么相干?”
“可是鸡半夜三更打鸣,确实就会吵到人家嘛!”
“自己睡不着,还来怪我的鸡!真好笑!”
“话不能这么说嘛,老人家!老年人本来瞌睡浅,一有什么动静,就容易惊醒,何况是长一声短一声的鸡叫……”
“那你怎么不管那些长一声短一声的鼾声呢?那些鼾声更扰民!”李明玉“啪”的一声就关了门,任凭青年警察再怎么敲门,她也不理不睬了。
李明玉虽然挫败了警察的干预,却终究没法习惯那一天天在肮脏而恶臭熏天的环境里生活。她不得不开始考虑把这些鸡送到哪里去。如果是野生动物,那倒是很好处理,带到野外去一放了事。但这些鸡可不能放到野外去。最后她还是想到了表兄周老倌,她要求周老倌给她养着,她出点饲料费。周老倌住在郊外,有一片大院子,家里也养了一群鸡鸭,没有什么为难的。事情也就这样子圆满解决了。只是后来那一群鸡,到底还是陆陆续续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听说是“黄鼠狼吃了几只”,“还有几只被偷鸡贼偷走了”,包括那只有灵性的大公鸡,这次却没有能够再次幸免于难。李明玉也就是去看她搭救下来的大公鸡到表兄那里去了两次。后来呢,就再也没上过他的门。她自然很怀疑了一阵,但是也拿周老倌没有办法。再后来,李明玉“认识到了放生的种种利益”,知道了放生需要有放生仪规,又参加了几次别人主持的放生仪式,一想到那次不知道算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放生往事,内心里就隐隐觉得很是不安。
这一回,李明玉是和张老妈、赵家婆婆、黄四姐一起出钱放生的。李明玉这回出钱多些。在其他几个“姊妹”看来,她并“不缺钱花”。她也并不总是为生活忙忙碌碌。这跟张老妈她们就大不一样。
张老妈是在菜市场旁边摆摊卖蔬菜的,她是一个话特别多的人,说起话来,你就简直插不上嘴。但是她“心肠好”,她一辈子风风雨雨,“吃过很多苦”,这里面包括离了三次婚,最后才跟了现在的这个因为患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的铁老头,她一直没有生育。她常常感叹自己的命运,说是“前世没有做好人”。这一辈子就只能“受苦受难”。她一直起早贪黑卖蔬菜,侍弄一块菜园子。得空就去参加兰城善心会的活动。听法师讲经开示啦,听大师讲人生真理啦,或者一群“姊妹们”互相倾诉一下心声。在善心会大家见了面,她熟练地双手合十,熟练地念叨:“阿弥陀佛!”她动作麻利,丝毫也没有一点老态。别人捐钱,她也从那辛辛苦苦卖蔬菜得来的零零碎碎小钱里捐一点出来。总之她在行善方面不甘落后,她真心诚意地希望自己的行为将来能得到“福报”。
她跟李明玉的表兄周老倌都住在郊外的一个村子里,两家挨得很近,所以很熟悉。她一般都是在周老倌的卖鱼摊子边停下她那张码满蔬菜的三轮车做生意。她总是极为热心地给周老倌帮腔卖鱼,并且不失时机地向买鱼的人更为积极地推销自己的蔬菜。周老倌偶尔问起李明玉的事情,她就一丝一毫也不隐瞒地全部倒豆子一样说给他听,包括上次买一笼鸡,周老倌就是从张老妈嘴里知道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周老倌起先对张老妈不是很看得顺眼,对她有点儿爱理不理,老觉得她似乎是蹭了他的油一样,脸上颜色死板板的,不大好看。但是后来张老妈很热心地跟他张罗了几单来自兰城善心会的放生生意以后,很明显他的脸色就友好得多了,言语也温和得多了。甚至于有一次兰城善心会的活动,张老妈还极力怂恿李明玉邀请了周老倌参加,虽然周老倌作为善主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犹犹豫豫地从钱包里拣拣选选了一会儿,总算抠出一张五元的毛票子捐了出来,但是后来他觉得还是很值得的,因为兰城善心会的放生生意基本上是被他收入囊中了——这都得益于热心的张老妈,他真该感谢她。其实后来他的确给了她一些小恩小惠——张老妈也确实喜欢占一点点好处,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生活不容易,大家都理解”。不用说,这一次放生活动,依然是张老妈给鼓动张罗的。至于李明玉,周老倌现在对她也好多了。虽然远不能说是关怀到无微不至的程度——每到一定的时候,他就会主动给她当搬运工,运运米,提提油。偶尔还会送一点点茶叶糕点什么的给她。只可惜李明玉吃长斋,不动荤腥,要不然,他也可能会“拎上几条鱼”送给她“尝尝鲜”呢。
李明玉因为认识张老妈而加入了兰城善心会,也因为善心会认识了赵家婆婆和黄四姐两人。赵家婆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已经多少岁了,因为她是自己的养父母辗转接来的孩子,她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她从出生下来,可能就被遗弃了,所以生日都不曾留下。她一个人住在兰城临江棚户区里的小巷口。她原来开一片裁缝铺谋生,无儿无女。老伴死后,孤苦伶仃,到现在眼花手抖了,还在干些零零碎碎缝缝补补的营生过活。她沉默寡言,性情温和,好像并不知道世间还有“苦辛”二字。黄四姐呢,是她认的干女儿,一只眼睛失明了,一头天然的黄头发,大概五十岁的样子,男人常年卧病,她靠在餐馆里面搞卫生拿点工资吃力地供一个丫头读书和全家人生活,也一天到晚像是个哑巴,难得听她说一句话。
李明玉一度很灰心丧气,她六十九岁生日时,竟然没有一个亲戚来看望她。只有几个人从很远的城市里打来了电话。周老倌根本就不晓得她的生日,这还罢了,最气人的是,女婿倒是打来了电话,女儿却一直没有跟她搭话。要不是几个“姊妹”偶尔串门跑来凑凑热闹,她倒还真是可能只有一个人关在家里黯然伤神。
李明玉回忆起她的一生,觉得她的脾气实在是犟得可怕,她自己也觉察出来了,但是她却一直控制不了自己。她感叹自己陷进了一种似乎不可抗拒的“业障”之中。她发愿要好好地改改自己,一点一滴地改变自己,一想起儿子的死亡,她就在心里涌起一股深深的负疚感。她觉得自己以前对丈夫炽热的怨恨,对儿子恨铁不成钢的强烈情感,对女儿的不经意的忽视,已经毁掉了她自己甚至是孩子们的一生。她以前常常会被一种激动的情绪所控制,她的专横使她和家里人都搞不好关系。丈夫最终离开了她。儿子一直在她的羽翼下生活,性格懦弱,最后居然因醉酒出了车祸而丧命。女儿打从叛逆期就一直跟她对着干,两人斗法斗了二十几年,到如今都似乎还没有一个完。她好端端的一个家庭,竟落得成了如今这样一种境地。这能怪谁呢?尤其是在儿子死后,她一度也绝望得想一死了之。她整个人都沉浸在一种莫名其妙萦绕不去的罪孽感中不可自拔。她总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儿子——虽然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她在梦中无数次看见儿子浑身血淋淋地来找她,站在她的面前,忧伤地望着她,却一言不发。她多么想温柔地跟他说话,但一开口却就变得跟往常一样怒不可遏。她厉声责问他为什么不思进取,好酒贪杯,混世度日,还要抛开家庭,抛开父母……那个渐渐模糊的可怜巴巴的影子消失了,她从悲痛中哭醒过来——她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地怨恨家人,怨恨自己。直到她偶然加入了兰城善心会。她才慢慢有了一点慰藉。她希望宇宙里除了这一个令人痛苦的现实世界外,还有一个可以让人安宁居住的極乐世界,那里没有烦恼,没有痛苦,没有生死,没有憎恶。那里,她可以和她挚爱的儿子将来再相会。那里不仅是人类的乐土,也是一切众生的乐土。天空里有飞翔的五颜六色的妙音鸟,水里有盛开的绚丽多彩的芙蕖花。地面铺满了贵重的金玉,树上结满了奇异的果实。在这个世上流转的灵魂,只要一心行善积德,都可以再生在那里。而在这个世上,解救那些困于刀俎的生灵,则善莫大焉。所获得的福报,据说就不可估量。还有一点,人死之后,可能托生为各种动物,所以我们看见的一切似乎跟我们没有关系的生灵,说不定就是我们以前的亲人变成的。在冥冥之中,我们就会重新看见他们,但却再也不认识他们。即使他们遭难,我们往往也全然不知不觉。唉!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李明玉因此暗暗发愿,希望在她以后度过的每个生日里,都放一次生。她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把这个想法和张老妈她们说了,谁知道张老妈极力赞成她的这个想法,并鼓动赵家婆婆和黄四姐两人也加入进来,一起促成这一件“福报很大”的事情。赵家婆婆和黄四姐只能拿出二十元钱来,这对她们来说,确实已经算是很大一笔钱了。张老妈也拿出了三十元,其余的都由李明玉掏。至于挑选什么放生,张老妈自然建议找周老倌买一塑料箱子鱼。究竟是什么鱼,她们也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大一点的鲤鱼,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容易活。周老倌甚至答应她们,会免费把她们和鱼一起送到兰江边,等她们放生后,再把她们拉回城里来,因为他自己有一辆载货用的三轮车。这样就方便不少。
李明玉匆匆忙忙在一个早点摊子上吃了一点稀饭,一个馒头,就提着塑料袋和几个“姊妹”一起到菜市场周老倌的卖鱼摊边汇合。周老倌早已经给她们准备好了一大塑料箱鲤鱼,都是斤把重的,里面还有鲜红色的锦鲤。一根供氧的塑料管插在水里,不停地咕嘟咕嘟冒着泡泡,里面的鱼有几条已经开始翻白了,有气无力地摆动着尾巴。李明玉有点担心地问周老倌:“这会不会是要死了?”周老倌拿手在水里把那几条翻白的鱼拨弄拨弄,鱼儿们似乎受了惊,就又潜进水底,打起精神来,尽量显出活蹦活跳的样子了。周老倌信心满满地说:“保管没问题!这是才抓来不久的。就是要尽快一点放生,不能拖太长时间。一个小箱子里,鱼的密度大,氧气供不上,就有点翻白。你们都坐在车厢后面看着鱼,我来开车送你们到兰江边。”
周老倌叫了几个人,一齐用力地把装了满满一箱水的鱼箱抬上了一辆摩托车改装的小三轮车车厢。然后李明玉她们也都爬上去,围着鱼箱蹲在车厢里。她们手都扶着鱼箱,目光都投向那些在水中惊慌游动的鱼群。一个帮忙的小老头拍拍周老倌的肩膀,笑嘻嘻地说:“我们帮了你一回忙,你总该给我们抽支烟吧?没看见你这么小气的!”
周老倌也笑了,他摊了摊两手,说:“我也是帮人家的忙!”
“看来我们只好自己捉鱼吃了。就晓得你这个小气鬼!”小老头冲周老倌挤了挤眼。咧开嘴呵呵笑着。
“你自己捉啊,隨你的便。”
周老倌发动了三轮车,车子启动了。坑坑洼洼的路面使鱼箱里的水晃荡个不停。有一条鲤鱼哧溜一声跳了起来,溅起一串水花,打湿了几个人的衣服。张老妈连忙念起了“阿弥陀佛!”其他几个人也跟着念佛,但是手却一点也不能松开鱼箱。一股鱼腥味弥漫在每个人的身上,李明玉最不喜欢衣服沾上味儿,就大声对周老倌说:“慢点开!车抖得太厉害了!水都荡出来了,鱼有点受不了。”
“等一下上水泥路就好了。这条路是有点难开的。”
“你还是慢点。不要还没等到水边,它们就死了!”
“它们主要是缺氧,要快一点放生。慢了就不行了。现在没有充氧了嘛。”
“我看你还是慢一点好。”
“那好吧。”
三轮车好容易拐上了一条平坦的水泥路面,这下平稳多了。李明玉觉得可以放开手了。她开始担心起来,先前那几条鱼又开始露出了肚皮。但就在这时候,她抬头向马路上一望,在不远处,她瞟见了一个人,骑着一辆旧摩托车跟着她们,车前面一个龇牙咧嘴的狼头贴标很打眼。那凶神恶煞般的贴标和车上嬉皮笑脸的小老头的那张脸形成了一个滑稽的对比。在车后座上还似乎绑了一张抓鱼用的竹竿作柄的网罩。这不就是刚才帮忙抬鱼的那个小老头吗?李明玉心里觉得有点奇怪。就在她疑惑的当儿,那个小老头似乎也看见了她,冲她笑嘻嘻点了点头,好像他们就是熟人一般打了个招呼。然后他拐进马路旁边的一条小巷子,消失了。
“刚才帮忙的那个小老头是谁?”
“你说哪个?”
“就是向你讨烟抽的那个。”
“喔!老钱。”
“他是干吗的?抓鱼的吗?”
“啊?抓鱼?——喔!他是卖鱼的。”
“阿弥陀佛!可千万不能死啊,鱼儿,你们很快就要得自由了。”张老妈念叨起来。赵家婆婆和黄四姐也跟着念佛。李明玉觉得腿脚有点发麻了,她想站起身来,但是又不敢,怕摔跤。她只是挪了挪身子,现在,她倒只希望车开得快一点,最好是马上就到兰江边。
出城后,往兰江边去的马路上车辆不多。周老倌把三轮车开在路中央,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不紧不慢地往前赶,全然不顾几个老大娘蹲在那抖个不休的车厢里腰膝酸软,难受得要命。只有张老妈嘀嘀咕咕,其余的人都一声不吭。
三轮车穿过一片茂密的芦苇间的水泥路,停在了一个废弃的渡口边上。有一对情人正坐在一片草地上勾肩搭背聊得火热,沿河岸还有一个钓鱼的人,他们似乎对这一车老大娘的突然到来感到莫名其妙,都不禁朝她们投来了好奇的眼光。三轮车停住了。周老倌下车跑到车厢里来,和大家一起把鱼箱推到最里面靠着车厢板——他要顺着渡口斜坡一直下到江边,这样才能方便放生。虽然他已经操作了许多次,但这确实还是一个难题,要小心,下坡时必须要防止鱼箱在车厢里滑动出意外。他确定鱼箱已经稳稳地靠在车厢板上,不会滑动了,这才叫李明玉她们都下了车,他自己重新上车,小心翼翼地紧握住刹车,一点一点慢慢吞吞顺坡下到江边。倾斜的鱼箱里荡漾的水不时泼溅出来,有一条鲤鱼甚至都泼出来了,落在车厢里慌乱地跳个不停。还好,三轮车已经下到了水边,周老倌稍稍拐了一个弯,把车横着转过来,车尾对着江面,熄了火。
“好了,等一下就从车上直接倒进江里去就好了。这么重,我们这几个人没法抬下来。你们开始做法事,要快点。”周老倌一面说,一面爬上车厢,把那条还在乱蹦乱跳的鲤鱼双手捧起来,依然“哧溜”一声丢进鱼箱里。
李明玉走过去朝鱼箱看了看,她发现经过一番折腾,鱼比先前翻白的又多了一些。但她只是嚅动了一下嘴唇,却什么也没有说。张老妈跟着挤了过去,她大惊小怪地嚷起来了:“唉呀!鱼都翻白了!真要快点放生了!阿弥陀佛!”赵家婆婆和黄四姐一齐双手合十,也都小声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李明玉从塑料袋里掏出线香和蜡烛,张老妈马上利索地在一旁打燃打火机。她们先把一根蜡烛点着。然后她们分别把线香和另一支蜡烛点上,整整齐齐插在江边。蜡烛橘黄色的亮光在明晃晃的阳光里闪烁不停,一缕缕青烟从线香顶端袅袅上升。那两个情侣不自然地站起身,慢慢地凑了过来,他们一头雾水的样子。只有那个钓鱼人依然坐在江岸上,一动也不动,静静地偶尔朝这边投来一瞥。
李明玉叫黄四姐手举着一本经书里的菩萨画像,挺直腰身站在水边,其余几个老人在她身后一字排开,都恭恭敬敬面对着菩萨像,从口袋里掏出一样的紫红绸布封面的经书。经书上面用工整的宋体印着烫金的“放生仪规”字样。李明玉带头翻开经书,老人们一个个也都跟着郑重其事地窸窸窣窣把经书翻开,捧在手上。李明玉清了清嗓子眼,开始用一种若隐若现的呢喃细语吟诵起来。她眼睛直直地盯着经书,吟诵得越来越快,可见得她对经文已经是烂熟于心。那些老人在刚开始时略微有点跟不上节奏,但是随着精神的集中和投入,她们也很快就都合拍了。只有赵家婆婆的嘴像是一张奄奄一息的鱼嘴,疲倦而缓慢地一张一合,不过她丝毫也没有显出焦急的神情,她似乎在心里面有一个声音正暗暗流淌着,合着这不断嗡嗡作响的呢喃,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神奇穿透力的柔韧声浪,在波涛滚滚的兰江边升腾起来,如同鸟群飞过晴朗的天空,如同激流穿过幽深的河床,似乎永远都不会停息。她们都沉浸在这一种声浪之中,一张张满是沧桑的脸上,都流露出了纯净和安宁的神情……
“快一点,鱼都要死了。鱼箱空间小,严重缺氧,时间可不能太长!”周老倌很不合时宜地大声嚷嚷了起来。
李明玉没有理他,其他的人继续跟着李明玉虔诚地念诵经文。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周老倌的嚷嚷声。周老倌蹲在三轮车旁,粗俗地吐了一口唾沫,继续仰起脸望着这几个喃喃不停诵经的人,他似乎感到有点窘迫。在念完“三皈依”后,中间的间隙里,李明玉朝周老倌瞧了瞧,只是回应了一句:“每次不都是这样,你还不懂?”
“这次天热,情况有点不同,这些鱼怕拖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了。”
“阿弥陀佛!我们可以简便点。仪式是一定要举行的,不然放生就没有意义了。”张老妈似乎在打圆场。
赵家婆婆望望周老倌,又望望李明玉,好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双手已经举得发酸的黄四姐低声地说:“李姐,能简便點,就简便点吧。”
“简便点。会简便点的。但无论怎样,仪式是一定要举行的,我们要让鱼也皈依,我们才能得福报。”
“这不是我们得福报的问题,张姐!”李明玉提醒张老妈。
“当然,鱼也会得福报嘛。准备洒甘露水了,李姐!”张老妈转过话题,提示李明玉,李明玉点了点头,就合上了经书,小心翼翼地塞进口袋。那个她带来的塑料袋在她脚下放着,她弯下腰在袋子里拿出一个小小青花瓷的碗,然后她慢慢走到河岸边,折下一枝细细的柳条,这才弯下身子,拿碗舀了一小碗河水。她一手端着水,一手拈着柳条,嘴里面一直喃喃不停。她再次走到装满了鲤鱼的塑料筐边,开始把柳条蘸上碗里的清水,挥洒在那些痛苦翕动着嘴巴的生灵上。有几尾鲤鱼已经完全翻白,直直地躺在水面上,一动也不动了。
“真的要快点了,这些鱼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周老倌拿手指戳了戳其中的一尾,它只有鳃还在缓慢地一张一张,表示它还在坚持活着。
李明玉依然有条不紊地一面围着水箱往鱼群洒水,一面带头念诵经文。周老倌哭丧着脸挨着这似乎漫长的时光,也像是一尾等待放生的鱼一样。他可能是焦急地想迅速回到自己的摊子上去,说不定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就已经错失了好几单生意。他不住地挠着猪鬃一样的油腻腻的头发,无可奈何地望着李明玉,心里只能干着急。
“这条鱼怕是要死了。”
“我们会简便点。周大哥,你不要急,鱼也要皈依才行。”
“我是不会急的,就是怕鱼会等不了……”
“不要紧的。”
“不要紧就好。我急什么,我看它们都翻白了……”
“阿弥陀佛!”
李明玉的念诵终于停住了。仪式结束,现在,就是放生了。周老倌一下子就变得精神抖擞,“噌”地跳上了车厢,开始费力地把沉重的水箱拖拽到车尾来。鱼又开始不安地跳跃。翻白的鱼这时也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一个个挣扎着强打起精神跌跌撞撞地游动起来。
“放生喽!”随着周老倌一声吆喝,他奋力地把水箱一端猛地抬了起来,水“哗哗”流进江里,一尾尾鲤鱼也随着水流“啪啪”地落进了江水里面。稠密的鱼群一下子在江边慢慢散开,有的迅速地游向幽深的江心,有的还呆头呆脑地留在原地鼓动腮帮子,似乎还没有明白过来发生了怎么一回事。还有一些则浮在水面,就像是晕车了一样,不明方向地随缓慢的水流打转。原来翻白的那几尾鱼,这时候勉强斜着身子,支撑着在岸边本能地微微划动着胸鳍。
“鱼儿,都游走吧。我们在西方再相会吧!”李明玉一面朝还留在岸边的鱼浇水,一面说。张老妈、赵家婆婆和黄四姐也都在江边蹲下身子,开始向鱼群浇水。有些鱼反而向她们聚拢过来。
“它们是在感恩呢,这些有灵性的鱼。”张老妈说,她一面不停地浇水,一面说:“走吧,走吧!鱼儿们,在西天我们再相会!”
那一对情侣默不作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紧紧地抿着嘴,似乎竭力想抑制住不笑出声来。
就在这个时候,李明玉口袋里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她掏出来一看,是女婿的电话号码。她有点激动地摁了接听键,就把手机按到耳朵边。
张老妈看见李明玉的脸色有点异样,她的眼睛里跳动着一种隐秘的光芒。好像她忽然被一种不可遏制的欣喜情绪所感染。她一直“嗯嗯”地应着。周老倌也没有敢打断她,尽管他早就坐在车上,打算发动三轮车回去了。他只是示意其他几个人先爬上车厢等一等李明玉。至于那些依然留恋江岸的鱼儿,它们迟早会回到茫茫的大水中去的。
李明玉终于挂了电话。她有点抑制不住兴奋地对周老倌说:“我女儿女婿都回来了。大家一起到我家去吃午饭。”
“阿弥陀佛!福报啊!”
“阿弥陀佛!”
“这些鱼还没有游走……”赵家婆婆说。“要不要再等等……”
“它们自己会走的。鱼儿,快走吧!西天再相会!阿弥陀佛!”张老妈高兴起来,对李明玉说:“李姐,我还没看见过你的女儿,她这回算是回心转意了。阿弥陀佛!看看,这就是福报啊!真灵验!我们今天就不去李姐家里了,你们娘母见面,肯定有很多话要说,我们明天见吧!”
“我想等一会……” 赵家婆婆说。
李明玉望了望周老倌,对赵家婆婆的话不置可否。
“那您只有自己走回家了,我不能等了,我还要做生意呢。”
赵家婆婆看了看黄四姐,黄四姐擦了擦她那一只瞎了的眼睛,也不做声。李明玉望望那边的钓鱼人和那一对好奇观望的情侣,也终于按捺不住说话了:“我看还是可以走了。走吧。放生的鱼,没有谁敢动。”
所有人都上了车厢,依然蹲在空空如也的塑料箱周围。车子启动了,在经过路边那片芦苇丛时,李明玉眼尖,一下子就看见了停在路边的那一辆旧摩托车,车头的那个龇牙咧嘴的狼头标贴真是太显眼了。这是那个笑嘻嘻的小老头的摩托车吗?他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这个人以前似乎在哪里见过,先前他跟我打招呼,看起来好像对我很熟悉……李明玉胡思乱想的时候,三轮车已经快进城了。在宽阔的马路上,周老倌依然挺直了胸膛把车开在最中央,一副凯旋而归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但这回,李明玉感觉车子似乎开得要平稳多了。一想到女儿女婿居然在她生日这天回来了,她确实感到惊喜,一想到往事,又不由得百感交集,她很希望立即就赶回家里……
码头上,那一对情侣还在对着停留在岸边的鱼群浇水。这时,只见一个小老头,从一片芦苇丛里走了出来。他肩上扛着一个抓鱼的网罩,手里提着一个锡桶,大摇大摆地走下渡口斜坡。
那个钓鱼的人看见了这个小老头,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开口说话了:“老钱,不是我说你,你这事做得是不是有点缺德?一次又一次的,这可是人家放生的鱼啊!”
“嘿!那些人精神有问题,你也有问题吧?鱼不就是吃的嘛?不然你在那里鹭鸶一样一待一整天守着,是在干吗呀?”
“真没法说你。这可是为后代子孙积阴德的事。”
“我讲求的就是实际。我认为实际最重要,没有实际,还有什么?所以啊,我只知道现在,只管得了现在。以后的事情,谁看得见,谁顾得了?”
小老头把那些还留在岸边的鲤鱼一条一条打捞了起来,两个情侣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熟练地捕捞。那个男的最后低低地问小老头说:“把鱼放生是干吗的啊?”
“浪费。”小老头答非所问地说。又一尾鲤鱼被他倒进锡桶,这是一条鲜红的锦鲤,它痛苦地在桶里翻滚着,一下子就跳出了桶沿,落到了那燃得正旺的香烛边,就在它马上要再次跌进江里时,小老头赶忙跑过去一脚把它踢回去,锦鲤掠过香烛,重重地落在岸上的草丛里。蜡烛倾斜下来,火焰忽然燃得很高,突突地跳动,烛泪飞快地流淌起来。
“老钱,你每回都抓那么多,吃得完吗?”
“别担心,吃不完还是跟以前一样,可以拿到菜市场便宜卖给周老倌去。”
“阿弥陀佛!遇上你这号人,鬼神也拿你没有办法了。”
小老头笑嘻嘻地依然肩扛着抓鱼的网罩,手提着沉甸甸的锡桶,大摇大摆地爬上渡口斜坡。他慢慢走到停靠在路边的摩托车边,把网罩绑在车座上,锡桶挂在车龙头上,然后骑上去启动油门,摩托车车尾喷吐出一股浓浓的黑烟,“突突突”很快就离开了。
渡口边,香烛还在缓慢地燃烧,李明玉她们应该快要到家了。而那两个情侣,依然还手拉着手在那里徘徊,望着已经空荡荡的江岸边,那个男的对那个女的说:“我们见证了一次神圣的放生。”
那个女的问道:“放生是干吗啊?”
那个男的于是就笑眯眯地搂住女子的腰,望着女的,撇撇嘴,假装很深情地说:“放生嘛,也就是放生呗。”
責任编辑:胡汀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