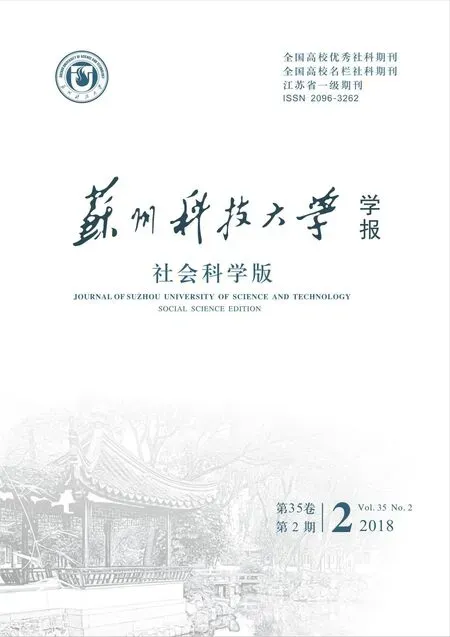“清军胁持高升号”说质疑*
2018-01-30韩剑尘
王 琦,韩剑尘
(安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一、“清军胁持高升号”说的由来
1894年7月25日,英国商船高升号在朝鲜半岛西海岸丰岛海面附近被日本军舰浪速号击沉。英国籍船长高惠悌、德国籍乘客汉纳根等人侥幸凫水逃生,船上搭乘的千余名清军士兵则悉数落水,大多以身殉国。此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公然为日军暴行进行辩护,声称事发之时中国军队胁持了高升号,“高升号船籍虽原属英国,但在事变中途,该船船长完全被剥夺行使其职务的自由,该船已为中国军官所控制;严格说来,当时英船高升号已被中国军官强占”[1]。然而,此番说辞并未被英国方面采信。8月7日,驻长崎英国海事裁判所作出判决,认为“高升号沉没之原因系日本国军舰浪速号之一再炮击”,“船长及海员,并无可以避免此种危险之手段”,对清军应承担何种责任则未提及。[2]就在同一日,日本政府派出驻英公使馆德国籍秘书西博尔德男爵拜访英国外交副大臣柏提,继续兜售“清军胁持高升号”说。西博尔德提出,“汉纳根先生、高惠悌船长和浪速船长可以作证。高升号船长已不再担任指挥,他已是中国人手中的囚犯。他们威胁他的生命,不让他放下小艇。从法律上说,他们已占据了这条船。因此,该船尽管还挂着英国旗,但已经不是英国人所有。作为该船代表的船长已失去自由,而成为一个犯人。他们这样做,不是船上中国军队的自愿行动,便是中国将领下达的命令”,“这样,浪速完全有理由采取这样的军事措施。因为控制船上配备的武装和采取敌对行动人员的反抗,是完全必要的”。[3]依笔者目力所及,这是日本方面首次完整提出“清军胁持高升号”的观点,并提供了三个核心证据,即当事人汉纳根、高惠悌和浪速船长东乡平八郎的证词。此后,英国方面态度发生明显变化,英国外交部公开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军队“强行夺去了对该船的指挥权”,“高升号于是不再处在中立的英国船长的控制之下”。至此,“清军胁持高升号”成为日英两国政府的定论,并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社会对高升号事件的认知与处置。
令人遗憾的是,清政府对所谓的“中国军队胁持高升号”一直未能予以有力的辩解与批驳。究其原因,在于清政府事发之后未能及时搜集并固定相关证据。日本军方证词自不待说,而英籍船长高惠悌的证言是在日方介入后才形成的,有大量不利于中方的记载。*高惠悌在证词中提到他在英国领事馆作此书面陈述之前,曾与日本法制局局长末松谦澄有过谈话。可见,日方曾介入高惠悌证词的形成过程中。参见《高升号船长高惠悌的证明》,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22-25页。至于汉纳根在第三方——朝鲜济物浦岛英国领事馆所提供的英文证言,笔者未能发现清政府方面所作的中文译本。目前该证言通行的,也是唯一的中文译本是孙瑞芹先生所译的《汉纳根大尉关于高升商轮被日军舰击沉之证言》一文(以下简称“孙译本”),所依据的底本是伏拉第米耳所著《中日战争》(China-JapanWar)一书中的英文附录部分,该书于1896年在伦敦出版。从内容看,孙译本中确有关于事发之时“船长丧失自由”的记载。正因为上述不利证据的存在,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研究甲午中日战争时,对清军是否曾胁持高升号这一重大问题或予以回避,或予以默认,并未能从正面回应此观点。*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雪儿简思:《大东亚的沉没:高升号事件的历史解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近日笔者发现了汉纳根证言的一种新的中文译本。经审阅,该译本对高升号事件若干关键问题的记载与现行孙译本迥然不同,为重新审视“清军胁持高升号”说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支撑史料。
二、新发现的汉纳根证言中译本
新发现的汉纳根证言中译本题为《详译德国教习汉纳根亲笔供词》,刊于1894年8月24日出版的新加坡华文报纸《叻报》第3831号第1版(以下简称“《叻报》译本”),此时距高升号事件发生仅一个月,其成文时间明显早于孙译本所依底本的出版时间。现将该译本全文照录如下:
详译德国教习汉纳根亲笔供词
六月二十三日(农历——笔者注)高升轮船被日兵船以谲诈击沉。该船教习德人汉纳根死里逃生,于二十八日至于仁川见英国副领事威金生君而书供签押焉。译若:高升轮船于六月二十一日由大沽载有弁兵一千二百廿二名,炮十二尊及快枪弹药等物启行往朝鲜。迨二十三早将抵朝境,已望见韩属群岛,瞥睹有大战舰一艘向西疾行,其船式与中国定远师船相仿佛,惟相距甚远,辨认难真,未几即踪迹已杳。迨钟鸣七点,又见一舰向济物浦而去,而高升则取道往牙山。及约八点钟时候,见一大战船绕某岛之后而出,越十分钟久,又见有两艘衔尾而来。斯时只见三船系大铁甲款式,惟何国之船一时难以辨认。至钟约九点,三船中有一船驶近,国旗上高扯白旗,始知为日本兵船,其船直驶而来,行稍近尚扯旗以示礼。至前所见行向济物浦之船,至是始知为操江文书船,为日船所逼,已反旆折向威海卫。日船多艘而行。时高升船人见日船多艘,心甚不安,及见其扯旗致礼,又以为只追逐操江,非注意于高升,或不致于有他虞。是时各船皆近,方知由某岛绕出之三船皆为日本兵舰,旋有一兵船悬旗并燃空炮两响,命高升停轮,遂遵命下碇。三日船即相聚,会忖其意,谓高升明为中国运兵船,乃悬英国旗号,将若何处置。未几即有一日舰将炮推出以向高升,相距不过一英里三分之一,复有一日船放下舢板向高升而来。时高升船中之华兵统领言于余,谓日人将欲华军拘絷,则宁付东流葬于江鱼之腹,不愿身处礼仪之乡而入无知之族,至为仇人所辱,即各兵亦甚鼓噪。余即力为开导,谓两国并未决裂,尚可妥商办理,无庸过虑,并将舆情告于船长。未几舢板即近,即有日弁带同数兵各持枪刀以见船主,旋将凭据纸查阅,确系英船,即命随同前往日本。时与日人言者惟船主,余则并未与闻,只弹压华军不可鼓噪。惟当日人未至之先,余已与船主商定,如日人不许船进朝鲜,必须极力折驳,告以船在大沽启行时,两国并未宣战。今即阻止,惟有驶回大沽,切不可随日舰他往。故船主胸有成竹,乃日人既至不待船主折驳,即勒令随同回日。船主即将日人之言告余,余转语华军,众情益愤,齐执刀枪,佥谓船主,倘随日人别往,即先与船上西人为仇。余又复弹压,着船主悬旗命日人速退。余即同船主在梯口与日人辩论,因见华军愤恨,恐其仇杀日人,遂禁止日人登船,惟持回大沽之说与日人相争。盖船当展轮之初,两军尚未开仗,今即决裂,揆诸公道,亦当请其返轮。故余与船主皆以为此事相合情,乃日人答以须回覆管驾。及舢板去后未及,即悬旗命高升船主水手即欧洲人等速即离船逃生。船主即悬旗回覆,答以华军羁留,不许离船。于是日舰即驶近高升一百五十蔑打之遥,随燃放水雷一响,大炮六响。水雷已中高升船旁,炸于煤舱,其时烟焰迷漫,不可辨认。余见大势已去,即呼诸人凫水逃生。是时高升船尾先沉,而日船尚陆续放枪炮轰击船中。华军知生机已绝,亦放枪回击。日船复下舢板满载日兵持枪而来,初犹以为来救船中难人。讵反将船上人攻击,并枪击凫水诸人,其立心险毒如此。时沉船中人亦对日人开枪,盖欲同归于尽也。计高升被击后约越半点钟久,即全船沉溺。倘日船悬旗着令停止时,断其锚链,假遵日人之命驶于近岸,则众军尚有生机。惟船主伙长等以船悬英旗,谓可有恃无恐,遂有保护船身之意,故不出此。至于船上华军,得生还者仅一百七十余人,其欧西人之逃生别处者则非我所知也。以上系汉君于六月廿八日在济物浦英领事署所缮之词,询为确凿可据。即此以观日人未下战书,先轰邻国商船,且枪毙逃难之人,实属违背公法,无理已极,乃日前有某西报谬引公法偏袒日人,是岂持平之论也哉。吾知公道存在人心,五洲之内自有月旦评也。(原本无标点——笔者注)
《叻报》译本作者系何人,所依何种底本,今已无从考证。幸运的是,汉纳根证言有一个日本官方的日文译本,题为《汉纳根ノ具申》*该译本收录于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海军省公文备考》之《明治27年战史编纂准备书类第22——高升号の始末及论评汽船益生号の件(1)》,第0496-0498页,现已在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全文公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日本官方将此译本的形成时间标注为在1894年7月24日至29日之间。(以下简称“日译本”)。经审阅,《叻报》译本与日译本成文时间相近,对高升号事件过程的记载又极为吻合,说明两者应为同一底本。令人生疑的是,此两种译本与现行孙译本出入较大,需要重新梳理高升号事件过程以探寻事实真相。
三、高升号事件过程之再考证
(一)高升号与日舰的遭遇经过
1894年7月23日(农历6月21日),高升号载有千余名清军士兵,12门炮以及军火弹药从大沽驶往朝鲜。
据《叻报》译本记载,7月25日(农历6月23日)清晨,在“将抵朝境,已望见韩属群岛”的地点,高升号发现一艘不明身份的船只向西行驶,“船式与中国定远师船相仿佛”。对此,日译本有相同记载,而孙译本无记载。
7点,据《叻报》译本记载,“又见一舰向济物浦而去”。日译本记载与之吻合,而孙译本对此亦无记载。
8点至8点10分期间,三种译本都记载了汉纳根在高升号上观察到两艘战舰尾随另一艘战舰绕岛而来,三舰同属大铁甲,但无法判断其国籍。
9点左右,三舰中位置处于最前面的一艘驶近高升号,汉纳根发现对方悬挂白旗,判断应为日本军舰,并注意到了对方有“扯旗示礼”的举动。对此,三种译本记载基本一致。而事实上,汉纳根判断失误,此船实为清军济远舰。
此后,汉纳根又出现两个至关重要的误判。
一是对日舰数量的误判。据《叻报》译本记载,汉纳根误判济远舰为日舰后,进而推测之前“由某岛绕出之三船皆为日本兵舰”。而之后日舰浪速号的驶来使得汉纳根深感高升号陷入四艘日舰的重围之中。在日译本和孙译本中,浪速号都被列为了“第四号日舰”。戚其章先生认为,对济远号身份的误判以及对方“扯旗示礼”举动的误解导致高升号高层“产生了麻痹思想”[4]。而据《叻报》译本记载,高升号高层的真实心态应该是“日船多艘”,“心甚不安”。
二是对日舰意图的误判。据《叻报》译本记载,汉纳根识别出日舰的同时,亦识别出之前遇到的向济物浦方向行驶的船只为中国军舰操江号。对于此事,日译本亦有相同记载,而孙译本却又无记载。另据7月25日随乘操江号的丹麦人弥伦斯的回忆,他曾在当日上午9点钟左右“见高升轮船为日本大铁甲三号拦住”[5]。由此可见,9点钟左右,高升号与操江号确可相互识别。而正是高悬龙旗的操江号的“及时出现”,使得汉纳根认为日舰的意图是“只追逐操江,非注意于高升,或不致于有他虞”。事后证明,汉纳根这一判断也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相较于孙译本,《叻报》译本对高升号与日舰遭遇过程的描述更为准确、细致、可信,将高升号决策者在与日舰相遇之后的心态变化暴露得一览无余。正是在恐惧兼有侥幸的心理作用下,当日舰浪速号悬旗鸣枪,勒令停轮时,高悬英国国旗的高升号立刻“遵命下碇”,相当配合,而这种心态又贯穿于高升号与日舰浪速号谈判过程的始终。
(二)高升号与浪速号的三次谈判过程
在高升号遭日舰浪速号拦截并击沉的过程中,双方共进行了三次谈判。
1.第一次谈判过程
据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日记的记载,在高升号停锚后,他派出人见大尉等人登船检查。人见大尉等人在确认高升号为英国籍船只后,要求船长高惠悌跟随日舰行驶。高惠悌表示同意,人见大尉等人遂下船返回浪速号。[6]
据船长高惠悌的证言,“日本军官离船回了浪速”,随后清军获悉了谈判内容,群情激昂,拒绝他往,要求返航大沽,“他们以手势相威胁,要割我们的头,刺我们,射击我们,他们挑选了一些人来看守我们执行命令。我们于是又发信号,请浪速再派小船来”[7]。
汉纳根证言对此事经过亦有记载。据孙译本的记载,“他们和士兵都喧嚷起来,用刀枪威胁船长、船员及所有船上的欧洲人,致船长不敢起锚。我又极力劝他们镇静,并请船长用信号请谈判的日本船再回来”;《叻报》译本作,“余转语华军,众情益愤,齐执刀枪,佥谓船主,倘随日人别往,即先与船上西人为仇。余又复弹压,着船主悬旗命日人速退”。日译本记载与之相近,不再赘述。
综合分析各当事人所述,可以厘清以下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所谓“清军胁持高升号”事件发生时,日军已经撤离高升号,并未在场目击。
第二,高升号上清军与英籍船方发生过冲突。船长高惠悌将此定性为“胁持”,并声称自己已处于清军看管之中。汉纳根承认冲突的存在,并认为由于自己的及时介入,事态发展已得到控制。
第三,清军并非是“请回日军,重启谈判”的决策者与执行者。汉纳根证言明确指出此决策是由他本人而非清军提议的,而具体执行者是船长高惠悌。船长高惠悌在证言中也提到“我们于是又发信号”,结合前文可知,高惠悌此处所说的“我们”显然不包括当时正处于敌对状态的清军。
2.第二次谈判过程
明确第二次谈判的地点与代表身份是揭露谎言、还原真相的关键所在。
第一,谈判地点问题。新发现的《叻报》译本披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即汉纳根不允许日军上船,所以第二次谈判是在高升号梯口处进行的,“余即同船主在梯口与日人辩论,因见华军愤恨,恐其仇杀日人,遂禁止日人登船”。日译本的记载也是在“梯口处”进行的谈判,同样是因为汉纳根担心清军会杀害日本士官。孙译本则未明确指出地点,仅记载汉纳根“这次亲自到跳板上与日本军官谈话”。而船长高惠悌则提供了一个重要旁证:“日军官靠近我们的船,我告诉他们带信给舰长,说华人拒绝高升号当作俘虏,坚持退回大沽口。”[7]
上述材料足以证实第二次谈判并非在高升号上进行的,在汉纳根刻意安排下,日军并没有再次登上高升号,也未与清军有所接触。故此,所谓“清军胁持高升号”发生之时,日军未在场;之后,日军也未能再次上船进行实地核实。
第二,高惠悌是否参加了第二次谈判的问题。据东乡平八郎日记的记载,在收到高升号信号后,他仍然指定人见大尉去参加第二次谈判。在了解高升号的要求后,“人见大尉告该船长说,既然如此,须等待本舰的命令”[6]。人见大尉在第一次登船检查时曾与船长高惠悌有过交涉,因此,断无错认船长身份的可能。
船长高惠悌的证言与东乡平八郎的记载相吻合,他直言是其本人与日军进行的第二次谈判,“日军官靠近我们的船,我告诉他们带信给舰长”[7]。而新发现的《叻报》译本亦可佐证这一点,“余即同船主在梯口与日人辩论”。可见,船长高惠悌确实参与了第二次谈判。
然而,在孙译本记载中,高惠悌却缺席了第二次谈判,因为此时他已经被中国军队控制,丧失了自由,是由汉纳根替代他参加的谈判,“船又来了,我这次亲自到跳板上与日本军官谈话。我告诉日本军官,船长已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兵士不许他这样做,军官与士兵坚持让他们回原出发的海口去”。
显而易见,孙译本中关于“船长丧失自由”的记载与日方记载不符,与当事人高惠悌的证言相矛盾,又与早出的《叻报》译本所述迥然相异,实属严重失实的虚构之词,不足为信。
3.第三次谈判过程
第二次谈判后人见大尉等人返回浪速号,又利用旗语信号与高升号进行过一次谈判。据东乡平八郎事发次日向司令官伊东祐亨所作报告,浪速号发信号令高升号弃船,高升号则要求送小艇过来,浪速号再发“可以彼之小艇前来之信号”,“商船答以我等不被允许”,东乡平八郎随即以“清兵胁迫船长拒绝我之命令”为由下令炮击高升号,高升号不久后沉没。
四、对“清军胁持高升号”说的三点质疑
综上所述,笔者对“清军胁持高升号”说提出以下质疑:
第一,日军证词并不能证明清军胁持了高升号。日军自第一次谈判结束撤离高升号后就再未登船,事发时不在场,之后又未上船实地核实,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认定“清兵胁迫船长”而下令炮击的依据也仅是高升号发出的旗语信号,并非日本军方的现场目击。事实上,日本军方并不具备搜集证据指证清军胁持高升号的客观条件,故此,日本军方于事后提供的关于“清军胁持高升号”的证词均属主观猜测,缺乏客观依据。
第二,汉纳根证言并不能证明清军胁持了高升号。早出的《叻报》译本与日译本均无直接记载“清军胁持高升号”,或“船长高惠悌丧失自由”,或与之类似话语;而晚出的孙译本中关于“船长丧失自由”的记载已被证实与事实不符,系伪造之词,折射出汉纳根证言文本在流传过程中遭到人为篡改,目的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嫁祸于人。
第三,高惠悌证言不足以证实清军胁持了高升号。事实上,高惠悌证言与汉纳根证言均可证实是高惠悌而非清军代表高升号参与了与日军三次谈判的全过程。正是在高惠悌、汉纳根等人的控制之下,在三次谈判过程中日本军方和清军自始至终都未发生过接触。第一次谈判,“与日人言者惟船主”,清军未参与;第二次谈判,高惠悌、汉纳根等人并未让日军登船,目的就是避免日军与清军发生接触;而第三次谈判是通过旗语信号进行的,日方的记载是两问两答,而在三种汉纳根证言中,对谈判过程的描述都是一问一答:日军要求弃船,高惠悌回复“华军羁留,不许离船”,日军随即开炮,缺少了“高升号要求日方送小艇过来接人,日方予以拒绝,反令高升号使用自身小艇送人过来”的这一对话环节。而在高惠悌证言中,对第三次谈判过程的描述也是两问两答,与日方记载相同,这说明即便是汉纳根也并不了解第三次谈判过程的具体细节,高升号上参与第三次谈判的只有高惠悌一人而已。故此,日军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并未与清军发生过任何接触,自始至终都是在和高惠悌等人谈判,何谈清军胁持高惠悌、夺取了高升号的指挥权呢?因此,并非高惠悌与高升号的命运掌握在清军手中,而是清军与高升号的命运始终掌握在高惠悌手中。
此外,日军与高惠悌对于第三次谈判过程的描述还存在一个明显的出入。从日方记录看,整个对话过程是“日方要求弃船→高升号要求日方送船过来→日方拒绝,反令高升号使用自己的小船→高升号回答小船被清军控制→日方炮击”;而从高惠悌的证词看,整个过程是“日方要求弃船→高升号回答小船被清军控制,要求日方送船过来→日方拒绝送船过来→日方炮击”。比较之下,高惠悌在证词中所述“清军控制高升号小船”这一重要情节在时间顺序上与日方记载存在明显出入,难以令人信服。日方证词与汉纳根证言均不能证明清军胁持了高升号,仅凭疑点重重的高惠悌证词是不足以证明清军胁持高升号的。
故此,三大核心证据证明力不足,日英等国所持的“清军胁持高升号”的论断难以成立。千余名爱国官兵生前命运不能自主,逝后失声不能自辩,这才是高升号事件最大的悲剧所在。
参考文献:
[1]陆奥宗光.蹇蹇录[M].伊舍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73.
[2]抄送驻长崎英国海事裁判所之高升号宣判书事[G]∥戚其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365-366.
[3]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723号附件三,丙号[G].东京: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3:361-367.
[4]戚其章.甲午战争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57.
[5]陈旭麓,顾廷龙,汪熙.甲午中日战争: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45.
[6]东乡平八郎击沉高升号日记[G]∥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六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32-33.
[7]高升号船长高惠悌的证明[G]∥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六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