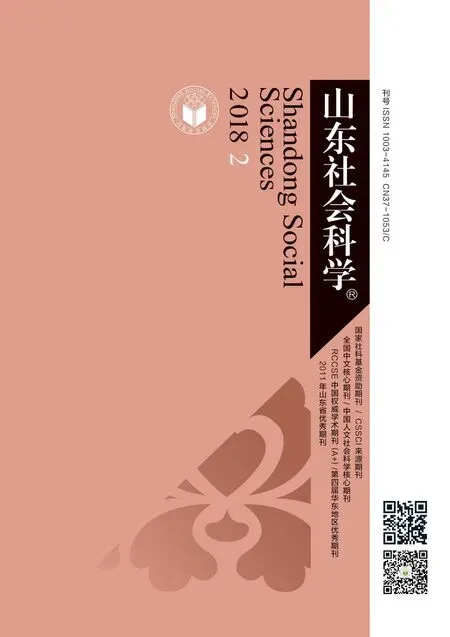社会变革视野下的大众文化定位: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众文化
2018-01-30官群
官 群
(山东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1)
媒体文化(Media Culture)的研究通常是指20世纪在西方社会出现的、针对大众媒体(主要是电视媒体,还包括出版社、广播和电影等)传播的影响力研究,这种影响力不仅包括舆论导向,还涉及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传播;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一词,被认为是媒体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重点强调了这种文化是大众媒体的产物*Jansson A., “The Mediatization of Consumption”, in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Vol. 2(March 2002), p.15-31.。大众文化,也被称为流行文化,特指20世纪早期至20世纪中期在西方现代工业社会中最早出现的,在20世纪末期开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一种市民文化传播现象。进入21世纪,凭借现代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这种文化传播现象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常见的大众文化类别又可以归为娱乐(包含电影、流行音乐、电视、游戏等)、体育、新闻、时尚与服饰潮流等。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伴随改革开放的浪潮而生的,横移西方大众文化传统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大众文化是不科学和不全面的。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提升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保障*杜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探索》2017年第2期。。
一、西方大众文化传统理论
纵观西方大众文化的理论研究,学者和思想家们对大众文化的态度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从早期的批判和全盘否定发展到部分肯定,再到后来的重新认识和积极肯定,大众文化逐渐被视为一种社会资源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早期,大众文化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愚蠢的”“表面的”“煽情的”或“腐败的”。罗森伯格和怀特在《大众文化》一书中提到,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低级的、微不足道的、无视了深刻的现实的文化。它往往忽略了性别区分,避免了对死亡、失败和悲剧的探讨,是一种单纯而简单的群众娱乐”*B. Osenberg and D. White, Mass Cul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Clencoe, 1957, p.22.。例如,在报纸新闻中大量的名流八卦和广告宣传,电视节目也已经用园艺、烹饪和其他生活类节目取代了高品质的戏剧节目,人们不断沉迷于关于名流琐事和与现实脱离的肥皂剧。对此评论家认为大众文化以大规模生产的无味的工业化文化替代了高品质艺术和民俗文化。伴随着大型媒体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大众文化也具有了全球的影响力。例如,在电影业,好莱坞文化和价值观影响着其他国家的电影制作,其电影制作强调震撼的价值和表面上的刺激特效,主题多集中描述侵略、报复、暴力和贪婪的人性本能,这些电影的模式均非常相似,似乎都遵循一个简单的标准化的模板,缺乏深层次的对话,人物也往往是简单的和超现实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众媒体创新技术促进了文化和社会的变革,大众文化的意义开始与群众文化、媒体文化、形象文化、消费文化等重叠。学者们将文化的中介作用研究转为对文化受到媒体运作方式影响过程的研究。社会各个领域都在依赖媒体传播其影响。约翰·斯特瑞(John Storey)对流行文化有六种定义,包括属于“高层文化”的遗产文化,比如简奥斯丁的小说与电视剧和查尔斯·狄更斯的许多跨界作品;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大众文化传播中具有重要的作用。*John Storey,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7 Edition). Routledge: New York, 2015, p 17.如果将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相提并论,这种文化形式被视为大众传媒和大众消费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可以被定义为民众的“正宗”文化。约翰·斯特瑞认为,大众文化有政治层面的意义;新古典主义霸权理论(Neo-GramscianHegemony Theory)认为它是民间文化视为社会下属群体的抵抗与社会主导群体利益的“斗争场所”;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t)的学者认为它可以是高层文化与民众文化的融合。
大众文化不断发展,形成潮流和漩涡,代表了以各种方式影响社会及其制度的相互依存的观点和价值观。其中,对大众文化的社会性和政治作用的研究最著名的两个学派为: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和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 。前者全面否认了大众文化在政治上起到的积极作用,大众文化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和逃避责任的大众娱乐,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认为文化应该具有批判性,而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则被他们认为是无思想性的,对社会的贡献仅限于充当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另一方面,伯明翰学派的思想家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大众力量,蕴含了青年文化、女性文化、工人阶级文化等,是一种可以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二、社会变革与西方大众文化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传统的文化理论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态度基本一致,代表人物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认为文化应该注重对崇高精神的追求和“精英主义”,只有“高层文化”才是具有内涵的,而大众文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而生的,其制作批量化、低俗和平庸,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应当予以抵制。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马克思·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认为大众文化的模式化和同一化使得人们丧失了对高品质艺术的追求,这是工业社会带来的负面冲击——休闲娱乐替代了对传统艺术的继承,电影和畅销书成为了人们追求的一种快感文化,大众文化丧失了艺术的严肃性和高雅性,是彻底的消费享乐的表现。但是,这些批判大众文化的理论家都不可回避地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即在宣扬自己是大众代言人的同时又极力贬低着大众,他们藐视大众文化的力量导致了在政治上失去了大众的广泛支持。对此,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指出那些脱离大众理解和体验的理论必然无法得到大众的认可,因为大众不愿意与对他们有贬低态度的政治结盟。
自二战后至20世纪中期,英国等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重要的社会变革,经济取得了全面的复苏,商业得到了稳步的发展,传媒技术日新月异。伴随着社会变革,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变革也在进行着。战后的人们向往平和安宁的生活状态,大众文化更多地走向了通俗化和娱乐化,其中流行音乐、广播节目、通俗小数、电影电视作品等大量涌现,借助日益发达的广播电视媒介在全世界范围迅速传播,受到了广大民众的追捧和喜爱。伴随着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一味地强调高层精英文化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和陈词滥调,对此伯明翰学派开始转向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伯明翰学派认为大众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消费的主要动力,从他们而来的大众文化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权力争夺、反抗霸权的表达。他们重新定义了“文化主义”的概念:从最初的文学研究方法转变为社会学研究方法,从对文学的评价转变为对文化(包括流行音乐、流行音乐、广播节目、通俗小数、电影电视作品)的评价。
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态度的巨大变化本质上反映了当时西方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首先,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西方社会更加注重民主发展,在商品化和传媒技术的推动下,以大众为主导的社会结构逐渐形成。大众消费促生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与大众文化相关的消费在整个市场独占鳌头,此时再对大众文化的一味批判成为对现实的否认;其次,在符合现实社会与市场需求的同时,伯明翰学派文化主义范式的转换与20世纪6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开始盛行存在密切的关系。这种对“文化主义”的重新定义是西方人文社科理论的重大变革,它从本质上体现的是社会存在的整体性、文化性和重叠性,文化革命呈现出社会历史活动的总体化结构变化。伯明翰学派的诸多代表人物的工人阶级背景能够更好地帮助研究者理解当时社会大众的实际需求和态度,是社会实践和成果的真实反映。
当代大众文化研究最著名的人物当属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明显区别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费斯克主张的“文化消费主义”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对大众文化探讨的深入和理解的提升,是以往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悲观主义的超越。其著作《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和《解读大众文化》(ReadingthePopularCulture)*[美]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强调了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起到的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他提出大众文化应当被视为“大众生产式文本”,如何促进大众文化消费和倡导积极快乐的大众文化精神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大众文化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消费市场的繁荣和消费精神的推广中,它还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力,体现在大众文化运动中对权力的抵抗和推动社会的变革中。费斯克归纳了两种社会变革模式——激进模式和大众模式。其中,大众文化的政治影响力是进步和微观的而非激进和宏观的,但是它可以被认为是激进的社会变革发生的基础。
费斯克的研究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认识,为理解和应用这种社会资源提供了正确的引导,为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价值。中国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阶段,一次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社会变革涉及到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多重方面。能否确保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品格和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积极影响和有效塑造大众主流的政治行为逻辑*张师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大众化与国家政治文化安全》,《探索》2017年第4期。,是中国社会变革方向的重要指引,也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执政长盛不衰的重大现实问题。大众文化的价值观走向与社会转型息息相关,对此进行深化研究和准确的价值定位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大众文化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同时也改变了大众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90年代开始,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率先出现了针对大众文化的消费,以大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消费迅速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然而,此时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一现象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秉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对大众文化采取了全盘否认和极度贬低的态度。大众文化被认为是一种思想麻醉,其内容毫无文化价值,完全是纯娱乐甚至是俗不可耐的,知识分子应当用精英主义的精神来抵制大众文化。
从中国社会变革与大众文化的发展角度来说, 中国的大众文化是在改革开放浪潮和现代化市场秩序建立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发展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市场经济带来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全方位的转变:商业化与城市化加剧,政治体制和文化教育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改变,并且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大众生活和大众文化。但是,刻板的理论横移和对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的不了解使中国早期的大众文化研究陷入了发展的困境。一方面,横移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批判,仅仅关注了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和娱乐性,而忽略了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的力量,以及其蕴含了文化性和意识形态的属性;另一方面,对中国“大众”的概念定位不准,没有从中国国情、社会环境和实际出发定位大众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单纯地移植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有违国情和民情。
当代中国处在经济与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众文化的兴起是当今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其发展态势将会伴随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逐渐增强。如何寻求一条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社会变革道路,同时保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特点,是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大众文化,作为反映现实社会需求和问题的最直接的方式,已经不单是文化的象征、观念和精神的反映,同时也是当代诸多马克思主义实践家彰显政治实践的空间。予以大众文化准确的价值定位, 必须将其与中国大众的实际需求、经济体制转型、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完善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研究,发展具有民族性与开放性兼顾、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与文化特色相结合的大众文化。
四、新时期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定位
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体现在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经济体制的变革带来思想意识的转变,本质是从符合原有经济的传统观念与新生产方式带来的新观念的变革。新的观念变革包括了思维方式、消费理念、价值观、家庭观和伦理观等的变革。只有配套的文化建设才能更好地解决新观念与传统观念产生的冲突,因为文化觉醒总是以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每一次社会变革之前,相匹配的文化建设是为社会变革开辟道路,为推陈出新的生产方式摇旗呐喊。除此之外,配套的文化建设可以影响社会变革的发展方向,加速变革的进程,以及对现实社会中存在和发现的问题予以及时的引导和干预,起到修正和规范的作用。
处在经济变革时期的中国面临着思想意识的转变与社会变革协调发展的问题,与社会变革同步协调发展的文化变革研究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主义以及批判大众文化的精英文化在中国没有共鸣,西方文化研究中对“大众”的认知和定义也同样不适用于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产生的背景和发展阶段具有自身的特点,在经济变革带来的社会与文化变革的背景下解析中国大众文化,开拓与中国社会变革相匹配的大众文化发展方向是近年来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邹广文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生成背景》一文中归纳了大众文化的六种基本属性,分别是(1)伴随现代工业文明所产生的、有别于之前的民间文化的“现代性”;(2)与消费市场和消费者偏好紧密相连的“商业性”;(3)以取悦大众为目的的“世俗性”;(4)工业化批量生产出来的“标准性”;(5)伴随现代传播手段而来的“时效性”;(6)以描述日常生活为主的“娱乐性”;同时,他指出全球信息一体化带来的媒体发展使得大众文化市场蓬勃发展,中国应当如何应对全球信息一体化浪潮并且保持大众文化健康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邹广文:《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生成背景》,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郭凤志在《中国特色大众文化研究》一文中提出西方语境中的大众文化与中国的“大众”的概念并非一致,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可否认地存在生产力水平较低、城乡差距客观存在、农村人口占比大等现实问题。*郭凤志:《中国特色大众文化研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在这种背景下的“大众”的概念与西方研究的“大众”有所不同,中国的大众包括了城市居民和广大的农村人口,大众文化如果只面向城市人口,就会失去它的现实基础。李明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我国当代大众文化价值观建设》一文中总结中国的大众文化建设要防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对大众文化生活的侵蚀,要避免低俗和腐朽的观念的文化作品对精神世界的恶劣影响,中国的大众文化发展要本着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和提高人民的思想精神文明为主要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大众文化作品中,让大众文化成为丰富百姓生活和净化心灵的文化食粮。*李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我国当代大众文化价值观建设》,《天府新论》2014年第1期。
发展新时期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要在借鉴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和资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与社会变革的实际进程,注重中国文化发展与运作方式,融入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开拓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大众文化建设:
第一,从中国人口构成的国情出发,对“大众”的概念精准地定位。大众文化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城市市民的需求,还应注重广大农村人口的欣赏品味,深入理解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满足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大众文化的协调发展。截止到2016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十分迅速,城镇常住人口已达到8亿2345万人,比2015年末增加2182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亿8973万人,减少1373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约为57.35%。中国的大众文化建设要适应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社会生活变化带来的消费需求和文化需求的变化,切实关注大众的社会生活变化,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消费产品,提升人民的文化品位。
第二,从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实际出发,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具有促进社会变革、引领社会思潮、修正和引导变革方向的作用。中国已经告别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世界接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也为文化开放和繁荣带来了新的契机。由于历史环境等原因,中国经历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急速且复杂的变化过程,变革体现在社会的基础型结构、前导型结构、社会生活方式结构和经济结构等多重方面,大众文化随着社会的变革而不停地被赋予新的意义。大众文化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产量最大、受众最多和影响力最大的消费文化,其蓬勃发展与中国所处的社会变革密不可分,两者相辅相成。一方面,倡导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途径应当是将其融入到大众文化之中,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喜爱,让人民自觉和自发地赞同与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起到引领社会思潮和提高全民价值观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变革与进步离不开大众的接纳与支持,大众文化的走向是人民群众对社会现状满意度的体现,理解和应用好大众文化这条通往人民生活的途径,可以建立正确的变革方向,促进变革成果的顺利转化和修正改革过程中的问题。中国文化正在面临着一场由转型而引发的新的文化价值观的当代重构,意在使我们能够站在多元文化视野中,自觉地审视定位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努力重塑能够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特质要求的自信包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价值观。*贾英健:《中国现代性发展中文化矛盾与价值观重构》,《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第三,从中国文化市场发展进程与运作方式出发,让大众文化建设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一致。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产生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建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可以说现在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放任大众文化完全走向市场化不适合现阶段的发展进程,因为中国的大众文化缺少了西方社会理性文化的洗礼,尚未建立起科学的发展方向和完善的市场管理体制,如果低俗的、三观不正的和盲目极端的思想得不到遏制,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建设不能是无政府的,应当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才能有利于提高大众文化素养,促进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
最后,从大众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新时期的中国大众文化既具有娱乐性、时效性、商业性、世俗性和全球一体化等大众文化的一般特征,同时又承载了中国历史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大众文化建设一方面不能闭关自守,应当合理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影响,但是也应当保持民族性和传统特色,这就塑造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多元性。多元的文化具有多重的价值观,有先进的价值观也有糟粕落后的价值观,大众文化建设的内容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提倡具有先进性和思想性的优秀作品,提高大众文化的艺术性和观赏性,促进大众文化健康发展,改善其中存在的不良价值导向,让文化市场发展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生动载体,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文化媒体实现传播,借助公益文化提高其渗透力度,利用大众文化市场实现其转化和落实,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