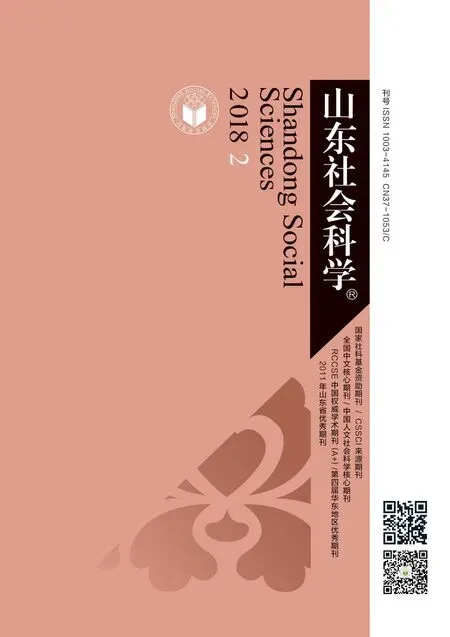《墨经》中的造物思想
2018-03-22李红贞潘鲁生
李红贞 潘鲁生
(山东大学 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墨经》是《墨子》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等篇章。《墨经》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许多学科领域,包括逻辑学、哲学、算术学、几何学、光学、力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以及伦理学等,以往学者主要从上述学科进行研究,忽略了其造物维度。事实上,《墨经》的形成离不开工匠的参与,因此,我们有必要从造物视角对《墨经》进行研究。《墨经》中的造物思想主要涉及造物功能、造物科技和造物之美三个方面。
一、《墨经》中的造物功能
义利统一是《墨经》造物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经上》明确指出,“义,利也。”*[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10页。关于《墨子》一书的引用皆出于此。《经说上》进一步解释为,“(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可见,在《墨经》中,义就是利,那么利是什么呢?《经上》解释,“利,所得而喜也”,其反面为害,“害,所得而恶也”。《经说上》则在阐释利、害时,将二者并举,说:“利,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恶,则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面对利与害,《墨经》明确指出,“欲正权利,且恶正权害”(《经上》)。高亨将其解释为:“人生而有欲,所欲者利也。但有利在前,宜加权称,有利则欲之,不有利则勿欲之,有利则取之,不有利则勿取之,斯乃不失其宜矣……人生而有恶,所恶者害也。但有害在前,宜加权称,有害则恶之,不有害则勿恶之,有害则除之,不有害则勿除之,斯乃不失其宜矣。”*高亨:《墨经校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也就是说,趋利避害是天下人的本性,而义、利的对象则是天下,它们维护的是天下百姓之义、利,所以要贵义尚利。墨子贵义尚利的目的是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害,他明确指出,“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兼爱中》)。
在墨子看来,为义的途径主要有谈辩、说书、从事,“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其中,从事就是造物活动,也就是说,造物活动能够为天下兴利除害。造物活动作为一项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其出发点就是为天下兴利除害。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正体现出墨子对造物功能的重视和强调。
《墨经》中的造物功能集中体现为实用功能,并发展出与之密切相关的节用功能和经济功能,三者联结在一起,彰显出器物的使用价值。
造物活动讲究制器为用,《说文解字》将“器”解释为:“器,皿也。”*[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9、104页。皿又意为“饭食之用器也”*[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9、104页。,一个“用”字集中体现了器物实用的、功利的价值取向,这也是人类社会最早产生的价值形态。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力量异常渺小,面对自然界中洪水猛兽等种种危险,不得不采取趋利避害的方法,从而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林惠祥认为,“原始的知识系统是极为实用的系统。他是半自动的,直见之于行为;而不就本身加以思虑。”*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3页。故此,造物活动从源头上说,一开始就打有极大的实用性烙印。黑格尔也说过:“人类有了种种需要,对于外界的‘自然’,结着一种实用的关系。”*[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由此可见,在造物活动之初,就已经天然地具有了实用功能。
在中国传统的制器思想中,关于实用、功利的思想比比皆是。《周易》多次论述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周易·系辞上》),“利用为大作”(《周易·益卦初九·爻辞》),“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周易·系辞上》),“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周易·系辞下》)从这些阐释“用”“利”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早就意识到器物实用功能的重要性,并把它当作是制器思想的核心。在漫长的器物发展历史中,实用功能始终居于第一位,是器物的本质所在。韩非子认为瓦器“至贱”,但“不漏可以盛酒”,比“至贵而无当,漏不可盛水”的“千金之玉卮”更为实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管子则从造物者角度出发,认为“古之良工,不劳其知巧以为玩好。是故无用之物,守法者不生”(《管子·五辅》)。张道一明确指出“物以致用”是“人的造物活动的目的和出发点,不论我国的先秦诸子还是古希腊的先哲们都关注过这个问题,并非是今天才提出的”*张道一:《走进“人化的自然”——〈设计艺术经典论著选读〉导言》,载奚传绩编:《设计艺术经典论著选读》,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器物的实用功能说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人类的需求是手工艺造物活动产生和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认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造物活动的目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造物活动首先满足的是人类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理需求。
在衣饰方面,《辞过》篇中说:“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凊。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棞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煖;夏则絺绤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在真正的衣服未出现之前,古代先民身着动物皮毛,用草编制绳带扎衣服,但不能在实用性上达到真正便利。于是,“圣王”教人们制作出丝麻布帛来做衣服,使身体更为舒适。
在饮食方面,墨子认为食物是用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辞过》)的,他在《七患》篇中说,“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这句话表明了食物是人们赖以生存和从事生产的基础。《周易》中《需》卦有云,“需者饮食之道也”,同样也体现了人类对维持自身生命的渴望。
在住的方面,墨子在《辞过》篇中指出:“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古代先民出于抗拒湿气、风寒、雪霜雨露的需求,创造了宫室建筑。出于别男女之礼的需求,对宫墙进行加高。《韩非子·五蠹》中也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在行的方面,《辞过》篇中说:“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由不知舟车到圣王作舟车后的行的便利,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这种“利多”也是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的。

器物的实用功能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人类基于生存和发展的必然的价值选择。“器物中所谓的‘实用性’,不是可有可无或是谁赋予的东西,而是生命价值的体现和投射;这种实用价值作为人类社会最古老而又最永恒的价值,是不可背离的,也是生活之物的根基。”*李砚祖:《生活之物与艺术之物——中国传统陶瓷的艺术与文化》,《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造物的实用功能在墨子那里发展到极致,形成一种节用功能。墨子非常推崇节用,认为“节用”是古之圣王之道,“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节用中》)。“节用”思想是墨子学说的重要内容。
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非常强调造物的节用功能。墨子认为,“仁者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在他看来,凡是利于人的就是有用的、好的,需要积极鼓励提倡的;凡是不利于人的,就是无用的、坏的,要加以反对和制止。墨子认为当时统治者为了豪华的宫室、华丽的衣服、轻便的舟车等,“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辞过》),这种骄奢淫逸的作风违反了圣人之道,也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非乐上》),容易引起社会混乱,危害政治统治,所以于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统治者“不可不节”(《辞过》)。

墨子的节用思想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具有积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尚不发达,很多底层人民连基本的衣食住行都难以保证,统治者却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享受,用金银、玉石、象牙等贵重材料制作器物,还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装饰器物,无疑加剧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负担,不仅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实际上也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节用可以节约有限的社会资源,提高利用率,以免耗费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不仅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治,还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司马迁所评价的,“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页。
节用功能反映了人对器物的态度,是墨子强化器物实用功能的结果,这也是器物对人的价值的体现。无论是实用功能还是节用功能,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器物具有经济功能,即器物能够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起到耗费少而收益多的效用。效用是指器物的功效和作用,这是器物实用功能的直接作用和结果。衡量一件手工艺品的经济效用就是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其实用功能,能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

墨子作为亲身参加生产实践的工匠,深切地意识到器物经济功能的重要性,所以在《墨经》进行了深入阐述。事实上,每一次生产力的巨大变革,都必然伴随着器物经济功能的重大发展。从原始造物到春秋战国时期,先后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都显示了器物在所处时代所产生的巨大效用。原始人类制作和使用石器等工具,使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铜器使人类从原始社会迈入奴隶社会;铁器使人类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留下了器物经济功能的烙印。
二、《墨经》中的造物科技
造物科技推动着造物活动的发展,“莱斯利·怀特认为‘一种文化是由技术的,社会的和观念的三个子系统构成的,技术系统是决定其余两者的基础,技术发展则是文化进步的内在动因’。就工艺文化而言,技术的子系统确实具有一种新生的力量,而且是工艺文化中活跃着的基础部分”*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造物科技作为一种巨大动力,始终为造物活动的目的和需要服务,张岱年指出:“墨家的自然科学研究从属于墨子的‘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最高宗旨。”*张岱年:《论墨子的救世精神与“摹物论言”之学》,《文史哲》1991年第5期。《墨经》集中反映了墨子的造物科技,在科学思维、科学认识、科学方法等方面具有深刻的见解,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高度发达的造物科技。
《墨经》以兴利除害的价值标准为导向,重视实践应用,使《墨经》体现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范岱年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这段话揭示了中西方科学发展路径不同的原因,不过爱因斯坦显然未考虑达到《墨经》的科学成就。《墨经》中的造物科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与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接轨。首先,中国传统造物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经验为基础。《墨经》造物科技虽然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但是又超越了经验,表现出强烈的逻辑性,只不过其逻辑研究侧重于实质分析,与西方的形式逻辑有所不同。其次,《墨经》重视科学实验,通过一系列观察和实验揭示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力学、光学等方面形成了具有一定系统性的自然科学理论。这些都是科学思维的产物,也是《墨经》造物科技区别于中国传统造物科技的显著特点。


《墨经》还阐释了“法”,即现代意义上的生产标准这一具体的科学方法。《经上》提出:“法,所若而然也”,《经说上》进一步解释为:“意规员(通“圆”)三也俱,可以为法。”也就是说,遵循“法”来行事造物,则物成其然,不循法则物不成其然,以圆形为例,意欲为一圆形为目的,圆规为工具,圆形为结果,通过操作运用而使三者具备,无所参差,才可谓之为法。*参见高亨:《墨经校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墨子非常重视生产标准,提出“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平以水(依孙诒让说补)。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已。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法仪》)。这句话揭示出“法”的三个层次:一、法仪是工匠造物活动成立的前提,离开法仪,造物活动将无法进行,它规定了器物制造的方法和准则;二、工匠的操作技能影响其如何遵循法仪,“巧者”能够严格地遵循“法仪”,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不巧者”尽量效仿,也胜过乱来;三、工匠需要凭借矩尺、圆规、墨绳、悬垂、水平仪等生产工具来遵守方、圆、直、正、平等具体生产准则。也就是说,墨子眼中的生产标准是生产方法、操作技能和生产工具三者的统一。
《墨经》还比较了生产标准的同异,以及如何处理同异问题,指出“法同则观其同。法异则观其宜”(《经上》)。可以解读为若生产标准相同,则审视其相同之处,不同,则选择适宜的生产标准。生产标准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人们最初在制作器物时,往往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制作方法也各有不同,人们对偶然性进行探索和研究后,逐渐发现其中的规律,并对其进行总结和推广,使之成为一种行业内部共同遵守的标准,在还没有成为共同标准时,则选择最适宜发挥器物最佳功能和价值的标准,从而达到省时、省力的目的。当然,这样的生产标准往往也代表了更高的技术水平,生产实践的发展也会促使标准的变更,技术越成熟、越先进,标准也就适宜、越完善。
生产标准首先必须具有“合理性”才能够要求“合法性”,“合理性”一方面是标准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行业内部经过充分商讨,最终达到观念一致的结果。“法”字强调了其“合法性”,要求行业内部必须遵循。墨子甚至将法仪与上天意志相类比,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天志上》)这样一来,法仪不仅是工匠制造器物必须遵循的法则和标准,还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强制性。
三、《墨经》中的造物之美
《墨经》中的造物之美不是抽象独立地存在的,而是与造物功能、造物科技等综合在一起构成造物活动的主要内容。造物活动源于人们直接的生活需求,自诞生之日起就体现出一种本元文化的特点。本元文化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是“科学技术、生产能力、人文素质、审美水平和经济条件的大综合,从而表现出实用性、艺术性、技术性、风尚性、经济性的统一”*张道一:《张道一选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72页。。正是由于这种统一,实现了造物之美与造物功能、造物科技的结合,从而夯实了造物之美的基础,扩大了造物之美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在本元文化中,实用性和审美性始终统一在一起,只不过二者既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从属的关系,其中,实用性是第一位的,审美性是第二位的,在实际情形中,实用性和审美性体现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自古以来,器物的实用性就是评价其审美性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思想中大多对器物的功用是肯定的,并积极倡导。“孔、孟、老、庄、荀、墨、韩、都从不同角度对此发表了自家看法,总体上,大家都认为实用是关键,是否有用是衡量事物美与不美的标准。只有有用的事物才可能是美的事物,不能体现实用价值的事物是不能与美沾边的”。*曹耀明:《设计美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可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用”和“美”是分不开的,“用”在功利层面上体现了一种合目的性的“善”,在无功利的层面上体现了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即“美”,中国传统思想向来讲究美善统一,有用为“善”,“善”即为“美”,因此,“用”和“美”是相通的。西方“有用便是美”和功能主义等主张虽然混淆了实用性和审美性,却也表明了用与美的联系。《墨经》对“利”“用”的强调使造物功能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但是因为其满足了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合乎人的目的性,不仅使人得到物质上的利益,还得到了情感上的愉悦和满足,从而体验到造物之美。另外,器物的审美功能必然地具有某种目的,即使表面上看似无目的,却依然潜在地符合一定的目的性,也就是说,器物的实用性和审美性在造物目的上是相通的,它们最终都是要为人们的各种生活需求服务的。造物之美从来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美,纯粹意义的美是人为分离的结果,那些在经济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实用性的需求早已得到极大满足,他们有能力去追逐“无用的”美,并利用自己强大的话语权把美局限在纯粹的层面,这无疑损伤了美与实际生活的广阔联系。只有明确器物的实用性始终是审美性基础的观念,才能更深刻地认识造物之美。
如果说造物功能从实质内容上体现了造物之美,那么造物科技则从形式上与造物之美联系起来,这也是功能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功能关系的体现。一般来说,器物若符合造物的科学原理和技术手段,其在实现功能的同时还往往体现出一种形式美。形式美是科学思维、科学认识、科学方法等造物科技综合作用的结果。墨子运用科学思维来认识和改造自然,不仅从形式上感知自然界中的各色事物,而且还从本质上进行深入研究,从而获得了许多形、数、方位等方面的科学认识。在形的观念方面,如“圜,一中同长也”,“方,柱隅四讙也”(《经上》),并进一步点明其成形工具,“圜,规写攴也”,“方,矩见攴也”(《经说上》)。在数的观念方面,如“倍,为二也”(《经上》),并从相反的运算法则进一步阐释,“倍,二尺与尺但去一”(《经说上》),再如,“一,少于二而多于五,说在建位”(《经下》),并进一步说明运算关系,“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经说下》)。在方位的观念方面,如“宇,东西家南北”(《经说上》),“长宇,徙而有处,宇。宇,南北在旦有在莫,宇徙久”(《经说下》)。这些科学认识抽象地揭示了自然中的美。在具体的造物过程中,墨子将这些科学认识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表现出来,从而在形式上表现出对称、均衡、简洁、精确等造物之美,同时也表现出质朴、纯然的生活形态。换句话说,表面上的形式美是内在科学逻辑的体现。当然,这种形式上所具有的美从深层来讲也是出于实用的需要。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通过“数”“和谐”“秩序”等概念来阐释美,与《墨经》的造物之美有异曲同工之妙。
功能和形式虽然“限制”了造物之美,但是人们在进行造物时,精神上处于自由自在的状态,自发地把内心的情感、理想、意愿等审美内容倾注在造物活动中,在获得更多审美感受的同时,也借助器物的功能和形式传达了自己的审美理念。
四、小结
通过对《墨经》的深入挖掘,我们发现造物功能、造物科技、造物之美构成了《墨经》的三重造物维度。其中,造物功能由对义利的阐释生发出来,造物科技并不涉及具体的造物流程和方法,而是从基础的科学原理、科学方法等方面揭示出造物的科学逻辑,造物之美甚至不涉及任何装饰(当然这也是墨子明确反对的),而是与造物功能、造物科技联结起来,从质的层面揭示出功能美、科技美的内容。它们深层阐释了造物活动对人、对生活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