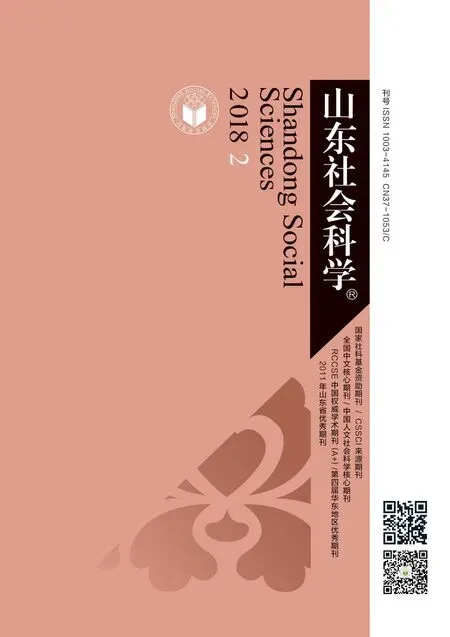从丰子恺与竹久梦二看现代东方绘画的共通性与艺术个性
2018-01-30郭尔雅
郭尔雅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中日绘画艺术之间一直存在着相互的影响和深层的关连,这一点我们通过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著名画家、诗人竹久梦二和中国的现代艺术家丰子恺的绘画,便可窥见一斑。竹久梦二的绘画源于对诗画合一和简笔淡墨的中国文人画,尤其是自文人画衍生而出的俳画中“非人情”之美的承袭。同时梦二也不仅局限于此,他抛开了文人画的风雅和俳画的禅意,将作画题材广泛化、通俗化,使其更贴近大众的审美趣味,摆脱行将衰落的文人画的母题,焕发出了蓬勃的生命力与吸引力,而正是这样的生命力与吸引力,虏获了赴日学画却画途难定的丰子恺的心神,开启了他的绘画旅程。
一、《梦二画集》对丰子恺的启发
丰子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历时曾经说过:“一九二一年春我搭了‘山城丸’赴日本的时候,自己满望着做了画家而归国的。到了东京窥见了些西洋美术的面影,回顾自己的贫乏的才力与境遇,渐渐感到画家的难做,不觉心灰意懒起来。每天上午在某洋画学校里当model(模特儿)休息的时候,总是无聊地燃起一支‘敷岛’,反复思量生活的前程,有时窃疑model与canvas(画布)究竟是否达到画家的唯一的途径。”*丰子恺:《〈子恺漫画〉题卷首》,载《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就在丰子恺对自己西洋画的“才力”和前路深觉怀疑的时候,他在东京神田的旧书店偶遇了《梦二画集·春之卷》。梦二简单的毛笔速写和简净的随笔题诗,让数月来囿于西洋画的浓墨重彩和技法技巧的丰子恺震颤,他说梦二的画“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我的眼,又以诗的意味感动我的心”*丰子恺:《绘画与文学》,载《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87页。。想来这样的感动,更多是源于他们相似的审美心胸和相近的文艺涵养。丰子恺此时的犹疑正是梦二十数年前的犹疑。他们同样在来不及认清自己的优长和确定自己艺术走向的时候,被涌入画坛的西洋画风裹挟着扑入了油画的修习。在学习中否定,在否定后抉择。这一过程,梦二用了整整4年,当毅然舍弃油画转投插画之后,他说:“想要表现绘画内部的感伤,未必非油画不可,我今后要画的插画,便是无声的诗。我不愿像日本的某某画师那样,成为用预定的颜料、预定的颜色和构图,大幅度地肆意填涂的健全派。我想要将单纯的官能感受用单纯的线条原原本本地再现出来。”除此之外,他还坦言:“与创作一幅绘画相比,我更愿意和少女谈笑度过一日。”*参见竹久梦二的《梦二画集·夏之卷》(东京洛阳堂明治43年版)所附《〈梦二画集·春之卷〉批评》一文。他的任情随性和纤细的感受性,注定了他不可能被囿于油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丰子恺与梦二是相似的。他有着对人间世相敏锐的感知、对万事万物广博的同情,以及蕴藏于心的东方诗情和文人意趣。他的老师夏丏尊盛赞其对生活高超的咀嚼玩味能力,朱光潜也曾指出:“子恺本来习过西画,在中国他最早木刻,这两点对于他的作风有显著的影响。但是这只是浮面的形象,他的基本精神还是中国的,或者说,东方的。”*朱光潜:《丰子恺先生的人品及画品》,载《丰子恺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现在看来,确也只有草草速笔的简洁才能追赶得上他们瞬息变幻的丰富感受,也只有水墨毛笔的婉致才足以抒写他们心中俄顷而起的诗情。与其说梦二的画影响了丰子恺的创作,毋宁说梦二以先行者的姿态激发了丰子恺的艺术潜能。
在寻找艺术去向一途上,丰子恺显然比梦二幸运,因为他得遇了绘画理念相对成熟的竹久梦二和已经编录成集的《春之卷》。他就这样怀揣着《梦二画集·春之卷》和因《春之卷》而种入心中的艺术种子回国,临行前还不忘嘱托友人黄涵秋替他留意梦二的其他画册,当《梦二画集》的夏、秋、冬三卷连同《京人形》《梦二画手本》寄到手中时,丰子恺自然喜不自胜。他在白马湖畔春晖中学教学之余,在《梦二画集》的启发之下,将平常所萦心的琐事细故一一乘兴描出,有时把平日所信口低吟的古诗句词也试译出来,译作小画,粘在座右,随时欣赏。丰子恺带回的艺术种子在他传统文化修为的滋养之下发芽,他这些仅为自娱的小画,获得了夏丏尊的盛赞,并由朱自清将其拿去发表,郑振铎也是辗转求画并将其刊载于《文学周报》上,还给这些画冠上了“漫画”的题头,从此,“子恺漫画”风靡全国。
丰子恺漫画的盛行引起了人们对丰子恺和梦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并对其进行影响和异同的比较。周作人便多有丰子恺的画“有点竹久梦二的气味”“似出于竹久梦二”“形似学竹久梦二”之类的评判,朱自清也常将丰子恺与梦二做对比以勉励他出印画集。一直到近年来出版的关于梦二的读物以及见载于杂志的研究论文,也都绕不开丰子恺与竹久梦二的关系。其中刘柠《逆旅——竹久梦二的世界》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梦二的一些重要材料,认为:“‘子恺漫画’正是以‘梦二式美人’为母体和发酵剂的艺术变种。”*刘柠:《逆旅——竹久梦二的世界》,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李兆忠从“寥寥数笔”“诗的意味”和“融合东西”三个关键词阐释梦二和丰子恺相近的艺术风貌、艺术追求和艺术理想;*李兆忠:《东方诗魂的共鸣——丰子恺与竹久梦二的漫画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1期。牟健则从二人绘画的表现形式、题材和审美等角度论述其艺术风格的差异,并从生活经历、文化背景和性格气质等方面论证其艺术风格差异的原因。*牟健:《浅析丰子恺和竹久梦二绘画艺术风格的差异性》,《台州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这些评说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只是简略地、印象性地指出了丰子恺与竹久梦二之间的关联,而要真正明白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与根本差异,我们还需要从绘画的类型、描绘的手法中进行细致的比对,更需要从审美意趣和美学思想中作出深层的挖掘。
二、绘画类型和表现手法的比较
关于漫画,毕克官、黄远林在《中国漫画史》中指出:“讽刺与幽默是它最突出的艺术特点,也是漫画特有的艺术功能。”*毕克官、黄远林:《中国漫画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然而丰子恺的漫画中,大部分却是描画那些让自己有感于心的所见所闻所思,其中讽刺与幽默的成分并不算多。毕克官和黄远林将这类漫画称作“抒情漫画”,并认为丰子恺“是抒情漫画这一画派的开创者”*毕克官、黄远林:《中国漫画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而丰子恺则将漫画作了更为广义的界定,即:“漫画是简笔而注重意义的一种绘画。”*丰子恺:《漫画的描法》,载《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页。此外,他还将漫画分为三种:宣传漫画、讽刺漫画、感想漫画。余连祥在《丰子恺美学思想研究》一书中写道:“在中国的漫画史上,讽刺漫画和宣传漫画一直比较发达,而‘感想漫画’几乎是丰子恺独创的。”*余连祥:《丰子恺美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1页。他指出,“感想漫画”是丰子恺创作最多、艺术性最强、最富于特色的漫画,正是这批“感想漫画”奠定了丰子恺在中国漫画史上无法替代的地位。然而所谓的“感想漫画”或者“抒情漫画”真的像毕克官、黄远林以及余连祥所说的那样,是丰子恺的独创吗?丰子恺认为“感想漫画”就是“吾人见闻思想所及,觉得某景象显示着一种人生相或世间相,心中感动不已,就用笔描出这景象,以舒展自己的胸怀”*丰子恺:《漫画的种类》,载《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74页。。根据丰子恺的界定,我们回看丰子恺极尽赞美的《梦二画集》,再从绘画的特点和表现方法上对丰子恺与竹久梦二加以对比,就会发现《梦二画集》中的简笔画大都属于丰子恺所说的“感想漫画”,而丰子恺的“感像漫画”也与《梦二画集》极为相似。例如丰子恺的《生机》,描画从破墙砖缝里生出的一株小草,这是丰子恺有感于天地的好生之德和小草的求生之心而作的。梦二的《鸟儿的标本与女子的贞操》则将一只鸟儿的标本和一位微微垂首的娴静女子画在一起,不禁让人感慨:那些谨守贞操的女子不就如同被剥制固定在标本架上的鸟儿吗?美则美矣,却丧失了生命与活力。这样的画作虽不过寥寥几笔,画面极为简单,却能够引发人深切的感慨和内心的共鸣。
在“感想漫画”上,丰子恺无疑受到了竹久梦二的影响和启发,此外关于丰子恺所界定的“宣传漫画”,二人也有着或多或少的牵连和值得比较之处;也正是从“宣传漫画”的比较中,我们才得以确定对丰子恺和竹久梦二进行影响研究时必须划定的时间界限。
丰子恺虽然也说:“争斗是人类生活的变态,宣传漫画是漫画的变态。”“漫画的本体,应该是艺术。” 但他仍然说,“我们不妨为正义人道而作宣传漫画。”*丰子恺:《漫画的种类》,载《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85页。事实上,他也的确创作了大量的宣传漫画。在全民抗战的特殊历史时期,几乎所有的漫画都是宣传抗战的主题,丰子恺也以笔为刀,作了不少鼓舞士气民心的宣传漫画。例如他那幅著名的断树抽枝的漫画,画面上是一棵被砍伐的大树在春天抽枝发芽的景象,画上题诗:“大树被砍斩,生机并不息。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这便是为宣扬中华民族顽强不息的精神而作的宣传漫画。同时,他还写下《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谈抗战艺术》之类的文章,都是在论说漫画对抗战所能发挥的积极意义。此外,《护生画集》也属于宣传佛教思想的宣传漫画,其中多有教诫的意味,而《护生画集》的创作几乎贯穿着丰子恺的整个漫画生涯。
竹久梦二也有过创作“宣传漫画”的时期,但他很快就完成了自己艺术的转型。梦二在17岁时怀抱艺术理想进京,因是违背父命,他并没有从家中获得多少经济资助,只得工读生活。送报纸、牛奶,甚至做人力车夫,这些经历让他对底层民众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同情,加之基督教人道主义和博爱思想的影响,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了社会主义,并与其时活跃的左翼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左翼知识人安部矶雄,普罗作家、左翼社运活动家荒畑寒村等相从甚密。这期间,他在社会主义运动机关杂志《直言》上发表反战插画,后又在《光》《平民新闻》等报纸上登载过许多作品。例如,《战争与花》中,那战地上荷枪负弹的兵士嗅闻手中野花的画面让人愈觉战争的残酷;在那幅最初牵动丰子恺心绪的《同班同学》中,人力车上的贵妇人和背着孩子蓬首蹒跚的贫家女擦肩而过的场景,则让人悲感阶级的不平等;他还写下了《山麓下的原野》这样直接讴歌革命的短文:“灼灼欲燃的胡荽花兀自盛放着。在原野上遇见这花,我就像遇见了革命者一样地欢喜。”*竹久梦二:《梦二画集·春之卷》,郭尔雅译,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页。然而随着当局对左翼思想钳制的强化和《平民新闻》等社会主义刊物的被迫停刊,梦二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失去了平台,直至1910年“大逆事件”发生,幸德秋水不幸罹难,梦二自己也作为“大逆事件”的参与嫌疑人被处以两日拘留,这迫使梦二完成了彻底的艺术转型。他消退了社会主义者的积极和热情,将对社会普泛关照的眼光收缩到对个人忧愁和虚无情绪的抒发以及对美与爱的追求上,他柔化了描绘过反战宣传画的利笔,转入了美人画,开始描绘思妇的闺情和青春的感伤。自此他的画似乎笼上了一层挥不开的轻愁,画中的美人大眼似泣非泣,腰肢纤弱欲折,神情空茫得像要随时消失。这样的画一经问世,便俘获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心。
而丰子恺所激赏的梦二画作,却是那些“专写深沉而严肃的人生滋味,使人看了慨念人生,抽发遐想”*丰子恺:《艺术漫谈·谈日本的漫画》,载《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18页。的作品,这指的显然是早期作为社会主义青年的竹久梦二的作品。至于梦二的美人画能否同样吸引丰子恺的目光,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丰子恺自己从未有过阅读梦二美人画的记载,他的藏书中也没有梦二的美人画,也许他终其一生也无缘得见“梦二式美人”,也许他的选择取向自动将美人画排除在外。无论如何,在我们将竹久梦二与丰子恺进行比较研究或影响分析的时候,绝不能简单将梦二画甚至是梦二的美人画和丰子恺的漫画进行对比。我们必须为两人的关联研究和比较研究划定时间界限,要明确意识到,是倾向社会主义思潮的早期的梦二画作对丰子恺产生了启发与影响。
而关于漫画的表现方法,丰子恺将其总结为:写实法、点睛法、比喻法、夸张法、假象法、象征法。其中,比喻法、夸张法、假象法、象征法多运用于宣传漫画和讽刺漫画中,而写实法与点睛法则多用于“感想漫画”,而这也正是竹久梦二的绘画中最常出现的表现手法。
所谓写实法,就是“漫画家在日常见闻中,选取富有意义的现象,把它如实描写,使看者能在小中见大,个中见全”*丰子恺:《漫画的描法》,载《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页。。如丰子恺的《父亲的手》,整个画面,只有一只用握毛笔的姿势握着钢笔的手,民国十二三年,钢笔刚刚流行,可那时候的父亲们却还保持着握毛笔的习惯,于是就有了这样有趣的画面。而竹久梦二的《晚归》中,丈夫归家,放下雨伞和包袱,举起小儿笑闹,妻子系着围裙立在一旁笑而不语,大约早已做好了饭菜等丈夫回家,尽管丈夫的裤子上还打着补丁,显见是生活拮据,可我们还是能够轻易感受到一家和乐的气氛。另一幅题词“青色的果实上,朝露湛然,晨起的女子,妆发慵懒”的画上,描绘着清晨的路边水果摊旁,妆发凌乱的女子买水果的场景,这在我们的生活中极为常见。
而点睛法则是指“描写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而加以警拔的题目,使画因题目而忽然生色,好比画龙点睛”,点睛法与写实法的不同在于“写实法靠画本身表现,并不全靠题目;点睛法则全靠题目。没有了题目,画就失却精采”*丰子恺:《漫画的描法》,载《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09页。。例如丰子恺的一幅画中画的是在树下卖香蕉、橘子的小贩,以及迎面走来的两个小学生,其中一个伸手指点着小贩,这样的场景原本极为平常,但有了《去年的先生》这样的画题,就变得耐人寻味了。而竹久梦二的画中,最初让丰子恺惊叹的那幅《同班同学》,便属于点睛的画法,画中坐着人力车的贵妇人和背着孩子的贫家女擦肩而过,原本是街上最普通的场景,可添上《同班同学》的题目,便会让人感慨良多。而在《她的窗》这幅画中,只有一年轻男子坐在山坡上目视远方的情景,并无特别之处,但以《她的窗》点题,便可以给我们无数关于恋情的联想。
在“感想漫画”“宣传漫画”这样的绘画类型以及写实法、点睛法这样的表现手法上,丰子恺在对竹久梦二加以承继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践创新和理论概括,对中国漫画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指导意义。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丰子恺在接受竹久梦二影响时的取舍和倾向性,这就需要我们从二人的思想基础和审美意趣方面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
三、儿童诗画与童真之美
众所周知,竹久梦二和丰子恺都创作了大量的描写儿童生活的绘画作品。他们熟知儿童的举动,深谙儿童的心理,同时又对儿童的特性和童真的世界满怀喜爱与向往,这成为他们作品中诗意与趣味的重要来源。
对于儿童,丰子恺有着深刻的论述,他认为:“他们没有目的,无所为,无所图。他们为游戏而游戏,手段就是目的,即所谓‘自己目的’,这真是艺术的!他们不计利害,不分人我,即所谓‘无我’,这真是宗教的!慎勿轻轻地斥他们为‘儿戏’!此间大人们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利己的,都是卑鄙龌龊的,安得像他们的游戏的纯洁而高贵呢!”*丰子恺:《告母性(代序)》,载《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关于这里所说的只为游戏的游戏,丰子恺和竹久梦二在绘画中都有表现,例如丰子恺《快乐的劳动者》中努力搬凳子拼建火车的两个孩子、《建筑的起源》中认真搭建积木的瞻瞻,如梦二的《孩子的国度》中骑竹马、放风筝的孩子,他们都全身心地玩乐,忘记自己也忘记辛劳,却有着成人难及的纯粹与乐趣。
孩子也将宇宙万物视作平等,丰子恺说:“天地创造的本意,宇宙万物原是一家,人与狗的阶级,物与我的区别,人与己的界限……这等都是后人私造的。钻进这世网而信受奉行这等私造的东西,至死不能脱身的大人,其实是很可怜的、奴隶的‘小人’;而物我无间,一视同仁的孩子们的态度,真是所谓‘大人’了。”*丰子恺:《告母性(代序)》,载《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正如丰子恺的漫画《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中,把自己软软的鞋子穿在凳子脚上拍手唱着“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小阿宝,就像竹久梦二的诗画中对着死去的花儿吹喇叭、对着布娃娃认真说话、和小狗分饰角色演士官和马的孩子们,他们难分主体、客体,却有着推己及人甚至推己及物的普泛同情,认为世间万物都和自己拥有同样的生命和感觉,于是他们对花唱歌,和小动物游戏,拥有了比成人更为广阔和诗意的世界。
此外,孩子们的一切行为,都出自本心,没有矫饰造作,也不会理智压抑,却最是真纯。不管是梦二诗画中的那一对在圣诞前夜给圣诞老人写信要礼物的兄妹、那个搞不清三九二十八还是二十九却最擅长画数学老师的脸的小秀吉、那个因为会带她去玩就认定叔叔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的小女孩,还是子恺漫画中因为嫌分给他的花生米少了而哭丧着脸的奇伟、那两个争夺饼干盒的孩子,他们就这样未加修饰地出现,用最原初的姿态和最坦率的要求,不管是小小的贪心还是偶尔的调皮捣蛋,也都让人觉得无比美好,这是蝇营狗苟的成人世界可望而不可及的真纯。
而在美好的孩子的眼中,成人世界也是美好的,他们对成人的世界充满了渴望,也尝试着模仿。在梦二的《孩子的国度》里,小女孩模仿妈妈的样子为布娃娃笨拙地清洗衣物,对它说话,为它取名,坚称布娃娃是自己所生;小堇模仿着奶奶的样子戴着老花镜看报,哪管拿倒了报纸;妙子偷偷跑到姐姐的化妆间学着姐姐的样子化妆,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美丽的嫁娘;而在丰子恺的漫画《穿了爸爸的衣服》中,瞻瞻穿着爸爸硕大的马夹,俨然一幅爸爸的样子,《软软新娘子,瞻瞻新官人,宝姊姊做媒人》中,画的便是从乡下吃喜酒回来,孩子们模仿大人婚礼的场景……在孩子的眼中,大人无所不能,他们拥有力量、智慧和美丽,而孩子们这些稚嫩的模仿,便造成了一个非真的、被孩童眼睛和行为美化过的成人世界,产生了成年人自己也无法想象和企及的美与诗意。
竹久梦二和丰子恺的儿童画都是在尊重儿童的天性、还原儿童的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这与中国常见的那些体现成人的文化期待和意志的儿童文学不同,他们没有成年人想要对未来一代种植价值观和施加影响力的优越感、支配感和设计感,在这一点上来说,丰子恺与竹久梦二一样,都是超脱的。这使得他们的儿童作品看起来极为相似,甚至有时连选用的题材也几乎相同。然而事实上,儿童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创作儿童诗画对于他们的意义也完全不同。
丰子恺极其喜爱儿童,他甚至将诗僧八指头陀咏儿童的诗刻在烟斗上:“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骂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对镜心常定,逢人语自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而他画儿童画,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作这些画的时候,是一个已有两三个孩子的二十八岁的青年。我同一般青年的父亲一样,疼爱我的孩子。我真心地爱他们……我当时对于我的孩子们,可说是热爱。这热爱便是作这些画的最初的动机。”*丰子恺:《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45、546页。他用手中的笔纪录着孩子们的生活,《建筑的起源》中瞻瞻搭积木时的认真,《你给我削瓜,我给你打扇》中姐姐给弟弟削瓜、弟弟给姐姐扇凉的温馨,《阿宝赤膊》里刚洗完澡只穿着裤子的阿宝双手护住胸口的娇羞……我们在感受这些画面中的童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作者流淌在画笔里的温柔与慈爱,以及父亲微微含笑温情凝视的眼神。
而竹久梦二则不然,他也有自己的孩子,但他从来都讨厌妻子谈及孩子的话题,对孩子也极其漠视。我们翻看《孩子的国度》《蓝色的船》等梦二的童诗童画就会发现,他的作品中很少出现丰子恺漫画中孩子与孩子嬉戏玩闹的场景,而大都是孩子与花草动物以及整个大自然的交流。在梦二的童话里,早晨,太阳会唤醒那个连闹钟、小鸟、南风、公鸡都叫不醒的孩子;到了晚上,月亮会哄着别别扭扭不肯睡觉的孩子入眠;看到衣衫褴褛的孩子,小羊会送上自己的羊毛,蜘蛛会把羊毛纺成丝线,促织会将丝线织成布匹,螃蟹会为他裁剪成衣。孩子面对偶然发现的鸟巢,也会默默地守候,看着鸟儿生卵,看着雏鸟孵化,看着幼鸟一天天长大,学会飞翔,最后飞向远方……而在描画这一切的时候,竹久梦二却将自身隐遁了起来,他没有作为成年人高高在上的俯视姿态,甚至也没有丰子恺那样的站在画外的温柔注视,他似乎消弥于无形,却又时隐时现于画面之中,他是那个晨起见不到妈妈就哇哇大哭的小春,是那个要替女王戍守宝座的黑猫,是在漆黑的冬夜独自舂米的水车。他到底还是《梦二画集》中那个游离于俗世之外、灵魂无处安放的孤独旅人,他用画笔构建起了一个真纯的“孩子的国度”,他退归孩童,甚至化身千亿,这里的一切都对彼此满怀友善与温情。自然对于孩子,是温柔的守护,是慷慨的赠予;孩子对于自然,是满心的依赖,是纯真的捍卫,他们交谈游戏、融为一体。这里是他用以避开俗世烦扰的乐园,而他的童诗童画,便是他排遣孤独、寻求心灵告慰的途径。
四、“绝缘”与“非人情”
在《东方艺术传统与竹久梦二的绘画之美》*郭尔雅:《东方艺术传统与竹久梦二的绘画之美》,《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一文中,笔者曾经对梦二诗画中的“非人情”之美作过论述,“非人情”是夏目漱石在《文学论》中提出的概念,而后又在《草枕》中通过一个漫游乡野的画工的体悟,以绘画性的叙述手法进行了诠释,指的是一种不逼仄不压抑的静观的审美距离,是对道德的超越以及脱离尘世、淡泊世情的审美态度。《梦二画集》中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身处世间而又无所适从的空茫与孤独之感,因此,无论是在诗中画中还是现实里,梦二总是不断地启程,将灵魂的归依寄望于暂离世尘的旅途;而那些“梦二式美人”则总是用略带哀愁的大眼静静地观望着世间,神情中带着游离世外的空茫与漠然;在《孩子的国度》《蓝色的船》这样的童诗童画中,梦二则描绘出了一个远离成人社会、充满着爱与美好的乐园。我们从这些作品中,都可以感受到梦二所构建的“非人情”的世界。
在丰子恺的美学思想中,有一个与“非人情”极为相近的概念——“绝缘”。《汉语大词典》“绝缘”条释义为:一,断绝因缘;二,不发生接触,不相关连。而“‘因缘’为佛教语,佛教谓使事物生起、变化和坏灭的主要条件为因,辅助条件为缘”*《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8页。。《四十二章经》卷十三:“沙门问佛,以何因缘,得知宿命,会其至道?”中的“因缘”便是此意。此外,“因缘”还有机会、缘分,依凭、依据,牵合、比附,发端、缘起,原因,关系等含义。因此丰子恺所提出的“绝缘”便是指通过剪断事物的所有前因后果、凭借牵连,以及各种世俗的功用功利和科学的智性关系,从而达到一种超越的审美状态。在《看展览会用的眼镜——告一般入场者》一文中,丰子恺写到了幼时游戏的体验:“分开两脚,弯下身子,把头倒挂在两股之间,倒望背后的风景”,或者“用手指打个圈子,从圈子的范围内眺望前面的风景”*丰子恺:《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都会使惯见的风景变得新颖而美丽。他认为,这样的腿间的倒望和手指的范围便是“绝缘”。他将“绝缘”比作一幅眼镜,认为“戴上这幅‘绝缘’的眼镜,望出来所见的森罗万象,个个是不相关系的独立的存在物。一切事物都变成了没有实用的、专为其自己而存在的有生命的现象。屋不是供人住的,车不是供交通的,花不是果实的原因,果实不是人的食品。都是专为观赏而设的。眼前一片玩具的世界”*丰子恺:《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01页。。在这样“绝缘”的世界里,我们无需去探察事物的本质,去顾虑它的前后变化以及与周围的关系,也不必计较利害得失因果,不用参照以往的知识智慧与经验,只需专注于眼前所见即可,这其中不正包括着“非人情”所说的静观的审美距离,超越尘世、淡泊世情的审美态度吗?当然,“绝缘”的范围要比“非人情”更广,因为“人情”只涉及道德、世情、人心,而“缘”则指向与俗世相关的一切。
此外,对于 “非人情”的 “脱离尘世”和《草枕》一文,丰子恺都是有所触及的,他在《暂时脱离尘世》一文中引用了夏目漱石《草枕》中的一段话:“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我也在三十年间经历过来,此中况味尝得够腻了。腻了还要在戏剧小说中反复体验同样的刺激,真吃不消。我所喜爱的诗,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丰子恺:《暂时脱离尘世》,载《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662页。他认为沉浸在尘世的苦痛、愤怒、叫嚣和哭泣里的人,也只是一架机器罢了,只有懂得脱离尘世的人,才是“最像人的人”。然而他紧接着却特别强调了“暂时”二字,他说:“但请注意‘暂时’这两个字,‘暂时脱离尘世’,是快适的、是安乐的、是营养的。”可见,在丰子恺看来,“非人情”的世界应当是暂时的,就如同长久劳作后的小憩,如同今人观看古装戏剧,是一种积极的调剂,而非竹久梦二一般消极的避世。这其间的差别其实与竹久梦二和丰子恺在个人气质和思想特征上的差异是一致的,竹久梦二是一个唯美唯爱、任情任性的风流才子,他的心中常怀不被世人理解的忧苦和灵魂无处安顿的孤独,因此总想要避世离尘,在旅途中、在一个又一个的美人身上、在童真童趣的“孩子的国度”中寻求心灵的归依;而丰子恺则是一个胸怀广博、虑世忧民的大艺术家,他有着普世的关怀和深厚的佛学修养,他尽管也主张通过“绝缘”的方法来达到审美的纯化境地,可他所关注的绝不仅仅是“美”,绝不仅仅是自己内心的喜乐与悲哀,更有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和对世间万事万物的关怀。这也造成了竹久梦二与丰子恺的最本质的区别,即对美与艺术、道德的理解,对“真、善、美”的追求次序上的差别,这是我们理解梦二与丰子恺,甚至理解中日艺术时最基本的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丰子恺童年时代就随父亲熟读四书五经,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到浙江一师后,又师事李叔同。李叔同以唐代裴行俭“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示之。从丰子恺的主要文艺论著来看,他完全接受了老师的观点。丰子恺说:“欲为艺术家者,必须先修美德,后习技术;必须美德为重,而技术为轻。”*丰子恺:《桂林艺术讲话之二》,载《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他认为“艺术以仁为本,艺术家必为仁者”*丰子恺:《桂林艺术讲话之一》,载《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他也从反面说明德行缺失的危害: 一位艺术家“倘学会了技术而缺乏美德,其人就不能正当地运用其技术,误用技术,反而害人”*丰子恺:《桂林艺术讲话之二》,载《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他认为:“新中国的艺术家者……毋宁为善良之人。”*丰子恺:《桂林艺术讲话之二》,载《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甚至说:“艺术就是道德,感情就是道德。”*丰子恺:《艺术必能建国》,载《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他认为鉴赏名作“不但有关于美术修养,又有关于德业”,并断言“艺术家必是大人格者”。当然,作为艺术家,丰子恺也是追求“美”的,他认为:“圆满的人格好比一个鼎,‘真、善、美’好比鼎的三足。缺了一足,鼎就站不住。”对于三者的相互关系,他的理解是:“‘真’、‘善’为‘美’的基础。‘美’是‘真’、‘善’的完成。‘真’、‘善’好比人体的骨骼,‘美’好比人体的皮肉。真善生美,美生艺术。”*丰子恺:《艺术与艺术家》,载《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01页。他即便也追求美,可到底还是以‘真’和‘善’为前提的。事实上他也在以身践行着这一主张,他对世间民众有着普泛的关怀和广博的同情,也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在抗战时期,他挈妇将雏流徙千里也拒不附逆求荣,“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丰子恺:《还我缘缘堂》,载《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铮铮宣告,掷地有声。丰子恺归根到底是注重国家社会的。国难之中,他以笔为枪协力抗战,做着“笔杆抗战的先锋”;国安民乐之时,则逸笔草草描绘世态人情、童趣诗心,实在堪称是他自己所崇尚的“胸怀芬芳悱恻”的艺术家。
然而,我们却不能以丰子恺的以真、善为中心的道行修养和言行标准去看待竹久梦二。单就梦二那一段又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恋情,已让诸正人君子们侧目。不管是和前妻他万喜反复的同居分居,和彦乃违抗父命的师生偷期,和唤他“爸爸”、被他称作“孩子”的叶子的忘年情爱,还是风流人妻顺子、美女编辑秀子,以及后来出入“山归来庄”的众多青春美丽的女子,没有哪一段是合乎婚姻道德和遵循社会伦常的。而他的诗画作品中,也时常表现出漠视“真”“善”,唯独求“美”的倾向。且不说转型之后唯情唯美的“梦二式”美人画,单看对丰子恺产生巨大影响的《梦二画集》,亦能看出他的唯美主张。他在《夏之卷》的序中,描述了自己参览画展的情形,他说:“每一幅画,都以其逼真的画技让我印象深刻。然而却再没有一幅让我渴望成为画中人。少年憧憬的世界,并不是‘真’与‘善’,而是‘美’,只要‘美’,就够了。”他对世间的忠孝礼法不屑一顾,唯愿沉浸在美的享受中:“在这世上的忠臣孝子熟读楠正成与二宫尊德的美谈的时候,我却躲在昏暗的仓库二楼,沉醉于《白缝物语》和《枕草子》,幻想着平安朝风雅的宫廷生活和江户时代春夜美梦一般幸福的青年与少女。”*竹久梦二:《梦二画集·夏之卷》(序),郭尔雅译,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他无视于社会的要求和功利的成就,画下“社会告诫我们成为有用的人。我们却只求真,求美”*竹久梦二:《梦二画集·春之卷》,郭尔雅译,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页。的作品。对于绘画,他也不求逼真,但求美感,他描述年少时看到的名家画作时说:“每一个女人都有着外国人一样的肤色,穿着暗色的粗厚和服,和服已有多处褪色。所有人都是一副顽愚的样子,这让我感到惊讶。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不画上穿着柔软丝绢和服的女子呐,白皙的皮肤,乌黑的头发,不是会更美吗?”他这样的审美趣味体现在《梦二画集》中,也延续在其后的美人画里。
对“美”至上与“善”至上的不同追求,造成了梦二与丰子恺艺术风格与思想内涵的本质差异,这也反映了中日两国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中国人善用伦理道德规制行为,日本人则多以审美标准判定价值。我们常惊叹日本艺术作品中背德情爱之多,更难解于何以违背道德伦常的情事却能带给我们美感和同情,而许多的日本人似乎也难以理解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为什么总愿意去做道德家的说教。对于这一差异,我们通过对竹久梦二与丰子恺的对比便可管中窥豹。
以上从具体的绘画类型、绘画手法到整体的审美意趣和美学思想方面,对竹久梦二和丰子恺的艺术特色作了比较和分析,我们既可以从中看到竹久梦二对丰子恺的影响,也可以明确感受到他们之间深层的、本质的差异,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丰子恺受到了竹久梦二的很大影响,就忽视丰子恺画作的中国文化底蕴;也不能因为竹久梦二在现代中国颇受欢迎,就将竹久梦二其人及作品作中国化的理解。这也为我们理解东方现代绘画乃至艺术之间的影响、融合以及其各自的艺术个性提供了参照和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