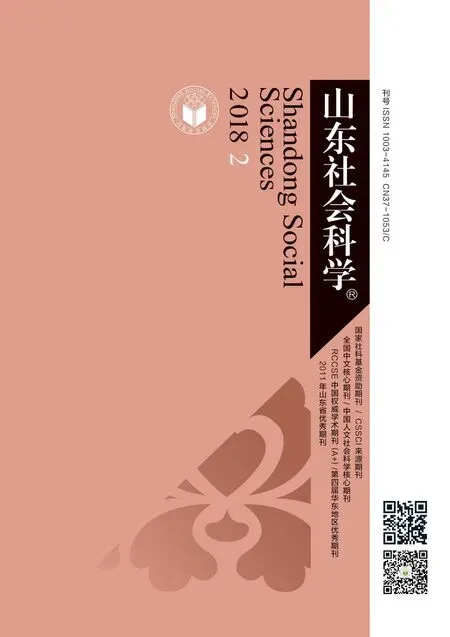从“东方学”看伏尔泰《风俗论》及“东方-西方”观
2018-01-30王向远
王向远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大学者伏尔泰(1694—1778)的巨著《风俗论》*《风俗论》,全称《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1756年初版,中文译本由梁守锵等人翻译,分上、中、下三册,由商务印书馆(北京)2000年出版。,是继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问世两千多年后,又一部世界视野的东西方历史或者世界史,从欧洲“东方学”的角度来看,也是一部东方学名著,不过,他的视野要比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开阔得多。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的活动,15世纪后海上探险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在东方的殖民活动,使得西方人对整个世界有了全面把握,这些都为伏尔泰《风俗论》的撰写提供了条件。在中国,正如何跃先生在《中国的伏尔泰史学研究述评》一文中所言,由于伏尔泰的史学名著翻译得太晚,滞后了国人对其史学思想的了解。*何跃:《中国的伏尔泰史学研究述评》,《云梦学刊》2001年第5期。至于《风俗论》,则直到1994年其中文译本才得以出版发行,中国学者站在中国立场上的研究评论很少。迄今为止除了张广智教授的《略论伏尔泰的史学家地位》(《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世界史重构的新潮流》(《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3期),还有王加丰博士的《伏尔泰的世界史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林芊的《历史理性与理性史学——伏尔泰史学思想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第一章第三节等少量文章及专著的有关章节之外,未见相关的专门论文,更未见从“东方学”的角度对《风俗论》所作的评论与研究。
一、“东方-西方”二元论与多元文明观的并置
关于伏尔泰撰写《风俗论》的缘由动机,他在该书的《序言》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是因为他不满意此前史家流于史料堆砌、对事件细节的罗列,而未能“从这些事件中整理出人类精神的历史”*[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页。版本下同。。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伏尔泰想写一部整一的世界史,另一方面也把世界按其文化的不同而予以二分,即“东方-西方”。因此,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他对人类精神历史的建构并非建立在中世纪以来一直流行的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中心论的基础之上,并不把这个世界看成是由上帝统御的整一的世界。他在《风俗论》中明确使用了“西方”与“东方”(欧洲与亚洲)的二元世界论,与希罗多德《历史》中的“东方-西方”二元观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一点上,伏尔泰的《风俗论》跨越两千多年,与希罗多德拉起手来。翻阅欧洲历史著作史就会知道,希罗多德之后不久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色诺芬的《长征记》等历史著作,虽然都写了当时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战争,但那只是具体的战争事件的记录,而不具备“东方-西方”的历史文化视野。而此后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中世纪的历史著作,大都把世界分为基督教的世界与异教徒的世界两部分,是以基督教上帝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世界图景,“西方-东方”不是二元的、对峙的关系,而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在基督教以其上帝为中心的普遍主义的历史构架中,“东方-西方”的二元观长期处于屏蔽状态,而东方是有待于被基督教统一覆盖的世界,甚至年龄稍长于伏尔泰的意大利思想家维科(1668—1774)的名著《新科学》(全称《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质的新科学的原则》,1725)也仍然如此。维科站在共同人性论的立场,通过“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来寻绎和建构人类历史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的轨迹、规律,他所说的“各民族世界”就是基督教一元论的同一的世界,而没有了“东方-西方”的二元。
与上述的一千多年间的历史著作不同,在《风俗论》中,伏尔泰首先是着眼于“东方-西方”的差异性,明确反对基督教史学家以犹太人为起点的世界历史观。例如,在谈到古代阿拉伯人的时候,伏尔泰写道:“西方所编造的世界史中没有谈到他们。我完全相信,他们跟犹太小民族毫无关系,而我们的所谓世界史却以这个犹太小民族作为描述对象和立论的根据。”*[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73页。在谈到法国近代著作家波舒哀的历史著作时,他评论道:波舒哀《关于世界史的演讲集》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暗示世间一切都是为了犹太民族而发生的;上帝把亚洲帝国赐予巴比伦人,是为了责罚犹太人;上帝让居鲁士统治波斯,是为了对犹太人进行报复;上帝派来了罗马人,仍然是为了惩处犹太人……但是他如果没有把古代东方民族完全抛之脑后那就好了;例如印度人和中国人,他们早在其他民族形成之前,便已占有重要的地位”*[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30-231页。。伏尔泰不仅反对在历史著作中敷衍《旧约》全书或希伯来圣经,而且认为它本身有许多记述荒唐不可信。他在对亚伯拉罕这个人物的记载加以分析之后,认为有关历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一切都超出我们的想象,在希伯来人的历史中,一切都充满奇迹”*[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77页。。
与他反对的基督教的一元历史观相反,伏尔泰所秉持的是“东方-西方”二分的世界观,而在此基础上则是“东方-西方”之下各民族多元的文化观。他的《风俗论》全书总体上是要表明:在西方(欧洲)之外,有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东方世界,伏尔泰随处使用了“我们西方民族”“我们西方人-他们东方人”“他们-我们”之类的提法,例如说中国人等东方人是“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48页。,显然是把作为“他们”的东方民族作为“我们西方”的对象。伏尔泰强调:“东西方风俗的差异之大不亚于语言的差异。这是一个值得哲学家注意的事。在这广袤的土地上生息的人民,纵然是最开化的,也与我们的文明不大一样。他们的艺术也与我们的艺术迥然有别。饮食、衣着、房屋、园林、法律、信仰、礼仪,一切都不相同……虽说人性从根本上说是四海相同的,但在他们的国度和我们的国度,在表现上却有着惊人的差异。”*[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20页。可见,在把“东方-西方”相对化、把东方世界作为西方世界的对象这一点上,伏尔泰继承了希罗多德的西方人本位的意识。他丝毫没有掩饰自己作为西方人的文化立场,因为他写《风俗论》的目的,是让他的女友、也是他的庇护人夏特莱侯爵夫人(1706—1749)真正了解历史。换言之,是让作为一个西方人的读者全面正确地了解历史,而不是像中世纪以降许多史家那样借历史著述来弘扬基督教的世界观与历史观。
与此相联系,由于伏尔泰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分出了“东方”,他也并不是因为“东方”各民族具有某些统一性、共性而将其称为“东方”,而是把除了“西方”之外的其他国家与民族都统称为“东方”。进而言之,他是以“西方”的同一性来应对和处理东方的多元性;但是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忽视东方各国文化的多元性,而是以东方的多元性来映衬西方的同一性。在写到东方各民族历史文化的时候,与其说他强调东方各国的同一性,不如说他更有兴趣强调东方各民族风俗文化的差异性乃至对立性。例如在谈到日本与中国之差异的时候,他一方面看到了孔子学说对日本的深刻影响,但也发现日本人和中国人敦厚的性格不同,“这些岛民秉性自负而暴烈”*[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14页。;又说:“日本人似乎是土生土长的。他们的法律、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和中国的毫无相同之处。”*[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16页。联想到一直以来,甚至中日两国许多人都在强调两国的“同文同种”,一些中国人认为日本接受了中国文化多方面的影响因而与中国大同小异;但伏尔泰却正是在相同中看出了中日之间的深刻差异,甚至得出了“毫无共同之处”的结论,对于18世纪的西方人来说,这真是了不起的眼光。
二、理性主义价值观及对东西方文明的评价
上述的“东方-西方”二元论与东方多元文明观这两种视域的融合,是伏尔泰《风俗论》历史文化价值观及东方观的前提。“东方-西方”二元论为他提供了站在西方而又“客观”东方的立场,同时,承认东方各国历史文化的多元性,而不是把东方仅仅视为西方的他者而作简单化的处理,又能一定程度地克服西方文化的宗教的、种族的种种偏见,从而有可能从合理的立场、理性的角度对东方各国作出观照和评价。事实上,在《风俗论》中,伏尔泰正是以启蒙主义者所推崇的“理性”为标准,对东方、西方的历史,特别是对西方人所撰写的关于东方的历史书籍,统统以常识、知性、逻辑的眼光审视之、分析之、纠正之、批判之,并试图以理性主义方法写出合乎常识、合乎逻辑、可以理解的世界历史。关于以往的历史著述,伏尔泰认为西方人对东方各民族历史的许多叙述是不可靠的,并断言——
西方人所写的关于几个世纪以前的东方民族的事情,在我们看来,几乎全都不像是真的;我们知道,在历史方面,凡是不像真事的东西,就几乎总是不真实的。*[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3页。
伏尔泰所谓“不像真事”,似乎主要指希罗多德的《历史》,因为在伏尔泰之前的两千多年间,真正对东方的文化风俗史记载最多、最系统的,当属希罗多德的《历史》了。而希罗多德对东方的描述主要靠亲自踏查和道听途说,传说与想象的成分是显而易见的。伏尔泰用理性主义的逻辑思维,对希罗多德关于东方的一些记述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例如,关于巴比伦的风俗,说所有巴比伦女人按法律规定一生中必须在神庙中和不相识的外地人苟合一次,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风俗在西方因希罗多德《历史》的记述而广为人知,对此伏尔泰从理性思考的角度提出了质疑:“难道这种无耻行为符合一个开化民族的特征?难道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城市的官员会制定这样的法律?难道丈夫会同意自己的妻子去卖淫?难道父亲会把女儿交给亚洲的马夫去泄欲?不合天性之事从来不会是真实的。”*[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58页。诚然,从理性的、逻辑的角度来看,这类事情的确是令人不可思议的。然而,不合天性、不合情理,甚至耸人听闻、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历史和现实中实在是太多了。伏尔泰似乎忘记了,事实上,现实与历史并不是按伏尔泰所理想的“理性”来安排和推进的。
从理性主义的推论与逻辑出发,伏尔泰排出了文明产生的先后顺序,他认为肥沃的土地会产生最早的文明,如两河流域的迦勒底人,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人,黄河流域的中国人,他们是农耕民族,土地不那么肥沃却又占地广阔的民族则只会游猎,而“海上贸易历来是各个民族最后的出路”*[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62页。。根据这一看法,他把东方主要文明民族定位为农耕民族,把欧洲民族定义为航海民族,而游走于东西方之间的民族则是游牧民族,亦即斯基泰(鞑靼)人。*[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69页。显然,这并不是简单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物质生产方式决定论,已经很接近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了。
伏尔泰认为,由于这些生活生产方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文化风俗。西方人之所以对中国及东方各国存在极大的误会,根本原因是“我们以我们的习俗为标准来评判他们的习俗,我们要把我们的偏执的门户之见带到世界各地”*[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55页。,这是不可取的。既然不能用西方的风俗文化标准来评判东方,同样地,也不能以东方的风俗文化标准来评判西方。不过评判标准毕竟是要有的,那就是“理性”。伏尔泰的“理性”在其最浅显的层面上指的是合情合理,在深刻的层面上就是发挥人类最为清醒、最为现实和真实、最为明智、最合人道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为此,伏尔泰“理性”的反义词常常是“虚构”“奇迹”“迷信”“荒唐”等。从理性出发,伏尔泰对东西方各民族的文化作出了价值评判。例如关于印度文明,伏尔泰总结道:“尽管印度的教义是如此明智,如此高尚,占上风的却是最低级、最疯狂的迷信……使真理淹没于各式各样的无稽之谈中。”*[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24页。这里点出了印度文化中矛盾的两面,后来马克思在《大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分析的印度宗教文化的两面性与矛盾性,显然与伏尔泰的观点有继承关系。伏尔泰在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风俗的评价中,也显示了“理性”分析的眼光,例如,关于东方的婚姻制度,伏尔泰认为西方社会的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似乎对妇女较为有利,而东方〔一夫多妻制〕的法律则有利于男人和国家”*[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309页。。他认为东方、西方各有各的合理性与两面性,而不能以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
伏尔泰理性主义的文化评价标准,集中地体现在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中。关于中国历史,他写道:“中国人在撰写帝王历史之前,没有任何史书。不像埃及人和希腊人,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就写得合情合理。”*[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86页。又说,“无可否认,世界上最古老的编年史是中国的编年史。中国的这些编年史连贯不断,详尽无遗,撰述严谨,没有掺杂任何神奇的成分……接近于翔实可靠。”*[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20页。这样的看法颇得要领,抓住了中国历史学的特色。伏尔泰还认为,中国在“国家管理”方面最值得称道:“神权政治不仅统治过很长时期,而且暴戾恣睢,干出了失去理智的人们所能干出的最可怕的暴行。这种统治越是自称受之于神,就越是可憎可恨。”而与此种情形形成对照的是,“在被不恰当地称为文明人的民族中,我只看到中国人没有干出这种荒唐绝顶的暴行。”*[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47页。又说,“除了中国以外,几乎在任何地方的法律、宗教和习俗中,都可以找到荒谬绝顶的东西,而明智的东西却寥寥无几。”*[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57页。
在东方国家中,伏尔泰尤其赞赏中国的国家管理与法律制度。他认为,中国的国家管理不利用其他民族常用的关于死后惩罚与褒赏之类的说教,“地狱之说虽然有用,但中国人的政府从不采纳。他们只满足于鼓励人们虔诚敬天和为人正直。他们相信,一种一贯实行的正确的政治制度,会比一些有可能受到攻击的舆论起更大的作用;人们更害怕的是现行的法典,而不是未来的律令。”*[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90页。伏尔泰赞赏中国人将法律意识与道德意识紧密结合:“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儿女孝敬是国家的基础……这种思想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49页。伏尔泰赞赏中国人把道德的褒赏作用引进法律中:“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50页。中国的这种法律带来了很多好处:“正因为全国一家是根本大法,所以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把维护公共利益视为首要责任。因之皇帝和官府始终极其关心修桥铺路,开凿运河,便利农耕和手工制作。”*[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49页。伏尔泰指出正因为中国人法律齐备,才使得那些蛮族入侵者“仍只得屈服于被他们夺取了皇位的国家的法律”*[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45页。。
伏尔泰还运用理性的原则,对东方及中国政治制度作出了分析评价,也触及了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就已提出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问题。长期以来,所谓“东方专制主义”是东方政治制度区别于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分水岭。法学家孟德斯鸠作为与伏尔泰同时代的学者,其《论法的精神》一书把东方各国的政治制度一律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而伏尔泰则与之不同,他对“东方专制”的判断是十分审慎的,他只在评价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及其政治制度的时候用了“专制”这个词。伏尔泰写道:“恶劣的是,没收财产成了苏丹私人收入的重要来源。一家之长被判刑,家族的财产便归国君所有,这是自古以来既定的专制制度之一。若有人给苏丹送上一名大臣的头颅,这颗头颅有时能值几百万。残暴的行为能取得如此高价的收入,这就不断引诱国君去当一个图财害命的贼。没有比这样一种权利更为丑恶的了。”*[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126页。显然,他所说的“专制”是极权恐怖的政治。当谈到波斯政治的时候,伏尔泰说:“旅行家夏尔丹说波斯皇帝没有土耳其皇帝那么专制”,“一般的看法,伊斯法罕(代指波斯——引者注)不及君士坦丁堡那么残酷”,可见“残暴的行为”即暴政是伏尔泰眼中“专制”制度的一个特征。在这一点上,土耳其奥斯曼是“专制”的,波斯的统治者有时残酷,但也难说是“专制”的,对此他写道:
所有有关波斯的叙述都使我们相信,没有一个君主国家享有比波斯更多的人权。这个国家民众比东方任何国家的民众具有更多地排遣烦恼的手段,而烦恼在任何地方都是生命的毒素。人们聚集在称为咖啡馆的大厅里,有的喝着这种直到17世纪末我们这里才有的饮料,有的在赌博,或者阅读,或者听人讲故事;在大厅的一端,一位教士为了挣几个钱在布道说教。在另一端,那些有本领使别人快乐的人正在施展他们的全部的才能。这一切都表明,他们是爱社交的民族。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这个民族是该当幸福的。有人说,在人称‘大王’的阿拔斯统治时期,波斯人是幸福的。这个大王是很残暴的,但是残暴的人珍爱秩序和公共财产也是不乏其例的。这个暴君只是对他身边的某些人凶,但他有时根据他自己制订的法律为国家办了好事。*[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97页。
这段话突出地表明了伏尔泰对古代东方政治的看法。土耳其奥斯曼式的残暴是普遍的,而波斯,乃至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其“残暴”行为是个别的,是针对有限的对象的。只要能确保人民的“人权”,使人民幸福,就不在“专制”的范畴内。伏尔泰使用了“君主国家”一词,而且认为君主国家可以使人们享有“更多的人权”。至少从这一点上看,“专制国家”作为暴政国家,与“君主国家”是不一样的。
在伏尔泰看来,所谓“专制制度”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君主是否有能力实施专制,在于法律的有效性及行政权力的有效性。他在分析印度莫卧儿帝国政治的时候,认为莫卧儿帝国治下的印度整个国家成为内战的战场,政府“极端腐败”。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所谓的专制统治是不存在的。皇帝的权威不足以使任何一个沙甲听命于他”。像莫卧儿帝国那样建立在军事武力征服基础上的统治,连“政府”的资格都不够,因为“这种仅仅建立在武力上的权力,只是在统帅军队时才能维持,这种专制权力能毁灭一切,但最终要自行毁灭。它以个人的随心所欲为准绳,而不依靠能保证其存在的法律”*[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508页。。在这种情况下,连专制者自身都朝不保夕,他根本无法实行“专制”。
伏尔泰并不是笼统地把不同于西方的东方的政治制度一概称之为“东方专制”,他把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土耳其、波斯等东方大国作了比较分析,在多元文化的视域中,区分东方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的特点。他认为像印度的莫卧儿王朝那样,只有武力征服,连像样的政治都谈不上,也就实现不了所谓的“专制”;像阿拔斯王朝那样,君主残暴却能保护百姓,很难说它是专制的;像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那样,才是真正的独裁、残暴的“专制”;中国则因为皇帝的权威、完备的行政机构与法律,使人民得到保护,因而不能算是专制独裁政府:“由于亲王们觊觎王位,土耳其苏丹们常下令将亲王绞死。而〔波斯的〕萨菲王朝的皇帝仅仅将亲王的眼珠剜去。中国的国君从来没有想过,为保全帝位,必须杀掉自己的兄弟或侄子,或者剜掉他们的眼珠。中国的皇帝总是给他们荣华富贵,而不给他们权力。一切都证明中国的风尚是东方最人道、最明智的。”*[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116页。在他看来,中国的德政、仁政与土耳其奥斯曼不可同日而言。伏尔泰写道:
中国比印度、波斯和土耳其幸运得多。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在中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这种制度下,皇帝要实行专制是不可能的。一般法令出自皇帝,但是,由于有那样的政府机构,皇帝不向精通法律的、选举出来的有识之士咨询是什么也做不成的。人们在皇帝面前必须像敬拜神明一样下跪,对他稍有不敬就要以冒犯天颜之罪受到惩处,所有这些,当然都不能说明这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独裁政府是这样的: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形式,只凭个人意志,毫无理由地剥夺臣民的财产或生命而不触犯法律。所以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执行这些法律的机构越多,行政系统就越不能专断。尽管有时君主可以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数人,但他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509-510页。
在伏尔泰看来,中国固然也是君主国家,但不是对人民残暴的专制暴政国家,因而不属于“东方专制”的范畴。显然,伏尔泰对“专制”的判断,不是在纯粹体制层面上的判断,而是更多地结合了君主的道德伦理与品德修养,特别是行使政权是否是合乎“理性”的原则。中国这样的君权国家是符合理性原则的,因而不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显然,这是对《风俗论》问世几年前刚出版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50)一书中“东方专制主义”论的一种批驳与否定。
三、“东方社会停滞”论与“西方后来居上”论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把东方置于人类文明先行者的位置:“在我看来,迦勒底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是开化最早的民族。”*[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47页。从而把人类文明的起点放在了东方(亚洲)。他在《风俗论》中首先写的是中国,其次是印度,再次是阿拉伯,第四才是欧洲。世界历史的撰著者一般认为,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中有一个是西方的希腊,但伏尔泰认为“希腊人和罗马人比起亚洲人来又晚近得多”*[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32页。,希腊的多山临海的地形使他们多次遭遇大洪水,“甚至可能正是这大洪水使希腊人成为一个相当晚近的民族。这些巨大的地理变迁使希腊人重新沦于蛮荒时代。”*[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105页。而他的理论根据就是地理与生活环境。他认为,“可以肯定,一切动物在最易于觅食的地方都能很快孳生繁殖”,人类文明也总是在这样的地方首先发生。从这一点上,他认为印度文明起源最早,因为“世上没有一块地方比恒河流域有着人们唾手可得的更新鲜、更可口、更丰富的食物。这里稻子不种自长;椰子、椰枣、无花果无处不有,可作菜肴;桔子、柠檬可作饮料,又可供食用;甘蔗俯拾皆是;棕榈树、宽叶无花果树浓荫蔽日。”*[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77页。因而其他民族也必然会来印度经商贸易,印度却无求于其他民族。“匮乏产生首批的强盗。只因印度富庶,这些强盗才侵入印度;而富庶民族必定早在强盗民族之前便已集结形成社会,便已臻于文明开化”*[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78页。。可见伏尔泰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自然环境是否优越。这从人类文明起源论上讲,是合情合理的。文明的起源靠环境条件,而文明的不断进步则要靠挑战和应战的机制,这是20世纪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伏尔泰只是在文明起源的初始时期,肯定了东方各国文明的先发性。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我们西方民族虽然对某些重要的事物的真理有所领悟,但在艺术、科学和国家管理方面却很缺乏知识。”*[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3页。这句话在今天的东方人听起来,也仍会有新奇之感。西方人一直以来所自豪的不正是“艺术、科学和国家管理”(即政治)吗?为什么伏尔泰认为这些方面西方不如东方呢?原来,这只是指初始阶段而言的。在这个阶段,就艺术的摇篮神话而言,“希腊人在神话方面只不过是印度人和埃及人的弟子而已”*[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61页。;“从希吉来历(指伊斯兰教历法——引者注)的第2世纪起,阿拉伯人却在科学与艺术方面,成为欧洲人的教师”*[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97页。。阿拉伯人把天文学教给欧洲,而且“化学与医学是由阿拉伯人创立的。我们今天发展完善了化学,但化学原来是他们传给我们的。人们统称为轻泻剂的那些新药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代数是阿拉伯人的发明……总之,西方基督徒肯定从穆罕默德的第2个世纪开始,就拜穆斯林为师了”*[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306页。。“从远古时代起,贤人来自西方便是印度人和中国人的一句格言。欧洲人则相反,说贤人来自东方。”*[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70页。他甚至说:“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31页。
伏尔泰认为东方本来领先于西方,但是东方后来落后了,西方“后来居上”。古代希腊接受了埃及、腓尼基、波斯、印度的一些影响,但是到了后来,“美丽的建筑、精美的雕刻、绘画、优美的音乐,真正的诗歌,真正的雄辩术,正确编写历史的方法,最后是哲学本身——虽然还不完善且晦涩难解——所有这一切,都是由希腊人传至各国的。后来居上,他们一切都比老师强”*[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109-110页。。要问为什么,关键的原因是希腊人有着最可贵的“自由”与“理性”,这一点“才使得希腊人成为世上最有创造才能的人”*[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114页。。这个结论令我们想起了希罗多德《历史》中对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原因分析,那就是希腊人作为自由人是为自己作战,是为国家的自由作战,而波斯人是作为君主的奴仆而被动地为君主而战。另一方面,伏尔泰没有像其他史学家那样把古希腊文明置于与东方其他三大文明相并列的位置,他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希腊文明的后来居上。换言之,在他看来,西方的后来居上,不是一般史家所认为的开始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而是早从古希腊时代就开始领先于东方了。这么说来,西方领先东方就已经有两千多年了,而不是晚近的五百来年。
关于西方国家后来居上的根源,伏尔泰还在对不同东方国家的落后原因的分析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他的主要依据仍是“理性”或“理性精神”。例如,在谈到印度落后时,伏尔泰指出:“不管怎么说,印度人已不是古希腊人前往他们那里学习时那样先进的民族了,他们只有迷信,而且由于受奴役,迷信甚至比以前更厉害了。就如同埃及人一样,当他们被罗马人征服后,迷信活动更多。”*[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111页。他认为印度人的落后根源于非理性的“迷信”,在于“精神蜕化”:“在印度,人们的精神已经蜕化。可能这是由于鞑靼人的统治使他们呆滞迟钝。”*[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64页。关于波斯和中国,伏尔泰指出:“波斯由于国家的动乱,科学也同样几乎湮灭殆尽。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科学达到我们中世纪那样的平庸的水平之后,便停滞不前。”*[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64页。“人们要问:既然在如此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已如此先进,为什么他们又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在中国,天文学如此古老,但其成就有限;为什么音乐方面他们还不知道半音?这些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似乎大自然赋予他们的器官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所需的一切,却无法有所前进。我们则相反,获得知识很晚,但却迅速地使一切臻于完善。”*[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48页。又接着发问道,“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悠久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他认为:“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流传下来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孝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已尽善尽美;另一原因在于他们语言的性质——语言是一切知识的第一要素。”他认为中国的语言太难学了,“在中国,学者就是识字最多的人;有的人直到老还写不好”*[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49页。。伏尔泰用崇古的文化心理与繁难的语言这两个原因来解答所谓中国停滞论的问题。
在谈到中国文学、中国古典戏剧的时候,伏尔泰又在中国与西方的对比中指出了中国文化的停滞与保守性:“我们的特点是不断完善,而中国人的特点是迄今为止停留在原来的水准。《赵氏孤儿》这出戏可能还属于埃斯库罗斯的初期试作一流。中国人在伦理方面总是高于其他民族,但其科学进步不大。毫无疑问,大自然赋予中国人以正直、明智的精神,却没有赋予他们以精神的力量。”*[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104页。这里所谓的“精神的力量”,联系伏尔泰全书的思想,指的似乎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不断探索、追求与超越。没有这种“精神的力量”,文明只有停滞。比起泥古心理与繁难的文字,所谓“精神的力量”的缺失当然是更为本质的原因。
在分析了中国、日本、印度、波斯等东方各民族的风俗文化及其演变之后,伏尔泰自豪地宣称:“日本像中国一样,几乎拥有我们所有的一切,以及我们所缺少的一切……过去这两个民族在文学艺术与手工艺方面远比我们西方民族先进。但是我们现在已把失去的时间夺回了!”*[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16页。他的结论是:“总之,不论我们谈论亚洲的哪个文明国家,我们都可以说,它曾走在我们前面,而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它。”*[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119页。综观整部《风俗论》,伏尔泰对人类风俗文化与精神发展史的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就在于此。
伏尔泰是启蒙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启蒙主义与理性主义也是进步主义,相信人类文化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不进则退,不改变就是停滞,不进步就是退步,这是其历史发展的信念与逻辑。他是在“东方-西方”二元观和此消彼长的矛盾运动中来把握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线索的,因而西方的进步必以东方的落后来衬托,西方的发展必以东方的停滞为参照物。伏尔泰毕竟不能认同东方人保守的、循环性的发展模式,而秉持西方人勇往直前的线性发展逻辑,并由此对“东方-西方”作出了起源上的“先-后”、发展上的“落后-进步”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不仅仅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作出的,而且也是从文学艺术等精神方面作出的。假如仅仅从经济的、社会生产力的角度看,则必以工业化为尺度,把最早实现了工业革命的西方视为先进,把以农业社会为主的东方视为落后。但是,若就精神、文学艺术角度而言,则很难作出“东方落后”的判断。印度莫卧儿王朝的艺术、中国明清的文学艺术、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学艺术,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发展,而且这种进步发展并不和西方在一个轨道上,难以绝对地比较其二者何者先进何者落后。虽然伏尔泰在对具体的文化习俗的评价中,反对以西方的标准强加于东方,但是,在抽象的层面上,伏尔泰还是使用了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东方,所体现的是近代西方人的线性发展观。这种自相矛盾,根本上是由伏尔泰的“西方本位”的立场所决定的。
伏尔泰处在法国及西方列强正在向东方殖民扩张的时代,《风俗论》也免不了带有殖民主义思想色彩。书中宣称:“我们西方民族表现出了远远胜过东方民族的智慧和勇气。我们已经在他们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而且常常是在克服了他们的抵抗之后。我们学会了他们的语言,我们教给他们一些我们的艺术。但是大自然赋予他们胜于我们的长处,把我们的长处全部抵消:这就是东方民族丝毫不需要我们,而我们却需要他们。”*[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25页。这段话可以表现出伏尔泰对当时18世纪西方初步殖民东方的一种态度和评价。东方不需要西方,故而东方人没有侵入西方的动机;西方需要东方,需要东方的人力、东方的资源、东方的市场,这就是西方入侵东方的理由。在这个问题上,伏尔泰秉持的仍然是西方的立场,而完全没有表示出反省的意思。
综观《风俗论》,这不仅是一部壮阔的人类文化史、精神发展史的巨著,而且从“东方学”的角度看,也是一部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相辅相成、此起彼伏的文明发展史之宏大变奏曲。《风俗论》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基督教为中心的一元论的历史观及世界史撰写模式,采用了“东方-西方”二元并置、二元对峙的模式,肯定了东方各民族文化精神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运用他的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对东西方文明、对东方民族历史上那些合乎理性的因素作了肯定;但《风俗论》也并非像有的研究者所言是没有偏见地平等地看待东西方,实际上书中的“东方”仅仅是“西方”的他者,主要是为了映衬西方世界而存在的,主要是为了说明他所处的西方世界、他所处的路易十四时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先端,从而在史学著述中满足自己的文化自豪感,也满足西方读者的文化自豪感。在这一点上,它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如孟德斯鸠,后来的黑格尔、赫尔德等人的“东方-西方”观大同小异,作为西方人主流的东方观之源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