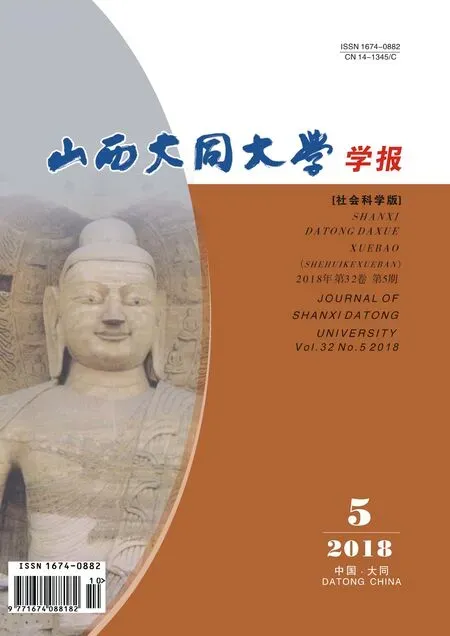昙曜身世研究
2018-01-29赵昆雨
赵昆雨
(云冈石窟研究院,山西 大同 037004)
高僧昙曜的名字首次见载于史籍,是在梁·慧皎《高僧传》中:“时河西国沮渠茂虔,时有沙门昙曜,亦以禅业见称,伪太傅张潭伏膺师礼。”[1](第50册,P398)慧皎没有为昙曜单独立传,以上21字只是附于“玄高传”条目下。至于昙曜的籍地、生卒师门等一概不言。慧皎是南朝梁代高僧,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生于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卒于梁元帝承圣三年(554)。他撰著的《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传,完成于公元540年前后,内中为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梁天监十八年(519)间的257位高僧立传。因慧皎系南朝人,故僧传中“缉裒吴越,叙略魏燕”,轻忽北方僧事。事实上,当时南北对峙阻隔,他也未必能够详悉北方僧事。
《高僧传》中关于昙曜记事的缺憾本有望在正史《魏书》中得到弥补,毕竟,昙曜做为北魏一代僧统,既有政治地位又有宗教影响力,加之《魏书》新增“释老志”欲畅论佛道。谈佛教,又怎能少了昙曜呢?然而,《魏书》中关于昙曜开篇即言:“沙门昙曜有操尚,又为恭宗所知礼。”又云:“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2](P3035-3037)同样不涉昙曜身世话题。
魏收,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人,生于宣武帝正始二年(505),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天保二年(551),魏收奉敕编撰《魏书》,4年后书成,此时距昙曜太和十年(486)最后一次露面隔70余年。按理说,魏收有条件也有能力找到关于昙曜的一些线索,为什么不去做呢?
有感于“僧史荒芜,高行明德,湮没无纪”,唐代丹徒人释道宣对慧皎《高僧传》进行了补苴增赓。道宣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十月卒,历隋、唐佛教全盛期。当时南北已经一统,不存在地域之困、交通之阻。道宣本人用力至勤,遍访郊郭碑碣,博览南北国史,编成《续高僧传》,除了叙述梁、陈、周、齐以来的高僧以外,还补叙北魏高僧昙曜、昙鸾、道辩、道登等人,缉成正传。其中《译经篇》列“魏北台石窟寺恒安沙门释昙曜传”,其云:“释昙曜,未详何许人也。少出家,摄行坚贞,风鉴闲约。以元魏和平年,住北台昭玄统。绥縎僧众,妙得其心。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1](第50册,P427)一句“未详何许人也”,宣告昙曜身世终成历史沉谜。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大慈恩寺始建,释僧靖迈受玄奘之请,为撰《古今译经图纪》四卷,其中有“昙耀”称名,文云:“沙门释昙耀,恒安石窟通乐寺僧。自少出家,器宇崇峙。风鉴闲约,戒行坚贞。……至和平三年岁次壬寅,昙耀为昭玄统。慨前陵废,欣今再兴,自于北台石窟寺,对印度沙门集诸大德译《净度三昧经》(一卷)、《付法传》(四卷),凡二部合五卷。”[1](第55册,P360)此处“昙耀”自是“昙曜”之异写。靖迈,梓潼人,四川简州福聚寺僧。这段文字中新增了一些内容,但毕竟到了靖迈的时代对昙曜已不能详述了。
一、昙曜入凉时间
昙曜刚一现身,便已入凉州之境。昙曜不是凉州籍僧人,而是入华的外国人,对此学界无异议。
从西晋永嘉之乱到东晋末世的百余年间,中原大地正经历着纷争扰攘的乱世,各割据政权兵燹未止,鏖战方殷。凉州地接西域,南奉晋室,远离诸王朝之争,得以保持社会秩序安定,经济丰饶。西来的商人及僧侣因中原战乱以此为终点,驻锡传法;中州的儒英、世族以此为流徙避乱之地,寻一份安心。凉州自张轨以后,世信佛教,沮渠蒙逊更是“素奉大法,志在弘道”。永安十二年(421),蒙逊攻克敦煌、高昌,得译经大师昙无谶,此后,无讖在姑臧城主持译场,凉州遂成为当时中国的译经中心及禅法流播之地。
游方弘化,是僧人宣法的主要途径。那么,昙曜是在何时进入凉州的呢?前引慧皎《高僧传》中如是言:
时河西国沮渠茂虔,时有沙门昙曜。
此言很值得玩味。河西国,指的是匈奴族卢水胡酋首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政权,先以张掖为都,永安二年(412)迁姑臧,称河西王,凉州牧。公元433年,蒙逊死,其子沮渠牧犍亦即“沮渠茂虔”继位。太延五年(439)七月,北魏攻陷姑臧,北凉灭。由此可知,蒙逊建立并统领北凉32年,牧犍在位仅6年。论影响,自然是开国之父沮渠蒙逊更有声誉威望。慧皎介绍昙曜时,不言“沮渠蒙逊”却称“沮渠茂虔”,或许慧皎在不经意间已陈述了一个事实——沮渠牧犍时代,昙曜到达凉州。
北凉从蒙逊建都张掖开始,一直到牧犍归降北魏,期间数次组织大规模译经活动,译经达82部、311卷,即便北魏大军即将踏破姑臧城时,由天竺沙门浮陀跋摩主译、道泰笔受翻译的百卷《大毗婆娑经》仍在冲刺完成。只是,发生在姑臧城的诸多译经活动,均不见昙曜参与。
看来,茂虔当政的6年时间里,昙曜初入凉土,年纪轻、资历浅,又师出无门,在注重师承的禅学之地姑臧城,他能受到太傅张潭的礼遇,寻得个立足之地,比起此时仍名不见经传的师贤已经算很不错了。同时表明,昙曜这时已具备一定的汉语交流能力。
二、罽宾:昙曜的故乡
一般认为,昙曜为罽宾人,但无直接支持的证据。
罽宾,是汉魏以前的称名,南北朝时称迦湿弥罗,今指克什米尔一带。罽宾盛小乘佛教,主张恪守佛教戒律,注重比丘自身戒律修行。该地域历史上曾为塞人所占,五世纪初,又遭白匈奴进犯,不堪侵扰的罽宾僧人,多离乡东游弘法。从东晋至南北朝,入华印度僧人共55人,其中来自罽宾的就有13人。前秦时期,在长安译经的昙摩蜱、僧伽跋澄、僧伽提婆等都是罽宾人。罽宾国虽以小乘教法著称,但也有大乘方等部的经典。
昙曜,“少出家”。由于同出罽宾的弗若多罗、昙摩耶舍、师贤等人也都是少出家,故有人据此认为“少出家”是罽宾僧人的特点。事实上,“少出家”现象普遍见于当时各国各地:北地人释慧义,少出家,风格秀举,志业弘正;凉州人释宝云,少出家,精勤有学行;临清人释普明,少出家,禀性清纯,以讖诵为业……所以,“少出家”尚不足以成为确认昙曜藉地的依据。欲探寻昙曜身世,有一个人和一部经不可忽视。人,指师贤;经,为《杂宝藏经》。
师贤是罽宾国王种人,他与昙曜先时同处于凉州,后又共同活动于平城。师贤在平城做道人统时,昙曜可能为辅职。和平初,师贤卒,昙曜继职。二人之间的关系,可谓于风轻云淡中见耐人寻味处。
师贤概年长于昙曜,其实他在凉州期间知名度尚不及昙曜,一生中也没有留下一纸译经。徙平城初期,师贤仍默默无闻,值玄高因罪被杀后,他才一跃荣升为道人统。做了那么大的僧官,佛教文献却不载,活端端地就像生生没此人此事!若不是《魏书》记载,师贤之名将湮灭于世。《魏书》云:
京师沙门师贤,本罽宾国王种人,少入道,东游凉城,凉平赴京。罢佛法时,师贤假为医术还俗,而守道不改。于修复日,即反沙门,其同辈五人。帝乃亲为下发。师贤仍为道人统。[2](P3036)
“道人统”一职始置于道武帝天兴元年,赵郡沙门法果为首任,明元帝时法果仍任此职,直至泰常(416-423)年中示寂。法果世寿八十余,其后由谁接替统领僧界,史书未载。文成复法后既称师贤“仍为道人统”,说明太武灭法前他可能已出任此职。
太平真君五年(444)九月十五日,43岁的玄高在平城东隅因诬被杀,追随他的凉州沙门、尚书韩万德的门师慧崇一同受诛遇害。次年五月十七日,玄畅仓惶逃离平城,南奔扬州,成为玄高罹难后唯一免灾南渡的弟子。
玄高,冯翊万年(今陕西省临潼)人,早在西秦国时就受到内外敬奉,被崇为国师。进游凉土后,为沮渠蒙逊深相敬事。北魏灭凉后,玄高被拓跋焘的舅父阳平王杜超迎请至平城,对于魏庭来说,玄高归之平城是一大盛事,它弥补了当年北魏与昙无谶失之交臂的遗憾。玄高既达平城,大流禅化,深受太武信重,此外,崇仰佛法的太子拓跋晃还事高为师。结果后来太子晃被谗有纂承之谋,太武帝心生疑窦,玄高既为太子师,即以教唆太子谋逆罪被羁押杀害。
玄高事件中,师贤、昙曜均不受牵连,说明他们当时处于玄高僧团势力范围之外。玄高死后,师贤被任命为道人统,成为北魏佛教的领袖。“沙门昙曜有操尚,又为恭宗所知礼”,太子晃师礼昙曜,也是玄高遇害之后的事情。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关中地区爆发盖吴起义。次年二月,太武帝亲征平乱,诏令全国灭法。法难时,师贤留在平城以医术行世,昙曜选择去了中山,两人分道避难,不致同灭。复法十余年后,师贤死了,昙曜接替其职。师贤既为罽宾人,昙曜与其相随相行、相处相继,既无师承关系,为同乡的可能性就增大了。
昙曜一生的光芒全部绽放在了平城,他的成就集中表现在文成复法后的沙门统任上,开窟造像、翻译佛经、改制寺院经济。他“慨前凌废,欣今载兴”,集诸众僧,广译佛经,以“流通后贤”、“住持无绝”。武州山通乐寺所设的官署译场,是中国石窟寺最早的译经场。昙曜译经僧团主要人员有吉迦叶、常那邪舍、昙靖以及负责笔录汉文的刘孝标等。
昙曜在武州山石窟寺组织过两次译经活动,一次是在和平三年(462),另一次是在延兴二年(472),相隔十年。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第六记云:“以和平三年壬寅故于北台石窟集诸德僧,对天竺沙门译吉义等经三部。……以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壬子,为昭玄统沙门昙曜译《大方广十地》等经五部,刘孝标笔受。”[1](第55册,P539-540)又,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第三云:“和平元三年昭玄沙门昙曜欣三宝再兴,遂于北台石窟寺,躬译《净度三昧经》一卷、《付法藏传》四卷,流通像法也。”[1](第49册,P43)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并记云:“《杂宝藏经》十三卷(阙)、《付法藏因缘经》六卷(阙)、《方便心论》二卷阙。右三部,凡二十一卷。宋明帝时,西域三藏吉迦夜于北国以伪延兴二年,共僧正昙曜译出,刘孝标笔受。此三经并未至京都。”[1](第55册,P13)
《魏书》记载的“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耶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此“新经十四部”,应包括以上两次译经的内容。
昙曜与吉迦叶在译经上关系甚密。
吉迦夜,又称“吉弗烟”,西域人,“游化戒虑,导物在心”。他与昙曜共同翻译了《方便心论》、《杂宝藏经》、《大方广菩萨十地经》,重译了昙曜于和平三年独立翻译的《付法藏传》四卷(今已不存)。关于重译《付法藏传》一事,陈垣先生说:“据现存大藏经《付法藏因缘传》六卷,题‘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可见吉迦夜当时系以昙曜所译者为底本,而从新改译,又在目上加‘因缘’二字也。自吉迦夜译本行,而昙曜译本遂废。以今存昙曜译《大吉义神咒经》推之,昙曜所译较为朴僿,不如吉迦夜译之文采,亦未可知。此与笔受人极有关,吉迦夜译笔受人为刘孝标,孝标固南朝著名文学家也。”[3]
吉迦叶作为西域译师,精通梵文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汉语的文采倒不一定好于昙曜多少。昙曜屡与他合作,看中的正是他强大的梵文译读能力。他们的合作是由吉迦叶口诵梵语,昙曜作为双语翻译,把吉迦叶讲的胡语口译成汉语讲给刘孝标听,转录汉文。之所以要重译《付法藏传》是昙曜译经时尚未遇到吉迦夜,他拿到的译本不是梵文原本,内容不完整。而此时,不但有吉迦叶带来的梵文原文,还天赐刘孝标这等笔受良才。
刘峻,字孝标,本名法武,平原(今山东平原县)人,本是东汉皇室胶东康王刘寄之后,生于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卒于梁普通二年(521)。他历宋、齐、梁三朝,是著名学者和骈文家,以注《世说新语》扬名后世。陈垣先生说:“以今日观之,孝标之注《世说》及撰《类苑》,均受其在云冈石窟寺时所译《杂宝藏经》之影响。印度人说经,喜引典故,南北朝人为文,亦喜引典故。《杂宝藏经》载印度故事,《世说》及《类苑》载中国故事。当时谈佛教故事者,多取材于《杂宝藏经》,谈中国故事者,多取材于《世说新语注》及《类苑》,实一时风尚。”[3]皇兴三年(469)北魏攻陷青州,这是南北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时年8岁的孝标被掳至中山,后又转徙平城。11岁时,迫于生活,他在武州山石窟寺出家为僧,因其才华出众,被安排参与译经活动。这一年是延兴二年,正值昙曜第二次译经期。《杂宝藏经》是吉迦夜与昙曜此次共译的重点经目,由刘孝标笔受。年仅11岁的孝标能胜任翻译工作吗?对此,陈垣先生早有置疑,认为孝标最多不过是“笔录”。太和十年(486)二月,因仕途不得意,孝标逃往江南,但他在云冈石窟寺译经的这段经历,对以后的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杂宝藏经》梵文原本今已散失,它是一部杂集抄聚分散在北传四阿含经以及各部派律藏中的因缘、譬喻及本生故事的小乘经集,全书共十卷,计121则故事,入梁后又增补为十五卷。全卷故事大致分为孝养、慈悲、业力、谄伪、诽谤、行施、教化、诤斗等八类,劝人作福、持戒、出生死、成菩提。该经译成后首先被用于云冈第9、10窟中,反映了沙门统昙曜作为佛教领袖地位的影响力。长广敏雄先生说:“第9、10双窟后室南壁充斥因缘故事浮雕,而且其多出典于《杂宝藏经》,这即便不是沙门昙曜直接筹划的结果,也不能否定他所起的某些作用(况且无法断然排除他直接筹划的可能性)。”[4](P206)
《杂宝藏经》中的许多故事发生地都是在罽宾。卷九“难陀王与那伽斯那共论缘”中的难陀王即指希腊人大夏王弥兰陀(或弥兰)王,“那伽斯那”则指那先比丘,他们的年代约在佛灭后二百年顷;卷八“月氏国王与三智臣作善亲友缘”中的言月支王名栴檀罽尼咤,其第一智臣是马鸣尊者。“栴檀罽尼咤王即迦腻色迦王,与马鸣尊者关系深厚,马鸣应为公元二世纪初人(A.D.100-160),与迦腻色迦王的时代相当。因此本经可视为在公元二世纪之时完成。”[5]经中提及的弥兰陀王、迦腻色迦王均曾统治过西北印度,说明《杂宝藏经》梵本应出自罽宾一带。
罽宾地区流行撰集譬喻类经典,是与该地区较完整地保存了小乘佛教“根本说一切有部”分不开的。“说一切有部”,简称“有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称之为毗昙宗,又称因缘宗。罽宾僧人精修毗昙学,毗昙经是来华僧人所携经卷中最多的一种。将譬喻故事与佛、菩萨、弟子传记结合在一起再去教化信众,通常会产生更强感染力的释法效果。[6]
昙曜选译《杂宝藏经》不是偶然的,这意味着他作为罽宾人对经中所反映的罽宾社会生活以及佛学理念所持有的与生俱来的兴趣与亲近感。
三、昙曜卒年
昙曜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经历了太武、文成、献文、孝文四朝,期间险象环生,略有疏忽,必以生命为代价。北魏伐凉时,他守待姑臧城豪赌魏军对他的善待,后至平城如日中天;入魏不久,他以不介入僧团,不介入政治派系的政治智慧与经验,轻松规避了玄高案;太武法难时,虽“誓欲守死”,终逾灭法之劫;文成复法,经举荐,“被命回京”,自导自演了一场“马识善人”的情景剧,得蒙重任,官至沙门统职;献文时,完美避染帝后宫闱之争,在异常复杂的政治交锋缝隙中独善其身;孝文时,游刃于冯氏、孝文“二皇”之间,将沙门统职权进行到底,牢握至终。针对太武灭法时的“胡本无佛”论,他主持营建的象征北魏五帝的“昙曜五窟”(第16~20窟),依靠皇权势力,既赢得统治者的首肯,又广聚沙门、同修定法,传达了让佛法流通后世、永存无绝的三世佛思想。每一生死攸关时刻,高僧昙曜都无不闪烁其卓越的佛教智慧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北魏僧官制度在道武帝一朝就设立了全国最早的僧务管理机构“监福曹”,“道人统”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全国最高僧官,法果、师贤均曾担此要职。文成帝时调整了僧署及僧官制度,改“监福曹”为“昭玄曹”,“道人统”为“沙门统”,昙曜为首任沙门统。北魏国家政权通过这一僧官体系控制和处理日常僧务工作。僧官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表明北魏政权以佛治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的政治态度。和平初,昙曜创造性地提出设立僧祗户、佛图户制度,解决了灾民赈济、救危急难的问题,取得了极好的社会效果。
据《魏书》记载,延兴二年夏四月,山东济州东平郡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灵像发辉,变成金铜之色。殊常之事,绝于往古;熙隆妙法,理在当今。有司与沙门统昙曜令州送像达都,使道俗咸睹实相之容,普告天下,皆使闻知。”[2](P3038)这也是昙曜在《魏书》中的最后一次露面,当时仍为沙门统。
道宣《广弘明集》卷24“帝以僧显为沙门都统诏”载:“近得录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门都统。比考德选贤,寤寐勤心,继佛之任,莫知谁寄。或有道高年尊,理无萦纡;或有器玄识邈,高挹尘务。今以思远寺主法师僧显,仁雅钦韶,澄风澡镜,深敏潜明,道心清亮。固堪兹任,式和妙众。近已口白,可敕令为沙门都统。又,副仪贰事,缁素攸同,顷因辉统独济,遂废兹任。今欲毗德赞善,固须其人。皇舅寺法师僧义,行恭神畅,温聪谨正,业懋道优,用膺副翼,可都维那,以光贤徒。”[1](第52册,P272)诏文的发布时间不详,由文意知是孝文帝与众臣商议拟定思远寺寺主僧显继任沙门统、皇舅寺法师僧义任副职之事。“副仪贰事”是前道人统所设的僚属,不知何因,过去由昙曜一身兼任,相当于废弃了此职。昭文表明,此时的沙门统昙曜已经卸职或者已经亡故。“思远寺,即方山(在今大同城北25公里)思远浮图,实为文明太后冯氏陵墓守灵之寺。太和三年(479)建寺,十四年(490)九月太后崩。孝文帝先后多次驾临方山,僧显为帝知赏,当在此间;擢任沙门统,当在此后。分析诏书,显统受任时,曜统已过世良久。”[7]
唐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1记:“《大吉义咒经》一部四卷。右,后魏太和十年昙曜译。”[1](第55册,P377)这是史籍中有关昙曜的最后可考时间记录。概译罢此经,昙曜已寿终正寝,其卒年不晚于文明太后,约当487-489年间。
永平二年(509),沙门统已更由惠深出任。永平四年(511),尚书令高肇奏言:“故沙门统昙曜,昔于承明元年,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立课积粟,拟济饥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2](P3042)宣武时僧祇户制度仍在沿用,昙曜早化为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