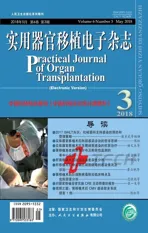实体器官移植术后早期细菌感染的抗菌治疗
2018-01-29杨文杰刘懿禾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感染科天津3009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ICU
杨文杰,刘懿禾(.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感染科,天津 3009;.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ICU)
器官移植是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的最有效手段,然而术后感染是最主要并发症之一,尤其随着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增加,多重耐药菌(multi-drug resistant bacteria,MDR)感染的发生率进一步增加[1-3],已成为患者预后不良的重要原因。因此,对器官移植者感染的有效防治是成功实施器官移植的重要环节。
根据感染病原菌的侧重不同,器官移植术后感染常分为3个阶段:术后30天以内发生者为早期感染、30 ~ 180天为术后中期感染、术后180天以后为晚期感染。尽管部分感染如导管血流感染、导管相关尿路感染、气管插管相关感染可以发生于术后任何阶段,但不同时间段病原菌分布特征不同,可以为移植术后发热患者最初的鉴别诊断、病原菌的评估提供重要依据[4], 超过50%的细菌感染发生于术后30天以内[5-6]。
1 实体器官移植术后早期感染的危险因素
移植术后早期感染通常和手术相关,病原菌多来源于院内环境及供体、移植受者自身携带。供者来源相关感染(doner-derived infection,DDI)发生率虽然不高,但病死率高达55.7%[7]。尤其是多重耐药菌感染的风险在器官捐献者经历长期入住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unit care,ICU)、多重耐药菌定植或感染、接受多种有创医疗干预后明显升高,部分供体捐献者病情危重,用于筛查和确定潜在或活动性感染的时间窗很短,使移植术后早期发生感染的风险增高。2015-2016年两年期间我国11家移植中心4419例移植手术患者调查显示,DDI发生率为1.02%,其中细菌感染41例占85.4%,其中碳青霉烯类耐药的革兰阴性(G-)菌占73.3%,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vancomycin-resistantEnterococcus,VRE)占17.1%,苯唑西林耐药的葡萄球菌占9.8%[8]。移植受者高龄、基础疾病、营养不良及免疫抑制剂使用、术前长期住院、多重耐药菌感染或定植、近期抗菌药应用、留置导管都会导致移植术后早期感染的发生,并且耐药菌感染发生率增加。移植器官保存液污染、手术时间过长、术中出血量大、留置异物等、移植器官灌注不良、再次移植或再次手术、吻合口瘘或肠瘘、不恰当的手术预防用药以及手术室环境因素等都是手术相关感染的危险因素[4,9]。因此,术前供体和受者的筛查、术前供受体感染的有效控制、包括抗菌药物的预防应用在内的围术期综合防控措施是减少术后感染的重要手段。
2 实体器官移植术后早期感染病原微生物分布与耐药现状
实体器官移植术后早期感染发生的部位、病原菌分布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差异,但病原菌阳性率普遍较低,多数研究阳性率不足30%[10-12]。Barchies等[13]对10年间330例移植患者随访研究发现,术后早期感染发生率占26.7%,总体上感染病原菌以G-菌居多,占67.9%,常见分离菌为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 Pneumoniae,KP)、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革兰阳性(G+)菌中屎肠球菌最常见,占G+菌的57%,其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19%)。药敏结果显示分离菌耐药严重,其中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carbapenem-resistantKlebsiella Pneumoniae,CRKP)占67%、MDR大肠埃希菌61%、MDR鲍曼不动杆菌50%、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分离率40%、甲氧西林耐药的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100%。意大利的研究显示,碳青霉烯类耐药的G-菌分离率高达26.5%,其中CRKP分离率最高为49.1%,中位时间是移植术后24天(IQR 14.5–30.5天) ,肝移植术后发生最早为18天,肾移植术后发生较晚,为29天;术前住院大于48小时的患者碳青霉烯类耐药的G-菌感染明显早于术前住院小于48小时的患者,两者分别为6天和26天。术后长时间住院以及肺和心脏移植患者是移植患者碳青霉烯类耐药的G-菌感染的危险因素[14]。对肾移植患者的研究显示,反复发作的尿路感染中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carbapenemresistantEnterobacteriaceae,CRE)感染比例 逐渐增加,第一、二、三次尿路感染中CRE发生率分别是 13%, 38% 和 45%[15]。G+菌中 VRE分离率逐年增高,已居于G+菌的首位,MRSA血流感染多见于肺移植患者,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感染多来源于中心静脉导管[12,16]。我国的调查显示病原菌耐药情况更为严重、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更常见[7,12],而耐药菌感染者是移植失败的重要原因[2,17]。
3 实体器官移植术后早期感染的抗菌治疗策略
移植术后感染的诊断依赖于临床表现和微生物学检查。但由于移植术后患者应用包括糖皮质激素在内的抗排异药物,临床表现往往不典型,缺乏发热等感染常见症状、微生物检测阳性率低[18]。而药物不良反应、排异等可以表现为发热和其他感染相关症状、定期常规微生物培养结果亦不能除外污染或定植,使得感染诊断困难。患者免疫抑制状态、耐药菌感染及药物间相互作用、移植术后器官功能状态、营养状况等多方面因素使抗感染治疗更复杂。
经验性抗菌药物的选择应依据当地或本中心的流行病学数据以及患者耐药菌感染或定植史、既往用药史等,充分考虑耐药风险、感染的严重程度。临床症状不典型的微生物培养结果需根据采集方法、部位等与污染和定植鉴别。目标治疗应基于体外药敏结果、感染部位组织浓度、适应证、不良反应以及费用等综合考虑[19-20]。抗菌疗程应根据感染的病原菌、感染部位、治疗反应、感染源的控制、不良反应的治疗个体化评估。感染源的控制-移除感染植入装置、充分引流,以及血流感染时迁徙性感染灶的筛查,都是有效控制感染的重要环节[21]。
轻中度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肠杆菌科菌感染(包括尿路感染、肝脓肿、胆道感染、腹膜炎、肺炎等局部感染)可结合药敏结果选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等,疗效不佳时可改为碳青霉烯类;重症感染宜首选碳青霉烯类,经治疗临床稳定后可降阶梯为β-内酰胺类抗菌药/β-内酰胺酶抑制剂合剂[22]。碳青霉烯类抗菌药耐药的G-菌常常为广泛耐药或全耐药菌株,建议联合用药[23-24],常用药物有[24-25]碳青霉烯类、替加环素、多黏菌素、磷霉素、氨基糖苷类、氟喹诺酮类、具有抗假单胞菌属的β-内酰胺类、含舒巴坦的制剂等等,需注意的是多黏菌素的异质性耐药问题,以及替加环素治疗过程中敏感性下降的问题,有报道多黏菌素异质性耐药发生率为10% ~ 100%,耐药率为0% ~ 46%。在治疗中应定期复查药敏试验。时间依赖性抗菌药应增加单次给药剂量、延长静脉输注时间以提高治疗成功率[25-26]。治疗药物浓度监测(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可以有效提高多重耐药G-菌引起的难治性感染的成功率[27]。有报道厄他培南联合大剂量美罗培南可以有效治疗产KPC型的CRKP所致血流感染[28],新开发的抗菌药头孢他啶/阿维巴坦和ceftolozane/他唑巴坦的三期临床显示对产KPC和0XA-48型碳青霉烯酶的G-菌疗效显著,有望在移植术后感染的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26]。
MRSA和VRE是移植术后感染常见的病原微生物,多见于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尿路感染、手术切口感染、腹腔感染[29-30]。常用药物万古霉素(VRE除外)、替考拉宁、利奈唑胺、替加环素、达托霉素、泰拉万星、奎奴普丁/达福普丁等药物。选择万古霉素治疗MRSA感染时应注意体外监测最小抑菌浓度(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值,如MIC≥1.5 mg/L时应选用其他药物,万古霉素高MIC值与治疗失败以及血流感染病死率升高相关,万古霉素谷浓度维持15 ~ 20 mg/L可提高治疗成功率。此外,需要关注的是,万古霉素MIC升高的MRSA菌株达托霉素的敏感性也降低,达托霉素不能用于治疗肺部感染,治疗后持续菌血症或微生物疗效失败时需警惕达托霉素急性耐药的发生[29]。
肠球菌对头孢菌素、抗葡萄球菌青霉素类、克林霉素天然耐药。VRE感染多发生于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如瘘或狭窄,尤其是再通或经皮介入、以及胰肾联合移植术后肾脏替代治疗、肾造瘘等。治疗可根据药敏情况给予氨苄西林联合氨基糖苷类药物治疗[30],屎肠球菌vanA介导耐药最常见,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均耐药,vanB型菌株对替考拉宁敏感。泰拉万星对vanA型VRE无活性,新的头孢菌素头孢吡普和头孢洛林对万古霉素敏感和耐药的粪肠球菌均有效,但对屎肠球菌无效,而替加环素由于浓度原因不适于治疗原发血流感染和尿路感染。
部分药物如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应注意给予负荷剂量、血药浓度监测、以及肝肾功能、血小板计数监测。需注意的是我国临床医生处方替考拉宁往往存在剂量不足,正确用药方法是根据不同部位感染给予负荷剂量6~12 mg/kg,q 12 h,共3次,维持剂量6~12 mg/kg,qd,根据肌酐清除率和药物浓度监测调整剂量[31]。
4 实体器官移植术后早期感染的防控措施
实体器官移植术后早期细菌感染的防控需从术前、术中、术后多环节综合防控。移植供体活动性和潜伏感染以及移植器官细菌定植都可能导致移植患者的术后感染,因而对于供体应常规行血常规、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以及影像学检查和血、尿、呼吸道分泌物等微生物培养检查,潜在的供体应定期行上述检查。供者器官保存液也应列为感染评估的常规,以便及时发现感染和对术后感染早期启动目标治疗,部分高危供体(如碳青霉烯类耐药的G-菌血流感染、未有效治疗的多重耐药G-菌感染、单核细胞增多性李斯特菌、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应禁止器官捐献[7-8]。对于术前存在感染的器官捐献者至少接受24 ~ 48小时抗菌治疗且临床有效才能进行移植手术。有研究报道肝移植受者术前选择性肠道去定植可以减少术后感染的发生[32]。对于接受感染高风险供者器官移植的受者应采取有效的感染防控措施、术前供体存在活动性感染时,移植受者术后应继续抗感染治疗,对于G-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念珠菌至少治疗为14天,低毒力菌株疗程可以缩短至最少7天[7,33]。围术期感染综合防控措施包括患者营养状态、血糖水平、医护人员手卫生、环境卫生及温湿度、备皮的时间和方法以及预防用药的品种、剂量、疗程、时机等等都与术后感染的发生密切相关[34],需要认真考虑和规范化处理。
总之,实体器官移植术后细菌感染是导致患者预后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仔细筛查、选择合适的供者,对于潜在供者定期监测相关感染指标,已存在感染者在有效控制感染后选择恰当移植时机。严格围术期感染控制措施、缩短受者术前术后留院时间,发生感染后积极留取微生物培养或相关血清学检查,根据培养结果选择恰当抗菌药物、足剂量、足疗程治疗是有效控制术后感染、防止发生细菌耐药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