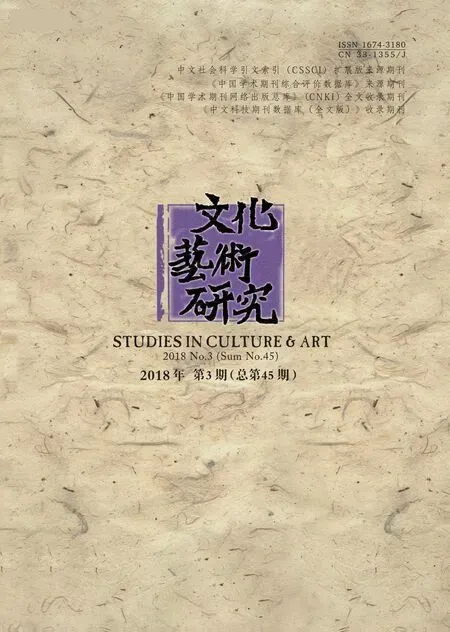隋唐时期江南地域商业行为的音乐生产与消费*
——隋唐时期江南音乐经济研究之二
2018-01-29韩启超
韩启超
(浙江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隋唐时期经过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江南经济快速发展,城镇人口迅速增长。自隋大业五年(609)至唐天宝元年(742),江南人口总数净增四倍多,跃居全国第二。[1]与此相适应的是江南土地进一步得到开发,环太湖流域由于农耕技术的发展、政府对水利建设的重视,稻作技术提高,一跃成为天下主要粮仓。[2]伴随着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多,隋唐政府对江南郡县设置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如隋代江南有68个郡,唐时又新增18个郡。经济的发达与交通的便利也促使江南之地陆续出现了类似北方都城的繁华中心城市,据《隋书·地理下》记载,宣城、毗陵(今常州)、吴郡(今苏州)、会稽(今绍兴)、余杭(今杭州)等地是“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3]603。
经济的发达,城市的繁荣以及自南朝而来的丰厚文化底蕴,使得隋唐时期江南文士层出不穷,北方的豪绅富商、士人官员、歌伎都纷纷来到江南城镇安居乐业,形成了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较高文化修养的庞大消费群体,构成了市民消费的主体,导致以声色为核心的消费风尚在江南蔓延。[4]社会纵酒享乐之风盛行,都市乐舞笙歌不断。诗人常常在此流连忘返,写下无数与乐舞消费有关的诗作。如李白曰“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5]1817(《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醉》),杜牧称江南之地“绿水桥边多酒楼”[5]5963(《润州二首》)。于是,茶楼酒肆、乐舞娱乐或携伎出游、酣歌宴饮,成为文人的一种时尚生活。
与此同时,江南的民间宗教活动也渐趋频繁。每年的春社秋社,祭祀乐舞活动极为壮观,男女老少、城内城外踏歌而舞,热闹非凡,所谓“南方淫祀古风俗,楚妪解唱迎神曲。……听此迎神送神曲,携觞欲吊屈原祠”[5]2144(李嘉祐:《夜问江南人家赛神因题即事》)。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5]5964(《江南春》)诗句也生动地描写了南朝以来江南佛教盛行的状况。
因此,这一历史时段、这一地域范围内的音乐经济发生、发展状况极具特色。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生产与消费是音乐经济的两个基本环节;从性质来看,这种循环过程可以分为商业性和非商业性两种,非商业行为的乐舞生产与消费更多的是指政府主导与私家蓄伎行为中的乐舞经济,它背后的动力推手则是国家乐籍制度。a参见笔者《隋唐江南非商业行为的音乐生产与消费》一文,刊载于《艺术百家》2018年第2期。而商业行为中的音乐生产与消费则以商业盈利为主要目的,乐人的服务性表演以及观众的娱乐消费都属于典型的市场行为。从史料来看,江南地域商业性的音乐生产与消费行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征,对整个江南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故本文专题论之。
一、隋唐时期江南地域商业行为的音乐生产
从音乐经济发生的场所和生产者的社会属性来看,隋唐时期江南地域商业性的乐舞生产方式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厅堂雇佣式、街头流动式、酒肆茶楼驻场式、民间风俗与宗教需求式。b曹丽娜在其硕士论文《唐代民间营利性乐舞的生产与流通》中将唐代民间营利性乐舞的生产归纳为街头卖艺、上堂卖艺等几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故本文所总结的四种生产方式是在其观点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提炼。见参考文献[19]。下面分而述之。
(一)厅堂雇佣式商业乐舞生产
厅堂雇佣式商业乐舞生产,是指社会上的在籍或非在籍乐人被当时的官员、贵族、文人、富商豪绅等雇用,并随之到雇主的府邸、厅堂或其他指定地点进行乐舞生产表演,并由此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雇主往往会提前支付艺人定金或酬劳,表演之后也会额外馈赠物品或金钱,以作为奖赏。如江西观察使在滕王阁举行的一次宴会上雇用豫章在籍乐人张好好演出,由于张的表演极为出色,主人便“赠之天马锦,副以水犀梳”[6]187。而贵族文人除了让所雇艺人在私家厅堂宴享时表演之外,还常常令其在游宴之中从事表演服务。如扬州诗人徐铉《月真歌》一诗描述了翰林殷舍人携广陵名伎月真赴宴,并令月真为在场宾客演奏琵琶的情景:“扬州胜地多丽人,其间丽者名月真。月真初年十四五,能弹琵琶善歌舞。……花前月下或游从……调弄琵琶郎为拍。”[5]8556
从生产者来说,这些受雇艺人的社会属性比较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来源于政府管辖的在籍乐人。隋唐时期政府有着严格的乐籍制度,从宫廷到江南州府辖有各类在籍乐人,他们是政府应差的主要群体。但在唐宪宗以后,由于宫廷乐人过多,教坊经费减少,管理松散。部分闲置的教坊乐工为了获取额外收入或明或暗地受雇于江南州府或驻扎在江南的军队,通过乐舞生产获取商业回报。如唐敬宗宝历二年(826)九月,京兆府刘栖楚上奏云:
伏见诸道方镇,下至州县军镇,皆置音乐,以为欢娱。岂惟夸盛军戎,实因接待宾旅。伏以府司每年重阳、上巳两度宴游,及大臣出领藩镇,皆须求雇教坊音声,以申宴饯。今请自于当已钱中,每年方图三二十千,以充前件乐人衣粮。伏请不令教坊收管,所冀公私永便。从之。[7]631
显然,京兆府刘栖楚奏折中所言情景属于政府认同的雇佣式商业演出行为,而更多的商业雇用则是一种私人行为。尤其是一些知名宫廷乐人因深受贵族文人的追捧,而私自受邀进行商业演出已经常态化。如顾况在《李供奉弹箜篌歌》诗中所描述的太常乐师李凭“白日为官家演奏,夜晚则与士流共娱乐”[8]。有开元时期“吹笛为第一部”之誉的宫廷教坊乐人李谟,曾因故请假去越州(今绍兴)商演,地方人士“公私更燕,以观其妙”。因其名气太大,越州的进士们也集资两千文邀其在镜湖聚会之中吹笛。[9]1553显然,这种私自受雇演出所获酬金极为可观,远比其进行轮值轮训时所获俸禄或补贴更多。因为从唐代文献来看,宫廷乐人的待遇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当乐人深受帝王喜爱时则待遇丰厚,俸禄超越宰相,甚至“大起宅第”,而普通乐人则是“四季给米”和免除部分赋税。[10]而在安史之乱后,政府已经无暇顾及乐人,更不要说给予乐人充分的俸禄和物质保障,这也正是在籍乐人竞相私自从事商业演出的根本原因。
江南州府管辖的在籍乐人受雇于地方权贵、文士进行商业性生产更是一种普遍现象。如唐长庆年间(821—824)杭州官伎商玲珑、谢好好二人,先是被时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邀请到府上以及随其在各种游宴中演出,后又被远居越州的元稹以重金邀请到府上演出。[11]54再如浙东观察使李讷在越州执政期间,每有小宴均请在籍乐人盛小丛檀板清歌助兴,还专门写诗《命妓盛小丛歌饯崔侍御还阙》记载其高超歌技。[6]209
第二,来源于流落江南或遣返到江南的宫廷乐人。流落江南的职业乐人主要是安史之乱后从宫廷逃逸出来的知名乐人,他们失去了政府的庇护,脱离了乐籍,四处流浪,常常以被雇用的形式游走于江南的富商、官员和贵族之家,进行商业性演出。遣返的乐人主要是指宫廷在籍乐人因在宫廷服役时间较长,年老色衰之际,被帝王赦免,脱离乐籍,返回江南养老。所以这类生产者并没有生活保障,频繁地在雇主的各种宴享中演出是他们获取经济收入的主要方式。
从文献来看,这一时期流落江南的知名乐人极多,代表性的有曾深受唐玄宗喜爱,被誉为“歌值千金”的官伎许和子(又名永新)。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了安史之乱后她流落江南以卖艺为生的困顿生活:
自渔阳之乱,六宫星散,永新为一士人所得。韦青避地广陵,因月夜凭栏于小河之上,忽闻舟中奏水调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与永新对泣久之。[12]
宫廷知名乐人李龟年也流落江南,以乐舞养家糊口,据说杜甫曾与之相会并写下名诗《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5]2562
盛唐时期著名的宫廷乐人李谟安史之乱后也流落江东,曾在越州刺史皇甫政的宴享中表演笛乐以获取生存所需。李谟外孙许云封也是梨园小部音声乐僮,安史之乱后亦飘零江南及更远的南海近四十年,直到贞元初才由韦应物举荐入和州乐府(今安徽和县)。[13]宫廷乐人李秋娘也是如此,据杜牧《杜秋娘诗并序》诗中记载,杜秋娘原籍金陵人,善歌曲和演奏笛、箫,曾是浙西节度使李锜的妾,因丈夫叛乱而充入宫中为乐人,在宫廷服役三十年,后被赐还金陵,但已经是年老且贫,很难再以歌舞色艺来赢取丰厚的金钱,只能勉强度日。杜牧与其重逢时,其状况是“寒衣一匹素,夜借邻人机”[5]5938(《杜秋娘诗并序》),令人痛惜。同样,白居易《江南遇天宝乐叟》诗也记载了擅琵琶、法曲,常陪侍玄宗左右的梨园乐人飘零江南,以技谋生的凄惨晚景:
白头病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 ……从此漂沦落南土,万人死尽一身存。秋风江上浪无限,暮雨舟中酒一尊。涸鱼久失风波势,枯草曾沾雨露恩。[5]4811
显然,大量的宫廷乐伎流落江南从事商业性的乐舞生产,不仅提升了江南乐舞的水平,也极大地促进了江南音乐经济的繁荣。
第三,来源于城镇的职业乐人(娼妓)。她们未必隶属州府乐籍,具有较大的人身自由、较高的艺术水准和文学素养,常常以酒楼、茶肆、妓院作为固定的活动场所,是文人墨客、州府官员、军队竞相雇用的宴饮娱乐对象。如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就记载了当时的军队从社会上雇用职业乐人进行乐舞生产服务,而受雇的乐人则可以根据自己的艺术水准和表演内容进行议价,具有极大的自主性,所谓:“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14]这充分说明此类艺人的商业行为和自由定价行为已经深受社会普遍认同。
第四,来源于民间流动的卖艺乐人,以音乐表演为专长,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有自己的家室。如唐代著名民间乐人刘采春在浙东一带卖艺时,因歌喉和美貌而深受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元稹的赏识,邀请其到府上演出。其女儿周德华也擅长“杨柳之词”,被越副戎崔朗中邀请至府中演出。[15]144-145
综上所述,受雇到雇主指定地域进行商业乐舞生产的艺人普遍具有较高的音乐水平,表演内容相对丰富、表演形式多样,声色娱人是主要活动内容,而且往往会借此获取高额的经济收入。但这本质上是一种被动式的商业生产行为,产品的价格决定权总体上受制于雇主。
(二)街头流动式商业乐舞生产
街头流动式商业乐舞生产方式,是指乐舞生产者主要通过在州县城镇的街市上进行商业性演出的乐舞生产行为,它是一种街头卖艺式乐舞生产,具有极大的流动性。生产者往往是社会底层的职业、半职业艺人,乐舞技能水平相对不高,但为生活所迫而在闹市区、人群聚集之地从事生产。此类乐舞经济活动方式为宋元时期艺人的“冲州撞府”奠定了基础。
根据生产者的规模来看,此类乐舞生产方式有两种基本类型:
其一是个体性的商业乐舞生产行为。表演者往往孤身一人,四处流浪漂泊,常常在人群集聚之地通过自己的乐舞表演来换取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演出的内容和形式相对单一,消费群体也比较杂乱。如白居易的《听田顺儿歌》诗描写了深受宫廷乐人御史娘点拨的歌童田顺在民间四处传演,并赚取大量金钱的情况:“戛玉敲冰声未停,嫌云不遏入青冥。争得黄金满衫袖,一时抛与断年听。”[5]5060王建《观蛮妓》也描写了民间流浪艺人的商业乐舞生产情况:“欲说昭君敛翠蛾,清声委曲怨于歌。谁家年少春风里,抛与金钱唱好多。”[5]3434
其二是以班社为核心的团体性商业生产行为。表演者往往是一个班社,拥有多个乐舞艺人,每个班社成员都拥有不同的乐舞技艺,相互组合成为一个团队,以表演一些难度较大或需要人数较多的艺术样式,诸如参军戏、歌舞戏等。班社成员的构成、管理主要是依靠血缘关系或师徒关系为纽带,其中由家庭成员组成的班社最为典型,往往会有一到两个名角作为演出的核心人物。代表性的如周季南班社,由江南籍乐人周季南及其弟周季崇、弟妻刘采春、侄女(采春之女)为主要成员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艺,周季南、周季崇擅长参军戏;刘采春善歌唱,开唱后“闺妇、行人莫不涟泣”,代表作品有歌舞戏《踏摇娘》,歌曲《望夫歌》;刘采春女儿擅歌舞。[15]139-141范摅《云溪友议》卷下“艳阳词”条就记载了贞元、元和年间(785—820 ) 周季南的家庭戏班从淮甸到浙东从事商业演出的情况:
(元稹)廉问浙东……乃有排(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元公)赠采春诗曰:“新妆巧样画双蛾,幔裹恒州透额罗。正面偷匀光滑笏,缓行轻踏破波纹。言词稚措风流足,举止低徊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15]139-140
产生于北齐的歌舞戏《踏摇娘》在唐代演出时构成了一种班社模式,增加了伴奏,角色也由两个增加到三个。唐天宝年间(742—756)常非月的《咏谈容娘》就描写了其在江南演出的场景:“举手整花钿,翻身舞锦筵。马围行处匝,人簇看场围。歌要齐声和,情教细语传。不知心大小,容得许多怜。”[5]2125
总的来说,街头流动式商业音乐生产的特点是艺人们到处流动,就地选取场所,以自行营业的方式,用精彩的、大众化的、小型的、流行的乐舞产品来获取生存资料,即便是多人组合的班社,也都组织灵活,形式丰富。其消费对象主要是城镇市民,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审美趣味相对较低。
(三)酒肆茶楼驻场式商业乐舞生产
酒肆茶楼驻场式商业乐舞生产,是指音乐生产者多为年轻貌美的女性,乐舞技艺比较高超,所服务的场所一般比较固定,主要是江南都市中的酒楼、茶肆、妓院等商业性的娱乐宴饮之地,很少会更换表演场所。乐人与酒肆、茶楼、妓院是一种共生、相互依存的雇佣关系。从商业服务的性质来看,乐舞娱人和色艺娱人同等重要。
当然,在固定场所进行乐舞生产的艺人社会阶层相对较低,属于典型的贱民阶层,有乐籍和非乐籍之分,在籍人员往往是隶属地方州府管辖的官伎,非在籍乐人主要是酒肆、茶楼、妓院所蓄私家娼妓。其乐舞生产行为不仅是酒楼、茶肆或妓院营业销售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工具,也是乐人自己获取经济回报和生存资料的唯一途径。从文献来看,这些乐舞生产者大多是良家子女,因生活贫困卖身,或被歹徒诱拐贩卖沦落为娼妓,然后在鸨母的严格管理下,经过长期的训练,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音乐技艺。但她们常常受制于鸨母的苛刻驱使和严酷榨取,很难脱离约束成为自由身,很多人晚年命运极为悲惨。对此,孙棨《北里志》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诸女自幼丐育,或佣其下里贫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鱼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其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朴备至。(乐伎)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内。[16]1
由于社会观念的制约、身份的低贱以及从事的职业属性导致他们形成了一种与外部相对隔绝的生活状态,成为一个独特的生活群体。但在另一方面,这些乐舞生产者深受社会名流、贵族的追捧,收入极高。《北里志》记载,当时普通娼妓服侍客人宴饮时的收费价格是“每饮率以三锾,继烛即倍之”[16]2。而知名娼妓则更高,如名妓郑举举“曲中常价,一席四锾,见烛即倍。新郎君更倍其数,故云复分钱也”[16]4。因此,她们往往衣着华丽,生活奢侈。这就造成了一种经济上的高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低贱性背离的特殊社会现象。
胡姬也是酒肆茶楼驻场式商业乐舞生产者之一。进入江南地区的胡姬,以独特的异域风情受到了文人墨客的关注,也成为文人商贾流连酒肆的主要动因之一。因此,很多文人写下了大量有关胡姬的诗作,描述了胡姬们在江南酒肆之中乐舞生产的情景。如白居易曾在《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诗中描绘了他在苏州城内酒肆宴饮时观看胡姬乐舞生产的情景:
江南九月未摇落,柳青蒲绿稻穟香。姑苏台榭倚苍霭,太湖山水含清光。可怜假日好天色,公门吏静风景凉。榜舟鞭马取宾客,扫楼拂席排壶觞。胡琴铮鏦指拨剌,吴娃美丽眉眼长。笙歌一曲思凝绝,金钿再拜光低昂。日脚欲落备灯烛,风头渐高加酒浆。觥盏艳翻菡萏叶,舞鬟摆落茱萸房。[5]4968
从文献来看,隋唐时期胡姬在江南酒肆中演出形式多样,有歌舞、乐器独奏、小乐队合奏等。当然,最典型的是极具地域色彩的“胡舞”,诸如《胡旋》《胡腾》《柘枝》《凉州》《绿腰》等,风靡一时。诗人张祜曾在《观杭州柘枝》诗中描述了在杭州城内酒肆中观看胡姬表演的精彩场面:“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仙蛾暂起来。红罨画衫缠腕出,碧排方胯背腰来。旁收拍拍金铃摆,却踏声声锦袎摧。看著遍头香袖褶,粉屏香帕又重隈。”[5]5827杨巨源《胡姬词》诗也记载了胡姬在酒肆中驻场为宾客表演劝酒的场景:“妍艳照江头,春风好客留。当垆知妾惯,送酒为郎羞。香渡传蕉扇,妆成上竹楼。数钱怜皓腕,非是不能留。”[5]3718
显然,如此繁多的胡姬酒肆歌舞诗充分说明胡姬表演在江南的盛行,同时也表明江南经济的繁荣和民众的多样化乐舞需求,是胡姬从中原进入江南的主要驱动力。而胡姬的特色化表演也为江南地域音乐的发展增加了异域属性。
(四) 民间风俗与宗教需求式商业乐舞生产
民间风俗与宗教需求式商业乐舞生产,是指在江南广大的乡村以及寺院、道观等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的商业性乐舞生产行为。
在民间乡村风俗中进行的乐舞生产,其生产者往往是底层的流动艺人或乡村中兼职的农民,他们具有一定的乐舞表演能力,通过在固定风俗中,诸如婚丧嫁娶、社祭赛神、节庆日等进行商业性的乐舞表演,换取一定的物质回报或经济收入。据《唐会要》卷八十三“嫁娶”条记载,隋唐民间婚俗中有“下婿”“撤障”等重要的活动仪式,活动中,邻里乡村居民或业余的音乐从业者以音乐歌舞围挡逗乐,借此邀乞酒食,获得婚礼主家的赏钱。[7]1629社祭赛神也是如此,如唐末人杜光庭在《录异记》中记载,合州(今合肥)石镜人赵燕奴,以捕鱼杀猪为业,常常在驱傩活动中从事乐舞生产,以获取经济利益。[17]诗人张籍的《蛮中》诗也描绘了南方沿海一带民间祭祀活动的乐舞生产行为,云:“铜柱南边毒草春,行人几日到金麟。玉镮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5]4361
斗乐是民间风俗中乐舞生产的一种常见形式,它不仅加剧了民间商业性乐舞活动的激烈紧张的气氛,也提高了观众的参与热情。如《录异记》卷二云,赵燕奴 “每斗船、驱傩及歌《竹枝词》较胜,必为首冠”[17]。刘禹锡在《竹枝词》序中也说“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5]4112。尤其是在婚丧嫁娶活动中尤为凸显,雇主往往会聘请多个乐人或乐班进行乐舞表演,不同乐人或乐班之间为了获得更高的地位或经济报酬,竞相比赛,从而以激烈的斗乐场面来吸引观众。有时斗乐则是乐人之间的有意为之,由行会出面,双方相约在固定场所,进行乐舞比赛,优胜者则可以获得奖励或赌资。如白行简在唐代传奇《李娃传》中就记载了两个挽歌从业者分别代表各自班社在闹市之中进行斗乐的活动,获胜者则可以获得两万钱的奖励。[18]107-108
在宗教活动场所中进行乐舞商业行为,也是隋唐时期江南地域的一个典型现象,它主要表现在寺院为了弘扬佛法,吸引善男信女,获得更多的供养,从社会上雇用职业艺人进行乐舞表演,表演内容与宗教密切相关,服务的对象则是普通信众。如当时很多寺庙培养、组建音声,蓄养歌伎,形成“种种音乐,尽来供养”的局面。而表演的场景则是 “仍闻开讲日,湖上少渔船”[5]5650(姚合:《赠常州院僧》)。
二、隋唐时期江南地域商业行为的音乐消费
(一)酒肆中的乐舞消费
隋唐时期江南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北方民众也大举迁入,由此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这进一步推动了江南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江南城市的性质较前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城镇的经济功能得以大大强化,不少城市的经济功能超过其政治功能。[4]这导致以传统文化氛围浓郁为特色的江南城镇居民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娱乐之风,文人墨客、达官贵族的饮酒之风日益炽盛,各州府县镇酒肆茶楼星罗棋布。所以,唐诗中存在大量的文人墨客在江南酒肆中饮酒作乐的诗作,描绘了他们在余杭(杭州)、吴郡(苏州)、越州(绍兴)等都市中的乐舞消费生活,鲜明地凸显了这一时代特征。
如李白在南京、扬州游览时写下了很多诗篇,描绘了他与朋友在酒肆中把酒言欢,乐舞娱乐消费的场景:
叹息两客鸟,裴回吴越间。共语一执手,留连夜将久。解我紫绮裘,且换金陵酒。酒来笑复歌,兴酣乐事多。(《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5]1855
昨玩西城月,青天垂玉钩。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半道逢吴姬,卷帘出揶揄。(《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5]1817
白居易也描述过他在苏州酒肆茶楼中宴饮娱乐消费的场景:
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 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 交印君相次,褰帷我在前。(《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5]5259
诗人丁仙芝也在《余杭醉歌赠吴山人》中描绘了此种状况:“晓幕红襟燕,春城白项乌。只来梁上语,不向府中趋。城头坎坎鼓声曙,满庭新种樱桃树。”而他的消费成本则是“十千兑得余杭酒,二月春城长命杯”[5]1156。
当然,隋唐时期江南文士热衷于在酒肆茶楼中宴享娱乐、雅集酣歌,并将其作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与魏晋名士宴饮清谈之风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与前代不同的是,隋唐之江南更多的是一种商业性的娱乐消费。而东晋南朝文士的宴饮强调的是一种雅集和自娱,乐舞消费的对象是私家乐伎和自身,很少出现雇用乐人现象。
总的来看,酒肆茶楼中的乐舞消费者主要是文人、贵族、商贾,消费内容多以诗乐歌舞为主。此外,酒令艺术也是重要内容之一,它包括律令、骰盘令、抛打令等,后逐渐艺术化、歌舞化,形成了送酒歌舞、著辞歌舞、抛打歌舞三种类型,甚至又加入歌舞大曲、曲子、唱和等形式,是酒肆通过艺人进行歌舞劝酒营利的重要途径。[19]
(二)妓馆中的乐舞消费
隋唐时期在繁盛的江南都市中出现了许多商业性的青楼妓馆,尤其是在扬州、益州、杭州、越州等经济繁荣的大城市,青楼妓馆更为繁多、庞大。安史之乱后,江南城镇中的青楼妓馆渐趋奢华,知名的妓馆有扬州的赏心亭,润州(镇江)的千岩楼等。
从消费者来看,青楼妓馆是贵族、文人以及官员享乐的场所,从中也反映出他们奢侈生活的又一个侧面,如唐代诗人杜牧《遣怀》诗中曾感慨:“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5]5998张 籍《江 南 曲》 云:“倡 楼 两岸悬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5]205《北里志·序》则进一步指出了唐代妓院的繁盛以及出入其中的社会阶层情况:
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16]
消费者在青楼妓馆的消费形式主要集中在宴享饮酒、乐舞娱乐、游戏、侍寝等几方面。中唐以后社会娱乐宴饮之风盛行,青楼妓馆的消费群体日益壮大,这种消费需求的扩大也导致乐舞产品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
当然,妓馆作为乐舞消费的主要场所和消费形式,与文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的奢侈享乐之风有着密切关系。隋唐时期江南文人深受魏晋名士风流的影响,倡导“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生命追求,热衷于声色之娱。安史之乱的政治变革使得大量的文人找不到仕途进阶,只能隐居于桃红柳绿之中,流连于青楼妓馆,抒情达意,这进一步加剧了江南的颓废奢乐风气。
文人对声色娱乐的追求,对歌舞伎乐人员的竞相追捧,以及在诗酒之中与民间娼妓的密切关系,进一步推动了市井艺妓的身价,提高了乐舞消费的成本。如元稹《赠吕三校书》诗云:“共占花园争赵辟,竞添钱贯定秋娘”[5]4570,温庭筠《懊恼曲》曰“玉白兰芳不相顾,倡楼一笑轻千金”[5]266,就说明此种现象。与此同时,无数青楼歌妓也凭借文人的诗作提升了自己的地位,尤其是经济收入。如《云溪友议》卷五记载吴楚之地的狂士崔涯,常常流连于妓馆,“每题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 。扬州名妓李端端曾被他作诗嘲讽,导致门客稀少,鲜有问津。对此,李端端忧心如病,就伏于道旁乞得诗人哀怜,于是崔涯又重新写一首赞美诗,诗云:“觅得黄骝鞁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自此之后,一时富豪之士复臻其门。[15]70-71由此可见文士群体对青楼乐舞消费的主导作用。
(三)宗教场所的乐舞消费
隋唐时期江南宗教场所乐舞活动频繁,尤其是中晚唐之后,为宣扬教义,吸引百姓,寺院、道观等一般都有较固定的演艺游乐场所,甚至专门设立戏场。各个宗教场所也极为重视组织和资助以弘法为核心的音乐活动,并积极为各种民间艺术提供演出场地。因此,寺院、道观等宗教场所就成为了市民游览观光、集市、贸易及文化娱乐的活动中心,成为市民乐舞消费的重要阵地,每每有歌舞演出时消费者人数众多,观者如堵。
裴铏在《传奇》中记载了在南京钟陵西山的道教风俗乐舞活动中,民众广泛参与其间的情况:
钟陵有西山,山有游帷观,即许仙君逊上升地也。每岁至中秋上升日,吴、越、蜀人,不远千里,而携挈名香、珍果、绘绣、金钱,设斋醮求福佑。时钟陵人万数,车马喧阗,士女栉比,数十里若阛阓。[20]88
文献说明吴、越、蜀地民众不远千里而来,除了参加道观节庆活动祈求福报之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观看乐舞表演。因为在此种场合常常会有豪绅富商“多以金召名姝善讴者,夜与丈夫间立,握臂连踏而唱”[20]89。
显然,宗教场所的乐舞消费者主要是普通民众,但与其他场所不同的是,这些普通民众作为最主要的消费群体,并不需要为乐舞消费支付相应费用,很多情况下乐舞艺人的酬劳是由寺院或供养者支付。如在佛诞日前后,或“六斋”期间,佛教徒为了纪念佛祖、宣扬佛法,常出资雇用各种艺人来寺院戏场为善男信女演出,民众往往是自发前往免费观看。
寺院、道观之所以会积极组织各种技艺超群、形式丰富的表演,除了要弘扬佛法、道教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是获得善男信女的供养。事实也的确如此,每当寺院有演出时,观众数量极为庞大,所谓“寺前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人”[9]3148。这些数量众多的民众在进行免费的乐舞消费之余,也给寺院上供数量庞大的香火钱。从这个角度来说,普通观众在免费乐舞消费的同时也是付出了一定的经济成本,只不过是以一种间接形式显现出来。
当然,普通民众在宗教场所,尤其是依附在寺院、道观之中或附近的“戏场”“舞场”“歌场”进行直接的商业性乐舞消费也极为突出,如任半塘先生就考证了唐代寺院伎艺表演的商业性质以及民众入场需缴纳一定费用的状况:“慈恩青龙诸戏场,露天居多,设备简单,乃卖艺性质,凡入场者须纳赀。”[21]不仅如此,据唐代话本《庐山远公话》记载,当时的道场也出现了观众付费方能聆听的情况:
是时有勑:“若要听道安讲者,每人纳绢一匹,方得听一日。”当时缘遇清平,百物时贱,每日纳绢一匹,约有三二万人。寺院狭小,无处安排。又写远表奏闻皇帝……当时有勑:“要听道安讲者,每人纳钱一百贯文,方得听讲一日。”如此隔勒,逐日不破三五千人。[22]
这充分说明了乐舞经济的市场化行为在江南宗教场所中也普遍存在,而且导致社会普遍存在通过演出价格来调节消费的现象。价格手段不仅导致了消费群体的分层,也提高了宗教场所的商业性乐舞消费成本。
(四)民俗市场中的音乐消费
江南民众尚巫重祀,频繁的民间祭祀、婚丧嫁娶、节庆日等重要风俗中存在着大量的歌舞活动,由此构建了民俗市场中的营利性音乐消费。如隋唐时期江南地域无论普通民众,还是豪绅富商、贵族王公之家,婚俗之中必然要雇用乐人“广奏音乐”,“杂奏丝竹”,或者邻里乡民主动以歌舞来参与其间,索要赏钱。因此,对于雇主来说无论是主动雇用乐人还是被动享用乡民乐舞生产,其费用都极为高昂,以至“邀致财物,动逾万计”[7]1529。即便是富庶、王公之家也很难承受。所以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左司徒郎中唐绍就上奏帝王,请求禁断。[7]1529
节庆生日期间进行乐舞消费也较为常见,如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条就记载了民众为庆祝生辰而进行观戏、听小说等音乐消费的案例:“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23]
同样,在民间丧葬活动中也存在大量的乐舞消费,尤其是汉魏时期江南之地的厚葬之风,以及由此产生的雇用职业挽歌乐人的消费行为在隋唐时期得到延续和发展。民众出于攀比富贵的心理,竞相高价聘请乐人,如唐代传奇《李娃传》记载了荥阳公子郑生落难之际,学习挽歌,并成为凶肆歌者,表演水平是“曲尽其妙,无有伦比”,虽要价颇高,但雇用者极多。[18]107-108除了挽歌之外,鼓吹乐、傀儡戏也是丧礼中的重要乐舞消费内容。如傀儡戏表演时常常设置祭盘帷帐,有的高达九十尺,用床三四百张,雕饰穷极技巧。因此,此类乐舞消费成本也很高,所谓“大者费千余贯,小者三四百贯 ”[11]272。
显然,民众的奢侈丧葬乐舞消费成本支出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如长庆三年(823),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奏称当地百姓厚葬之风盛行,常常“于道途盛设祭奠,兼设音乐等。并以音乐荣其送终,或结社相资,或息利自办,生产储蓄,为之皆空,习以为常,不敢自废,人户贫破”[7]697。于是,希望朝廷下令“百姓等丧葬祭,并不许以金银锦绣为饰,及陈设音乐 ”[7]697。
综上所述,民间风俗活动中的乐舞消费极为普遍,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江南地域的奢侈风气导致民众的消费支出极高,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此种现象更为严重。这一方面说明江南风俗市场中的乐舞消费需求巨大,另一方面也说明江南经济的富足极大地支撑了此种乐舞消费行为。
三、 隋唐时期江南商业性乐舞生产消费的基本特征
相较汉魏南朝时期,隋唐时期江南商业性乐舞生产与消费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归纳起来,其音乐生产消费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
第一,商业性乐舞生产与消费的场所多样化。
随着隋唐时期江南经济的繁荣以及城镇格局的扩大,商业性乐舞生产与消费的场所随处可见。如前文所述,在州府的城镇之中,尤其是城镇经济繁荣的杭州、绍兴、苏州、南京等地,酒肆、茶楼、妓馆之中都遍布商业性乐舞生产与消费,乐舞艺人充斥店厅,文人、贵族、官员甚至普通民众往来络绎不绝。
不仅如此,一些城镇的街头巷尾、寺院道观及民众的婚丧嫁娶等场所都成为了商业性乐舞生产与消费的场所。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了大量依附寺院、道观、城镇的专业性音乐表演场所,诸如专门建设的高台、戏场、歌场、乐棚等。尤其是乐棚的出现,标志着露天戏场、高台等表演形式得到进一步发展,观众可以风雨无阻地进行乐舞消费。如元稹在《哭女樊》诗中描写乐棚在江南已经非常普遍,深受民众的欢迎,“腾踏游江舫,攀援看乐棚”[5]4514。显然,这些多样化的乐舞生产与消费场所充分体现了当时乐舞经济的繁荣景象。
第二,商业性乐舞生产从业者增多,乐人普遍具有商业意识和品牌意识。
隋唐时期江南的商业性乐舞生产者规模相对庞大,遍布城镇、乡村的各个角落,渗入了文人、贵族、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如城镇的酒肆中有大量歌伎劝酒歌舞,妓馆中充斥着大量的色艺俱佳的歌舞艺人,寺院、道观等宗教场所则通过雇用艺人、培养职业僧人、蓄养大批乐舞说唱艺人等形式为善男信女进行乐舞服务,而民众的婚丧嫁娶更是存在着大量的职业和非职业的乐舞生产者。因此,即便文献没有明确指出这一时期在江南从事商业性乐舞生产的乐伎数量,但从乐伎活动及唐诗中大量有关乐伎的诗文,就可以判断出这一时期的商业乐舞从业者之多,远超前代。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乐舞生产者普遍具有了商业意识和品牌意识。当然,广义上的品牌意识实际上是艺人在商业的生产中,强调乐舞技能的专一性和超越性,即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回报,艺人通过刻苦的训练提升自己的某一项专长能力,诸如曾为教坊乐工的李谟,因善吹笛,使得远在越州的士人联合集资聘请其演出。而当其流落在江南之际,也因为“吹笛为第一部”的美誉,在江南民间的乐舞生涯中获得不菲的经济回报。再如歌舞戏艺人刘采春一家,作为家庭乐班,为了打造品牌效应,乐班中的每个人都各具专长。因为有品牌意识,有所擅技艺,所以很多艺人可以在雇佣关系中享有较大的自由性,可以时刻根据自己的技艺水平、演唱内容进行价格调整。
第三,商业性乐舞生产与消费的产品类型多元化。
商业性乐舞产品类型与消费者的需求、场所,以及生产者水平有着密切的共生关系。消费场所的多样化以及生产者的水平和地位的差异性,消费者审美需求的多元化导致商业性乐舞生产与消费产品类型的多元化。因此,这一时期江南城镇中的商业性乐舞生产与消费的产品主要有四类: 一是曲子、文人歌诗、民歌等歌舞音乐;二是变文、俗讲等说唱音乐;三是参军戏、歌舞戏、杂耍、傀儡等散乐百戏;四是各类乐器制作与演奏。
酒肆和文人宴享之中的消费主要是诗乐作品,代表性的有《杨柳枝》《乌衣巷》《竹枝词》《春词》等,这些作品大都出自江南诗人之手,诸如金华的张松龄、张志和,嘉兴的朱巨川等。[24]除此之外,还有融诗乐舞于一体的酒令艺术、胡姬表演的异族歌舞,以及琵琶、琴等器乐演奏。
民间风俗场所中则出现了大量的鼓吹乐、民歌、祭祀乐舞。即便是寺院、道观等宗教场所也出现了专门的产品类型,其形式包括变文、说话、俗讲、歌舞、器乐等,一旦开场就会形成“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5]5712(姚合:《听僧云端讲经》)的现象。
除此之外,江南地域还盛行参军戏、傀儡等散乐百戏。如周季南和刘采春在江南到处传演“ 陆参军”[15]139-141,大司徒杜佑曾向自己的宾客幕僚吐露心迹,说自己最大的理想是退休之后能够常常入市看盘铃傀儡。[25]
因此,多元化的乐舞产品迎合了民众的审美口味,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各种社会群体的需求,推动了乐舞经济的商业化。
第四,商业性乐舞生产消费与国家乐籍制度存在背离现象。
从乐舞生产与消费背后的运行机制来看,这一时期江南地域商业性的乐舞经济发展与国家乐籍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相对于非商业性的乐舞经济是建立在国家乐籍制度的基础之上的现象来说,商业行为的乐舞经济则呈现出与国家乐籍制度相背离的现象,即国家乐籍制度的存在及其严格执行制约了商业性乐舞生产与消费的发展。
因为,商业行为乐舞消费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官员、文人、商贾,乐舞生产者的主体是隶属政府管理的在籍乐人(官伎)。正因为有了乐籍制度的制约,各类在籍乐人只能以应差的形式为国家服务,为各级政府服务,国家和地方政府则通过制度形式支付乐人俸禄,提供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减免赋税杂役等,从而调控和推动着在籍乐人为政府进行乐舞生产的积极性,满足政府的消费需求,这是一种内在循环的非商业性乐舞生产消费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乐籍制度保证了从国家到地方长期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职业乐人,保证了乐舞生产的非商业性。因此,在籍乐人不仅有着充分的生活保障,还受制于严格的制度约束,繁忙地应对各种公差,这极大地影响和限制了乐人从事商业活动的积极性。国家和地方州府乐舞消费的礼仪性、程序化和规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乐人的创新,导致乐人只能亦步亦趋地按照政府的意志与需求进行乐舞生产。
但是,随着唐中后期乐籍制度的一度松弛,加上安史之乱后宫廷及各级州府对在籍乐人的管理难以为继,导致部分在籍乐人失去了制度上的物质保障和规则约束,为了基本的物质需要和更大的商业利益,开始从事公开和半公开的商业乐舞生产。同时,政府规则的松弛也推动了民众的乐舞消费需求。由此,社会商业性乐舞经济得到突出发展,诸如王公大臣、文士商贾竞相雇用职业乐人进行各种形式的商演,甚至竞相抬高乐人的演出价格。乐人不仅频繁出入于商贾、大臣之家,还受雇于官员、文士游宴之中,甚至不远千里去外地商演。在江南商业发达的城市中甚至出现了政府组织乐人进行商业化生产的现象。与此相适应的是江南城镇社会娱乐丰富,乐舞从业者繁多,新的艺术形式产生,乐舞产品类型多样化,民众精神需求得到极大满足,整个社会乐舞发展呈现出繁荣局面。这充分说明严格的乐籍制度对于乐舞生产消费的商业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国家乐籍制度,社会乐舞的商业经济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