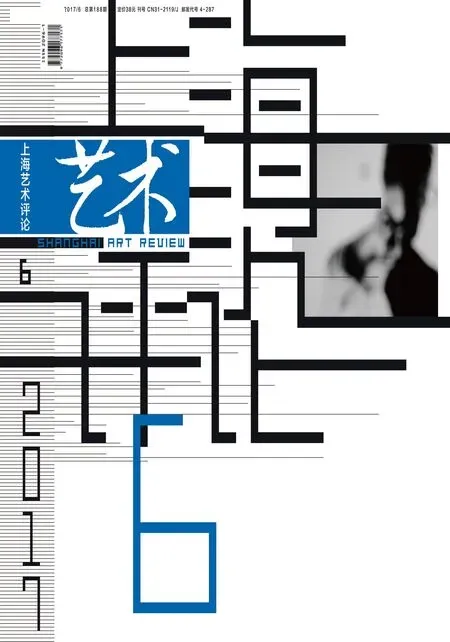中国神话没“谱”
2018-01-29刘宗迪
刘宗迪
一
神话源自洪荒的古老故事,神话也是亘古常新的话题。
在人类还不能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历史、故事和知识之前,先民们就已经在用史诗、用歌谣等口耳相传的形式讲述着天地开辟的奥秘、诸神造物的奇迹、祖先迁徙的传奇以及英雄历险的故事,讲述着人类与生俱来的爱的欢愉、生的欲望、死的恐惧,讲述着宇宙万象、日月运行、季节轮回、大地草木、林间群兽以及尘世间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的来历,讲述着时间的开始和终止,讲述着大地的深度和广度,讲述着人类的诞生、灭亡和再生,讲述着那些游荡于远方白云之间、出没于群山深处的神仙或者妖怪的故事……在狩猎时代的林间空地上,在农耕时代的丰收庆典上,在古代王公贵族的宫殿上,在乡间村社的树荫下、水泉畔、篝火旁,世世代代的歌手们一边抚琴弹奏一边高歌低吟的就是这样一些口耳相传的故事,这是每一个民族历史上最古老的故事,这些在口传时代流传下来的故事,蕴含了人类最深沉的智慧和情感,寄托了一个民族最古老的记忆,它们不是别的,就是所谓神话。
这些古老的神话,是人类最古老的故事,但这也是一些永远生生不息、新新不已的故事,因此是超越时代而恒久流传的故事。因为在这些古老神话瑰奇恢诡、古彩斑斓的表象下面,所蕴含的是人类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追问和回答。这是我们人类、我们每一个男人和女人从遥远的过去、到纷繁的当下、直至渺茫的未来都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解答的一些也许永远也不会有最终答案的问题,一些我们在还是懵懂初启的时候就会想到但是直到年迈迟暮之时仍然会念兹在兹的问题,一些每一代人都会不断重提、不断做出新的回答的问题。

电影《指环王》
比如说,宇宙是如何创生的?宇宙的创生在什么时候?终结又在什么时候?这个深不可测的星空究竟是亘古浑沌一团,还是自有其永恒的秩序和界限?又是谁为宇宙制定了这些秩序、划定了如此的界限?太阳为什么每天升起于东降落于西?月亮为什么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夜空中为什么会有漫天的星斗亘古不灭?一年为什么分四季?雷、电、风、雨是上帝的愤怒还是女神的哭泣?大地为什么会有高山、大河、湖泊、平原?大海之外是否还有另一个世界,那里住着像我们一样的人类,还是住着奇形怪状的怪物?谁发明了种植五谷养育我们人类?五谷的种子最初由何而来?什么人教会人类用火,化生食为熟食?我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是纯属偶然,还是得到了造物的特殊眷顾?世界上的第一人是谁?人由何而生?人为什么会死?人在死后究竟到了哪里?是否还有灵魂?人既然会死,那么这个短促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人为什么男人和女人长得不一样?为什么男人和女人天生就彼此渴慕又互相仇恨?为什么男女之爱会给人带来如此巨大的狂喜却又让人陷入无尽的怨恨?……
这是一些充满了孩子气但又足以气死哲学家的莫测高深的问题。它们是神话,它们也是哲学:这些问题关乎宇宙最深的奥秘、致高的哲理,所以它们是哲学问题,而古往今来的人们又只能凭直觉、想象和激情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对它们的回答往往变成神话。“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此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洪泉极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焉有虬龙,负熊以游?雄虺九首,倏忽焉在?”“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诗人屈原在《天问》中,借助迷离惝恍的诗歌意象所追问的就是这样一些横绝寰宇、纠缠人心的大问题,而在这些倏忽隐现、异彩纷呈的诗句背后,神话正如天末闪电般穿透鸿蒙,灵光乍现。针对诸如此类大同小异的根本性问题,每个民族从其各自不同的处境和才情出发,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各具千秋的神话体系和诸神谱系。
诸如此类关乎宇宙人生的根本性问题,是人类为了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位置、从而理解生命的意义所必定遭遇的问题,但是人类的生命相对于宇宙洪荒和悠长历史的有限性,又决定了我们永远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无法跳出自身短促的生命之外,站到生死轮回、劫波成毁之外,去审视和度量那浩瀚的宇宙和漫长的岁月,所以我们的所有回答,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女娲抟土造人,到大禹治水,直到现代宇宙学理论,包括大爆炸学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乃至现代巫师霍金的超弦理论,其实都仅仅是些幼稚得让上帝发笑的浅薄猜测。
因为没有最后的答案,所以才不息地追问,所以那些古老的神话才历经岁月沧桑而世代流传,经久弥新。远古游吟诗人、巫祝祭司的吟唱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成为绝响,但他们在史诗和歌谣中讲述的诸神故事、英雄传奇,却被后来的人们用文字铭记下来,印于泥版,刻于金石,著于竹帛而留诸永远。千百年来,那些古老的神话故事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演绎着,也许随着时过境迁,故事的人物换了,故事的场景变了,但故事的情节骨架没变,构成这个骨架的一个个母题要素也没变,故事依然是那个故事,故事中的智慧和教诲依然是那些启迪了先民们的智慧和教诲,正义战胜邪恶,死亡击溃生命,诸神死而复生,英雄历险归来……
二
直到今天,随着知识载体和传播媒体的发展,人类讲述故事的方式早已与口耳相传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古代游吟诗人孤独而悠长的吟唱早已被综合运用声、光、电等表达手段逼真呈现故事场景、给人的感官和心灵带来全方位的震撼的电影、电视乃至互联网、多媒体所代替,在日新月异的现代传媒艺术中,我们仍每每会与神话中那些古老的故事不期而遇。电影《星球大战》将古希腊神话搬上了浩瀚太空,希腊英雄的帆船换成了宇宙飞船;《指环王》将凯尔特神话移植到中州世界的高山峻岭之中,亚瑟王的命运圣杯变成了召唤黑暗势力的致命戒指;《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再现了西方中世纪传说中好巫师与黑巫师斗法的故事;《异形》中那些在陌生星球上潜生暗滋的致命怪物难道不会让你想起古老的东方奇书《山海经》吗?随着人类探索未知之域的步伐向外太空推进,人类对异类和怪物的恐惧也从大地上的边界移到了太空中的新边疆;至于日本卡通片《圣斗士星矢》,则更将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凯尔特神话、印度神话乃至中国神话熔为一炉,每一个民族的观者都会从中获得蓦然回首般的快感。
可以说,与启蒙主义的先驱们所期待的相反,现代科学技术并没有带来神话时代的结束,反倒让神话的再生产如虎添翼,给神话获得了空前强大的繁殖和传播能力。互联网的诞生和普及,更为神话提供了一个无限自由和广阔的多维空间。五花八门的网络游戏充分利用了世界各民族的神话和民间故事资源,当一个网游少年登陆网络游戏,化身网游中的英雄、美女出生入死、在虚拟世界中浪迹天涯时,他也就依游戏路线图的指引而漫游神话王国。网游是虚拟的冒险,而神话又何尝不是冒险的虚拟?网络游戏实际上正是古老神话在数字时代的延伸。
经历了网络游戏的漫游时代而成长起来的一代数字新人,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别人编就的虚拟世界中扮演角色、经历神话,他们开始创造和改写属于自己的神话,于是,在写实主义文学日渐式微的同时,青年写手们恣意拼写的幻想文学(人们习惯上将之称为玄幻文学,而我宁愿将之正名为幻想文学)却风靡网络,激起一波波阅读热潮,倾倒了无数红尘年少。一个个古老的神话母题化作异彩闪烁的文化碎片,超越民族、语言和疆域的界限,在烟波浩淼、歧路丛生的网络世界中自由飘荡,一个无名的节点,一次偶然的点击,可能就会在一个网络写手的心中激发出电光石火般的灵感,从而演绎出绵绵不绝的文字和故事。在各种文学网站上,幻想文学每日每时都在被大量的生产、传播、消费着,各路写手风云际会,争奇斗艳,而青年写手自发的表达欲望和网络商业资本的结盟,正在将网络幻想文化变成一种蔚为壮观的当代文化奇观。
学院批评家、精英学者可以对这些架空历史、脱离现实、白日飞升、装神弄鬼的文学写作嗤之以鼻,但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严肃的、有文化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的学者,你就不能不努力去思考、去理解他们,你该知道,这一代人就是汲取卡通文学、网络游戏和数字神话的文化营养发育成熟的,网络神话的文化因子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正在越来越有力地影响着他们的语言修辞、思想逻辑和生活方式。当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虚拟世界的光晕迟早会侵入现实世界。梦想照进现实,会变得比现实更强大,比现实更真实,迟早会按照虚拟世界的模式改造和重建现实世界。就像那些古老神话中神秘的神谕和诅咒,迟早会在将来某一天变成现实一样。虚幻的神话,之所以能够超越历史而世代流传,正因为神话中蕴涵了人类最深沉的欲望和最瑰丽的想象,如果我们放长眼光,我们也许会看到,网络游戏、玄幻文学、卡通文化、科幻电影等等这些数字时代文化新势力,遥遥承接的正是神话中生生不息的欲望和想象。在人类历史宏大叙事的背景下度量眼下这股风起云涌的玄幻文学,也许就不会想当然地把它们视为时尚泡沫或者文化垃圾而不屑一顾了。
不过,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是泥沙俱下的,而时间自会从泥沙中淘洗出永不褪色的金子,时下风靡网络的玄幻文学,也确实充斥着乌七八糟的文化垃圾,在此意义上,学院批评家对于玄幻文学的斥责不无道理。斥之为瞎编乱造,斥之为装神弄鬼,反映了学院知识分子对于网络玄幻文学缺乏文化关怀和历史底蕴的忧思,而文化关怀和历史底蕴的缺失,却迟早会导致创造力的枯竭,凭空架构,装神弄鬼,其实正是创造力衰竭的表征。因此,许多自我标榜为原创的玄幻文学,往往只是西方幻想文学的笨拙模仿,作品中的人物名字、道具、场景,可能是从唐诗宋词、传奇话本、武侠小说中出来的,但是华丽藻饰的中国外衣下,却掩饰不住的日本卡通和美国科幻的粗硬质地。有些作者即使有意识地使用诸如《山海经》《搜神记》《封神演义》之类的中国神话典籍进行演绎,但演绎的路数却是遵循的西方神话的脚本,中国神话最后仅仅成了点缀在西方神话情节模式上的符号碎片,中国神话似乎只有依托在西方神话才能借尸还魂。难道我们的先民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竟然丧失了再生和繁殖的能力了吗?
三
中国神话自我再生产能力的丧失,追本溯源其实还是在中国神话本身。有史以来,无数的故事产生了,有些故事很快就湮灭了,有些故事则永久地流传下来。熟悉故事学的人都知道,历史上那些无可计数的故事,其实只是有限几个故事的不断重生、翻版、拼凑和分衍。那些流传下来并传播开来的伟大故事,正是因为被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们翻来覆去地讲述着,才得以不断地移形换景、生生不息,衍化出众多的变体和支脉,拥有了无限的生机和意蕴,从而成长为超越时空局限的宏大叙事,成就为贯通古今的伟大神话。而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故事,之所以能够被一代又一代的讲述者和写作者不断地重述和演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个伟大的故事首先需要有一个既头绪清晰、结构严整,又线索错综、山重水复的情节脉络,清晰的头绪让故事容易理解,错综的线索则使故事富于分叉和衍生的可能。而情节源于不同人物和性格的相遇,因此,情节的展开和推进首先取决于故事中出场的人物,以及众多的出场人物相互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所以,一个伟大的故事的背后,总有一张既结构明确又纵横错互的人物关系谱。正是这些被命运卷进同一个故事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正是这些人物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将英雄美人送上了命运的不归路,为故事情节的展开铺垫了舞台,为一个伟大故事的生长奠定了基础。
中国神话所缺少的正是这样一个富于召唤力的情节模式和富于启示力的诸神谱系。对比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中国神话在这一方面的缺失一目了然。公元前八、七世纪前后,那些长期以来在被各地的游吟歌手们传唱的神话故事、英雄传说就被天才诗人荷马收集、整理、编纂为长篇的英雄史诗,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荷马独运匠心,运用特洛伊战争和奥德修斯的历险为间架,将流传在希腊各地原本参差多端、歧义丛生甚至是毫不相干的诗篇熔为一炉,陶铸成两篇结构严整、角色众多、故事情节跌宕回旋、人物命运动人心魄的伟大诗篇。在诗人的号召下,希腊世界各路神仙纷纷登场,联袂出演,辅佐希腊英雄儿女,共同谱就了一曲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英雄史诗。如果说,荷马史诗用一个又一个相互衔接、络绎呈现的故事将希腊神话贯穿为同一个宏伟的情节,那么,比荷马稍晚的另一位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神谱》,则以年代为经、以血统为纬,将希腊众神的身世来历掰着指头从头说起,一一追溯到最高天神宙斯的身上,由此建立了一个层次分明、统系明晰的希腊众神谱系,赫西俄德的《神谱》,就是希腊众神的家谱。至此,希腊神话大致定型,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神谱》,为希腊神话的再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后世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对希腊神话进行再创作的不竭的灵感源泉。

夸父追日主题岩画(供图:刘海粟美术馆)
相比之下,中国神话却完全是另一番境况,在相当于古希腊城邦时代的战国时期,华夏世界贤哲百出,群星璀璨,其对于天地奥妙、人情世故的思考,一点也不亚于希腊的哲学家和诗人,但是,我们既没有荷马,也没有赫西俄德,既没有熔原始神话于一炉的英雄史诗,也没有纳各路神明于一家的神谱,大量的古代神话因此没有被汇集、整理而永远风流云散了,众多的神明也因为没有登记造谱而永远湮灭无闻了。为什么同处文明轴心期的两大文明,其文化选择会如此大相径庭,个中缘由,一言难尽,但儒家传统对于形而上问题和宇宙终极问题的悬置,肯定难辞其咎。《论语》说,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对于天道不关心,对于生死问题不在意,当然也就不会对于谈论宇宙终极和人生终极问题的神话感兴趣。《论语》还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大量的古代神话,肯定就被孔子这位华夏传统的掌门人当成说不得的“怪力乱神”而打上天机不可泄漏的封条,永远沉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了。从此之后,古代神话成绝响,侥幸流传下来的只是一些散见于经、史典籍和诸子著作中的残片断简,在这些散乱零落的文化碎片,诸神面目早已经变得漫漶模糊,难求其真,诸神故事更是支离破碎,难知其详。
中国神话“没谱”,没有形成一个像古希腊、北欧那样的神话史诗那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早熟。中国的史官制度在商代就已经发达,《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王朝的史官用文字记录商王的军事、行政、祭祀等方面的大事,这些记载就是最早的历史文献,安阳殷墟考古发现的甲骨文就是商代史官占卜的文书档案。到了周代,史官制度更趋发达和成熟,在《周官》(又题《周礼》)所构想的王朝官僚体系中,每一个官府部门都有多名史官负责记录、保存文书档案,故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史官制度的成熟,决定了在中国古代王朝中,担当保存历史记忆的不是用口头说唱故事的歌手,而是用文献记录事实的史官。希腊城邦是剧场政治,中国王朝是文书行政,剧场的核心是诗人,文书的核心是史官,口头讲述更长于讲故事,书面记载则长于记历史,所以希腊有史诗,中国有《春秋》,孟子云:“诗亡然后春秋作。”就道出了历史编纂学与史诗传统之间的相克关系。中国也有讲故事的瞎子,希腊也有写史书的史家,但两者在各自社会的地位是不同的,中国说书瞎子的地位无法跟希腊的荷马相比,而希腊的希罗多德《史书》的地位也没法跟孔子的春秋相比。
孔子对于原始文化中“怪力乱神”之物的荡除和史官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记述,体现出可贵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使华夏民族从整体上避免了对于宗教和神秘主义的迷狂,但是,因此而导致华夏古代神话在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的散失,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永远的缺憾。古代神话的散乱,让我们丧失了一个强有力的文化表达手段,让我们民族的文化表达在激情洋溢、想象奔放的西方文化面前,永远输却三分春色。尤其是当今这个大众传媒和文化产业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时代,包括传统神话在内的文化表达方式已经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表现。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成为现时代主要的传播渠道,随着多媒体数字技术的表现手法和叙事技巧越来越圆熟,那些古老的神话故事、神话人物和神话母题,正因其与生俱来的想象和激情而日益成为数字化时代文化生产和文化表达的重要资源。因此,如何从历史的文化遗留中发掘中国神话的文化宝藏,如何在充分认识和尊重中国神话遗产文化内涵和固有理路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文化传播和文化生产的需要,对原本散落、零碎的中国神话进行收集、盘点,整理出大致完整的神话故事和神谱体系,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利用中国神话遗产打下坚实的基础,是神话学界、文学界和传媒界的有志之士义不容辞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