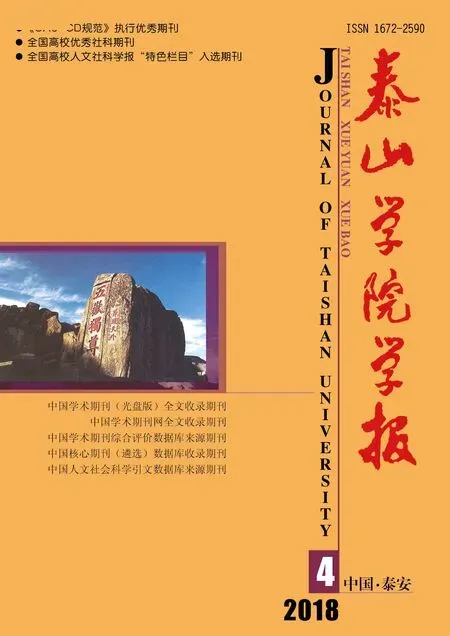书场内外:女弹词艺人的“职场”互动
2018-01-28刘思瀚秦箬茜
刘思瀚,秦箬茜
(1.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2.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评弹艺术是深受江南地区民众喜爱的一种曲艺形式,不过,自明清以降,评弹演艺事业长期处于男性艺人主导的状态。直至民国时期,职业女弹词才逐渐出现,打破了男性主导下的评弹演艺市场的性别格局。这一变化,引起了男性艺人的抵抗。1935年,以苏州光裕社为首的男性艺人群体为维护其在业界的垄断地位,对女弹词进行排挤打压,禁止男女拼档。女弹词艺人为求生存,以男女职业平等为由与光裕社展开斗争,终以普余社的成立以及女子登台说书合法化取得胜利[1]。不过,在女弹词登上书台之后,她们所要面临的社会关系依然复杂。对女弹词而言,尤其需要谨慎对待的,无疑是与书场诸角的互动关系。有学者指出,“演员、听众、场东构成了书场‘小社会’”[2],这正对应了职场中同事、客户与资方的角色。从这一角度而言,书场便是弹词演员“职场”之所在。因此,本文拟分析女弹词艺人的“职场”互动,以探讨女弹词艺人是否如同获得演出权一般,在职场上也获得了平等的权利。
一、同行之争——女弹词与竞争者的互动
书场并非一个太平之地,各种冲突屡见不鲜,同行之争更属“家常便饭”。这一现象是由评弹演出的特性决定的,毕竟对于一个评弹艺人而言,搭档少,对手多,而你的搭档,随时可能转化成为你最大的对手。因此,评弹艺人之间的冲突,屡见不鲜。轻则口角不绝,在自己演出的内容中对他人进行“扦讲”;重者甚至拔拳相向,定要分个“你死我活”。若是两个男性艺人大大出手,或许令人见怪不怪,但男女艺人之间发生的肢体冲突,则真是让人啧啧称奇了。事实上,在女弹词走上书台之后,这类现象并不少见。
擅说《万年青》的盲目评话家王抱良,曾与普余社钱家班的女艺人钱醉仙同在上海三北轮船公司接演长期堂会。王抱良的演出时间原本定于每日午后四时半至五时,钱醉仙紧随其后,由五时起演至五时半。不过,王抱良常常需要赶场,不能准时到达开演。钱醉仙则趁此机会抢占先机,提前上台演出。导致王抱良姗姗来迟之时,却只能在台下“欣赏”钱醉仙的演出。日积月累,王抱良心生不满也在情理之中。
一日,王抱良准时到场开讲,却听见钱醉仙在台下与男听客谈笑风生,遂认为钱醉仙存心与他捣蛋,破坏他的演出,再加上王抱良早就对钱醉仙心怀怨气,积攒的怒火一触即发。下台后,王抱良即骂钱醉仙:“你又不是向导社,说笑吵闹,捣什么蛋。”[3]钱当然不甘受辱,马上回嘴。谁知王抱良此时已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竟揪住钱醉仙一顿拳脚相加。双方经人调解之后,方才作罢。不过,钱醉仙事后每每想起此事,心中的怨气难以平息。于是约了几位“动手朋友”,待王抱良在光裕公所茶叙时,娘子军一轰而至,将王抱良团团围住,钱醉仙更是上前“一记耳光”,报了此前的“一箭之仇”。事已至此,双方都难以善罢甘休。只得由王抱良的师父与钱醉仙的丈夫钱景章出面调停,才将此事化解。
男性在公众场合殴打女性,本身已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女艺人钱醉仙即便有错在先,但遭到男艺人殴打的遭遇,理应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不过,因为她身为“抛头露脸”的女艺人,大众却常常将这类女性与“生性不检点”、“喜好惹是生非”等特点挂钩。在此之后,尽管钱醉仙身为钱景章的妻子,却也受到多方指摘,难以在上海书场中继续立足,女艺人的弱势与无助,可见一斑。
除了与男艺人的冲突,女艺人之间的摩擦也不在少数。双方矛盾的焦点大多在于某个听客专门为了一个女弹词家捧场而冷落了同场的另一个女弹词,遂使后者心生不快。女弹词家徐雪月和沈玉英之间便曾发生此类事情。
中南书场曾于1936年组织过一场贺寿演出,邀请徐氏三兄妹与沈丽斌、沈玉英一同演出。此时,徐氏三兄妹正是风头无二,尤其是是雪月,表演功力远超她十五岁的年龄,“听客们多欢喜她的口齿老练”[4]。因此,他们演出之时,竟有五个听客,点了五只开篇,把他们规定的时间唱过了多时,原定十一点钟下场,直延至十二时才歇。台下沈玉英早已等不耐烦,本想离开弃演,最终被众人劝回。而待到她登台演出之时,却未急于开场,对听客说道:
现在有位×先生×先生,他们情愿每人拿出五块钱来,点两只开篇,并且指定星期日晚上在中西电台唱给他听,现在我在此谢谢两位先生,星期天那天,一准在空气中孝敬他听。[4]
不难发现,沈玉英这番话是说给徐雪月听的。为了表明自己不差于有人点唱的徐雪月,沈玉英不得不说上这么一段如此“刻意”的陈述,自己心中的“醋意”。
与之相类似的,某岁年尾,普余社留沪诸男女弹词家,为筹募该社经费串演书戏。准备上演《双珠凤》,早先已经定醉疑仙出演女主角霍定金,但这部书中还有一位充满正义感的丫鬟秋环,在文相府中规行矩步,目睹主妇文张氏私恋俊仆,写信告诉了在外问花寻柳的主人文平章,卒遭陷害入狱。秋环这个角色在戏中的戏份亦是相当重要,主办方本定沈玉英饰演,但醉疑仙因为也想出演丫鬟秋环一角,“被主持剧务者不允,羞愤填膺,在后台放声大哭。”[5]
钱醉仙的这一表现,与前文所述她在与王抱良争执中的举动可谓大相径庭,显得相当克制。而沈玉英在已经准备弃演而被人劝回的情况下,也仅仅只是说了几句略带“醋意”的自白,并未撕破脸皮,当场倾泻自己的怨气。可见,女弹词艺人显然不具备男性艺人能够在同行之争中“肆意妄为”的条件,社会舆论的支持更是无从谈起。就这一层面而言,男女评弹艺人距离“平等互动”,尚有不小的距离。
二、“捧损之间”——女弹词与听客的交往
评弹艺人在书台上说书,听客在台下听书,是一种互动关系,听客能够对于艺人的表演做出直观的反馈。尤其是一些老听客,不仅对书情较为熟悉,往往还能从专业角度出发,对艺人的水平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对初登书台的艺人来说,老听客的意见对他们提高自身的艺术水平十分重要。如果某个艺人在台上说的那一节书有不合理的地方,或是唱词运腔不得当等等,听客还会当面“扳错头”。普余社中的女艺人文化素养都不高,常常会出现别字乱读,虚字瞎用的情况。“如‘鬼鬼祟祟’,读‘鬼鬼崇崇’;‘棘手’读‘辣手’,诸如此类的字,不胜枚举。”[6]偶尔有些听客会不留情面地指出来,这让女艺人下不来台。譬如女弹词家谢乐天,“她可说是女说书中的翘楚,但是对识字,实在是太不幸了。她常常有别字读出来。”所以她的女弟子谢小天,常常在一上台唱开篇的时候,先对听客打一个招呼,说:“有别字请诸位原谅。”[6]
除了对评弹艺人的技艺进行反馈,听客也对艺人在书台上的行为进行监督。若是艺人为人处世较为谦逊有礼,对听客提出的意见虚怀如故,那么即便是刚出道的小先生也能获得听客的好感与追捧。但若是艺人“恃宠而骄”,目中无人,那么即便是再红的艺人也不会得到听众的喜欢。外号“走油肉”的女弹词家邹蕴玉,说书时嗲声嗲气,以娇媚巧笑取悦听客,一时听客众多,人气颇旺。这位娇滴滴的邹蕴玉却有烟霞之癖,某天因戒绝嗜好,请医打针,导致误场二十分钟,被座客当面责问。不知是否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邹蕴玉登台后非但没有向观众致歉,居然还表示“此间共有书场三家,意谓:愿否来听,悉听客便”[7]。引得在场听众勃然大怒,一场演出即将化为闹剧。场东见众怒难犯,恐怕事态扩大难以收场,便出面调解,嘱蕴玉向座客大打招呼,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对弹词艺人水平的反馈与对其行为的监督,无疑是女弹词与听客之间的良性互动。但在此之外,两者的非常态互动也多有例证。由于在传统社会中,评弹艺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尤其是女艺人,可能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在跑码头的过程中,女弹词就常常遭到达官显贵、地痞流氓的任意欺辱。
1940年,刚满12岁的徐丽仙跟着师姐醉仙到苏州城郊木渎的一户姓石的人家做堂会。两姐妹结束了一天的演出,已过午夜,当她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准备离开时,突然从旁窜出两个大汉。这两个满脸怒气冲冲、醉气熏熏的无赖自称是隔壁邻居,说是丽仙姐妹俩唱堂会影响到他们休息了,所以拦住她们要她们也去自己家里唱上几段算是补偿损失。醉仙与丽仙自然想拒绝这无理的要求,但见二人来势汹汹,又无处寻求帮助,只得顺从。刚进家门,那两个无赖便把房门落了锁,居然拔出手枪威胁丽仙姐妹唱到天亮。她俩一段接一段地唱下去,把会唱的全唱完了,只唱到口舌发干,嗓子冒烟。两个家伙还不放她们走,让她们会唱的唱,不会唱的也得唱。最后只得等到两个家伙睡熟了,发出了重重的鼾声,姐妹俩才敢偷偷逃走。
女弹词的生存环境便是如此险恶。为求自保,女弹词认“寄爷”的现象就多了起来。“寄爷”也称“过房爷”,是近代以来十分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与如今的认“干爹”有异曲同工之妙。据时人介绍,拜寄爷这一举动最初兴起于京剧行当,随后才在曲艺界流行开来。有钱有势的先生认艺人为干儿子、干女儿风行于当时的都市文化圈。过房的关系是公开的,对于双方都有一定的利益。对于过房爷来说,能够充当红极一时的艺人的保护伞是自己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体现;对于艺人来说,有钱有势的过房爷可以为自己的演艺生涯保驾护航,一定程度上改变任人欺压的被动局面。更为重要的一点,这是艺人们接近上层社会财富和权力的标志。以至于有些女艺人沉迷其中,连拜多个“寄爷”:
拜过房爷若干女说书偏亦东施效颦,今日拜先生明日拜寄爷,一个寄爷不算,再拜一个,两个不够,再拜第三个,以至四个、五个,多者有至半打以上,甚有不问此人有名与否,能够买双皮鞋,送一件旗袍者,都是寄爷。尝见某女说书一脚踏进书场,连叫五声“寄爷”。[8]
过房爷除了在经济上给予艺人帮助,在社会关系上也会给予艺人各种支持。“弹词皇后”范雪君在常州初登书坛之时,便得到当地名耆逊清遗老“钱亲王”的垂青,每日必定莅往书场聆听。不仅如此,这位“钱亲王”还动用关系,每日为她作文一篇刊登于报。范雪君成名之后,为谢其恩,便“拜钱亲王为寄爷”[9]。在众多女弹词所拜的寄爷之中,老听客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些听客大多是具有一定文学修养的文人,他们时常会写一些揄扬文字来品评女艺人技艺的优劣[10]。有时文人听客间甚至会针对一位女艺人是应该“捧”或“不捧”打起笔墨官司,女艺人则通过文人听客的“捧角”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例如被称为“书坛小鸟”的张丽君就曾拜评弹专栏的作者张健帆为义父。“书坛小迷汤”周蝶影也因为技艺受到常州报人范秉毅先生的赏识而被收作“过房囡”,并举办了隆重的仪式。
三、“利字当先”——女弹词与场方的纠葛
艺人与场方之间的互动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旧式的书场聘请艺人说书,主要采用拆账制度,场方根据每场听客人数按照比例将每场的演出收入与艺人分成,或四六分,或对半分。艺人自身的名气也是影响收入的因素,等到每场结束,艺人下台后,场方老板会将现钞包在纸里,上面标注卖座人数,当面交付给艺人,称为“拆签”。到了民国后期,上海的新型书场转而采用“包银”的办法,即按月支付艺人的酬劳。
一般情况下,艺人与场方之间是相互帮持的关系,因为彼此间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在艺人与听客产生矛盾的时候,场方往往会从旁调解。但若牵涉到各自利益的时候,艺人与场方之间的矛盾却往往难以调和,甚至需要对簿公堂才能解决。女弹词家范雪君和大华书场老板张作舟就因《秋海棠》一书的弹唱权问题,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纠葛。
范雪君素有“弹词皇后”之称,20世纪40年代走红于上海各大书场。1944年,上海大华隆记公司开设了大华书场,大华书场的经理张作舟很是看好范雪君,认为她“‘皮子挺’,色相光鲜,能说各处方言,起角色逼肖,还能唱几支流行歌曲,在书坛上善抛眼风,为场下听众痴迷。”[11]有鉴于此,张作舟决定为范雪君量身打造适合她的评弹脚本。而早在这之前的几年,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文人秦瘦鸥曾写过一部名为《秋海棠》的小说,这部被称为“民国第一言情小说”的文学作品,以民国初年为背景,讲述了梨园名旦秋海棠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出身的罗湘绮之间悲惨的爱情故事,在上海沦陷后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张作舟看中了《秋海棠》改编为评弹脚本的潜力,为此,他请来将张恨水《啼笑因缘》改编为评弹脚本并大获成功的陆澹安,请他为范雪君量身打造《秋海棠》弹词脚本。
陆澹安的改编很是顺利,范雪君也对此十分满意。在范雪君登台说唱之前,张作舟提出,陆澹安所编的《秋海棠》之说唱权归大华隆记书场所有,未经书场负责人张作舟的同意,范雪君不得在其他书场弹唱此书。只有在范雪君于大华书场将《秋海棠》唱满四遍的情况下,该脚本的永久弹唱权才归范所有。在合同期间,范雪君除了要在大华书场弹唱《秋海棠》,也需应书场要求弹唱其他篇目。大华书场则每月为范雪君提供国币二万元作为报酬。而陆澹安作为脚本的改编者,无论范雪君在何处演出,他均享有提成演出收益作为“编导税”的权利,具体数额,由张作舟与范雪君协商决定。
以上双方的约定,看似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但都建立在《秋海棠》演出十分顺利的基础之上。实际的情况却不似书场与艺人想象的那么乐观。1945年元旦之后,范雪君在大华、仙乐(征得张作舟同意的)两家书场说这部书的时候,听客的反响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上座率不是很理想,范雪君不得不提前剪书离去,并未在大华书场“唱满四遍”。至1946年10月,范雪君从苏锡等地的书码头返回上海,在新仙林和同孚两家书场开书,说的却正是陆澹安改编的《秋海棠》,这样一来明显违背了当初和大华隆记的约定。张作舟便向范交涉,要求范履行契约,因范前未满四遍之约,应依约缴付版税。而“范方则以在沪虽仅弹唱未满约定,但后在苏续唱,已唱满四遍,当时曾在苏交付陆伪币五百万元、法币五万元以作版税,故契约业已全部履行完毕,自可自行弹唱,不受干涉,致事遂成僵局,虽经人调解,卒无效果”[12]。双方僵持不下,张作舟便一纸诉状将范雪君告到了上海地方法院。
陆澹安作为《秋海棠》的改编者,也不得不牵连其中。为了赢得舆论,范氏父女在《新闻报》上连续两天刊登启示,声明自己在去年已经将弹词的版税一次性付予改编者陆澹安,并指出《秋海棠》原著作者应为秦瘦鸥,张作舟让陆澹安改编《秋海棠》也是一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范雪君方面强调自己已经向陆澹安支付了买断版权的费用,并支付了大华书场伪币五百万、法币五万作为弹唱四遍的费用,他们认为陆澹安对张作舟隐瞒了此事。但实际上上述所付款项与陆澹安是毫无关系的,范玉山是曾托苏州的宣乃鼎向陆澹安转交了两万五千元作为酬劳费,陆澹安“因不明其计算之方法,乃迳去函诘问,旋据被告之父范玉山复函,约至上海再算。”[13]所以双方之间因此有了误会。“廿二日《新闻报》又刊雪君再度声明广告,对陆更不客气,竟有‘斯文扫地’等字句。”[14]这样一来又惹恼了陆澹安,他也在报上刊登启示回击,并将之前与范玉山往来的书信、范雪君在报上刊登的启示、原始合同全部拿出作为证据,以“故意诽谤、妨害名誉”为由将范雪君告上法庭。陆澹安公开表示,自己与秦瘦鸥交好,改编《秋海棠》纯属“友情难却,写作技痒”,还公开发表声明若是此案胜诉,即将名誉损失的补偿款以及版税余额全部捐助慈善机构。
陆澹安此举一出,大众的舆论导向由同情范雪君被场方盘剥、受压迫转而认为范雪君“人红是非多”、“不知报恩”,光裕社的男艺人朱耀祥就认为范雪君对陆澹安的所作所为太“不近人情”,因为陆澹安早先曾帮朱耀祥、赵稼秋双档将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改编为弹词,范雪君也曾说过此书,所以朱耀祥就在警告范雪君的信函中称《啼笑因缘》弹唱权,为其所有,不准他人奏唱,应立即停唱,并须赔偿过去数年间擅自弹唱并侵略弹唱权益之损害费。[15]如此一来,范雪君作为被告将被三方告上法庭,官司缠身,且舆论的倾向大多倾向于陆澹安一方,对于范雪君的指责也越来越多,三面夹攻让她焦头烂额,严重影响了她的演艺生活。
1946年11月26日下午,范玉山作为范雪君的代理人出席了上海地方法院的开庭。范雪君一方的两位辩护律师桂裕、鄂森将辩护的重点放在了《秋海棠》作品版权的归属权上,他们认为陆澹安仅是此书的编导,而真正的著作权应该属于原著作者秦瘦鸥。言下之意即陆澹安对作品的改编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侵权的行为。再者,范雪君在书场所说的《秋海棠》弹词已经根据自己的演出实践加以改变,并非陆澹安的初稿。最后,范雪君方面表明通过经济方式已向著作权所有人陆澹庵取得永远弹唱权,张作舟不过当时之传达人,自无权过问,与大华书场订立之四全遍,亦于大华闭歇后在苏州补足。上海地方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之后,认为张作舟要求范雪君禁止弹唱的请求依据不足,理由在于:其一,双方签订的合同当时已经逾期,失去效力;其二,大华书场尚未待到范雪君弹唱四遍,已自行避歇,没有为范雪君提供演出场所,“依据原契约原告尚有未尽之责,何得更禁被告在他处演唱”[16];其三,《秋海棠》的著作权不属大华书场所有,原告无权要求被告禁演;其四,范雪君此次演出的《秋海棠》,已与陆澹安的改编脚本有“根本不同”,“陆澹安亦无主张权利之余地”[16]。
根据以上四条理由,法院最终驳回了张作舟要求范雪君禁止弹唱《秋海棠》的诉讼请求。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大相径庭的是,舆论对范雪君的指责声却更加激烈,有的报道认为范雪君“不是东西”,是个“烂小人运气派”;陆澹安与范雪君打交道也是“倒了霉的,会和烂小人绕不清起来,怕是前世造的孽吧”[17],甚至有人将范雪君斥为“书妖”。在这种情况下,范雪君方面不得不请人出面调解,《秋海棠》原著作者秦瘦鸥与双方都有交情,所以愿为双方调解,他主张范雪君刊登启事向陆澹庵道歉,最后范雪君在《新闻报》上刊登了道歉启事,陆澹安也随之撤诉表示对妨害名誉一案不予追究,双方各让一步,此事才算平息。
《秋海棠》弹词一案是艺人与场方之间关于经济利益的博弈,但也反映出评弹艺人,尤其是女艺人在演艺生涯中所要面临和处理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和关系。范雪君虽是官司的被告人,但实际上所有的合同都是其父范玉山代她所签订,范玉山扮演着女艺人经纪人的角色,帮她打理演出外的一切事务。但在出现问题的时候,社会大众会选择将范雪君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而非其背后的始作俑者范玉山。在与大华书场的交涉中,范雪君虽也有处理不当的地方,但总的来说范的行为是合乎法律规范的,法院的判决也支持了这一点。反而是场方张作舟在经济利益驱使之下,有意为难范雪君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由于陆澹安的社会影响力较大,舆论便纷纷将矛头指向了范雪君,认为她不懂得知恩图报、忘恩负义,在大众的眼中,范雪君就是一个“无耻的书妖”[17]。大众的非议似洪水猛兽,在这种情况下,被推到台前的女艺人承载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为了能继续在书台上谋生,也只能以低姿态向公众道歉。
通过对女弹词三组“职场”互动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即便是在女弹词独立登台演出之后,女性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不仅受到男性的欺辱,更多的情况下女弹词还需要依附于男性,无论是师父、“寄爷”还是父亲,都成为她们谋求生存的保护人。因此,女弹词登台权利的合法化,只是众多女弹词所期冀的男女平等的起点,而非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