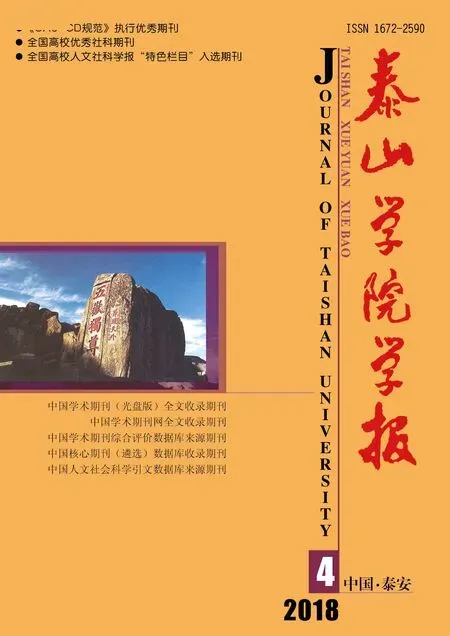科举与政争:明清时期苏州弹词传统书目选编的历史因素分析
2018-01-28沈家悦
付 楠,沈家悦
(1.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1620;2.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苏州评弹是一种在明清时期盛行于江南地区的地方曲艺,分为评话和弹词两种形式。书目作为评弹艺术的载体,其创作、流传和传承的过程,本身就是受众选择和艺术主体自我创新的过程。本文中所涉及的书目均为一类书,即经过长期流传、经过历代艺人加工成熟的传统书目。[1](P1)
评话书目大多改编自明代至清初文人根据民间流传已久的故事,重新整理创作的通俗长篇小说,如《西游》《水浒》《三国》等等。原本已经非常成熟,易于艺人搬演,是评弹表演初期的绝对主流。但成熟且早已流传甚广的原本故事,限制了艺人对书目的理解和二次创作,在反映江南社会大众价值观念上有所不足。
在评话的基础上所发展出的弹词,题材以男女情爱、家庭纷争为主,更贴合评弹表演的长处,即艺人可基于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体验灵活处理细节、充实人物形象,容易营造出真实感,也更易于与听众产生共鸣。所以在反映历史细节和社会价值取向上,弹词更具优势,甚至有不少书目在经过艺人改编后,与原本有很大出入,体现出了鲜明的独属于评弹的特点。而评弹艺术发展越成熟,弹词的优势愈发凸显。所以表现在弹词书目中的“共性”更引人注目,以下也将主要以弹词书目进行分析。
一、弹词传统长篇的书目和成书年代考析
根据《评弹文化词典》所录弹词书目,在清代已打磨成熟、并有艺人表演的传统长篇有《西厢记》《白蛇传》《九丝绦》《白鹤图》《绣香囊》《文武香球》《双珠球》《三笑》《倭袍》《落金扇》《双金锭》《大红袍》《玉蜻蜓》《描金凤》《七美缘》《双珠凤》《黄金印》《珍珠塔》这18部。民国时期根据清代文本改编的则有《青蛇传》《荆钗记》《再生缘》《十五贯》《顾鼎臣》《十美图》《麒麟豹》《二度梅》《四香缘》《长生殿》《玉连环》这11部。这29部书只是弹词书目中的一小部分,但却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原因在于:其一,这批书目是有确切表演记载的演出书目;其二,这批书目有较详尽的传承谱系。当中有一半左右的书目是评弹艺术中最精华、最成熟的代表书目。[2](P9)
分析弹词传统长篇的成型年代,不仅要考析原文本的刊刻年代,也要注意艺人进行编演的年代,这两者在部分书目中相隔很近,或直接由艺人创编表演,有些则相隔很远。
前文所录的清代已演出的18部书中,计有13部的最早刊本或者演出记载在乾嘉道年间。《珍珠塔》《玉蜻蜓》《白蛇传》《倭袍》《九丝绦》等均有乾隆年间刊本[3](P52),《落金扇》是乾隆年间艺人王周士御前表演书目;《三笑》《双金锭》《双珠凤》《绣香囊》等有嘉庆年间刊本;《黄金印》《文武香球》最早刊本为道光年间,《双珠球》是道光年间艺人颜春泉根据同名评话改编。
而民国改编清代文本的11部书中,也有相当部分的书目原文本刊刻年代在清中前期。《二度梅》改编自清初天花主人的同名小说,《十五贯》改编自清初朱素臣的传奇《双熊梦》,《再生缘》改编自清乾嘉年间弹词作家陈端生的同名小说,《十美图》《麒麟豹》《四香缘》的最早刊本也在道光年间。可见传统长篇中的比较成熟的书目,大部分原文本的刊刻和流传年代主要集中在乾嘉道三朝。[4](P64-86)所以这批书目上承明末大众俗文学的脉络,往下成为清代兴盛的评弹曲艺的文库,其所反映的科举和政争方面的价值观念,与明清两代的社会变迁有明显的联系,具有很典型的代表性。
传统书目中也有如《杨乃武》《金陵杀马》《啼笑因缘》《秋海棠》这般的特例,但这几部书与上文所论述的传统长篇来源、主旨均不相同,因此暂不详述。
二、传统书目的共性主题
(一)论功名:对科举的盲目崇拜
对科举的追求是明代之后所创作的俗文学作品中不可忽视的主题之一,在评弹传统长篇中,几乎所有的书目都会提及科举的重要性,这足以反映明清以来弥漫在整个江南社会中的极度迷恋科举的大众心态。
在这些故事中,科举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这点在《珍珠塔》经典唱段《痛责哭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方卿二进花园,隐瞒已中状元的事实到陈家来奚落当初轻视他的姑姑,谎称自己弃举子业去做了游方道士,未婚妻陈翠娥大怒说道:
念书人不问你功名事,欲问功名问何人。不是功名两个字,哪能够伸冤雪恨振门庭。不是功名两个字,哪能够显扬父母荫儿孙。……你不为功?不为名?当初何必读经纶?[5](P386)
可见读书全为科举,而科举是为了振门庭、显父母、荫儿孙,这种现实利益确实是促使大部分士子耗费自己的一生去博取功名的最大动力。而书目中诸如徐惠兰(《描金凤》)、曾荣(《十美图》)、王玉卿(《双金锭》)、方卿(《珍珠塔》)等学子,还需要借助科举洗去父祖或自己身上的冤屈,“冤屈”使得士子身处于与其身份不相符的较低的社会阶层中,而借助科举这架“通天梯”就可以重回较高的社会阶层,并解决他们在现实中遇到的一切困难。这是科举所带来的权力,也是大众对科举功利心态的一种表现。
而抛开这些科举的现实利益不谈,科举还是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正业”,不仅士子本人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连他们身边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譬如上文中陈翠娥的《痛责哭诉》,再如《玉蜻蜓》中金张氏规劝丈夫时说:“香烟一脉单传你,理应钟鼎簪缨炳国华。劝君及早回头转,中道回车未晚耶。”[7]而《描金凤》中的老仆陈荣,年近六十还要每天挑着扁担出去做小本营生,以供养小主人徐惠兰,所图的也无非是“只愿大爷勤把书来读,仍旧风光司寇门”[8]而已。
对科举的崇拜和迷信渗透在传统书目中,再借由评弹艺人之口广泛传播到民众中去,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强化了科举在民众心中神圣的映像,无形中促使了更多人投身并长期安于科举一途,既压制了思想活跃也保证了社会稳定。当然,这种程度上的教化作用还是不能让评弹逃脱被禁毁的遭遇的。
(二)忠奸斗:朝堂斗争的二元对立认知
“忠奸斗争”是俗文学中一个比较古老的主题,譬如岳飞和杨家将的故事从宋元之际就开始流传,到明代被整理创作为长篇通俗演义小说,并成为说史、评话等曲艺中的首选书目。但从苏州弹词传统书目来看,这种“忠奸斗争”的主题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是这一主题的滥觞,前文所述的29部传统弹词长篇中,大约有一半的书目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忠奸斗争”的情节和背景设定。其次是“忠奸”认知的简化,忠臣和奸臣呈现单纯的二元对立和角色脸谱化的倾向。第三,在弹词书目中,“忠奸斗争”基本是作为故事大背景和最高主旨做暗线处理的,很少作为故事主旨做明线处理,因为这一主题远离百姓的日常生活,是不利于弹词艺人进行合理描绘和灵活发挥的。
这批书目的故事或相关的支线故事重合度比较高,可以简要概括为:忠臣为奸臣陷害,满门抄斩,忠臣之子在逃亡的过程中,得到了其他忠臣和仰慕其父气节的人的帮助,最终得中状元、婚姻美满,并反奸成功,洗刷了家族冤屈。不管是作为明线处理的《玉夔龙》《十美图》《倭袍》等,还是作为暗线处理的《珍珠塔》《描金凤》等,基本都是这样的情节。
受限于创作者、表演者和受众的知识水平,复杂的朝堂斗争、政治博弈是不可能为他们所知的,但这一题材确实具有教化作用也比较受欢迎,所以简单化处理后就变成“忠奸斗争”了。《十美图》是这类书的代表,该书别名《沉香阁》,创作者和创作年代均不详,可追溯到的最早版本是清道光二十(1840)年爱莲堂本,序言说该故事于此前已经有“梨园演剧,名士讴歌”[8]。该书以嘉靖帝赐曾铣二子纳娶十妻的故事为蓝本,1928年评弹艺人张鉴庭将其改编为弹词书目开始表演。除了评弹之外,《十美图》故事还被川剧、京剧、扬剧、锡剧等多种曲艺搬演,可见其流传的广泛性和影响力。
《十美图》整个故事框架基本与上文概括的相一致,将“忠奸斗争”的主题背后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基本省去。甚至在“忠”与“奸”的分野下,其他的评价标准都模糊了,譬如曾氏兄弟在逃亡过程中前后与十位闺秀订下终身,有些行为是十分令人不齿的,书中解释为兄弟二人美姿容且满腹才学,但其“忠良之后”的身份,才应是作者所给出的最终解释。为了烘托“忠奸斗争”的戏剧张力,书中设计了严兰贞和赵婉贞这两个女性角色,严赵二女均为奸臣之女,但二女都认为“身适曾郎即是曾门之媳”[8]、“终身如一没商量”[8],甚至严兰贞还认为“自怨父祖行不正,到如今报应昭彰天网恢”[8]。在曾荣从严府逃走之时,严赵二女尽力相助于他,甚至自己也不得不逃出家门,结果遇到豪仆欲行不轨,幸得海瑞路过,二女甚至不敢告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自己是曾家媳才得救。书中海瑞也曾说:“当初巷门破户之时,若知(是)严赵之女,下官决然不肯收留。”[8]忠奸分野如此壁垒分明,严赵二女作为奸臣之后,其一是她们所处的尴尬境地,只能选择忠臣一方才能栖身,而忠臣对她们也不无挑剔;其二是选择了忠臣一方,就必须抛弃血缘亲情,从道德层面上对父祖进行批判。如此处理固然体现了忠奸斗争的正义性,但严赵二女何其无辜?
三、弹词选编共性主题背后的历史因素
(一)明代成熟的科举制与“功利”心态
明代是一个科举社会,科举制是学子实现社会阶级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以苏州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从明代开始便是全国文化中心,科甲之盛甲于天下。如长洲文氏、华亭徐氏、昆山顾氏等吴中大族,都是因科举起家的文化世族。但明清两代科举实行分省定额制度,竞争之激烈,令人瞠目,明文徵明曾说:“略以吾苏一郡八县言之,大约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贡不及二十,乡试所举不过三十。”[9](P583)清代则初定江南一百六十三名,分上下江后江苏占十分之六,乾隆九年后定江苏省举额为六十九名,至光绪年间江苏省才增广举额十八名。[10](P104-105)
名额的稀少并没有熄灭众多学子科举的热情,却造成了规模庞大的各级士绅群体滞留在乡间,而江南作为科举兴盛之地,人数自然更多。士绅作为地方领袖,是官民之间的连接纽带,同时,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也会传导到民众中去。随着江南地区开发越发深入,商业氛围也在浸染着这片土地。随之而来是士绅阶层心态上的变化,“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节,游宦来归,客或询其囊橐,必唾斥之。今天下自大夫至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形之齿颊。”[11](P80)
当科举入仕与个人财富、社会地位,乃至于家族势力相挂钩,成熟的科举制催生了强烈的功利心态,最终形成了“非利无学”的状况。科举是为了“第以位跻槐棘,阶荣祖父,荫及子孙,身后祀名宦、入乡贤,墓志文章夸扬于后世”[12](P7)。与苏州府相邻的松江府,风俗最为豪奢,即便“寒畯初举进士,即有田数十顷、宅数区、僮数百指,饮食起处,动拟王侯”[13](P16下)。尽管三吴不及,相差也并不远。
经由科举,士绅拉大了与小民的距离,这在某些方面有鲜明的表现。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中说明季缙绅“婚丧之家,绅衿不与齐民同座,另构一室,名曰‘大宾堂’”。同时,士绅拥有优免丁田赋税等特权,这本是对明代官员薄俸的补偿,但明中后期所谓“飞洒、诡寄、投献、埋没”等弊端越演越烈,士绅借由特权从中牟利,如苏州徐履祥任尚宝少卿、其侄任奉天府尹时,徐家富甲三吴,宅大而广。更遑论晚明士绅对地方事务的干预,到了惊人的地步,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别,不仅使士绅入仕则求权、居乡则贪利,小民更是看到这种阶级之间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的差距,如何能不向往呢?
士绅的“功利”心态就借由这种巨大的差距传导给了小民。士人登第,为官富且贪者,“谓之能吏,市人慕之,乡党尊之,教子弟者劝之。有为吏而廉者,出无舆,食无肉,衣无裘,谓之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14](P312)而弹词长篇所取材的话本小说的创作者和受众,自然也深受这种心态的影响。
(二)忠奸之辨与晚明党争风气的遗留
明代士人在科举上的功利心态与晚明激烈的党争风气,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联系的。明代士人大多通过科举确定自己的身份,功利性就促使士人从踏上科举道路开始,就必须经营好地缘、姻戚、同年、声气等各种人际关系,自然不可避免地出现门户之分、党派之别,进而发展出党争风气。
晚明党争风气的失控始于嘉靖朝倒严,到天启朝倒阉为最高峰,并一直绵延至明亡。万历末年东林党、复社诸人发起的“清议”“乡评”等活动,使党争从朝堂斗争蔓延成社会争论,并进一步扩大化为君子小人之类的道德争论。朋党风气之重,到了“诸司不问职业,而言门户;朝廷不重法纪,而顾私交”[15](P680)的地步。
而在朋党的基础上严忠奸、君子小人之分,正是以大义之名行相互攻讦之实,正如陈子龙所说:“夫全盛之朝,贤能并进,大才受大位,小才受小位,当世之时,无所谓邪正之分。及乎私交日盛,事变日出,而君子小人之名遂立于朝廷之上”,遂至“百官之众,万几之多,寂然无一事可为,而为君子小人之是争”[16](P599)的地步。可惜即使陈子龙有这般的认识,却依然落入“为人君者,惟有速去小人,删除迸放之务尽,独用君子以责其成效可也”[16](P600)的窠臼,可见当朋党之争演化为别邪正、辨忠奸,即便当时有远见卓识之士,依然难以脱出这一语境进行思考。
这种非忠即奸、非黑即白的党争风气,借由明代士人好参政议政的风气,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评价体系。崇祯年间,连民间小儿玩耍也相互痛扑,就是要效仿东林诸人,“须自幼炼铜筋铁骨,他时立朝,好做个忠臣也”[17](P175),可见这种风气在民间影响之深远。而这种风气还一直延续到清代。卢文弨是乾隆年间人,家中藏有严嵩的《铃山堂集》,“友朋见者辄命毁之”[18](P9),对严嵩的痛恨即便过去二百余年还是没有平息,而海瑞则“至今犹重其名,因谓其书可以辟邪,以故赝作者亦不免”[19](P8)。这种风气影响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久,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了小说戏曲中,事实上海瑞、严嵩都是此后文学曲艺创作者所青睐的人物原型,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戏曲和话本小说中,而忠奸斗争这一主题也正是明末之后才被广泛运用到俗文学创作中去的。
(三)社会舆论的兴盛和世俗文化的繁荣
晚明从万历末年东林党渐成气候后,形成了朝野和民间两个舆论中心。由于皇帝的长期怠政,一是官方公务机密外泄难以制止,万历朝重臣于慎行说:“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而已先发抄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已有传者。”[20](P127)二是官方对信息和舆论上的管控逐渐失效。这为民间舆论的兴盛大开方便之门。
民间舆论的中心以江南的东林党、复社诸人为主,借清议、乡评等方式品评官绅、讨论国是,初期虽是出自公心,但发展到明末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党争的漩涡中,还因其政治人格代表着君子,对官方的话语权更为有害。万历年间就已经出现“阁中称是,外论必以为非;阁中所非,外论必以为是”[21]的现象了,到崇祯朝则已成“上与下异心,朝与野异议”[22](P6676)之相。而东林党、复社诸人操舆论之权,威势赫赫,如复社可以“挟持官府,遥执朝权……郡县有司亦俯首听执牛尔”[23](P42)。但东、复诸人虽代表“君子”“忠臣”一方,却并不代表他们的清议、乡评是完全公正的,君子小人如何界定也无明确标准,当中自然不乏借此行私心者。这种话语权操之于下的危害当时已有人认识到,魏禧论当时所谓之君子,“及其名日盛而权日归”,既可借名排除异己,也可因名高而收厚利[24](P75),矛头直指“君子”结党的危害。而陆世仪直言“处士横议,天下何赖焉”[25](P8),舆论失控必然导致政局不稳。清初有学者持“东林误国”之论,也就并不奇怪了。
尽管社会舆论的兴盛对政局的稳定造成了损害,但对世俗文学的繁荣却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郑振铎将晚明视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和戏曲的时代”[26](P843),这是由多方因素所共同促成的。第一,因为官方对社会舆论管控松弛,才使得世俗文学的创作非常自由,许多文人主动参与通俗文学的创作,且晚明人并不讳言本朝人事;第二,晚明江南地区商业化的社会氛围,促进了地方曲艺的繁荣,诸如评书、鼓词、平湖调、讲史、评话等纷纷出现,这些曲艺擅演评时事,与通俗文学结合紧密;第三,儒学普及化推动了出版业的极大发展,晚明“版行猥滥”,各种日常用书、戏曲院本、话本小说大量印行,万历二十九年官方曾要求焚毁“一切邪说伪书”,并要求今后出版物须由提学官查阅审定,但从结果看效果并不明显。
自由的舆论环境、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氛围所催生的地方曲艺和通俗文学,将晚明社会舆论的风向、社会评价体系的转变,深入地传播到广大民众中去。评弹的前身说书也正是这当中的一个环节,因而在艺术载体弹词长篇中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这种痕迹的表现就是众多书目不约而同所选择的共性主题。
四、结论
苏州评弹是一种与地方社会深度结合和互动的曲艺形式,作为其艺术载体,弹词传统长篇从选编、表演、传承这三个环节,都一直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必须迎合广大民众的喜好并不断有所创新。这种艺术特质使得弹词传统长篇在反映大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具有较大的优势。
一般情况下,艺人会先选取比较受欢迎的话本、院本进行改编,或直接借鉴其他曲艺的故事;改编表演后,再根据听众的反映考虑是改编新书或者继续改进。这种改编——改进的过程在一部长篇的传承历史中会重复多次,部分长篇会因各种原因在这一过程中失传,但地方曲艺能长久地传唱某些长篇,也同样表明了这些长篇是持续受到受众欢迎的。如此多部代表性长篇中的共性主题,正是对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的一种反映。
科举和政争这两个主题,明显源自于原创者,也就是文人的思想。事实上,这反映了士绅阶层的观念向下传播的现象,以及这种向下传播中被改造后,重新反馈到士绅阶层的一个过程。晚明时期,文人会主动参与通俗文学的创作和整理,这一传统还一直延续到清代,乾嘉道时期刊印的不少书目,均有文人参与改编的记载[3](P29)。而晚明文人受到当时所处环境的影响而创作的作品,是清代文人创作通俗文学的最佳素材,很多情节和形式被不断重复套用,最明显的一点莫过于才子佳人情节的沿袭。但弹词长篇所择取的故事大部分还是在清初成型的,这些故事中重复使用科举和政争的主题、出现明代背景、采用明朝臣子作为原型,当中既有明代遗留的观念和思考,也必有清初文人群体和大众心态的潜变,这与清初江南地区的社会环境变化是相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