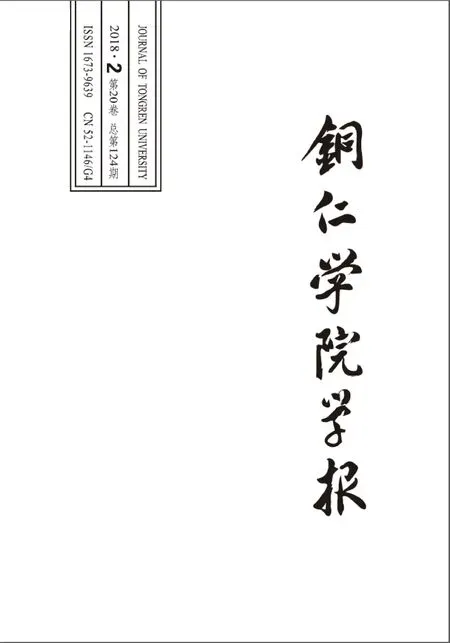健康中国背景下梵净山佛教养生思想研究
2018-01-28刘坤新罗忠青
刘坤新,罗忠青
( 1.铜仁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2.铜仁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征程上,中国佛教可谓天降大任,任重道远。”[1]佛教文化中包含了大量的生态、健康、养生的思想,深刻挖掘梵净山佛教文化中健康养生文化,对于实现梵净山地区的“同步小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梵净山佛教的自然养生
梵净山森林覆盖率高达 95%,大气、水源、土壤、环境均未被污染,负氧离子浓度最高可达 18.9万个/cm3。良好的生态成为梵净山最响亮的品牌,最突出的优势。2016年1月13日,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在全省宣传干部会议上,将贵州的人文精神概括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也被我国中医学视为养生的重要内容。《黄帝·内经》首先提出“天人相应”,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协同发展,作为养生健身的第一要素”,并“把人体疾病与健康,看成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养生必须要顺应自然规律”。[2]梵净山地区富含被称为“空气维生素”的负氧离子,为人体健康提供充足的“空气罐头”。现代科学研究证明:当空气中负氧离子达到10万个/cm3以上时,负氧离子可充分进入血液,可以促进新陈代谢,激活肌体多种酶,从而达到镇静、消除疲劳、调节神经、提高人体免疫力、防病治病的功效。
好水贵天然,汇聚梵净山。梵净山地区不但拥有优质的空气资源,而且拥有丰富的优质水资源。梵净山地区水中富含锂、锶、锌、硒、氡、硅酸等四十多微量元素和有益矿物,大大优于我国天然饮用矿泉水标准,具有良好的养生与保健的功效。水资源是梵净山的又一张“名片”。养生之道,在于自然,在于山水,梵净山的好山好水使之成为我国著名的养生地之一。梵净山地区不但长寿老人比比皆是,而且很多外地患病之人亦前来居住,期待通过梵净山的好山好水治愈疾病。梵净山地区人民努力将优质的水资源变为发展的优势资源。随着农夫山泉、娃哈哈、康师傅等知名企业的纷纷入驻,使铜仁经济增速明显,打开了“生态美、百姓福”的多彩铜仁新局面。
而梵净山之所以拥有如此优良的生态环境,这与梵净山作为一座千年佛教名山而积淀的浓厚的佛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3]与传统儒学相比,佛教尤其是在勾通天、人方面有着明显的长处。佛教秉承共生共荣、仁爱万物的理念,包含善待生命和自然的生活方式,强调:“顺乎自然,保养正气”是强身健体,防病治病,延年益寿的根本保障。加之,“特定的宗教场所能够帮助信奉者理解宗教意义和自我”。[4]
梵净山“山水名区,地名幽胜,溪涧以萦纡致,峰峦以峭拔呈奇,寺观多据山水佳处。”[5]1092随着时间的积淀,梵净山逐渐形成“梵刹林立”的盛况,成为“众名岳之宗”“梵天净土”。清康熙年间,梵净山已形成“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四十八脚庵”的佛教寺院建筑群。梵净山远离闹市区,远离尘世,自然环境优美,可“拒山外红尘滚滚”,有利于佛僧精进学修,提高宗教学识和道德修养。梵净山佛寺依山而建,殿阁巍峨,气势恢弘,震撼心灵,仿佛“心中没有了城市”“没有了一切色相。”[6]人们沿着山路石阶层层登高,通过不懈努力一步步接近追求和信仰的目标,是心灵提升的过程,也是克服各种外在干扰超越自我,追求心灵宁静的过程。[7]自古至今,“梵净山朝山之人,昼夜不绝于途”,人们“为名为利为长寿”,由“万步云梯”上山,身体和心灵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净化”。
二、梵净山佛教茶文化养生
好山好水出好茶。梵净山与佛结缘,自古就享有“古佛道场”的佛教圣誉。梵净山地区最早的植茶人是寺庙的和尚,所以该地区茶叶的种植、生产及传播很早就与佛教有着紧密的关系。梵净山坝梅寺附近的梅溪茶场,又称弥陀茶场,据当地人讲是“当年那些和尚栽种的。”一方面,佛教寺院多开辟有一定的土地,为茶的生产提供相应的“土壤”;另一方面,佛教倡导“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农禅并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所以,梵净山佛僧时常刻苦自励,植物造林,开渠灌林,种植了茶、水稻等多种农林作物。经过多年不断的积累和发展,梵净山地区现有茶园百万亩以上,拥有梵净山翠峰、石阡苔茶等数十种茶叶品牌。
明人顾元庆《茶谱》中记载:“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痤、少睡、利尿、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对于佛寺人士而言,茶可以辅助“苦修”。一方面,茶具有止渴解乏、恢复体力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日夜前进,在睡眠缺乏和粮食短缺的情况下,“饮茶一杯,复又前进,三十六小时无食物进口”。[8]另一方面,茶有三德,即坐禅时助醒神、满腹时助消化、抑制性欲。梵净山的佛僧严格执行“坐禅”“苦修”“断肉”“少食”“过午不食”“戒色”等戒规。因此,他们可以通过茶消除积食,更可以补足身体之营养,保持体力,减少性欲。据《黔记·方志传二》载:
铜化寺、慈化寺俱县西五十里。慈化僧颇众,其地产茗,远近取给。[5]1098
慈化寺在今梵净山地区的务川县,该地盛产茶叶,不仅可以满足本寺僧众的茶叶需求,还可以供给其他地方僧众及百姓。“茶之为用,味至寒”“苦茶久食,益思”,还可以“调神和内,倦解慵除”“令人少睡”,故“精行俭德之人”最宜。研习佛经是梵净山佛僧的必修课,茶可助其提神醒脑,领悟佛经内涵。
茶叶有利于佛僧的治病和养生。在我国古代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茶常被佛僧视为“治已病”之良药,故有“茶为万病之药”之说。在陶弘景《神农本草经》中载:“荼(茶)味苦,饮之令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史载隋文帝患头痛之症,“僧告以煮茗作药,服之果效”。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写有“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的诗句,也赞誉了茶的药用功效。梵净山地区的土壤、气候、湿度非常适宜茶的种植。故陆羽在《茶经》赞道“黔中生思州……其味极佳”。同时,《明实录》中亦载:“思州方物茶为上。”梵净山地处亚热带,气候潮湿,所以茶常被当地百姓及佛僧用来祛除湿热之毒。佛僧还用茶“治未病”,并将茶视为“养生之仙药,延寿之妙术,人若饮之,则寿则长”。据钱易《南部新书》载,唐大中三年(849),洛阳有一高僧,年 120岁,唐宣宗向其询问长寿之秘诀。高僧言:“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从文献记载可知,饮茶可以延年益寿。自唐代始,饭后三碗茶也成为“和尚家风”,梵净山佛僧亦遵循此法。现代医学也证明,茶能够防病治病而延年益寿。
三、梵净山佛教医药及心理养生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医药事业产生了很大影响,丰富了我国中医药的内容,对今天的医药工作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9]佛医主张使用植物、矿物类药物,认为因治病而杀生有碍慈悲教法。武陵山素有“天然药库”之称,而梵净山作为武陵山的主峰,因其多样地形、地势、地貌、地质、气候环境,再加之交通不便,人为活动较少,故而孕育出丰富的药材资源,尤其是珍稀濒危及特有药用植物较为丰富。据学者统计,梵净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仅药用类植物就有 460种,是贵州省乃至全国重要的中药材生产基地之一。因此,中医药是梵净山的再一张“名片”。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医药学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5000多年文明的结晶”。[10]据统计,中医全年诊疗人数达到9.1亿人次。因此,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推进我国及世界生命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同时,研究和发展梵净山地区中医药事业,对于梵净山人民的幸福健康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诚如香港法住文化书院霍韬晦教授所说:“一切宗教都是广义的医学”,佛教医药属于中医学的一部分。慈悲是佛教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慈爱众生并给与快乐(与乐),称为慈;同感其苦,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拔苦),称为悲;二者合称为慈悲。”[11]因此,慈悲智慧一直为佛僧所崇尚。在文献资料中,有大量关于佛陀、观音等治病救人的记载。如思南府《观音阁记》载:
大士前劫,妙庄王季女也。孩身悟佛法,浮海入香山……王末岁破溃痤,不治。大士化医白王……乃治也。[5]1095
梵净山的历代高僧本着慈悲之心治病救人,为该地区医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据乾隆时期檀萃所著《楚庭稗珠录·黔囊》载:
唐天宝时,通惠禅师于思州之鳌山上建般若提会。上患疾,有道士奏师能治,上召之,不经期而诣厥,上果愈,赐金帛不受,赐乘马还山,亦不终期而至,后不知所之。
《印江县志》也记载了五代十国时期,湛智和尚用中草药为印江百姓治病的史事。还有,“清初,佛僧在贵州各架桥铺路,植树造林,救死扶伤。”[12]历代的梵净山佛僧通过不懈的努力,传播医学知识,大大地改观了该地区的医药卫生状况。《黔记》载:“悦禅有戒形,善化诲愚迷”。[5]1083随着佛教文化传入,梵净山地区各族人民去愚昧,讲卫生,“华风渐被”,“信医药,晓道理,无异中土”,卫生、医药水平有了较大发展。
佛教善为“治心”之学,梵净山佛僧也强调“修心”来解除精神及心理的诸多疾病。现代医学也表明:人的精神状态与健康有着密切关系。精神状态良好,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相反,长期处于忧虑和紧张状态,则难以保持身体健康。因此,一个道德自律,乐观、宽容的人,更容易较好地生活。在《黔记方外列传》中,有诸多梵净山佛僧因严守戒律、静心修行而长寿的记载。“性良,戒形笃实,年八十四”。“拜经和尚,诵《法华经》,每字一拜一木板,岁久,木为之穿,四十年未尝下山,其戒行端谨类此,年七十”。“悦禅,有戒形,善化诲愚迷,年九十余”。“明然不趋势,不衔名”,“年七十六”。[5]1083
此外,梵净山佛僧还为其信众祛病禳灾、超荐亡灵和驱邪赶鬼,满足当地居民心理层面的需要。伴随梵净山佛教文化的兴盛,每当梵净山地区各族人民遇到天灾、人祸、疾病时,当地居民通过“朝山”,求得心理安慰。因此,梵净山“每当会期,四方信香众朝山蜂拥而入。”[13]音乐是佛教中“十供养”之一,具有通过教化人心辅助治疗疾病的功效。一方面,佛教音乐音声较为单一,没有强烈的高低音,给人以纯朴且亲切、回归自然的感觉,因此它对教化人心有较大的功效。另一方面,音乐还可以治疗疾病,唐代义净和尚在《南海寄归传》中,明确指出了佛教音乐的六大作用,即“一能知佛德之深远,二体制文之次第,三令舌根清净,四得胸藏开通,五则处众不惶,六乃长命无病。”因此,佛教音乐逐渐发展成为佛僧教化人心、去除疾病的常用方法,梵净山佛教寺庙也不例外。梵净山佛教音乐的主要特征是清雅、平和,如龙泉寺所演唱的佛乐,其主旋律悠远而宁静,速度较慢,曲调平缓、均匀。[14]梵净山佛教音乐通过柔和、平缓的曲调,使人们心情舒畅和平静,达到治病养生的目的。
四、梵净山佛教饮食养生
梵净山优质的生态环境,孕育出梵净山的绿色食品,这也是梵净山地区人们长寿老人众多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鉴于食品对于养生的重要性,梵净山地区打出“梵净山珍·健康养生”的名片,这对于梵净山地区经济和佛教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佛教传入我国之初,对佛僧的饮食没有严格规定。但随着佛教与我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佛僧开始提出“荤菜生食生瞋,熟食助淫”之说。于是,在南朝后期我国佛教逐渐形成坚持“断肉戒律”的传统。梵净山为“古佛道场”,自开山时起,梵净山所有寺院僧众都遵循“断肉戒律”,提倡“素食”、“饮茶”等饮食习惯,而且建立较为严苛的进食仪规,刻苦修行,白粥成为梵净山佛僧日常主要食物之一。据佛教律典《摩诃僧祇律》记载,食粥有“十益”,即资色、增力、益寿、安乐、辞清、辩说、消宿食、除风、除饥、消渴。现代医学也证明:喝粥可以帮助消化、增强食欲、调养肠胃,预防感冒、便秘、喉干等疾病。因为梵净山佛僧严格遵循“素食”戒律,在传世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较多高寿僧人的记载。
随着梵净山佛教影响的逐步扩大,四方香客“来朝”。梵净山佛僧用素食款待各路香客及观光之人,促进了梵净山佛教全素肴馔的发展。如民国时期,梵净山太平寺秉坤和尚用素食做出“山珍海味”来款待印江县长。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素食因为具有较高的养生价值而倍受人们的青睐。因此,努力弘扬梵净山佛教饮食文化中的科学内容,不但有助于梵净山地区居民及全国人民群众的健康、科学饮食习惯的形成,也可以更好地实现梵净山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在、共处、共生。梵净山佛僧把倡导素食作为自我修持和引渡众生的弘佛之道,大力宣传。一方面受梵净山佛僧的影响,另一方面为了追求自身的“福祉”,环梵净山定居的人民群众逐渐形成通过素食调养身体的习惯,而这亦是梵净山附近居民长寿的重要因素之一。佛经《摩诃止观》将病因系统地分为六大类,称为“病起六缘”,其中之一就是“饮食不节”。梵净山佛僧严格遵守节制饮食的习惯,以便抵御外部的诱惑,强化内心的信仰。由上可见,梵净山佛僧通过一定的饮食戒律,不仅锤炼了佛性,而且吃出了健康。
五、小结
习近平总书记把健康中国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强调“康”是全民健康、全民小康。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国的佛教文化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梵净山地区丰富的佛教文化资源,也成为梵净山地区及贵州地区连接“一带一路”战略最好的纽带,有利于加快梵净山地区的“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还有,在当前我国大力推进“大健康”建设的部署之下,梵净山地区成为我国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地区之一。梵净山佛教人士积极参与其中,努力将“防未病”、“治未病”理念注入到群众的生活中去,使当地群众的思想从“治病”向“防病”转变。因此,梵净山地区以“大生态”“大健康”“大文化”思想为发展战略,努力推进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一方面,他们努力用佛教文化智慧,尤其是佛教生态、健康、养生等方面的思想,启迪群众;另一方面,努力用这种思想为梵净山地区经济、医疗卫生以及文化的发展而努力,促进当地社会和谐安定、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EB/OL].http://cpc.people.com.cn/n/2014/0328/c64094-24759342.html,2017-01-09.
[2] 刘小华,蔡艺.《黄帝内经》养生思想窥探[J].宜春学院学报,2008(2):130-131.
[3] 张明.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生态保护探析[J].贵州大学学报,2013(2):55-60.
[4] Shampa Mazumdar, Sanjoy Mazumdar. Religion and Place Attachment: A Study of Sacred Plac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4(24).
[5] (明)郭子章.黔记[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6] 王存良.论新世纪贵州散文中的苦难意识[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6):49-58.
[7] 卫春梅.环境心理学视域下的佛寺建筑布局——以中国汉传佛寺为例[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4(2):44-51.
[8] 徐永成,毛先旦.饮茶与健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5.
[9] 邓来送.论佛教医药对中医药的影响[J].五台山研究,2005(1):32-39.
[10] 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http://china.cnr.cn/news/20160821/t20160821_5 23044689.shtml,2018-01-09.
[11] 倪秀兰.佛教的慈悲观[D].成都:四川大学,2005.
[12] 王路平.贵州佛教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41.
[13] 王路平.贵州第一佛教名山梵净山佛教考述[J].贵州民族研究,2000(3):130-140.
[14] 林春菲,易亚辉.梵净山佛教音乐的基本特征及当代价值[J].文史博览,2016(7):5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