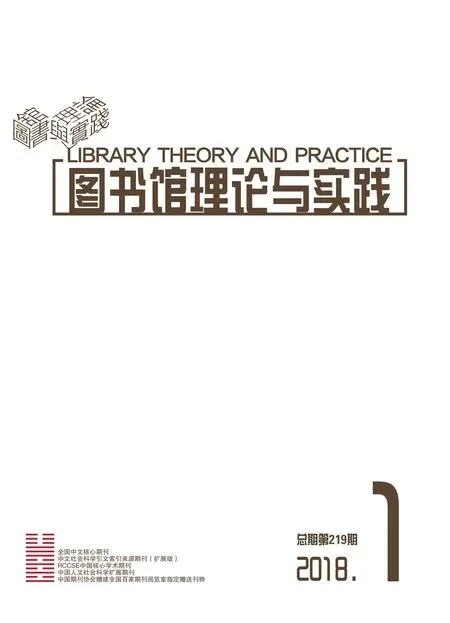《拾遗记》由史入子考
2018-01-28张千帆
张千帆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王谟在《汉魏丛书·拾遗记跋》中提到“有王嘉《拾遗记》,梁萧绮录,共10卷。……而《志》侧之杂史,谬矣!《通考》以入小说家,尚为近之”。[1]121《拾遗记》在书目中的这一变化引起了笔者的思考,《拾遗记》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呢?其从史部杂史类到子部小说类的著录是如何演变的?王谟的观点合理吗?杂史与小说又有何区别呢?对上述诸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澄清《拾遗记》的流传轨迹,而且也有益于对图书目录学史发展理论的探索。
一、王嘉生平与唐太宗修史观念新探
《拾遗记》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呢?笔者认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了解一下本书作者王嘉其人其事。通过查阅资料,笔者发现记载王嘉事迹比较详细的有《晋书·艺术传》、《高僧传》初集卷五《释道安传》附 《王嘉传》、《云笈七签》卷一一○《洞仙传》、曾慥《类说》卷三引《王氏神仙传》“未央”条等四处。而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中对王嘉的介绍,则全据《晋书》,兹以《晋书》为主,参稽其他资料对王嘉作以简单介绍。
《晋书》卷九十五《艺术传》云:
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也……好为譬喻,状如戏调;言未然之事,辞如谶记,当时鲜能晓之,事过皆验。坚将南征,遣使者问之。嘉曰:“金刚火强。”乃乘使者马,正衣冠,徐徐东行数百步,而策马驰反,脱衣服,弃冠履而归,下马踞床,一无所言。使者还告,坚不悟,复遣问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为吉。明年癸未,败于淮南,所谓未年而有殃也。人侯之者,至心则见之,不至心则隐形不见……苌既与苻登相持,问嘉曰:“吾得杀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苌怒曰:“得当云得,何略之有!”遂斩之……苻登闻嘉死,设坛哭之,赠太师,谥曰文。及苌死,苌子兴字子略方杀坚,“略得”之谓也。嘉之死日,人有陇上见之。其所造《牵三歌谶》,事过皆验,累世犹传之。又著《拾遗录》十卷,其记事多诡怪,今行于世。[2]
从《晋书》的记载不难看出,王嘉是一个识谶纬,深受统治者重视,而又行事非常诡怪之人。如记载苻坚问王嘉“吾世祚云何?”,而王嘉回答“未央”。在朝臣看来是为祥瑞,而苻坚却败于淮南,众人才悟是“未年而有殃也”。又如记载姚苌问王嘉其能否杀苻登而得天下,王嘉回答“略得之”。等到姚苌死后,其子姚子略得天下,方应王嘉之谶。可见王嘉的谶言虽然被时人所误解,但事后却总能应验。这在对谶纬思想非常热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无怪乎王嘉的事迹被引以为神了。①《晋书》云“嘉之死日,人有陇上见之。”《高僧传》初集卷五《释道安传》附《王嘉传》云“及姚苌正害嘉之日,有人于陇上见之,及遣书于苌。安之潜契神人,皆此类也。”[3]由两处记载可见,甚至连王嘉本人也被神化,竟能死而复生了。最后,《晋书》提到王嘉有《牵三歌谶》《拾遗录》等著作。
在了解了王嘉其人之后,再来看为何唐初在修《隋志》时,会把《拾遗记》放在杂史类。初唐承六朝遗韵,旖靡好奇之风尚未褪尽,如虞世南曾经劝谏太宗好尚迤逦文风为不经之学。加上唐太宗又是以弑兄逼父的形式登上皇帝宝座的,他对自己的这一段经历内心是不安的,如对唐初历史的篡改,要求房玄龄献上起居注给自己观看等。如果这时能有一些像《拾遗记》这一类对谶纬言之甚灵的书出现会对太宗来说多么的有用。无独有偶,和唐太宗用相似方法登上皇位的唐玄宗对《拾遗记》则表现了很大兴趣,据王应麟《玉海·艺文·录篇》引《集贤注记》:“天宝六载十二月,敕索《孝经钩命决》《王子年拾遗》《仁子道论》等四十余部以进。”[4]1108把《拾遗记》和《孝经钩命决》等纬书放在一起进呈,不得不让人想到唐玄宗对谶纬之书的追求了。但因《拾遗记》的叙事庞杂,不可以为正史。
二、唐至清间《拾遗记》书目著录变化考
在历代公私目录中,最早对《拾遗记》进行著录的是《隋书·经籍志》,其在杂史类云:“《拾遗录》二卷,伪秦姚苌方士王子年撰。《王子年拾遗记》十卷,萧绮撰。”[5]1015从《隋书·经籍志》成书情况来看,主要依据的是《隋嘉则殿藏书目录》,该书目是对宋、齐、梁、陈、隋五代书目著录的汇集,故《隋书·经籍志》可以说反映了五代以来的官私藏书情形。然《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二卷本《拾遗录》则很可能是隋代保存的历经姚秦至隋流传数百年的残缺之本,因为据萧绮序称:“《拾遗记》者,晋陇西安阳人王嘉字子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为残缺。”[6]而萧绮撰作的十卷本《王子年拾遗记》则是在王嘉原书基础上的增修改编之本。
《旧唐书·经籍志》卷四十七杂史类著录:“《拾遗录》三卷,王嘉撰。《王子年拾遗记》十卷,萧绮录。”[7]《旧唐书·经籍志》主要承袭毋煚《古今书录》而来,主要反映唐玄宗开元之前国家藏书情况。因此,《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情况与《隋书·经籍志》著录基本相同,唯其将《拾遗录》二卷改为三卷,恐怕是对《隋书·经籍志》的纠正。
《新唐书·艺文志》卷五十八杂史类著录:“王嘉《拾遗录》三卷,又《拾遗记》十卷,萧绮录。”[8]《新唐书·艺文志》是在《旧唐书·经籍志》基础上,又对唐玄宗开元以后的国家藏书情况进行了补充,因此其反映的是有唐一代的国家藏书情形。《新唐书·艺文志》对《拾遗录》的著录应该是承袭《旧唐书·经籍志》而来。
《崇文总目》卷二十一传记类著录:“《王子年拾遗记》十卷。”[9]《崇文总目》的修成是在宋真宗时期,因此它是反映宋代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家的藏书情况。从《崇文总目》的著录来看,王嘉所著《拾遗录》原本到了宋初已经亡佚,仅萧绮编录的十卷本《王子年拾遗记》保存了下来。
南宋陈骙等编撰的《中兴馆阁书目》别史类著录:“晋王嘉撰著《拾遗记》十卷,事多诡怪,今行于世。梁萧绮序云,本十九卷,书后残缺,绮因删集为卷。”[4]109《中兴馆阁书目》主要反映的是南宋前期的国家藏书情况,其所著录的十卷本《拾遗记》应是萧绮编录的《王子年拾遗记》,但却不加择察,妄题为王嘉撰著。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九史部传记类著录:“《王子年拾遗记》十卷,梁萧绮叙录。”[10]《郡斋读书志》是晃公武对自己家藏书籍进行整理著录的一部书目,因此其著录的萧绮叙录《王子年拾遗记》应为其家藏之本。由此可见《拾遗记》在宋代流传是十分广泛的。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子部小说家类著录:“《拾遗记》十卷。晋陇西王嘉子年撰,萧绮叙录。又《名山记》一卷,亦称王子年,即前之第十卷,大抵皆诡诞。”[11]《直斋书录解题》也是陈振孙对自己私家藏书情况的反映,值得一提的是其又称王嘉撰《名山记》一卷。
宋末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二一五子部小说家类著录:“《王子年拾遗记》十卷,《名山记》一卷。”[12]《文献大通考·经籍考》基本承袭《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而来,因此其对《拾遗记》的著录应该是抄录《直斋书录解题》而来。
《宋史·艺文志》卷二一六小说家类著录:“《王子年拾遗记》十卷,晋王嘉撰。”[13]据黄爱平研究《宋史·艺文志》云其“主要依据宋人编纂的四种《国史艺文志》……并补充宁宗以后书目编纂而成……缺乏剪裁编定之历力,存在一些颠倒错乱之处,如尤袤《遂初堂书目》误为《遂安堂书目》等。”[14]《宋史·艺文志》对《王子年拾遗记》作者萧绮错著成了王嘉,很明显是承袭旧录,不加考察而来。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著录:“《拾遗记》十卷(内府藏本)。秦王嘉撰。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事迹具《晋书·艺术传》。故旧本系之晋代。然嘉实苻秦方士,是时关中云扰,与典午隔绝久矣。称晋人者,非也。其书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后经乱亡残阙,梁萧绮搜罗补缀,定为十卷,并附著所论,命之曰录,即此本也。绮序称文起羲、炎以来,事迄西晋之末。然第九卷记石虎燋龙至石氏破灭,则事在穆帝永和六年之后,入东晋久矣。绮亦约略言之也。”[15]《四库全书总目》不但对《拾遗记》作者王嘉所处时代进行了考证,而且对萧绮所《录》之流行本《王子年拾遗记》来历、内容作了分析说明,应该说《四库全书总目》考证是比较中肯的。
综上所述,王嘉所撰原本《拾遗记》最迟在宋初便已不存于世。从宋代开始便只有萧绮作《录》的十卷本《王子年拾遗记》流行于世,而这个本子是在王嘉原书十九卷散佚基础上,搜罗补缀而成的,因此已经部分脱离了王嘉原书的面貌。但因其内容丰富,文字优美,便取代了王嘉原书成为后世唯一通行之本。
三、唐至清间有关《拾遗记》诸家观点析疑
最早对《拾遗记》的内容提出看法的是萧绮,②他在给《拾遗记》写的序中提出:“王子年乃搜撰异同,而殊怪必举,纪事存朴,爱广尚奇。宪章稽古之文,绮综编杂之部。《山海经》所不载,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记矣……盖绝世而弘博矣!”[6]可见萧绮认为《拾遗记》是一部记事广博,语多涉祥瑞之书,对该书做出了很高评价。而到了唐代的刘知几,则对《拾遗记》提出了否定的看法。他在《史通·杂述篇》中说“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即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16]可见刘知几认为所谓逸事,是后人对前史的补遗,广求异说,有助于正史完善。而如王嘉《拾遗记》之类,则全属虚构,炫人耳目而已,非但无益于正史,而且流弊甚深。值得一提的是,刘知几是在史馆撰修《唐书》,与主管官员修史立场不合的情况下,才愤而撰写《史通》的,而其对《拾遗记》态度也与《隋书·经籍志》撰修者将《拾遗记》放入杂史类作法相佐。可见刘知几的主张是与当时整个官方学术风气不协调的。
因此同时期的张柬之在《洞冥记跋》中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昔葛洪造《汉武内传》《西京杂记》、虞义造《王子年拾遗录》,王俭造《汉武故事》,并操觚凿空,恣情迂诞,而学者耽阅,以广闻见,亦各其志,庸何伤乎!”[17]张柬之在此处提到“虞义造《王子年拾遗录》”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萧绮撰《王子年拾遗记》有异。大概是王嘉在撰作《拾遗记》之后,该书在流传过程中有所散佚,虞义、萧绮等人又对其进行补充增改。张柬之对《拾遗记》看法就与刘知几有很大不同,他认为《拾遗记》一类书有助于学者增广见闻,各尽其志。张柬之作为当时朝廷重臣,他的观点应该说与官方主流思想相一致。
到了宋代晃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认为“晋王嘉字子年,尝著书百二十篇,载伏羲以来异事,前世奇诡之说。”[11]晃公武虽然把《拾遗记》放在史部传记类,但是又认为其多奇诡说,表示了对《拾遗记》内容记载真实性的怀疑。而上文所引《中兴馆阁书目》则将《拾遗记》放在了别史类,但是也认为其“事多诡怪”。可见至迟在南宋初期,虽然公私目录仍然将《拾遗记》著录在史部,但是学者已经对此书内容的可信程度产生了非常大的怀疑。这与唐代官方主流思想对《拾遗记》的看法是相迥异的。
到了明代,学者在宋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拾遗记》提出了质疑。杨慎在《丹铅总录》卷十中说:“其书全无凭证,只讲虚空。首篇谓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为悖乱。嘉盖无德而诡隐,无才而强饰,如今之走帐黄冠,游方羽客;伪荐欺人,假丹误俗,是其故智,而移于笔札,世犹传信之,深可怪也哉。”[18]杨慎从宋明理学思想出发,认为《拾遗记》首篇所记少昊之母有桑中之行,不符合传统儒家道德规范,进而对《拾遗记》一书做出了全面的否定,甚至对王嘉本人做出了强烈批判。但是从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少昊之世很有可能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因此少昊之母做出桑中之行并不足奇。倒是扬慎把春秋时期出现以至发展到宋明时期儒家理学思想强加于三皇五帝时期之人,可见其迂不可及。总之,杨慎对《拾遗记》的批判并没有任何的说服力。
胡应麟在他的《少室山房笔丛》中对杨慎的说法进行了修正,“《拾遗记》称王嘉子年、萧绮传录,盖即绮传而托之王嘉。中所记无一事实者。皇娥等歌,浮艳浅薄,然词人往往用之,以境界相近故。又《名山记》亦赝作,今不传”。[19]胡应麟虽然也认为《拾遗记》之记载缺乏真实性,但是又认为其可供词人取资。胡应麟并不像杨慎那样单纯从儒家传统思想出发对《拾遗记》进行全面否定,而是从传统的辨伪学出发,对《拾遗记》的文献价值作出了客观评价。
到了清代,虽然也有王谟在《汉魏丛书·拾遗记跋》中提出:“而嘉乃凿空著书,专说伏羲以来异事。其甚者,至以《卫风·桑中》托始皇娥,为有淫佚之行。诬枉不道如此,其见杀于苌,非不幸也。”[1]121可以看出王谟的观点是对杨慎旧说的老调重弹。因此在清代,胡应麟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而王谟的看法则不被人们所重视。如顾春世德堂本《拾遗记》跋:“王子年《拾遗记》十卷,上溯羲、农,下沿典午,旁及海外瑰奇诡异之说,无不具载。萧绮复节为之录,搜抉典坟,符证秘隐,词藻灿然。……邵伯温有云:‘四海九州之外,何物不有,特人耳目未及,辄谓之妄;矧邃古之事,何可必其为无耶?博洽者固将有取矣。’”[20]就连四库馆臣也不得不承认:“然历代词人,取材不竭,亦刘勰所谓‘事本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者乎。《虞初》九百,汉人备录,六朝旧笈,今亦存备採掇焉。”[15]就上述两条资料来看,当时人们已认为《拾遗记》“有助文章”,“而词条艳发,摛华掞藻者,挹取不穷。”把关注的重心从史的记载荒诞不经的方面转到了小说注重文采,可以作为文章素材来源的方面上了。
到了谭献,他把《拾遗记》的地位再次提高了,并提出了与杨慎和王谟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在《复堂日记》卷五云:“《拾遗记》,艳异之祖,恢谲之尤,文富旨荒,不为典要,予少时之话如此。今三复乃见作者之用心,奎虐之朝,阳九之运,述往事以讥切时王,所谓陈古以刺今也。篇中于忠谏之辞,兴亡之迹,三致意焉。萧绮附录,大义轨于正道,是非不谬于圣人者已。”[21]可见谭献认为《拾遗记》是一部明兴亡之迹,陈大义,辅圣人的用世之书,这超过此前所有人对《拾遗记》的评价。
综上所述,历代学者对《拾遗记》一书的文献价值认知,基本是与其所处时代学术风气相始终的。如唐代上有统治者的倡导,下有文人对诗赋取士的需要,故有唐一代基本对《拾遗记》是持肯定态度的。如宋代注重历史记载的真实可靠性,这一点从宋代出现多种体裁的史部著作可以看出,所以宋代学者对《拾遗记》一书记载可靠性多持怀疑态度。之后有一些卓著文献学家能够突破时代限制,提出具有令人启发意义的创论,如刘知几、胡应麟等人。总之,从历代各家的分析论断来看,在文章开篇所提出王谟观点是基本符合学术发展主流的。
四、《拾遗记》由史入子因缘再析
关于《拾遗记》在历代书目中的变化情况,可以引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六十六云:
《拾遗记》十卷,秦王嘉撰。《四库全书》著录。《隋志》杂史类作《拾遗录》二卷。新、旧《唐志》杂史类俱作《拾遗录》三卷,又《拾遗记》十卷,注云:“萧绮录。”《崇文总目》传记类、《读书志》传记类、《书录解题》《通考》《宋志》俱作《拾遗记》十卷。盖子年撰而绮叙录,故二《唐志》俱分载也。据绮序,知王氏书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经乱佚阙,绮掇拾残文,编为十卷,并为之《录》,《录》即论赞之别名也。然则隋、唐志所载二卷、三卷之本,亦非子年之原书矣。所记上起三皇,下迄石虎,事迹奇诡,十不一真,徒以词条丰蔚,颇有资于词章。至绮所论断,虽为畅达,亦不过扬其颓波耳。[22]
从这段话中可以发现《拾遗记》的分类发生了三次变化,从《隋志》和新、旧《唐志》的杂史类,到《崇文总目》和《郡斋读书志》传记类,再到《书录解题》《通考》《宋志》小说类,而这三次变化也可简单归为从史部到子部的变化。如何认识这样的变化呢?笔者认为可以从王应麟的《玉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找到蛛丝马迹。
王应麟《玉海·艺文·纪志篇》提到:“《中兴书目·别史类》,晋王嘉撰著《拾遗记》十卷,事多诡怪,今行于世。”[4]109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九传记类也提到:“晋王嘉字子年,尝著书百二十篇,载伏羲以来异事,前世奇诡之说。”[11]对比两条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兴书目》和《郡斋读书志》中都认为《拾遗记》是一部“事多诡怪”之书。据此推论,到了宋代当时大多数目录学家认为《拾遗记》的内容与史书要求记载真实可信性相脱离,但还是囿于前人之说,依然将其著录于史部。而到了陈振孙才勇敢迈出了这一步,将《拾遗记》著录在子部小说类。对此有人可能会感到疑惑,记事多诡怪怎么会归到小说类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杂史类与小说类的区别。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对杂史解释云:
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5]1010
而《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对小说家的解释云: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5]1012
对比一下我们可以发现,杂家类重在通众家之思想学说,来表现王者的政绩,所谓“无所不冠者也”。而小说家则重在记一些道听途说,街谈巷语之事。正如鲁迅所说:“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23]相对于杂史,小说更容易让人产生记事诡怪,多虚枉不实之印象。而且关于杂史与小说的关系,四库馆臣在《四库提要》小说家类杂事之属后云“案记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对此王瑶先生也有精辟的见解“小说本出于方士对闾里传说的改造和修饰,所以即如《洞冥》《拾遗》,也是凭借于史的”。[24]
综上所述,《拾遗记》最初著录在史部杂史类,与唐代的政治环境与学术风气紧密相关。乃至北宋、南宋初期,随着目录学理论进一步深化,对史部著作分类的更加规范,虽然仍将其归入史部,但已将其由杂史类降入了记传类。而南宋中期的陈振孙则更将《拾遗记》归入子部小说类,亦为后世所认可。
[注释]
① 如魏晋时期出现“当涂高”,“牛为马后”等大量谶语,见陈寿《三国志》、房玄龄等编《晋书》。
② 关于萧绮生活的年代,目前大概的推测是在隋以前,因为最早提到萧绮的是《隋书》,在《隋志》杂史类里提到《王子年拾遗记》十卷,萧绮撰。
[1](清)王谟.汉魏丛书[M]//.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496-2497.
[3](南梁)代释慧皎.高僧传合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33.
[4](宋)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5](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后秦)王嘉.萧绮.拾遗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5:1.
[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45.
[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66.
[9](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5.
[10]孙猛.郡斋读书志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67.
[11](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16.
[1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1755.
[13](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5219.
[14]黄爱平,等.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出版社,2010:294.
[15](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207.
[16](清)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74-275.
[17](宋)晁载之.续谈助[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16.
[18](明)杨慎.丹铅总录 [M]//.四库全书 (第85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13:433-434.
[19](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318.
[20](后秦)王嘉.拾遗记[M].明嘉靖顾春世德堂本.
[21](清)谭献.复堂日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10.
[22](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1306.
[2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4:25
[24]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