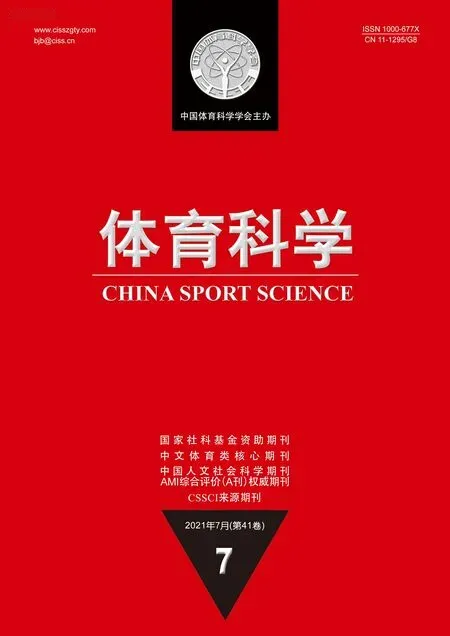超人类主义对体育的挑战
2018-01-28朱彦明
朱彦明
超人类主义对体育的挑战
朱彦明
华侨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超人类主义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崛起的一场知识和文化运动,近年来也逐渐渗透到体育领域。超人类主义支持通过新科技改善人的体能、智力、情感等方面,虽然这与体育追求卓越的精神“合拍”,但对体育来说更多的是挑战。尤其是超人类主义主张的超越人生物的、遗传的限度,它的“后人类”目标,不仅质疑了体育赛事禁止兴奋剂包括基因兴奋剂的合理性,而且还为体育赛事接纳“超人类运动员”、“后人类运动员”以及“基因增强的运动员”作理论辩护。超人类主义追求的超越人类生物限度的完美主义,都是一种病态的完美主义,这不仅背离了体育运动的本质,而且也摧毁了人性基础。
超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体育;公平;自主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崛起了一场知识和文化运动即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运动。由于超人类主义的目标是“后人类”(posthuman),所以它与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有着内涵上的重叠,但超人类主义更强调超越的过程、趋向和路径。简单地说,超人类主义就是利用科技进步——尤其是生物技术的进步——对当前人类的体能、智力、情感、道德等方方面面进行改善的浩大工程。这一工程(有的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实验)甚至被称为一场“革命”[1]。超人类主义虽然流派众多,观点各异,但其代表大都是技术乐观主义者。尽管超人类主义者也认识到使用新技术(比如,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再生医学、机器人技术、3D打印和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风险,但他们还是对新技术的应用前景充满热情,并要求大胆地、创造性地利用新技术来改善人类。超人类主义在媒体、艺术、哲学、政治等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年来,超人类主义也逐渐渗透到体育领域,学界开始讨论“超人类运动员”、“后人类运动员”、“基因增强的运动员”等,就是典型的表现。但是,在笔者看来,超人类主义对体育界来说更多地是挑战,因为它使体育的公平、诚信、正义、追求卓越等精神价值都发生了变化,甚至陷入困境。应对这种挑战,不光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以及相关体育机构的职责,也需要体育学界乃至其他领域的思想家、学者们积极参与讨论,并为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做出理论上的贡献。
1 什么是超人类主义?
“超人类主义”这个概念最早由进化论生物学家赫胥黎(Julian Huxley)在1957年提出。它表达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性发展的思想。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超人类主义逐渐发展成一种影响广泛的知识和文化运动。1990年,美国哲学家摩尔(Max More)最先从哲学上定义了超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属于一种生命哲学范畴,它追求智力生命进化的连续和加速,由改善生命的原则和价值引导,利用科学和技术手段超越当前人的形式和限度。[8]”随后,欧洲超人类主义哲学家博斯特伦(Nick Bostrom)和皮尔斯(David Pearce)在1998年创立了“世界超人类协会”(WTA)。它的目的是推进人们对超人类主义的理解,并拥有自己专门的杂志。WTA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会员,影响巨大,并在2009年更名为H+。它的活动包括在互联网上进行学术交流、组织会议以及专门为学生讨论开设的网上交流等。
超人类主义吸引了很多科学家、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的参与,还获得了谷歌公司的资金支持。在英国、瑞典、澳大利亚、美国、比利时、法国、奥地利等地都有自己的超人类主义研究机构以及大量的追随者。超人类主义之所以在西方世界影响广泛,还存在另外两大支柱:1)“超人类主义宣言”(以下简称“宣言”);2)4份超人类主义研究报告。
“宣言”系两大超人类主义代表即博斯特伦和摩尔执笔完成,共有8条内容。它指明了超人类主义利用科技改善人类的前景,同时也要求研究风险,尊重人权、关注个人的权利和尊严等[1]。从2003年到2009年,超人类主义运动陆续产生了4份重要的报告。大体而言,这些报告既反映了人们对新技术应用前景的热情和乐观情绪,同时也表达了某种担忧。其中,围绕着“增强”/“治疗”的生物学和医学的争论影响甚大,这也拉开了生物激进主义者和生物保守主义者之间的理论大战。很多超人类主义者都属于生物激进主义,认为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人性是可以无限完善的。他们还把古典人文主义者,比如米兰多拉(Pic de la Mirandole)、孔多塞、康德、卢梭、培根、拉美特利等看成是超人类主义的先驱。而像福山(Francis Fukuyama)、桑德尔(Michael Sandel)和哈贝马斯则属于生物保守主义阵营。他们都反对任何非治疗性的“增强”人的做法,认为医学应当停留在以治疗为目的的传统框架中。他们尤其批判了利用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来制造“超级(优秀)儿童”、“不会衰老的身体”等计划[1]。不管怎样,这4份报告都传达了一个声音,利用新技术来增强人(不管是以治疗为目的,还是非治疗目的)将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大趋势。我们可以思考它带来的益处以及可能产生的风险,但是无法无视或否定它的存在。
超人类主义虽然流派众多,观点各异,但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阵营。第1个阵营“仅仅”要求改善人类,而不牺牲人性。这个阵营的超人类主义代表将自身看成是过去人文主义的延续,主张人的无限完善性。前文所述的摩尔和博斯特伦都属于这个阵营。他们都强调,超人类主义继承了启蒙理性主义的遗产,但它与传统人文主义的差别在于,他们认为,可以利用新技术成果克服人生物的、遗传上的局限,而不是仅仅通过教育和文化教化来塑造人。特别是新技术的发展,使超人类主义看到了超越“人的条件”的可能性。即是说,可以按照人们所希望的方式塑造自身,利用新技术,人们可以变成“后人类”[8]。这不是意味着走向新物种,但在体能、智力、情感等方面都肯定超越了现在的人。
第2个阵营以莫拉维茨(Hans Moravec)和库兹韦尔(Ray Kurzweil)为代表。与第1个阵营不同,莫拉维茨和库兹韦尔代表的阵营,通常称为“奇点论派”或“宇宙派”。因为他们都认为随着技术的(指数级的)发展,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趋近“奇点”(singularity)。它标志着人类社会将会发生断裂式的改变,撕裂人类历史和社会结构。“奇点”的到来,人类生物性将被人机联合的超智能所取代,人类的“后代”将完全超越人类。这个时间点就是“技术奇点”,即人类将向完全的智能化、非生物化迈进,并在本世纪末成为宇宙智能的一部分。库兹韦尔说:“奇点将允许我们超越身体和大脑的限制:我们将获得超越命运的力量;我们将可以控制死亡;我们将可以活到自己想达到的年龄(这与‘永生’有细微差别)。我们将充分理解人类的思想并极大程度地拓展思想的外延。在21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人类智能的非生物部分将无限超越人类智能本身。[3]”可以看出,与第1个阵营要求仅仅增强人类相比,第2个阵营则思考了人类向非生物化迈进,其“后人类”目标,完全是一个新物种。
不过,在笔者看来,上面这两个阵营之间,并不存在绝对清晰的界限。或者说,前一个阵营很有可能会滑向后一个阵营。因为追求人的无限完善,如果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就有可能要求创造一个新物种,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不妨这样来区分两者,前者可以理解为趋向“后人类”的路径或过程,而后者则可以视为结果或终点。即使一开始这两个阵营之间存在差异,但最终还是可能殊途同归。一旦没有技术应用上的防范措施,或没有确定道德底线,这个可能就无法避免。
超人类主义者大都是技术乐观主义者,虽然他们也要求认真对待技术应用的风险问题,但这仍然不能让人放心。首先,它将人类存在问题弄成了一个技术处理的问题,这多少带有技术决定论的倾向。在此方面,它也引发了生物保守主义者像福山、桑德尔、哈贝马斯等人的强烈反对。其次,它的一些计划和想象,还是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它思考的对人的改善,与启蒙思考的改善人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不同,它更注重改善我们“内部”生物数据。这引发了对“人”、“人性”等问题的争论。还有,像死亡问题,这不再属于神话、宗教或哲学问题,而是属于医学、生物学,尤其是著名的NBIC(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问题。它甚至相信通过新技术可以攻克死亡。不管怎样,超人类主义都拥有众多的追随者。正是在这种技术乐观主义的影响下,新技术爱好者们尤其是那些跨国公司的老板们愿意为它投资,并相信这样一定能够带来成功和利益。比如,谷歌首席执行官施密特(Eric Schmidt)强调:技术不仅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且如果我们做得足够好,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世界上的所有问题。这种信念,在美国硅谷非常流行。
2 超人类主义对体育的影响和挑战
超人类主义者主张超越人的生物体能限度,而体育从古希腊开始就追求身体“德性”的实现,追求优秀和卓越。现代精英体育,以“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不断挑战极限,通过改造运动装备(比如网球拍、游泳衣、运动鞋)来提升运动员成绩,利用科技手段锻炼运动员适应能力(比如营造低氧环境),这冒似与超人类主义理想相“合拍”。所以,有的学者认为,精英体育可以证明超人类主义的合理性,因为精英体育已经是超人类主义的方式了[6]。现代体育中,运动设施、装备、专门的食谱等,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有利于提高运动成绩,增强技能。运动员不断地爆出兴奋剂丑闻,从反面也印证了这种对“增强”的追求。如果说这些还不能算成真正的超人类主义,那么今天的体育学界开始讨论“超人类运动员”、“后人类运动员”、“基因增强的运动员”等概念,已经毫无争议的表明,超人类主义已经渗透到了体育领域。
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超人类主义渗透到体育领域,它将给体育带来巨大的改变:“今天,精英体育在日益不合规则的领域找到了自身。在此之前,运动员使用技术是为了优化生物技能,许多方法甚至都没有经过权威部门检验。从为运动进行的基因测试,到使用超人义肢来增强人,这达到了甚至今天的反兴奋剂规则都没有达到的程度。这些技术改变了精英体育,但是下个10年可能意味着对我们擅长的体育的大修正……我们将有此问,是否关于运动技能的伦理争论将要结束,而优胜者的领奖台将会为超人类运动员腾出空间?[7]”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未来将会怎样,可能是无法预测的。一旦出现基因改变或增强运动员,是否允许他/她与非增强运动员同台竞技呢?这是否会改变体育运动的本质呢?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不管怎样,超人类主义对于体育领域来说,更多地是挑战。
1. 它挑战了禁止兴奋剂包括基因兴奋剂的合理性。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对于非治疗目的增强即从服用违禁药物到基因兴奋剂都严令禁止,认为增强运动员会伤害运动员身体,违背公平竞赛规则,有悖于体育精神。按照WADA的定义,基因或细胞兴奋剂是指非治疗目的的使用能够提高运动能力的细胞、基因、遗传物质。包括红细胞生成素(EPO)、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1)、生长荷尔蒙(GH)、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肌生成抑制素(Myostain)等。这些都属于被禁之列[2]。基因兴奋剂可以起到专门的增强效果,比如,为肌肉输送更多的养分,促进肉身生长、增强耐力等。有些虽然在医学上被认可(比如,医学上使用能够提高肌肉力量的基因药物、抗衰老的药物、加快骨髓恢复的药物等),但在体育上却是被禁止的。超人类主义者所质疑的,就是这种禁止的理由。
以米阿(Andy Miah)为代表的超人类主义理论家认为,禁止增强运动员的做法,没有充分的理由。他说:“关于基因兴奋剂,WADA并没有与基因伦理学委员会、合法权威、智囊或政府顾问团体进行对话。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基因兴奋剂的政策制定,与更宽泛的生物伦理以及关于可以接受的合法决策之间并不协调。[14]”米阿的意思是,关于人的自然性、人格、人性、规范性、自主性以及诚信等问题,都需要在体育伦理学和生物伦理学的双重层面上来讨论。因为是否禁止基因兴奋剂不仅仅是体育权威部门的问题,还需要考虑到人追求生命繁荣的权利。同时,体育权威部门不仅是处理运动员的诚信问题,也是处理社会上那些基因增强的人是否有资格参与体育比赛的问题。如果认为基因增强都是违反体育诚信,那么如果基因干预在一个人的胚胎阶段发生,难道也要禁止他或她长大之后从事竞技体育吗?简言之,米阿表明的是,决定是否禁止基因兴奋剂的问题,不能抛开社会大背景。如果某些基因改造项目被社会所接受,那么体育上的禁止就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
2. 它反驳了基因兴奋剂损害运动员健康的说法,认为强行禁止反而助长了家长式作风。基因兴奋剂会损害运动员的健康吗?至少目前为止,临床基因治疗还是相对安全的,医学上也有一些先例。体育机构或主管部门为了基因检测,要求运动员无条件提交自身生物遗传数据,这难道不是侵犯人的隐私权吗?这实际上也限制了运动员的自我选择的自由。“当前反对基因兴奋剂还是家长式的:禁止兴奋剂是为了保证运动实践者的健康。于是,运动员在他确定为适宜的行为方式上也被阻止了。职业运动员不允许自我决定他们在追求事业中要冒的风险。[15]”国家或体育部门对运动员个人自由选择进行强制性干预。即便是为了运动员的健康考虑,也往往带有限制运动员自由的嫌疑。“通过一种家长式的方式,坚持我们比运动员自身就什么是对他们最好的而言知道得更多,我们是在否定他们的自信、人格实现以及自主……将他们看成是小孩子,认为他们不能对影响他们的东西作出选择。[12]”另外,即使是加以限制,运动员增强的冲动也无法去除,反而会导致以地下的方式偷偷地尝试。一旦这种地下医疗环境存在,运动员仍然会铤而走险。
3. 它认为基因不是决定运动的根本因素。通常认为,正常选手和基因增强的运动员同台竞技,就会产生不公平、非正义并使体育丧失本来就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或者认为体育因此就会失去了观赏性、悬念或者不可预测的特征。在超人类主义者看来,这些观点都是夸大其词。因为即使基因增强的运动员参赛,目前为止也没有产生什么神奇效果。南非残疾运动员皮斯托留斯(被称为“无腿飞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在体育比赛装上的义肢一度被认为有“增强”技能的效果,但由于论据不足,国际田联最终还是不得不允许他参加正常人的体育比赛(条件是他要达到参赛资格)。如果运动员是靠神奇的药物赢得的比赛,或者说他在某一天接受了基因增强的医学帮助就可以一下子获胜,在目前的精英体育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努力、投入热情以及自我克服仍然是体育比赛的关键因素。这不是基因的“运气”造成的[11]。所以,即使是基因增强的运动员参赛,也需要经过艰苦训练才能取得好成绩,这并没有违背体育精神。
实际上,在竞技体育中,运动员的基因差异或基因不平等,一开始就是给定的。比如,某些运动员努力训练并提高了技能,但有可能仍然无法战胜其他更优秀者。通常会认为,赢得奖牌的都是一些刻苦训练并有着特殊天赋的运动员。这不正是承认基因不平等吗?但是,事实是,我们通常都会忽略这个问题,认为运动员的运动技能、人格特质才是关键的决定因素。所以,不是说运动员在基因上越是平等,体育越是公平。胜利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由基因因素决定的,而是靠努力实现的。如果增强问题可以进行医学控制,确定每一种体育比赛的标准,竞赛可能就会越来越平等。竞技体育,可能因此变得更有趣,更加刺激。[11]总之,他们认为,那种认为基因增强就会绝对影响体育道德的结论是草率的,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限制运动员进行基因增强。只要我们尊重运动员的意愿,而不是强制其基因增强,那么我们就可以接纳“超人类运动员”。
上述以米阿为代表的超人类主义者虽然不是公然挑战体育机构和权威部门禁止非医学性增强的措施,但是,该理论明显是怀疑这些措施的合理性,并且提出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理由。他们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即认为体育上对非治疗性的增强包括对基因兴奋剂的禁止,理由并不充分,需要讨论和修正。他们的超人类主义立场坚持认为,正常运动员和基因改变的运动员同台竞技,并不会影响公平竞赛,也不会破坏体育精神。
体育赛事中兴奋剂药物屡禁不止,说明基因兴奋剂肯定也将成为部分运动员追求的目标,尽管目前还没有运用于体育上。现在,超人类主义的观念又在背后“撑腰”,这必将给体育带来巨大的挑战。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反兴奋剂机构也都非常担忧,因为它不像其他兴奋剂药物,被改变的基因不可能在尿液甚至血检中查出来,基因检测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很可能会造成一个后果:检测技术和增强技术的相互博弈。医学上对某些基因治疗和增强的认可,也使得此类禁令在体育领域面临考验。体育是否应当接受医学权威部门作出的裁决,还是坚持人自然天赋的标准,这些都需要体育学界和其他领域的理论家和学者们,多方位、多角度地探讨这个问题,毕竟体育无法孤立于社会环境。只有如此,才能找到制定更为合理的政策和措施的理由和根据。
3 如何应对超人类主义的挑战?
在当前西方理论竞技场中,虽然超人类主义势头强劲,但是,我们也能够发现不同甚至相反的倾向,比如一些推崇自然主义、自然教育以及主张回归人文精神思潮的出现。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利伯曼(Daniel Lieberman)代表的进化生物学就非常有代表性。2013年,利伯曼出版了《人体的故事:进化、健康和疾病》,该书虽然没有直接回应超人类主义或后人类主义,但其中却包含了可以批判后者的重要观点。在人类进化历史中,利伯曼认为,人类虽然利用科学和技术创造了更好的生活条件,但也会使文明产生一些不匹配的新疾病,那种认为人工改变会比自然赋予更好的肯定是一种危险的傲慢态度。我们不能像科幻故事或电影表达的那样超越人的生物限度,变成赛博格,而是要善待我们的身体和生物性。他说:“从自身物种的丰富而又复杂的进化史中,可以学习的、最受用的教训,就是文化不容许我们超越自身生物学。人的进化从来不是智力胜过体力,我们要怀疑那种认为未来将会不同的科学幻想。[4]”与此类似,有的学者还提出了新的“进化本体论”,肯定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生成,反对那种反自然的进化观念,也反对技术主导的进化理论[13]。这种新本体论指出,人类文明在今天的困境(尤其是环境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视自然对文化的协调能力造成的,结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笔者看来,上述这些思潮,虽然很少讨论到体育,但仍然对体育领域在应对超人类主义的挑战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把人的自然性、生物性作为人性基础,前文以福山、桑德尔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生物保守主义,也表达了类似的观念。他们都反对超人类主义者主张的非治疗性“增强”的观念,反对技术主宰的进化,要求尊重自然和人的尊严,而不是走向非人化的赛博格或新物种。本文在此重点讨论桑德尔的思想,因为他在《反对完美:基因工程时代的伦理学》中不仅批判了超人类主义,而且还直接讨论了“仿生运动员”问题,这也是对体育上的超人类主义的直接回应。
桑德尔认为,运动员越是依赖药物或者基因增强,他的表现越是背离他自身的努力成就和优秀品质。我们可以想象机器人、仿生运动员的出现,但是,这不再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员了,而是他的发明者的“成绩”了。今天一个棒球运动员没有击中反弹球,他的教练可能会认为他站的位置不对,但是,未来教练可能会谴责他个子矮(即应当进行基因增强)。一旦基因增强在体育领域盛行,势必会破坏体育的至高理想。体育不再是鼓舞人心的项目,而是变成了“景观”(spectacle)一样的娱乐。“对于基因工程时代来说,体育降为景观并非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但是,它证明了增强技能的技术,基因技术或者其他技术,可能摧毁运动员以及人们对自然天资和天赋艺术展现的尊重。[10]”那么,这必然引发对完美基因知识的追求,造成了追求完美的疯狂竞赛。“随着增强作用的提高,我们对运动员的表现不会刮目相看了。或者说,比赛从看运动员的能力变成了看药剂师的本事”[10]。我们不再惊叹运动员的表现,而是惊叹增强运动员的技术。技术变成了主角,运动员的能力和天赋则是成为了次要的。桑德尔对超人类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指出了超人类主义会使我们从现存的伦理,即对自然天赋的感激转向了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绝对控制。这破坏了人类物种的谦卑、无辜与相互帮助的价值。
同样讨论人性,美国哲学家、伦理学家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也反对超人类主义的论调。在她《爱的知识》中的最后一章,她讨论了“超越人性”的问题,并将之与体育运动关联起来。纳斯鲍姆肯定了人追求卓越、优秀的激情和能力,从古希腊神话开始(她讨论了《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放弃追求不朽,宁愿漂泊回到故乡的故事),人追求的就是有限度的、有死的生活,这与奥林匹亚众神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是绝对完美,永恒不朽,人的追求只能达到相对的完美。这种完美主义,是一种“内在超越”。它不是要放弃或拒绝人的限度,而是在自然限度的基础上自我超越,追求完美。纳斯鲍姆将这个思想应用于体育领域,她认为,体育一开始就是通过人的(有限度的)身体来实现的优秀。对于运动员或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一样,这是一种悖论,即他/她都是通过自己的限度来实现完美,而不是超出限度。“人的限度成就人的优秀,赋予优秀行为意义”[9]。虽然我们常常说超越极限,但是限度仍然是存在的。没有限度,就等于背离了人的生活,人的本性。如果运动员没有身体的限度,没有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优秀,即使成绩再好,也将会不受尊敬。这就好比我们观看技术或机器表演一样,不会对此种“完美运动员”刮目相看。纳斯鲍姆从古希腊神话中发现了体现在运动员乃至人类物种身上的人性特质:人的一切行为都立足于有限性基础。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或排除这个限度,必将摧毁人性本身。
纳斯鲍姆的这种观点得到了体育哲学家麦克纳米(Michael McNamee)的声援,他在讨论超人类主义完美观念的时候也区分了相对完美和绝对完美[5]。前者指的是完成了某个任务,关联着具体的方法、作用、技能等。后者往往存在于某种神学或伦理学中,关联的是人的整个存在问题。相对完美不是没有缺陷,它是展现人在某一个方面的能力、技巧以及人格特质。运动员的完美,也应当是这个相对的概念。运动场上的完美,可以是某次击球、某个点球、某个动作等,如果表达完美,或者几乎没有什么缺陷和不足,这当然令人羡慕,但这都是根据某个具体目标或者发挥某种具体的作用来说的。也就是说,这里的完美是具体的、相对的概念。
麦克纳米认为,我们不应当将“超人类运动员”思考为最完美的运动员。“超人类运动员”给人的感觉是超越人类(自身限度)去实现优秀,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观念,也就是说,为了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或者运动员,我们就需要超越人类共同的本质。这是一种病态的完美[16]。对于运动员来说是这样,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如此。人性,作为我们的本性,我们的存在方式,是构成我们尊严的东西。那种想要超越人性的做法是病态的。去除了人的限度等同于去除了赋予体育意义和价值的框架和思想。超人类主义的理想体现在体育上,就是让我们看一场机器人或半机器人的表演,这只不过是让人欣赏技术罢了。从根本上看,体育上的超人类主义是一种狭隘的体育观念,就是将体育看成是人的潜能的最大化,生物技术的发展,为它打开了新的可能性。但是,它明显只是关注体育自身的价值,忽视了体育之外的社会、文化价值,把体育与社会上技术主宰的幻觉混杂起来,即便我们承认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但超越人性的做法也是极其荒谬的。
利用新技术增强运动员,我们大致可以分成3种立场:1)功利主义的立场。它将体育看成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体育没有自身目的,它只是服务于体育之外的目的。比如,一些商业性质的体育公司开发体育,就是为了赚钱的目的。2)比较偏狭的运动观。这种立场认为体育就是不断地“进步”、“超越”,打破记录。它认为只要能够帮助体育竞技实现完美,一切技术手段都是可以接受的,包括兴奋剂药物、基因增强等。3)体育伦理学立场。它把体育理解为一种社会实践,并且带有规范、价值以及内在的善。它主张体育应当捍卫、保护和培养规范和价值,而不是仅仅追求技能的提高。本文讨论的超人类主义,当然是第1种立场和第2种立场的混杂,它明显排除了第3种立场。可以这样说,超人类主义运动,代表了一场经济、技术、知识之间的新的联合。塑造“超人类运动员”,不仅是新技术的应用,而且还是投资集团的利益追求以及技术完美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借助利伯曼、桑德尔、纳斯鲍姆、麦克纳米等人的思想,本文倾向于第3种立场,认为人的有限性成就了人的价值和人的行为意义,成就了人的爱、谦卑、团结、互助以及关心他者。因此,应当批判那种功利主义的、狭隘的体育观念。它的超人类主义追求的完美,也是一种狭隘的、病态的完美。体育是通过人的身体和天赋实现的优秀,那种想要通过技术超越人的自然性、生物性的做法,不仅违背了体育的本质,也摧毁了它的人性基础。
4 结语
超人类主义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它的背后不仅有着强大的经济力量支持,而且还有意识形态为之张目。超人类主义者自称是启蒙遗产的继承者,推崇理性和进步。但是,矛盾的地方是,西方启蒙对人的社会和政治解放的思考、对人自主性的强调,这些宏伟目标都被超人类主义者还原为一种技术主宰的雄心和幻觉。本来作为手段的东西,现在被当成了目的本身。“当时的人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掌握能让我们主宰世界的手段,还有主宰世界之后我们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有),因此,当时人对科学的兴趣还不是纯粹的‘技术员’式的、‘工具性’的,或者仅仅出于对‘实用性’的兴趣。对康德、伏尔泰还有笛卡尔来说,通过科学知识和人的意志在理论和实践上主宰世界,并不是纯粹出于对自身力量自恋式的迷恋以及主宰的快感。这不是为了控制而控制,而是要认识世界,利用我们的智慧来实现一些更高的目标。[1]”如果说西方启蒙理想中一开始还有全人类的自由和幸福的至高目标,那么今天这种技术狂热、技术乐观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服务于机械的自由竞争。历史没有目的因,历史不是被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更高的目标所引导,而是被一些动力因或被技术创新和发展的绝对命令强迫着、推动着前进。这难道不是启蒙理想的退化吗?
就目前来看,超人类主义在中国还没有流行起来。但是,我们当然不能忽视这种价值的输出。像很多美国科幻电影(比如《黑客帝国》《星际迷航》等)就宣扬了超人类主义。如果我们对超人类主义缺乏清醒的判断和理解,便可能被这种思想所“俘虏”。随着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未来超人类主义的影响和渗透将更为强烈。对此,我们应当做好迎接和应对的准备:1)要对超人类主义的不同形式有充分的了解和分析,确定哪些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哪些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拒绝的。2)可以通过激活中国古代科技思想,比如“技进乎道”,来批判极端的超人类主义,凸显技术与天地人整体之间的关联,守护好生态环境和家园。3)教育和培养人的技术素养,弘扬人文精神。我们不反对技术可以应用于体育竞技活动,体育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但也要警惕那种将体育变成一种完全商业化的、技术化的、排除了价值和规范引导的狭隘概念。体育是人生活的一部分,应当服务于人的理想和价值。
[1] 费希.超人类革命[M].周行,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4, 35-36, 16-19,181.
[2] 胡扬, 刘双虎.基因兴奋剂[J].体育科学,2007,27(4):95-97.
[3] 库兹韦尔.奇点临近[M].李庆诚,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2.
[4] LIEBERMAN D. The History of Human Body: Evolution, Health, and Diesease[M].New York: Pantheon Books,2013:387.
[5] MCNAMEE M. Sport, Virtues and Vices: Morality Play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2008:194-205.
[6] MIAH A. Be very afraid: Cyborg athletes, transhuman ideals & posthumanity[J].J Evol Technol,2003,13(2):75-90.
[7] MIAH A. Genetically Modified Athlete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4:10.
[8] MORE M,VITA-MORE N. The Transhumanism Reader[C]. New Jersey:Wiley-Blackwell, 2013:3,5.
[9] NUSSBAUM M. Love’s Knowled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378.
[10] SANDEL M.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M].Americ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4,25.
[11] SAVULESCU J,FODDY B,CLAYTON M. Why we should allow performance enhancing drugs in sport[J].Br J Sports Med,2004,38(3):660-678.
[12] SCHNEIDER A,RUPERT J. Constructing winners: The science and ethics of genetically manipulating athletes[J].J Philos Sports,2009,36(1):93-102.
[13] SMAJS J. Evolution Ontology: Reclaiming the Value of Nature by Transforming Culture[M]. Amsterdam-New York: Rodopi, 2008:2-3.
[14] TAMHURRIN C,TANNSJO T. The Ethics of Sports Medicin[C].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37.
[15] TAMHURRIN C,TANNSJO T. Values in Sport[C].London and New York: E. and FN, 2000:292.
[16] TOLLENEER J, STERCKX S, BONTE P. Athletic Enhancement, Human Nature and Ethics[C]. New York: Springer, 2013:185-200.
The Challenges of Transhumanism to the Sport
ZHU Yan-ming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China.
As a world-wid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movement in the west from 1990s, transhumanism permeates in the sport in resent years, whose aims of improvement of human body,intelligence and emotions ,in some respect, are “harmonious” with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the sport,but basically are challenges. The idea of its transcending the limits of human biologic and genetic condition,its “posthuman” goal, not only calls in question the prohibition of gene doping in the sport,but also justifies for “transhuman athlete”,“posthuman athlete” and “gene-enhanced athlete”.This perfectionism of transcending human limits, however, as a pathological conception,breaches the essence of sports and smashes humanity as well.
1000-677X(2018)07-0092-06
10.16469/j.css.201807022
G80-05
A
2018-03-28;
2018-07-05
朱彦明,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西方哲学、技术哲学、体育哲学,Email:zhuyanming20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