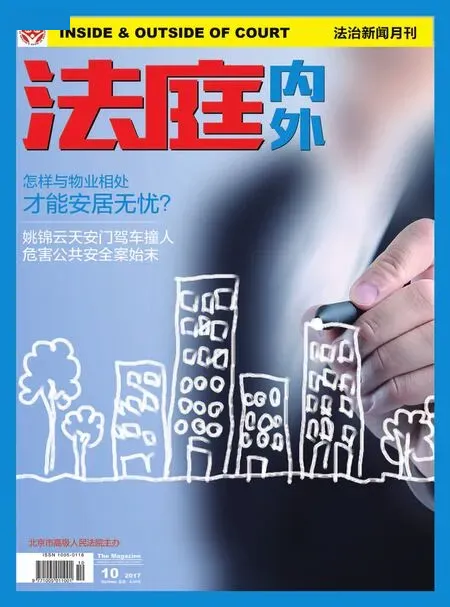北京大学违反“正当程序”被判败诉“抄袭者”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2018-01-26赵锋
赵锋
2017年6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于艳茹诉北京大学撤销博士学位决定一案作出终审判决,北京大学作出的校学位[2015]1号《关于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以下简称《撤销决定》)因程序违法被撤销,备受关注的案件审理告一段落。
案件判决后,舆论并没有停止,反而在社会上引发热议。令人惊喜的是,公众对于案件的关注不仅仅停留在案件结果的层面上,而是深入到判理研究的层面,尤其是对本案运用的正当程序原则给予高度关注和深入分析。这反映出公民权利意识的勃兴和公众法律素养的提升,也从侧面体现出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显著进步。
事实上,本案所运用的正当程序原则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90年代,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中,法官就已经在判决中对正当程序原则进行了阐释。该案例在2014年还被选入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38号指导案例。时隔18年,正当程序原则又再次出现在高校行政诉讼案件中,大学也再次因为违反正当程序原则栽了跟头。此时,我们不由会问,正当程序原则到底为何物?行政机关是否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对于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行政行为,法院应当如何处理?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于艳茹案的发展经过。
案情始末:撤销博士学位决定因程序违法被撤销
于艳茹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于2013年7月5日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2013年1月,于艳茹将其撰写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以下简称《运动》)向《国际新闻界》杂志社投稿。同年3月18日,该杂志社编辑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于艳茹按照该刊格式规范对《运动》一文进行修改。同年4月8日,于艳茹按照该杂志社要求通过电子邮件提交了修改稿。同年5月31日,于艳茹将该论文作为科研成果列入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注明“《国际新闻界》,2013年待发”。同年7月23日,《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7期)刊登《运动》一文。2014年8月17日,《国际新闻界》发布《关于于艳茹论文抄袭的公告》,认为于艳茹在《运动》一文中大段翻译原作者的论文,直接采用原作者引用的文献作为注释,其行为已构成严重抄袭。
随后,北京大学成立专家调查小组对于艳茹涉嫌抄袭一事进行调查。同年9月1日,北京大学专家调查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聘请法国史及法语专家对于艳茹的博士学位论文、《运动》一文及在校期间发表的其他论文进行审查。9月9日,于艳茹参加了专家调查小组第二次会议,于艳茹就涉案论文是否存在抄袭情况进行了陈述。
其间,外聘专家对涉案论文发表了评审意见,认为《运动》一文“属于严重抄袭”。10月8日,专家调查小组作出调查报告,该报告提到审查小组第三次会议中,审查小组成员认为《运动》一文“基本翻译外国学者的作品,因而可以视为严重抄袭,应给予严肃处理”。11月12日,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第117次会议,对于艳茹涉嫌抄袭事件进行审议,决定请法律专家对现有管理文件的法律效力进行审查。
2015年1月9日,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第118次会议,全票通过决定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同日,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于艳茹不服,向北京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同年3月16日,北京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作出申诉复查决定,决定维持《撤销决定》。3月18日,于艳茹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教委)提出申诉。5月18日,市教委作出《学生申诉答复意见书》,对于艳茹的申诉请求不予支持。于艳茹仍不服,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2017年1月17日,海淀法院经审理认为,学位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未对撤销博士学位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但撤销博士学位涉及相对人重大切身利益,是对取得博士学位人员获得的相应学术水平作出否定,对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因此,北京大学在作出被诉《撤销决定》之前,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听取于艳茹的陈述和申辩,保障于艳茹享有相应的权利。本案中,北京大学虽然在调查初期与于艳茹进行过一次约谈,于艳茹就涉案论文是否存在抄袭陈述了意见;但此次约谈是北京大学的专家调查小组进行的调查程序;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未充分听取于艳茹的陈述和申辩。
因此,北京大学作出的对于艳茹不利的《撤销决定》,有违正当程序原则。此外,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中未能明确其所适用的具体条款,适用法律亦存有不当之处。据此,海淀法院判决撤销了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北京大学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纵观本案,《撤销决定》被判决撤销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北京大学针对程序问题提出了两个层面的抗辩主张:一是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学校在作出撤销学位决定之前必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二是北京大学在作出决定前,曾经约谈过于艳茹,已经给其提供了充分陈述与申辩的机会。没有相关规定要求,上诉人必须向于艳茹说明其学位可能被撤销的后果。而且约谈属于调查程序,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向于艳茹提及最终处理结果的问题。于艳茹在受到处分之后,也已向学生申诉受理委员会提出申诉,委员会予以受理并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于艳茹本人的申辩,并进行了讨论。
此案一审判决结果公布后,引发了社会的热烈讨论,横亘于论文抄袭与“抄袭者”权益保护之间的鸿沟似乎成为了“自相矛盾”的痛点。
案件上诉到北京一中院,承办人在跟合议庭其他成员认真研究了案情后,针对北京大学的程序抗辩主张进行了逐条的分析。其中,有3个涉及正当程序原则的问题值得关注。
理解正当程序的两个关键词:“事前”与“充分”
任何权力必须公正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这是英美普通法的一个重要原则,称为自然公正原则。其核心思想被凝练为两句法律箴言: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响之前都要被听取意见。在行政实践中这个原则表现为行政机关的决定对当事人有不利的影响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能片面认定事实,剥夺对方辩护权利。
正当程序原则的核心内容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对当事人不利决定前,必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该原则保障的是相对人的程序参与权,通过相对人的陈述与申辩,使行政机关能够更加全面把握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防止偏听偏信,确保程序与结果的公正。因此,在理解和运用正当程序原则时需要把握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事前”。听取陈述与申辩须在作出决定之前,当事人陈述的意见应当作为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参考,作出决定之后再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则毫无意义。

北京大学提出,于艳茹在受到处分之后向学生申诉受理委员会提出申诉,委员会予以受理并专门召开会议听取其申辩,这一主张显然违背了事前听证的原则。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充分”。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而不是走形式。而充分陈述意见的前提是充分掌握信息、了解情况。相对人只有在充分了解案件事实、法律规定以及可能面临的不利后果之情形下,才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陈述与申辩,发表有价值的意见,从而保证其真正地参与执法程序,而不是流于形式。例如,行政处罚法在设定处罚听证程序时就明确规定,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
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仅由调查小组约谈过一次于艳茹,约谈的内容也仅涉及《运动》一文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至于该问题是否足以导致于艳茹的学位被撤销,北京大学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提示,于艳茹在未意识到其学位可能因此被撤销这一风险的情形下,也难以进行充分的陈述与申辩。因此,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由调查小组进行的约谈,不足以认定其已经履行正当程序。
行政机关不能对正当程序原则选择性适用
纵观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正当程序原则可谓一个通行的程序规则。如上所述,在英国,正当程序原则包含于自然公正原则之中,是对公正行使权力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在美国,其宪法中明确载有“正当程序”条款。在法国,虽然宪法中未包含“正当程序”条款,但法院仍然逐渐发展出类似于英国自然公正原则的“防御权”,其主要内容包括:告知所有指控的内容、给予充分的时间准备防御(答辩)等,该原则也逐渐被法律所吸收。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1979年12月20日首次在案件中宣示正当行政程序乃宪法之要求。
可以说,正当程序原则是裁决争端的基本原则及最低的公正标准,其在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基本行政法律规范中均有体现。作为最基本的公正程序规则,只要成文法没有排除或另有特殊情形,行政机关都要遵守。即使法律中没有明确的程序规定,行政机关也不能认为自己不受程序限制,甚至连最基本的正当程序原则都可以不遵守。应该说,对于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行政机关没有自由裁量权。只是在法律未对正当程序原则设定具体的程序性规定时,行政机关可以就履行正当程序的具体方式作出选择。本案中,北京大学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在行使学位授予或撤销权时,亦应当遵守正当程序原则。即便相关法律、法规未对撤销学位的具体程序作出规定,其也应自觉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践行上述原则,以保证其决定程序的公正性。
法院如何处理——不同原则与价值观间的取舍
如果前两个问题还较多停留于理论上的说明,那么第三个问题则在具体适用上显得更加复杂。总的说来,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属于程序违法,对于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应当如何裁判,这取决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于行政程序违法的容忍度。
从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来看,对待行政程序违法的态度并不相同,而对于程序违法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不同原则与价值观之间的对立。一是法治国家原则与程序经济原则之间的对立,二是程序独立价值观与程序工具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对立。一个国家如何在两种对立的原则与价值观中作出抉择,这需要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结合具体国情来仔细斟酌。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制定行政程序法,立法者对于程序违法的态度,我们可从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加以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0条规定,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该法第74条规定,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基于此,我们可得出如下分析:第一,我国的成文法中并未规定程序补正制度,更不可能涉及在诉讼程序中如何对行政程序违法进行补正的问题。如果法官在个案中允许行政机关进行补正,则属于“判例造法”;第二,我国立法机关对于行政程序违法采取区分处理的方式和有限容忍的态度。原则上,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应当被撤销,这是法治国家原则和程序独立价值观的体现。作为例外情形,当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法院仅判决确认违法,但不予撤销,这是程序经济原则的体现;第三,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编著的权威读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一书第205页对行政诉讼法第74条作了如下解读:“……对于什么是程序轻微违法,各国有不同认识,如应当经过听证而未听证的程序违法,日本认为不属于程序轻微违法,而德国则规定为可以补正的程序轻微违法。我国立法和司法判例中将告知申辩权、听证等都作为重要程序,一旦违反,属于重大程序违法应予撤销的行政行为……”这一段文字也说明立法者在制定该条规定时已经充分考虑了程序违法的不同情形,进而在法治国家原则和程序经济原则之间作出平衡。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严格遵循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程序违法行政行为的相关规定,慎用违法程序补正制度,唯有此才能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和立法本意。
编者延伸:“终审胜诉”言之过早
在经历了充分的合议和讨论之后,北京一中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北京大学上诉,维持原判。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使得北京大学被判撤销决定。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该院同时驳回了于艳茹要求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法律效力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法院的判决一方面认定北大作出行政行为时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另一方面回避了撤销博士学位是否合法这一实体问题。社会上对于这个问题也曾有过争议,认为法院对于是否能够恢复学位这一关键问题是在逃避审判责任。对此,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邓学平的评论可以正听:
根据我国的《学位条例》,高校在授予、撤销学位时,属于法律授权的、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北大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的行为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但是,法院只能审查撤销学位的程序是否正当、法律依据是否明确,对于实体上是否应当授予或者撤销某人学位则法院没有审查权。学术问题不可诉,其实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司法惯例。其中的理由很简单。学术问题依赖于高度的专业判断,法官在此问题上并无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