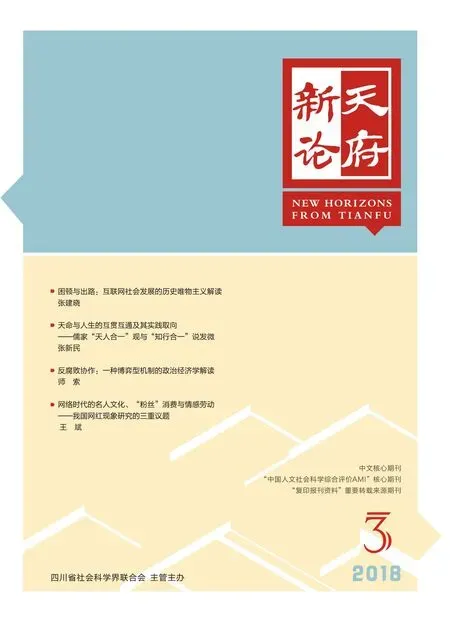网络时代的名人文化“、粉丝”消费与情感劳动
——我国网红现象研究的三重议题
2018-01-26王斌
王 斌
一、提出问题:网红现象背后的理论诉求
网红即网络红人,他们是由市场经济与互联网媒体共同催生的产物。网红并非中国的特有现象,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交媒体中同样活跃着大批网络红人。只不过,由于当前资金疯狂涌入本土互联网领域,我国少数的新兴网红正以一种 “搏出位”甚至是 “秀下限”的手段导入 “粉丝”流量。网红成名方式低俗化、网红言论行为失范化以及网红经济变现非法化,正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诸多的不良影响。
这种挑战社会道德的乱象也引发了中外媒体对于我国网红的集体关注。BBC新闻在2016年8月发表了 《网红:收入颇丰的中国线上明星》一文,该文对中国网红群体的构成、收入来源和职业属性做了相关报道。①G race Tsoi, “Wang Hong: China's Online Stars Making Real Cash”,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36802769, 2016-08-01.国内主流媒体也对网红现象进行了建设性的批判与评议。2016年4月,《人民日报》的 “人民时评”版块刊登了题为 《网红经济应有益于公序良俗》的文章。该文指出:网红不仅是商业模式,更是一类需要被引导和规范的社会文化现象。②韩立勇:《网红经济应有益于公序良俗》,《人民日报》2016年4月29日,第5版。而后,《光明日报》的 “光明时评”也发表了题为 《冷静看待 “网红”经济兴起》的评论,并称:网红不是坏事物,但对该群体 “出格”和 “踩线”的行为则必须加强监管。③陈方:《冷静看待 “网红”经济兴起》,《光明日报》2016年5月18日,第2版。
国内学界对网红同样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2016年第11期的 《中国青年研究》通过 “特别策划”栏目集中组稿,召集青年学者多维度讨论了我国网红现象。中国社会科学网也以 “网红现象剖析”为主题,将有关论述进行了重新集结与整合。大致来讲,学者们对网红的研究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在 “生命周期”的视角下梳理了我国网红的进化历程。通过划分互联网的文字时代、图文时代和宽频时代等不同阶段,相关论者归纳出了网红的多元类型及特征。④沈霄,等:《我国网红现象的发展历程、特征分析与治理对策》,《情报杂志》2016年第11期。.二是回答网红 “野蛮生长”的社会逻辑。研究显示,信息技术升级、利益回报率走高、文化消费风靡以及媒体把关弱化,都是催生网红的重要因素。⑤敖鹏:《网红为什么这样红?——基于网红现象的解读和思考》,《当代传播》2016年第4期。三是提出网红引发的社会问题及相应的对策措施。学者们普遍认为:网红在未来的发展必须摆脱其生产方式的简单、粗暴,只有完善法律环境、制度建设、专业分工和产业链条,才能保证网红群体为受众提供健康的内容与服务。⑥薛深,聂惠:《网红现象的生成逻辑及其引导》,《中州学刊》2017年第4期。
上述研究为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扎实的学理基础,但却未及时发展出能够整体解释中国网红现象的理论架构。这一方面造成了我们缺少对西方理论的批判反思,另一方面也使得研究者无法基于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对中国网红议题做到真正的 “鉴往知来”。因此,本文将以网络时代的名人文化、“粉丝”消费与情感劳动为框架,从理论脉络中分别梳理出网红的生成背景、运作目的及劳动体制,从而弥补当前理论研究的盲点,为建构网络社会治理的中国话语提供有益的思考。
二、名人文化:市场与媒介转型下的网红制造
网红是网络社会的线上名人,BBC新闻曾以 “cewebrity” (web celebrity的缩写)来指称网络红人。不过,在西方学界的惯用表达中,网红常被称作 “Internet/online/micro celebrity” 或 “cyberstar”。有论者认为,网红是指 “那些通过网络摄像头、视频、音频、博客和社交网站等新型在线技术来提高自身名气的网民”。⑦Alice E.Marwick, Status Update: Celebrity, Publicity, and Branding in the Social Media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115.胡泳等学者进一步指出,我国网红是随着互联网崛起的 “新名人”,他们构成了全球流行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⑧胡泳,张月朦:《网红的兴起及走向》,《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1期。是故,名人文化是我们讨论网红现象的基本前提。
事实上,名人文化研究在西方理论界已较为成熟,在学者们看来,名人是一种能够折射特定时期内公众价值取向的文化标识;⑨Kineta Hung, Kimmy W.Chan, Caleb H.Tse, “Assessing Celebrity Endorsement Effects in China: A Consumer-Celebrity Relat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2011, vol.51, no.4, pp.6-21.名人文化是关于名人何以被生产、名人会引发怎样的效应以及公众如何看待名人等现象的总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全球文化产业的形成以及大众媒体的普及,培育并开发名人的商业价值也就构成了名人文化的主要面相。可以说,现阶段的名人文化就是市场与媒体在全球化背景下联手制造的流行文化形态。
从我国历史来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内,名人主要是由领袖、英雄和模范构成,他们在 “总体性社会”中代表并维护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面向市场的名人文化几乎没有存在空间。20世纪90年代后期,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西方的商品与生活方式开始通过名人影像及其文化产品大量涌进中国。与此同时,各级政府逐步放宽了对文化娱乐业的管制,中国名人产生的渠道愈发多样、名人与市场关系更加紧密,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人文化初步形成。进入21世纪后,中国名人文化与全球接轨的速度明显提升。福布斯在2004年首次发布了中国名人榜,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我国名人参与国际品牌代言的案例也持续增多。①Louise Edwards, Elaine Jeffreys, “ Celebrity/China”, in Louise Edwards, Elaine Jeffreys ( eds.), Celebrity in China,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 p.13.
中国名人文化在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市场化特征,是现阶段网红诞生的前提条件。除此之外,我们还应看到,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同,中国名人文化的变迁也离不开媒体的影响。埃利斯·卡什莫尔(Ellis Cashmore)曾指出,当前名人文化的本质已经从 “以成就为基础的名声” (achievement-based fame)变成了 “以媒体为导向的名气”(media-driven renown)。②Ellis Cashmore, Celebrity/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7.换言之,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名人的成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他对社会有何实质性的贡献,而更因其 “长袖善舞”而能吸引媒体的关注。具体到我国现实来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8年前,我国所有的信息流动都被宣传部门统摄,报刊充当了革命的宣扬者、鼓动者和组织者。③陈秋心,胡泳:《宣传逻辑与市场逻辑——新媒体时代中国新闻伦理的 “两难格局”》,《二十一世纪》2016年第1期。这也就导致了那一阶段的中国名人主要是在生产与政治的笼罩下诞生。20世纪80年代以后,媒体才从 “宣传逻辑”向 “市场逻辑”转型,大众媒体得以普及,我国名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娱乐领域集中,大众媒介作为塑造名人的平台显示出了日益重要的功能。2005年,李宇春因获得350余万条短信投票在 “超级女声”节目中夺冠,随后更以 “亚洲英雄”的称号登上了同年度 《时代周刊》特刊封面。于是,在21世纪初的中国内地,大众媒介与移动通信技术共同造就了一位具有空前影响力的草根选秀名人。有论者就此现象提出:“中国的快速技术扩张为原先边缘化的个体创造了新形式的主体地位,同时也为他们赢得了在公共领域发声的机会。”④Louise Edwards, Elaine Jeffreys, “ Celebrity/China”, in Louise Edwards, Elaine Jeffreys ( eds.) , Celebrity in China,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 p.13.
其实,早在电视与非智能移动手机联手打造 “新星”之前,互联网就已开始推动网络名人的生产了。自1994年中国接入互联网以来,网络社区中的专业写手和意见领袖迅速成长,他们靠着不俗的文字才能获得网民的追捧,一跃而成了我国的初代网络红人。2005年前后,与李宇春同期成名的芙蓉姐姐,更以令人捧腹的造型与言论,成为首位拥有运作团队并深嵌进互联网产业的网红 “开山怪”。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伯茨 (I.D.Roberts)曾做出如下评价:芙蓉姐姐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互联网能让名人的产生更加民主,因为如果仅靠她现有的个人能力根本无法在中国主流媒体上现身;从这个层面上讲,互联网的确克服了传统媒体的狭隘属性,赋予了更多网民 “凡人的胜利”。⑤I.D.Roberts, “China Internet Celebrity: Furong Jiejie”, in Louise Edwards, Elaine Jeffreys (eds.), Celebrity in China,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35.
数字化测绘技术是对人工模拟测绘技术的升级,它利用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化测图软件大大提高了测绘工程测量水平和效率,而且代替了人工模拟测图技术,保证测量数据的可靠性。同时,数字化测绘技术使数据采集与数控绘图仪进行有效结合,并建立了数据采集、处理和自动测绘系统,实现了测量技术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发展。此外,数字化测绘技术对降低绘图的难度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为测量人员提供了诸多便利。
毋庸置疑,网红现象折射了名人文化和名人阶层在中国社会的 “平民转向”,⑥杨玲:《网红文化与网红经济》,《人民日报》2016年6月28日,第23版。这一转向的实质就是名人生产机制的民主化。马歇尔早在1997年就曾指出:由于个体的成名方式已不再完全仰仗传统的财富跟身份,成名的自致性为民主化时代的到来打开了机遇之门。⑦Marshall, P.David, Celebrity and Power: Fame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6.特纳对此补充道:由网络技术带来的新媒体普及,能让公众便利地推选自己心仪的偶像,名人的形成因之带有更浓厚的民意基础。①Graeme Turner, Understanding Celebrity, London: Sage, 2004, p.20.展开来讲,我国名人文化在信息时代的民主化变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网民只需点击“关注”就能瞬间成为 “粉丝”,创造与支持网红的方式日益智能化和便捷化;二是社交媒体令个人的才能和独特性能够被迅速发掘和推送。在网民的 “集体欢腾”之下,即便是一条段子或一段视频,都能引发难以估量的点击、转发、评论甚至是病毒式的 “围观”, “流量”成了网红的 “选票”。在线 “圈粉”的逻辑,更让新媒体跃迁成了制造名人的数字化机器。
但这种名人文化的民主化趋势也并非完全如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积极正面,尤其是在我国互联网领域法制建设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网络经济向线下市场的扩张必然会冲击现有规则和法律,“非法兴起”在部分网红的成名过程中显得较为严重。②胡凌:《“非法兴起”:理解中国互联网演进的一个视角》,《文化纵横》2016年第5期。比如,网络直播在我国内地发展的最初阶段,由于各部门缺少相应的监管细则,少数网红为得到更多的 “打赏”而罔顾法律,向公众直播低俗、色情和暴力等违禁内容,这最终促使了 《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的出台。故此,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名人文化 “民主化范式”,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红群体生产。如何正确处理名人文化中的市场与新媒体要素,完善审查技术及法律体系,为网民提供风清气正的线上名人塑造平台及展演空间,才是本土社会理论更新所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
三、“粉丝”消费:从消费名人到成为网红
如果说,名人文化的视角能让我们理解中国网红是如何被生产的;那么,我们也亟需从 “粉丝”研究的角度,回答网红与消费的关联。从某种程度上讲,名人与 “粉丝”是一组 “成对概念”(paired concept),随着名人越来越多地涉入消费领域,“粉丝”也被催化成了消费的主体。作为一个英文舶来词,“粉丝”是fans的音译,其拉丁词源为 “fanaticus”,意指神庙;在进入世俗社会后,该词逐渐淡化了宗教色彩,被用以描述 “流行文化中对某一人或事物的追随者、热爱者 (devotees)或崇拜者”③Ellis Cashmore, Celebrity/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79, p.22.。其实,网红在中国并不是新生事物,但该群体直到2016年才成为一个互联网经济的现象级话题。究其原因,这是由于媒介技术的升级疏通了网红吸引 “粉丝”的通道,电商、广告和内容付费等都离不开 “粉丝”的支持,网红潜在的商业价值由此被急速放大。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红的 “粉丝”总人数已达到4.7亿人,较之于2016年增长了20.6%。④艾瑞咨询:《2017年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2017年6月15日,http://www.iresearch.com.cn/report/3009.html。巨大的 “粉丝”基数推动了网红及相关产业的持续火热。
我国 “粉丝”数量的剧增,得益于商业资本与社交媒体的深度融合。一方面,新媒体让影像能够被无限地流通、重放、下载和复制,作为符号的名人随媒体而普遍融入到了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之中。⑤Su Holmes, Sean Redmond, Framing Celebrity: New Directions in Celebrity 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11.另一方面,当线上和线下空间都被各类名人符号占据之后,消费者或多或少地会被 “规训”成名人及其所代言商品的 “粉丝”。⑥Ellis Cashmore, Celebrity/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79, p.22.于是,名人与 “粉丝”结成了一个在物质与精神联系上都十分紧密的 “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当下,我国网红正逐渐从 “泛娱乐化”向各个细分的垂直化市场进军,美妆、运动、竞技、教育和旅游等领域的网红层出不穷。网红由此提升了 “粉丝”群体基于兴趣、猎奇或知识获取的付费意愿,并更精准、广泛地引领了 “粉丝”的消费行为。
“粉丝”购买网红提供的新型服务及产品的意愿增强,也折射了我国大众消费阶段的来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以及社会结构转型同步发生,市民消费迅速提档升级。我国现今已基本进入到了大众消费阶段,这意味着除了汽车和住房等大额消费占主导之外,一些新兴的消费形式也在快速发展。①李培林:《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4页。“粉丝”在直播平台中对网红的 “点亮”、“打赏”和 “送礼物”,就是这类新兴消费的集中表达。孙佳山认为,“粉丝”群体针对网红的新兴消费,在本质上是对真实的消费:“粉丝”们已逐渐厌倦那些 “云遮雾绕”的传统偶像,转而追捧能够陪伴自己并及时与之互动的网红。②孙佳山:《粉丝文化,涅槃还是沉沦?》,《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20日,第6版。
可以说,网红能多大程度地向网民 “袒露”自我,他就能多大范围地 “圈粉”和推动 “粉丝”的购买行为。循此理路,黛博拉·鲁特 (Deborah Root)才会批判性地指出:消费场域里的真实性是一个带有欺骗意味的概念,“这个词可以被操纵,用来说服人们相信:当他们购买商品后,能从中获得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③Deborah Root, Cannibal Culture: Art, Appropriation,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Differenc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p.78.。由此看来,“粉丝”们热衷消费的真实性要么是该群体一厢情愿的想象,要么是网红为迎合消费者而刻意制造出来的商品,唯一的真实或许只发生于 “粉丝”的消费行为之中。
不过,“粉丝”并不单是在消费网红。依托于社交媒体,“粉丝”自身也在消费过程中生产了优质内容,从而具备将自己转化为网红的潜能。具体来讲,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已使其不再满足于消费者的单次购买行为,它正利用新媒体加速促成消费者从 “跟随者” (followers)向 “粉丝消费者”(fan-consumers)升级。前者只是对商品感兴趣的普通消费者,其消费兴趣很容易被其他商品替代;与此相较,后者才是资本眼中最理想的受众。特别是在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后,出于对品牌及其代言人的热爱,“粉丝消费者”不仅会主动购买产品,更会在新媒体中发布商品的使用体验。换言之,作为“粉丝”的消费者能通过自身的社会网络而提高品牌的曝光度,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因其在社交媒体中的显著营销效果而被广告运营方选择为在线推广品牌的新晋网红,由此成为与资本合作的 “共同生产人” (co-producers)。④Henrik Linden, Sara Linden, Fans and Fan Cultur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10-11.从 “粉丝” 向网红的身份转变,说明了新媒体造就的 “产消者” (pro⁃sumer)能够在消费中完成内容生产。故此,网络社交媒体的兴起,令消费与生产、名人与 “粉丝”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新媒体也越来越真切地完成了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在1969年所做的预言—— “在未来,每个人都能有15分钟举世闻名的机会”。
四、情感劳动:生产网红的劳动体制
作为在社交媒体条件下吸引 “粉丝”消费的新名人,网红也需要付出相应的劳动才能获得流量和内容的最终变现。所以,探讨塑造网红的劳动体制就显得极为必要。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劳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也是人类改造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基础实践。劳动形态是随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丰富的。比如,伴随农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一、二产业的劳动岗位逐渐朝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倾斜,隶属于非物质劳动 (immaterial labor)的情感劳动 (affective labor)变得愈益重要。①Michael Hardt, “Affective Labor”, Boundary 2, 1999, Vol.26, No.2, pp.89-90.学界将情感劳动定义为:通过服从岗位固定的情感规则,达到商业目的或获取薪金报酬的工作形式。情感劳动不仅牵涉对情绪的调控,更对劳动者的形象呈现 (包括体重、妆发、仪态等)有着细致而微的规制。情感劳动在虚拟社会中更显突出,因为线上虚拟产品和劳动的非物质化程度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一时期,在线提供情感服务已经与代码、信息、图像等传统产品的供给同等重要了。②M ichael Hardt, “Foreword: What Affects Are Good For”, in Patricia Ticineto Clough, Jean Halley (eds.), 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zing the Socia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xii.邱林川早在2009年就提到,情感劳动在当代中国的信息服务业中已不可或缺,那些基于新型传播技术手段的 “心理咨询节目、网站上的软性色情内容、动漫配音、广告公关,都或多或少涉及情感劳动”。③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网络名人和内容付费都发生巨量增长的当下,我国学者却较少关注网红的情感劳动。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本土学者对后现代主义论述的过分倚重,而忽视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待网红的新型劳动。后现代理论的基本预设是认为高度发达的媒体令现实被符号取代,“做什么都不如获得公众的注视来得重要”;因此,包括网红在内的新名人根本不需要付出劳动和专业技能,他们仅凭借自己高度的可见性 (visibility)就能赚取收益。④Ellis Cashmore, Celebrity/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10-12.对符号的过度强调事实上遮蔽了网红劳动的存在价值,这并不利于我们揭开网红成名的真实因由。特别是在中国快速数字化的进程下,随着社交网络活跃用户数量不断攀升以及行业细分程度继续深化,网红越来越脱离业余状态而变成了一类 “职业”和 “产业”,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回归到劳动分析的坐标体系之中。
网红的情感劳动之所以重要,同样离不开 “粉丝”与资本的共同推动。一方面,“粉丝”群体的消费转型令网红必须提供相应的情感服务与产品。正如前文所述,“粉丝”们的集体兴奋已转向了对名人真实生活的消费,他们希望能与名人结成相互陪伴的关联。而且,这种需求在中国 “粉丝”社群里表现得尤为旺盛。张玮玉曾指出,中国的乡土性传统仍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粉丝”仍旧习惯于建构一种承载着社会情感的 “关系”,以期能与名人展开更加长久的、充满人情味的往来。⑤Zhang Weiyu, The Internet and New Social Formation in China: Fandom Publics in the Mak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122.由于网红与传统明星相较更具草根性,他们为维持和延长 “粉丝”的热情,就必须通过高强度的情感劳动来满足 “粉丝”对情感关系的诉求,这在主播类网红群体中表现得极其明显。
网红主播 “圈粉”的特质正在于其付出了高强度的、制造亲密关系的情感劳动,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认识。首先,网红会允许、鼓励 “粉丝”通过网络摄像头进入自己的私人空间,以此营造出 “面对面”的、亲昵的陪伴式交流环境。其次,网红会展现一些另类的才艺和私密的信息,并及时与消费能力较强的 “粉丝”展开深度互动,透过屏幕来完成 “粉丝”的要求与 “指令”。最后,网红还会放大自我情绪,他们在有 “粉丝”赠送礼物时会卖力地表演;而一旦 “粉丝”关注下降之后,则会表达出 “宝宝不开心”的郁闷。所以,为更加有效地制造在线的亲密,网红会将自我的私人空间、情绪和身体进行最大限度地公开化处理,从而形成与 “粉丝”长时间的、即时的互动,这也是网红与传统名人的情感劳动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
另一方面,资本打造 “情感化品牌”(emotional branding)的战略也需要网红的情感劳动与之配合。笔者在前文已指证了全球资本欲将消费者转变成 “粉丝”的企图,而构建情感化品牌正是实现这一企图的关键举措。区别于普通品牌,情感化品牌更加强调体验、信任与个性化服务,它试图与消费者建立起稳固的感性联系。①马格·戈拜:《情感化的品牌》,王毅、王梦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28-32页。网红打造情感化品牌的优势不仅在于其可以长期在线陪伴消费者,更因为他们能够通过风格化的情感劳动来俘获 “粉丝”。比如,网红往往通过段子、图片集、短视频和直播等方式,在社交平台上全面展现自己对品牌的理解与体验。这就使得网红创造的广告文案并不流于干瘪、简单的叙事,而是融合了网红的个人特质和情感渲染,以此诱导 “粉丝”购买产品。究其实质,网红的情感劳动依然折射了情感在数字时代的商品化趋势,“欢乐、微笑、轻松、关切,这些都可以通过表情、声音和动作,再通过符号化、数码化、网络化,最终变成商品”②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技水平、娱乐产业和信息化基础等 “社会技术”的催化下,劳动体制还会对劳动者的身体产生动态的干预和影响。③Elizabeth Wissinger, “Always on Display: Affective Production in the Modeling Industry”, in Patricia Ticineto Clough, Jean Halley(eds.), 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zing the Socia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31.换言之,线上的情感劳动不单对网红的情绪表达有具体规范,更会在线下对他们的身体造成显见的规制。以网红主播为例,为了能在网络镜头之下符合 “粉丝”在线凝视的审美,他们大都会精心准备妆发和衣着来展现 “身体资本”,并在 “粉丝”们的要求下对自我的身体呈现做进一步调整。而且,塑造网红的产业体系也决定了开发 “身体资本”是网红的入门工作。当前,孵化线上名人的 “网红学院”大都由以往的模特培训公司跨界而成,它们除了提供新媒体的运营技巧之外,更多的还是向网红学员传授化妆技巧、形体礼仪以及拍摄站位等内容。“年轻、貌美、身材好”似乎已成为网红的标配,“网红脸”的流行更反映出网络时代的情感劳动体制对劳动者自我的审美与身体形成的双重扭曲。
当然,并非所有网红的情感劳动都会被资本收编和异化。当市场在着手孵化网红的同时,我国政府及宣传部门也同样积极地塑造着传递正能量的主流网红。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就曾在人民网“地方留言板”中公开表示:“我们将带着为民意识上网,成为群众信赖的 ‘网红’……我们将带着情感意识上网,用真诚赢得网民的点赞”④乔新生:《领导干部要做群众信赖的 “网红”》,《学习月刊》2016年第17期。。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也在2016年启动了 “主流网红”的打造计划,试图推动知名记者从基于传统媒体的 “纸红”转型为全媒体的 “网红”,“以创新、活泼、互动的方式方法传播重要信息和主流价值”。⑤《南方 “主流网红” 是怎样打造的?》, 南方网, 2017年 2 月 17日, http://news.southcn.com/zhuanti/wanghong/topic/content/2017-02/17/content_165406542.htm。从这一层面上看,主流网红的情感劳动并不直接面向市场,而是更多地在维护和建设国家意识形态上发挥作用。如何将主流网红聚合为 “新媒体矩阵”,把他们的情感劳动升华为对网络社会的情感治理,也就成了本土社会理论建设必须直面的关键议题。
五、结论与讨论:面向中国网红现象的理论建构
本文从名人文化、粉丝消费和情感劳动的维度,对我国的网红现象进行了多层次的理论阐释。论者认为,作为中国新名人的网红并不完全是互联网传媒技术变革的产物,这一群体的诞生更寓于我国名人文化市场化和新媒体化的浪潮之中。新媒体背景下的中国名人文化不仅生产了网红,而且也令网红坐拥了数量庞大的 “粉丝”群体。当前,网红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虚构的真实性去诱导 “粉丝”进行消费,但 “粉丝”并非完全是被网红主宰的 “单向度的人”,他们亦能在消费过程中产出优质内容从而将自身转化为新生网红。因此,生产与消费、网红与 “粉丝”的区隔在Web2.0时代加速瓦解。不过,劳动的价值却并未在信息社会中被消解,情感劳动反而成为网红维系与 “粉丝”在线亲密的有效方式。一方面,情感劳动升级为网红获得 “粉丝”关注和打赏的一项技能;另一方面,网红的情感劳动也迎合了资本打造 “情感化品牌”的新兴战略。
长远来看,随着我国文化工业与互联网产业融合程度的加深,网红在社交媒体和内容付费兴起背景下仍将长期存在。网红 “圈粉”、 “吸金”与话题制造的能力已迅速赶超传统名人,其 “一呼百应”的偶像效应也正深刻地改变着我国信息社会中的权力格局。对这类互联网新名人的学术探讨,无疑将成为我国网络社会理论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社会理论虽能为我们提供分析问题的工具与视角,但却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网红现象。比如,由于在初期缺少相应的法律与监管,我国名人文化的 “平民转向”非但没有带来西方学者设想的社会良性运行;相反,本土网红的 “非法崛起”和 “野蛮生长”却显现出了名人文化变迁背后的种种危机。另外,西方学者对网红情感劳动的分析,也过于集中在市场和资本领域,无力解释我国主流网红利用情感劳动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维护作用。我们认为,网红这一称谓中的 “红”虽日渐剥离了革命化的色彩,被用以指代名人的市场号召力与商业价值,但发挥网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条红线的宣传和引领功能,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显重要。
因此,对网红现象乃至对我国网络社会的研究,都应主动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和分析。当前,不仅我国学者在积极利用马克思主义建设本土网络社会理论,西方互联网研究者同样地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就曾在其主编的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Marx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一书中提到:2008年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让西方理论界再次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互联网研究也需要重拾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理论的范式,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来去重新发现数字环境下的媒体、技术与传播。①Christian Fuchs, “Towards Marxian Internet Studies”, in Christian Fuchs, Vincent Mosco (eds.), Marx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Leiden: Brill, 2016, p.24.在此语境下,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网络社会研究,必然与本土社会具体的地区差异、城乡分隔和信息产业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无疑为网红现象的分析指明了继续深化的路径。
总之,为更加扎实地做好中国网红现象研究,我们一定要避免盲目套用西方社会理论,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导向,大力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大众化与时代化,发挥网红在促进网络社会治理精细化和专业化层面上的积极作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建立具有理论自信的中国话语,助推我国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