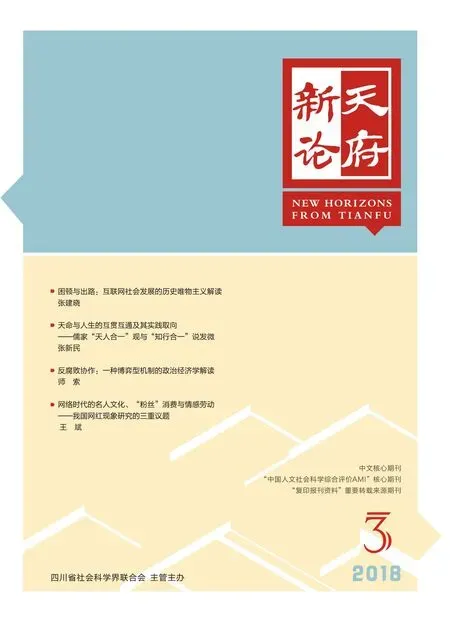为何资本积累先于原始积累?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性的双重批判
2018-01-26杨雨濠
杨雨濠
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1卷及其最为重要的草稿 《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下文简称 《1857—1858年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进行了讨论。其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这两部著作当中,对于本应该作为资本积累前提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被马克思放到了最后的部分,而作为原始积累结果的资本循环与资本积累过程的论述却被安排到了在先的章节。这样倒叙式的论证方式似乎并不利于读者直观地理解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但是马克思为什么还是选择了这样的编排顺序?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在《资本论的哲学》一书的开篇部分就对 《资本论》的逻辑起点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质疑了那种认为“从 ‘商品’出发是 《资本论》绝对要求”的看法,并提出了从历史和逻辑上都应该是 “一般生产先行”的观点。此外,广松涉甚至还认为 《资本论》 “可能还有第三个出发点”①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页。。可见,对 《资本论》逻辑顺序的理解,学界尚有不少争论。
无论是讨论 “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资本形态相互转化的资本循环过程,还是讨论资本家通过源源不断的榨取剩余价值而实现的资本大规模扩张的资本积累过程,都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逻辑起点的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它是怎样成为资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诞生,它又是如何开始运转的?只有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解答,马克思方能使其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立于坚实的基础之上。正如马克思本人在 《资本论》中对考察原始积累的重要性做出说明时所指出的:“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 ‘原始’积累 (亚当·斯密称为 ‘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0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十分清楚原始积累是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得以开启的理论原点,更是其资本理论的立论之基。诚然,如果将资本原始积累后于资本积累的编排顺序视作一种 “逻辑在先”的论证方式,即马克思在优先保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规律”这一核心命题被详尽论述之后才对资本起点进行补充交代,这样并无不可,自然也就不会存在本文所提出的问题。但是,笔者经过研究发现,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正义性时,运用资本积累在先的行文方式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对此进行阐释,将有助于我们厘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性进行批判的逻辑脉络,同时也将有助于我们对 “塔克—伍德”命题做出有效的回应。
一、正当性不等于正义性
罗伯特·塔克 (Robert C.Tucker)曾指出,克罗齐和列宁等人都同意 “马克思主义在道德上是空场”这一观点。然而塔克却认为,即使马克思本人由于没有考察至善本性而不能被称为传统意义的道德哲学家,那也不能证明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缺乏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实际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就是在 “道德基础上提出的道德主题和道德内容”②罗伯特·查尔斯·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高岸起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第69页,第69页。。拉斯基和林赛曾提出过这样一种被学界普遍接受的看法——马克思是怀着对公平正义的一腔热情对资本主义进行谴责的。塔克对此也进行了反驳。塔克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把共产主义社会想象成 “公平王国”。因此,塔克认为,马克思并没有从公平的角度去批判资本主义。相反,在马克思看来,拥有工资是工人的权利,占有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权利,两者无非都是同样的权利的不同表达方式,根本无所谓正义不正义。并且 “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其自己的分配方式和有其自己的公平方式,从某种其他的观点对其作出评价是毫无意义的”③罗伯特·查尔斯·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高岸起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第69页,第69页。。塔克就是这样从分配公平的角度得出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是罪恶的,但却不是不公平的”④罗伯特·查尔斯·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高岸起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第69页,第69页。观点。
艾伦·伍德 (Allen W.Wood)在塔克率先抛出的命题的基础上将其往前推进了一步。伍德认为“马克思没有详细讨论资本主义的不正义”。他试图从资本主义剥削、法权和生产方式三个层面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观点进行反驳。首先,伍德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主要是针对剥削制度进行的,而没有批评资本主义的正义性。其次,伍德强调,“正义”是一种与法律和权利相关的概念,由于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法权的范围有多大,所以他也就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是不是正义领域之外的东西。最后,对于这种法权观点和相应的正义概念,伍德还强调需要从社会生活及其他因素与二者的联系中去看待它们,并从 “现行的生产方式中把握它们的作用时,才能得到合理地理解”⑤艾伦·伍德:《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见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页,第27页,第27页。。和塔克一样,伍德也认为对资本主义正义性的评价应该依据其内在的生产方式为标准,而不是从 “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正义或权利标准”⑥艾伦·伍德:《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见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页,第27页,第27页。去斥责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伍德指出,这种做法和这些所谓的 “标准”都是错误的、缺乏根据的,因此都无法合理地适用于资本主义自身之上。此外,伍德还将生产方式联系于交易正义,认为这种正义的交易就是与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他引用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的一段论述解释了这一观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9页。这也正是伍德论证 “马克思为资本主义正义性辩护”的最直接证据之一。
塔克和伍德对于马克思正义性问题的讨论掀起了晚近半世纪以来学界持续不断的理论交锋。虽然塔克是该问题的发起者,但是他能拿出的直接论据却少之又少。“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6页,第226页。《资本论》中的这一论述成为他证明剥削并非不公平的关键证据。须强调的是,实际上,联系上下文,我们能看到,马克思的这段话欲论述的核心是劳动力如何成为商品,这属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塔克所引用的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当中,马克思还对工人的悲惨现状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工人不交出使用价值就得不到价值:“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6页,第226页。试想,工人只有卖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才能获得免于 “饥饿”的价值,这种所谓的 “不是不公平”的反义用法怎么可能是在肯定剥削的正义性?这种段落当然也就不能作为马克思认同资本主义正义性的直接证据了。
伍德和塔克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马克思的 “正义”概念与 “正当”概念。无论是塔克所谓的基于资本主义 “商品交换规律”的分配公平,还是伍德所谓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 “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正义,这些论证充其量只能算作对资本主义历史合理性的辩护。也就是说,他们的论证归根结底只是对资本主义历史正当性的论证。马克思从来没有否认过资本主义的历史正当性,还在 《共产党宣言》中毫不吝啬地赞赏资本主义制度在短短一百年中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任何时代还要多、还要大。但是,正当性绝不等于正义性,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却绝非正义的必然。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既是非正义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逻辑必然的非正义。
最后,我们再来审视塔克所提出的从分配公平的角度论证资本主义正义性的观点。无论是生产前的生产资料分配、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配,还是生产完成之后的价值分配或利润分配,全都是资本循环过程的派生环节,因此,这将涉及对资本积累过程的讨论范畴。而伍德强调通过对生产方式的追问,基于法权思想和交易正义证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的标准或原则评价其正义性都是无效的,从这点来看,伍德所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标准又将涉及对原始积累这一历史阶段的讨论。事实上,马克思的论证路径正是如此。但是马克思的目的和结论却与二者截然相反,马克思从资本积累和原始积累两个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并根据其论证的理论说服力合理地安排了资本积累与资本原始积累二者的先后顺序。
二、必然的非正义——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非正义实质的现实表现
(一)资本积累与原始积累的区别
马克思在撰写 《哲学贫困》的时候还未严格地将 “资本积累”与 “资本原始积累”进行区分。譬如,他曾在这一时期指出,“由于美洲大陆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进而促成了资本积累”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6页。。实际上,这里的 “资本积累”是 “资本原始积累”的意思。到了撰写 《1857—1858年手稿》时期,马克思就已经非常明确地区分使用这两组概念了,并且他还借用斯密的 “预先积累”作为原始积累的同义语使用。譬如,他指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而表现为预先积累并通过预先积累而支配劳动”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0页。。这里的 “预先积累”就是原始积累的意思。
资本积累指的是资本的现在进行时,主要是针对剩余价值不断地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而言的,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家通过剥削劳动获得了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后又继续为资本家榨取新的剩余价值,资本在这种循环运动中得到迅速累积和增值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说创造资本的剩余价值是以创造剩余劳动为基础的,那么资本作为资本来增加 (即积累……)则取决于这种剩余的一部分转化为新资本。”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4-435页,第451页。资本积累理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学说和剥削劳动理论。而资本的原始积累则截然不同,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资本的过去时,是资本主义得以可能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马克思使用了 “洪水期”、“形成史”和 “现代史”来形象地区别这两组概念:“准资本”和 “准资本家”②本文为了便于理解,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之前那些即将成为资本家的人称为 “准资本家”,将他们手中那些即将投入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财富和生产资料称为 “准资本”。从逻辑推演上来看,资本主义诞生前夕, “准资本家”凭借手中 “准资本”榨取到第一笔剩余价值,此时,他们的身份就跃变为资本家了,当然 “准资本”也就随之跃变成资本了。即将跃变成为资本和资本家的历史前提与历史条件是资本主义的 “洪水期”;而当“准资本”成为资本后,是资本的现代史;此前的时期则是资本的形成史。马克思指出,当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4-435页,第451页。资本的形成史时期实际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原始积累的核心是 “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
(二)资本主义非正义的实质在于虚幻 “公平”下自由的丧失
诚然,剩余价值学说和剥削理论是资本循环 (G—W—G或W—G—W④马克思指出,在货币资本的循环中,总流通的形式是:G—W—G(G—W.W—G);在生产资本的循环中,总流通的形式却是W—G—W(W—G.G—W),具体可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页。)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最重要的基石。诸多学者在为资本主义正义性辩护时,都将问题的矛头指向了马克思的经典剥削理论。他们或认为剥削理论与正义与否无关,只是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如前文提到的伍德就持有这种立场;或干脆就直接否认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如塔克和诺齐克就是这样做的。塔克以工人与资本家在商品交换规律下平等地获得权利来否认马克思用剥削理论证明了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诺齐克 (Robert Nozick)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否定得更为彻底,他指出,工人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原因在于 “工人没有掌握生产资料”⑤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03页。,这是马克思剥削理论得以成立的基础。因此,在诺齐克假设的乌托邦中,只要让工人掌握了足够的生产资料并自愿将劳动交付给资本家,那么剥削理论就会不攻自破,资本主义的正义性也就不证自明了。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没有看到这一问题背后的实质,那就是为什么剥削理论一旦成立,资本主义的正义性就可以被证伪?
刘佳好看的嘴巴马上就扁了,眼睛里水汪汪的,我跟我妈说,不许杀鸡吃。我妈一眼瞪过来,陈胖子,不杀鸡吃你怎么长得这么胖的。
究其根本,这是由于剥削理论背后呈现的是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丧失自由之后的被奴役状态。马克思语境中的不正义,实际上指的就是人类的不平等和不自由。但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家们却总是试图用所谓 “买卖的平等权利”、 “交易正义”等说法去遮掩资本主义褫夺人性和自由的真相。剥削的隐蔽性恰恰体现在当劳动力成了与商品一样可以自由买卖的东西之后,在交易过程中,工人完全丧失自由和自己劳动产品的事实却被看似 “自由公平”的市场交易原则重新贴上了 “自由平等”的标签。马克思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种 “虚幻公平”背后资本主义不正义的实质,他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的描述犀利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非正义性。马克思认为,在法律规定下自由平等的劳动者,“他要是把劳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他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变成奴隶,从商品所有者变成商品。”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5页,第349页。劳动者本来是自身劳动的自由的支配者,但在与资本家交易后却突然发现:“他不是 ‘自由的当事人’。”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5页,第349页。马克思通过剥削理论直指现象背后的本质:也许工人在出卖劳动力之前的一刹那还能像诺齐克所言 “可以是自愿的”,但是无论如何,从他出卖劳动力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再也不可能是自由的了,他的劳动及劳动产品都将归资本家所有。基于这样的情形,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不断榨取才得以可能,资本循环才能够开启,资本积累才如滚雪球般膨胀。这也正是资本主义最可怕、最无正义可言之处:每个个体在资本强大的逻辑之下,犹如被卷入了洪水和流沙之中,都不可能逃离资本的奴役。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问题成了一个核心命题,资本主义是一种必然的非正义,这种必然的非正义不因资本主义所制造的虚幻假象而被掩盖,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反而因为它的这种 “虚伪性”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三)准确界定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正义性时惯用的反讽风格
众所周知,马克思以犀利的言辞和尖锐的批判著称,并且他非常擅长运用反讽的文风,以此来达到最佳的批判效果。但是,众多为资本主义正义性辩护的学者们经常有意或无意地脱离文本语境去引用马克思的原话,断章取义或者歪曲原意。他们总是把马克思非常明显的正话反说的段落或者反问的文本解读成他们想要的样子。胡萨米 (Ziyad Husami)就曾据此批评塔克和伍德对马克思的诠释所“依托的那个段落是虚假的——它出现在马克思直白地讽刺资本主义的上下文中”①齐雅德·胡萨米:《马克思论分配正义》,见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页。。因此,准确界定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时常用的反讽语气和正话反说的风格对研究马克思的思想来讲是极为重要的。
伍德还认为马克思没有具体地表达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果真如此吗?让我们再看一段马克思正话反说的原话吧:“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他们还要得到一大笔利润……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61页。这难道真的是马克思在称赞资本主义的公平与正义吗?答案根本无需多言。而正是这样的语言,却也能够被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们解读成马克思是在为资本主义的正义性大唱赞歌,可见,他们的论证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此外,笔者经过研究还发现,在 《资本论》第一卷中,除脚注和对他人观点的引用之外,马克思直接对资本主义的公正和正义做出评价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个位置:其中之一就是上述引文的出处——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一章当中;而另一处则集中出现在对原始积累进行讨论的开篇部分,这也将是下文讨论的重心所在。
三、非正义的必然——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非正义实质的历史前提
(一)原始积累是对非剩余资本G0来源的讨论
望月清司指出,资本积累可以描述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非剩余资本G0经过 “第一循环”(或称 “本源循环”)后获得了剩余资本G1和剩余价值g1(也就是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赚取的 “第一桶金”);继续将 “第一桶金”投入再生产,又经 “第二循环” (或称 “本来循环”)、“第三循环”等多次循环后逐渐获得资本累加的过程③日本学界将资本的非剩余资本G0产生出第一个剩余价值g1的循环过程翻译为 “第一循环”或 “本源循环”,公式:G0—W—G′(G0+g1),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第一次资本循环过程;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基于G0与剩余价值g1再次获得剩余价值g2的循环过程译为 “第二循环”或 “本来循环”,公式:G′(G0+g1)—W—G” (G′+g2),第三、四等循环以此类推。详细参见望月清司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第六章。。其中,非剩余资本G0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之前的产物,资本原始积累的核心就是对非剩余资本G0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进行讨论。非剩余资本G0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可能的关键。马克思指出,“资本家要成为资本,就必须把通过他本人的劳动或通过其他方式 (只要不是通过已经存在的过去的雇佣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投入流通这样一个条件。”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1页,第452页。《1857—1858年手稿》中的这段话说明了三个关键点:第一,“资本”成为资本的史前时期一定是即将成为资本家 (“准资本家”)的人积累了一笔原始的财富G0;第二,G0与劳动和劳动创造的价值有关;第三,创造G0的劳动是资本家本人的或者是他人的(其他方式的)。
究竟G0是资本家本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还是他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如果是他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资本家又是如何将其占为己有的?这将涉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性的拷问。在 《1857—1858年手稿》对原始积累的讨论中,马克思一开始勉强接受了G0来自于国民经济学家们所称赞的 “准资本家们”的节俭美德的观点,然而他也指出,还有除本人劳动之外的其他方式。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指出其他方式指的是什么,但是此时的马克思确实尚不否定资本家本人的劳动是G0产生的原因之一。他指出:“如果说货币或自为存在的价值最初生成为资本时,要以资本家作为非资本家时所实现的一定积累——即使是靠节约他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和价值等等——为前提。”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1页,第452页。同时,为了考察原始积累的来源,马克思还试探性地研究了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直到撰写 《资本论》的时候,马克思才真正对原始积累的来源做出了明确的判断。
(二)暴力掠夺——资本主义非正义的原罪
与 《1857—1858年手稿》不同,马克思在 《资本论》的 《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直接对歌颂“原始积累是资本家勤俭美德所带来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流行的经济学观点认为:一种人(能成为资本家的富人精英)勤劳、聪明、节俭积累财富,另一种人 (大多数穷人)懒惰、无赖耗尽一切。马克思讽刺道: “梯也尔先生为了替所有权辩护……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 ‘劳动’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1页,第871页,第823页。“暴力”一词跃然纸上。马克思认为,给资本家带来 “第一桶金”的非剩余资本G0根本不是靠什么勤俭美德积攒的,而是靠暴力掠夺抢来的。这也是马克思为什么说资本从来到世间那一刻起,“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1页,第871页,第823页。的根本原因。
(三)非正义的必然——劳动领有规律的转变
马克思在 《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所有权在资本上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劳动产品的权利,进一步表现为所有权在资本上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控制,即转化为对工人劳动的所有权—— “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9页,第450页,第452页,第463页,第455页。。一方面,所有权转化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另一方面,所有权 “转化为把它本身的劳动的产品和它本身的劳动看作属于他人的价值的义务”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9页,第450页,第452页,第463页,第455页。。也就是说,“劳动 (Arbeits)”如果和 “所有权”是统一的,即 “我劳动我所有”[望月清司称之为 “第一条领有 (Aneignung)规律”③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8页。]的话,只有这条领有规律,资本主义形成史是不可能出现的。只有当“劳动”与 “所有权”分离时 (望月清司称为 “第二条领有规律”),资本主义的形成才得以可能。马克思还直接指明:“资产阶级所有权的这第二条规律是第一条规律 [即对自己劳动的产品拥有所有权的规律]转变来的。”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9页,第450页,第452页,第463页,第455页。
资产阶级的这种所有权一旦形成,将通过继承权等规则长久的存在下去。从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来看,私有制所有权从诞生开始,就不会因为某一两个资本家的存在或死亡而遭受影响,所以,原始积累中形成的这一关系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仍然适用。这也是为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在卖出劳动力的同时,其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也随之丧失了的根本原因所在。“第一条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同一性;第二条是劳动表现为被否定的所有权,或者说所有权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异己性的否定。”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9页,第450页,第452页,第463页,第455页。劳动领有规律的转变带来了 “不公平、不正义”的粉墨登场。从 “我劳动我所有”到 “我劳动我一无所有”,马克思就是这样完成了对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这种非正义性的揭露和批判。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当劳动者意识到产品是自己的劳动能力所制造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9页,第450页,第452页,第463页,第455页。。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辩护者们口中所谓 “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劳动者是自由的”这一谎言就这样被彻底戳破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实际上促使劳动者大量失去生产资料,成为只能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并逼迫他们不得不依附于资本家为生,同时,它还带来了社会的两极分化。⑦宋希仁:《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53页。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一方面生产着资本家,另一方面又为资本家源源不断地生产着廉价的工人阶层。可以说,劳动领有规律的转变带来了资本原始积累非正义的必然,而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非正义性又必然带来资本积累 (抑或说资本主义)的非正义。
四、为何资本积累先于原始积累
回到本文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何在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都采用了资本积累先于原始积累的逻辑顺序?
这是由于从资本主义内部逻辑上证明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远远比从资本主义历史起点上证明更具有理论说服力。因此,马克思把资本积累这一时间顺序上晚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放在了优先的论述位置上。
罗默 (John E.Roemer)的观点与马克思恰恰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不公正的来源应该追溯到资本主义生产之前的 “财产的初始分配的不平等”⑧约翰·E.罗默:《在自由中丧失》,段忠桥、刘磊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5页。上,是这种起初的不平等才导致了资本主义 “劳动和所得到的收入的不公正”,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初始分配不平等是资本主义非正义性的根源。因此,罗默详细地讨论了抢劫和掠夺,认为对原始积累的讨论更为重要。罗默或许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逻辑顺序问题。显然,马克思并不认为对资本原始积累论述的重要性超过了对资本积累的论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为如下两个命题:A.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因为资本逻辑自身就是最大的非正义 (资本积累过程中工人丧失自由和平等);B.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因为资本的诞生过程是非正义的 (原始积累过程中劳动者丧失劳动和劳动产品的所有权)。A命题和B命题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性批判的双重逻辑:二者既相互关联 (原始积累是起点,资本积累是结果)又彼此分离,它们呈现出两条截然不同的对资本非正义性论证的逻辑 (A命题与B命题各自独立成立)。然而,比较而言,马克思肯定清楚地意识到B命题的理论说服力远远小于A命题。
试想,如果资本主义的诞生过程是不正义的,而资本主义的展开逻辑却是正义的,那么,“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将能够充分弥补其诞生历史上犯下的 “原罪”,对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指控和批判都将会被大打折扣。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不公,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内部强大的非正义性逻辑造成的。资本积累过程的非正义性使得资本起源的干净与否变得不再重要,来源再 “干净”的资本只要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大染缸”之中,产生出来的注定只会是 “沾满血和肮脏东西”的剥削产物。所以,马克思在 《1857—1858年手稿》中甚至退一步选择去相信,即使资本的诞生过程 (原始积累)是干净的,最终也毫不影响他对资本主义正义性所做的批判。当然,对资本正义性的双重批判路径同时存在才能使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更为完整,才能使马克思的论证更具说服力。所以,马克思对两条批判路径同时兼顾,但是在论证的顺序上,他选择从资本积累开始,优先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上去揭示其非正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