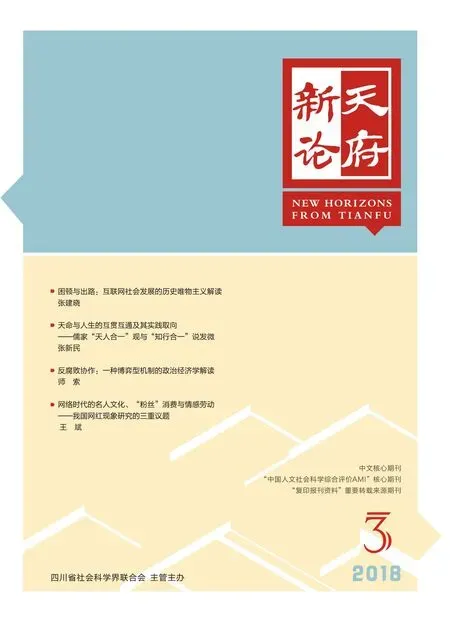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维度
2018-01-26祁松林
祁松林
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快速发展,诸如环境污染、化学废料和生态圈破坏等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各种生态主义理论与运动也随之兴起并形成了潮流。然而,生态主义者只看到了现代化工业大生产所引发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却并没有深入到对这一现象背后社会根源的认识。只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才能深刻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根源正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一、生态主义与生产问题
工业文明的进步带来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然而,人类在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福祉的同时,与自然的关系却日趋紧张,各种全球性生态问题日益凸显。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 《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引发了全美甚至全球范围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各种“生态保护运动”应运而生。20世纪70年代,“生态保护运动”从自发走向了自觉,诸多理论相继诞生,并且逐步系统化、多元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具有当代意义的环境理论与生态学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英国学者安德鲁·杜伯森在 《绿色政治思想》(1995年)一书中明确提出“生态主义”一词①参见布赖恩·巴克斯特:《生态主义导论》,曾建平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页。。此后,“生态主义”成为这一运动及其理论的标签,并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思潮活跃在世界舞台。
“生态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并不属于某个特定流派或社会团体,它甚至与各类较为激进的思潮广泛联姻,形成了诸如环境主义、动物权利论、生命中心论、生态中心论以及生态女权主义、生态后现代主义等不同分支。随着 “生态保护运动”风起云涌,生态主义理论的影响不断扩大,不但深入到当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理念与政党理论的建设领域,而且对全球发展模式与国际关系准则亦产生了日趋重要的影响。广义地说,生态主义社会思潮以重新思考人类现代工业文明以物质生产为主导的社会整体存在形态为主要诉求,包括对现存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清算与重估。生态主义者否定工业文明的进步,试图对人类社会做出新的规划与选择,追求一种自然与社会生态平衡的 “绿色社会”。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主义理论虽然各有侧重,但总体而言具有如下特征:第一,“自然为本”的整体主义原则。在生态主义者看来,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必须以整体、系统、关联与平衡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充分尊重自然生物的多样性与自然界的根本性地位。他们还将这种思考引入到社会生活领域,以此强调人类文化的多元性。第二,“万物一齐”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从 “自然为本”的总原则出发,生态主义者普遍认为,自然界是由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所有生命体构成的网络系统,这些生命体构成的各个子系统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互为联系、不可分割。如果割断了各系统之间的联系,使得某个子系统遭到破坏,那么,整体的平衡必将被打破并进而引发致命的生态危机。所以,必须坚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狂悖,以平等主义原则看待、处理自然界之生命万有。第三,“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念。在生态主义者看来,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生态危机的 “幽灵”正是人类试图以先进的生产力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 “心魔”所致。“生态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要求转变这种 “征服者”的思维与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他们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的伦理实体,以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作为价值诉求,并将之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总之,在生态主义者看来,生态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为生态主义者的典型代表,较为激进的 “深绿”思潮从生态主义伦理观出发,将自然与文明尖锐对立,在反对以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为特征的现代生产方式的前提下,把生态文明看作是人类生产实践之外的 “荒野”。在他们眼里,“自然”是 “一种未被污染的、未被人类之手接触过的、远离都市的东西。……是与由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人们对都市生活的厌倦以及渴望回归想象中的乡间田园生活的情感相联系在一起的”①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5页。。而现代工业文明 “具有急剧影响的生产技术已经取代了那些毁灭性较小的技术。环境危机是这个逆生态模式不断增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②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因此,他们主张 “自然价值论”与 “自然权利论”,要求放弃生产技术的发展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甚至全面否定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成就。
基于生态主义的以上认识,我们可以把生态问题聚焦于 “生产问题”之上。马克思说:“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页。”由此可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生产问题”占据着根本性地位,直接规定着 “现实的个人”及其 “现实生活过程”。而在生态主义者眼中,从事实层面来看,生态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现代化的工业大生产;从理论层面来看,生态问题凸显着人与自然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正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现实反映。
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人类历史活动的第一原则,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无感慨:“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第36页。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发展起来的工业文明给予了高度肯定,他们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第36页。。诚然,作为在工业文明时期形成的思想,正如王南湜教授指出的,“马克思的确继承了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支配自然这一核心内容”③王南湜:《马克思会如何回应鲍德里亚的批判?》,《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2期。,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一些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在否定现代工业文明时,也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思想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肯定 “支配自然”的物质生产运动,相信依靠生产技术的进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能够解决生态问题,具有鲜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特征。与此相应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同样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把劳动看作价值财富的源泉,却没有将自然界纳入人类的价值体系之中。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也涉及生态学要素,充其量只是一些简要的旁白。
毋庸置疑,生态主义思潮具有显著的后现代特征。后现代主义以非同一性、差异化原则内蕴着对现代化工业文明的解构。在后现代主义的生态学视域中,现代性的实质就是人类以技术手段征服自然、改造世界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理性主义传统。在这种传统下,人类主体性意识日益膨胀,进而完全把自然界当作可以量化、操作与征服的客观对象,突破种种自然极限,引发了一系列可能毁灭人类的生态危机。生态主义者同样秉持后现代主义的某些价值旨趣,他们一方面对现代工业文明进行了彻底批判,将生产技术的应用视为一切生态危机的根源;另一方面,他们也将人类的情感移植到自然领域,主张将自然纳入人类的伦理关怀,甚至将非理性的直觉体验运用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中,企图通过个人生活方式与思维观念的革新来化解生态危机。事实上,这是一种脱离人类历史的抽象自然观,正如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所批评的,只是 “诗意的神秘主义或东方宗教的方式”④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页。。
从这种抽象自然观出发,生态主义者仅仅将生态问题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笼统地批判一切现代化的物质生产,却并没有深入到 “生产问题”本身之中去考察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根源。事实上,在 《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早就发出过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把自然界当作人类活动的外在对象,而是将其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 “生产条件”。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自然界从来不在人类生产活动的目的之外,而是与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人类的历史活动。所以,对生态危机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就不能像生态主义者那样仅仅把目光投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而是要将理论的触角深入到人类社会本身。这就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批判。
二、两种 “生产”及其辨析
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肯定 “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并指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第162页,第161页,第163页,第516、519页,第531页,第519页,第519页,第519页,第162页,第162页,第238页。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以 “劳动”为中介阐述了人作为 “类存在物”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认为,作为人的 “类生活”的 “生产生活”就是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同时认为,“生产”并不是人的专利,动物也有 “生产”,但是 “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第162页,第161页,第163页,第516、519页,第531页,第519页,第519页,第519页,第162页,第162页,第238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第162页,第161页,第163页,第516、519页,第531页,第519页,第519页,第519页,第162页,第162页,第238页。。这个由人 “再生产”的 “自然界”,就是人类历史活动中的自然。一方面,“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第162页,第161页,第163页,第516、519页,第531页,第519页,第519页,第519页,第162页,第162页,第238页。另一方面,“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第162页,第161页,第163页,第516、519页,第531页,第519页,第519页,第519页,第162页,第162页,第238页。事实上,没有自然界,人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无法展开。自然界既是维持人类肉体存在的手段,又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对象。用康德的术语,这是一个 “自然因果性”领域,体现着人作为 “自然存在”的 “合规律性”的必然性特征。但是,人与自然界并非处在对立的两极,人类的任何生产活动只能在自然中展开,自然界既是人无机的身体,也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作品和现实——人的活动 “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自然界也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 “生产条件”。用康德的术语,这又是一个“自由因果性”领域,体现着人超越 “自然存在”的 “合目的性”的创造性活动。就此而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 “合规律性”与 “合目的性”的统一,既服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又具有主体自觉的创造性,这充分体现为人作为 “类存在物”的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表达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时郑重强调,“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这是一些 “现实的个人”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第162页,第161页,第163页,第516、519页,第531页,第519页,第519页,第519页,第162页,第162页,第238页。,这些 “现实的个人”的 “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第162页,第161页,第163页,第516、519页,第531页,第519页,第519页,第519页,第162页,第162页,第238页。“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第162页,第161页,第163页,第516、519页,第531页,第519页,第519页,第519页,第162页,第162页,第238页。由此可见,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物质生产是人类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首要标志。
在同一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指出,“现实的个人”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对于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而言,“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第162页,第161页,第163页,第516、519页,第531页,第519页,第519页,第519页,第162页,第162页,第238页。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基于现实生活的经验判断,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言,这一论断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在这里,“个人的肉体组织”意味着 “现实的个人”是作为 “自然存在”这个基本的理论前提,而 “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则揭示出 “现实的个人”这个 “自然存在”处在与 “其他自然”的关系之中。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现实的个人”既不是黑格尔哲学中抽象的 “意识主体”,也不是作为自然生命的单纯的生物个体,而是 “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第162页,第161页,第163页,第516、519页,第531页,第519页,第519页,第519页,第162页,第162页,第238页。。因此, “现实的个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 “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关于 “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就正是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马克思说,人是 “类存在物”,“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第162页,第161页,第163页,第516、519页,第531页,第519页,第519页,第519页,第162页,第162页,第238页。,而 “生产生活”就是人的 “类生活”。所以,作为人的 “类生活”的 “生产生活”的活动就是 “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因此,马克思又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第162页,第161页,第163页,第516、519页,第531页,第519页,第519页,第519页,第162页,第162页,第238页。。与人是 “类存在物”不同,动物只是作为 “种”的存在,只能按照物种自身的尺度生产,它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每个动物都必须独立生活和保卫自己”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第162页,第161页,第163页,第516、519页,第531页,第519页,第519页,第519页,第162页,第162页,第238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第162页,第161页,第163页,第516、519页,第531页,第519页,第519页,第519页,第162页,第162页,第238页。,它与自己的生命活动保持着直接的同一。动物作为 “种”的存在,就其自身的现实性而言,它的生命活动是个体性的生存。人是 “类存在物”,人的生命活动是 “类”的生活。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并且通过普遍的交易和交换相互为用,这就构成了人作为 “类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因此,作为人的 “类生活”的 “生产生活”的活动,就不仅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包括作为 “自然存在”的人本身的生产以及人作为 “类存在物”彼此之间关系的生产。 “关系的生产”让人类进入 “社会”层面。所以,人作为 “类存在物”的 “生产生活”及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既是生产 “自然”的活动也是生产 “社会”的活动,“自然”与 “社会”的二重性就统一在人的 “类活动”之中。
简而言之,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人类的历史就是 “现实的个人”的生产史,人作为 “类存在物”、“生产生活”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自然”从来不在人的历史之外,而是作为 “生产条件”与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统一于人类的历史活动之中。人类的生产史既体现着人作为有意识的 “类存在物”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又要服从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第159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应有之义,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 “生产问题”的真实内涵。
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2页,第47页,第47页,第51页。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就是直接性生产,而这一生产的直接性体现为人作为 “类存在物”、 “生产生活”的 “类活动”。马克思指出,资本的降临剥夺了“直接生产者”,在资本支配下的生产已不再是直接性生产,生产本身已经成了资本实现自身增值的手段。“直接生产者”作为生产主体的被剥夺首先表现为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分离、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在此情形下,生产活动对于劳动者而言,就不再是人作为 “类存在物”自由自觉的 “类活动”,而成了劳动者作为生产主体谋生的手段。这样,原本作为人的 “类生活”的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就成了外在的强制性劳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③《马 克思 恩格 斯文 集》 (第1卷) ,人 民出 版社 ,2009年, 第161页, 第159页。
资本以实现自身增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分离,使得劳动产品不再属于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而成了受资本逻辑支配的 “商品”,因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2页,第47页,第47页,第51页。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以 “商品”为逻辑起点,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我们知道,物的有用性使物具有使用价值,人类生产活动的劳动产品作为物,也因其有用性才能具有使用价值。作为人类生产活动的劳动产品,本来是 “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2页,第47页,第47页,第51页。,“就是使用价值”。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产品作为用于交换的商品,它就不仅具有使用价值,也具有了交换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有在通过交换实现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的过程中才体现出来。于是,商品的特性就表现为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二重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 “直接生产者被剥夺”,商品作为劳动产品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再是直接用来满足劳动主体需要的物,而是与生产活动一起沦为资本实现自身增值的手段,必须通过交换获取利润才能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商品的生产不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的生产,而是为了获得实现资本增值目的的交换价值的生产。因此,作为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也就丧失了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
通过对商品二重性的分析,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二重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商品使用价值自身独立性的丧失,使得商品作为劳动产品有用性的积极性意义一同消失,“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⑥《马克思 恩格斯文集 》(第5卷),人民 出版社,2009年 ,第872页,第47页,第47页,第51页。因此,资本的生产逻辑在让商品的使用价值丧失独立性的同时,也使得人类 “生产生活”的具体劳动丧失了独立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就集中表现为: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对商品交换价值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活动在生产过程中异化了自身,不再是为了满足生产主体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7页。
生产活动的异化即是劳动的异化。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自然界与劳动者作为生产条件与生产主体,伴随着劳动本身的异化而异化,全部退出了生产目的本身。因此,“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91页,第90、第91页。而资本必将试图 “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③总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只是为了让资本增值,不但自然界与劳动者一起沦为资本实现自身增值的手段,自然界本身也不可避免地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活动加以支配、征服的客观对象。这正是生态问题的真正根源,也是资本主义 “生产问题”的真实显现。
三、作为生态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
两种原则下 “生产问题”的剖析,为回应生态主义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片面批判以及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思想对立的理论局限提供了启示:人类的历史就是 “现实的个人”的生产史,而问题在于 “怎样生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同样指出,资本的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消除生态危机的最大障碍,而 “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④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III页。。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进一步考察生态主义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质,能够更为深入地领会马克思哲学作为生态世界观的真实意义。
如前所述,在生态主义者看来,生态危机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他们主张变革以物质生产为主导的现代工业社会。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主义理论自有其积极意义,他们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捕捉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内蕴的 “支配自然”的思想实质。但是,生态主义理论却不能反观自身,他们在以 “生产主义”为鹄的批判现代工业文明时,也暴露了自身理论的局限以及由此带来的自我矛盾。在生态主义者看来,生态问题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漠视与对象化征服,他们主张 “自然为本”,将自然界看作一个整体。但是,他们眼里的自然又往往是一个处在人类生产实践之外与人无关的 “荒野”。可以说,生态主义的思考仍然囿于西方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蕴含着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与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特征。
生态主义语境中的 “自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费尔巴哈 “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0页,第528页,第528页。保持着一致,这个自然界游离于人类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实践之外,用 “物” (自然)的外貌掩盖了个人意识的主观构造。在生态主义者眼里,自然界似乎从来都是 “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0页,第528页,第528页。。因而,他们的世界观止步于人类历史,总是会 “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0页,第528页,第528页。。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外在于人类生产实践、“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对于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而言却是一个 “不存在的自然界”。生态主义者混同了认识论与存在论,在认知个体的自我意识中构造了一个自然的概念,却并不能理解他们所直观到的感性世界以及身处其中的自然界正是人类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历史活动的产物。
当然,生态主义自然观有其特定的针对性,它发旨于工业化大生产对自然界的过度侵占。毋庸讳言,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史,这一历史进程不但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大量积累的历史,也是自然环境严重破坏、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的历史。生态主义者认为,正是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以一种征服者的姿势凌驾于自然之上,割裂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引发了一系列生态问题。因而,他们提倡以 “自然为本”,试图通过生态主义理论的传播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去构造一个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 “绿色社会”。诚然,他们用朴素的情怀批判着工业社会的生产现实,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担忧,不过,如前所述,由于生态主义理论缺乏历史的眼光,未能深入到对 “生产问题”本身的认识。所以,他们不能理解割裂人与自然统一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而并非作为普遍性的人类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活动。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基本形式,也是人作为自然存在本身的存在形式,人与自然的统一理应建立在人类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历史活动之上。因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人所面对的自然界正是人类生产活动中 “历史的自然”。正如英国学者乔纳森·休斯指出的:“人类对自然的改变并不必然与人类对自然的依赖相矛盾,并且实际上人类对自然的改变是社会的生态视角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张晓琼、侯晓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生态主义者主张 “自然为本”的整体性原则,但是,他们在批判现代工业文明割裂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却又将一个 “整体的自然”安置在了人类社会的彼岸,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未能突破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在生态主义者看来,现代工业文明奠基于人类以先进的生产力对自然界的征服。在这一进程中,人类的主体性意识日益膨胀,不断突破种种自然极限,破坏了自然界的整体平衡。生态主义者主张整体主义自然观,试图以此消解工业化大生产 “支配自然”的思想观念。生态主义者认为,这种 “支配自然”的观念植根于人类主义中心传统。按照人类主义中心传统,人是自然界中最高的目的,只有人的存在才是自然万物之中 “自在”的价值本身。因此,在这一观念主导下的生产活动理所当然地将自然界看作可以支配、征服的对象,以至于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但是,生态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时,却又用 “自然为本”的思维逻辑制造了新的对立。如刘福森教授所言:“走出了一个 ‘主体形而上学’的 ‘房间’,又进入了另一个‘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 ‘房间’。”②刘福森:《西方的 “生态伦理观”与 “形而上学困境”》,《哲学研究》2017年第1期。只是用一种 “自然为本”的形而上学反对 “人本主义”形而上学,依旧沉陷于本质主义的泥淖。
不可否认,面对生态危机的全球化蔓延,生态主义思潮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现实批判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但是,“反观20世纪的各种主流绿色生态理论和运动,它们不仅没有阻止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相反,生态危机却愈加严重,并已经威胁到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③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7年,第47页。究其根源,这正是因为生态主义者只看到了现代化工业大生产所引发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却并没有深入到对这一现象背后社会根源的认识。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所指出的,“每一个资本主义的机构和每一种资本主义的文化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赚钱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自我扩张系统,其目的是无限增长。”这就造成了资本自我扩张的无限性与自然本身的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而这一矛盾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④参见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活动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 “类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9页。。人在这一活动过程中,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第158页,第539页,第185页,第187页。“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第158页,第539页,第185页,第187页。,人类也就无法生存。所以,自然界必定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现实基础,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正如福斯特指出的,人类与地球在整个物质进化过程中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人类对自然的关系是自然历史现象和长期自然选择的过程③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历史唯物主义将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强调:“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第158页,第539页,第185页,第187页。就此而言,马克思哲学作为生态世界观的意义也正体现在人类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永恒追求之中,因为共产主义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定、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⑤《马 克思 恩格 斯文 集》 (第1卷) ,人 民出 版社 ,2009年, 第161页, 第158页 ,第539页 ,第185页, 第187页。。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之中,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从来不应以资本财富的积累与生产技术的发展为最终目的,而是始终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统一作为内在的目的本身,共产主义作为 “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第158页,第539页,第185页,第187页。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生态哲学理论基础的内涵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