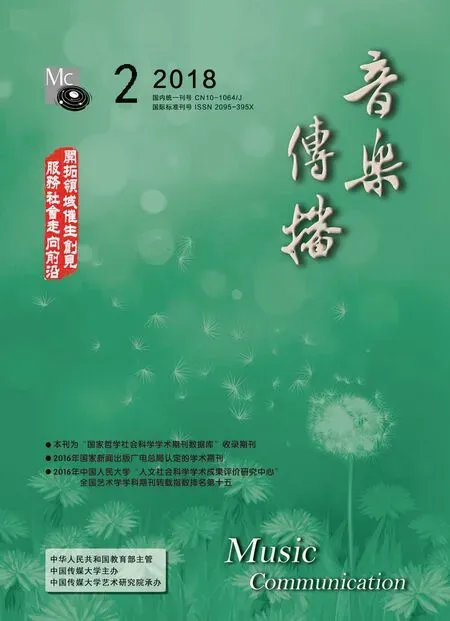古代国家制度视域下的“曲子”研究新路向
——郭威著《曲子的发生学意义》评述
2018-01-25常江涛
■常江涛
(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050024)
有关“曲子”之研究论题,音乐学界和文史学界一直以来多有探讨,其学术观点呈现出“百家争鸣”之态,如:音乐学界有杨荫浏民间“艺术歌曲”论、①详见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黄翔鹏“今之乐,犹古之乐”论、②详见黄翔鹏《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分期研究及有关新材料、新问题》,载《黄翔鹏文存》,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洛地“以文化乐”论、③详见洛地著《词乐曲唱》,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乔建中“曲牌细胞”论、④详见乔建中《曲牌论》,载乔建中著《土地与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冯光钰“曲牌音乐传播”论⑤详见冯光钰著《中国曲牌考》,安徽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等,文史学界(包括戏曲界、曲艺界)则有“音乐文学”之论域等,相关学术成果不可不谓之丰硕,为曲子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总体而言,学界既往研究大多将曲子视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讨论——音乐成了文学的附庸;抑或是关注曲子之音乐本体层面,以及与文学的关系,而对中国音乐文化自身的体系化、制度化的发展规律缺少深入辨析。在“文学主体”论的主流观点“冲刷”下,曲子研究难以获得真正客观的认知。由此,学界出现“曲子的生存环境如何?其音乐形态如何?如何表演和传承?这也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⑥王小盾《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载王小盾著《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56页。之呼声,也就不足为怪。
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郭威副研究员所著,2013年由我国台湾地区学生书局出版的《曲子的发生学意义》⑦郭威著《曲子的发生学意义》,学生书局2013年版。一书,在充分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采用发生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研究理念,从古代国家制度下的“乐籍体系”入手,并结合上下相通之“地方官府教坊司体系”,从整体化/体系化层面对曲子做了一番颇有新意的研究。作者针对诸多关键学术问题——曲子究竟有着怎样的演化体系;曲子、曲艺、戏曲等诸多音声技艺之间依托什么得以承传;乐籍制度下,全国究竟构建了怎样的用乐体系,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礼乐与俗乐依托什么进行了怎样的转化;经济、政治、交通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传播有着怎样的具体影响等等——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曲子研究的新路向。
一、从古代国家制度层面探究曲子的生成、创承与传播机制
“制度是一个社会诸种形态和谐有序的保障,音乐概不能外。所谓‘书同文、车同轨’的国家理念在历代帝王之中只有强化而非削弱,这必须有制度的保障。音乐本体的生成与发展亦为制度显现;无论是礼乐还是俗乐,同样离不开制度。”①项阳《由音乐历史分期引发的相关思考》,载《音乐研究》2009年第4期,第17页。制度,背后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大一统观念的外显。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得以有序延绵传承数千年,与相关的国家用乐制度(如礼乐制度、乐籍制度等)密切相关,这也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整体一致性下区域丰富性”情状的重要影响因素。
《曲子的发生学意义》一书,最大之特点在于从古代国家制度层面(乐籍制度、地方官府“教坊乐系”机构),对曲子的生成、创承及传播机制进行了深入辨析,这对于揭示曲子的内涵与外延、特点与流变,及其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一)官属女性乐籍群体之作用
作为国家法令强制设立的乐籍制度,自北魏被确立直至清雍正年间除籍前后,始终都是礼乐、俗乐类下的包括曲子在内的多种音声技艺形式的主要创承者,普遍服务于宫廷、王府、各级地方官府、卫所军旅之中,其数量庞大“何啻亿万”。此乃“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于其京师及其通都大邑,必有乐籍,论世者多忽而不察”。②龚自珍《京师乐籍说》,载《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7-118页。
学界对乐人、女妓群体的关注早已有之,且成果颇丰,诸如王国维《优语录》、王书奴《中国娼妓史》、毛水清《唐代乐人考述》、孙民纪《优伶考述》、曹明升《宋代歌妓略论》等,比比皆是。上述学术成果从不同角度对乐人,尤其是承载俗乐之女乐群体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为相关史料挖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其中也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是对乐人(女乐)群体之制度化、体系化存在和官方身份的认知,以及官属乐人群体对于含曲子在内的多种音声技艺形式的“创承”意义等问题,关注相对薄弱。正如作者所言:“关注乐人不等于囿于乐人;关注乐人承载不应该忽视其背后的制度层面;而关注制度,不应该将其简化为(或止步于)一种人员归属的考察,还应该到其运转机制对于音声技艺的深刻而具体的影响,应该注意到制度的历史延续性与区域中心文化积淀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对音声技艺创造、传承、传播的深远影响。”③郭威著《曲子的发生学意义》,学生书局2013年版,第365页。
因此,作者从社会学之职业身份角度对唐代“妓女”主体身份进行了辨析,认为其职业身份是官属乐人,主体身份是贱民,她们是国家意义层面上体系化、制度化的存在。从曲子生发来看,其乃是文人与女乐共同创造的结果,且在实际演出与传承阶段,则主要由女乐群体来完成,该群体的历史地位不言而喻,这就揭示出了曲子在发展演化过程中谁是主要的创造与承载者的问题。这种认知,较之前学界普遍共识——文人是曲子创造的主体有明显不同。
(二)地方官府“教坊乐系”之作用
乐籍体系既然是一种国家用乐制度,必然要有一套相应的组织机构予以承载和管理。这套相应的组织机构就是宫廷教坊及各级地方官府、王府、卫所教坊司机构,即“教坊乐系”。王昆吾曾指出:“曲子的大量产生,是教坊设立的结果,宫妓和教坊妓的歌唱,造成了隋至盛唐的曲子辞繁荣。”④王昆吾著《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3页。对此,作者进一步认为:“教坊是乐籍体系基础性的机构设置。隋唐以降,宫廷与分布于各地的教坊成为音声技艺能够上下相通、体系内传承、面向社会传播的重要结点和传输平台,其与轮值轮训相辅相成,是音声技艺发生、发展的基本动力与核心所在。”⑤《曲子的发生学意义》,第109页。在书中,作者对隋唐时期地方官府音乐机构之“府县教坊”、“府县散乐”、“诸州散乐”、“乐营”之全国体系化构建进行全面辨析,并对隋唐以降历代地方教坊发展做了系统梳理,如宋代“衙前乐营”,以及元明清三代地方“教坊司”等,从而展现出地方音乐机构一以贯之的延续性。
在遍布全国的各级地方官府教坊中,官属乐人群体一方面服务于官方日常“礼”与“俗”的用乐需求,另一方面还对外服务于大众群体,作为一种商业经营产业增加官方经济收入——其对外营业范围包括青楼楚馆、茶楼酒肆、勾栏瓦舍等等。作者认为从宫廷到宅邸再到地方(青楼楚馆、茶楼酒肆、勾栏瓦舍等)固定演出场合,既为乐人及其承载的音声技艺形式提供了广阔的演艺空间与平台,又为受众群体提供了一条充分接触以乐籍作为主体承载的多种音声技艺形式的重要途径。另外,通过轮值轮训、分配、配给、供应等体系内管理,以及脱籍乐人、非乐籍者之间的体系内外互动,包括曲子在内的多种音乐艺术形式得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流传。“乐籍体系……由宫廷与各级地方官方组织构成的,以轮值轮训制为核心动力,以国家制度为外部保障的音声技艺创承(创造、传承)与传播机制。”“在这种机制中,轮值轮训使得各种音声技艺得以在乐籍体系内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传轮;由宫廷、各级地方构成的‘音/用乐机构’体系,成为传输的平台和枢纽。”①《曲子的发生学意义》,第21-22页。
以往学界探讨乐人群体归属问题时,往往聚焦于宫廷层面,对其更为广泛存在的地方官府层面则鲜有关照,作者这种将研究触角伸向各级地方官府用乐机构的做法,极大扩展了对乐人群体归属的认知,同时也为从国家制度层面辨析曲子的传播提供了新视角。作者上述认知,对深入辨析遍布各地、各个乐种中大批具有相通一致性的曲牌、曲目之状况提供了新的阐释角度。
二、曲子内涵彰显“河流”、“细胞”与“母体”意义
长期以来,学界对曲子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反复进行探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曲子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到底处于何种地位?其又具有何种功能和意义呢?作者认为,曲子之最大特点在于其“母体”特性,这种母体性使其具有特殊意义。在文中,作者从学界对曲子的两个既有认知,即“河流”的意义和“细胞”的意义入手,对曲子之“母体”意义做了阐述。
首先,将传统音乐发展比作源远流长的“河流”,是学界的一种普遍共识,它展示出中国音乐历史的传承性和相通性。在作者眼中,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成分——曲子也同样具有这种“河流”属性。我国著名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认为,曲子是“被选择、推荐、加工”而“不同于一般的民歌”,它是“民歌通向高级艺术的桥梁”;曲子经“唱赚、诸宫调、南北曲、昆曲、器乐(如苏南十番鼓、西安鼓乐)”,而“在佛教和道教的宗教歌曲中间,也存有一些曲子的音调”。②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195、296页。对此,作者对杨先生的理念表示赞同,认为其不仅道出了曲子与曲艺、戏曲、器乐、宗教等音声技艺形式在体系内的密切关系,也说明了曲子“母体”意义的实质。其次,作者还抓住乔建中先生《曲牌论》中有关曲牌之“细胞”论的理念,③详见乔建中《曲牌论》,载乔建中著《土地与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并进一步提出“单个的曲子,既可以成为独立作品,又可以成为作品的段落,或变异为新形式的作品,由此,它既是独立的音声技艺,又是某种音声技艺的组成部分或变异基础。对于音声技艺的传承而言,这种灵活性的优势,使曲子成为各种音声技艺的‘母体’”。④《曲子的发生学意义》,第232页。作者认为曲子不仅在创作与发展的意义上为众多音声技艺提供给养,而且在传承、传播的意义上,也是众多音声技艺得以流传、延续、转化的基本途径。
那么,曲子之“母体”意义是如何生产的?其嬗变演化过程又是如何实现的?作者将其与乐籍制度相联系,进行详细论证辨析。作者一方面认为,“曲子由生成到‘大量汇集’需要制度的条件”,“乐籍体系由形成到成熟需要过程”,“文人创作与区域中心对‘曲子汇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⑤《曲子的发生学意义》,第228-229页。;另一方面,认为在“‘嬗变’过程中,曲子作为‘细胞’成为转化的载体和关键,因为它是最小单位又在宫调、曲式等方面具有创作上的拓展空间,而乐籍体系的统一规范,使音声技艺的承载者——乐人,以曲子的学习作为开始和学习基础,进而在创作中以曲子为基础进行创造”。⑥《曲子的发生学意义》,第235页。对于这个问题,项阳先生也曾有深刻认知:“我们看到,其后的发展更是清晰,即多种音声技艺形式(涵盖诸宫调、杂剧、院本、南戏、传奇、小唱乃至一些器乐化的作品)都是由曲子演化而来,可以说,曲子成为这些音声技艺形式的母体,直到明代所谓‘四大声腔’的戏曲也都是曲牌体的样式,所以文人士夫可在不同历史阶段参与到不同音声作品的创制之中,但承载(亦可称创承)这些曲子者为乐人是毫无疑问的现实存在。”⑦项阳《一本元代乐籍佼佼者的传书——关于夏庭芝的〈青楼集〉》,载《音乐研究》2010年第2期,第44页。
项阳先生和作者这种从乐籍体系角度认知曲子“母体”意义的方式,不仅重新诠释了学界“河流”、“细胞”之观念,而且更加深刻地揭示出曲子延绵不绝、不断嬗变演化的特征,以及与其他诸种音声技艺形式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这种研究理念和思路,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
三、曲子研究理念的转变:发生学,从“是什么”到“为什么”
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在学术研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面对相同的材料,或因采取不同的研究理念与方法,而导致最后的研究结果有着很大不同。学界既往曲子之研究,大多停留在“是什么”的阶段——借用“5W”之说,即其中的what(事件)、who(人物)、when(时间)、where(地点)等方面,而对于“为什么”,即why(原因、条件)则把握相对不足。笔者认为只有当把五个“W”,尤其是why(“为什么”)都辨析清楚之后,才能对曲子的内涵、外延,以及发展演化过程,即“how”有更为深刻的认知。而对于“为什么”的追问与探究,正是“发生学”所彰显出的重要学理特点。
人文学科视域下的发生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范式来源于自然科学,其最早可追溯至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的“发生认识论”。发生学不同于起源学,起源学探寻事物发生的过程,而发生学探讨事物发生的原因和条件。对于发生学给人文科学学术范式带来的转变,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副教授汪晓云将其体现归纳为“从静态的现象描述到动态的历史—发生学分析,从注重外在形式要素的研究到注重整体内容与功能的研究,从对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的研究到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的研究,从事件与现象的历史性研究到观念与认识的逻辑性研究”。发生学探究与认识相关的结构生成,不仅研究认识如何发生,也研究认识为何发生,因此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就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而言,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方法与途径。①参见汪晓云《人文科学发生学:意义、方法与问题》,载《光明日报》2005年1月11日。
在该著的研究中,作者采用发生学之研究理念,不是简单地以某个事件出现为标志,而是以此事件出现所需具备的条件为关注点。在书中,他以乐籍体系为主体的创承群体,以及该群体所依托的各级地方官府用乐机构为定位点,对曲子生发、演化、定型,以及传承、传播的一系列关键条件做了辨析。因此,笔者认为该著与前贤研究之最大不同,在于作者不是以探讨有关曲子之词曲关系、旋律宫调、乐人归属等“是什么”的问题为出发点,而是重点探寻曲子的生成机制,即“为什么”的问题。这是较既往研究在观念上的一种较大转变,而这种转变对揭示曲子的本质内涵,乃至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的动因都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发生学的运用并非局限在其具体的学科概念、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层面,而是将发生学的理念运用到实际研究中去,将学科研究作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来看待。同时,在采用发生学理念之时,作者还结合多学科的方法与研究成果,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对曲子之生成机制进行多角度交叉式的探究。对此,可以看到作者将研究理念、方法仅仅视为一种研究手段,而非研究之目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书名中注明“发生学”,但在书中却找不到任何有关发生学学科概念、方法、范畴等具体内容,但当通读全著后可以感受到曲子背后发生学意义的存在。笔者认为这是在学术研究中合理运用研究理念、方法的一种正确方式和有效途径。
余 论
或许囿于时间和篇幅所限,作者主要从历史文献层面对曲子进行把握,侧重自上而下之表述,相对来说,缺少一种自下而上、实地调查之逆向考察维度。黄翔鹏先生曾言“传统是一条河流”。这条河从远古走来,连绵不绝、传承有序地发展至今。所以,如果作者能够从当下活态遗存角度入手,通过对各地音声技艺形式,如戏曲、曲艺、器乐等进行田野调查来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将其与历史大传统相接通,那么不仅可为书中相关论点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还能形成作者自身有关曲子研究之更为完整的学理表述。
在《曲子的发生学意义》一书中,作者打破既往研究陈规,从发生学理念出发,以制度性传播为核心理念,紧紧抓住“乐籍制度”、“地方官方用乐机构的国家体系”这两个关键点,将曲子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研究得别有声色。从整体来看,作者所选曲子之论题,以小见大,折射出乐籍制度、地方官府用乐机构背后蕴含的古代国家制度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的“主脉性”影响,在学界研究中具有较强的创新性。诚如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淡江大学颜崑阳教授所评价:“本论文之史料基础厚实、文献梳理全面而深入、研究方法创新而精当、跨学科理论的应用也颇为多元而合宜……能突破前人成说而提出不少创新性的论见,的确是一本优质的学术论文。”②该评语见该著封皮。笔者认为该著作的研究视角与学术理念,对中国音乐文化整体研究皆有一定启示作用,值得学界认真思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