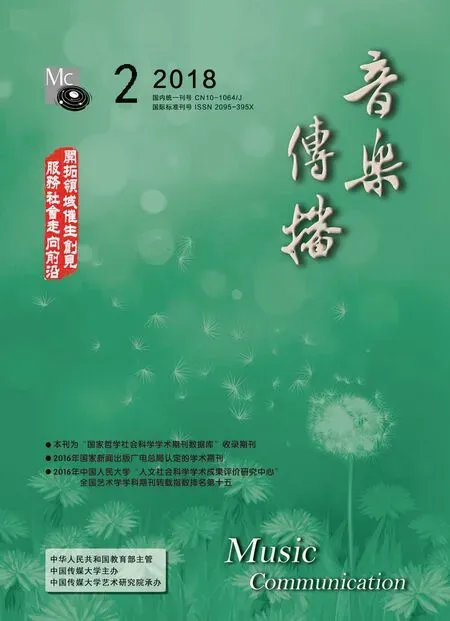对古筝艺术崇尚“逸”的探索
2018-01-25贾阳果
■贾阳果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州,510520)
中国各门类的传统文化艺术之间有着不少相通的属性,比如诗有隐逸诗,画有山水国墨,音有逸情之乐,这样,不管是诗歌、墨画还是音乐,均有隐逸风格的出现,而这应该均有一定的深层次因素使然。笔者认为,古筝的“逸情”之风,在客观上受到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隐逸文化的影响,在主观上也与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的自然情趣是分不开的。下文试结合中国文化史中的相关论述简析之。
一、中国古代隐逸文化对古筝音乐的影响
从字源上来看,“隐”有隐藏、隐蔽、隐居的意思,“逸”有逃跑、奔跑、释放、安闲、安逸、超越的意思,二者均有远避尘世、悄然生活之意。但是,“隐”强调的是从尘世中脱离出来,而“逸”更注重的是精神上的超越,以及追求闲适和自在的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二者结合使用时,指的多是隐居之高士。嵇康《述志诗》言:“严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①逯钦立编《先秦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9页。这句诗就说明了古代的逸士不仅在生活上追求脱离尘世,而且在精神上也要追求融入自然、超凡入圣的境界。隐逸现象有着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使得这一主题在整个中国的各个朝代都留下颇多印迹。
(一)古代隐逸文化的成因
具体来说,古之隐者文化,至少有以下三类原因。
主动远离官场而隐。在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专制社会的政权是威力十足的“尚方宝剑”,使许多人在权力的漩涡中迷失自我,并掉入政治泥沼之中。中国古代政权的频繁更迭,也与人对王权、皇权或各种官位的极度渴望有关。当然,古代政权并非一无是处,但更有其非常黑暗的一面。看透了当时社会黑暗面的一部分人,乐意远离政治,以免掉进政治深渊。中国最早的隐士、逸者,可追溯到三代时期的巢父、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他们历来被称为隐士的先驱。这些人以功名利禄为樊篱,视富贵为浮云,同时又具备道德、人品和才学方面的超绝素养,以出世修身为本务,故受到尧、舜、禹等人的敬佩和仰慕。后来,庄子的“无己”、“无功”、“无名”、“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生不仕,以快吾志焉”([汉]司马迁《史记》)的洒脱,魏晋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与玄远的清淡风气,谢灵运的纵情山水,陶渊明的田园归居,孟浩然的山水禅韵等,均已说明真的隐士一般不从政,视官场为人生羁绊,希望脱离功利纷争,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与山间日月为伴,与石上清泉为友,伴山乐水,仰望长空,低头浅酌,追求一份洒脱、一份逍遥、一种精神上的自由逸格。
仕途不畅而“心隐”。古代中国实现功名利禄的常规途径就是通过察举推荐,或经过层层的科举考试。察举制的不公自然无须多言,而即便是科举制也没能实现许多文人经世济民的抱负。就算克服了重重困难,身心疲惫地通过了马拉松般的考试,黑暗的官场也会把许多得到了功名的文人雅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正直公平者被妒忌、被陷害,一贬再贬甚至身陷冤狱也屡见不鲜。于是,不少人只好收敛自己的才气与能力,身在仕途,心却隐逸。古代有理想的文人喜欢把精神生活寄托在山水诗画、乐舞辞赋之中,所谓“弹琴吟唱,陶然自得”(《晋书·隐逸列传》),“心手相忘到混成,又非湘瑟与琴筝。秋来独坐水边石,固来水之弦上声?易度寸心闲有味,能谐群耳淡无情。夕阳会首山犹好,更起松风一段清。”(《宋书·隐逸列传》)他们通过弦上之音来体味自由之趣,身心相忘于秋水、夕阳和松风中。他们还会沉浸于道法与佛法之中,体会一种宁静、平和、淡雅的心境。如苏轼仕途不畅,先因“乌台诗案”下狱,差点掉了脑袋(因宋代有不杀士大夫之政策才得以活命),出狱后被贬到黄州当小官,心灰意冷,又屡贬至惠州、儋州,最后卒于周转奔波途中。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身心交瘁,他因此把心灵归隐至佛法禅韵。他被贬在杭州做官期间,常与圣山寺的僧侣佛印参禅悟佛,饮茶作诗为乐,并在寺中亲自操筝以抒怀。除此之外,还有“青莲居士”李白、“香山居士”白居易、“耐辱居士”司空图、“维摩诘居士”王维、“六一居士”欧阳修、“清真居士”周邦彦、“淮海居士”秦观、“稼轩居士”辛弃疾、“湛然居士”耶律楚材、“青藤居士”徐渭、“温陵居士”李贽、“六如居士”唐寅、“芹溪居士”曹雪芹、“柳泉居士”蒲松龄等,都以“居士”自居,系取在家修行之义。这不仅使这些文人墨客在心灵上受到抚慰,而且还使他们能够在艰难险阻中保持并追求一份闲逸之情。
清心修行而隐。道教和佛教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两块“净土”,同时为喜好修行之人提供了虔心的场所。道教在东汉末年形成,是一种多神宗教,它建立在我国古代道家思想理论的基础上,但也吸收神仙方术、民间鬼神崇拜观念和巫术活动的成分,主张潜心修道养生、清静无为,方可“得道成仙”、“长生不老”。许多名人如张三丰、邱处机、葛洪、孙思邈、吕洞宾、王重阳等都隐居山中的固定地点(具体有终南山、罗浮山、仙山、东海山等)修行,并创立各自的门派,在当时的民间影响很大。佛教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发源于古印度,东汉时期传入中国,提倡心性本净、见性成佛、众善奉行等,讲求的也是排除杂念,追求平和安宁的心境。自佛教流行中国以来,不少善男信女脱下战袍,披上佛袍,伴着青灯微光和木鱼声声,置身于深山寺庙中,虔诚地修行炼法。这些甘愿脱离世间纷扰的教徒,在宗教中消解自己、忘怀得失,也滋生了一种隐逸情调。
(二)古筝与古代隐逸文化
隐逸是一种在历史中积淀而成的文化现象,它促进了古筝艺术创作主题的多元化趋势,使古筝成为隐逸高士们抒情达意的文化载体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对古筝艺术的发展与辉煌起了重要作用。
古筝历来被认为是善于表达情感的乐器,其演奏音色的悲情性,使它有了“情筝”的称号。但是,隐逸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普遍存在,它使得古筝创作主题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除了纯粹表达悲情主题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追求自然之乐与高士胸怀之情的主题。晋代贾彬《筝赋》云:“钟子授筝,伯牙同节,唱《葛天》之高韵,赞《幽兰》与《白雪》。”钟子期是隐逸于山林的樵夫,却有着非同常人的音乐天赋,就贾彬《筝赋》中之言,恰恰可见隐逸文化对古筝的影响。古筝之音,可以表现幽兰之韵与白雪之调,可以畅弹隐逸之风。古筝同样也可以用来表达山水情结,如传统筝曲三个版本的《高山流水》,均取高山与流水意象,在描绘山水之形的同时,抒发了对自然之物的欣赏与热爱,还表达着追求高山般的巍峨与流水般的柔情的胸臆。
除此之外,古筝的创作主题还可以是花草之情,如《幽兰》、《采莲》、《风摆翠竹》、《出水莲》、《粉红莲》、《茉莉芬芳》、《莲花谣》、《梅花引》、《梅花三弄》等;另外,表现大自然怡景逸意的有《渔舟唱晚》、《平湖秋色》、《漓江春色》、《春江花月夜》、《明湖月歌》、《美丽的微山湖》等;传达逸士胸怀之情的有《平沙落雁》、《高山流水》、《梅花三弄》等。可以说,其中大部分都受到了隐逸文化的影响,由此在主题上表现出多元的趋势。这种创作主题的趋势也一直绵延至今,《南湖秋水》、《禅院钟声》和《铁马吟》等曲也在传达着现代人追求宁静心境,寻求内心平和的精神家园的愿望,当然也体现出了置身于闹市中的人正在享受着回归自然的心隐之趣。
在表达的主题多样化的同时,古筝更是逸士高人抒情达意的载体,它抒发着隐者心中的志趣、所追求的精神境界,疏导和宣泄着逸士心中的不快。比如,白居易仕途坎坷,命运多舛。他病重时甚爱抚筝,抚起来经常是“自弹自感暗低容”(《夜筝》)。明弘治年间的文学家、戏剧家康海,号“太白山人”,在音乐特别是筝和琵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其为人正直、敢说敢为,但仕途不通,罢官为民。在罢官的四十年间,他更加不羁,常以诗酒筝乐自乐。他在中秋佳节的夜晚,“凭鸾篱,搊银筝,半绮罗扇”(《仙吕·八声甘州·中秋》,《沜东乐府》卷二);或者在彭麓山房,“银筝叶,风箫闲,度遇景,当行乐,休教光阴虚度了”(《雁儿落带过得胜令·宴乐》,《沜东乐府》卷一);或为朋友祝寿,亲自弹筝,“银筝、玉笛、锦瑟、鸾箫,纤罗务谷相辉煌,般般妙。更绮筵翻新词,忧如日听《钓天乐》”(《南吕·一支花·寿北山先生》,《沜东乐府》卷二)。其好友兼亲家王九思所写的词句“沜东曲,锦筝拈”(《南吕·一支花》,《碧山乐府》卷一),恰恰说明康海创作散曲,用筝来弹奏,抒其逸气,逍遥自得,乐在其中。王九思与亲家同时因刘瑾案株连而被罢免,后也是游弄寄情于锦瑟筝乐之中:“世事且衔杯,勋业休看镜,桑榆易晚,龙虎难成。恋阙心,登山兴,醉倚东风栏干凭,笑英雄白发星星。且看这花间锦筝,樽前绣领,柳外春莺。”(《中吕·普天乐·对酒》,《碧山乐府》卷一)他还诉说着昔日的豪情壮志:“平生有志扶红日,叨列在青霄。营蝇止棘遭谗口,倦鸟投林觅旧巢。筝排雁,酒换貂,常寻几个布衣交。”(《南曲次韵》)物是人非事事休之后,他隐居于山林,寻几个布衣之交,一起喝酒弄筝度日。通过其词和曲,也可以看出锦瑟瑶筝带给这些古代失意士人的些许欢畅、惬意和风流。
二、人的尚“逸”心理基础对古筝音乐的影响
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之一。在法律的制约下和道德意识的敦促下,人可以获得一定的自由,不过,物质生活的羁绊也让心灵受到一些世俗的干扰。因此,追求自然和向往自由依然是人类内心最真实的渴求。筝乐在此也可扮演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角色。动听的筝韵引人入胜,可以使演奏者或聆听者如同置身于高山河川之中,品自然万物之景,享受其中的逸情之趣,以便更好地投入未来的工作。
(一)向往自然与洒脱是一种美的人生境界
被封建统治机器教条化后的儒家学说不能使古代的社会政治一直处于稳定和谐之中。战乱和虐政时常使古代中国民不聊生,即便不遇到这些情况,人性也常受制于某些严苛礼法之中,由此使身心感到不自由。因此,寻找能够让心灵处于放松、宁静的栖息中的道家思想便隐隐地有着市场。道家推崇人的自然本性,向往返璞归真,追求自然之美和天人合一的境界。“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从《老子》的“道法自然”开始,尊崇自然之心的情愫就没有消失过。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洒脱、逍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内篇·逍遥游》)的境界,追求“游乎尘垢之外”(《庄子·齐物论》)的豪迈态度和潇洒的精神意境,钟情“山林与,泉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庄子·知北游》)的浓浓的自然情趣,都散发着道家的风骨神韵。魏晋名士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在生活上放浪形骸、不拘一格,言如“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行如“扪虱而谈”,大讲玄学,清幽通脱。他们在精神上崇尚自然,超然物外,气质上率真任为,高雅脱俗,尽有仙气逸姿。比如陶渊明就有“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的高旷人格,他感悟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的纯真喜悦,在躬耕自持、淡泊闲适的田园生活中,捕捉到了人生逸趣。谢灵运“白云抱幽石,绿筿媚清涟”(《过始宁墅》)、“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的山水情韵,让读者也如同在游山遨水。至唐代,王维高居于“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的尘外之世,写道“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桃源行》),独享其纯净美好的精神家园;孟浩然沉浸于“逸气假毫翰,清风在竹林”(《洗然弟竹亭》)、“竹露闲夜滴,松风清昼吹”(《齿坐呈山南诸隐》)的高洁志趣中,追求着空灵和诗意的人格精神;浪漫风格明显的李白则道出了“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源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问答》)这样隐逸的心声。宋人也有不少继承了老庄的 超然情怀,比如周密写道:“信山阴、道上景多奇,仙翁幻吟壶。爱一丘一壑,一花一草,窈窕扶疏。染就春云五色,更种玉千株。咳唾骚香在,四壁骊珠。曲折冷红幽翠,涉流花涧净,步月堂虚。羡风流鱼鸟,来往贺家湖。认秦鬟,越妆窥镜,倚斜阳,人在会稽图。图多赏,池香洗砚,山秀藏书。”(《甘州·题疏寮园》)他在自然山水花草间寻求精神的解脱,享受平淡悠远的自然和艺术意趣。元代书画家杨维桢的诗画墨韵,也流露出除尘拔俗的逸气和对自然美的追求,比如:“千涧沄沄一径通,长松尽入白云中。征君更在山深处,满谷桃花烂漫红。”(《题山居图》)明代的李贽在世俗社会中不忘向往“尔但一开两朵,我来万水千山”(《焚书》)的情怀,而清代善画兰竹的“扬州八怪”,虽身在闹市,心却超然于物外,身不入深山,心却似高山流水。如郑板桥的“举世爱栽花,老夫只栽竹,霜雪满庭除,洒然照新绿。幽篁一夜雪,疏影失青绿,莫被风吹散,玲珑碎空玉”(《竹》)便写透了娴雅之心。
当代不少人每天奔波着似乎在与时间赛跑,其实他们大多也渴望着不被过于琐碎的事务所束缚。正如景观设计者不忘为我们带来某些大自然的宁静、恬淡与自由感一样,也有一部分人沉浸于音声诗画之中,体味着多元艺术带来的乐趣。
(二)古筝与尚“逸”情趣
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没有太多时间与自然合一,于是纷纷寻找适合寄托情愫的载体。古筝便是这样的载体之一。它音韵空灵、古雅、朴实、圆润、清逸,适合创作和演奏表达自然山水的曲风,爱好自然意象的审美者可以通过古筝音乐来欣赏其逸情之趣。“钟子授筝,伯牙同节,唱《葛天》之高韵,赞《幽兰》与《白雪》”(贾彬《筝赋》)传达着出尘脱俗的逸韵。当今古筝家王中山的作品《南湖秋水》意象取自李白的《陪族叔刑部侍郎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第二首中的“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借助南湖秋水的古意,表达创作者及现代人渴望暂避现实的纷扰,追求与自然相融、尽享自然所给予的生命的心境。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与水的意象符号,代表了文人雅士内心所追求的境界,故几于道。随手一捻《高山流水》,双手置于筝前,右手以浑厚、雄壮的八度附点音符奏出高山的巍峨之躯、谐和的五声音响,左手依着旋律吟揉相间、按滑相成,衬托出音符的柔媚色彩,呈现出流水般的温情。雄壮巍峨的高山伴着涓涓细流的旋律,似乎让人置身于天地万物尽收眼底之处。筝声引人入境,乐曲让人入神,分不清是坐于筝前还是高山流水之中。
此外,梅妻鹤子素来是隐士心神所往。梅花高雅,荷花高洁,均为君子之乐道,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也象征着君子之格。聆听筝曲《梅花三弄》,其舒缓典雅的旋律,形象地描绘了梅花不畏严寒、在风霜中俨然屹立的可贵形象。爱梅者可以在筝乐中领悟到梅花“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唐]崔道融《梅花》)的袭人神韵,可以感受古人“茅舍疏篱,半飘残雪,斜卧低枝。可更相宜,烟笼修竹,月在寒溪”([明]杨无咎《柳梢春》),不为世俗所羁绊、宁与残梅为伍追求淡泊的情思。一曲《出水莲》,淡雅古朴的筝韵刻画出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宋]周敦颐《爱莲说》)的清丽形象。审美者静听时,随着音韵的流动,缓缓进入音乐之中,似乎可观赏到“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唐]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之风姿,令心神浸入“了无一点尘凡气”([宋]蔡伸《踏莎行》)的逸境之中。可以说,筝音乐对尚“逸”的表现,今后仍大有探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