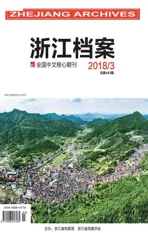农民工身份认同中档案的作用
2018-01-24陈玉杰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陈玉杰/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流动性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人口流动和身份变迁成为常态,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属于哪个群体”的问题逐渐成为困扰流动人群的难题,社会对于身份认同的关注日益增加、研究也日益深入。作为流动人口的主力军,农民工经历了第一代、第二代和“新生代”的变迁过程,他们在涌入城市务工谋生的过程中,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并得到社会认同。然而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程度存在差异等原因,农民工处于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受到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双重制度性歧视和排斥,因此他们渴望得到身份认同,寻求自我归属。而 “档案,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应称之为‘文件’,在建构社会历史、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方面具有很大作用,因为从中我们可以确定如何作为个体、群体、公民”[1]。笔者通过对身份认同进行分析,发现档案可以凭借其凭证属性、记忆属性和文化属性,帮助农民工实现个体身份认同、社会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从而促进农民工提高自我认知、提升文化水平,实现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并融入城市之中。
1 档案与农民工身份认同
1.1 农民工档案
“农民工档案”是反映农民工个人的自然状况及其社会活动、体现其历史和记忆的各种形式的原始记录。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农民工身份资历、社会关系、成长经历、住址和联络方式、特长和求职意愿、计生状况、和农民工参与社会活动产生的其他档案资料”[2]。
目前我国农民工档案信息资源建设还处于探索的阶段。有些地方要求用工单位为农民工建立个人档案,有些地方为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员建立了反映其基本状况的专题数据库,有些地方还建立了小型的农民工档案馆或博物馆,这些尝试和探索维护了转型期集体记忆的完整性,有利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10月25日哈尔滨市道里区首建农民工档案馆,为1.4万农村劳动力建立了个人档案;紧接着天津市为320万农民工建立健康档案和各类信用档案;重庆市渝中区为该区农民工建立了电子档案;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为农民工建立了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建立了动态管理机制等”[3]。此外,北京建立了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四川建立了金堂县中国农民工博物馆,这些都彰显了社会对农民工群体及其形成的档案的关注与重视。
1.2 农民工身份认同
本文所指的“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4];本文认为“农民工身份认同”可以定义为农民在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中产生对自我身份、情感和文化的认知,以及群体的归属需求和对未来的期望。现实当中,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城市的影响更深,因而更渴望融入城市,摆脱农村人的身份,有学者称之为“去农村化”。然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目前身份归属和将来身体归属的双重困境,他们的身份认同现状令人担忧。深圳市总工会2010年主持的一项“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显示,深圳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没有务农经历,他们一年难得回一趟农村,普遍渴望城市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然而现实的困境是,他们往往农村回不去、城市又难以融入,不少人、不少外来务工群体都存在身份认同危机[5]。因此,对农民工身份认同进行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3 农民工档案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关系
身份认同不仅需要人主观意识上的认同,还需要客观上显示人们身份的特征或者符号(比如身份证、护照等)加以佐证。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总结了档案的四个范式:证据、记忆、认同和社区,他指出当前档案处于第三个范式——认同当中,“档案从支撑学术精英的文化遗产转变为服务于认同和正义的社会资源”[6],因此档案作为一种固化的叙事材料,可以用来建构身份认同。档案对身份认同的作用具体表现在:第一,档案具有凭证属性,可以为身份认同提供合法性证明,凝固和佐证身份认同;第二,档案具有记忆属性,“是集体记忆的重要承载形式,能够有效参与身份认同的建构、重构和强化”[7];第三,档案具有文化属性,可以为实现身份认同提供文化支撑和文化自信心;第四,档案并不是为人们实现身份认同而生的,档案可以通过其凭证属性、记忆属性和文化属性综合作用于身份认同。
2 档案在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作用
2.1 档案的凭证属性有助于判定农民工的“身份”
对个体身份的认同有助于个体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个体通过对自我特点进行描述,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独特性,从而获得对自我及自我价值的认知。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一词,标志着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特点鲜明的群体已被写入历史。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并得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较为清晰,且大多从职业视角认识自己的身份,68.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工人”[8]的结论。
笔者认为,实现农民工个体身份认同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让他们拥有职业自豪感,这种职业自豪感可以通过评价职业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中的价值来获得。而对职业价值的认定和评价,则可以通过档案这种社会发展的历史记录来获取。农民工档案记录了农民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是农民工参与城市建设、推动社会发展的真凭实据,是农民工了解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历史资料。通过查阅农民工档案,农民工可以了解他们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白城市进步离不开他们、城市发展需要他们,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小人物”,应该为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价值感到自豪。
2.2 档案的记忆属性有利于激发农民工的群体归属感
根据Tajfel(1978)的社会认同理论,“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9],由此看来,想要获得社会身份认同,群体归属感和价值感是必要因素。而集体记忆作为特定群体共享的经验积累和情感依附,正是群体归属感和价值感之所在。又因“档案不仅以身份证件这种明显的方式提供组织和个人的身份凭证,还借助其蕴藏的信息提供某个时刻或整个时期的集体记忆、群体故事及个人身份,帮助社会与其遗产建立联系,帮助人们保护自身的权利”[10],因此可以认为,档案通过对集体记忆进行建构,使群体获得社会身份认同。
具体来说,档案、集体记忆与社会身份认同的相互关系如下。首先,档案是集体记忆的重要承载形式。根据“档案记忆观”,我们可以认为农民工档案拥有记忆属性,记录着农民工生产生活的全部。农民工档案与农民工集体记忆的互动关系体现如下:一方面,农民工档案是农民工集体记忆的载体,用以寻找遗失的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的事实真相,并以一种固化的叙事载体的形式,使农民工记忆得以流传;另一方面,农民工档案是农民工记忆的“触媒”,可以构建、重构和强化农民工记忆。其次,集体记忆的建构能够促进群体的社会身份认同。社会学家卡斯特尔认为:“所有的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与象征性内容、集体记忆、个人幻觉、制度、权力机器等有关。”[11]农民工记忆的建构,有利于农民工形成群体归属感,同时在明白自己的“身份”后,能够意识到自身的独特性及其在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最后,根据前文提到的档案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农民工档案通过对农民工记忆进行构建、重构和强化,间接地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身份认同。
2.3 档案的文化属性有益于提高农民工的文化自信心
身份认同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需要考虑到社会文化背景对身份认同产生的影响。群体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其发展有利于群体成员形成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从而提高群体的社会地位。其中“文化认同既存在于个体层面,也存在于社会层面,是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12]。
就农民工而言,农民工文化的发展是对个体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的巩固与加强,能够增强其文化自信心、增加凝聚力并提高社会地位,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之中,实现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档案作为文化载体,承担着积累和传播文化的任务。农民工档案记录着农民工的历史,是农民工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传播农民工文化的基础。通过对农民工档案进行挖掘、整理和展出,一方面可以加深农民工对自身文化的认识、提高其文化自信心,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更新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认识,使农民工群体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与尊重。
3 档案在农民工身份认同中的实现路径
3.1 建立和完善农民工档案资源体系,使农民工身份认同有据可依
丰富农民工档案资源体系是实现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基础,直接影响到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工档案资源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农民工档案的建档主体、归属部门、管理现状等方面,可见农民工档案资源建设存在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当前建立与完善农民工档案资源体系势在必行,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实现和农民工权益的保障,也是落实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由于农民工群体存在特殊性,其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存在很多困难,各地农民工立档单位应以农民工的需求为导向,创新收集方式、扩大收集范围、优化管理流程、拓宽利用渠道,建立内容广泛、合理系统的农民工档案资源体系。
3.2 优化农民工档案管理体系,保障农民工档案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强、工作变动频繁,为保证农民工档案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需要优化农民工档案管理体系,规范农民工档案管理工作。优化农民工档案管理体系可采取以下措施:首先,需要完善农民工档案相关管理法规,确定农民工档案的建档主体、建档范围、标准格式等问题,确保档案的完整性;其次,需要健全农民工档案监管体系,提高各部门对农民工档案的重视;最后,需要加快农民工档案信息化进程,特别要实现劳务输出地和劳务输入地档案部门的合作,保障农民工档案的真实性。
3.3 创新农民工档案利用方式,促进农民工文化的发展
农民工群体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往往不重视自身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而是更关注如何获得经济来源,因此开展农民工档案的利用工作不能完全采用传统的工作方式,需要根据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进行开发利用。建立农民工博物馆,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创新农民工档案的方式。如北京皮村打工艺术博物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农民工档案馆,它以“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为展览专题,从打工历史、打工姐妹、留守儿童等多个方面展示了30年来农民工生活的变化。“打工者艺术博物馆是一种自发兴起的文化,也是一种能动性的文化。它的意义就在于自己来记录自己的历史,自己从这种历史中寻找、发现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建立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13]。建立农民工博物馆进一步拉近了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距离,有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
农民工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逐步完成身份制度的融入、经济活动的融入、社会生活方式的融入、语言与公共媒体的融入、社会心理融入。尽管档案在农民工身份认同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能够从其凭证属性、记忆属性和文化属性方面促进农民工群体的自我肯定和发展,但农民工群体的认同更需要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支持,使农民工在户籍制度、保障制度、司法救济制度方面得到保障,实现真正的社会融入。
注释与参考文献:
[1]Schwartz,J.M,and T.Cook.“Archives, Records,and Power: The Making of Modern Memory”. Archival Science,2002(2):1-19.
[2]张予军.对建立农民工档案的几点思考[J].档案管理,2011(02):85-87.
[3]李忠香.建立农民工档案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J].兰台世界,2011(02):53-54.
[4]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02):21-27.
[5]深圳市总工会.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EB/OL].[2010-7-15].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5-07/07/c_134387648.htm.
[6]T.Cook.Evidence, memory, identity, and community:four shifting archival paradigms.Archival Science, 2013(2):95-120.
[7]冯惠玲.当代身份认同中的档案价值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01):96-103.
[8]刘晓丽.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3(01):45-50.
[9]Tajfel H.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hapters1—3. London: Academic Press,1978.
[10]杜梅.2012年国际档案大会:新环境新变化[J].中国档案,2011(04):85.
[11]曼纽尔·卡斯特尔.认同的力量[M].第2版,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2]杨宜音.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演进与创新为例.张存武主编: 海外华族研究论集,第三卷.文化、教育与认同,台北:华侨协会总会出版社,2002: 407-420.
[13]王亚楠.首个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破茧”.[EB/OL]. [2008-10-07]http://firm.workercn.cn/c/2008/10/07/34 9f6c84d1924a5eb99a26517553a8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