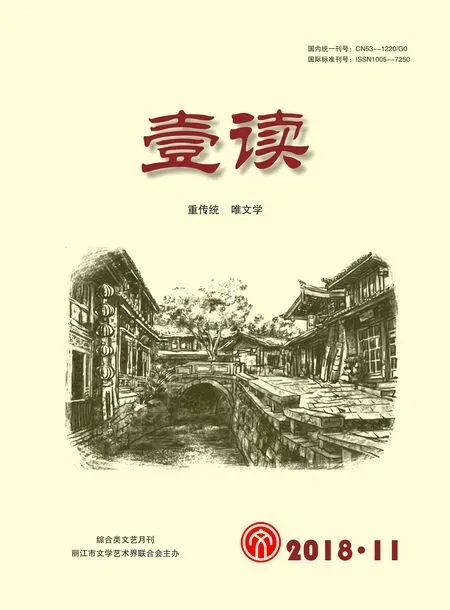群山里的晚霞(组诗)
2018-01-24阿卓日古
阿卓日古
打乱
昨天和同事走在路上
没有理由的走在路上
孩子在哭
路人诡异的看着我们
也许像一阵风
刮过厅堂
打乱了
某个中午
抱着木盒的女人
打乱了
那个抱着木盒的下午
打乱了很多人的木盒
那里装满寺庙里的经文
荒山
荒山
余光里的最后一点幻想
那个猎人走出森林的最后
脚步
多少人也模仿不来
最后的背影
消失的村口
没有人留意
他的消失
就像很多人
没留意,村东头的苏尼
是如何回答神灵的提问的
左手
左手什么也拉不住
凋落的影子
漆黑一片
左手,被什么东西牵了一下
也许是落叶
也许是荒草
也许是指路经里未诵完的部分
也许什么也不是
左手,从身体的另一半
脱缰而出
很多人误以为
要去拉住什么
平静
平静,野草已经长到了额头
很快,几只
候鸟穿过
土堆,来到人间
没有谷子,也没有
鼓胀的草垛
没有吹口哨的年轻人
也没有裂骨测算出的吉凶
平静
这个地方,什么也没有
只有不会张口的
鸟巢
和来不及开口的人
回声
跟着走
命里注定的东西
我们都会一一遇见
有时候穿着宽松的上衣
在火葬场
聆听属于肋骨吹响的那部分声音
有时候也会停顿在
牧羊人的披毡里
没有说出一个字
从山的这头
喊过去
对面,有时候有回声
有时候没有
事故
一首诗里
只听得进一句
不管对错
金沙江边的人
有时候什么也听不进去
有什么也做不下去
只能呆呆的看着
那个踩错油门的人
被捞上岸
其实他什么错也没有
江还是那样平缓的流淌
人还是那样的匆忙
只是这里多了几个指示牌
和隐秘的传说
村庄
山口,已经很少有人
闲散而过
风吹的很大
只有破布在摇晃
只有未犁完的半亩土地
还在疯狂生产荒草
石堆的围栏在风里
其实它更想成为
车站吧
把要来的带来
把要走的人送走
把我这样的人
徘徊在站台
吹奏
走向石头
在漫无边际的地方
磨破嘴皮
其中一些
脸型和脚步已被盖好
硬鼓的敲打者
在某座土坯房里
座无虚席的听众
有几个左耳失聪
有几个手握信封
有几个用烟堵住漏出的语言
信号
开始漫无边际的探头
雪容纳了我这个污点
从南到南
从名字到名字
一路假设自己
无数可能性词语
最终卡在枝头
高压电线里
乌鸦再一次筑巢
再一次给人无数信号
或生或死
声音
破布翻动的深夜
不要和经文联系起来
手鼓敲打人心的偏激
时间只从一月走到十二月
一杯茶就是一个人一生打下的江山
群山不经意
留下了一座破土屋顶
里面不一定会住满
乌鸦
但一定会有声音
时常打断你的梦
面对
翻到第十四页
里面活着的
不一定就是自己
那个涂鸦的错别字
体无完肤,还在咄咄逼人
在某座,海拔高达4500米的山顶上
面对旧房
面对筑巢的乌鸦
也许它的每一句鸣叫
我都听不懂,也许我正为此
伤心不已
遗留
路过寺庙
其实就是路过了老家那个破旧的
土坯房
里面的诵经声
有几句,也像
小时候奶奶讲的故事
打动人心
与其说这些都是不经意遐想
不如说
这都是我刻意遗留
寺庙旁,孤独的人越来越多
寺庙旁,堆砌的石块越来越厚
寺庙旁,我偷偷看了他一眼
那个心无旁骛的信徒
一个下午
没有人,也没有风
甚至一句话也没有
跋涉
也许找不到我
山太高,你应该会恐高
也许就在昨夜
我已经抵达,你们所说的
破旧土坯房旁
生了篝火
端坐,路还是那些
只是越来越安静
只是越来越狭窄
人还是那些人
端坐各自山头
早出晚归,习惯清贫
尽管他们什么也听不到
什么也说不出
也许卷起裤腿爬上山
只是因为我
又一次想到了他们
和土墙里故事
语言
你应该和破布,打声招呼
它的撕心裂肺
也和你一样
它的独守山林
也和你一样的执拗
你应该从它们身边轻轻走过
也许你和曾经穿戴它们的人
有着深仇大恨
你也应该和他们端坐在一起
徒步
走,又停了下来
手电筒里
再也拔不出光线
一个人失去了方向
甚至失去了语言
矮松林,无数次的
吹起了口哨
也许是指迎
也许是别的
停,又走了一段
脚步声打断树与树之间的
窃窃私语者
也许是鸟鸣
也许是别的
安静
风平浪静,没有人
可以给你脸色
一个人
缓慢的从左到右
和寺庙合影
也许无数人
也这样,暗自神伤的离开
不是因为经文
不是因为,脚步
也不是因为沉默的诵经者
而是因为别的什么
突然走进了
他荒芜的世界